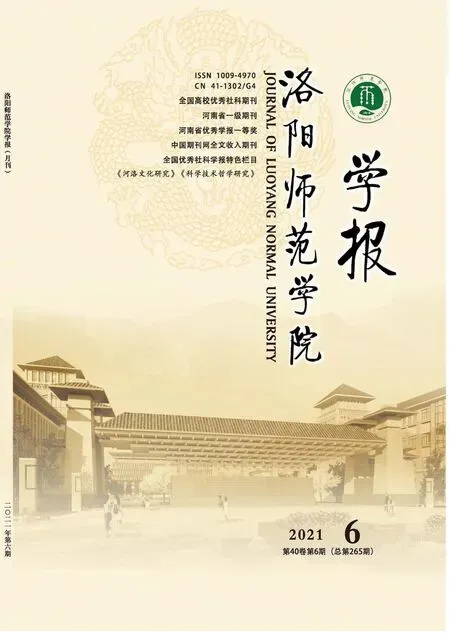论老舍对女性命运的悲剧书写
2021-12-29李文静
李文静
(徐州工程学院 人文学院,江苏 徐州 221000)
“人民艺术家”老舍一生著作颇丰,他用独具特色的平民化语言讲述了底层小人物的喜怒哀乐,也塑造了众多个性鲜明、深入人心的人物形象。老舍作为描写城市贫民生活的高手,为文学史贡献了一批“其他作家很少提供的,既有典型意义,又有个性特征的城市贫民形象”[1]。在老舍的诸多小说中,男性往往是叙事主人公,其着力塑造的,是那些生活在城市底层,受尽人生苦难的男性形象,骆驼祥子是其中的代表。而与男性形象相呼应的,便是老舍笔下着墨不多,但依然让人过目难忘的各类女性形象。这些女性如同开在枝头的花朵,虽没有主干那么庞大,却也有着不可小觑的地位。
一、老舍小说中的悲剧化女性形象
老舍笔下的悲剧化女性形象大致可以归为以下四种:一是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贫苦女子。如《月牙儿》中的“我”,《骆驼祥子》中的小福子和《赵子曰》中的谭玉娥。这类女性住在简陋的胡同里,基本上都没受过学校教育,尚未成年就被迫承担起谋生的重任,或是幼年丧母,或是不幸失去父亲。如《月牙儿》中的“我”在四岁的时候目睹了父亲在破旧小屋中的死亡。小福子在很小的时候也失去了母亲,跟着父亲和几个弟弟过日子。这种身世设定体现了老舍小说独特的“戏剧化”色彩,也为女性人物的悲剧命运作了环境上的铺垫。二是在“五四”精神影响下追求自由独立的一群新女性。如《阳光》中的“我”,《四世同堂》中的胖菊子和《赵子曰》中的秀莲。她们在学堂里上过学,经过五四新文化的“洗礼”,做起了摩登女郎。她们把头发烫得像鸡窝,踩着高跟鞋招摇过市,她们要过充满浪漫色彩的、突出女性地位的新生活,最重要的是要寻求恋爱的自由。三是一批贤妻良母型的女性。如《四世同堂》中的韵梅和钱太太、《离婚》中的张大嫂、《正红旗下》中的大姐。她们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公婆、丈夫和孩子,不善言谈也不爱交际,她们的生活中除了柴米油盐,就是洗衣做饭。四是一群霸道的悍妇形象。如《四世同堂》中的大赤包、《牛天赐传》中的牛太太和《骆驼祥子》中的虎妞。这类女性往往有经济独立的能力,不仅可以帮助父母或辅助丈夫,甚至比他们更有商业头脑。这种优势决定了她们在家庭中有着不可或缺的地位,也导致了其强势、凶悍的性格特征。
二、悲剧化女性形象的类别
通过对老舍小说中女性形象的分类可以发现,老舍对于不同女性形象是有所偏爱和厌恶的。在小说中,他常常通过女性们的言行举止来传达出这种好恶,而她们的命运走向,也因这种好恶而各归其位。但是无论哪一类女性形象,她们的命运都具有悲剧化的色彩,最终的结局也大都让人唏嘘。人物的命运结局在老舍那里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是老舍表现情感倾向的重要方面,也是他塑造人物最紧要的一笔。不同的女性在老舍笔下有着各异的命运和结局,这种书写不是一时的突发奇想,既是小说情节发展的必然,也是作者个人生活与爱憎态度的投射。
(一)屈从现实的贤妻良母
在老舍笔下,有一类女性是被他投以深切的人文关怀的,那就是他作品中塑造的贤妻良母形象。老舍之所以热衷于塑造这类只为别人而活、甘愿牺牲自我的妇女形象,与其从小的个人生活经历密切相关。老舍出生在北京小羊圈胡同一个底层家庭,父亲是一个月薪仅3两饷银的护军。他出生时,父亲正在皇城当值,母亲因为失血过多昏迷不醒,幸亏大姐及时赶到,老舍才不至于冻死。老舍出生后不久,他的父亲就死于八国联军侵华的战火,兄妹五人和婆婆、姑母的吃穿用度全落到了还未从丧夫之痛中走出来的母亲身上。“北城尽穷人,她能做些什么来谋生呢!只有终日洗洗刷刷、缝缝补补!日子极其困苦,她不到五十岁,就已老眼昏花。”[2]母亲的含辛茹苦、忍辱负重和宽以待人都被年幼的老舍记在心里。老舍曾在《我的母亲》中说:“母亲生在农家,所以勤俭诚实,身体也好。这一点事实却极为重要,因为假如我没有这样一位母亲,我恐怕也要大大的打个折扣了。”[3]5另外,老舍的三姐,为了帮母亲分担养家的重担,成了老姑娘才出嫁,这对老舍的心灵也造成了极大的冲击。在塑造不同的女性人物、安排其命运走向时,读者经常能看到老舍的母亲和三姐的影子。《四世同堂》中的“小顺妈”,连个名字都没有,她劳碌一生,仅有的持家法则就是“尽责”,“她只能用尽责去保障她的身份与地位,她须叫公婆承认她是个能干的媳妇,叫亲友承认她是很像样的祁家少奶奶,也叫丈夫不得不承认她是个贤内助”[4]280。她从不多嘴说一句话,而是看着全家人的脸色行事,当她看到大家都快活时,她的反应就是更卖力地工作。《离婚》中的张大嫂,一切都看张大哥的眼色行事,为了一双儿女整天操心不已。她也曾有过抱怨,但最后还是会说:“谁叫咱们是女人呢,女人天生的倒霉就结了!好处全是男人的,坏处全是咱们当老娘们的,认命!”当邻居二妹妹夸奖她:“像您这样的人真算少有,说洗就洗,说作就作,买东道西,什么全成。”[5]她的怨气也就随之烟消云散了。
通过分析小说中的人物可以发现,老舍把对母亲和三姐的敬重与怀恋融进了小说人物的塑造中,这类女性往往是隐忍而坚强的,她们勤俭、内敛、为人真诚,有时会被公婆或丈夫欺负,但是她们会通过自己的坚持和善良化解矛盾,成为一个家庭不可或缺的存在。老舍往往会给她们安排一个较为完满的结局,不会让她们经受什么厄运。但是研究这些“贤妻良母”的心理动态时可以发现,她们的人生实则充满了无奈。她们过上所谓“幸福”生活的前提是要严格地恪守三从四德,她们的快乐是以取悦周围人,尤其是丈夫和公婆为代价的。在这类人物的身上,老舍时常会通过主人公们的内心独白来揭示其强颜欢笑背后的辛酸与无奈。
(二)沦落风尘的贫苦少女
老舍对女性的细腻刻画充分体现了其平日里严谨与细致的观察。或许是因为相似的困顿生活,他对下层的不幸女子在客观叙述中往往透出更多的同情与无奈。《月牙儿》是以女性为叙事主体的小说,故事中的“我”用散文诗般伤感唯美的语言向读者娓娓讲述了黑暗的旧社会是如何逼良为娼的。“我”从小生活在一个穷苦的家庭里,父亲的死让本来就捉襟见肘的生活雪上加霜,“我”的母亲,一个柔弱的妇人,为了生计给别人洗臭袜子和脏衣服,但仍养活不了母女二人。万般无奈之下,母亲开始做暗娼,并把“我”送进了学校读书。她找到了一个看似可靠的男人后,又带着“我”改嫁,但浮萍般的日子没过多久便宣告结束。《月牙儿》的整个叙事基调是压抑、沉重的,这和母女二人的悲剧命运相互映照。小说中的母亲从一个良家妇女沦落为暗娼,其彷徨、挣扎的过程老舍并未过多地呈现。但她的女儿,一个接受过几年学校教育的少女,经过五四新思想的洗礼,知道了自食其力的重要性,所以她一直在反抗命运,试图冲破母亲的“老路”,她努力地想要通过自己的劳动在社会上立足,但还是一步步失败。虽然不想重复母亲的路,但是到最后却发现这是唯一能活着的路,不愿意走,就只能等死。
贯穿全篇的“月牙儿”这一意象在一开始就暗示了“我”的命运。“它无倚无靠地在灰蓝的天上挂着,光儿微弱,不大一会便被黑暗包住。”[3]8在小说中,老舍向我们展示了那个时代的女性悲剧,生活在一个男权社会里,女人只能是个附属品,愿意隐忍、妥协、放弃尊严才能谋个安稳。想要自由,那就是自讨苦吃、死路一条。一次次的反抗换来的永远是欺骗与嘲笑,“我”终于妥协了,这“叫我咬牙切齿,叫我心中冒火,可是妇女的命运不在自己手里”。命运的无情打击让“我”没能逃出魔咒,“我”像母亲一样沦为了暗娼,“我”把一年当成十年来过,在麻木中看着青春飞一般地流逝。《骆驼祥子》中的小福子也有着相似的命运,她年轻、善良、肯吃苦,却有个好吃懒做、暴力虚荣的父亲,她的母亲被父亲酒后家暴致死,留下两个未成年的弟弟和穷困破败的家。祥子把她当成理想的对象,却又不敢挑起负责她全家温饱的担子。经过了短暂的彷徨与挣扎,小福子最终沦为暗娼,她成为左邻右舍嘲讽的对象,也打破了她对爱情最后的向往。绝望过后,她逃出了那个剥夺了自己尊严与生机的白房子,在一棵树上吊死了。
(三)迷失自我的“摩登新人”
和“月牙儿”相对立的,是有着优越的物质条件却逐渐迷失了自我、自甘沉沦的“摩登新人”形象。在对“摩登新人”这类女性形象的塑造中,老舍给她们安排了另外一种截然不同的命运。对这类人物,老舍表现出了某种不友好,甚至是厌恶的情绪。在追求自由、解放、平等的外衣下,她们的言行中处处透露出懒散、虚荣、自私和不成熟。小说《阳光》中的主人公是其中的一个典型代表,她出生在有钱人家,在父母兄弟的溺爱中长大,虽然在学校读书,却并不把知识当成改变命运的武器。她上中学、大学只是因为校园里自由,她可以随心所欲地去做在家里不能做的事。“我们三个一群,两个一伙,挤着搂着,充分自由的讲究那些我们并不十分明白而愿意明白的事。”[6]她们所学到的不是怎样去争取人格独立和自由,而是怎样穿衣打扮。对她们来说,家庭的力量仍旧起到决定作用,因为她们大多没法经济独立,也没有勇气去过那种自食其力的生活,在面对家庭束缚与个人独立的矛盾时,她们还是会乖乖回到家庭,等待父母兄长来安排以后的命运。对于这类盲目追随新思想的举动,老舍是持保留甚至是怀疑态度的,当时众多女子自由恋爱后被抛弃、沦入风尘等事件的发生让他看到了这些行为的危险。因此老舍给这类人物安排的结局也大多不好,她们或是被许配给道貌岸然的有钱人,或是被恋人抛弃后灰头土脸地回归家庭,或是沦落风尘。
(四)失掉本性的凶蛮悍妇
凶蛮悍妇是老舍笔下极力夸张和嘲讽的一种人物类别,这类女性往往虚荣、自大、蛮横无理。老舍为了表达对这类人物的反感,在外形上对她们进行了丑化,悍妇们往往相貌丑陋,身材臃肿,污言秽语也是信手拈来,使人一看就会产生厌恶之感。比如在形容《四世同堂》中的冠太太时,老舍写道:“已经快五十了还专爱穿大红衣服,所以外号叫大赤包。脸上有不少皱纹,而且鼻子上有许多雀斑,尽管她还擦粉抹红,也盖不了脸上的褶子与黑点。”[4]420这些明显带有感情倾向的描述让读者无形中把此人当成了小丑一样的人物,而后面其卖国求荣、想尽一切办法当汉奸的无耻行径则进一步凸显了她的丑陋形象。尤其是当她谋得了妓女改造机构的官职时,她的气派之大已使女儿不敢叫妈,丈夫不敢叫太太,而都须叫所长。在给瑞丰的太太改名时,她不假思索地说:“菊子好!像日本名字!凡是带日本味儿的都要时兴起来!”[4]424这种凶蛮暴力的作风极大地淡化了其女性的柔和特质,使其变得不伦不类,也达到了强烈讽刺的效果。在描写《骆驼祥子》中的虎妞时,老舍也有着相似的批判态度,“她长得虎头虎脑,外表丑陋,她像一个大黑塔,不讲仁义,粗俗凶悍”。而祥子之所以不喜欢虎妞,是因为在他眼里她是“既旧又新的一个什么奇怪的东西,是姑娘,也是娘们,像女的,又像男的,像人,又像什么凶恶的走兽!”祥子眼里的虎妞除了霸道与恐怖,全无半点可爱之处。老舍在这类悍妇的言行举止的描绘中表达了他的反感与否定,她们的结局或众叛亲离,或凄惨而死。
值得思考的是,老舍笔下无论哪一类女性形象,都无一例外地处于从属地位,若有人想改变这种处境,其结局大多是惨败。相对好的结果不过是向男权社会的封建家长妥协,丧失尊严地维持着卑微的地位。和同时期的作家相比,老舍的小说特别吝啬展示女性的成长,他笔下的女性大都处于一种被社会、家庭压制的状态。这些女性无论试图以何种方式寻求独立或是进行反抗,最终都以悲剧收场。如《月牙儿》中的“我”始终被贫穷包围,无法翻身;《阳光》中的“我”靠父兄维持虚荣生活,难以突破;小福子要担起养活年幼弟弟的重担,无路可走;霸道的虎妞虽然精明能干,但一直被当成赚钱的工具……这种压抑的状态和无力反抗的绝望最终导致了女性们的悲剧命运。
三、女性悲剧命运的创作来源
(一)个人的生活经历
从作品中可以看出,老舍对贤妻良母和悲情少女是维护的,凶蛮悍妇和虚荣“新人”则是他重点批判的对象。对不同女性命运的悲剧书写首先来源于老舍个人的生活经验。老舍早年的生活清苦而坎坷,他生活在狭窄而热闹的小羊圈胡同里,每天上演的是车夫、巡警、裱糊匠和暗门子、洗衣妇们的悲喜剧。少年时的落魄经历为老舍后来的创作提供了源流。他耳闻目睹了小人物们的喜怒哀乐,其小说人物惹人唏嘘的悲剧正是源于老舍的生活经历。老舍本是个以幽默喜剧出道的作家,但纵览其后来的创作,悲剧反而成为一种中心式的存在。其绝大部分小说都隐现着绝望、愤怒、悲戚。有人曾说,老舍作品中最感人的瞬间就是那些小人物遭遇劫难的时刻,老舍之所以能用这些悲凉的瞬间打动读者,正因为这些惨剧曾在他的身边真实地上演过。老舍幼年丧父,靠着母亲含辛茹苦地做粗活把自己养大,让老舍深受“贫穷”折磨的同时,有了对“孤独”和“虚无”最直接的体验,这些经历成为老舍小说悲剧意识的重要来源。
(二)新旧文化的碰撞
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大团圆”结局向来是备受青睐的叙事模式,这种结局体现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心理期待,但却并不能反映社会中真实的一面。鲁迅将其叫作“瞒和骗”的文学,胡适称之为“说谎的文学”。鲁迅还把文学的这种封闭、凝固、粗糙的“团圆”模式上升到国民的“劣根性”,在《论睁了眼看》一文中明确地表示:“因为凡事总要‘团圆’,正无须我们焦躁﹔放心喝茶,睡觉大吉。”于是“无问题﹐无缺陷,无不平﹐也就无解决,无改革,无反抗”。[7]老舍也不屑于用文字去制造不切实际的团圆泡沫,而致力于用悲剧去描摹真实的生活,用女性的彷徨无奈来表现集体无意识与国民的劣根性。在这里,引入“现代性”这一概念有助于进一步分析作家的创作心理。“现代性”是随着现代化的发展而出现的一个术语,它包含进化论、新胜于旧等价值判断,指的是与社会现代化相匹配的精神气质或心理状态。中国的现代性发生于新旧社会转型之际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它既推动了文学思潮的发生与发展,也影响着作家的创作。鲁迅、老舍们作为有留学背景的知识分子,现代性对他们的影响或多或少地投射到了文学作品之中。
(三)康拉德悲剧小说的影响
老舍在分享其小说创作经验时,曾毫不吝言地表达对英国作家康拉德的喜爱与赞赏,同时也透露出自己的小说创作从结构到情节安排都大量借鉴了前者。康拉德的作品不但以印象主义著称,更以其悲剧性的特质震撼着人们的心灵。在文学创作中,社会环境和次要人物是非常重要的两个方面,主人公往往是因为大环境的压迫和恶势力的欺凌才展开反抗和斗争,从而促进情节的进一步发展。老舍在进行女性命运书写时,会有意识地将其安排在某种特定的、戏剧化的环境之下。例如《月牙儿》《微神》《阳光》等都是在大量的戏剧场景中塑造人物并展开情节的,“这种戏剧性使老舍的小说创作更加生动形象、故事精彩、可读性强”[8],也让读者更深切地感受到这些女性悲剧命运的社会来源。老舍对悲剧环境的特别安排明显受到了康拉德的影响。在康拉德的创作中,环境对人物的压制作用几乎是难以规避的,他通过人物的毁灭过程传达给读者的是“有一个宽阔有力的,看不见的手随时准备落在我们地球的蚁蛭上,抓住我们任何一个人的肩膀,把我们的脑袋砰的一声互相撞到一处,然后把我们朝许多预见不了的方向抛去,于是我们通通不可思议地向四面八方飞逃”[9]。这种近乎悲观的“宿命论”式的书写,和老舍说过的人物和环境的关系正如“蝇逃不出蛛网”的论述惊人地一致,他在创作过程中显然借鉴了康拉德这一手法。并且老舍在进行女性命运书写时,大多数时候并不刻意渲染外部势力对个人的损耗,而是营造出“命运不可逆转”的消极氛围。正如康拉德在小说中“一方面强调内化于人性中的道德原则如何执行自我审判的职能,另一方面却又强调在面对现实时人性的软弱性和不可知性”[10]。老舍对女性悲剧命运的书写,既指出了环境对人性的荼毒,也强调了思想独立的关键性。同时也批判了女性在不可知的困境里所暴露出的软弱与无力。在此过程中,老舍流露出“人生没有出路,抵抗只是徒劳”的生命悲感和对个人存在意义的无奈追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