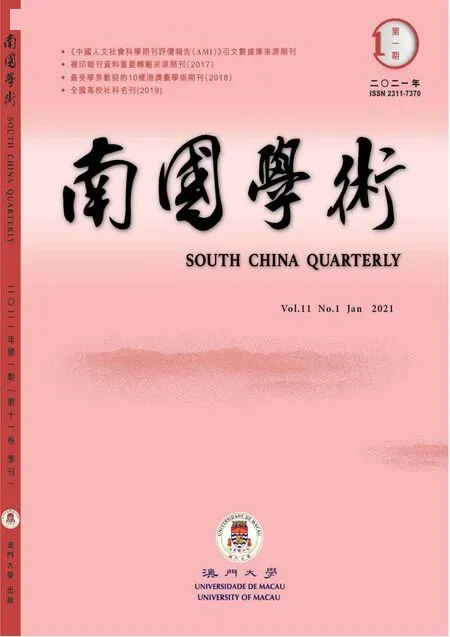現象學觀念是如何源的?
——德里達與胡塞爾的分歧
2021-12-28尚傑
尚傑
[關鍵詞] 觀念 現象學 解構 時間 起源
德國哲學家胡塞爾(E.Husserl,1859—1938)的現象學的秘密,在於他重新思考觀念的起源;“起源”是基礎,它支撐起整個現象學思想大廈。但是,在法國哲學家德里達(J.Derrida,1930—2004)看來,這一現象學觀念的基礎並不牢固,因爲胡塞爾並沒有說清它的起源,衹是將起源的時間路徑視爲通暢的、現成的,而沒有看到觀念的時間起源路徑中的種種障礙,會導致現象學觀念自行消解,在效果上就是解構。正是在“起源”看法上的不同,把德里達與德國現象學傳統區別開來,德里達的哲學也正是從批評現象學起步的。本文擬從德里達早期的兩部著作入手,討論他在起源問題上與胡塞爾現象學的分歧。
一 現象學衝動來自瞬間某種神秘的渴望
胡塞爾在晚年寫了一篇非常重要的文章《幾何學的起源》,它是理解胡塞爾現象學秘密的一把鑰匙,現象學所涉及的主要問題幾乎都在裏面了。廣義上的幾何學觀念,是胡塞爾說的哲學“觀念”的一個雛形。如果再考慮到胡塞爾的數學出身以及他被弗雷格(F.L.G.Frege,1848—1925)的意義理論驚醒從而放棄了“算術哲學”中隱含的心理主義立場,我們就要避免一種根本性的偏差——認爲胡塞爾的思想在倒向東方的哲學而不是在批判性地繼承柏拉圖(Πλατών,前427—前347)的思想。爲什麽呢?因爲胡塞爾的觀念就是“理念”。說這個理念是哲學意義上的,根據在於它是科學意義上的;而爲了找到哲學與科學觀念的雛形,胡塞爾首先想到的是幾何學。他所感興趣的,一言以蔽之,就是從感性的質料出發,如何朝向幾何學的觀念?觀念與感性質料之間到底是怎樣的關係?觀念是起源於感性質料嗎?
感性質料,或者說,人們的生活世界,是活生生的、原始的,它在科學沒有產生之前就已經存在了。生活世界在什麽意義上是又不是科學世界的來源?生活世界還包含了人們的日常語言或自然語言,但並不自動包括人工或人爲建立起來的所謂“科學語言”,如幾何學語言、電腦語言等。科學語言,就像《聖經》裏說的,是一座語言的巴別塔,它可以實現人類一種普遍語言的夢想,實現人類之間無障礙地交流思想。用胡塞爾的話說,它使人與人之間建立起一種“主體間性”。在這種普遍的語言面前,人人即我,我即人人。
德里達爲胡塞爾的《幾何學起源》寫了一篇著名的“導論”,胡塞爾的原文衹有43頁,而德里達的“導論”寫了171頁。這個不對稱的篇幅對比意味深長,而且德里達把自己很多原創性的思想放在衆多的註腳裏。這裏有解構式閱讀的原初秘密。這種秘密就在於,在閱讀時,首先要懷着尊敬與虔誠的心情努力去接近原著的意圖,不要在閱讀之前懷有任何偏見或蓄意不讚成。一種完美的理解就是,從原著內部出發,發現其中的細微模糊之處、發現其中隱蔽的可能性,然後加以創造性的澄清,使原著以新的面貌出現在世人面前;①康德從理性內部對理性重新思考,提出理性在何種意義上是可能的或者不可能的。在這裏,重要的不在於康德的結論是正確的,而在於他所使用“從內部瓦解”的批判方法。海德格爾和德里達的解構,與康德的“解構”不期而遇。而這種思想面貌,是出乎原作者意料之外的。
什麽是胡塞爾的理念或夢呢?在德里達看來,就是對日常經驗現象的“還原”,也叫做“擱置”“加括弧”——這些玄而又玄的哲學術語,其實質內容是簡化經驗內容。經過這樣的簡化,經驗變得清楚明白了、透明了、本質化了,同時也貧困化了。這是理性、觀念論或理念論的效果,是邏輯與科學的效果,但不是幽靈或者靈魂的效果。在這個過程中,清晰性掩蓋了秘密性,具有前提性的觀念假設代替了模棱兩可的神秘性。正是這樣的解讀,暴露出哲學研究兩種根本不同的可能性,胡塞爾現象學代表了西方古典哲學的最後痕迹,而德里達對胡塞爾的批評或解構式閱讀,預示着“後現代思想”的未來走向。
以上有一個關鍵詞,叫“推遲”,或者說推遲夢的實現。這個推遲,就是德里達後來大名鼎鼎的“延異”(différance)一詞的原初表達方式,是產生差異的學理依據。在胡塞爾非常莊嚴地叫做“意向性”之處,德里達稱之爲抽象的意志有一種現象學衝動,它始終朝向胡塞爾的理念世界。這種抽象的理性衝動可以反復進行,但每次衝動之間的區別衹是數量上的,而不是質量上的。這就像三角形代表古今中外的一切三角形,它衹與空間有關,與時間的流逝無關。意向活動的“再一次”永遠指向原初的出發點,這就是從外感官的自然經驗的態度中還原出來的“抽象目光”或者叫“本質的還原”,它所瞄準的其實並非一個對象模式上的意義,而是一個抽象的X 。
數學—幾何學的研究對象是純粹觀念性的,它脫離或不依賴任何具體個人的經驗主體、任何具體時間場所,它不是此時此刻纔顯現,而是事先“已經”存在於一個純粹觀念的世界之中了。接下來,還會反復提到這個“已經”。它在價值上,等於“永恆”。另一個需要澄清的的概念,在胡塞爾那裏,“歷史性”(l’historicité)問題不等於“歷史”(l’historire)問題,“歷史性”屬於理念本身的領域,而“歷史”屬於經驗的或生活世界。當人們對歷史實施一種嚴格的現象學還原時,“歷史性”本身就顯露出來。現象學還原就像是一個純粹哲學態度的篩子,把一切非哲學的因素或者所謂“自然的態度”,無論這些因素或者“態度”是歷史上的還是現實的,都篩除乾淨。剩下的,就是純粹理性的沉積物,胡塞爾將它叫做“現象學剩餘”。這個剩餘或這個痕迹,在自然態度下是無論如何發現不了的,普通人或者說非哲學的民族意識中沒有這個夢。這種情形,同樣適用於現象學態度中的“自我”概念。這是哲學的“我”,具有普遍性或“主體間性”,與自然態度下的任何個人沒有關係。在這裏,身份問題非常重要。當胡塞爾這樣的哲學家說“我”時,其所指是超越他個人的。這是一個高貴的“我”,即精神的高貴,也就是理性。這種高貴的理性,或者說現象學態度即哲學態度,保證了“歷史性”能完美地送還回來。
爲了準確理解胡塞爾,首先必須做的,就是澄清他所使用的一系列概念。這個工作的嚴肅性有點像笛卡爾(R.Descartes,1596—1650),也叫做“掃清思想障礙”。例如,胡塞爾說,爲了實施純粹哲學思考,要使普通人的日常心理活動失效,他用的術語叫“中立化”(neutralisation),其實就是對日常現象的“還原”。換上“幾何學起源”的情形,胡塞爾的意思是說,幾何學觀念在經驗層面上是何時“第一次”發生的,是如何發生的,純粹哲學的態度不關心這樣的問題,把這樣的問題擱置起來。這種擱置,就是哲學與非哲學之間、或者說科學與非科學之間的界限,這是一種中斷,或者叫“超越”。但是,這種中斷或者超越一定有“第一次”,這個“第一次”絕對不是經驗層面上的,胡塞爾思想的糾結和德里達的敏感,就在於如何看待這個“第一次”。
總起來看,所謂擱置、使之失去作用、中斷、哲學態度或意向性的改變,這些詞語,都是現象學還原的不同說法。有人簡單地把這些叫做“現象學方法”,但我認爲這絕不僅是方法問題,而是事物本身的問題,是事物本身如何出場的問題。在這些詞語裏,最有深意的是“中斷”。中斷一定有第一次,這意味着它是瞬間發生的。瞬間在這裏遭遇到“第一次”,瞬間與“第一次”在這裏是一種重合關係。“中斷”敞開了一個新的空間——幾何學的空間。自然世界裏原本衹有類似三角形狀的物體,但沒有幾何公理定義下的三角形觀念。在這個意義上說,幾何學觀念對自然世界的“中斷”體現了精神的高貴或精神的科學抽象能力。
但是,不要誤以爲,在胡塞爾那裏,哲學的態度等同於幾何學的態度。不是的,在他那裏,哲學的態度與幾何學態度之間有着十分微小卻又是本質的區別:哲學家關注“幾何學觀念的起源”問題,而幾何學家是從現成的“幾何學觀念”出發的。胡塞爾說,不能埋葬起源問題,不能埋葬時間問題。胡塞爾的困難在於,既要說到起源,但又不是在經驗的意義上討論起源,而德里達也是這個意思,兩個人的態度都是哲學的,但涉及哲學研究的兩種不同方向。
上面談到的“第一次”不是指經驗層面,而是在邏輯意義上說的。人們並不在乎誰是第一個幾何學家,或者誰在某年某月某日某時靈光閃現,想到了某個幾何學公理;人們所重視的,衹是邏輯上一定有“第一次”或者叫“發生”。這也就超越了在鐘錶意義上討論世俗的時間概念,而是討論時間的哲學意義。同樣,在邏輯上一定有某個人某時刻有了關於幾何學的正確觀念,於是在文明史上人類思維能力有了驚人的一跳。這個人嘗試着從這樣的幾何觀念出發,開啓了一個嶄新的思想方向。後人的工作,就是一次又一次地重複“第一次”。用我的話說,這驚人一跳的瞬間思想,從此定格爲永恆(所謂“放之四海而皆準”,用法文亦可表示爲“l’omnitemporalit锓l’universalté”),而胡塞爾所謂“還原”或“中斷”,在顯露出“事物本身”或“本質”的意義上說,在效果上等於同時擱置了赫拉克利特(ράκλειτος,前540—前480)的時間之河或柏格森(H.Bergson,1859—1941)式的綿延。時間不再重要,“歷史性”從歷史中解放出來。觀念的“第一次”是精神的一種創造性活動,它所意向的對象是非常抽象的,它從前並不存在。經驗的目光永遠創造不出幾何學的觀念,就像我們無論怎樣觀察兩個蘋果,要從中抽象出數字2,目光必須發生性質的改變,也就是對兩個蘋果的具體形狀視而不見。這個過程同時又是兩種痕迹:一個是兩個蘋果的痕迹,一個是數字2的痕迹。這兩種痕迹的性質完全不同。這裏出現了悖謬或不對稱的情形:也許兩個蘋果能激發創造數字2的靈感,但數字2與兩個蘋果之間一點兒關係都沒有,它們之間的相遇是極其偶然的。即使它們不相遇,一點兒也不會影響到數字2自身的性質與意義,康德(I.Kant,1724—1804)把這種情形叫做“先驗性”——這個過程有目光的解放、先驗的冒險。
先驗目光下的“經驗”不再是經驗,而衹是“經驗”一詞的類比,就像幾何學圖形的形狀並不真的存在於現實世界之中。胡塞爾的類似說法是,無論人們是在夢中還是醒着,2+3永遠等於5,正方形永遠有4個角。關於這些幾何學和數學的公理,19世紀法國大數學家彭加勒(J.H.Poincaré,1854—1912)也認爲,它們來自虛構或約定的假說。胡塞爾說它們來自自由想象過程中的本質直觀,它最終獲得一個不變的本質性結論。它們脫離了實際經驗,因而是“不真實的”,但它們是被打上了引號的“不真實”,這裏我們看到了柏拉圖理念論的痕迹。在這裏,所謂“起源”,就是原創性。這裏的“第一次創造”,出現了“精神擰巴”的情形。所謂“擰巴”,就是說這種精神創造性活動同時既是經驗的、個別的,又是先驗的、本質的、普遍的;既是事實,又是虛構;既是事實,又是意義。用德里達在《導論》中的說法,就是“一次就代表了全部幾何學‘現象’,這時,幾何學的可能性被構造出來……”①Jacques Derrida,“Tranduction et introduction par”,L’origine de la géométrie(Paris: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1962),35.德里達這裏說到“遠距離交流”的可能性,有點類似於尼采(F.W.Nietzsche,1844—1900)說的“永遠回來”——返回,歐幾里得的幾何學公理在兩千多年前與現在一模一樣。換句話說,幾何學原本不是歷史學,但現在討論幾何學的起源,把歷史因素摻雜進來,這個思路可能預示着思想的突破,因爲它在原本清晰的內容之中加入了混沌。幾何學不再是純粹的了,而成爲“幾何學哲學”。
解構的態度,首先對一切總體性判斷保持警惕(無論其句子成分中是否包含係詞“being”),例如“歷史事實”。哲學家往往能敏銳察覺出判斷句得以成立的前提,因爲說出“歷史事實”這句話的人,暗含着他已經知道了什麽是“歷史”,即他對“歷史”這一概念已經有了事先的理解;就像笛卡爾做出“我思故我在”的判斷時,暗含他已經知道了什麽是“我”“思”“在”,其各自的含義是不變的,否則這個著名哲學命題得以成立的基礎就要坍塌。以上對“歷史”含義的事先理解,也可以被用到“語言”和“傳統”,但事實上,歷史、語言、傳統都可以是別的樣子。
德里達的“延異”(différance),還有“在形象中思想、在情景中思想”的意思。這些形象與情景具有感性的抽象性——這是一種自相矛盾的說法,我異想天開地把它與胡塞爾關於“自由想象”的說法對應起來。一方面,德里達的“延異”不是一個真正的文字,它不過“好像”是文字,是一個自由想象的結果;另一方面,“延異”又是創造出來的,它存在於真實而抽象的感性世界之中。感性一旦進入想象之中,感性一旦被想象化,就不再是經驗的而是“超驗”的,不再是外感覺的而是內感受的,不再是視覺的而是心靈的;或者說,是活躍在心靈裏的“視覺能力”。“延異”是心靈視覺的特殊效果。所謂心靈視覺,不過是“想象”或“意象”的另一種說法而已,但我這個“心”的說法強調“思”是心的。所謂心,也就是把感受賦予思想,反之亦然,使感受具有思想。感受因具體生動而爲近,思想因抽象而爲遠,但我卻認爲,在這裏,距離最近的與最遠的以悖謬的方式扭結在一起,形成心靈視覺的厚度,它不是透明的而是混沌的。與此同時,思想永遠保持着超越心靈狀態、超越感情狀態。這是思想的衝動,而不是世俗世界中的慾望。
幾何學是一個發明,就來自類似的思想衝動。這個衝動的性質,不僅是幾何學的,而且是哲學的。胡塞爾說是“柏拉圖式的幾何學”①Jacques Derrida,“Tranduction et introduction par”,L’origine de la géométrie,137.。這裏的抽象情形,甚至使我想到應當糾正一種長期以來的錯誤理解:即所謂“唯心論”其實不過是“觀念論”。“idealism”不是“唯心論”,而是觀念論。無論觀念在“外”(例如,柏拉圖的“理念”或“客觀的觀念論”)還是“內”(例如,貝克萊的主觀觀念論),觀念總是超越心靈的(要看到,心靈與思想的邊界綫是混沌的;與此同時,也要具備將兩者加以區分的能力,這是思想的衝動,這是哲學的能力)。作爲最典型的“理論的態度”,觀念論是滋生單義論的溫床。觀念使哲學家擺脫了情緒,使哲學家在說“我”的時候不再單指他自己。從此,無盡的觀念向哲學家敞開,以往哲學家的使命就是清晰地分析這些觀念。
幾何學公理和命題,數學中的負數、無理數等,“最純粹的”哲學概念,愛因斯坦的相對論,等等,這裏我試圖列舉一切不是來自外部經驗的、純粹自由想象的精神產品。無論這些精神產品是觀念性的或“本質的”,還是感受性的藝術的,它們一概是我們不可能經驗、不能經歷、不能實現,現實生活中不可能有的。總之,是超越的、超驗的。所謂超越或超驗的另一層含義,就是描述無中生有,或者既無經驗根據甚至有時也無可理解性的根據,單憑某種野性而抽象的直覺洞察力創造出某種情形——這確實不可思議,但這種創造力及其成就的存在卻是一個事實。這裏包括了對幾何學起源的描述。這裏的“起源”,是抽象的時刻、抽象的瞬間,也就是“有厚度的瞬間”。這個抽象瞬間是世俗時間的“殘留物”,它創造出超越經驗與歷史的精神產品。但這個精神產品不是現成的,它是瞬間的精神遭遇。不能說在這個遭遇之前,精神產品在冥冥世界中就已經存在了。由於忽略了創造的過程或抽象瞬間的作用,柏拉圖主義是站不住腳的。
瞬間與瞬間之間本來是平等的關係,但上述“抽象的瞬間”一躍而成爲關鍵時刻,這也是做出判斷或選擇的時刻。問題是,爲什麽絕大多數判斷或選擇都是平庸的?因爲,它們衹是現成的判斷與選擇,它們衹是重複着曾經的存在,它們衹不過相當於解釋,或者爲了符合某個暗中的標準而做的註解。天才式的或真正的判斷或選擇,是沒有充分理由的;或者說,它是一種試錯,尚沒有獲得充分理解,但它與擲骰子那樣的運氣有微妙而本質的區別——它的發生,同時是臨時的與本質的,取決於一種瞬間洞察本質的能力。這是一種偶然性之中的本質性選擇——一錘定音,這是創造性的瞬間而非重複性的瞬間。
爲什麽觀念論站不住腳?因爲它把觀念看成一個自身封閉的整體,邏輯的術語也叫它“集合”。不可能徹底實現這個整體或者集合,我們衹能設想它的存在、在推理或計算中無限接近它的存在,但無法落實它的全部存在。在這個意義上,一切被命名的觀念都不實際。可以把觀念描述爲異域裏的X,觀念是本質性的無限大或無限小,但無法被觸到。觀念是清晰的,因爲它是本質的、確定的;觀念又是混沌的、神秘的,因爲它是不確定的、是X;觀念還是形式的,因爲其內容無法在直觀(胡塞爾用“純粹意向”取代了康德的“直觀”)中實現。觀念是理想,是意向性所朝向的神;觀念不是意向的對象,而是X意味上的意向意義(這個“意義”衹是“觀念”的延伸說法)。觀念高於證明,因爲它是沒有被充分“證明”但是爲真的判斷(例如無理數)。這又是“現象學”的“現象”一詞最容易迷惑人的地方,因爲“現象學的觀念”從來就不顯現出來,缺乏直觀的本質意向從來不顯形。
有時候,胡塞爾也用“本質直觀”取代“本質意向”。這裏的“直觀”一詞又是迷惑人的、“說不通的”,胡塞爾說它就像“木製的鐵”。理性對歷史的“超越”其實是不能超越的,而不能超越的卻一定要強行超越,思想的全部糾纏和哲學家的血性都在這裏了。這個“木製的鐵”,改造了康德所謂“純粹直觀的形式”,它有看不見的“陽光”。對這“看不見的陽光”,德里達卻另有解釋:“胡塞爾懷着‘回到事物本身’的動機批判心理主義,‘回到事物本身’是作爲‘真正的實證論’出現的,胡塞爾促使我們朝向心靈的幽靈能力、瞄準古典實體論的全部痕迹。”①Jacques Derrida,“Tranduction et introduction par”,L’origine de la géométrie,160.衹有幽靈般的能力,纔確保我們能“回到事物本身”,而這竟然被說成是區別於心理主義的“真正的實證論”和“古典實體論的全部痕迹”——在這裏,德里達釋放出令人眼花繚亂的新的精神連綫,也就是後來被他稱作“解構”的策略——他將一些概念重新配對,暗中轉移了這些概念原有的含義。這當然沒有經過胡塞爾的同意,德里達仿佛是在說:哲學與文學的界限趨於消失,幽靈般的感受本身就是“實證”的,就是在“回到事物本身”。
以上是以“超越”一詞的歧義性作爲例子,“歧義”之間的批判關係推遲了單義性的實現。推遲或者延緩,這是從內向外發出的思想信號。思想在綿延過程中總在連接新的意思,在自由想象過程中進行着試錯的過程,蜿蜒曲折。每個折點或精神的拐點都是“出發點”,但不是一元論意義上的起源。絕對的起源總是別的什麽,總是在異域。這些,就是活生生的當下狀態。
二 觀念源的原初複雜性
原初的構成問題,即事物本來是如何出場的?德里達批評並且放棄了現象學的意向性方法,他試圖打開或者解構胡塞爾先驗的還原,指出時間不可以“永恆”作爲基礎,認爲胡塞爾發動的哲學革命在於不斷強調超越。在我看來,這種超越,在海德格爾(M.Heidegger,1889—1976)那裏變異爲一種“激進的解釋(學)”,到了德里達則進一步衍變爲“延異”或者“解構”。在這裏,不能從字面上理解概念。比如,所謂“激進的”,不是“過分的”而是“原樣的”,它源於尼采說的要“回到一個原樣的世界”。至於“超越”,對於建立在永恆基礎上的保守力量而言,已然是一種激進了,但在這裏,哲學的關鍵問題恰恰在於與字面的意思相反——持保守的觀點由於不符合“事物的原樣”,因此是過分的;而堅持“超越”的觀點,卻與“事物的原樣”相吻合,衹是從保守的觀點來看纔是激進的。德里達一生都在關注起源的原初複雜性,用我自己的話說,就是“瞬間的厚度”。
原初的複雜性,在學理上極具思考爆發力。它欲破除思考的單義性,破除意向性或意向方向的單一性,破除同時性的單義性或單一性,這使得對於原初的複雜性分析,不能不同時也是關於時間與空間問題的分析。對於哲學自身而言,這是一件極其嚴肅的大事情。但是,與此同時,這件大事卻具有幽默感或趣味性,因爲它關注意外和偶然性。所謂原初的複雜性,就是說,起源的瞬間是有厚度的瞬間;任何簡單性、單純性、單一性、單義性——在我們說它們的瞬間就已經不純粹了,就已經感染“細菌”了,衹是我們的注意力沒有朝這個方向思考。任何事物在發生的瞬間,都是以與自身保持距離的方式發生。換句話說,事物總喜歡把自身躲藏起來,這當然不由得使我們又想到赫拉克利特和柏格森。原初的這種複雜性從一開始就對抗語言。語言,尤其是以判斷句作爲含義支撐的哲學語言,它把一切思想的出場都還原爲一個“精確的”瞬間,這是一個詞語或思想含義與自身相同一的瞬間。這其實並不是瞬間,因爲這種同一性在以後每個瞬間都反復出現。換句話說,後來的所有瞬間都集中在“原初的瞬間”,都是人們已經事先知道(概念的含義已經被完成)了的瞬間,因此它也就不再是瞬間而是永恆、不是運動變化而是靜止呆滯。
其實,也可以說康德的哲學革命是從討論時間問題出發的,是從探討事物起源問題出發的。他所謂“先驗綜合判斷”,也是在描述“原初的複雜性”。德里達是這樣歸納的,在康德那裏,“一切綜合都是建立在先驗綜合基礎上的,關於事物的‘發生’問題,就是關於這種先驗綜合的意義的‘發生’問題。如果對於全部判斷和一切可能的經驗來說,先驗綜合處於源頭和基礎的地位,不就是使我們回溯到一種模糊不定的辯證法嗎?”②德里達與康德一樣,瞄準了“出發點”的複雜性;而把這個“出發點”讀解爲別的,應該是複雜性的應有含義之一。例如,一切出發點都可以被理解爲瞬間,都發生在某瞬間,而且不應該把這個瞬間理解爲一個透明的點。這個有厚度的瞬間的厚度或不透明性,就在於原樣的瞬間潛含着個各種各樣的可能性,而以往的哲學卻往往衹看到了其中一種可能性,因此在效果上等於排斥了可能性。原樣的可能性是這樣的可能性,即一種可能性自身就已經包含着與自身不同的其他可能性。這種自身含有的差異因素,被德里達稱爲“感染”(une contamination)。由於有這樣的感染,一切界限都是靠不住的,都會伴隨歲月的流逝而趨向於瓦解。哲學應該去研究這些不易被察覺的、躲藏起來的感染,發現其中同時的多樣性,發現其中同時在疏遠自身的異化現象,就像在“我”中發現“另一個我”,“我”同時有不同的身份與“面孔”。這不是道德問題而是“原樣”的問題,從而解放了“我”;就像庸俗的時間同時也是高雅而激動人心的時間,從而解放了時間;就像缺失的其實是在場的,而被人們習慣地稱作“真實起源”的東西,其實卻極有可能是被人們根據一種已經事先構造好了的意義(或概念、立場),預先就人爲地界定好了。至於先驗的“我”,也會遭遇同樣的命運,由於它是被構造的,因而不符合“我”的原樣,或者說是掩蓋了“我”的其他可能性,比如掩蓋了“我”原本是在生活世界中發生的。總之,由於時間因素的介入,一切對立的界限都不牢固,感染和蔓延現象無處不在。一句話中包含了很多話(不斷從變化了的前提出發,起源的起源,痕迹的痕迹)。漢語表達的最高境界就在這裏。
“發生,就是出生,就是瞬間或‘瞬間’(我在這裏使用‘瞬間’一詞,是因爲瞬間的含義是不確定的,它同時在時間和存在這兩個領域之中——德里達原註)完全是突然的出現,不能還原爲前一個瞬間;發生,就是創造,就是原創性,就是本來的激進性自主地連接到一個不是自身的他者。”①Jacques Derrida , Leproblème de la genèsedans la philosophie de Husserl, 7.也就是說,所謂發生,是事物自身由某個不是自身的別一事物產生的,而且永遠如此。這就使“絕對的唯一起源”問題被無限期地永久地擱置了、推遲了——這個問題無法被真正提出來並加以準確的解答,因爲在這個問題發生之前的“如何發生”的問題更早、更接近事物的原樣。
理解“先驗”一詞有兩種方式:一種是以往的哲學,把“先驗”理解爲先天就有的,也就是各種各樣的“已經”。這些“已經”不但與經驗無關,反而是任意經驗都無法逃脫的宿命。因爲,從語法修辭角度說,“已經”是時間上的完成時態,它封閉了意外的可能性,從而排斥了純粹的偶然性。另一種理解認爲,“先驗”不過是說一種新經驗是任意產生的,它與從前已有的經驗之間或者不發生關係,或者是一種純粹偶然相遇的關係——這就與以往的哲學不同。因爲,“先驗”與經驗之間不再是互相排斥的關係,而是以某種獨一無二的方式連接起來:經驗的發生同時也就是先驗的發生,從而是一種與康德完全不同的“先驗綜合判斷”。現象與本質之間,現象與自在之物之間,再沒有萬丈深淵。經驗不僅是已有的,還是發現的,甚至是被發明的——這是先驗與經驗之間的渾濁狀態、感覺與感受之間的渾濁狀態,判斷沒有偏向其中的任何一方,從而是一個中性的、中立的、事實的判斷。它要回歸一個原樣的世界,或者說,要竭盡一切努力保存事物的“原貌”。這就叫“綜合”,也就是複雜性。於是,“發生”的問題遭遇“綜合”的問題。這當然不是關於“發生”的虛構,而是真實的發生,即任何“發生”都是複雜的發生。同樣,先驗的問題遭遇經驗的問題,這當然也不是關於“經驗”的虛構,而是真實的經驗,即任何經驗都具有任意性,不會照搬已有的經驗(不是人們想不想照搬的問題,而是無法做到照搬)。
那麽,哲學呢?哲學也是由不同於它自身的因素形成的,哲學的真諦在非哲學那裏,在非哲學的領域之中。哲學爲了拯救自身,就得開放自身。胡塞爾在晚年,不也是到生活世界尋找哲學的根嗎?但是,從經驗的發生到先驗的發生並不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時間階段,它們是同時發生的。試圖還原出某種純而又純的精神狀態,這種情形衹發生在理論態度中的虛構,而不是自然而然的事實。
純粹的分析,是在靜態下進行的,它已經對真實的運動實施了各種各樣的割裂,各種概念已經經歷了還原。“分析”作爲過程,卻把真實的時間排斥在外,即使“分析”實際上在經歷着時間,卻好像時間因素在這裏完全不發生作用似的。就這樣,“分析”不過就是一種把各種概念逐一列舉並讓它們相互衍生的過程。如此看來,“分析”的精準性其實並不精準,“分析”的理性其實並不理性。“分析”的這種不理性,就表現在它總是假定事物的原樣已經被給予我們。“分析”的這種先驗性表明它脫離了活生生的事物當下狀態,它發生在時間之前。但與此同時,我們也可以說它發生在時間之後,它是“事後諸葛亮”。在這裏,“分析”和語言本身的情形面臨着同樣的尷尬——語言表達或者發生在實際感受之前,或者發生在實際感受之後,從來就沒有擊中真正的感受本身。因此, 當“先驗的”(a priori)與“後驗的/經驗的”(a posteriori)遭遇,雖然表面上似乎也在談論“之前”與“之後”,但這裏的“之前”“之後”與時間的真實發生無關。德里達在批評胡塞爾關於《內時間意識現象學》時也指出了類似問題:如果時間是內感受的形式,那我們就不可能在感受本身之外去談論時間是什麽,去談論過去、現在、將來,因爲這種談論是把時間本身作爲我們的談論對象了。也就是說,在這個時刻,談論者站到了時間之外。
換句話說,以上對“分析”的描述同樣適用於“綜合”。所謂綜合,也就是“一次性地”把所有的時刻匯總到一起,用一種現象學式的括弧把它們囚禁在一起。這些性質不同的時刻或瞬間,都把自己的貞操獻給了綜合(供綜合“綜合”使用);而在做這樣的奉獻時,這些性質不同的時刻在“綜合”那裏是彼此外在的關係,是以生硬的方式撮合在一起的“婚姻”。再換句話說,所謂連續性其實是不連續的,並不存在唯一的起源,起源總是處於時間或“延異”之中的起源,處於改變之中的“起源”。
“儘管胡塞爾在從事着一種內在性的哲學革命,但是他仍舊是一種偉大的古典傳統的囚徒。”①這指的是胡塞爾對時間或關於“發生”問題的立場。胡塞爾哲學思想的起源,就來自對“起源”本身的思考。與康德不同,在理論出發點上,胡塞爾詢問一個更具體的問題:邏輯學與心理學的關係?在回答這個問題時,胡塞爾使用的術語,在廣義上都是“發生學”的。在康德那裏,“先驗的”在緣起上絕對不能混同於“經驗的”。所謂經驗的,也就是充滿偶然性的心理內容,因此“先驗的”在本質上是形式的、邏輯的。一開始,在“發生”問題上,胡塞爾斷然拒絕了康德的先驗形式模式,認爲類似休謨(D.Hume,1711—1776)主張的心理經驗比康德的先驗論更能接近真正的先驗哲學。但是,讓胡塞爾兩難的是,他既反對康德主義,也反對心理主義,他不得不面對同一個主體的兩面性:這個主體既是經驗的也是先驗的,既是活躍在世界上的又是純粹精神的。這是一個有厚度的主體,它把相互衝突的傾向糾結、重疊在一起,就好像經驗與沉醉同時發生、“去行爲”與“被行爲”同時發生,就像快就是慢、之前就是之後、回憶就是展望,如此等等。
三 去中心化: 原初發生與本質直觀的過程
德里達排斥以任何模式的方式看待意識和語言,無論是布倫坦諾—胡塞爾的意向性結構,還是索緒爾(F.d.Saussure,1857—1913)關於詞語的能指—所指結構。關於意向性的思想,也是關於意識結構的思想,在用某種結構統攝全域這一點上,它與結構主義關於結構的思想相似,衹不過前者所針對的是意識,後者針對的是語言。不可以說“一切意識都是關於某事物的意識”,因爲意識完全可能沒有被想到的對象,就像不能說一切意志都是爲了實現某一目的的意志。
我的這一說法,康德可能不會讚成。因爲,按照他的認識論立場:概念沒有直觀就是空的,直觀沒有概念就是盲的。胡塞爾倒是進了一步,胡塞爾承認有本質直觀或範疇直觀,但沒有洞察到自己關於本質直觀的說法暗中與意識的意向性是衝突的。所謂本質直觀,暗示沒有藉助任何對象性思維;或者借用胡塞爾的說法,“回到事物本身”(自身就是自身的“對象”或內容)。與其說本質直觀是思想,不如說本質直觀是精神的行爲。精神行爲與思想的區別在於,在以往的哲學中,思想往往受制於某種思想結構(比如,“二元對立”的模式),而精神行爲自身就是自由的自在之物。不是說某對象本身呈現於意識(不是意識與對象“對立統一”的認識論模式),而是說一切因素都在意識之中自由而內在地發生。我們的任務是,描述這些“自由而內在地發生”究竟是如何發生的。按照胡塞爾的說法,是先驗的綜合,就像是“木製的鐵”,也就是我所謂的“瞬間的厚度”。精神在出發點上就是複雜的,而不是像黑格爾(G.W.F.Hegel,1770—1831)辯證法所謂從簡單到複雜;精神在出發點上就是具體而抽象的,而非黑格爾所說的在內容上空洞簡單純粹。
本質直觀就是“木製的鐵”——康德從來沒有這樣思考,他的認識論不能容忍邏輯上的自相矛盾。這使康德哲學表面上是晦澀的,其實是清晰的。他認爲自相矛盾的情形超出了人的認識能力,什麽“木製的鐵”啊,“圓的方”啊,都是不可思議的。康德用邏輯推理的方式指出類似“木製的鐵”的情形屬於邏輯錯誤,因此是“先驗的幻象”,從而超越了理解的可能性。但康德還是爲不遵守邏輯的領域留出了地盤,也就是“自在之物”。因而,胡塞爾現在說,“木製的鐵”是可能的,是可以理解的,因爲本質直觀是可能的,不需要把本質直觀劃歸爲宗教信仰的領域,本質直觀就屬於真正的哲學問題。胡塞爾的哲學版圖比康德更爲廣大,其中包含了在形式邏輯上說不通的思想內容。
所謂“木製的鐵”,即內容自身就是形式,形式自身就是內容〔預言了信息時代到來的麥克盧漢(M.Mcluhan,1911—1980)所謂“媒介即信息”,就是這個意思〕。直觀與本質並不是割裂的,不是認識的兩個階段或在時間發生上的兩個過程,因爲直觀與本質是同時發生的。同樣,經驗與先驗並不是割裂的,不是認識的兩個階段或在時間發生上的兩個過程,因爲經驗與先驗是同時發生的。“媒介即信息”相當於“木製的鐵”的另一個說法,是因爲它把在以往看來“不是一回事”的兩樣東西看成是一樣的,這並非比喻成一樣,而是實質上一樣。它的哲學意義在於告訴人們,什麽是信息?並沒有“現成的”說法。同樣,什麽是形式、內容、經驗、先驗等等,也一概沒有“現成的”說法。進一步講,與其說我在這裏想說的真正意思是“不是沒有現成的說法”,不如說是“不應該死守着現成的說法”。直觀改造、感染着本質,本質改造、感染着直觀,從而使直觀與本質都不再是自己本來的樣子。這就像男人的原形在女人那裏,反之亦然。當然,在這裏,“原形”往往隱藏起來,就像赫拉克利特說的,事物喜歡把自己隱藏起來。能洞察到被隱藏的因素,這,就是本質直觀。
任何關於結構的思想,任何結構,都是已經“被結構”了,思想在出發點上就有着尋找結構的強烈意向。這種先入之見,其實不過是思考者在思考的某個瞬間臨時想到的;但這個臨時閃過的念頭,卻成爲今後堅定不移的意志,被說成“主義”。這,就是以往哲學的“軟肋”。這個軟肋的軟肋,在於結構之所以被稱爲“結構”,不僅在於它被設想爲固定不變的(比如,一個詞語必須有“能指”“所指”,這種劃分與在某些情況下“能指”變成“所指”或“所指”變成“能指”無關,因爲關於結構的思想,所強調的是思想的“分割”或“分析”本身),更在於結構的意向性,指向了某個固定的起源。這種指向性是一種假定,卻被認爲是不言而喻的。無論這個“起源”是時間的起源還是思想的起源,在效果上都起着“中心”的作用,有五花八門的“中心”(它們既是出發點又是終點,既是動機又是目的)。比如,在弗洛伊德(S.Freud,1856—1939)那裏,“性慾”成爲推進人類文明的“中心”(或者叫“發動機”),在唯物主義那裏是“物質”,在唯心主義那裏是“精神”,如此等等。這個中心起着穩定結構中各種不同因素的作用。凡是結構都是有組織的,不允許有絕對的任性或自由,因此,在以往的哲學中,沒有自由消遣的地位。
去除中心化,首先是消解“固定的起源”這一頑念,從而“結構”這一頑念也就自行消解。“中心”是一個點、一個瞬間,同時也是一個“牢房”或結構。它告訴人們,玩耍衹能在結構內部進行,必須被組織管理起來。因此,關於中心的思想,就是關於控制、紀律的思想。這個所謂中心貌似在結構之內,其實卻在結構之外,因爲結構是由“中心”創立起來的。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心”是締造者、主宰者、獨斷者。結構無法約束中心,而中心卻可以重組結構。但另一方面,“中心”又衹有依賴“結構”纔能生存下去,如果結構中的諸因素不聽命於“中心”,中心也就不再能自稱爲“中心”,就成了任意一個普通的點。所以,即使在中心那裏,由於它的生存有賴於結構,它的隨心所欲也是條件的,因此也是有限制的自由。
在西方,思想史的核心是哲學史。關於中心與結構的思想,也是哲學的“中心思想”,它的基礎是“是”(being),總由“是”出場(presence)亮相,衹要它一登場,就被稱爲“存在”(赫拉克利特卻極力躲避這樣的“是”及其存在效果,他說事物喜歡躲藏起來)。這種以“being”爲中心建立起來的“存在”結構,是中心中的中心,結構中的結構。這種“先驗的幻象”有一系列置換的說法,如真理、理念、原始、良心、上帝、人等等。由此可以理解,去除各種“中心論”如歐洲中心論、邏各斯中心論、語音中心論、人類中心論等等,並非等同於從此歐洲文明、邏各斯、語音、人不再發揮各自的作用了,而是說,它們的真諦未必有着像其“中心論”所說的那種作用。它們的真諦在於,它們的原形不是其“中心論”所說的那個樣子,而是別的樣子。例如,“主體”仍舊存在,但不是以思想中心點的方式存在,如此等等;也就是說,應該放棄的不是形而上學的概念,而是這些概念原有的功能。去除中心化的批判矛頭,也指向了重複或代替。由於一切重複或替換都衹能發生在時間之中,因此,所有的再一次,都是有差異的再一次,完全的重複或取代是不可能的。換句話說,“中心”從來就衹是以慾望的形式存在,而非自然中真實實現了的存在。這就像一切表面一致的系統,都不過是由差異構造起來的系統。
很難看出“一切符號都是關於某事物的符號”或“一切意向都是關於某事物的意向”與以上“中心論”之間有非常密切的關聯。其實,它們的關聯就在於,既然可以把“中心”請出某“一致性”系統之外並換之以有差異的系統,那麽,被詞語或意識“關於”的某事物,完全可能不再是某事物或者是差異着的、處於延異之中的某事物,即時刻在發生着位移或者偏離的某事物,從而某事物的原形不可確定。在以上的意義上說,去除中心化的工作,也是去掉原有的功能或使用價值。例如,誰都知道家庭裏的電視機是做什麽用的,但在特殊場合,電視機也可以被當做收音機(如果衹聽聲音不看畫面)、檯燈(如果聲音與畫面全不要,衹要電視機的光亮)使用,甚至在危急的瞬間可以把電視機當成防禦的武器。在效果上,這是電視機對其自身的批判,但這並不意味着電視機的原有功能不再存在。就像儘管20世紀的哲學家們總是以批判的姿態掙扎着要擺脫形而上學,結果還是深陷於形而上學之中,但這並不意味着哲學家的批判工作是沒有成效的,因爲他們收穫的是不一樣的形而上學,形而上學發生了形態的改變。
以上的情形也可以這樣說,並沒有唯一的真理,在某一瞬間進入某一事物的途徑,就是該事物臨時的意義或者真理。神聖性不再在於擁抱了理想對象本身或實現了某一動機,而在於處於途徑之中,在於我們正走在思想之路上。
如果把全部26個英文字母比喻爲“整體化”的一個例子的話,那麽,由這26個字母所組成的單詞和句子,在理論上可以無限多、千變萬化。有限中包含着無限,這已經是矛盾(芝諾早就看出這個悖論:正整數1可以被無限個1/2分割下去),就像數學中的負數意味着比什麽都沒有還少。有限中包含着無限與負數,都是悖理的,就像“木製的鐵”和“圓的方”。負數是進入數學的一個途徑。倘若沒有負數,數學就沒有進展,數學就不是今天這個樣子。同樣,胡塞爾的本質直觀也是進入哲學的一個新途徑,倘若沒有他的本質直觀,哲學就沒有新的進展,哲學就不是今天這個樣子。那無限單詞中的每一個,都由某幾個英文字母所組成,但這幾個字母卻無法概括新單詞的含義。新單詞使字母本身發生了性質的改變,字母衹是被新單詞加以利用的形式工具。新單詞的增加,總是趨向於越來越複雜抽象(這與人類文字發展史是吻合的,即從圖畫文字到象形文字和表意文字,到字母文字)。也就是說,越來越多的單詞衹有含義而沒有被加以落實的實物形狀。如果借用索緒爾的概念,就是詞語的能指永遠多於所指,以至於符號要超越或突破自身而成爲“非符號”,例如德里達的“延異”就不再是“關於某某的”。換句話說,慾望永遠要多於實現,慾望的意義不在“實現”那裏。慾望和意志什麽都不是,但與此同時,慾望和意志卻是一切,它們時刻在充滿、在缺失、在增補,否則,人類文明史就不會有新的進展。所謂“解構”,德里達說它不是破壞和推翻,它衹是提醒人們注意隱含的意義。①[法]德里達:“結構、符號,與人文科學話語中的嬉戲”,王逢振、盛寧、李自修 編《最新西方文論選》(桂林:灕江出版社,1991),第153頁。
在胡塞爾那裏,應該把個人的經驗心理加上現象學的括弧,這已經是一種先驗活動,是“事先預見”,這是他反對心理主義的學理依據。因此,當他說“初始的經驗活動”時,指的就是先驗活動。現象學的經驗,是在先驗原則指引下顯現出來的,也叫原初的綜合活動或先驗的構造活動,其實就是先驗綜合,這是胡塞爾思想中的康德痕迹。但是,這個過程本身卻是忽視過程的,即它忽視了先驗的原形就是內在的經驗;或者更直接地說,是胡塞爾或康德的“個人心理活動”。先驗的同時就是經驗的,這種情形發生在“先驗”被想到的瞬間,但在胡塞爾和康德那裏,這個瞬間仿佛不存在似的。
於是,這是一個不在時間之中的以自我同一的方式構造出來的先驗主體,它超越了具體的個人。在這個基礎上,後來所“發生”的一切都是觀念論的。這種觀念論是以永恆的方式被闡述的,即使它也不時地談論時間。我這裏批評的根據,就在於胡塞爾擱置了個人真實的外部與內部的經驗,這些經驗在康德與胡塞爾哲學態度的出發點上,似乎就不再發生作用。這種擱置不符合事物的原樣,因此是一種純粹的玄想。這種先驗的觀念論必然會把自己囚禁在古典認識論範圍,它的標誌就是建立起認識的對象。所謂先驗的綜合,並非發生在純粹的內感知,而是建立起某個認識的對象,無論這個對象是一個紅蘋果的“紅”還是2+2=4的意義。至於把這裏的2+2稱爲意義,把4叫做對象,即這裏存在着意義與對象的區分,在我看來卻並不具有實質區分的效果,因爲它們都屬於“對象性思維”——這充分體現在胡塞爾對現象學活動即意向性活動所下的定義,可以把這個定義歸結爲“一切意向或概念都是關於某事物的意向或概念”。這裏的“關於某事物”,其意向的方向是對象性的、是認識論的或知識論的,它建立起意向的結構。也可以說,在胡塞爾那裏,現象學就是關於抽象的某事物之可能性的學問。但如上所述,這個“某事物”逃避了它“心理發生”的瞬間,並因此是一個永恆的某事物。
四 現象學的“是”其實是“好像是”
胡塞爾的立場,與語言學關於符號的定義相吻合:一切符號,都是關於某事物的符號。這裏的某事物,即符號所指向的對象。用哲學語言,就是說要有感覺或感受的內容。所謂“關於某事物”的核心,是關於係詞“是”(從邏輯上說,“不是”是作爲“是”的變形形態被包含在“是”之中的,它們是同一類性質的問題),某事物乃“是”之所指。“是”與某事物是相互依存的,這種糾纏不清的情形,纔導致漢語哲學界爭論究竟應該把“being”翻譯爲“是”還是“存在”。換句話說,意向必須落實,意向不能爲空。看到了這一點,康德纔說,沒有直觀,概念就是空的。胡塞爾的“本質直觀”並沒有從根本上扭轉這種必須有意向對象的思維方式,胡塞爾衹是把概念本身當成了意向對象,因此他認爲衹要具有運算式的含義或意義,就可以成爲意向對象,例如“金山”或“圓的方”,即使前者在現實世界中並不存在、後者在邏輯上自相矛盾。在德里達看來,胡塞爾上述的全部“意向對象”類型,是全部古典形而上學“最後的”痕迹,即總由“是”在出場,而“不是”或甚至“不存在”的情形,暗中也要被“being”統攝起來(例如,“圓的方”既是圓形的又是方形的)。衹要是用語言這個媒介去表達,這就是不可避免的、無法破壞的結果。德里達並不想破壞它更不想顛覆它,他所思考的是超越語言(超越形而上學的語言、超越以“being”爲核心的語言)的可能性——海德格爾的《存在與時間》已經在思考這種可性能,他在“being”上面劃叉叉,進而區分了“存在”與“存在者”。但是,無論怎樣,海氏還是在討論“存在”。一言以蔽之,在德里達看來,即使海德格爾,也與胡塞爾一樣,保留着“在場”(presence,即“being”顯現出來)的形而上學。
在以往哲學中,一切意向都是朝向或者說是以“being”作爲思考出發點的,即使如康德所說,“being”不是一個真實的謂詞。康德的意思是說,“being”不是一個真實的概念,要把係詞與概念區別開來。後來,海德格爾進一步說,要把“being”與“存在”區別開來(我認爲,這個說法比漢語學界通常翻譯的“區別存在與存在者”更準確),西方哲學的歷史遺忘了這種區別。康德沒有進一步說“being”事實上成爲了一切概念的隱蔽的原形形態,是一切概念得以顯現的前提。“Being”已經暗含了一切哲學意向,甚至就是意向本身,儘管哲學的這種“核心痕迹”是隱藏着的;如果“拋棄”了“being”,似乎哲學可能就不存在了。但是,海德格爾的《存在與時間》所做的,正是這種似乎不可能完成的工作——他描述了很多意向性爲空的情形,如焦慮、恐懼、深度無聊感等等;同時,他在著作中越來越少使用“意向性”並對“being”一詞持批評態度(同樣道理,“先驗”“主體”概念在海德格爾那裏也遭到了冷遇)。哲學在分析焦慮、恐懼、深度無聊感的時候遇到了大麻煩,事實上以往的哲學基本上不把這些極深的內感受內容視爲嚴謹哲學的思考對象。這些極深的內感受內容難以用語言表達出來,甚至是“破壞”語言的。在這個意義上,海德格爾的哲學並非像學界通常認爲的那樣,會導致某種“哲學解釋學”,而是導致了描述。哲學從論證導向了描述,海德格爾對“being”所做的詞源學追溯和解釋,衹是這種描述的前期鋪墊。於是,哲學就有了兩種不同的“原始性”或“出發點”:或者是以上反復提到的“先驗的綜合”(其核心是“being”的出場),或者“being”不再是起主導作用的思想描述。“思想描述”與“思想論證”分道揚鑣。“思想描述”不排除思想的圖像、場景,甚至隱喻,這需要退回到“being”誕生之前,探究“being”究竟是如何發生的、如何出場的。
數學上的0、負數(比什麽都沒有還少)在經驗上是不可能的,它們是我們在自由想象中誕生的抽象可能性,無法在經驗中感受和觸摸到它們,但它們的可能性卻實實在在。負數,還有無理數——從字面講,屬於“沒有道理的數”,與其說這是出自邏輯意義上的判斷,不如說是先驗的本質直觀。在這裏,本質直觀代替了邏輯判斷,本質直觀避開了“being”,用直觀取代判斷,這是理解胡塞爾哲學的關鍵所在。他從此出發,離開了康德,並啓發了後來的哲學家。例如,對海德格爾的“深度無聊感”不能做“being”式的判斷,它來自類似“本質直觀”的感受,儘管海氏自己不一定會直接這樣說。本質直觀,理性的“事實”而不是經驗的事實,這裏有先驗而原始的發生。
“本質”一詞區別於具體的能被感覺器官感知的所指。在做這種區別時,我們清楚地知道本質不是什麽,但與此同時,我們並不能澄清本質是什麽。在這裏,本質排斥判斷詞“是”,我們對深度無聊感衹能描述而無法判斷,這種無聊感屬於“一般”但卻超越了可以用“是”加以界定的範疇那樣的“一般”。也就是說,一般或本質,也不是一個樣子的。不需要用“是”描述的“一般”,其情形可能數不勝數,如“而且”“或者”“如果”等等。於是,從邏輯角度,我們可以說本質是排斥了“是”的抽象感受之集合,但這個運算式是自相矛盾的,因爲它使用了判斷詞“是”。也許我們可以說,雖然都使用了“是”,但不一定都是在做判斷,或者衹是表面上看似判斷,其實在描述;或者說,是一種非常弱的在說“是”的同時就在自我否定的“判斷”,也就是在暗中“判斷”已經變異爲描述。以往哲學家似乎極少想過深度無聊感與“而且”“或者”“如果”之間有密切關係,它們是一些尚無法落實的抽象感受或抽象表達,它們同屬於“一般性”。所謂無法落實,是由於這些情形中都缺少判斷係詞“是”。也許有人會說,其中已經裹挾着“是”,但這已經相當於被胡塞爾加過現象學括弧的“是”了,或者是被海德格爾打上叉的“being”了。毫無疑問,這個括弧或這個叉叉,並不同時意味着“不是”,而是意味着擱置,不做判斷——這是現象學的態度,或者說是哲學的態度,但意味深長的是,胡塞爾否認這是理論的態度。哲學的態度竟然不是理論的態度而是純粹“一般性描述”的態度、本質直觀的態度,在這裏胡塞爾與康德的區別就更爲明顯了。
不同於以“being”作爲判斷中樞的語言表達,胡塞爾的“本質直觀”更爲靠近的不是語言表達而是內在感受性的功能,但這種功能不是康德的純粹先天的感性形式,因爲後者是純形式的、靜止的,而胡塞爾的“本質直觀”包含了生動的內容,儘管這些內容也同時屬於“一般性”。爲什麽說生動?因爲其中有內感知時間因素的作用。
抽象的功能,無論是說不出口的深度無聊、恐懼、絕望、羞愧、內疚、尷尬、不好意思、沉醉等等(這些都是深度思想氣氛),還是似乎在表達其實卻衹是在顯現抽象功能的“而且”“或者”“如果”“和”,它們都是被抽象的內感知洞察到的。這種洞察力同時“是思維”但又抗拒思維,徘徊在兩者之間。在這裏,似乎應該把顯現與表達區別開來。例如,人在深感無聊、絕望、沉醉的時候,有顯現的深度思想氣氛狀態,但沒有表達或無法表達。在這個時候,思想最深處的抽象功能在發揮着作用,也就是心靈。但是,胡塞爾現象學的純粹意識卻絕口不談心靈,他用起着“括弧”作用的篩子把心靈的痕迹清除乾淨。如果我們繼續追問,被什麽直觀(不是直觀什麽)呢?我覺得是被一個起着X功能的黑洞。這個黑洞,既抽象又鮮活,我們對它無以言表,硬稱之爲心靈(感應)、幽靈等等。這個X的一個功能被叫做“主體”“自我意識”“中心”“先驗”等等,但這些引號裏的詞語都衹是受制於語言運算式的概念,X的功能不僅限於概念。心靈、幽靈與綿延、延異一樣,其含義並非是概念意義上的,而是極其混沌的。既可以說它什麽都不是,也可以說它是一切;它不能被說出來,但它顯現出來。例如,以上列舉的“深度思想氣氛”,同時也是抽象的思想形狀或思想畫面。說它們是鮮活的,因爲它們同時也是時間畫面——這些思想氣氛總是以“如此這般”的方式在我們的靈魂深處顯示出來,衆多“如此這般”之間衹是表面上連接其實卻是斷裂的關係。
“深度思想氣氛”中的直觀思維,絕非朝向自然的方向,無法落實到具體對象,而之所以說不出口或沒有對象,乃因爲在“思想氣氛”內部充滿了隨機的“邏輯”。“思想氣氛”諸元素之間的關係幾乎都是臨時的、遭遇的,它們本來是沒有關係的,或者說“思想氣氛”諸元素之間的關係是被創造出來的,但遺憾的是,由於這些創造性總是在沉默中顯現於心情進而轉瞬即逝,這些在天性上不平庸的精神因素中的絕大多數總是永遠消失了。
海德格爾與胡塞爾的區別,在於胡塞爾仍舊頑固地從“本質直觀”中分析出“抽象的或一般的對象”,而海德格爾式的“本質直觀”不但從此再不討論一分爲二的對象式思維(也許不應該說胡塞爾的“本質直觀”是對象性思維,因爲本質直觀是返回自身的,但是當胡塞爾把本質直觀理解爲“關於一般對象的”的時候,其思維方式顯然是古典符號學意義上的),甚至就連“本質直觀”這種表達,在海氏那裏也被類似深度無聊或厭惡恐懼死亡之類所替換。
胡塞爾用“本質直觀”的描述,取代了康德的先天綜合判斷。沒有經過胡塞爾、海德格爾的同意,我用“深度思想氣氛”描述胡塞爾式的本質直觀:一方面,思想氣氛不是來自外部世界的自然經驗,就此而言,思想氣氛是不實際的“好像”。但另一方面,思想氣氛有本質直觀意義上的真實,它切切實實地觸摸到我們的靈魂深處——這裏充滿了胡塞爾所謂“自由想象的變幻”,即設想某些情景,可以是任何不實際的情景(既可以分別是思想情節和“故事情節”,也可以同時是這兩者)。在這個過程中,既可以把外感官的事實變成“非事實”,也可以根本不顧外感官僅憑直覺虛構事實。顯然,在這個過程中,“being”由於跟不上“好像”的速度而失去了作用,代之以一些令人眼花繚亂的純粹精神上的可能性,以致於“不可能性”也成爲一種可能性,甚至可以不顧精神的分裂,去設想某些真實的可能性原本是不可能的。總之,在本質直觀中沒有什麽不可以。
在本質直觀中,“感覺”不再是事實感覺,而是“好像是事實感覺”,像盧梭(J-J.Rousseau,1712—1778)式的感受。儘管盧梭沒有說他親吻華倫夫人踏過的地板的癡迷舉止是“本質的”感覺(在此時此刻的文字中,盧梭是作家而非哲學家,衹有哲學家纔使用如此笨拙的“本質”詞語)。這個道理,又與“雞尾酒裏的現象學”相一致。不能用康德的先驗形式代替這種感受,因爲後者是有內容的,即使是“不實際”的內容。於是,本質直觀,木製的鐵——對感覺的描述不動聲色地瞬間變異(即加上“現象學括弧”的效果,它殘留下“現象學剩餘”的痕迹)爲本質的描述。這些描述,也圍繞着一個“綜合”,即創造某種聞所未聞的深度新感情或不是概念的“概念”(在盧梭那裏叫“浪漫”、海德格爾描述了“深度無聊”、勒維納斯創造了“他者”、德里達則是“延異”)。顯而易見,這裏的“綜合”有賴於直覺或自由想象,它既區別於形式邏輯的歸納法,也區別於康德的先天綜合判斷。
“胡塞爾在其事業的出發點,提出了與康德同樣的問題:先天綜合判斷是如何可能的?但胡塞爾同時處於康德之內與之外:胡塞爾處於批判哲學之內,因爲他用心理學術語,也就是經驗的術語提出問題;但是,在另一種意義上,由於意向性概念向胡塞爾提供了避開康德純粹形式構造論的可能性,他已經超越了康德。悖謬的是,正是由於胡塞爾在《算術哲學》中的心理主義態度,使他後來能避免陷入康德式的心理主義。康德的心理主義就在於,在非經驗的或數學領域,爲先驗綜合判斷劃定了界限,約束先驗綜合判斷的是一個形式主體概念,而不是意向性。”①Jacques Derrida , Leproblème de la genèsedans la philosophie de Husserl , 77.胡塞爾用“意向性”概念取代康德的純粹先天形式,意向性同時含有內容與形式(例如,本質直觀)。也正是由於孕育着後來“本質直觀”意義上的意向性概念,使早期胡塞爾在《算術哲學》中的“心理主義”態度顯然已經具有不同於康德先天綜合判斷中的心理主義的傾向。換句話說,胡塞爾的直觀是現象學的“意向性”意義上的,康德的直觀是“先驗綜合”的經驗意義上的——這是一種在先驗與經驗之間先割裂後縫合的關係,其中儘管康德提到了先驗,但他所謂先驗,是沒有內容的純粹形式,而胡塞爾已經把本質自身作爲了直觀的內容。
胡塞爾現象學的全部秘密也許隱藏在對“先驗”一詞的使用之中。這是一個有厚度的先驗,它同時是篩除的與疊加的:一方面,先驗既不是囚禁於個人經驗的、不依賴於某個人的自然心理,也不是純粹邏輯的、不是純粹的形式;另一方面,就先驗有本質直觀的內容而言,又是有內容的、是“事實”,因而是在一種非常獨特的“經驗”的想象(這也是“心理生活”)中發生的,而非依賴於外部經驗的“發生”。甚至可以說,本質直觀是“最純粹的心理生活”,是原始的或具有開創性的具體經驗。它從此再不具有康德純粹形式上的先驗性,而是有內容的先驗性了,而且本質直觀與心理主義、邏輯主義都劃清了界限(因爲,這兩種主義都在尋求唯一的出發點。前者忽視了本質或者說“超越”,後者忽視了直觀或者說“純粹經驗”)。這種本質直觀又是批判邏各斯的——藝術家並非先學習了美學知識纔懂得如何進行藝術創作的,自然人也不是先學會了邏輯學纔會說話的。思維與直觀之間、或本質與直觀之間的過渡,是可以一蹴而就的(這也是瞬間的精神精華),無需像康德那樣先把先驗與經驗(或者說形式與內容)割裂開來然後又把兩者說成是兩個性質不同的來源拼湊在一起並標上“先驗綜合判斷”。不要在兩者之間劃分時間上的或邏輯上的先後,兩者之間任何一方都不具有特殊地位。這種“原初發生”的厚度,也避免了康德難以自拔的“理性醜聞”即著名的“二律背反”;把它說成“醜聞”,是因爲立場是形式的或先驗邏輯的。
所謂同時性的厚度,就是再也不糾結於先(驗)與後(驗),因爲先與後是同時的。這也同樣適用於現象學的“發生”——它是擱置了自然態度之後所發生的哲學態度,給我們留下了“現象學剩餘”或本質還原。自然界中的一切仍舊存在,改變的是我們的態度或者說是意向,就像“雞尾酒裏的現象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