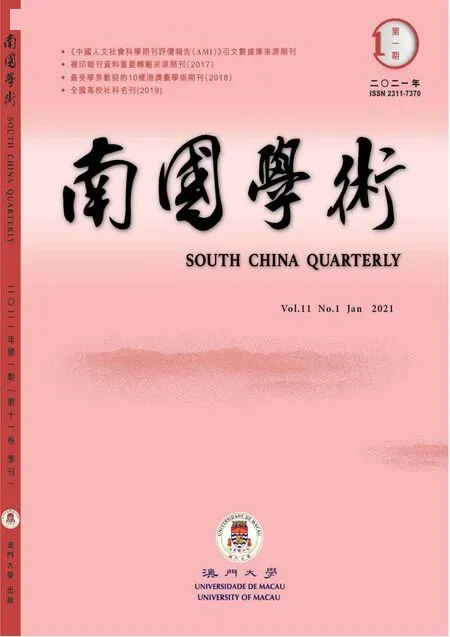明清間西方傳教經費中轉站的盛衰
——經濟生活視角下的澳門與內地關係
2021-12-28康志傑
康志傑 吳 青
[關鍵詞] 明清時期 天主教 傳教經費 澳門與內地 中轉站
晚明時期,天主教東傳,中國的澳門成爲西方傳教士進入內地的中轉站。關於澳門在中西交通史、中西文化史中的地位與功能,學界多有研究,但對於天主教傳教經費如何經澳門輸入內地,以及經濟生活視角下的澳門與內地關係,至今還是學術盲點。那麽,晚明至清中期的傳教經費如何從澳門進入內地?澳門天主教對不同傳教體系的傳教士持何態度?各傳教修會在澳門設立的賬房如何運作?鴉片戰爭之後的澳門賬房因何弱化?本文擬對這些問題進行討論,由此揭櫫中國天主教史、中西交通史以及澳門史中的一個獨特層面。
一 明清之際西方傳教經費如何由澳門進入內地
明嘉靖年間,受葡萄牙保教權支持的耶穌會士率先進入中國。1582年,即耶穌會士沙勿略(F.Xavier,1506—1552)在廣東上川島離世三十年之後①[西]沙勿略• 萊昂-迪富爾:《聖方濟各• 沙勿略傳:東方使徒神秘的心路歷程》(上海:天主教上海教區光啓社,2005),第144頁。,耶穌會士羅明堅(M.Ruggier,1543—1607)“領到葡王的津貼,乘坐葡國的商船,先在中國邊境的葡萄城(澳門)內暫住,由葡商引導來到中國;以後,又由廣州進入肇慶”②[法] 裴化行:《天主教十六世紀在華傳教志》(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蕭浚華 譯,第221頁。。
進入內地之後,耶穌會士的生存狀況與長住澳門的同會們不可同日而語,原因在於,逐漸遠離澳門後,經費獲取十分困難。例如,明萬曆十年(1582)之前,羅明堅曾先後四次進入內地瞭解情況,花費不少;萬曆十一年(1583),羅明堅、利瑪竇(M.Ricci,1552—1610)準備由廣州赴肇慶,因葡國商船在臺灣海峽遭巨風沉海,所需的路費難以湊齊,幸得澳門一位葡萄牙富翁威加(Caspar Viegas)捐資,兩人纔於1583年9月10日抵達肇慶。③羅光:《利瑪竇傳》(臺北:臺灣輔仁大學出版社,1982),第41頁。可見,晚明時期進入內地的耶穌會士在生活窘迫時,唯一辦法就是向澳門的葡萄牙人求助,“他們的命運緊緊與葡商相聯”④[法] 裴化行:《天主教十六世紀在華傳教志》(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蕭浚華 譯,第221頁。。
羅明堅抵達肇慶後,首要任務是修建教堂,可是,地基擇好了,經費卻短絀,他衹好折回澳門求助,但商船又未歸,挨到次年四月,纔攜款返回。當教堂及住所在肇慶的崇禧塔旁落成後,好景不長,被兩廣總督劉繼文看中並佔用,羅明堅又返回澳門,利瑪竇則於萬曆十七年(1589)轉入韶州府(今廣東韶關)繼續其傳教事業。
澳門是耶穌會士進入中國內地的跳板,但兩地(澳門與內地)傳教士在經濟方面的處境卻是天上地下。駐澳門的傳教士能夠輕易得到經費資助,生活無憂,可以潛心學習、傳教⑤例如,羅明堅在澳門學習中文時曾得到官員的周濟。據裴化行《天主教十六世紀在華傳教志》第188頁記曰:羅明堅初到澳門,“人人爭先恐後地來看西僧……竟有低級的官員到羅明堅那裏去拜會,並且給與金錢的周濟”。羅明堅在澳門時,還曾得到一位意人的三百元葡國銀洋資助 ([法] 裴化行:《天主教十六世紀在華傳教志》,第199頁註釋35)。,而深入中原腹地的傳教士則沒這麽幸運,雖然也能通過澳門獲得傳教經費及生活津貼,但畢竟不如駐澳門或廣東沿海的傳教士獲取經費那樣便捷,此形勢通過利瑪竇的信函可略見端倪。
利氏入華傳教的第一站是廣東肇慶。萬曆十三年(1585),他在發往歐洲的信函中說:“一切生活費都有葡萄牙商人奉獻我們,印度亞歐總督甚至葡萄牙國王都照顧我們。”⑥[意]利瑪竇:“致拿玻里馬塞利神父書”(1585年11月10日撰於肇慶),《利瑪竇全集》(臺北:臺灣輔仁大學出版社/臺灣光啓出版社,1986),羅漁 譯,第3冊,第77頁。十年之後,利瑪竇移居江西南昌,由於逐漸遠離澳門,其經濟處境與在廣東時就不大一樣了,他在信函中訴說了教會面臨的經濟境況:
我們必須要獲得總督或帝王每年一次的匯款,有了它,我們纔能維持生活,因爲,直到現在他所給我們的不夠支付,這是神父所知道的,勉強地衹足以維持韶州會院我們四位會士的生活;現在又增加了這個新會院,又添了兩個人,神父就很能瞭解我們需要的是多少了;還有,我們必須在新會院裏建造聖堂。⑦[意]利瑪竇:“利氏致澳門孟三德神父書”(1595年8月29日撰於南昌),《利瑪竇全集》,第3冊,第164頁。
這是利瑪竇向駐澳門的同會孟三德(E.d.Sande,1547—1599)發出的求援函。隨着傳教路綫不斷北進,購房建堂的開支也在逐漸增大:萬曆十七年(1589),利瑪竇在韶州建教堂及住所;萬曆二十三年(1595),又在南昌以六十兩白銀買房做教堂;萬曆三十五年(1607),利瑪竇的同事李瑪諾(E.Diaz,1559—1639)以一百兩白銀購置一處較大的房屋;萬曆二十七年(1599),利瑪竇等在南京建教堂,澳門耶穌會爲此籌集了約九百兩銀子,作爲購置南京房屋及北上的費用。①轉引自宋黎明:《神父的新裝——利瑪竇在中國(1582—1610)》(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1),第150頁。萬曆二十七年(1599),利瑪竇第三次到南京,住城南承恩寺,隨後買下了城西戶部官員劉斗墟的宅院,並在廳中建一個祭臺,奉天主聖像於其中,這是南京最初的天主教堂。
在傳教事業不斷擴大的同時,利瑪竇越來越感到從澳門獲取經費之艱辛。利瑪竇在南昌時,經濟一度陷入拮据,幸“蘇如望(Jean Soerio)神甫攜金至”②[法]費賴之:《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北京:中華書局,1995),馮承鈞 譯,第35頁。,纔解決了亟需經費的難題;中國修士鍾巴相因爲沒有語言障礙,不斷奔波於各教區,“冒着生命危險,去澳門領到錢財及其他必需物品,發放於不同的傳教點”③[法]費賴之:《明清間在華耶穌會士列傳(1552—1773)》(上海:天主教上海教區光啓社,1997),梅乘騏、梅乘駿 譯,第60、494、514頁。,以維持教務正常運轉。萬曆二十九年(1601),利瑪竇定居北京,四年後,用五百兩銀子在宣武門左側購一屋作教堂,即南堂。從利瑪竇北上拓展教務的歷史脈絡可以發現,儘管資金籌措日益艱難,但通過傳教士們的奔波輾轉,仍然獲取了來自澳門的一筆筆經費,中國內地數個傳教站由此建立起來。
在明清之際,進入中國內陸省份的耶穌會士,主要接受的是葡萄牙王室的經濟援助。每年一次的經費輸入,除了教務活動開支外,也包括傳教士的生活津貼。例如,耶穌會最早華籍修士鍾鳴仁“所費銀兩在澳中來,每年約有一二百兩”④〔明〕徐昌治 訂:《聖朝破邪集》(北京:國家圖書館藏本),第13頁。。由於澳門的耶穌會與進入中國內陸的耶穌會士屬於同一傳教系統,經費流動渠道基本暢通。
清康熙年間,受法王路易十四資助的耶穌會士開始進入中國。他們與受葡萄牙王室資助的耶穌會士(如利瑪竇、湯若望等)不同,“法籍耶穌會士的傳教區是在法國路易十四時期創建的,既不屬於日本省區,也不屬於中國副省區,而是一個單獨的機構,有它自己的成員、神長、住院和經濟,並受到一位熱誠的教友國王即法王的庇護”⑤[法]費賴之:《明清間在華耶穌會士列傳• 紐若翰》,第889頁。。由於分屬不同的傳教系統,法國耶穌會士選擇了避開澳門,在寧波登陸的方案,但經費則需要通過設在澳門的賬房領取。
兩個傳教團隊關係微妙,甚至心存芥蒂,“澳門的葡萄牙人,對新來的傳教士們多方設置障礙:凡來自法國的資金、書籍等物均予扣押。這一情況,使神甫們陷於困境”;⑥[法]費賴之:《明清間在華耶穌會士列傳(1552—1773)》(上海:天主教上海教區光啓社,1997),梅乘騏、梅乘駿 譯,第60、494、514頁。法國耶穌會士李明(L.L.Comte,1655—1728)曾在山西、陝西傳教,而來自法國的生活津貼一度被澳門葡萄牙人扣壓,導致李明、劉應、洪若翰(J.d.Fontaney,1643—1710)三人一時生活無着,不得不離開自己的傳教區,轉輾沿海城市。李明甚至陪同洪若翰南下廣東,就“經費被截”向澳門耶穌會提出抗議。⑦[法]費賴之:《明清間在華耶穌會士列傳(1552—1773)》(上海:天主教上海教區光啓社,1997),梅乘騏、梅乘駿 譯,第60、494、514頁。
關於法、葡耶穌會之間的矛盾,法國遣使會士顧鐸德(F.X.T.Danicourt)在1835年的報告中有所披露:“澳門各法籍傳教團體的賬房曾一度被澳門葡國當局所捕,後來在新任臥亞總督的命令下又被釋放。”⑧轉引自陳方中:《法國天主教傳教士在華傳教活動與影響(1860—1870)》(博士論文,1999),第61頁。
由此看來,不同背景的傳教團隊從澳門支取經費情況存在差異:葡萄牙資助的耶穌會士多能比較順利地在澳門獲得經費,但逐漸深入內陸省份後,由於距離澳門遙遠,經費時常無法到位;法籍耶穌會士的經費來自法國王室,有時會受到澳門葡萄牙人的掣肘,嚴重時會影響內地傳教士的生活;方濟各會、道明會等老修會與澳門的關係若即若離,他們有時不得不放棄澳門,轉而從呂宋(今菲律賓)或者新西班牙(墨西哥)尋求經濟支持。通過不同傳教系統的經費進入中國內地的情況反映出,不同傳教修會之間、不同西方國家世俗政權之間,關係微妙而複雜,而澳門在不同傳教團隊眼中的地位與分量也有所不同。
二 禁教之後的澳門經費如何進入內地
雍正二年(1724),清政府下令禁止天主教,中國天主教以澳門爲中轉站獲取傳教經費的格局發生變化。雖然朝廷嚴禁天主教,“然教士仍有偷渡入境,或去而復返者”①方豪:“乾隆十三年江南教難案始末”,李東華編《方豪晚年論文輯》(臺北:臺灣輔仁大學出版社,2010),第129頁。;而且,外來經費還表現出對口援助的趨向:
德國巴伐利亞(Bavaria)的統治者很多年資助了耶穌會在華的傳教工作,而路易十四支持巴黎外方傳教會。早期的時候,法國國王和華夏皇帝支付了北京傳教工作的開銷,西班牙傳教士的部分資助來自西班牙政府,在華的耶穌會士也開始放款借錢……②[美]賴德烈:《基督教在華傳教史》(香港:道風書社,2009),雷立柏 等譯,第163頁。
歸屬耶穌會管轄的教區被禁之後,仍由教會派人從澳門領取經費,如江南教會的司鐸及修生們的生活費,每年靠澳門寄來的息金維持;③轉引自[法]史式微:《江南傳教史》(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3),天主教上海教區史料譯寫組 譯,第1卷,第18—19頁。而在福建傳教的道明我會的經費,部分經澳門秘密進入內地,另有一部分從呂宋經福建流入內地。④關於傳教經費由呂宋進入中國的情況,可參見雍正十一年九月二十六日,福建總督臣郝玉麟謹奏《爲奸民私載番人潛入內地事》,載《四庫全書• 史部• 詔令奏議類• 詔令之屬• 世宗憲皇帝硃批諭旨》(文淵閣版):“據張天駿(按:閩安協副將)稟稱:有久住呂宋福寧州民,帶有呂宋夷人二名,出租船番錢一百五十圓,船主出有保狀,與彼處夷主。其番人帶有四甲箱番錢,約計五千金,在大擔門外雇小船,乘夜到漳州福河廠蔡家村內投住,欲在漳泉招人歸伊天主教等語……”在山東傳教的方濟各會士宜利策希望從新西班牙獲得經費援助,於19世紀初遠渡大洋,不幸在返回途中遇害。⑤[德]郎汝略:“山東開教史”,《恒毅》6(1975):18—19,趙慶源 譯。郎汝略認爲,宜利策死於1810年。
清禁教時期,福建的天主教活動依然活躍,從澳門獲取經費的情況引起官府警覺,福州將軍兼管閩海事務新柱奏報:“(天主教)其銀每年兩次從廣東澳門取至,嗜利之徒視同奇貨信之。”⑥“乾隆十一年福州將軍兼管閩海事務臣新柱奏”,《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華活動檔案史料》(北京:中華書局,2003),第1冊,第83頁。向朝廷奏報傳教士派人赴澳門領取經費的摺子,以福建巡撫周學健爲多。其中,乾隆十一年(1746)九月的奏摺,信息量很大:
查西洋人精心計劃,獨於行教中國一事,不惜鉅費。現訊據白多祿等,並每年雇往澳門取銀之民人繆上禹等,俱稱澳門共有八堂,一堂經管一省,每年該國錢糧,運交呂宋會長,呂宋轉運澳門各堂散給……臣前於福安各堂內,搜出番冊一本,訊係冊報番王之姓名,凡從教之人,已能誦經堅心歸教者,即給以番名。每年赴澳門領銀時,用番字冊報國王,國王按冊報人數多少加賞。現在福安從教男婦,計二千六百餘人……⑦《清實錄• 高宗純皇帝實錄(四)》(北京:中華書局,1985),第12冊,第599頁。
周學健認爲:“此等行教夷人來至中國,彼國皆每歲解送錢糧至廣東澳門,澳門夷人雇請本處土人帶銀兩密往四處散給”的行徑⑧“福建巡撫周學健奏報嚴禁天主教”(乾隆十一年五月二十八日),《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華活動檔案史料》第1冊,第86頁。,違反了中國法律;而根據“番名”(領洗時的聖名)數目,請專人赴澳領取經費,在周學健看來,更是危及國家安全的犯罪行爲,欲以“邪教”之名竭力剿滅之。
福建省位於中國東南沿海,便利的地理位置使在此傳教的道明會除了從澳門獲取經費外,菲律賓也成爲經費的中轉站。“1646年,道明會Gonzáles帶着500比索(Pesos)到福安,這筆錢主要用於傳教事業。”⑨P.Dr.M.Benno,O.P.Biermann, Die Anfänge Der Neueren Dominikanermission in China, Münster in Westfalen 1927, Verlag der Aschendorffschen Verlagsbuchhandlung, S.91.道明會把來往海上領取經費者稱爲“信差”(messengers),信差到澳門領取經費,“工作一次是10個比索”⑩AMEP, vol.436; in Eugen Menegon, Ancestors, Virgins, & Friars Christianity as a Local Religion in Late Imperial China (Cambridge and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247.。雖然路途存在風險,但信差們爲了養家餬口,甘願鋌而走險。
內地傳教士從澳門領取津貼以年度計算,但嚴峻的禁教形勢導致經費輸入內地極不穩定。以南京主教南莪德(G.X.d.Laimbeckhoven,1707—1787)爲例,1766年,葡萄牙國王曾許諾提供其津貼,但因葡萄牙對耶穌會心存芥蒂,遂中止了對南莪德的經濟援助。1771年,南莪德在寫給耶穌會總長的信函中述說了其生活窘境:
我五年來毫無收入,葡萄牙王不願在他享有保教權的國家有一名耶穌會士;我的唯一依靠果阿總主教也置我不顧。是不是辭去主教之職,退居羅馬“日爾曼公學”以度我餘年,這樣更加好?父台有什麽意見?凡仍以我爲耶穌會一員,視我爲耶穌會士的人,我希望他受到天主的祝福!①轉引自[法]高龍鞶:《江南傳教史》(臺北:輔大書坊,2013),周士良 譯,第2冊,第607、632頁。
由於沒有生活津貼,南莪德生活極度困難,“他巡行會口,靠各會口的接濟度日”②轉引自[法]高龍鞶:《江南傳教史》(臺北:輔大書坊,2013),周士良 譯,第2冊,第607、632頁。。
經費不能按時到位,影響、制約着教務發展及傳教士的日常生活:北京西堂神甫在給傳信部的信函中說:“每年西洋寄來各人分例(按:分例是神甫的津貼),即能到手,尚不足用。”③“北京西堂傳教士羅機洲給中堂大人信”,藏羅馬傳信部檔案館,卷宗號:SC Cina e Regni adiacenti Misc.1;信函無時間。由此可見,禁教之後內地傳教士所得“分例”十分有限。
乾隆四十九年(1784),“由於四名方濟各會士被人指控與當時反清廷的陝甘地區穆斯林有聯繫,清廷文告通令逮捕中外神甫以及允許外國人進入中國的官員,並要教徒放棄信仰,摧毀教堂”④[美]克蘭西(B.Clancy):《武昌教區史》“二章• 1784年的教難”(英文手抄本)。關於1784年的禁教,湖廣總督特成額在奏摺中有詳細的陳述,參見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清前期西洋天主教在華活動檔案史料》,第2冊,第462—465頁。。
事實上,這次事件的起因與天主教沒有絲毫關係。此事的原委是:清中葉以後,西北地區回民因不甘清政府的民族壓迫而爆發起義。乾隆四十六年(1781),甘肅伊斯蘭教徒馬明心創新派,後被捕。其穆斯林兄弟蘇四十三起事,據河州,攻蘭州,清廷派兵鎮壓,蘇四十三敗死。乾隆四十九年,甘肅回民田五等再起事反抗,清廷派兵鎮壓,田五戰死,回民起義失敗。恰巧是年,澳門主教秉承羅馬傳信部的意旨,向內地派出三批傳教士,其中有四位傳教士行至湖北襄陽,被當地兵弁拿獲。事情上報朝廷,乾隆帝大怒,聯想到西北地方連續爆發回民起義,進而懷疑歐洲傳教士進入內地是想勾結西北穆斯林一同造反,於是下令對西洋教士以及穆斯林“迅速嚴拿”,並嚴禁外國人潛入內陸。
關於這次朝廷禁教,旅法中國神甫衛青心(L.W.Tsing-sing,1903—2001)在其著作中有一段描述及分析:
爲了鎮壓反叛、維護國內安定,中國政府採取了一系列防範措施。清廷官吏非常害怕教徒同反叛者串通一氣,擔心成群結隊到中國傳教的歐洲傳教士支持中國的伊斯蘭教徒建立基督教-伊斯蘭教同盟。皇帝也產生了這類疑懼心理,遂在衆臣迭請之下,屢頒敕令,拆毀教堂,查拿歐洲人及中國教士、教徒;各省督撫如有瀆職放歐洲人入內地者,將受到貶謫處分。於是,一場新的反基督教運動開始了。⑤[法]衛青心:《法國對華傳教政策——清末五口通商和傳教自由(1842—1856)》(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1),黃慶華譯,上冊,第29頁
不久,這場禁教運動波及廣東、福建、陝西、四川、山東、山西、直隸、甘肅等省。因爲四名方濟各會士在湖北襄陽被捕,導致毗鄰襄陽的谷城天主教會遭到重創,時在谷城深山中傳教的神甫郭類思給北京遣使會會長羅廣祥(N-J.Raux,1754—1801)的信函,生動反映了這一時期內地教會的經濟窘境:
一七八七、八八、八九之三年傳教薪金,由呂葛思默手業經收到。茲就王君回廣之便,請代爲說明,以作憑信。至余名下之王上(法)俸金,懇特費神向廣東經理處代爲領取,俾與傳教薪費一併寄來。在布公Mr.Bourgogne處,余尚存款幾何,余不知確數,乞向楊公一爲探詢,彼當能明曉也,余從其手曾收過三年之款,自一七八七年到本年,爲余積存王賜俸金,又三年所矣。前此一切經理手續如何,余理莫知其詳細……
下文有羅廣祥的補充:
郭鐸以右函托余向廣東或澳門代領其名下應得之王俸,爲作證憑,余故附畫押。北京一七九〇年十月廿三日,Raux簽字。①郭類思的信函寫於1790年9月3日,由谷城茶園溝寄出,後刊載於寧波出版的法文月報(1921年7月),成和德譯成中文。見成和德:《湖北襄鄖屬教史記略》(上海:上海土山灣印書館,1924),第3—4頁。郭類思原隸屬於耶穌會管轄的教區由遣使會接手,故郭類思致函遣使會會長羅文祥說明接受傳教經費一事。
這封信函儘管文字不多,但透露出禁教時期內地教會與澳門的關係:即經費先由澳門轉到廣州(賬房),然後由廣州賬房秘密送往內地教會。
禁教時期,傳教士無法公開活動,前往澳門獲取經費的艱巨任務常由平信徒完成。據史式微《江南教務近代史》記載:
一八三七年,江南教友有杜姓者,聖名保祿,前在澳門修院讀書,出院後,充任司事(按:傳道員),每年至澳門代取傳教士之常年經費(蓋澳門各修會置有田房產業,取其常年生息,提作各省傳教經費)。②[法]史式微:“江南教務近代史”,《聖教雜誌》3(1921):144、188、188,漁人 譯。
1842年,第一次鴉片戰爭結束,中英簽訂《南京條約》,除五口之外,內地天主教活動仍被清廷視爲非法,杜保祿仍然每年一次遠赴澳門,任務是,給江南的司鐸捎去信函,帶回教區財產的息金,然後“運用這筆款子購買貨物,再回到江南變賣生利”③轉引自[法]史式微:《江南傳教史》,第1卷,第18—19頁。,其“所有贏餘,悉充傳教開銷”④[法]史式微:“江南教務近代史”,《聖教雜誌》3(1921):144、188、188,漁人 譯。。
鴉片戰爭之前,在華傳教修會有各自的籌款渠道:屬於葡萄牙保教權的耶穌會,接受葡萄牙王室的經濟援助;屬於西班牙修會系統的奧斯定會、道明會、方濟各會,直接受馬尼拉會長的管理,且不願隸屬於中國的宗座代牧;此外還有接受法國國王資助的法籍耶穌會。但無論哪一個系統的傳教士,都是從澳門領取經費。即便葡萄牙勢力衰退之後,由於澳門的地理位置特殊,一些傳教修會仍在澳門設立賬房,以方便經費進入內地。
三 澳門賬房在傳教經費流動中的功能與作用
天主教的發展不僅需要人力、物力,也需要大量資金,否則,傳教機器將停止運轉。在明清時期,傳教經費或由傳教士直接帶入內地,或派專人到澳門領取。爲了方便資金的管理與分配,各傳教機構便在澳門設立了管理傳教資金的機構——賬房。
澳門耶穌會賬房設在聖若瑟公學內,賬房神甫定期向內地匯寄經費。以江南教會爲例:“司鐸之傳教經費,修院之常年經費,皆在澳門。澳門置有江南傳教產業,由葡國善士慷慨捐助而來。澳門若瑟公學之管賬司鐸總理一切。”⑤[法]史式微:“江南教務近代史”,《聖教雜誌》3(1921):144、188、188,漁人 譯。此爲澳門與江南教會財務經濟關係的真實寫照。作爲賬房,它的主要職責有兩項:一是將境外林林總總的傳教資金輸送至內地,二是負責本教區(或本修會)傳教經費的分配、管理及使用。
法屬耶穌會士進入中國之後,“1736年,葡萄牙王始允許法國教士寄寓澳門,法國傳教士即於此時在澳門設置賬房”⑥[法]高龍鞶:《江南傳教史》,第2冊,第475、628頁。。但是,駐澳門的葡萄牙人排斥法屬耶穌會,於是,北京法屬耶穌會士“請求皇帝,允准傳信部在廣州設置賬房”。⑦[法]高龍鞶:《江南傳教史》,第2冊,第475、628頁。
康熙四十四年(1705),羅馬教廷派特使多羅(C.T.M.d.Tournon,1668—1710)來華解決“禮儀之爭”,多羅藉機在廣州購置會院一所,設立傳信部駐華辦事處,會院成爲傳信部賬房,經管分發津貼、分遣部派傳教士、傳達教廷指令等事宜。⑧[法]高龍鞶:《江南傳教史》,第2冊,第370頁;方豪:《中國天主教史人物傳·多羅》(上海:光啓天主教上海光啓社,2003),第459頁。而傳信部之所以將賬房設在廣州,是希望廣州發揮澳門與內地教會橋樑的功能,如此不僅避開了葡萄牙保教權的干擾與掣肘,且“羅馬與中國聯繫更爲方便”①[法]高龍鞶:《江南傳教史》,第2冊,第637、463、474、623頁。。但是,教廷傳信部廣州辦事處的運氣實在不佳,成立伊始就遭遇全國禁教,卻仍堅守運作。雍正時期,閆彌格(Michel-Anye Miralta)任廣州傳信部賬房,不斷接獲傳信部的命令;②[法]高龍鞶:《江南傳教史》,第2冊,第637、463、474、623頁。此後,遣使會士畢天祥(L.A.A.Appiani, 1663—1732)負責傳信部賬房工作。③[法]高龍鞶:《江南傳教史》,第2冊,第637、463、474、623頁。
從晚明至耶穌會解散(1773年),葡屬與法屬耶穌會士都有各自的財務系統。④[法]高龍鞶:《江南傳教史》,第2冊,第637、463、474、623頁。耶穌會解散後,遣使會接續其在華傳教事業。爲了方便教務管理,遣使會開始創辦屬於自己傳教體系的賬房。嘉慶二十四年(1819),法國遣使會傳教士南彌德(L.Lamiot,1767—1831)在澳門建立若瑟修院,同時建立本會賬房。此後,負責賬房的還有陶若翰(J.B.Torrette,1801—1840)等人。
近代以後,傳教修會在內地設立賬房增多,以應對快速發展的教務。1851年(清咸豐元年)9月8日,遣使會總會長的首席助理普蘇(Poussou)在寧波召開會議,決定將澳門遣使會的賬房遷往寧波。究其原因,此時寧波爲開放口岸,可以自由傳教,而澳門則有可能會受到葡萄牙的干擾。次年,遣使會賬房順利搬遷。咸豐六年(1856),賬房又遷至上海法租界,定名爲首善堂。⑤郭慕天 主編:《浙江天主教史略》(待出版),第164頁。《上海法租界史》記載的清咸豐七年(1857)五月十三日編制的房地產名單中有遣使會賬房負責人吉埃里(Guierry),此人即蘇鳳文。
巴黎外方傳教會是清中期在華傳教的主力軍,曾在澳門設立賬房。第二次鴉片戰爭後(1863年),又在上海設立了辦事處,取名三德堂。
方濟各會最初把賬房設在澳門,鴉片戰爭之後,開始在內地建立賬房,但實施中並非一帆風順。清咸豐八年(1858),卡洛齊神甫在蘇州總鐸區傳教,“受傳信部駐香港辦事處的方濟各賬房神父昂布羅齊的委託,要他在上海建立一所賬房,但沒有成功”⑥[法]史式微:《江南傳教史》,第1卷,第364頁。。1923年,瑪利亞方濟各傳教女修會(FMM)要求一位方濟會士爲指導司鐸,經總會長赫龍柏(B.Klumper,1864—1931)批准,上海成立方濟賬房。次年,上海方濟賬房款待了來滬出席全國教務會議的會士⑦[德]金普斯、麥克羅斯基:《方濟會來華史(1294—1955)》(香港:香港天主教方濟各會,2000),李志忠 譯,第30頁。,充分發揮出賬房在財務與教務中的雙重功能。伴隨着教務的發展,在中國內地設立賬房或分賬房,目標是進一步規範傳教經費的管理與分配;而資金渠道的暢通,爲更多傳教經費進入中國內陸帶來了便利。
綜上所述,澳門不僅是西方傳教士進入中國內地的跳板,也是海外傳教經費輸入中國的中轉站。它因此承擔了聯絡海外傳教機構與中國內地天主教的重任,各傳教修會紛紛在澳門設立賬房,如葡屬耶穌會賬房、法屬耶穌會賬房、遣使會賬房、巴黎外方傳教會賬房等。由於天主教在華活動與整個大歷史息息相關,因而各傳教機構從澳門獲取傳教經費的情況存在差異,駐澳門傳教士對深入內陸、分屬不同傳教體系的傳教士的態度也有親疏之別;中國地域遼闊,越往北行,傳教士距離澳門越遠,除了福建等沿海教會能夠從澳門獲得經費,大部分區域一年一次,有時一年一次的經費也難以兌現。鑒於各傳教修會從澳門獲取的經費多來自海外,隨着傳教士在內地不斷開拓新的傳教區,一些教區開始考慮利用澳門的地緣優勢進行資金積累,如江南教區的傳道員杜保祿每年前往澳門,就是領取教區財產的息金,而本金則留在澳門的金融機構升值,由此保證傳教經費的延續性。鴉片戰爭後,隨着葡萄牙殖民勢力的衰落,更多殖民列強侵入中國,分屬不同國家的國際金融機構紛紛進駐中國內地的大都市(上海、天津、漢口等),不同傳教修會開始把經費直接輸入在中國內地的外國金融機構,或在內地都市設立賬房,如上海的首善堂(遣使會賬房)、普愛堂(聖母聖心會帳房)、三德堂(巴黎外方傳教會賬房),天津的崇德堂(耶穌會賬房)、仁德堂(聖言會賬房)、方濟堂(方濟各會賬房)等,而澳門作爲天主教傳教經費中轉站的功能開始弱化,曾經繁忙的澳門賬房部分業務或分賬房轉入中國內地的賬房或分賬房,天主教在華傳教事業呈現更加複雜的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