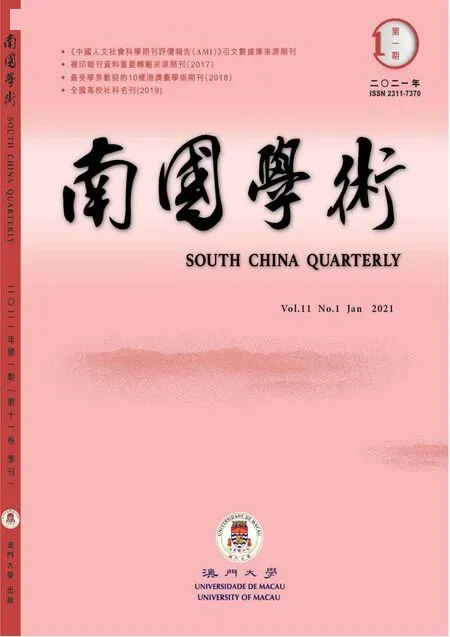歷史書寫的語言張力──管窺《左傳》中的歷史美學
2021-12-28路新生
路新生
[關鍵詞] 語言 《左傳》 歷史美學 古今對比
引言
“語言”是心靈與思想的外化,人類一切活動,都必須有廣義語言的參與。“歷史”則涵括了人類曾經的“人”—“生”總和。按照“一切歷史都是思想史”的邏輯,語言既成爲“歷史”(人類以往之一切活動)的必然要素;同時它又是“歷史學”(史家在思想狀態下對於“歷史”的言說)的基本骨幹。黑格爾(G.W.F.Hegel,1770—1831)的《美學》有兩段專談“語言”:
語文這種彈性最大的材料(媒介)也是直接屬於精神的,是最有能力掌握精神的旨趣和活動,並且顯現出它們在內心中那種生動鮮明模樣的。①[德]黑格爾:《美學》(北京:商務印書館,1981),第3卷(下冊),朱光潛 譯,第19、52頁。
語文畢竟是最易理解的最適合於精神的手段,能掌握住而且表達出高深領城的一切認識活動和內心世界中的一切東西。②[德]黑格爾:《美學》(北京:商務印書館,1981),第3卷(下冊),朱光潛 譯,第19、52頁。
黑氏的“語文”,其實就是指凝固成文字的“語言”,其着眼點落在“精神”上。史著亦史家“精神”的產品,“語言”無疑是顯示史家“精神旨趣”、“內心中那種生動鮮明模樣”的“最適合於精神的手段”。類似黑格爾的這種認識,中國也有,而且比黑氏早得多。《漢書• 藝文志》有:“左史記言,言爲《尚書》。右史記事,事爲《春秋》。”對於歷史學來說,“記言”“記事”同等重要。班固按照史書體例區別《尚書》與《春秋》,自然有其道理,但沒有見出傳統史學“言”中有“事”與 “事”中涵“言”的歷史書寫特點。七百年後,劉知幾撰《史通》,在獨家所創、同時也是《史通》綱領性篇章的“六家”“二體”之後,緊接着的便是“載言”,起手便云:
古者言爲《尚書》,事爲《春秋》,左右二史,分尸其職。蓋桓、文作霸,乣(通“糾”)合同盟,春秋之時,事之大者也,而《尚書》闕紀;秦師敗績,繆公誡誓,《尚書》之中,言之大者也,而《春秋》靡錄。
齊桓公、晉文公“乣合同盟”稱霸是謂“事”,然必待同盟者之“言”,其“事”乃可成,《尚書》卻“闕紀”;此處之未“言”,“事”便少了一個要件。秦繆公之“言”即“誡誓”,亦必有其敗績之“事”,《春秋》卻“靡錄”;此處未“言”,“事”即不完整。一失史家當“言”而未“言”,一闕歷史人物應“言”而不“言”。“言”即“事”,“事”亦“言”,劉知幾深刻認識到了“事”“言”的相輔相成。所以,他大力表彰《左傳》,認爲直到左丘明,纔克服了《尚書》《春秋》過分拘泥於區別“紀言”“紀事”之體例;其“不遵古法,言之與事,同在傳中”的歷史書寫方法,彌補了《尚書》《春秋》的不足。與此同時,劉知幾特別強調《左傳》的語言魅力——“言事相兼,煩省合理,使讀者尋繹不倦,覽諷忘疲。”“其文典而美,其語博而奧,述遠古則委曲如存,徵近代則循環可覆。”③〔唐〕劉知幾:《史通• 申左》(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2011),第 405頁。
的確,作爲“十三經”中唯一一部名副其實的“史”,《左傳》富含“歷史美學”——借用美學之慧眼回審“歷史”和“歷史學”——諸要素:《左傳》中由語言構成的“動作”“情景”以及二者結合所形成的歷史“場景”跌宕起伏,攝人心魄;《左傳》全書結構謹嚴,邏輯通貫,遣詞用語恰到好處,運筆行文渾然天成,不矯揉,不造作,自自然然,不露斧鑿之痕,不帶絲毫的“俗氣”“煙火氣”。尤其《左傳》“言”中有“事”(用歷史人物對話本身敍“事”即敍史),“事”中蘊“言”(歷史敍事中採用歷史人物對話)的敍事風格,將善、惡、美、醜放入一個調色盤內融於史著之中,像一部轟鳴的交響曲,大氣朗然。《左傳》不僅對《史記》以下的中國傳統史學產生了先導性、典範性影響,而且在理解運用語言本身以制約“歷史”之運動(藉助美學審視“歷史”)、鑒賞性閱讀給讀者帶來豐滿的美感體驗(用美學眼光看待“歷史學”)方面,都能給人以深刻啓迪。
黑格爾論詩人用“語言”展現靈魂時說:“詩人因此能深入到精神內容意蘊的深處,把隱藏在那裏的東西搜尋出來,帶到意識的光輝裏。”①[德]黑格爾:《美學》,第3卷(下冊),第52、38頁。又特別強調有“兩種散文”——“歷史寫作的藝術和說話修辭的藝術”,它們“在各自的界限之內最能接近藝術”。②[德]黑格爾:《美學》,第3卷(下冊),第52、38頁。而在美學中,“詩”=“藝術”,這就揭示了“詩”“史”同源的真理。無論是“詩”還是“史”,都是人的精神產品,因此,若將史家代入黑氏之“詩人”,史家實亦與詩人一樣,他們都“深入到精神內容意蘊的深處”,用“語言”“把隱藏在那裏的東西搜尋出來,帶到意識的光輝裏”。美學的本質,決定了它特別重視那些“能夠指向高貴的意向”,滋潤心田,不“使人心變得乾枯”③[德]康德:《判斷力批判》(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鄧曉芒 譯,第113頁。的內容。有鑒於此,本文擬以《左傳》關於晉國前期歷史(至晉文公以前)之書寫爲樣本,剖析並鑒賞它的敍事語言,以及《左傳》中的“情致”“動作”“情節”——“人性”制約下的“動作系列”——之展開,管窺《左傳》如何寫“人”敍史,體味其中的歷史美學意味,以爲當今史學之鏡鑒。
一 成師滅仇與晉武公崛
豆萁相煎,兄弟鬩牆,這些在現實生活中屢見不鮮之事,常常被藝術作品採爲創作的素材。它不僅作爲戲劇主題久演不衰,也成爲中國傳統史家高度關注的對象而屢述不絕。骨肉相殘、兄弟之間的惡鬥,是春秋時晉國早期歷史的顯著特色。《左傳》中晉國早期史之書寫,可謂開啓了此類題材敍史之先河。
關於晉之起源,《呂氏春秋• 重言》說,周成王與弟唐叔虞間曾有“翦桐之戲”:
成王與唐叔虞燕居,援梧葉以爲圭,而授唐叔虞曰:“余以此封女。”叔虞喜,以告周公。周公以請曰:“天子其封虞邪?”成王曰:“余一人與虞戲也。”周公對曰:“臣聞之,天子無戲言。天子言則史書之,工誦之,士稱之。”於是,遂封叔虞於晉。
晉首次出現於《左傳》,是在魯隱公五年(前718),《經》無載。但這並不是說,晉此前無“史”,而是因爲長期內亂,無暇告知魯,魯《不修春秋》不載晉事,孔子據《不修春秋》所撰《春秋》因此不書。但《左傳》卻對隱公五年及以前晉事書之鑿鑿,可知《左傳》必有除《春秋》以外的其他史料來源。正如劉知幾所說:“觀夫丘明受經立傳,廣包諸國,蓋當時有《周志》《晉乘》《鄭書》《楚杌》等篇,遂乃聚而編之,混成一錄。向使專憑魯策,獨詢孔氏,何以能殫見洽聞,若斯之博也?”④〔唐〕劉知幾:《史通• 採撰》,第192頁。
晉國內亂,從長兄仇一支與親兄弟成師一支的內鬥開始,至成師後裔晉武公徹底征服仇一支,完成晉內部統一,內亂方告一段落。對此,《左傳》桓公二年(前710)記:
初,晉穆侯之夫人姜氏以條之役生太子,命之曰仇。其弟以千畝之戰生,命之曰成師。師服曰:“異哉,君之名子也!夫名以制義……易則生亂。嘉耦曰妃,怨耦曰仇,古之命也。今君命太子曰仇,弟曰成師,始兆亂矣。兄其替乎!”
在《竹書紀年》中,也有“王師及晉穆侯伐條戎,王師敗逃”的記載。周宣王敗逃,則晉穆侯亦必隨之敗逃。出師不利,穆侯名其子曰“仇”以誌之。又據《史記• 晉世家》載:
穆侯四年,取齊女姜氏爲夫人。七年,伐條。生太子仇。十年,伐千畝,有功。生少子,名曰成師。晉人師服曰:“異哉,君之命子也!太子曰仇,仇者讎也。少子曰成師,成師大號,成之者也。……今適庶(“適”同“嫡”,長子;弟則爲庶)名反逆,此後晉其能毋亂乎?”
師服一語成讖,晉內亂開始。
《左傳》桓公二年記:
惠(魯惠公)之二十四年(周平王二十六年),晉始亂,故封桓叔於曲沃。……師服曰:“吾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今晉,甸侯也,而建國,本既弱矣,其能久乎?”
《史記• 晉世家》載:
昭侯元年,封文侯弟成師於曲沃。曲沃邑大於翼。翼,晉君都邑也。成師封曲沃,號爲桓叔。……桓叔是時年五十八矣,好德,晉國之衆皆附焉。君子曰:“晉之亂其在曲沃矣。末大於本而得民心,不亂何待!”
桓叔即成師,其與長兄仇不和,周天子不會不知,卻仍封桓叔於曲沃。晉國都翼,曲沃面積卻大於翼,且爲晉宗祠所在。師服所謂“天子建國”,所謂“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左氏均藉師服之口而貶天子。緣此,文中“故”字所用精當:一謂天子直接插手了晉國內亂;二謂天子“故意”於晉國邊再立一“國”。然此“國”又非“國家”之國,而係“耦國”之國——足以與國都翼相抗衡之大城曲沃。面對侯國內部的矛盾,周王火上澆油,存心扶植非長子故非“正統”之成師。左氏批評矛頭明確指向周天子。
桓叔被封於曲沃,爲成師一支崛起之始。其人“好德”得民心,“晉國之衆皆附”,太史公之“晉國”又不僅是指成師曲沃之“晉國”,且包括仇統治下之“晉國”。桓叔既“好德”,又有根據地與晉侯相頡頏,故對立面仇一支雖屢屢反抗,最終無功而返,成師一支徹底剪滅了仇一支。
《左傳》桓公二年記:“惠之三十年,晉潘父弒昭侯(仇一支之後)而納桓叔,不克。晉人立孝侯。”《史記• 晉世家》載:
鄂侯(仇一支之後)六年卒,曲沃莊伯聞鄂侯卒,乃興兵伐晉。周平王使 虢公將兵伐曲沃莊伯,莊伯走保曲沃。…… 哀侯二年,曲沃莊伯卒,子稱代莊伯立,是爲曲沃武公。……晉侯二十八年(魯莊公十六年)曲沃武公伐晉侯緡,滅之,盡以其寶器賂獻於周釐王。釐王命曲沃武公爲晉君,列爲諸侯,於是盡並晉地而有之。
周王對待晉國,可謂前後矛盾:先封桓叔於曲沃,挑動晉國內亂;見晉武公不經請示伐翼,顏面有失,心有不甘,又授命虢公爲首伐武公。晉、虢後成爲世仇,“假道伐虢”並滅之。晉武公滅緡,盡以其寶器賄賂周王,周王貪利受賄,並不得不承認現實,遂命武公爲晉君,列爲諸侯。
《左傳》莊公十六年(前678)記:“王使虢公命曲沃伯(曲沃武公)以一軍爲晉侯。”按照《周禮• 夏官》:“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爲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晉武公(曲沃武公)本有一軍,但非晉軍而爲“曲沃軍”;現周王承認武公可制一軍,“曲沃軍”升格成爲“國軍”,合法化了。
《史記• 晉世家》載:“武公代晉二歲,卒。……子獻公詭諸立。”晉獻公繼位後,晉國又開始了一輪新的內訌。
二 晉獻公時的內訌
就成師一支而言,晉獻公繼位後,內部的火併仍然不斷。獻公在位凡二十六年,殘忍、固執、專斷,且耽溺於色。二十六年間,他先滅“外親”,即削除與他有叔伯親屬關係之群公子;後由於貪色的結果,復誅“內親”,逼死太子申生。
(一)誅滅桓(桓叔)﹑莊(莊伯)之族
據《左傳》莊公二十三年(前671)記,“晉桓(桓叔)、莊(莊伯)之族偪”,壓迫公室,獻公憂慮,與士蔿謀,先翦除了桓、莊族群公子的謀士富子。次年,又挑唆群公子殺桓、莊同黨“游氏之二子”的後代。對此,《左傳》莊公二十五年(前669)寫道:
晉士蔿使群公子盡殺游氏之族,乃城聚(聚,邑名)而處之。冬,晉侯圍聚,盡殺群公子。
士蔿營造“聚”城時,已經預謀將群公子“聚”而殲之。“圍聚”二字,正可作“城聚”之註腳。“處”字二訓:“處於”之處,意在建“城”而“聚”之;又訓“處置”,誅滅也。故“聚”用字精當。《史通• 敍事》:“夫國史之美者,以敍事爲工,而敍事之工者,以簡要爲主。簡之時義大矣哉!”左氏筆力簡淨雄健,足以當之。
(二)強娶驪姬
獻公好色,類似康德(I.Kant,1724—1804)所詛咒的“老年散蕩之徒”①康德說,這類人“是世界上最下賤的存在物”〔[德]康德:“對美感與崇高感的觀察”,《康德美學文集》(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3),曹俊峰 譯,第19頁〕。。他不聽史蘇之勸,討伐驪戎,娶驪姬,由此種下動亂的禍根。
《左傳》莊公二十八年(前666)記:“晉獻公娶於賈,無子。烝於齊姜,生秦穆夫人及太子申生。又娶二女於戎,大戎狐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此條史料提示,獻公原育有三子一女,而太子申生與秦穆夫人爲親兄妹。然而,《左傳》同時又記:“晉伐驪戎,驪戎男(獻上)女以驪姬,歸,生奚齊,其娣生卓子。驪姬嬖,欲立其子,賂外嬖梁五與東關嬖五。”關於晉獻公伐驪戎娶驪姬,《國語• 晉語》提供了較《左傳》更豐富的史實,尤因其披露了一條中國早期史官作用的史實,故贅敍如下:
春秋時,戰前必卜。晉獻公卜問討伐驪戎,史蘇是掌握卜筮的史官,占卜後說:“勝而不吉。”獻公問:“此話怎講?”史蘇回答:“從兆象看是齒牙互相夾持,銜着一塊骨頭,齒牙咬弄它,象徵驪戎和晉國的互相衝突。齒牙交對,就是交替取勝,所以說是‘勝而不吉’。兆象最怕遇到口,口意味着百姓離棄,國家將會不穩。”獻公說;“哪來什麽口!口由我控制,我不接受,誰敢說話?”史蘇答道:“假如連百姓都可以離棄,那麽入耳的甜言蜜語必然會欣然接受。如此任性而不自知,又怎麽防止禍患?”獻公不聽,堅持討伐驪戎而取勝,俘獲驪姬並把她帶回晉國。驪姬得寵,被立爲夫人,此爲後話。一次,獻公設酒宴款待參戰將士,命司正官斟酒遞給史蘇,說:“衹飲酒不許吃菜。當初討伐驪戎,你說‘勝而不吉’,所以現在衹賞你酒,而罰你不許吃菜。打敗敵國得到愛妃,還有比這更大的吉利嗎?”史蘇飲完酒,低頭拜謝道:
兆有之,臣不敢蔽。蔽兆之紀,失臣之官,有二罪焉,何以事君?大罰將及,不唯無肴。抑君亦樂其吉而備其凶,凶之無有,備之何害?若其有凶,備之爲瘳。臣之不信,國之福也,何敢憚罰?
在史蘇的對白中,最堪體悟的就是“兆有之,臣不敢蔽”一語。史蘇深知,隱瞞兆象,一者違背職業道德,二是如此必將遭遇“大罰”也就是“天罰”。有職業道德和“天罰”的雙重制約,哪怕國君喜諛拒諫甚至一意孤行,史蘇仍然直言不諱。史蘇最後一句“我占的卜不靈驗,是國家的福氣,我豈敢害怕受罰”,是把“實錄”與國家的興衰榮辱相聯繫,因此將個人安危置諸度外。正是在主知天象、通人神、定人事的過程中,史官培養起了歷史學的精神主幹——“秉筆直書”和“求真”。
關於驪姬,《公羊傳》僖公十年(前650)有載:“驪姬者,國色也。”何休《公羊解詁》解“國色”:“其顏色,一國之選也。”在娶驪姬前,獻公曾卜且筮之。《左傳》僖公四年(前656)記:
初,晉獻公欲以驪姬爲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公曰:“從筮。”卜人曰:“筮短龜長,不如從長。”弗聽,立之。生奚齊,其娣生卓子。
“筮”即“筮草”,“龜”即靈龜,均用作卜占。然一爲植物,一爲動物,龜卜比筮占重要,是謂“筮短龜長”。對於這種衹是“在根本上與性的吸引力有關”並足以“銷魂”者,獻公根本不考慮其“過度的誘惑力”可能成爲“造成不良傾向和不幸的源泉”。②[德]康德:“對美感與崇高感的觀察”,《康德美學文集》,第41頁。
驪姬被立爲夫人,後宮局面失衡,導致王室內部“所涉及的各種力量之間原有的和諧”被徹底“否定或消除掉”了,雙方“轉到互相對立,互相排斥:從此每一動作在具體情況下都要實現一種目的或性格……由於各有獨立的定性,就片面孤立化了,這就必然激發對方的對立情致,導致不可避免的衝突”③[德]黑格爾:《美學》,第3卷(下冊),第286頁。;並使“分裂和由分裂來的定性終於形成了情境的本質,因而使情境見出一種衝突,衝突又導致反應動作,這就形成真正動作的出發點和轉化過程”。這一“真正動作的出發點和轉化過程”①[德]黑格爾:《美學》,第1卷,第255、302―303頁。的“衝突”,此刻即表現爲後宮爭寵和接踵而來的爭立太子。
(三) 驪姬妒忌評析
成爲“夫人”後的驪姬之所以惡行累累,均源於妒忌而產生的貪婪。妒忌是人身最邪惡的秉性之一。叔本華(A.Schopenhauer,1788—1860)這樣定位“妒忌”:
惡意的主要來源之一是妒忌;或者更確切地說,妒忌自身就是惡意。由看到別人的快樂、財富或優勢所燃起。
看到別人痛苦便稱心地、由衷地感到高興,這是一個壞透的心腸和道德極爲卑微的標誌。應該永遠躲開這種人。②[德]叔本華:《倫理學的两個基本問題》(北京:商務印書館,1996),第224—225頁。
有學者甚至說,妒忌起源於雄性動物對雌性的絕對佔有慾和雌性動物對於其他同類的絕對排他性。此說當否勿論,但說妒忌主要反映人動物性的一面;當事涉男女關係時尤其如此,則確然無疑。康德曾經幽默地認爲,“婚前”的嫉妒可以“作爲戀人的快樂和希望之間的痛苦……是一種調料……但在婚後生活中,卻變成毒藥”③[德]康德:“實用人類學”,《康德美學文集》,第193頁。。驪姬即如此。
驪姬婚後育有奚齊。據《左傳》莊公二十八年記:“驪姬嬖,欲立其子。”而之前申生已被立爲太子,若使奚齊代之,申生就成爲必須鏟滅的對象。
(四)殘害太子申生
1.使申生率領部分軍隊。《左傳》閔公元年(前661)記:
晉侯作二軍,公將上軍,太子申生將下軍。……滅耿、滅霍、滅魏。還,爲太子城曲沃。……士蔿曰:“太子不得立矣。分之都城,而位以卿,先爲之極,又焉得立?不如逃之,無使罪至。爲吳大伯,不亦可乎?猶有令名,與其及也。”
晉獻公由一軍而“作”二軍,並未經周王批准。王室衰微,衹能聽之任之。獻公使申生將下軍,爲之“城曲沃”,士蔿老辣,立刻探得了獻公明升暗廢的心思,知“太子不得立矣”!還是當初那個心狠手毒助獻公“聚殲”群公子的士蔿,現見申生將遭厄運,戚戚焉又生同情。殘忍與仁慈,冰炭不容之兩種秉性集於士蔿一身。此正類似於黑格爾談《荷馬史詩》中阿喀琉斯的秉性時,認爲他集殘暴與仁慈於一身。黑格爾發問:像阿喀琉斯那種“心腸很柔軟的人”“怎麽可能懷着惡毒的仇恨拖着赫克托的屍首繞着特洛伊城走呢?”又自問自答:對於阿喀琉斯,“我們可以說:這是一個人!高貴的人格的多方面性在這個人身上顯出了它的全部豐富性。”④[德]黑格爾:《美學》,第1卷,第255、302―303頁。
對於人性的豐富性、複雜性,左丘明亦有黑格爾同樣的洞見。人性的多面相,好比一塊塊切片,左丘明因此不作空泛的誇張與提升,也不抱不切實際的奢望與幻想,他衹是用一個個真實的歷史故事告示人們:這就是人!所以,《左傳》中的人纔顯得豐滿鮮活。
士蔿勸申生逃亡,說:“爲吳大伯,不亦可乎?猶有令名,與其及也。”理由冠冕堂皇,但不把話說透。他抬出因“亡”而成大君子的吳太伯,再後綴一狀語副詞“令名”,遂使詞義變得晦澀不清、朦朧難解,有似“猜謎”:此“及”究竟是“禍及”之及?還是如吳太伯般的“令名”之及?按照錢鍾書的意見,士蔿話說得欠完整,至少應在“與其及也”後補上“不如奔也”或“寧奔也”一句⑤錢鍾書:《管錐編》(北京:中華書局,1979),第1冊,第179頁。,認爲這是左氏“引而不發”的筆法。今似可爲錢氏“引而不發”說再贅一註:此左氏之“用晦”也。妙就妙在士蔿欲言又止、半吞半吐,就是不把那個“奔”字說出口。“奔”者,“亡奔”也可解;“及”吳太伯“令名”之“奔”亦通。然勸人“政治流亡”卻要承擔巨大政治責任。士蔿因有此顧慮,故“引而不發”。《史通• 敍事》棄“顯”而用“晦”,理由是:“顯也者,繁詞縟說,理盡於篇中;晦也者,省字約文,事溢於句外。”以之衡鑒《左傳》,至爲恰當。
2.使申生攻打東山皋落氏。《左傳》閔公二年(前660)記:
晉侯使大子申生伐東山皋落氏。里克諫曰:“太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視君膳者也,故曰冢子。……且臣聞皋落氏將戰。君其舍之!”公曰:“寡人有子,未知其誰立焉!”不對而退。
獻公命申生伐狄,主意出自驪姬。《國語• 晉語一》載:
驪姬曰:“以皋落狄之朝夕苛我邊鄙……君盍使之伐狄,以觀其果於衆也,與衆之信輯睦焉。若不勝狄,雖濟其罪可也;若勝狄,則善用衆矣,求必益廣,乃可厚圖也。”……公說。是故使申生伐東山。
而獻公“寡人有子,未知其誰立焉”之說,其欲廢太子已呼之欲出。
《左傳》閔公二年再記:
大子帥師,公衣之偏衣,佩之金玦。……狐突歎曰:“……衣之尨服,遠其躬也;佩以金玦,棄其衷也。……尨,涼;冬,殺;金,寒;玦,離;胡可恃也?雖欲勉之,狄可盡乎?”……罕夷曰:“尨奇無常,金玦不復。雖復何爲?君有心矣。”先丹木曰:“是服也,狂夫阻之。曰‘盡敵而反’,敵可盡乎?雖盡敵,猶有內讒,不如違之。”
亞里士多德(Αριστοτέλης,前384—前322)認爲,悲劇的“媒介是語言,具有各種悅耳之音,分別在劇的各部分使用”①劉厚生:“序”,[古希臘]亞里士多德《〈詩學〉〈修辭學〉》(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羅念生 譯,第36頁。。據此看《左傳》遣詞,恰如詩筆之用於史著。“尨,涼;冬,殺;金,寒;玦,離”,一字一頓,一頓一義;“衣之尨服,遠其躬也;佩以金玦,棄其衷也”,真“翩翩奕奕,良可詠也”(藉用《史通》贊班固語)。而《左傳》敍事之巧妙,錢鍾書有言:
狐突歎曰:“……雖欲勉之,狄可盡乎?”……先丹木曰:“是服也,狂夫阻之,曰‘盡敵而反’,狄可盡乎?雖盡敵,猶有內讒,不如違之。”觀先丹木之語,即針對晉侯之命而發。先此獻公面命申生一段情事,不加敍述,而以傍人語中一“曰”字達之,《史通• 敍事》篇贊《左傳》“睹一事於句中,反三隅於事外”,此可以當之。②錢鍾書:《管錐編》,第1冊,第180頁。
運用對話來敍事(此種史學傳統,中西皆然,如《尚書》之《堯典》《牧誓》,如希羅多德《歷史》、修昔底德《伯羅奔尼薩戰爭史》,而以中國出類拔萃),這是《左傳》的高明之處,也是傳統史學的突出特點。這樣做,方便了讀者從中體味出對話人的品質、性格,並因此促成讀者理解史實時的“角色代入”,增強了趣味性和可讀性。如錢鍾書所說:
用對話體來發表思想,比較容易打動讀者的興趣,因爲對話中包含幾個角色,帶些戲劇的成分。……我們讀的時候……興味並不在辯論的勝負是非,倒在辯論中閃爍着各角色的性質品格,一種人的興味代替了硬性的學術研究,像讀戲劇一樣。③錢鍾書:《錢鍾書散文》(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1997),第141頁。
以此再來體悟晉獻公之意,其實申生戰死即借“刀”殺之是獻公最希望見到的結果,如上文中的冬戰、尨衣、金玦,均爲不祥之物兆,寄託着獻公的暗想;面喻申生“盡敵而反”,即敵未盡而勿反之意,同樣陰伏殺機。
對於父親的心思,申生並非不察。獻公受驪姬蠱惑,以死逼申生,這就形成了最高的衝突要素——生與死。但是,人是有精神“底綫”即“價值觀念”的。一旦底綫面臨突破,價值破滅,肉身存在的生命形式就會成爲“價值體現”的首選對象而表現爲“崇高”即死亡。申生明知此事凶多吉少,仍然準備拼死一戰,狐突強諫之弗聽,即申生守護“價值”使然。《國語• 晉語一》載:
狐突諫曰:“不可。突聞之……”申生曰:“不可,君之使我,非歡也,抑欲測吾心也。是故賜我奇服,而告我權,又有甘言焉。言之大甘,其中必苦,譖在中矣,君故生心……不若戰也。不戰而反,我罪滋厚。我戰死,猶有令名焉。”果戰,敗狄於稷桑而反。讒言益起。
申生臨滅頂之災而不顧,這讓人想起了黑格爾所說的“道德責任”論:
因爲道德要靠思考,要明確地認識到什麽纔是職責,要按照這種認識去行事。職責本身就是意志的法律,是人憑自己自由地建立的法律。人決定要完成這職責,就依據這職責和它須完成的道理。這就是說,他先有這是善事的信心,然後纔去做這善事。這種法律——這種依據自由的信心和內在的良心,爲着職責的緣故,選擇來作爲生活準繩。①[德]黑格爾:《美學》,第1卷,第65、64、260、228、278頁。
他又說:
藝術使人認識真正的道德的善,這就是說,通過教訓,就同時產生淨化;因此,衹有改善人類纔是藝術的用處,纔是藝術的最高的目的。②[德]黑格爾:《美學》,第1卷,第65、64、260、228、278頁。
史著的作用同於藝術作品。通過《左傳》,用了太子申生的例,左丘明亦必懷着一顆讓人“認識真正的道德的善”之心,從而達到“改善人類”的“最高目的”。
3.申生遇害。《左傳》摹寫申生遇害,很符合古羅馬美學家郎吉努斯的“崇高”說與黑格爾的悲劇論。郎吉努斯說:
崇高風格到了緊要關頭,像劍一樣突然脫鞘而出,像閃電一樣把所碰到的一切劈得粉碎,這就把作者的全副力量在一閃耀之中完全顯現出來。③轉引自朱光潛:《西方美學史》(北京:中華書局,2013) ,上冊,第123、535頁。
黑格爾在談悲劇時指出,衹有在矛盾的發展導致“衝突”時“情境纔開始見出嚴肅性和重要性”④[德]黑格爾:《美學》,第1卷,第65、64、260、228、278頁。;又說道:
人格的偉大和剛強衹有藉矛盾對立的偉大和剛強纔能衡量出來。心靈從這對立矛盾中掙扎出來,纔使自己回到統一。環境的互相衝突愈衆多,愈艱巨,矛盾的破壞力愈大而心靈仍能堅持自己的性格,也就愈顯出主體性格的深厚和堅強。⑤[德]黑格爾:《美學》,第1卷,第65、64、260、228、278頁。
朱光潛對此解讀道:“悲劇所表現的是兩種對立的理想或‘普遍力量’的衝突和調解。”“這是一種成全某一方面就必犧牲其對立面的兩難之境。悲劇的解決就是使代表片面理想的人物遭受痛苦或毀滅。”⑥轉引自朱光潛:《西方美學史》(北京:中華書局,2013) ,上冊,第123、535頁。
左氏筆下的驪姬殘害申生,活脫脫一場歷史劇,卻非虛構而係實錄。驪姬心思縝密,設套規局,一計接一計,採取了眼花繚亂的一連串“動作”,充分顯現出其“人性”中“最深刻的方面”⑦[德]黑格爾:《美學》,第1卷,第65、64、260、228、278頁。——她的手腕、心計,她的妒忌、貪婪、褊狹、刻毒。而獻公的昏庸、殘忍,與驪姬相輔相成,終於逼迫申生自縊。獻公和驪姬在“維護”並“實現”他們的“倫理理想”的把戲中“陷入了罪過”⑧[德]黑格爾:《美學》,第3卷(下冊),第286頁。。
《左傳》僖公四年記:
及將立奚齊,既與中大夫成謀,姬謂大子曰:“君夢齊姜,必速祭之!”大子祭於曲沃,歸胙於公。公田,姬寘諸宮六日。公至,毒而獻之。公祭之地,地墳。與犬,犬斃。與小臣,小臣亦斃。姬泣曰:“賊由大子。”大子奔新城。公殺其傅杜原款。或謂大子:“子辭,君必辯焉。”大子曰:“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飽。我辭,姬必有罪。君老矣,吾又不樂。”曰:“子其行乎!”大子曰:“君實不察其罪,被此名也以出,人誰納我?”十二月戊申,縊於新城。
《左傳》此段敍事,雖寥寥百餘字,卻要言不煩、字字珠璣,其間懸念迭起、暗潮湧動,如“活劇”一般;以徐而不疾的史筆,展示出跌宕起伏、驚心動魄的歷史場景。敍事有背景、有情境、有對話,特因其“真實”,遂使發生於兩千五百年前的“真人真事”較一般虛構的文學作品表現出更強烈的勾魂攝魄之魅力。
黑格爾認爲,藝術作品最難把握的是找到“可以顯現心靈方面的深刻而重要的旨趣和真正意蘊的那種情境”①[德]黑格爾:《美學》,第1卷,第254、37、277、294、261、232、260、278頁。,它需要“抓住事件、個別人物以及行動的轉變和結局所具有的人的旨趣和精神價值,把它表現出來”②[德]黑格爾:《美學》,第1卷,第254、37、277、294、261、232、260、278頁。。黑格爾強調的這些“藝術創作”要領,同樣也是歷史敍事的樞軸而爲《左傳》所擅長。
《左傳》利用“情境和動作的演變”,通過太子申生特別是驪姬的形象塑造,使讀者並不僅僅根據人的“名字和外表”,而是通過“動作”去認識申生和驪姬“究竟是什麽樣的人”③[德]黑格爾:《美學》,第1卷,第254、37、277、294、261、232、260、278頁。。換言之,左氏的宗旨最終是落在認識“人”及其“類性”上的。亞里士多德《修辭學》爲悲劇中的“恐懼”下過這樣的定義:“一種痛苦的感覺,其原因是由於人看見一種足以引起破壞或痛苦的災禍落到不應遭受的人頭上。”又說:“恐懼的定義可以這樣下:一種痛苦的感覺,由於想象有足以導致毀滅或痛苦的、迫在眉睫的禍害而引起的痛苦或不安的情緒。”④[古希臘]亞里士多德:《〈詩學〉〈修辭學〉》,第215頁。看左氏筆下的申生,善良而懦弱,類似莎士比亞(W.Shakespeare,1564—1616)筆下哈姆雷特“在實行方面”有其“本身的軟弱”——哈姆雷特的“延宕又延宕”,“內傾反省、多愁善感、愛沉思”,“因此不善於採取迅速行動”的秉性,也都能在太子申生身上找到相像的蹤影。讀者在扼腕痛惜申生秉質的同時,若能像亞里士多德一樣,體悟出申生也正在遭遇“不應遭受”的“足以導致毀滅或痛苦的、迫在眉睫的禍害”,並且能夠體悟申生與哈姆雷特一樣有“很美的心情”,則不枉辜左氏一片苦心!更遑論申生與哈姆雷特有“真”“假”之別哉!最妙處是,左氏拿了申生這種“很美的心情”——“善”的秉質,處處與驪姬相比照,以凸顯驪姬的“旨趣和精神價值”。這種相互映襯與對比,使整個事件藉助善惡的衝突產生出強烈的“戲劇性觀感”。驪姬自是主角,申生作爲陪襯。《左傳》並不迴避“醜”。選擇驪姬作主角,即如藝術作品“在表現外在情況時可以走到單純的醜”,左氏意在用申生之“美”烘托驪姬之“醜”,以凸顯驪姬“最本質的核心和意義”,昭示人性中普遍存在的陰霾,使讀者理解人性的複雜面相,祛除醜惡,純淨秉性。⑤[德]黑格爾:《美學》,第1卷,第254、37、277、294、261、232、260、278頁。《左傳》抓住最能反映“情境”所需要的“可以顯現心靈方面的深刻而重要的旨趣和真正意蘊”之諸要素,用“具象”的史實使其“抽象”的“意蘊”隱隱“透”出。這體現在三個方面:
其一,驪姬先“與中大夫成謀”而立奚齊,然“成謀”尚處於“策劃”階段,即奚齊“將立”而未立。“及將立”“既與”,非有此五字作底襯,便敍不得驪姬步步緊逼的後續“動作”。左氏敍事針細縷密,真如金聖歎贊《水滸》第十一回所云:“非非常之才,無以構其思也;非非常之筆,無以摛其才也。又非非常之力,亦無以副其筆也。”⑥〔明〕施耐庵:《水滸傳》(北京:中華書局,2009) 上冊,第97、122頁。此時,借用黑格爾的美學用語,“定性”已經形成,“本質上的差異面(與善相對立的惡),而且與另一面(申生)相對立”,“衝突”已在所難免。但“衝突”畢竟“還不是‘動作’,它衹是包含着一種動作的開端和前提”⑦[德]黑格爾:《美學》,第1卷,第254、37、277、294、261、232、260、278頁。——它還衹是整個事件的“背景”。
其二,驪姬必須進一步採取構陷太子的“動作”,藉獻公之手而殺之;復因她的“動作”“起源於心靈”,故最能顯現驪姬作爲“人”的“最深刻的方面”。⑧[德]黑格爾:《美學》,第1卷,第254、37、277、294、261、232、260、278頁。驪姬爲此分四步行動:一是托夢,誆騙申生前往曲沃(晉宗祠所在地)祭母,申生心善中計。二是申生由曲沃帶回祭品,入驪姬所設圈套。三是驪姬制毒,獻公試毒。她先“寘胙(祭品)六日”,使之變質;猶恐毒性不夠,再自行加毒而獻之於獻公。驪姬之歹毒遂因其心細更見其老辣。“毒而獻之”後,忽又插入“公祭之地”一事,直教讀者意會出此必是驪姬的主意。此種敍事法,借用金聖歎評《水滸》語:“能令讀者心前眼前,若有無數事情,無數說話”,“靈心妙筆,一至於此”也。⑨〔明〕施耐庵:《水滸傳》(北京:中華書局,2009) 上冊,第97、122頁。試毒對象則由“賤”而“貴”,先“地”後“犬”復“小臣”:“公祭之地,地墳;與犬,犬斃;與小臣,小臣亦斃”,一句一頓,一頓一事,紊而不亂。《莊子• 列禦寇》載孔子論人心難知時說:“凡人心險於山川,難於知天。天猶有春秋冬夏旦暮之期,人者厚貌深情。”而在獻公試毒之時,其腦際存何種思慮?何不立即食“胙”而需“試毒”?此等處《左傳》皆妙用“言不盡意”亦“不必”盡“意”之法一概省略,遂於“留白”式的“用簡”中騰出讓讀者體悟的餘地,使敍事極具張力。四是驪姬栽贓申生,申生被害。“姬泣曰”三字,活脫脫一副嬌嗔耍賴、反咬一口的潑婦相,獻公平日寵之愛之、唯言是聽、唯計是從的昏聵狀亦深隱其中。以上四步,首尾連貫,環環相扣,一氣呵成,顯現出作爲史家的左氏撰史如撰“劇”,其藝術性構想體大思精、嚴絲合縫、邏輯貫通。在敍事中,左氏充分調動了視覺、聽覺、觸覺諸要素,使之與“人”的關係密切,也因此充滿了“人味”“趣味”。讀《左傳》常能夠有“人味”“趣味”的享受,原因在此。在申生善良軟弱的烘托下,驪姬陰險老辣、成謀深算的秉性格外鮮活。
其三,驪姬陷害太子全過程始終有語言伴隨。比起金屬、顏料、石塊、音符等,語言作爲“材料”更能體現歷史主體——人的內在精神。因此,它在歷史敍事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由於《左傳》高超絕倫的情節構思、敍事運筆歸根結底需服務於發掘並表彰那些“可以顯現偉大心靈力量的分裂與和解”①[德]黑格爾:《美學》,第1卷,第260、278頁。,這也爲傳統史學從敍事之方法論、撰史目的論上立下了圭臬。
黑格爾說:“人的最深刻方面衹有通過動作纔見諸現實,而動作由於起源於心靈,也衹有在心靈性的表現即語言中纔獲得最大限度的清晰和明確。”②[德]黑格爾:《美學》,第1卷,第260、278頁。又說:
詩藝要找出一個情節或事件,一個民族的代表人物或一個傑出的歷史人物的最本質的核心和意義,把周圍同時發生作用的一些偶然因素和不關要旨的附帶情節以及衹是相對的情境和人物性格都一齊拋開,衹用能突出地顯現主題內在實體的那些人物和事迹,這樣就會使得上述最本質的核心和意義通過對外在事物面貌的改造而獲得適合的客觀存在。③[德]黑格爾:《美學》,第3卷(下冊),第47—48頁。
所謂“史藝”,亦即“詩藝”。爲了“突出地顯現主題內在實體的那些人物和事迹”,左丘明剪除了所有的枝蔓而緊緊咬住驪姬不放。史家當有慧眼,在相反相成的人性空間中深度開掘,以此彰顯正義,增強歷史的震撼力。左氏深知此理。
(五)驪姬遭報應
申生雖死,但奚齊繼位障礙猶存。驪姬故伎重演,再誣陷晉公的另外兩個兒子重耳、夷吾是太子同黨。《左傳》僖公四年記:“姬遂譖二公子曰:‘皆知之。’重耳奔蒲,夷吾奔屈。”重耳最終奔狄,夷吾奔梁。
道德常常能彌補智慧的缺陷,智慧卻永遠填補不了道德的空白。這個生活的常識,是有操守人的戒律,卻不是驪姬的。驪姬機關算盡,遂心所願而得逞於一時,然而卻不解“愛人者,人必從而愛之;利人者,人必從而利之;惡人者,人必從而惡之;害人者,人必從而害之”④《墨子• 兼愛中》,收入《諸子集成》(北京:中華書局,1954),第4冊,第67頁。這一爲人處世的根本守則。她的膨脹情慾,不僅“反算了卿卿性命”,而且殃及無辜的奚齊、卓子被殺。魯僖公九年(前651)九月,晉獻公病重,深知自造的惡業最終會報應在奚齊身上,於是先使重臣荀息爲奚齊之傅,臨死前再召荀息“托孤”,反復要求其立誓保奚齊。荀息也是君子,有風範,稽首而誓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然晉獻公之惡天理難容,荀息以死殉之,雖確如《國語• 晉語二》以“君子曰”贊其“不食其言”,但荀息爲惡辯護,畢竟“愚忠”。故對於荀息“君子一言,駟馬難追”的承諾,仍當以左氏的批評爲準:“君子曰:《詩》所謂‘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荀息有焉。”
《左傳》僖公九年記:
晉獻公卒。十月,里克殺奚齊於次(次,喪次,居喪之草廬,不抹泥。後世謂之“築廬”)……十一月,里克殺公子卓於朝。又據劉向《列女傳• 孽嬖傳》:“奚齊立,里克殺之。卓子立,又殺之。乃戮驪姬,鞭而殺之。”
亞里士多德說:“我們應當對於得到不應當得到的厄運的人表示安慰和憐憫,對於得到不應當得到的好運的人表示憤慨,這是由於不應當得到而得到是一件不公平的事。”從這個意義上,亞氏肯定了“天神也具有憤慨的情感”。①[古希臘]亞里士多德:《〈詩學〉〈修辭學〉》,第228頁。君主制下政治角鬥的無情與險惡,使得奚齊、卓子童年即成爲政治傾軋的犧牲品,他們的厄運令人唏噓,禍根就在驪姬作惡。驪姬母子的遭際,真正應驗了平頭百姓常說的“遠在兒女近在身”的“現世報”。錢大昕嘗引徐乾學“做官時少,做人時多;做人時少,做鬼時多”指斥蔡京、明成祖之流作惡多端,而作評道:“此輩惜未聞斯語!”②〔清〕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83),第429頁。借用錢氏之詈,獻公、驪姬輩亦“惜未聞斯語!”
三 秦晉交惡及兩國關係大逆轉
(一)夷吾登基
晉獻公的子嗣在“窩裏鬥”中大部分凋零,有實力繼承君位者就是重耳、夷吾了。雖然殺死獻公的里克等人看好重耳(即後來的晉文公),但夷吾爲了早登大位,不擇手段,在秦穆公的扶持下首先登上王位。
據《左傳》僖公九年記:“里克、丕鄭欲納文公。”兩人之所以不看好夷吾,除去他們與重耳“黨同”故“伐異”因素外,就人品優劣而言,重耳與夷吾也的確存在差異。《國語• 晉語二》的描述更爲細膩,當奚齊、卓子被殺後,里克、丕鄭曾“使屠岸夷告公子重耳於狄”,意欲召之回國繼承王位。然此時的重耳因受獻公、驪姬迫害流亡異國後久經錘煉,心智已足夠成熟,深明政治上迎拒進退的取予之道,故在狐偃勸說下,婉拒了來使。但夷吾則不然,當晉國的呂甥、郤稱“使蒲城午告公子夷吾於梁”,召他回國即位時,夷吾的追隨者冀芮(即《左傳》中的郤芮)竭力鼓動夷吾應允,以爲“非亂何入?非危何安?”並且替夷吾想出一個挾秦自重的主意:“盡國以賂外內,無愛虛(不惜空虛國庫)以求入。……亡人無狷潔,狷潔不行。重賂配德,公子盡之,無愛財!”即不惜空虛國庫、賄賂秦人,來達到目的。此即《左傳》僖公九年所說的“重賂秦以求入(回國)”。由於夷吾登位心切,因此,即使賣國割地也在所不惜,故以重賂許秦穆公及晋大夫,並讓使者對秦穆公說出了這樣一番諂媚之詞:“終君之重愛,受君之重貺,而群臣受其大德,晉國其誰非君之群隸臣也?”
當然,對秦穆公來說,究竟是幫助重耳還是夷吾?自然有他的算計。由於他想要一個“聽話”的傀儡,所以,派往考察重耳、夷吾的使者公子縶的話正合其心意:“君若求置晉君而載之,置仁不亦可乎?君若求置晉君以成名於天下,則不如置不仁以猾其中,且可以進退。”③《國語• 晉語二》(北京:中華書局,2002),第297頁。是故《左傳》云,穆公“先置公子夷吾,實爲惠公”。此一“先”,用字精當,隱涵了日後另立重耳爲晉君之伏脈。左氏筆力雄健,於此又可洞見。夷吾終於在秦穆公的扶持下登上王位。因左氏已先對夷吾的品質作了鋪墊,是故惠公登位後的所作所爲就顯得順理成章,讀者並不感意外。“言近而旨遠,辭淺而意深,雖發語已殫,而含義未盡。睹一事於句中,反三隅於字外。”《左傳》深副《史通• 敍事》所贊“用晦”之要領而貫穿始終。
(二)夷吾醜行
1.“烝”嫂。《左傳》僖公十年(前650)記:
晉侯(惠公)改葬共大子(申生)。秋,狐突適下國,遇大子。大子使(狐突)登,僕,而告之曰:“夷吾無禮,余得請於帝矣,將以晉畀秦,秦將祀余。”“夷吾無禮”,實暗指惠公“烝”——強娶申生的妃子賈君。此即《左傳》僖公十五年(前645)所說的“晉侯之入也,秦穆姬屬賈君焉……晉侯烝於賈君”。由於秦穆夫人以亡嫂相託,當在夷吾入君之前,夷吾亦當允諾;但是,登上君位後,他卻即刻“烝”之。
2.斥“群公子”。《左傳》僖公十五年記:
晉侯之入也,秦穆姬屬賈君焉,且曰:“盡納群公子。”晉侯烝於賈君,又不納群公子,是以穆姬怨之。
楊伯峻“註”:“獻公之子九人,除申生、奚齊、卓子已死,夷吾立爲君外,尚有重耳等五人,即所謂群公子。”惠公欲排除所有可能對他的王位構成威脅者,尤其是重耳,他當然“不納”群公子。
3.言而無信,以怨報德。據《左傳》僖公十五年記,夷吾在返國之前,爲了讓秦穆公幫助登位,“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東盡虢略,南及華山,內及解梁城”;但一上臺,立刻變卦,“既而不與”。如果說當初允諾割地是一種策略的話,那麽,晉惠公四年(前647)晉國遭遇饑荒,“秦於是乎輸粟於晉”,次年冬“秦饑,使乞糴於晉,晉人弗與”,就顯得絕情寡義了。是故,晉君子慶鄭指斥他:“背施,無親;幸災,不仁;貪愛,不祥;怒鄰,不義。四德皆失,何以安國?”然而,慶鄭之諫是聽不進去的,反倒是虢射的“(濟秦)無損於怨,而厚於寇,不如勿與”更對他的心思。
晉惠公忘恩負義、幸災樂禍的行爲徹底激怒了秦穆公,也引起了秦國民衆的憤慨。此時,“人心感到爲起作用的環境所迫,不得不採取行動去對抗那些阻撓他的目的和情慾的擾亂和阻礙的力量”①[德]黑格爾:《美學》,第1卷,第275頁。,秦之伐晉如箭在弦上。晉惠公六年(魯僖公十五年),秦穆公伐晉,晉惠公在韓原之戰中淪爲戰俘。“(晉軍)三敗及韓。……秦獲晉侯以歸。”
(三)秦穆姬救弟
秦、晉兵戎相見,晉惠公被俘。按照《史記• 秦本紀》的說法,秦穆公原本打算殺惠公以祭天:“穆公虜晉君以歸,令於國:齋宿,吾將以晉君祀上帝。”但在秦穆姬——穆公夫人、惠公之姊以自焚相要脅下,最終打消了此念。《左傳》僖公十五年記:
穆姬聞晉侯將至,以太子罃、弘與女簡璧登臺而履薪焉。使以免服衰絰逆,且告曰:“上天降災,使我兩君匪以玉帛相見,而以興戎。若晉君朝以入,則婢子夕以死;夕以入,則朝以死。唯君裁之!”乃舍諸靈臺。
“免服衰絰,登臺履薪”,秦穆夫人堂堂正正迎面而來,如見其人。對於穆姬捨命救弟的巾幗丈夫氣概,左氏竭力凸顯並予以了正面肯定。換言之,作爲史家,這一點至關重要。因爲,此段史實不僅顯現出動人心魄的悲劇式“崇高美”,且其中蘊涵了《左傳》對“人性”“戰爭”取捨評判的重要價值觀念。
康德說:“女人……美麗,富有魅力,這就夠了。”②[德]康德:“對美感與崇高感的觀察”,《康德美學文集》,第46、36、42頁。“女人身上不應該有火藥味,正如男子不應該有麝香味一樣。”③[德]康德:“對美感與崇高感的觀察”,《康德美學文集》,第46、36、42頁。從這一意義上說,女人原本應遠離戰爭。然而,當女人也和男人一樣不得不面對戰爭時,她們往往能以柔軟而親和的人性魅力表現出一種不同於男子的堅強與智慧——穆姬的剛(以死相逼)柔(婚姻、家庭、子女)相濟,以柔(區區女身)克剛(男人、“戎”、戰爭),用女性特有的陰柔意蘊,用“親情”式的柔韌去抗衡戰爭的殘忍與非人性。這是與戰爭的剛烈、火爆截然不同的另一種“崇高”。“一個女人如果有一種女性的魅力,而且那種魅力顯示出道德的崇高,這個女人就在‘美’的本來意義上稱爲美的。”④[德]康德:“對美感與崇高感的觀察”,《康德美學文集》,第46、36、42頁。穆姬大義凜然,有不容予奪、不讓鬚眉的丈夫氣,讀來令人動容。發生在兩千五百年前的穆姬往事何以至今仍具有強大的生命力和感染力?蓋因有一“人性”之魂魄貫穿其中。
說穆姬救弟具有悲劇的“崇高”,又因爲其情節類似於黑格爾崇尚的希臘悲劇《安蒂貢》。該劇有這樣的情節:安蒂貢是波里涅色斯的妹妹。波里涅色斯爲爭奪忒拜國王位,藉外兵進攻祖國,死於戰中。國王克里安下令,嚴禁任何人收葬他。此時,安蒂貢已與王子訂婚,她卻不顧國王的禁令,毅然收葬了兄弟。國王下令燒死安蒂貢,安蒂貢自殺,王子也自殺。①[古希臘]索福克勒斯:《悲劇二種》(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1) 羅念生 譯,第9、33頁。黑格爾高度評價《安蒂貢》,認爲索福克里斯這部悲劇是古希臘以來所有悲劇的典範②[德]黑格爾《美學》,第1卷,第280頁,朱光潛“註”。,並指出,“作爲國家的首領”,國王下令禁止收葬波里涅色斯,“在本質上是有道理的,它要照顧到全國的幸福”;但安蒂貢不顧禁令收葬兄弟,同樣是“合理”的,因爲“他對弟兄的愛也是神聖的”——如果不安葬兄弟,就“違反了骨肉至親的情誼”。③[德]黑格爾《美學》,第1卷,第280頁,朱光潛“註”。
對照《安蒂貢》及黑氏語,反觀《左傳》:晉侯作惡,秦獲晉侯,穆公擬殺晉侯以齋祭,這些舉措“本質上”都是“有道理的”。但《左傳》可貴處在於,闡明此“理”的同時卻濃墨重筆,竭力表彰與秦穆公旨意相對立的穆姬之“情”即“人性”——穆姬着喪服率子女“登臺而履薪”,以自焚相逼。她的捨身救弟,在《左傳》敍事中的“權重”大大超過了秦穆公之擬殺晉侯,因其合“情”因此更加“合理”。秦穆夫人若不營救晉侯,就“違反了骨肉至親的情誼”和“對弟兄的神聖的愛”。
穆姬捨身救弟,是晉國前期骨肉相殘歷史暗夜中唯一耀眼的閃光點。而穆姬之所以出此壯舉,是“血濃於水”。
1.“天倫”與“人倫”。“人”都要面對“親情”,中西方皆然。然而,各自觀念同中有異。黑格爾說 :
形成悲劇動作情節的真正內容意蘊……是在人類意志領域中具有實體性的本身就有理由的一系列力量:首先是夫妻,父母,兒女,兄弟姊妹之間的親屬愛。④[德]黑格爾:《美學》,第3卷(下冊),第284頁。
黑氏的“親屬愛”中有父母、兒女、兄弟姊妹,這與中國相同;但是,將夫妻也包括於“親屬愛”中並置於首位,卻與中國傳統認知相異。中國有“親親相隱”“愛有差等”的親情觀,所重在血緣。首先是父母與兒女,然後是兄弟和姊妹,夫妻關係則被排除在外。《論語• 子路》載: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直在其中矣。”
郭店楚簡《六德》:
爲父絕君,不爲君絕父;爲昆弟絕妻,不爲妻絕昆弟;爲宗族殺朋友,不爲朋友殺宗族。
此禮爲“親屬容隱”的道德法則,皆以血緣關係爲據。郭店楚簡《六德》又載:“門內之治恩掩義,門外之治義斬恩。”這與《禮記• 喪服四制》相合:“門內之治恩掩義,門外之治義斷恩。”意謂,在個人領域,私恩壓倒公義;在公共領域,公義大於私恩。因此,《云夢秦簡• 法律答問》載:“子告父母,臣妾告主,非公室告,勿聽。而行告,告者罪。”⑤楊海:“父親殺了人,兒子怎麽辦?”,《中華讀書報》2012-05-23。
2.“牉”字訓。由於夫妻間沒有血緣關係,因此,以上“血濃於水”之禮均不包括夫妻。段玉裁《經韻樓集》卷二有“夫妻牉合”條,從訓詁學角度深刻剖析了夫妻關係:
“牉”當作“片”作“半”,合二體爲牉字。《周禮》:“媒氏掌萬民之判。”註曰:“判,半也。得耦爲合,主合其半……是半合爲一體也,字作‘半’。”⑥〔清〕段玉裁:《經韻樓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第35頁。
然而,“牉”又同“判”,因此,段氏又說:
考諸《說文》:“片,判木也。”“半,物中分也。”凡物合而分之曰“半”,分而合之亦得曰“半”。⑦〔清〕段玉裁:《經韻樓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第35頁。又,《辭海》釋“牉”爲“一物中分爲二”。其“牉合”條曰:
亦作“片合”“判合”。兩性相配合,男女結合成爲夫妻。牉,半。一方爲半,合其半以成配偶。《儀禮• 喪服傳》“夫妻牉合也。”
按照段玉裁、《辭海》的解釋,“牉”,夫妻“合”“半”爲“一體”而成“伴”,則“牉”通“伴”,然其未“合”時非“伴”;又,“半”“判”亦通解,“半,物中分也”,是夫妻既可以“合”爲“伴侶”之“伴”,也能夠“物中分也”,由“相合”“判”而爲“半”。父母與子女,兄弟和姐妹則不可“牉”——既不可“合”而爲“伴”,更不能“分”而爲“判”。所以,錢鍾書正確地指出:
就血胤論之,兄弟,天倫也,夫婦則人倫耳;是以友於骨肉之親當過於刑於室家之好。……“兄弟”之先於“妻子”,較然可識。①錢鍾書:《管錐編》,第1冊,第83頁。
因爲,“天倫”者,“天然”之倫也;“人倫”者,“人爲”之倫也。“天然”之倫不能改變,“人爲”之倫卻可以更張。故就血胤而言,“天倫”重於“人倫”。秦穆姬以自焚相挾拯救晉惠公的根本原因即在於此。
(四)《左傳》戰爭觀剖析
《左傳》以“人性”對抗“戰爭”,這一點最爲可貴,顯現出它非同一般的戰爭觀。穆姬所言“上天降災,使我兩君匪以玉帛相見,而以興戎”,以“戎”爲“災”而與“玉帛”相對舉,此種厭惡戰爭、批判戰爭、崇尚和平的立場並不僅僅是穆姬個人的,更是《左傳》的。
《左傳》雖亦有“兵不可去”即戰爭不可避免的認知(如魯襄公二十七年所記),但更多的是厭惡戰爭、批判戰爭之論述。換言之,類似於穆姬以“戎”爲“災”之論,在《左傳》中更多、更普遍。早在魯隱公四年(前719),左氏已藉衛州吁之“阻兵而安忍”發論:“阻兵,無衆;安忍,無親。衆叛、親離,難以濟矣。夫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也。”將“兵”即戰爭擬爲“火”而主“戢”,否則“將自焚”。此種理念,《左傳》曾一申再申。例如,魯宣公十二年(前597),晉、楚泌之戰,楚大勝,楚將潘黨建議楚莊王趁勢“京觀”即炫耀武功,楚莊王則說道:
非爾所知也。夫文,止戈爲武。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於時夏,允王保之。”……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也,故使子孫無忘其章。……武有七德,我無一焉,何以示子孫?
又如,《左傳》襄公二十四年(前549)記:“陳文子曰:‘齊將有寇。吾聞之:兵不戢,必取其族。’”再如,《左傳》襄公二十七年(前546),晉韓宣子論戰爭:“兵,民之殘也,財用之蠹,小國之大災也。”
左氏以“兵”擬“火”而主“戢”,以“戢兵”爲武功之“七德”之一,藉楚莊王引《周頌• 時邁》“載戢干戈,載櫜弓矢”,以及陳文子所言“兵不戢,必取其族”,均與穆姬以“戎”爲“災”之理念相一致,表達了一種否定戰爭、渴望和平的理念。雖然《左傳》以“止戈爲武”解“武”字並不符合“武”字之訓詁義,但誠如海登• 懷特(H.White,1928—2018)所說:儘管歷史書寫“話語可能包含了錯誤信息並存在可能有損其論證的邏輯矛盾”,它仍然能使“過去產生意義”。②[美]海登• 懷特:《元史學》(南京:譯林出版社,2004),陳新 譯,“中譯本前言”第2頁。《左傳》中蘊涵的“止戈爲武”即“止戈戢兵”即消滅戰爭的思想卻更加偉大。因爲戰爭的本質是殺戮,所以與人性直接對立。無論戰爭本身有沒有“正義”“非正義”之分,但人類社會的最終理想一定不是提倡、鼓勵戰爭,而是約束乃至消滅戰爭。作爲“類”的“人”的這一崇高理想,兩千五百年前的左丘明已揭示無遺,《左傳》中蘊涵的“止戈爲武”即“止戈戢兵”即消滅戰爭的思想就顯得更加偉大。
朱光潛曾經引車爾尼雪夫斯基(Н.Г.Чернышевский,1828—1889)的《生活與美學》替“美”下的定義:“任何事物,我們在那裏面看得見依照我們的理解應當如此的生活,那就是美的。”①朱光潛:《西方美學史》,上冊,第85頁。《左傳》表達的反對戰爭的觀點,是不是符合“依照我們的理解應當如此”的“人類理想”?答案是毫無疑問的。看清了這一點,纔能真正明瞭《左傳》用骨肉親情來與戰爭相對抗之苦心孤詣。
(五)秦晉媾和
秦穆姬奮力救弟,甚至不惜以身及子女自焚相要脅,穆公對此極爲震撼。《左傳》僖公十五年記:
大夫請以(晉惠公)入。公曰:“獲晉侯以厚(豐厚)歸也;既而喪歸,焉用之?大夫其何有焉?且晉人戚憂以重我,天地以要我。不圖晉憂,重其怒也;我食吾言,背天地也。重怒難任,背天不祥,必歸晉君。”公子縶曰:“不如殺之,無聚慝焉。”子桑曰:“歸之而質其太子,必得大成。晉未可滅,而殺其君,衹以成惡。”……乃許晉平。
秦穆公最終選擇以惠公之子爲人質而“許晉平”即與晉媾和,絕不僅僅出於穆姬之逼迫,更應視爲穆公之理智使然:“既而喪歸,焉用之?”大“勝”原應爲“厚歸”,但結果遭遇的卻是“喪歸”。試問:是喪妻亡子家庭覆滅當緊?還是“享受”戰勝國的“榮譽”有趣?這是《左傳》藉秦穆公之口爲讀者預設的一個重大問題;喪妻亡子又絕非一家的“晦氣”,秦穆公更看清了兩國間化干戈爲玉帛即視“兵”如“火”必須“戢之”的重要性。若非如此,類似“喪歸”的悲劇將一演再演,則“厚歸何用”?秦穆公的理性之舉,使秦晉兩國關係出現了逆轉,由相互仇恨變爲相互友好,而這一點也恰恰是《左傳》高度肯定的。“秦晉之好”雖最終實現於晉文公時,然而在秦穆公“特赦”晉惠公時已經奠定了基礎。而尤需注意者,是對促成秦晉之好的人性諸要素,左氏給予了充分的重視和讚許性評價。
(六)晉國陰飴甥與秦穆公對話賞析
當然,作爲一位成熟的政治家,秦穆公在與晉媾和之前還要試探一下晉國的民情,瞭解晉國內對於此事的看法,然後採取相應的行動。爲此,他召見了晉大臣。《左傳》僖公十五年記:
十月,晉陰飴甥會秦伯,盟於王城。秦伯曰:“晉國和乎?”對曰:“不和。小人恥失其君而悼喪其親,不憚征繕以立圉也,曰:‘必報讎,寧事戎狄。’君子愛其君而知其罪,不憚征繕以待秦命,曰:‘必報德,有死無二。’以此不和。”秦伯曰:“國謂君何?”對曰:“小人慼,謂之不免;君子恕,以爲必歸。小人曰:‘我毒秦,秦豈歸君?’君子曰:‘我知罪矣,秦必歸君。貳執之,服而舍之,德莫厚焉,刑莫威焉。服者懷德,貳者畏刑。此一役也,秦可以霸。納而不定,廢而不立,以德爲怨,秦不其然。’”秦伯曰:“是吾心也。”改館晉侯,饋七牢焉。這是一篇對話美文,類此者《左傳》中俯拾盡是,卻也因其普遍性,故足以拿它來細細品味、舉一反三。
首先,左丘明原惜墨如金,在此卻大段引出秦穆公與陰飴甥的對話,其旨意在於,藉助二人對話,彰顯一種貴族式的幽默,透露出一種人格精神——機智、優雅、淡定、自信;處事不慌不忙,運辭不卑不亢,於風輕云淡、波瀾不驚中蘊藏大智慧,在酒酣說笑間肩起扭轉乾坤的大擔當。
“君子”“小人”之分爲此段對話之文眼。此說以論晉何以“不和”爲說辭,內蘊五層意涵:(1)“小人”與“君子”各持己見,故謂之“不和”。(2)小人“恥失其君而悼喪其親”故“不憚征繕”,基本立場是“必報讎,寧事戎狄”。(3)君子同樣“不憚征繕”而“以待秦命”,曰:“必報德,有死無二。”可見兩“不憚征繕”的目的、性質全然不同。“征繕”本身是一把“雙刃劍”,可以從“利”“害”的兩面割:因勢利導可爲“利”,逆勢而爲能變“害”。它既可被小人用來“復仇”,與秦爲敵從而成爲秦國大隱患;也能被“君子”用來“報德”,變爲秦國之大功利:“征繕”適可造成對於秦截然相反的兩種後果,最終取決於穆公如何對待惠公。(4)小人認爲惠公既已得罪秦,穆公必不肯饒恕且釋放之;君子持義則相反。(5)韓原之戰以後“秦可以霸”,前提是釋放——“納”惠公而“定”之,恢復其王位。若不釋放甚至“廢而不立”,那麽,秦穆公也是小人,因爲他與晉國小人一般見識;秦原本可收晉國感恩戴德之利,卻可能惡變爲晉國積怨滿腹靠攏戎狄之禍。陰飴甥“秦不其然”直指秦穆公本人:就看你睚眥必報還是寬宏大量,願意作“君子”還是爲“小人”。
晉陰飴甥的說辭,沉厚內斂,綿裏藏針,軟硬兼施,一語數關,既誠懇又尖銳,正應驗了亞里士多德“政治演說所追求的目的”:“獲得好處,避免災難”;“犧牲小益而獲得大益,避免大難而遭受小難”;“對於有爭議的好東西,可以這樣推斷:其反面是壞東西的,是好東西;其反面對敵人有益的,是好東西”。①[古希臘]亞里士多德:《〈詩學〉〈修辭學〉》,第158頁。陰飴甥說辭充分顯示出語言本身足以撬動“歷史變動”的偉力,提供了以“美學”視角觀察“歷史”的絕好範例。陰飴甥說辭一言歆動秦穆公,曰“是吾心也”,惠公因此受到高規格禮遇,由原先拘於靈臺而“改館”並享有諸侯待遇——“饋七牢”。秦晉兩國關係至此出現大逆轉。
四 “作爰田”析
晉惠公淪爲階下囚、受盡屈辱,晉亦國將不國。在此緊要關頭,他先有發自肺腑的自責反省,卻在不經意間觸動了“調整生產關係”的樞機,產生了改革土地制度的關鍵性“動作”——“作爰田”。在這一過程中,語言本身又一次顯示出撬動歷史的影響力。《左傳》僖公十五年記:
晉侯使郤乞告瑕呂飴甥,且召之。子金教之言曰:“朝國人而以君命賞。且告之曰:‘孤雖歸,辱社稷矣,其卜貳圉也。’”衆皆哭,晉於是乎作爰田。呂甥曰:“君亡之不恤,而群臣是憂,惠之至也,將若君何?”衆曰:“何爲而可?”對曰:“征繕以輔孺子。諸侯聞之,喪君有君,群臣輯睦,甲兵益多。好我者勸,惡我者懼,庶有益乎!”衆說,晉於是乎作州兵。
《國語• 晉語三》“作爰田”的描述更具體:
公在秦三月,聞秦將成,乃使郤乞告呂甥。呂甥教之言,令國人於朝曰:“君使乞告二三子曰:‘秦將歸寡人,寡人不足以辱社稷,二三子其改置以代圉也。’”且賞以悅衆,衆皆哭,焉作轅田。
對於“作爰田”,當今史家有多種解釋,但均認爲“作爰田”是春秋歷史上第一次變更土地制度。郭沫若主編的《中國史稿》指出:
面對着(禮崩樂壞)這種現實,各國的統治者不得不進行一些改革,以適應社會變化的動向,維繫自己的統治。周襄王七年(前645),秦國和晉國打仗,晉惠公戰敗,被秦俘虜了。晉國的大臣爲了挽回這種劣勢,便把國人召集起來,假稱君命,把田地賞給大家,名之曰“作爰田”,廢除了周初以來土地定期分配的制度。大家因爲受了賞田,紛紛稱道晉惠公,情願爲他效命,晉於是“作州兵”。顯然,晉國大臣“作爰田”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民衆服兵役,因而開了後來按軍功賜田宅的先例。②郭沫若 主編:《中國史稿》(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第1冊,第325頁。
郭沫若的解讀有精當處。如謂“‘作爰田’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民衆服兵役,開了後來按軍功賜田宅的先例”。春秋時期“禮崩樂壞”,按軍功賜田宅,這是當時政治領域的重大事變,正是禮崩樂壞的典型反映。對這個要害問題,郭的眼光很敏銳。
但是,郭說晉國大臣爲挽回劣勢,“假稱君命”而“作爰田”,違背了史實。無論《左傳》還是《國語》,都說是惠公“使”——命令郤乞告呂甥。雖說呂甥“教”之言,但此“言”總須得到惠公的首肯纔行,所以不能說呂甥“假稱君命”。將“作爰田”解爲晉惠公“主動改革”,也缺乏根據。據《國語• 晉語三》對《左傳》的補充,可知惠公“作爰田”,將土地賞賜國人是爲了取悅民衆凝聚人心,並沒有“廢除周初以來土地定期分配的制度”的意思。《中國史稿》僅着眼於“社會生產關係”“階級秩序”的變化,認爲“各國的統治者不得不進行一些改革,以適應社會變化的動向”,對於惠公的懺悔,晉國人悲痛“皆哭”等史實,《中國史稿》未置一喙,缺乏“同情之理解”。就晉國當時面臨的情勢看,惠公被俘,國難當頭,凝聚人心刻不容緩。作爰田的主觀目的在此。“調整生產關係”,“改革土地制度”這些“宏大目標”,並不在惠公的考慮範圍之內,衹是在不經意間觸動了“生產關係”的按鈕,因此是一種不自覺行爲,在不自覺狀態下創造歷史,實現了歷史的目的性。
五 重耳流亡與晉文公登基
重耳出逃在外十九年,其中十二年在戎狄(重耳母爲狄人),七年在齊、衛、曹、宋、鄭、楚、秦七國間輾轉流亡;在飽嘗艱辛的同時,也錘煉了意志,提升了品格。這些閱歷,對他登基後的執政產生了重要影響。
在流亡期間,重耳既享受了如齊桓公、宋襄公、楚成王、秦穆公的厚待與尊重,也體驗了如衛文公、曹共公、鄭文公的無禮與薄情。以禮遇而言,秦穆公以諸侯之禮設宴款待,讓重耳倍感榮耀。據《國語• 晉語四》記述了宴會時的場景:
秦伯賦《采菽》,子餘使公子降拜,秦伯降辭。子餘曰:“君以天子之命服命重耳,重耳敢有安志,敢不降拜?”
不僅如此,秦穆公還“納女五人,懷嬴與焉”①楊伯峻 編著:《春秋左傳注》(北京:中華書局,1981)“僖公二十三年”,第410頁。。這位懷嬴,就是晉惠公之子子圉在秦國當人質時的妻子。《左傳》僖公十七年(前643)記:“夏,晉太子圉爲質於秦,秦歸河東而妻之。”懷嬴因有才,深得秦穆公鍾愛。現改嫁重耳,穆公對重耳說:“寡人之適(嫁女),此爲才。子圉之辱,備嬪嬙焉。”②《國語• 晉語四》,第333頁。
懷嬴爲何改嫁?因爲子圉拋棄了她。子圉婚後五年即逃歸晉。《左傳• 僖公二十二年(前638)記:
晉太子圉爲質於秦,將逃歸,謂嬴氏曰:“與子歸乎?”對曰:“子,晉太子,而辱於秦。子之欲歸,不亦宜乎?寡君之使婢子侍執巾櫛,以固子也。從子而歸,棄君命也。不敢從,亦不敢言。”遂逃歸。
他爲何逃歸?是爲了爭奪王位。《史記• 晉世家》載:
十三年,晉惠公病,內有數子。太子圉曰:“吾母家在梁,梁今秦灭之。我外輕於秦而內無援於國。君即不起,病大夫輕,更立他公子。”乃謀與其妻俱亡歸。
子圉的急於歸國繼位,與乃父何其相似!此事再次開罪了秦穆公。故在嫁女後,穆公準備幫助重耳登基。《史記• 晉世家》載:“子圉之亡,秦怨之,乃求公子重耳,欲內之。”《左傳》僖公二十四年(前636)記,秦穆公從楚國召回重耳送之歸晉,又派公子縶赴晉軍曉以利害,晉軍大“反水”,歸順重耳,重耳殺懷公(子圉),登上君位,晉國歷史翻開新的一頁。
作爲繼康德、黑格爾之後最具代表性的美學家叔本華,雖對歷史學抱有偏見,但卻難得一見地對“歷史”與“藝術”的關係說了一句中肯的話:“敍述性和戲劇性”可以從“歷史”中“提取個別之物,精確地把它及其個體性描繪出來,並以此表現了整個人類的存在”③〔清〕顧炎武:《日知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史記》於敍事中寓論斷”,第1884頁。。《左傳》中關於春秋早期晉國史敍事中的歷史美學要素,正可以作如叔本華觀。
餘論
(一)史家撰史之“隱身法”
撰史之功,莫大於語言。撰史之“語言”,實際上有兩方面內涵:第一,史家的語言。而史家懂得“隱身”,尤爲重要。黑格爾在談《荷馬史詩》時有一段提示:
爲着顯示出整部史詩的客觀性,詩人作爲主體必須從所寫對象退到後臺,在對象裏見不到他。表現出來的是詩作品而不是詩人本人,可是在詩裏表現出來的畢竟還是他自己的,他按照自己的看法寫成了這部作品,把他自己的整個靈魂和精神都放進去了。他這樣做,並不露痕迹。例如在《伊利亞特》這部史詩裏,敍述事迹的有時是一位卡爾克斯,有時是一位涅斯特,但是真正的敍述者還是詩人自己。①[德]黑格爾:《美學》,第3卷(下冊),第113頁。
黑格爾此段話,顯然受到了席勒(J.C.F.v.Schiller,1759—1805)的啓示。在美學觀上比較感傷詩與“素樸詩”,席勒高度讚賞後者。席勒舉荷馬《伊利亞特》與文藝復興時期意大利詩人阿里奧斯托(L.Ariosto,1474—1533)《瘋狂的羅蘭》筆法的差異,認爲二者“都很美地描繪出道德感對激情的勝利,都憑心情的素樸使我們感動”,但兩位詩人的描寫手法卻大不相同。阿里奧斯托是一位近代的感傷詩人,他“在敍述這件事之中,毫不隱藏自己的驚羨和感動”,“突然拋開對對象的描繪,自己插進場面裏去”,以詩人的身份表示他對“古代騎士風”的讚賞。至於荷馬,卻絲毫不露主觀情緒,“好像他那副胸膛裏根本沒有一顆心似的”;“他所用來處理題材的那種冰冷的真實簡直近於無情。他專心致志地對着他的對象。……他隱藏在他的作品後面,他自己就是他的作品,他的作品就是他自己”。②轉引自朱光潛:《西方美學史》,下冊,第495頁。此種書寫的“隱身法”,顧炎武的《日知錄》在評論司馬遷敍事手法時就已提到;儘管是在論歷史的書寫,卻要比席勒、黑格爾更早:
古人作史有不待論斷而於敍事之中即見其指者,惟太史公能之。《平准書》末載卜氏語;《王翦傳》末載客語;《荊軻傳》末載魯勾踐語;《晁錯傳》末載鄧公與景帝語……皆史家於敍事中寓論斷法也。後人知此法者鮮矣,惟班孟堅間一有之。③
顧炎武之“古人作史有不待論斷而於敍事之中即見其指者”有稍不確者。此種書寫方法並非昉於司馬遷,而實肇始於《左傳》。《左傳》因有此特點,配以生動傳神的文筆,故具有高度的可讀性。
黑格爾、席勒凸顯了詩家——按照史、詩相通之理就可以解喻爲史家——主體對於“客觀性”的追求。而黑氏所說的“退到後臺,在對象裏見不到他”,是指作者站在第三者立場上敍事,透過史實而非直接表露史作者的“意蘊”即史義。這正是美學中的“鑒賞”原則和方法在歷史學中的運用。
以此來看《左傳》,儘管左丘明也“把他自己的整個靈魂和精神都放進去了”,但他並不露出痕迹而是隱在幕後——他的敍事站在了第三方的立場。這表明,他主觀上遵循着盡可能客觀的歷史學法則。此種敍事方法,又不僅能使歷史書寫更加客觀,它還與歷史中受人性制約的“情致”湧動和“動作”的發生——其結果即歷史“情節”的起承轉合——息息相關。
第二,歷史人物的語言。撰史無“語言”不成。然歷史書寫之“語言”,既是敍事主體的語言,同時也是敍事對象的語言。史家著史敍事時,不僅要“自己說”,更要多讓“別人說”,讓歷史人物自己開口發言,讓他的語言充當敍事的工具。在這當口,史家無需越俎代庖、喧賓奪主,替代歷史人物。《左傳》中秦穆公、晉陰飴甥等等歷史人物的大量對話,就成功運用了這一敍事方法。黑格爾所舉卡爾克斯的例子,明示的也是這個道理。用這種手段敍事,遵循的仍然是顧炎武的“古人作史有不待論斷而於敍事之中即見其指”之法,亦即黑格爾所說“詩人”——史家——“作爲主體必須從所寫對象退到後臺,在對象裏見不到他”,主觀上追求的還是那一個“真”字。
(二)如何評價《左傳》的“君子曰”即史學評論
文論人石天強對小說“每章最後的敍述文字”感到“費解”,並指出:
這些文字可以理解爲敍述人對現實的各種感悟,它們是如此強烈,以至於敍述人不得不站出來現身說法。但這種議論性文字的頻繁呈現,卻也暗示着敍述的蒼白。敍述人所編織的文字難以承擔如此沉重的內容,它迫使敍述人破壞敍述的完整性,而以議論的形式出現。而這恰恰意味着敍述的失敗。①石天強:“再見了,馬原們!”,《文匯報》2012-04-14。
這種認識,在文論界有相當的普遍性。此處藉石論復視《左傳》之“君子曰”,或許有助於從一個側面理解歷史敍事的語言運用。
歷史之敍事法實亦似小說,其中並非不可以帶有史家本人對歷史的裁斷,但它應隱藏在敍事之中,在與事件水乳交融的狀態下讓裁斷本身“透出來”。那麽,對《左傳》中的“君子曰”史評該如何評價,能否捨棄而不發議論?是否也帶有石天強所指責者的某種瑕疵?在此有必要做一區分。
《左傳》用“君子曰”處並不多,都是在那些極其緊要、事已至此不得不“發”的“節骨眼”上纔用——《左傳》中並沒有脫離事件而空發議論的“君子曰”。也就是說,左丘明敍事至“君子曰”前,若不在此緊要關頭“發”一下、“論”一番,那反而“假”了。就好像人壓抑太久,到了緊要關口,他衹有而且必須長出一口氣纔能“解恨”“解悶”,要不然就要憋屈死了!讀者至此若是見不到《左傳》“君子曰”有感而發,也會有大遺恨。所以,當讀至“君子曰”處,並不覺得它是“贅瘤”,反倒有一種與左丘明一致的“是矣!是矣!”“快哉!快哉!”之感。
然而,作爲史家,左丘明卻又必須“把持”着情感的閘門而不過分,不能像錢鍾書批評的那種“徒以宣洩爲快有如西人所嘲之‘靈魂之便溺’”②錢鍾書:《管錐編》,第1冊,第57—58頁。。這種“恰到好處”,使得左氏在“不經意”間又創造出了一種新史體——“史評體”。所以,對“於敍事之中即見其指”的法則,既應“大體”遵循,又不能拘滯不通“食古不化”,還是應當像王若虛《滹南遺老集• 文辨》所說的那樣:“或問:‘文章有體乎?’曰:‘無。’又問:‘無體乎?’曰:‘有。’‘然則果何如?’曰:‘定體則無,大體則有。’”
(三)現今史著之“語言癥結”回省
拿了黑格爾拈出的“敍事”兩要素,結合《左傳》,轉過來審視現代中國史著。首先可以見出,史家不甚懂得“隱身”“從所寫對象退到後臺”的道理。歷史書寫的性質是敍事的而不是說理的,須站在“第三方”而不是“第一方”,二者立場不同,方法各異,產生的效果便大相徑庭。閱當今史著,其中並非沒有史實,之所以有事實而不夠“公正”,原因之一就在於,史家每每會急不可耐地從“後臺”走到“前臺”充當“主角”,急於做一個歷史的裁判員而不是敍述者。因此,他們總想有選擇的向讀者“灌輸”自己的裁斷亦即他們的理念,而不是讓歷史人物自己開口,忘記了讓理念“融化”於史實之中,把發言權留給史實本身;傳統史學“以言蘊事”的撰史法、歷史人物的對話這一撰史要點,被現代史家剔除於史著之外了!而在傳統史學中,不要說《史記》《漢書》,就連學術史(如《明儒學案》等)、典制史(如《通典》《通志》等)中,都有大量情趣盎然的對話。總之,沒有了語言以及與語言身影相隨的情節,是現今史著的痼疾。
產生這一痼疾之病因,又在於史家特別是通史和斷代史作者的視域重點並不在活生生的人和“人性”上,因此,書寫用語是他們自己的語言而非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的語言。而早在1983年,錢鍾書已經發現了史學界的這個弊端,撰有《一節歷史掌故、一個宗教寓言、一篇小說》一文。他寫道,如果像諾法利斯(H.Novalis,1772—1801)那樣,認爲“歷史是一個大掌故”,或像梅里美(P.Merimee,1803—1870)那樣坦白承認,“我衹喜愛歷史裏的掌故”,這一定會被歷史學家嘲笑。因爲,“在史學家聽來,這是文人們地地道道的淺見薄識”,是“衹追求小‘趣味’,看不到大問題”的表現。①錢鍾書:《錢鍾書散文》,第366頁。[德]黑格爾:《小邏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0),賀麟 譯,第140頁。
那麽,現今史家的“興奮點”在哪裏呢?所關注的往往是諸如生產力、生產關係、歷史“發展階段”、歷史的“進步”還是“倒退”等等“大問題”上。如錢鍾書所說:
在人文科學裏,歷史也許是最早爭取有“科學性”的一門。輕視或無視個人在歷史上作用的理論(transpersonal or impersonal theories of history)已成今天的主流,史學家都衹探找歷史演變的“規律”“模式”(pattern)或“韻節”(rhythm)了。②錢鍾書:《錢鍾書散文》,第366頁。
又因爲,這些論旨又與現實利益緊密粘連。受此影響,現代史家會往往首先認定一些“公理”“公例”作爲“套路”,然後“選擇”那些符合套路的史料去迎合。這就違背了“鑒賞”的原則。而非“鑒賞”必不“公正”,不公正也就不可能客觀。
行文至此,我們可以拿《左傳》的敍事語言與現代史家的著作一番比較。二者給人感覺大不一樣:前者是親切的、和顏悅色的,像拉家常說故事那樣娓娓道來;後者下筆運語則疾言厲色,充斥着“霸氣”,一副板起面孔教訓人的口吻。前者鮮活、靈動,充滿生氣和情趣;後者呆板、乾癟,套話連篇,文字灼眼卻不耐看。歸根結底,《左傳》的核心理念是人性,現代史家則缺乏人性關照,“見物不見人”,所以造成了與《左傳》的巨大差異。本文以《左傳》爲範本,體味其歷史美學之意味,初衷在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