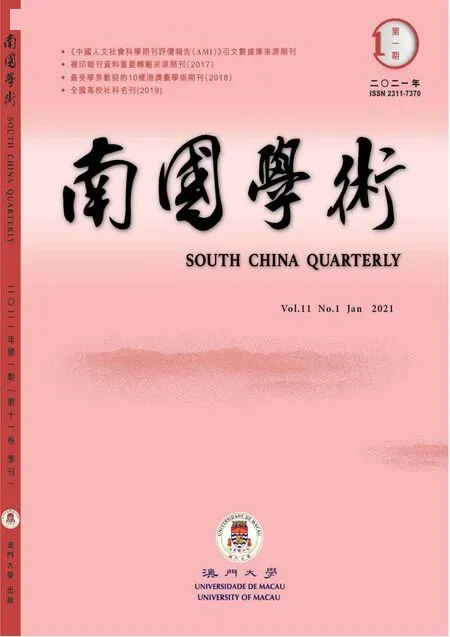清代大陸兵力對臺灣的跨海投送──以乾隆朝平定林爽文的戰爭爲例
2021-12-28李智君
李智君
[關鍵詞] 台灣島 林爽文叛亂 清兵投送與補給
在清代,政府經略外洋島嶼的難度與成本,遠高於久經“教化”的內陸國土。每當遇到突發事件,險惡的海峽海況,不僅是兵力投送與補給的“距離殺手”,同時也是“時間殺手”。乾隆五十一年(1786),臺灣府彰化縣發生了以天地會首領林爽文爲首的叛亂,並迅速向其他縣蔓延,清政府爲此動用大量人力物力,費時十五個月將事件平息。深入考察清政府如何突破“距離殺手”“時間殺手”來完成兵力的跨海投送與補給,如何選擇兵丁、糧餉的補給區,如何選擇長距離投送兵力的路綫,不僅可以從細微處觀察影響戰爭進程的諸因素,也能對現代軍事條件下的兵力投送與補給提供啓示。
一 前沿補給區: 從福建省投送兵力
乾隆五十一年八九月間,閩浙總督常青坐鎮泉州府蚶江港,指揮平定了臺灣府諸羅縣(今臺南市佳里區)楊光勛、楊媽世兄弟爭財引起的械鬥回到省城不久,十一月二十七至二十九日,彰化縣天地會首領林爽文便因臺灣府知府孫景燧取締天地會、逮捕林爽文之叔伯而率衆劫獄,並且“聚衆攻陷城池,殺害官長,阻截文報”。常青一方面於十二月十二日“飛諮水師提臣黃仕簡,率領本標兵一千名,金門鎮兵五百名,南澳鎮銅山營兵五百名,由鹿耳門飛渡前進。派令副將丁朝雄、參將穆素里帶領臣標兵八百名。海壇鎮兵四百名,閩安烽火營兵三百名,聽海壇鎮總兵郝壯猷調遣,由閩安出口,至淡水前進,兩路圍攻。又,參將潘韜、都司馬元勛,帶領陸路提標兵一千名,前赴鹿仔港堵禦”①“乾隆五十一年十二月十二日,閩浙總督常青奏摺”,《清宮宮中檔奏摺臺灣史料》(臺北:故宫博物院,2001),第8冊,第730頁上。,一方面又駐扎泉州,會同陸路提督任承恩居中調度。其實,任承恩本想在第一時間前往臺灣,但因“漳、泉地方,不可一日無大員鎮壓,未敢輕動”②“乾隆五十一年十二月十三日,福建陸路提督任承恩奏摺”,《清宮宮中檔奏摺臺灣史料》,第8冊,第733頁下。,直至常青調金門鎮總兵羅英笈赴廈門彈壓,任承恩纔於十四日登舟,十七日開駕,率一千二百名提標精兵赴臺,由鹿耳門(今臺南市安平港)上岸進剿。
考慮到此次事件非同尋常,僅憑藉福建一省調去的六千兵丁難以勝任,故常青同時諮會兩廣總督孫士毅、浙江巡撫覺羅琅玕,“飭沿海各營及地方官,嚴密防範,毋致匪徒潛竄內地”,並“於附近水師營內酌撥備戰兵二三千名,配齊器械,在交界本境駐扎,以便徵發,亦可藉爲聲援”。③“乾隆五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浙江巡撫覺羅琅玕奏摺”,《清宮宮中檔奏摺臺灣史料》,第9冊,第19頁下。但是,這一“預設機宜,一體防範”的明智之舉,卻因乾隆帝錯判戰勢而擱淺:“看來伊等辦理此事,俱不免張惶失措。此等奸民糾衆滋事,不過么䯢烏合……而漳泉爲沿海要地,其鎮將尚不可輕易調遣,乃任承恩竟欲親往,豈有水陸兩提督俱遠渡重洋,置內地於不顧、辦一匪類之理?”④“乾隆五十二年正月十三日,常青奏摺”,《清宮宮中檔奏摺臺灣史料》,第9冊,第47—48頁。顯然,乾隆將林爽文視爲臺灣府尋常械鬥之匪首,因此對福建水、陸提督置沿海要地於不顧,皆帶兵赴臺,極爲不滿。常青因此被乾隆易職,改任湖廣總督,旋即又命其渡臺視師。
與“軍旅非所素習”的常青相比,新任閩浙總督李侍堯可謂素習軍旅,參加過平定蘇四十三、田五等戰爭;但其“屢以貪黷坐法,上終憐其才,爲之曲赦”⑤《清史稿• 李侍堯傳》(北京:中華書局,1977),第10822頁。,豐富的人生閱歷和過硬的軍事素質,使得作爲前綫總指揮的李侍堯敢於直面問題,而不是對乾隆帝唯命是從。由於乾隆拒絕從福建省外調兵,而閩省兵力畢竟有限,至五十二年(1787)三月初,當福建省內調兵人數達到一萬一千多名時,問題就出現了。對此,李侍堯直陳:“閩兵除先後派調外,內地各營存留較少,且兵律久弛,增調亦不得用,即如臺灣額設戍兵本有一萬餘名,已不爲不多,當林爽文猝起時,竟毫無抵禦,僅柴大紀帶兵千數百名在鹽埕橋堵守,而保護府城,尚係兵民兼用,其餘或係傷亡,或係衝散……是舊有之戍兵已屬有名無實,現在所用衹內地調往之一萬一千餘名。而兩月以來情形又如此將怯卒惰,已可概見,是閩兵竟不必更調。”⑥“乾隆五十二年三月初八日,閩浙總督李侍堯奏摺”,《清宮宮中檔奏摺臺灣史料》,第9冊,第129頁。
福建所調動的駐防滿兵、綠營兵,主要來自福州、金門、南澳、海壇、閩安、延平、建寧、汀州、興化、福寧、桐山、羅源等地,但因漳州“濱臨大海,而臺灣逆匪祖籍多係漳人”①“乾隆五十二年正月初六日,福建漳州鎮總兵官常泰奏摺”,《清宮宮中檔奏摺臺灣史料》,第9冊,第35頁上。,所以,對駐守漳州的兵丁調與不調、調多調少,內中頗多講究。
在常青看來,“漳泉一帶,民俗刁悍,且臺灣逆匪林爽文又係漳人,尤不可不嚴加防範”②“乾隆五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常青奏摺”,《清宮宮中檔奏摺臺灣史料》,第9冊,第7頁上。,因此,常青對漳州之兵“並未調派,示其不動聲色”③“乾隆五十二年正月十二日,常青奏摺”,《清宮宮中檔奏摺臺灣史料》,第9冊,第43頁下。。儘管如此謹慎,乾隆還是要求常青對漳州人,“惟有視其順逆,分別誅賞。斷不存歧視之見,少露形迹,以致漳民疑懼”④“乾隆五十二年正月十五日,常青奏摺”,《清宮宮中檔奏摺臺灣史料》,第9冊,第60頁下。。當臺灣府城、諸羅被林爽文部下包圍,四面楚歌之時,李侍堯一面“仰皇上添派大兵,用全力痛加殲除”,一面考慮調用漳州兵力:“查閩兵存營無幾,未便再調。惟漳州鎮有兵四千,上年因林爽文賊夥多係漳人,是以獨未調用。雖漳州兵素稱強勁,然以派往藍元枚處,俾漳人統漳兵,或未必不得力。而以之派往常青處,臣亦不敢放心。況賊既鴟張,漳州聲息相通。臣現在風聞,有逆首林爽文密遣人來內地勾結會匪之說……是漳屬一帶亦不可不預爲防範。”⑤“乾隆五十二年六月十一日,李侍堯奏摺”,《清宮宮中檔奏摺臺灣史料》,第9冊,第272頁上。與常青相比,李侍堯的策略是,對漳州兵既用又防。漳州府漳浦人藍元枚,則對漳州不同營的軍人區別對待:“漳鎮兵內平和、漳浦二營,難保無會匪在內。其詔安、雲霄二營兵,最爲勇健得用。鎮標中右二營及城守同安二營,亦俱可得力,保無他虞。倘得此等兵五千,不獨可以禦賊,即相機進剿似亦不難。”⑥“乾隆五十二年七月初五日,李侍堯奏摺”,《清宮宮中檔奏摺臺灣史料》,第9冊,第302頁下。久經戎行的福康安,比前三位的方法更爲實用:“再查泉州民人素與漳人有隙。凡係居住臺灣之泉人,多有充當義民者,殺賊保莊,倍加勇往,賊匪不敢輕犯。因思泉州地方風俗剽悍,向有械鬥滋事之案。若此時召集泉州鄉勇,既可隨同剿賊,又可安戢地方。臣於到閩時,先遣妥人密辦,及行過泉州,即有鄉勇多人懇請隨征進剿。觀其情辭懇切,當經面加撫諭,飭委同安縣知縣單瑞龍、教諭郭廷筠揀選身家殷實之人,互相保結,准其前往。一時報名投效者絡繹不絕,臣於此內擇其精壯者二千四百餘名,商同李侍堯酌賞安家口食銀兩,令其隨往。又恐內地漳人聞知疑慮,復遣妥員召集漳州鄉勇百餘名,以泯形迹。”⑦“乾隆五十二年十月二十四日,福康安奏摺”,《清宮宮中檔奏摺臺灣史料》,第9冊,第668頁。可見,隨着臺灣戰爭形勢逐漸吃緊和兵力需求的增加,漳州兵丁經歷了被整體排除到分類選用的過程。
戰爭初期,軍隊糧餉也是從福建省內調撥。但福建的糧食供應狀況並不樂觀,“第上游延、建、汀、邵等六府州,俱係崇山疊巘,挽運維難,多費腳價。下游漳、泉等府,雖有存穀,亦須酌留地方,以備緩急,未便盡數用完。兼以各營兵糧,向係臺灣各縣解運穀石供支,今臺地無穀可解,並應解上年之穀亦尚未結清,又須內地倉穀動支。且漳泉民食,向恃臺米販來接濟,今臺米稀少,內地糧價漸增,將來恐不免平糶,則倉儲不敷應用”⑧“乾隆五十二年四月二十六日,李侍堯奏摺”,《清宮宮中檔奏摺臺灣史料》,第9冊,第197頁下。。乾隆五十一年,福建存糧嚴重不足,通省缺穀五十四萬餘石。⑨“乾隆五十二年三月二十八日,李侍堯奏摺”,《清宮宮中檔奏摺臺灣史料》,第9冊,第151頁上。在糧餉的供應方面,乾隆與李侍堯的看法相同,即寬爲預備。乾隆五十二年二月十九日,福建省內的糧餉調撥已經出現問題,李侍堯奏報:“今內地所宜接應者,口糧最爲緊要,臣詢常青、徐嗣曾已飭各州縣碾米四萬五千石,分貯廈門、泉州等處,現在尚未解到,臣一面嚴催,以備陸續應用,不致有誤。”⑩“乾隆五十二年二月十九日,李侍堯奏摺”,《清宮宮中檔奏摺臺灣史料》,第9冊,第108頁。隨着戰爭規模的進一步擴大,福建省內的糧餉消耗與日俱增,至四月初八日,總計消耗的糧餉是:“自上年十二月起,陸續解往銀已二十萬餘兩,米一萬九千餘石,又委員齎銀三萬兩前往買米,計可得一萬數千石,近又准常青諮取銀十萬兩,並淡水同知徐夢麟帶往銀一萬兩。”⑪“乾隆五十二年四月初八日,李侍堯奏摺”,《清宮宮中檔奏摺臺灣史料》,第9冊,第164頁。這衹是臺灣前綫的糧餉消耗。加上運腳及置辦裝備的費用,戰爭消耗會更多。因此,僅從福建來補給糧餉,已無法維持臺灣戰爭所需,“所有糧餉等項……臺灣道府,紛紛請撥前來”①“乾隆五十二年三月十九日,李侍堯奏摺”,《清宮宮中檔奏摺臺灣史料》,第9冊,第139—140頁。。事實上,戰爭爆發後,不僅一萬多官兵需要吃飯,大量的難民也需要政府救濟,糧食缺口很大。“又稟稱彰化縣屬,僅存鹿仔港一處尚在固守,各村莊男女老幼,咸來避匿,不下十萬餘人,無處得食,似應仿照災賑之例,量爲賑恤。”②“乾隆五十二年四月初八日,李侍堯奏摺”,《清宮宮中檔奏摺臺灣史料》,第9冊,第164頁上。在這樣的背景下,從福建省外補給兵力已是大勢所趨。
在論及閩兵的戰力時,儘管李侍堯有“潮州、碣石二鎮既兵較閩兵精銳”③“乾隆五十二年三月初十日,李侍堯奏摺”,《清宮宮中檔奏摺臺灣史料》,第9冊,第132頁上。、閩兵“將怯而卒惰”等評價,甚至阿桂還有如下推測之辭:“前後調往官兵雖已不少,然其中如福建本省兵丁竟難深信。即如該提鎮等遇賊打仗,屢報多兵不知下落,此項兵丁豈盡死傷逃亡,未必不因與賊同鄉,遂爾附從。”④“乾隆五十二年九月初二日,阿桂奏摺”,《清宮宮中檔奏摺臺灣史料》,第9冊,第500頁上。但縱觀十五個月的戰爭,無論是參與戰爭的兵丁數量、戰鬥次數還是兵力投送的及時程度,福建兵丁無疑是作戰的中堅力量。乾隆帝可以憑藉其雄厚的國力,從秦嶺—淮河以南的廣大地域補給兵力,但當臺灣府城和諸羅出現危機時,終究緩不濟急,還得從福建緊急調兵。糧食亦如此,如臺灣村莊因戰爭俱遭焚搶,民衆嗷嗷待哺時,也首先是從福建調糧撫恤。⑤“乾隆五十二年四月十六日,李侍堯奏片”,《清宮宮中檔奏摺臺灣史料》,第9冊,第181頁下。
二 協防補給區: 從粵浙兩省投送兵力
原本在乾隆帝眼裏,林爽文“不過么䯢小醜”⑥“乾隆五十二年二月初八日,兩廣總督孫士毅奏摺”,《清宮宮中檔奏摺臺灣史料》,第9冊,第98頁上。,但三個月後的二月二十七日,他驚訝地發現,“林爽文竟有自稱爲王及僭立年號之事”⑦“乾隆五十二年二月二十九日,李侍堯奏摺”,《清宮宮中檔奏摺臺灣史料》,第9冊,第124頁上。——成了自立爲王的割據者。顯然,問題的性質發生了根本性轉變,乾隆的用兵策略也需要作出調整。然而,此時的福建不僅無兵無糧可調,已調往臺灣的官兵也解決不了問題,故李侍堯不得不再次提議從鄰省徵調兵力。
(一)從廣東調運兵力
除乾隆皇帝外,常青、李侍堯、福康安、孫士毅,都是決定此次臺灣戰爭走向的勝負手。作爲兩廣總督,孫士毅衹是毗連省份兵力補給的調度者,但因廣東“潮州、碣石二鎮兵既較閩兵精銳,且地近泉廈,較之閩省自延、建調來更爲近便”⑧“乾隆五十二年三月初十日,李侍堯奏摺”,《清宮宮中檔奏摺臺灣史料》,第9冊,第132頁上。,因此,他調度的重要性僅次於閩浙總督。其實,從戰爭伊始,孫士毅就未雨綢繆,從廣東省城急赴潮州調度兵力,但因乾隆錯判戰爭形勢,孫士毅反被羞辱一番:“是孫士毅不但不諳軍務,而於事體輕重亦毫無定見,朕轉不值加以責備,而該督辦事識見如此,適足爲朕所輕矣!”⑨“乾隆五十二年二月初一日,孫士毅奏摺”,《清宮宮中檔奏摺臺灣史料》,第9冊,第90頁上。
等孫士毅迅速從潮州趕回廣州後,乾隆又以“閩粵境壤毗連,難保無逸匪竄往,自當督率各隘口,嚴密堵拿。況惠、潮民人入天地匪會者不少,必須徹底查辦,淨絕根株。其從外竄逃入境及內地勾引入會之人,均應逐一搜捕,不留餘孽。若孫士毅往來查察,督率緝捕,豈不較總兵彭承堯及道府等更爲有益”等理由,再把孫士毅申飭一番:“乃該督將一切稽查防範事宜,交與署提督彭承堯料理,率行回省,全不知事體緩急,因時制宜,何以拘泥錯謬若此,著傳旨申飭。”⑩“乾隆五十二年二月二十七日,孫士毅奏摺”,《清宮宮中檔奏摺臺灣史料》,第9冊,第122頁。其實,無論是自粵省投送兵力,還是護送貴州、廣西兵力過境,孫士毅都做到了滴水不漏。
因孫士毅籌劃有方,加之投送距離短,水運便捷,故從廣東所調之兵力,是一支除福建兵力外,補給和投送最快捷的部隊。首批四千名粵兵“定於三月十六日即令頭起官兵自潮起程,每起二百五十名,間一日行走。若由水路赴廈門、蚶江等處,海洋風信靡常,不免耽延時日。查自粵省黃岡入閩省詔安境,相去止數十里,自詔安至廈門、蚶江等處,亦止數日可到,是以統由黃岡陸路出境。照依李侍堯派定數目,以二千五百名赴廈門,一千五百名赴蚶江,配船渡臺。”①“乾隆五十二年三月十四日,孫士毅奏摺”,《清宮宮中檔奏摺臺灣史料》,第9冊,第138頁。原計劃兵分兩處的粵兵,因乾隆皇帝“以臺灣府城兵力尚單,令將調赴鹿仔港之粵兵一千五百名,改由廈門齊赴府城”②“乾隆五十二年四月十一日,李侍堯奏摺”,《清宮宮中檔奏摺臺灣史料》,第9冊,第171頁下。,該四千兵於四月中旬全部到達臺灣府城③“乾隆五十二年五月二十五日,李侍堯奏摺”,《清宮宮中檔奏摺臺灣史料》,第9冊,第252頁下。。由於首批四千粵兵,主要從毗連閩省的潮州府各營調撥,當六月初八日常青再請調粵兵時,孫士毅已經提前預備了兩千名,即督標兵一千,提標兵五百,左翼鎮兵五百④“乾隆五十二年六月初九日,孫士毅奏摺”,《清宮宮中檔奏摺臺灣史料》,第9冊,第268頁下。,駐扎在潮州貼防,接到調令即迅速啓程,六月十三日便全部入閩境,前後衹用了五天時間。其後調的四千名,即督標兵一千,右翼鎮兵一千,提標兵五百,左翼鎮兵五百,增城營兵三百,惠來營二百,肇慶、羅定、惠州三協共兵五百,於八月初二到閩省。乾隆准調的粵省駐防滿兵一千五百名⑤“乾隆五十二年七月初二日,孫士毅奏摺”,《清宮宮中檔奏摺臺灣史料》,第9冊,第294頁下。,也於七月二十八日入閩省詔安境⑥“乾隆五十二年八月初八日,孫士毅奏摺”,《清宮宮中檔奏摺臺灣史料》,第9冊,第393頁上。,九月初三日到廈門⑦“乾隆五十二年八月十七日,李侍堯奏摺”,《清宮宮中檔奏摺臺灣史料》,第9冊,第453頁下。。七月二十六日,鹿港藍元枚告急,諭令孫士毅又從潮州調兵一千,約於八月二十日前到閩省。至此,粵省調兵人數已達一萬二千五百人。
雖然粵東潮州一帶,在明朝還是福建漳、泉一帶糧食的供應地之一,但至清代,“廣東所產之米,即年歲豐收,亦僅足供半年之食”⑧雍正《廣西通志• 藝文》,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21頁b。,而粵東缺糧更加嚴重,“東粵少穀,恒仰資於西粵”⑨〔清〕屈大均:《廣東新語• 食語• 穀》,清康熙水天閣刻本,第1頁a。,因此,此次戰爭中,朝廷並未從廣東調撥米穀,主要是調撥餉銀。乾隆五十二年四月初五日上諭:“因思廣東近在鄰省,粵海關稅及鹽課銀兩俱屬充裕,著傳諭孫士毅於此二項內不拘何項,酌撥銀三四十萬兩,一面奏聞,一面即行派委妥員,迅速解往閩省交界,交與李侍堯,派員接押,以備應用。”⑩“乾隆五十二年八月十六日,李侍堯奏摺”,《清宮宮中檔奏摺臺灣史料》,第9冊,第183頁下。從廣東調撥的四十萬餉銀,主要從粵海關稅中支取。⑪“乾隆五十二年四月二十三日,佛寧奏摺”,《清宮宮中檔奏摺臺灣史料》,第9冊,第189頁下。八月,朝廷諭令:“酌撥粵海關五十二年分稅銀二十萬兩,解閩備用。”⑫“乾隆五十二年八月十五日,粵海關監督佛寧奏摺”,《清宮宮中檔奏摺臺灣史料》,第9冊,第437頁上。其後,朝廷又命廣東調撥地丁鹽課銀五十萬兩,粵海關本年稅銀五十萬兩,解往閩省,並於五十三年(1788)四月初八日全數運交閩省泉州總局兌收。⑬“乾隆五十三年四月初八日,孫士毅奏摺”,《清宮宮中檔奏摺臺灣史料》,第10冊,第466—467頁。廣東省解閩餉銀共計二百萬兩。其中一半的銀兩由粵海關撥出,三分之一由地丁鹽課銀內撥出。另外,通過兵丁隨身攜帶及三次額外運送,廣東共向福建調運火藥二十萬觔。⑭“乾隆五十二年八月二十九日,孫士毅奏摺”,《清宮宮中檔奏摺臺灣史料》,第9冊,第494頁上。
(二)從浙江調運兵力
李侍堯原計劃調四千浙江官兵,其中“提標右營兵五百名,鎮海營兵五百名,黃岩鎮標兵一千名,溫州鎮標暨里安營兵一千名。又添調距閩較近之衢州鎮標兵一千名”⑮“乾隆五十二年四月初二日,浙江提督陳大用奏摺”,《清宮宮中檔奏摺臺灣史料》,第9冊,第157—158頁。。但在乾隆看來,“浙省兵丁素性懦弱……閩兵攻剿尚不能得勝,何況浙省之兵,更不如閩省,調往協剿,豈能得力?”⑯“乾隆五十二年四月十二日,陳大用奏摺”,《清宮宮中檔奏摺臺灣史料》,第9冊,第173頁。因此,李侍堯衹調來了三千浙省兵丁。另外一千兵丁,則被閩省駐防旗兵所替代。其實,這部分常青早想調動的旗兵,之前卻被乾隆以“恒瑞旗兵更不宜輕動”⑰“乾隆五十二年正月十三日,常青奏摺”,《清宮宮中檔奏摺臺灣史料》,第9冊,第49頁上。爲由制止。再次徵調時,臺灣的戰火已成燎原之勢。可見,在乾隆心目中,衹有滿兵纔是彈壓地方最值得信賴的力量。三千浙江兵丁,由藍元枚帶領二千名,於五十二年四月初七日,由蚶江配渡前往鹿仔港(今臺灣省彰化縣鹿港鎮)。由魏大斌帶領一千名,於四月二十九日,由廈門前往臺灣府城。①“乾隆五十二年五月,李侍堯奏摺”,《清宮宮中檔奏摺臺灣史料》,第9冊,第211—212頁。從浙江僅有的一次調兵來看,受交通條件的制約,其兵源主要分佈在海港附近及與閩省毗連州縣。
乾隆五十二年四月二十六日,李侍堯奏請撥浙米十萬石備用②“乾陵五十二年四月二十六日,覺羅琅玕奏摺”,《清宮宮中檔奏摺臺灣史料》,第9冊,第200頁上。。乾隆五十一年,浙江省實存倉穀“一百三十萬石”,從中調撥十萬石米自然不是問題。考慮到“此項米石若於通省動撥,由陸路起運,須用人夫背送,腳費浩繁,且道里綿長,有稽時日”,因此,浙江巡撫覺羅琅玕認爲:“應即由海運赴閩,庶爲省便。”故浙江調取的十萬石米,主要由臨近港口各府碾備:“飭行藩司,於乍浦口附近之杭州、嘉興、湖州三府屬,先爲酌撥八萬石,於寧波、溫州二海口附近之寧波、紹興、溫州、台州四府屬,酌撥穀八萬石,即令預行碾備,以免臨期遲延。”③“乾陵五十二年四月二十六日,覺羅琅玕奏摺”,《清宮宮中檔奏摺臺灣史料》,第9冊,第201頁下。
十萬石米,要從浙江的乍浦、溫州、寧波運往福建廈門、泉州,海上運輸難度可謂不小。當時每隻海船約能載五百石米,運送十萬石就需二百隻船。而在浙江沿海衹雇到百餘隻海船,且“內有挑出陳舊不堪應用者二十餘隻”,船隻數量不足。考慮到“乍浦海口與江南上海口相距百餘里,往來船隻一潮可至,甚爲近便”,琅玕“徑行飛飭江蘇松太道,立即於上海口岸代雇船隻”,該道雇覓海船三十隻,纔得以解燃眉之急。④“乾陵五十二年五月初三日,覺羅琅玕奏摺”,《清宮宮中檔奏摺臺灣史料》,第9冊,第204頁下。
六月十三日,李侍堯諮會琅玕,動撥浙省庫項銀六十萬兩,解閩備用。⑤“乾隆五十二年六月十八日,覺羅琅玕奏摺”,《清宮宮中檔奏摺臺灣史料》,第9冊,第281頁下。八月初八日,又於兩浙鹽課項下撥銀八十萬兩,解往閩省。⑥“乾隆五十二年八月初六,覺羅琅玕奏摺”,《清宮宮中檔奏摺臺灣史料》,第9冊,第389頁上。十月十二日,又接諭旨,於浙江地丁、漕項、鹽課三項內通融撥銀五十萬兩,又浙海關本年稅銀四萬兩。此五十四萬兩銀,於十月十九日啓程解閩。其後,又應福建兌換錢文的要求,兌換五萬四千餘串,運往上海,附搭米船解閩。⑦“乾隆五十二年十月二十八日,覺羅琅玕奏摺”,《清宮宮中檔奏摺臺灣史料》,第9冊,第688—689頁。至此,浙江共計向福建省撥銀超過二百萬兩。
粵、浙兩省雖非主戰場,但從臺灣竄逃回來的林爽文兵丁有可能從廣東、浙江上岸,因此,兩省的首要任務是協防,其次纔是補給兵力。兩省雖同處協防補給區,但兩省兵力補給能力卻各有所長。兵丁補給方面,廣東的十二萬五千兵丁與浙江的三千兵丁,完全不是一個數量級。餉銀方面,浙江與廣東持平。從浙江調撥火藥十萬觔⑧“乾隆五十二年五月二十九日,覺羅琅玕奏摺”,《清宮宮中檔奏摺臺灣史料》,第9冊,第257頁,僅僅是廣東的一半,但在糧食供給方面,浙江強於廣東省。總之,雄厚的經濟基礎,毗連福建的地理區位,便捷的水運條件,使廣東、浙江兩省成爲此次戰爭中僅次於福建的第二兵力補給區。而在兩省內部,受空間經濟規律的制約,廣東潮州和浙江沿海,則是主要的兵力補給區。
三 周邊補給區: 從長江流域調兵運糧
從四川、湖北、湖南、江西、江蘇、廣西、貴州等省調運兵力,並向臺灣投送,主要有兩條運輸路綫:一是由長江進入鄱陽湖,沿撫河逆流而上,至江西建昌府新城縣五福鎮,再由旱路至福建省邵武府光澤縣水口鎮,順閩江而下,經海路至泉州晉江蚶江港和廈門港;二是順長江而下,出江口至江蘇上海港、浙江乍浦港,再沿近海航綫南下至蚶江和廈門。在臺灣海峽,則由蚶江港—鹿仔港、廈門港—臺灣府城港四個港口對渡。
(一)從江西調運糧餉
從江西省調米,與李侍堯奏請從廣東、浙江調兵調糧不同,完全是乾隆籌慮的結果:“臺灣府城,現在兵數陸續加增,鄉勇義民人數本衆,皆須按日支給口糧,現又有投順者二千餘人以及無食難民,亦須量給養贍,自應寬裕接濟……今思江西素稱‘產米之鄉’,且與閩省接壤,著傳諭何裕城,將該省倉穀即行碾米十餘萬石,派員迅速運往福建。應由何路運往,及閩省由何處接收,方爲妥便之處,並著何裕城劄知李侍堯妥協酌商。”江西所調之米,主要從水運較爲便捷的府縣內調撥,據何裕城奏:“江西省之南昌、瑞州、臨江、吉安、撫州、建昌、廣信、饒州、南康等府所屬各縣,雖不皆毗連閩省,尚俱附近水口。隨按其倉糧存數之多寡,量行派撥,計動支穀三十萬石,碾米十五萬石,每二萬五千石爲一起,分作六起,委官六員,按起領運。”①“乾隆五十二年五月初八日,江西巡撫何裕城奏摺”,《清宮宮中檔奏摺臺灣史料》,第9冊,第216頁。對乾隆提出的“何路運往”問題,由於經“江西省入閩之路有三,其廣信府之鉛山縣一路,有陸程四五站;寧都州之瑞金縣一路,更係山僻小路,挽運維艱;惟建昌府之新城縣,由五福地方陸運八十里,至閩省邵武府光澤縣之上水口,即可用竹簰及小船駁運,此係向來解運銅鉛之大路。由上水口再四十里至光澤縣,又可換大船運至省城,再用海船裝運至泉、廈等”,因此,何裕城與李侍堯商議,江米擬由新城五福運往邵武光澤,接收地是光澤縣的上水口。據李侍堯奏:“江省之米應在光澤縣之上水口交兌。查五福起旱,係江省新城縣地方,雇夫挑運,應由江省辦理,自上水口雇船及竹簰駁運,應由閩省辦理。仍各委大員在上水口公同交收,所有腳價各歸本省報銷。”②“乾隆五十二年五月十五日,李侍堯奏摺”,《清宮宮中檔奏摺臺灣史料》,第9冊,第232—233頁。
從江西到達福建,除水陸聯運外,還可江海聯運。但問題是江西人沒有海運的經驗,正如何裕城所云:“臣雖查知米由長江裝運,乘此夏多南風時日,頗能迅速,而上海關以外,海道情形,臣未經親歷,其或不及陸運之穩,或較之陸運加速,臣不能深知,是以未敢輕議。”③“乾隆五十二年五月初八日,何裕城奏摺”,《清宮宮中檔奏摺臺灣史料》,第9冊,第217—218頁。江西的米運至江蘇上海港後,卻無海船可用。究其原因,是時任兩江總督的李世傑爲了邀功請賞,主動奏請由江蘇向閩省撥米十萬石。這樣一來,江蘇海船自己尚且不敷用,哪裏還有船隻幫江西運米。何裕城因運糧遲誤,被乾隆痛斥:“總由何裕城往返劄商,辦理錯悮,又不酌定何路早行具奏,業經將何裕城交部議處。”④“乾隆五十二年七月十八日,何裕城奏摺”,《清宮宮中檔奏摺臺灣史料》,第9冊,第328頁下。
江西還協濟閩省六萬觔火藥⑤“乾隆五十二年十一月初一日,何裕城奏摺”,《清宮宮中檔奏摺臺灣史料》,第9冊,第689頁下。,又遵旨動撥江西地丁銀五十萬兩,九江關稅銀三十萬兩,解赴閩省。其中,“江西地丁銀兩,向係撥充本省及雲貴兵餉、雲南銅本等用,自應酌撥歸款。請於該省漕項銀內撥銀十萬兩,九江關本年稅銀內再撥銀三十萬兩,滸墅關本年稅銀內撥銀十萬兩,共銀五十萬兩,抵補江西動撥之數”。⑥“乾隆五十二年十月初六日,經筵講官太子太保文華殿大學士管理戶部事務和珅等奏摺”,《清宮宮中檔奏摺臺灣史料》,第9冊,第610頁。
按理,從江西調兵,比從四川、貴州等地調兵要近便。常青也動過這個心思。據李侍堯奏:“至常青摺內有增調江西、廣西兵各三千之請。而聲敍柴大紀諮文,又有增兵一萬之請,雖覺迹涉張惶,然看來亦不得不再爲接濟。與其零星續派,自不如用大力,以期一舉撲滅之功。查江西贛州兵素稱強勁,且距閩省路亦近便,粵西之兵亦尚可用,如蒙皇上照常青所請之數調派三千前來,合之臣此次續調至閩兵三千,則兵力亦已壯盛。”⑦“乾隆五十二年八月初九日,李侍堯奏摺”,《清宮宮中檔奏摺臺灣史料》,第9冊,第404—405頁。李侍堯奏請調用江西之兵,卻並未曾先行諮會江西巡撫何裕城,何九月初四日接到暫停調兵的諭旨,纔知有此事,自然沒有調兵之舉,算是又少犯一個錯誤。不過乾隆對江西、廣西兵的輕視,估計讓何裕城很沒面子:
以江西、廣西之兵在綠營中最爲無用。若派調前往剿捕,豈能得力?且常青請調官兵,原爲救援諸羅起見,此等無用之兵,若資以剿賊,適足虛糜兵餉,輕試賊鋒,於事何益……江西之兵較廣西更爲平常,且此時添調之兵,不爲不多,斷無庸派往。著傳諭何裕城如常青已經檄調該撫辦理,尚未啓程,即可停止。如業已派撥啓程,行抵何處,即於何處撤回,毋庸前進。所有兵丁往返資給費用,俱著令常青按數罰出。其已調之廣西兵到,若能剿捕得力則已,如不能得力,所有一切支給費用,亦着常青照數罰出。①“乾隆五十二年九月初十日,孫士毅奏摺”,《清宮宮中檔奏摺臺灣史料》,第9冊,第526頁。
孫士毅是九月初九日接到諭旨的,而此時廣西三千兵,已經分六起全數出境。陰差陽錯,比江西兵稍強一點的廣西兵,最終得以成行,而江西卻沒有一兵一卒前往臺灣。
(二)從江蘇調運糧餉
與江西相比,因爲有海道相通,從江蘇調糧調兵運往福建無疑要便捷很多。因此,看到浙江、江西先後運米協濟閩省,兩江總督李世傑、江蘇巡撫閔鶚元自然不甘人後,恭請動撥江蘇省米運閩:“蘇省之松、太一帶海口,與浙省乍浦毗連,時有商船往來閩廣,海道順利。臣等同司道悉心商酌,請於就近之蘇州、松江、常州、鎮江、太倉各屬常平倉貯項下,動撥穀二十萬石,碾米十萬石,運赴閩省泉州、廈門一帶交收,聽候閩浙督臣李侍堯酌量撥用。”“至運裝船隻,必須往來閩廣之船,認識沙綫,方堪應用。現在松、太海口船隻,協濟浙省運米。所有江省米十萬石,應俟浙米起運後,將江、浙兩處續到海船,通融挑備,仍分作兩起,先後啓行。瞬屆夏杪秋初,北風得令,更可一帆直達。”面對李世傑等人的急功行爲,乾隆硃批:“雖屬爾等急公之見,但未慮及警動人心矣。”②“乾隆五十二年五月十八日,兩江總督李世傑、江蘇巡撫閔鶚元奏摺”,《清宮宮中檔奏摺臺灣史料》,第9冊,第236—237頁。隨後把球踢給了李侍堯:“據李世傑等奏請,碾米十萬石運閩,以濟軍需一事,著李侍堯查看情形,如不須鄰省協濟,即諮會李世傑等停止起運。倘閩省糧米尚有爲敷,亦即諮會李世傑等,令其委員押運赴閩。”儘管已得到浙江、江西三十一萬石米的協濟,閩省之米頗覺充裕,但久經沙場的李侍堯深知,戰場風雲變化無常,因此奏報:“近接常青知會,以賊匪甚多,又請添兵剿捕,則米糧自以多備爲要。兼以臺灣支給鄉勇,撫恤難民等項需米既多。且向來內地各營兵米多由臺灣運來支放,今不惟臺灣無米運來,而臺灣班兵轉須內地運米往給,兩面核算,又增八萬餘石之用。又,近日漳、泉一帶,雨澤較少,晚禾尚未栽插,將來不免平糶等事,則閩省籌備米石自以多多益善。臣再四籌酌,江蘇省既碾備米十萬石,似應即令陸續委員運閩,更爲有備。”③“乾隆五十二年六月初八日,李侍堯奏摺”,《清宮宮中檔奏摺臺灣史料》,第9冊,第266頁。
在江蘇,有人恭請撥米,自然有人主動請纓。江南提督陳傑早在李世傑等之前,就曾奏請:“念奴才年雖已過六十,自揣精力尚壯,馬上步下,不讓少年。雖未曾出兵渡臺,然江、浙、閩省海面皆曾走過,較之未曾登舟者,自然少知風水之性。況奴才在東南二十餘年,所有南方風土人情,略知大概。惟有叩求皇上天恩,賞准奴才帶兵前往臺灣,盡力殺賊,俾稍抒奴才憤恨之心。斷不致如總兵郝壯猷、把總高大捷之怯懦畏葸,辜負聖恩者。惟是若仍用福建之兵,語言先自不通,兵將未能一心,仍恐不能得力。奴才現在水陸兩標內,密行挑兵一千二百名,將備九員,整束行裝,恭候命下。”乾隆硃批:“孟浪不堪。”④“乾隆五十二年五月初六日,江南提督陳傑奏摺”,《清宮宮中檔奏摺臺灣史料》,第9冊,第209—210頁。因此,未從江蘇徵調一兵一卒。
江蘇向福建運送錢文十六萬串。以每庫平紋銀一兩,易換定串錢九百九十文計算,共計用銀十六萬一千六百十六兩。其中的十二萬串,價值銀十二萬一千二百一十二兩,於滸關稅銀內動支,四萬串錢文於寶蘇局存貯中調取。⑤“乾隆五十二年十一月十一日,江蘇巡撫閔鶚元奏摺”,《清宮宮中檔奏摺臺灣史料》,第9冊,第721—722頁。
(三)從四川運糧調兵
從四川運米,是乾隆爲穩定閩省人心、摧垮林爽文心理防綫而實施的心理戰術:“李侍堯接奉此旨,不妨將現在又於江南、川省運米數十萬石前來接濟之處,先令閩人知之,俾軍民口食有資,市價不致踴貴,方爲妥善。”⑥“乾隆五十二年六月二十八日,兩江總督李世傑、江蘇巡撫閔鄂元奏摺”,《清宮宮中檔奏摺臺灣史料》,第9冊,第288頁上。李侍堯更是直言:“是米之在漳、泉,固所以綏靖地方;而米之到臺灣,尤足散賊黨而省兵力。”⑦“乾隆五十二年八月初二日,李侍堯奏摺”,《清宮宮中檔奏摺臺灣史料》,第9冊,第380頁下。但該戰術實行的前提是,四川有米可運。“川省素爲產米之區,連歲收成豐稔,積儲較裕。”⑧“乾隆五十二年六月二十八日,李世傑、閔鶚元奏摺”,《清宮宮中檔奏摺臺灣史料》,第9冊,第288頁上。四川總督保寧於六月二十一日奉上諭,運川米二十萬石,續令再採買三十萬石。此五十萬石米,除採買三萬八千石米外,其餘四十六萬二千石米,考慮到“採買市米,雖似便宜,但川省民間素鮮蓋藏,目下早稻甫經收割,未能集輳一時,採買多米,市價易致騰踴。若倉穀則取之於官,亦可不動聲色而立辦。將來遵旨於暇時買補辦理,甚屬從容。且新米性帶潮濕,遠運恐非所宜,亦不若倉穀乾結,可無黴變之虞。而加緊碾米,尚爲迅速”,因此,共調撥長江幹流及岷江、沱江、嘉陵江等沿岸州縣倉穀九十二萬四千石,碾成米後用小船運至重慶,換裝大船,由川江東下。①“乾隆五十二年七月二十日,四川總督保寧奏摺”,《清宮宮中檔奏摺臺灣史料》,第9冊,第338—339頁。頭運米於七月十九日開行,時值秋季,“川江秋水方盛,順流東下,雖風水靡常,舟行總屬迅速。其自漢口而下,川船素未經行,必須換船前進”②“乾隆五十二年七月十八日,保寧奏摺”,《清宮宮中檔奏摺臺灣史料》,第9冊,第334頁上。,因此,長江中下游的船舶,主要由湖北備辦,運至江蘇上海,則再換海船,運往福建。五十萬石米還沒有完全運到福建時,臺灣戰爭已經結束,真正運到福建的米衹有三十二萬石,其餘十八萬石,諭令江蘇“酌量截留,以抵買補倉儲之用”。③“乾隆五十三年三月初四日,閔鶚元奏摺”,《清宮宮中檔奏摺臺灣史料》,第10冊,第361頁下。
可見,此次調運川米,不僅是臺灣戰爭期間調糧數量最多的一次,也是運輸距離最長的一次。從長江頭運至長江尾不說,還要跨越三千餘里海面,從上海海口運至泉州、廈門,用時長達九個月,還衹運完了其中的三分之二。“千里不運糧,百里不運草。”川米的運費比米價低不了多少。因此,此川米的真正價值不在於其食用價值,而是其所具有的綏靖漳泉地方、渙散臺灣叛亂者軍心的戰略價值。這正是乾隆調川米的初衷:“令李侍堯多備糧餉,足敷十萬官兵之用,使外間相互傳說,賊人聞風膽落。”④“乾隆五十二年八月十八日,福康安奏摺”,《清宮宮中檔奏摺臺灣史料》,第9冊,第463頁上。
與運米不同,乾隆從四川調兵,絕對出於戰爭需要。保寧等於乾隆五十二年八月十一日接六百里加急諭旨:“臺灣前後所調兵丁不爲不多,但該處山深箐密,路徑崎嶇,因思川省屯練、降番,素稱矯捷,前曾經調往甘省剿捕逆回,甚爲得力,著傳諭保寧即於屯練、降番內挑選二千名,並揀派曾經行陣、奮勇出力之將領張芝元等分起帶領,從川江順流而下,由湖北、江南、浙江一路前赴閩省。”⑤“乾隆五十二年八月十二日,鄂輝、保寧、成德奏摺”,《清宮宮中檔奏摺臺灣史料》,第9冊,第430、431頁下。屯練、降番是四川土兵。乾隆征廓爾喀,討安南,都有土兵隨征,一向以驍勇善戰著稱。兩千名川兵中,屯練一千六百名,降番四百名,於八月二十一至二十七日從成都開行,九月初一日至初七日自重慶換船進發。川江水道此時正忙於運送川米,米、兵爭船嚴重。解決之道是米讓兵:“倘番練等行至重慶,尚無多餘船隻,即將復運三十萬石尾幫之船,暫停運米,先盡兵行,再將續到之船隨後運米,亦不致守候稽延。”⑥“乾隆五十二年八月十二日,鄂輝、保寧、成德奏摺”,《清宮宮中檔奏摺臺灣史料》,第9冊,第430、431頁下。爲了保障屯番在川江險灘航行的安全,“兵番等均可於過灘時,上岸行走,不過一二里,仍即下船”⑦“乾隆五十二年八月二十一日,保寧奏摺”,《清宮宮中檔奏摺臺灣史料》,第9冊,第469頁上。。川兵原本擬定的行進綫路,即“由長江行走,經過鎮江至嚴州、衢州等處,計程有二千三百餘里。若由江西玉山至常山,徑至衢州,計程止有一千三百餘里,路程較近”,因此改道行進。又經何裕城諮會修正,行程更爲便捷:“川兵如不經由浙江,即從河口鎮起旱,由鉛山過嶺,徑入閩省之崇安縣,達建寧府前進,較之浙省所擬路程又可少行五百六十餘里,兼可少過一嶺,更爲便捷。”⑧“乾隆五十二年九月十二日,李世傑奏摺”,《清宮宮中檔奏摺臺灣史料》,第9冊,第534頁。川兵經由此綫行進,於十月初一至初八日到達崇安縣。⑨“乾隆五十二年十月初十日,何裕城奏摺”,《清宮宮中檔奏摺臺灣史料》,第9冊,第616頁下。十月十六日至二十三全部抵達蚶江。全程用時五十五天,衹相當於運糧時間的五分之一。由此可見,四川土兵乃戰爭前綫之急需力量。
(四)從湘、鄂、黔調運兵糧
湖南、湖北協濟福建米穀各十萬石,完全是湖廣總督舒常等人邀功請賞的結果:“湖北省早稻豐收,秋成可卜大有,現於臨近水次州縣,動支倉穀二十萬石,碾米十萬石,分作四起,委員由江西新城縣五福地方,旱運赴閩。”⑩“乾隆五十二年七月二十日,何裕城奏摺”,《清宮宮中檔奏摺臺灣史料》,第9冊,第335頁上。又,“湖南省年歲豐稔,存穀尚多……附近水次二十五州縣,約存穀四十餘萬,足敷撥運。隨各按倉貯多寡酌量派定,共動穀二十萬石,碾米十萬石”。乾隆之所以同意撥運,是因爲“此等運閩米石,原係預爲儲備,止須源源接運,以備應用,本非必需同時運到也”①“乾隆五十二年八月初十日,浦霖奏摺”,《清宮宮中檔奏摺臺灣史料》,第9冊,第410頁上。,因此,湘、鄂米穀就慢慢悠悠,從江西五福運往福建,以至於臺灣戰爭“大功告蕆”,大部分楚米還在路上。
徵調湘、鄂、黔兵丁,與徵調川兵的理由頗爲相近。乾隆五十二年八月初二日諭旨:“因思湖廣、貴州兵丁,前經調赴金川軍營,於馳陟山險較爲便捷。若調往臺灣助剿,自更得力。著傳諭舒常等於湖北、湖南各挑備兵二千,富綱、李慶棻於貴州挑備兵二千,揀選曾經行陣奮勇幹練之將備帶領。”②“乾隆五十二年八月十一日,何裕城奏摺”,《清宮宮中檔奏摺臺灣史料》,第9冊,第418頁下。其中,湖廣官兵即從本省由江西一路行走,貴州兵丁從廣西、廣東一帶行走,前抵福建。貴州兵於九月十八至二十四日由古州威寧鎮全數開船③“乾隆五十二年九月二十四日,貴州巡撫李慶芬奏摺”,《清宮宮中檔奏摺臺灣史料》,第9冊,第577頁上。,十月二十六日全數到達福建詔安縣④“乾隆五十二年十月二十六日,李侍堯奏摺”,《清宮宮中檔奏摺臺灣史料》,第9冊,第674頁上。,十一月初三至初八日全部到達蚶江⑤“乾隆五十二年十一月十二日,李侍堯奏摺”,《清宮宮中檔奏摺臺灣史料》,第9冊,第725頁下。,用時四十五天。
總之,從周邊區補給投送兵力,尤其是糧食,很大程度上是一種威懾手段,很難實際派上用場。但兵丁的調動則不然,無論是川、楚還是黔兵,都是久經沙場,善於山地和亞熱帶環境作戰的“特種”部隊,深得乾隆信任。“川省屯練最爲矯健,而黔兵於陟山履險素稱便捷。此四千兵實足當數萬之用。”⑥“乾隆五十二年九月十六日,阿桂奏摺”,《清宮宮中檔奏摺臺灣史料》,第9冊,第544頁下。因此,他們的投送,沿途應用船隻及一切應付事宜,都由所經地方預爲籌備。所以,無論是川兵用時五十五天,還是黔兵用時四十五天,都是乾隆令其“加緊兼程行走,愈速愈妙”,不計成本投送的結果。
四 大陸兵力投送與補給的諸因素
此次兵力的投送與補給,無論是官兵、糧餉還是火藥,從福建到粵、浙,再到長江流域諸省,隨着距離的增大,其數量皆呈逐級遞減的趨勢。雖然戰爭行爲,不同於日常經濟行爲,並不以利益最大化爲目的,但如果無理性地超長距離投送兵力,就背離了“兵貴神速”的戰爭原則。儘管乾隆帝本着兵力“預爲寬備”的思想打仗,但也未調“京營勁旅”南下,理由正如他自己所言:“至京營勁旅,朕非靳於調撥,惟念道里遙遠,且不能服習臺灣水土,即派往亦不能得力。”⑦“乾隆五十二年十月二十四日,福康安奏摺”,《清宮宮中檔奏摺臺灣史料》,第9冊,第666頁下。除受基本空間經濟規律制約外,不難看出,有三個方面,是此次兵力投送和補給的主要限制性因素。
其一,交通運力對兵力投送的制約。清乾隆朝,南方的交通仍以水運爲主,包括河運與海運。此次兵力投送,內河航綫,以長江幹支流和閩江爲主;近海航綫,以長江口的上海港、乍浦港,晉江和九龍江口的蚶江港、廈門港,臺灣島西海岸的鹿港、臺灣府城港口等組成的L形航綫爲主。
河流流量有汛期和枯水期之分。河流上游段,水淺灘多,遇枯水期,通航里程大幅縮短,無論是武夷山脈西側的撫河、信江,還是東側的閩江,無一例外。而在河流的分水嶺,客貨都需上岸轉運,因山路崎嶇,需人力搬運,嚴重影響運輸的效率。以翻越武夷山脈爲例,“閩省辦理兵差、運送軍械等項,除海運外,皆係陸路,逾山越嶺,向無車馬,惟恃雇募人夫。緣平日另有一種江西及本省遊食之人,專以受雇充夫爲業,故農民各安田畝,不知有應差之事。即遇有重大差使,農民習以爲常,謂各站各有充夫之人,於民間無與,是以州縣遇有差務,俱係現雇人夫應用,從不能派及里下。非如陝、甘、雲、貴等省,可以按田派夫,使之領價應役。而此等專以充夫爲業之人,明知官府不能簽派鄉夫,每值差務緊急,輒一名索數名之價,否則不肯就道。地方官惟恐誤差,不得不曲徇其意,增給價值。此閩省實在情形也”。戰時緊迫,當然無暇推廣陝、甘等省的經驗,李侍堯衹好仰懇皇上用經濟手段來解決:“量增雇價,使人樂於受雇,則雖素不充夫之人,皆踴躍趨事,素不充夫之既來受雇,則專以充夫爲業之人,轉不敢刁難,而地方官應付差使,可不致竭蹶。”①“乾隆五十二年八月十七日,李侍堯奏摺”,《清宮宮中檔奏摺臺灣史料》,第9冊,第458頁。
臺灣海峽的風浪,是此次兵力跨海投送的最大障礙。不遠千里投送到蚶江、廈門的官兵,幾乎沒有不守風待渡的。例如,福康安從京城接受了乾隆的密令,一路風塵僕僕,於九月十四日抵達廈門,恰遇颶風頻作,連日不止,衹好在大擔門登舟候風。守風旬日,洋面依然風信頻作。十月十一日開船,又被風打回。“十四日,得有順風,與海蘭察同舟放洋。駛行半日,風色又轉東北,船戶即欲在料羅地方暫泊。臣仍令折戧開行,無如側帆迎借旁風,往來轉折,水道迂迴,不能迅速。二十二日已至外海大洋,日暮時大風陡起,不及落帆,水深又不能寄碇,隨風折回。至二十三日卯刻望見崇武大山,將近泉州惠安縣洋面。維時風信愈烈,詢據船戶僉稱,現值暴期,三四日方能平順。當令收入崇武澳中灣泊,普爾普、舒亮及巴圖魯侍衛等船隻後隨至。臣遣人赴各船看視,皆因不慣乘舟,又遇風濤傾簸,頭暈嘔吐不能飲食,間有患病者。臣以現在灣泊候風,並須添帶淡水,該侍衛等既多疾病,不必在船坐守,即令登岸稍爲歇息,一遇順風,即刻開船。”②“乾隆五十二年十月二十四日,福康安奏摺”,《清宮宮中檔奏摺臺灣史料》,第9冊,第664頁上。直至二十八日申刻第三次放洋,二十九日申刻至鹿港後,又因潮退不能進口,十一月初一日清晨纔登岸。火速前進的福康安,爲渡臺灣海峽,就耗時四十八天,比黔兵趕到廈門的用時還要多三天。至於在臺灣海峽,因風急浪高,溺斃官兵、沉失糧餉、延誤文報等事故,更是在在多有。另外,江海聯運,常常因海船不足,使長江流域的兵力補給,無法以最快的速度從長江口到達泉廈。
其二,通信遲滯對兵力投送的影響。在以驛遞爲主要通信手段的時代,中國的絕大多數戰爭都集中在大陸上。無論首都佈局在中原中樞地帶,還是在近海中樞地帶,作爲戰爭的最高決策者——皇帝,與前綫指揮之間的情報往來,一般不超過一個月時間。而在臺灣用兵則不然,海島孤懸海外,且不說海峽風汛無常、往返之間動輒月餘,單從北京到福建,山路崎嶇,溪河縱橫,加之“閩省驛站,向無額設馬匹,衹設遞夫馳送公文”③“乾隆五十二年八月十三日,福建布政使覺羅伍拉納奏摺”,《清宮宮中檔奏摺臺灣史料》,第9冊,第435頁上。,幾乎是耗時最長的通信綫路。因臺灣戰況信息被海峽風浪“封鎖”,無論是常青、李侍堯、孫士毅還是福康安,常常落入“旬日以來,尚未續得信息,惟於進口商船密爲探訪”的窘境。海峽西岸尚且如此,遠在北京的乾隆帝更是一頭霧水,不得要領。因此,戰亂初起時,乾隆因得不到及時準確的戰況信息,從而錯判戰爭形勢,致使林爽文趁機坐大。同樣因爲消息滯後,導致李侍堯、孫士毅先期調了乾隆極不滿意的浙江兵和廣西兵。甚至身爲兩廣總督的孫士毅,其主要職責之一,竟然是替乾隆打探臺灣戰況的小道消息。儘管孫士毅道聼塗説的消息,經常性地失實,但對於“宵旰焦勞至於廢寢,下懷縈切夢寐難安”的乾隆來說,有點消息總比沒消息的日子要好過,因此從不怪罪於他。
其三,乾隆個人好惡對兵力投送、糧餉補給的影響。先說糧餉,自乾隆五十一年十二月至五十三年二月,先後運到臺灣的米穀共計四十餘萬石,比調運的五十萬石川米還少;銀共計四百四十餘萬兩④“乾隆五十三年二月初十日,李侍堯奏摺”,《清宮宮中檔奏摺臺灣史料》,第10冊,第275頁下。,衹相當於粵、浙兩省補給的數量。單就糧食來說,臺灣並非缺米,據李侍堯奏:“查臺灣自賊擾以來,專販米穀之商船日漸減少,惟運送兵丁糧餉到臺之船回棹時,有附載米穀內渡者。六、七月間,每旬或數百石,至一二千石。八、九月以來,海多風暴,回船本少。近日始有陸續回來,每船不過帶米數十石,均係船戶自買食米,其自北淡水回者,尚間有數十石、百餘石不等。”⑤“乾隆五十二年十一月初五日,李侍堯、徐嗣曾奏摺”,《清宮宮中檔奏摺臺灣史料》,第9冊,第696頁下。由此看來,乾隆因帑銀充盈,於辦理軍務“預爲寬備”“從無靳惜”的做法,值得商榷。其實,大範圍的調糧,幾乎沒達到“散賊黨而省兵力”的效果。倒是福康安虛張聲勢的十萬大軍,一定程度上摧垮了林爽文集團的心理防綫。再說兵力調配,乾隆根據自己五十二年的皇帝生涯以及用兵的經歷,對各地兵丁強弱排定的座次(川兵、黔兵最厲害,其次是楚兵、粵兵、閩兵、浙兵、廣西兵,江西兵最爲無用),不能說沒有道理,但認爲江西兵於綠營中最爲無用,以至於不調一兵一卒,有失公允,李侍堯就認爲“江西贛州兵素稱強勁,且距閩省路亦近便”,值得徵調。至於對將軍、總督、提督信賴程度的差異,如對常青、何裕城的偏見,對李侍堯的信賴,對福康安的依靠,對藍元枚的過度期待,雖然是人之常情,也有一定的合理性,但還是多多少少影響到了戰爭的進程。不過,以古稀望八之年,乾隆帝依然有清醒的頭腦,運籌帷幄之中,決勝萬里之外,已經算是很在行的皇帝了。
餘論
兵力投送,其實是征服空間距離,並與時間賽跑的過程,古今中外概莫能外。理想的結果是,及時將充裕的兵力投送至戰場前綫。一些研究清代平定林爽文戰爭的著述,均喜歡用調撥錢糧總數來衡量此戰的規模,其實,真正運過臺灣海峽的糧食衹有四十餘萬石,銀四百四十萬兩,不及常見統計資料“一千萬”錢糧的一半。除一些錢糧直至戰爭結束還在路上外,大部分都囤積在海峽西岸的福建。因此,戰爭之所以持續十五個月,其難度主要是海島孤立無援與海峽風浪阻隔造成的。否則,在“人多力量大”的冷兵器時代,以林爽文區區一二縣之兵力,倘若在無海峽阻隔的內地,是很難成氣候的。再者,常青、李侍堯、福康安等的奏摺從臺灣投出,收到乾隆的硃批或諭旨已是一兩個月後了,因此,十五個月的戰爭,實在算不上用時太長的戰爭。因此,乾隆在《御製剿滅臺灣逆賊生擒林爽文紀事語》①此碑現藏福建省廈門市南普陀寺內。碑文中,對此次戰爭,以“遲與速”爲主題做了總結,可謂切中肯綮。值得他慶幸的是,鹿仔港、鹿耳門周邊大多數聚落是泉州莊和廣東莊,假如是漳州莊的話,就有可能在林爽文號召下,阻斷海上交通咽喉,那麽,此次戰爭結束的時間也就難以預測了。
其實,遠離大陸的島嶼國土,因自然環境惡劣,對於不同經濟類型的國家,其價值和經營理念相差很大。對於那些很早就步入遠洋貿易和漁業,並從中獲利的國家或地區的人們來說,有淡水的島嶼,或者能避風的岩礁,便是補給點和避風港,是茫茫大海中的“驛站”,因此也是他們搶先佔領、經營和守護的海洋國土。而對於傳統大陸農業國家來說,如果島嶼上沒有可供耕種的土地,就沒有經濟價值可言,自然也就不會着力經營,更難用國土的標準佔領並守護了。從自然條件和農業基礎來看,台灣島絕對是寶島,但這些條件,並不是康熙皇帝開疆拓土、收復臺灣的原動力。當初施琅帶兵收復臺灣和澎湖,根本目的是爲了徹底肅清自明代以來就以此爲基地、長期滋擾東南財富之地的土海盜或洋海盜。因此,在臺灣內屬後,清政府對臺灣治理的基本理念,便是派重兵彈壓,使其“雖有奸萌,不敢復發”。但是,臺灣島自給自足的資源稟賦,易守難攻的地域形勝,偷渡移民的冒險精神,分類械鬥培養出的嗜血性格,以及海盜文化中天生的民主團結,如堆積在一起的硫磺、硝石和木炭,一旦比例恰當,星星之火,即可燎原。因此,儘管乾隆帝眼中的林爽文被視爲“么䯢小醜”,卻讓他宵衣旰食,吃盡苦頭,實屬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