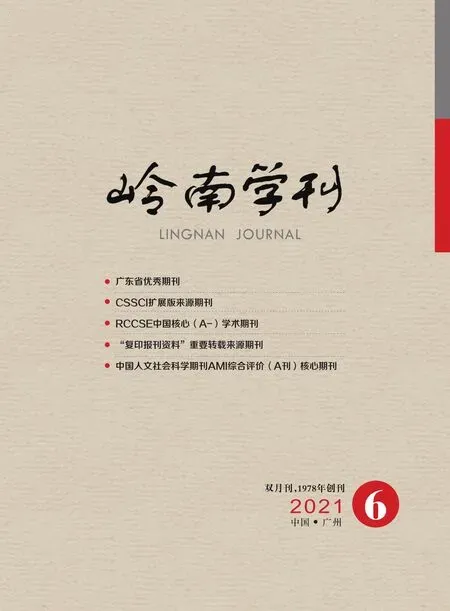数字化生存与自我身份认同
2021-12-28李晓培
李晓培
(1.广东农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广东 广州 510507;2.中央财经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081 )
数字化生存时代的到来构成了自我身份认同的新的历史性前提,为自我的身份认同提供了新的历史语境,由此导致了游戏规则和生成逻辑的变化。因此,从哲学上对这一时代命题进行分析具有较强的理论意义和时代意义。
一、数字化生存——自我身份认同的时代语境
在互联网技术的推动下,我们已经进入到数字化生存时代,这构成了我们理解自我身份认同的基本历史语境。数字化生存时代就像一种无形的磁场,不仅影响和改变了自我对自身的认知,而且引起了社会对自我评价方式的改变,更重要的是对自我身份认同的实践方式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自我身份认同关系的数字化语境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135从这个意义上讲,人是流动性的存在,不同的时代以及由此产生的不同的社会关系定义了人的本质,从而决定了人的身份。在数字化生存时代,自我的身份认同显然具备了区别于之前任何时代的特征,即数字化存在。从人与人的关系看,在数字化生存时代,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不再局限于传统的面对面,即人—人交流的模式,也不再局限于传统的人—物—人交流的模式(例如书信、电话、电报等方式),而是可以通过数字化平台实现人—机—人的交流模式。传统的人与人的关系通常表现为三种情况,一是即时的在场,比如说面对面的交流,这是一种同时在场的真实的交流;二是非即时非在场,比如说是书信、电报交流,这是不在场的文字交流;三是即时非在场,例如电话交流,这是一种不在场的语言交流。在数字化生存时代,人与人之间的交流通过数字化平台突破了传统的时空界限,使真实的不在场变成了不在场的真实。传统的人与人之间以“物”为中介,数字化生存时代人与人的交流以“机”(数字化平台)为中介。前者只能在有限的时空中和有限的真实的人进行交流,后者则可以突破时空的界限,实现超时空的真实的或非真实(虚拟)的交流。从人与社会的关系看,数字化生存时代形成了“人—机—社会”交流的模式。传统社会中人的出场是以分工为标志的,不同的社会分工决定了一个人的社会关系网络以及由此形成的社会角色和身份认同。但是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分工决定了人们从事工作的单一性,教师的职责在于教书育人、工人的职责在于从事工业生产、律师的职责在于维护社会正义等等,不同的社会分工塑造着不同的社会形象。所谓隔行如隔山,不同的工种之间隔着一道墙。这就意味着传统的人与社会的关系具有典型的业缘式特征。在数字化生存时代,这种传统的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正在发生改变。以数字化串联起来的人们的生活领域正在逐步突破传统的地域和行业的界限,形成了以“网缘”为特征的新的社会关系。自我社会角色以及身份认同逐渐剥离传统认知走向“网缘认知”。
(二)自我身份认同评价的数字化语境
在数字化生存时代,社会对自我形象的认知、评价以及身份认同具有了鲜明的数字化气息。首先,社会对自我的形象认知具有数字化特征。在前数字化生存时代,自我的形象被锁定在象牙塔,局限在很小的范围,一般民众和自我之间仿佛隔着一道墙,很难建立起感性直观的形象塑造。然而,在数字化生存时代,通过互联网的连接,社会大众和自我之间搭建了一座“互联网之桥”,自我的形象塑造披上了数字化的外衣,呈现出大众化的特征。也就是说,在数字化生存时代,借助互联网技术,自我的形象正在被重新塑造;其次,社会对自我的形象评价具有数字化特征。在数字化生存时代,社会对自我的评价正在走出传统评价的窠臼,评价的内容更加多样,评价的手段更加多元,评价的效果更加客观。从评价内容来看,自我的网络形象、网络话语、网络影响力已经构成自我身份认同的重要内容;从评价手段看,云计算、大数据等互联网技术已经应用到自我身份评价之中;从评价的效果看,用数据说话已经成为社会评价的重要尺度,评价的效果更加公正。最后,社会对自我的身份认同具有数字化特征。和过去相比,自我再也不能躲在象牙塔内“孤芳自赏”,在“互联网”之外,作为一个局外人的身份已经显得和这个时代格格不入。在数字化生存时代,自我身份认同的评价正在通过数字化平台被重新塑造。
(三)自我身份认同实践的数字化语境
马克思主义认为,实践构成了人存在的基本方式,“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的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种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1]135-136实践本质上是一种对象化活动,是主体客体化和客体主体化双向互动的过程。传统意义上,自我正是在实践活动中确立着自身的意义和价值,实现着自身的理想和抱负,同时塑造自身身份。在数字化生存时代,自我的实践方式的确正在发生着巨大的变革,实践的内容和形式都在发生着改变,带有更多的数字化气息。数字化实践活动开创了全新的网络世界。和传统社会实践相比,数字化实践作为一种新的实践活动,在人们日常生活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电脑和网络的出现,创造出一种新型的交往关系——‘网缘关系’。‘网缘关系’在质上完全不同于以往的‘血缘、地缘、业缘’等关系类型,它是一种通过虚拟空间建构的人际关系,网上交往既可以不必有血缘关联,也可以不必有地缘和业缘关联。”[2]46这种“网缘关系”是数字化实践活动形成的一种全新的样态,是实践的主客体以及中介被数字化后的一种自然呈现。需要指出的是,互联网发展的趋势方兴未艾,新的数字化技术层出不穷,数字化实践的方式会伴随技术的涌现而不断改变。但可以确定的是,数字化实践已经成为自我身份认同的重要路径,并由此改变着人们对自我的身份认知。
二、信息座架——自我身份认同的游戏规则
在数字化生存时代,自我身份认同形成了独特的游戏规则,信息变成了自我生存的基本方式,构成了自我出场的路径、对话交流的平台以及身份认同的机制。
(一)信息座架:自我出场的路径
在数字化生存时代,信息座架对自我的生存状态形成了重要影响,构成了自我出场的路径。首先,信息决定存在。自我作为存在者本身出场的方式多种多样(人有七情六欲、喜怒哀怨、不同的生活习性、品位风格、着装打扮,这些都是人的出场方式的显现),但是我们认为数字化生存已经构成了自我的基本生存方式,从而决定了其出场方式。一个在互联网之外的自我很难进入现代人的生活圈之中,更难被别人接受,其通常会被视为一个局外人,是一种没有被意识到的存在。实际上,作为现代人,自我的存在已经被数字化信息重新定义了。“笛卡尔哲学的‘我思故我在’正在演化为‘我在线故我在’。尼葛洛庞帝所谓的‘数字化生存’正日益成为后现代的日常生活状态,人们熟悉的生活和体制正在产生极为深刻的变化。”[3]24-25因此,在数字化生存时代,自我仿佛被促逼着进入了数字化生存的境遇之中,信息座架构成了他们出场的基本路径。其次,信息决定生活。在数字化生存时代,数字化信息可以说无孔不入,已经进入了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正在塑造着一种全新的数字化生活方式,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信息决定生活。“我们都相信,随着计算机日益普及而变得无处不在,它将戏剧性地改变和影响我们的生活品质,不但会改变科学发展的面貌,而且还会影响我们生活的每一个方面。”[4]224数字化信息对生活的塑造不是局部的而是全局的,不是单个的而是群体的,不是浅显的而是深刻的。最后,信息决定思维方式。在数字化生存时代,由数字化技术开创的独特的人类生存空间,不仅仅极大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体验,而且正在改变着人们认知世界的思维方式。和传统的世界相比,由数字化连接的信息世界具有明显的“信息座架”的特征,一切都被还原成信息语言,一切都被信息重新定义,以至于思维方式变成了信息思维方式。自我要寻求身份认同,就要进入互联网平台,具备互联网思维,和互联网同频共振。
(二)信息座架:对话交流的平台
在数字化生存时代,数字化渗透到自我的生活之中并成为交流的基本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人们要通过什么方式表达、表达什么以及表达的效果如何都和数字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人们的对话交流进入到了信息座架,从而构成了交流的历史前提。在信息座架的操纵下,自我的话语是以信息符号的方式呈现出来的,信息决定了话语的方式、内容和效果。首先,信息决定话语方式。自我的沟通方式很多,语言交流、文字交流、身体交流、眼神交流、心灵交流等都可以起到很好的交流效果。有效的话语交流成为人类文明基本的必要性条件,但这并不意味着不同时代人们的交流方式都是千篇一律的。“人类第一次中介革命的标志是语言文字符号的产生,而虚拟的数字化方式是比语言文字符号更为重要的一次革命,是一种现实关系的表达和创造,语言符号创造了人的思维空间、符号空间,而虚拟则是在思维空间、符号空间中发生的革命,它在思维空间、符号空间中又创造出了虚拟空间、数字空间。虚拟是数字化表达方式和构成方式的总称,它构成了人类新的中介革命,是人类新的元起点。”[5]这种新的技术革命在话语交流上是以“信息座架”的形式呈现出来的,即自我的对话交流只有进入到信息的磁场之中才会成为可能,才会具有意义和价值。和传统意义上人们的话语交流相比,数字化生存时代人们的话语交流极大地突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使“地球村”从概念变成了现实,使文明的代际传播增加了更加丰富多彩的内容。其次,信息决定话语内容。在数字化生存时代,信息座架不仅决定了自我如何去交流,而且还决定了交流的内容。数字化对自我的生活领域的渗透总是潜移默化的,在不知不觉之中,其生活方式包括交流方式已经受到了信息的深刻影响,以至于其话语总是以不自觉的信息化方式呈现出来。我们做出这样的判断并不意味着传统话语的终结或者消亡,而是在数字化生存时代,传统话语的式微已经成为一种趋势,而与之相伴的是信息话语的兴起。我们不排除在日常生活中传统的对话方式依然起着重要作用,我们也无法时刻沉浸在信息话语之中,但值得注意的是,信息话语已经变成了一种主流趋势。网络流行语的不断兴起是典型的信息还原法的具体表现。例如,用数字替代文字意义的网络用语、用表情包替代情感意义的网络用语等都是在数字化生存时代自我适应信息社会的快速发展而形成的一种新的话语表达方式。这些网络用语构成了当下自我语言交流的基本符号。而且我们相信,随着数字信息化的不断深入推进,话语还会增加新的内容,从而塑造数字化生存时代自我交流的新语言景观。最后,信息决定话语效果。在传统意义上,人的对话交流是全面的,即人的交流总是在一定的场域之中进行的交流,语言仅仅是交流的一种手段而已,除此之外,肢体语言、眼神交流、心灵感知等构成了一个对话交流的场域,彼此获得的信息是在这个场域中捕捉到的信息总和。所以,我们通常都会体认到在不同的话语交流场域中,我们的精气神是不一样的,从而我们获得的感知也是不一样的。然而,在数字化生存时代,人与人之间的话语交流发生了深刻的变革,其中最大的变化是信息磁场替代了话语场域,传统对话场域中存在的话语因素被信息流截断了,多样性的话语感知被单一的信息流代替了,在信息座架的操纵下,一种以数字化信息为平台的新的虚拟对话交流的范式正在形成。比如,线上教学就是依托计算机网络进行虚拟对话,甚至在VR的场景下进行人机对话。教师身体的不在场意味着在虚拟交流的过程中,包括身体语言在内的许多生动的语言形式被网络遮蔽了,这样的交流缺乏身体气息,学生很难感受到情感的感染力,导致教师和学生之间的交流变成了学生与信息之间的交流,对方是谁显得不怎么重要了。
(三)信息座架:身份认同的机制
关于身份认同的争论一直是哲学界关注的课题,“自从帕门尼德斯和毕达哥拉斯以来,哲学家们一直在与自我和身份问题作斗争,而且在现代哲学中当然也是如此,包括一方面以洛克式经验主义为代表、另一方面以康德先验哲学为代表的关于个人身份的辩论。”[6]作为一种社会性存在,自我天生具有身份标识,这一方面源于先天的因素,一方面源于后天社会的因素。在数字化生存时代,传统的身份认同机制遭遇了危机,由数字信息链接的世界正在塑造一种全新的身份认同机制。在信息座架的操纵下,传统的血缘、地缘、业缘正在被“网缘”替代,信息变成了识别身份的主渠道,主要体现在:信息代表身份、信息改变身份、信息决定身份。首先,信息代表身份。在传统社会中,自我的身份具有职业固化的特征。然而,在信息化社会的信息磁场中,身份识别的职业固化正在被解构,替而代之的是信息身份的凸显。自我的身份认知已经渐渐走出了“职业固化”的窠臼,开始以信息为主渠道,重新去定义身份,这意味着信息变成了自我身份识别的重要砝码。其次,信息改变身份。在传统社会,“职业固化”形成了相对稳定的身份认知机制,因而身份是很难改变的。然而在数字化生存时代,这种固化的身份认同机制在信息流的冲击下发生了变化,主要体现在流动身份得以可能。学界对互联网的研究“越来越多地强调了我们的在线身份与离线身份在很大程度上是连续的”[6]。互联网社会开放包容的特征使我们几乎可以平等地拥有信息,这些信息和家庭或者从事的行业可以毫不相关。一个公开的网络课程,大学生可以尝试学习,工人、农民也可以学习。因此可以说,在数字化生存时代,我们第一次可以真正意义上享受到资源共享的平等性,这为身份的转换提供了一种可能。最后,信息决定身份。在传统社会中,一般而言,地位决定了身份。然而在数字化生存时代,在信息座架的操控下,信息逐渐代替了地位并决定着身份的存在。我们认为,这种权威者的身份既和传统社会密切相关,又和网络时代紧密相连,即一般意义上来看,在传统社会中各行各业的意见领袖如果借助互联网平台发表言论,会发生权威的数字化转移,同样成为数字化平台上的身份权威。传统社会中的学术泰斗如果在“信息圈”中发声,自然会成为这个“信息圈”的身份权威,这是权威的数字化转移。在数字化生存时代,身份权威并不是对传统社会的一种简单的数字化转移,它正以不同方式开辟无限的可能,自我身份的确认具有极强的可塑性。
三、二元交融——自我身份认同的生成逻辑
自我身份认同以历史为大前提,在不同的时代,身份认同生成的逻辑及表现的形态也不尽相同。在数字化生存时代,自我身份认同的生成逻辑体现出了在场与缺场、业缘与网缘、现实与虚拟“二元交融”的特征。
(一)在场与缺场:自我身份认同的二元存在
“在场”是指自我处在线下的一种状态,“不在场”是指自我处在线上的一种状态,这两种状态构成了数字化生存时代自我独特的生存景观,代表着两种不同的角色,从而形成了身份认同的“二元性”。从“在场”的角度看,数字化生存并不意味着真实的自我身份的消亡,“在场”仍然是自我角色认同的主要领域;从“缺场”的视角看,“缺场”是另一种“在场”,它不是“不在场”,而是现实的缺席、在线的在场。从时间的角度看,自我可以超越“此在”的时间限制,以“缺场”的形式获得身份认同。“虚拟实践的形成和发展使人们打破‘时钟时间’的桎梏这一愿望转变成可喜的现实。”[2]166这种打破是以数字化技术为前提的,其带来的意义就是突破了传统时间的窠臼,使得时间具有了可塑性。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超越“此在”的时间并不意味着真正意义上的时光倒流或者穿越到未来,而是数字化虚拟的技术尝试,让人们感觉仿佛可以这样,而实际上仅仅是虚拟实践中的一种情感体验。即便是这样,在数字化生存时代,数字化技术打开了一个全新空间,其影响力已经远远突破了传统社会时间上的局限性,变得无时不在。在数字化生存时代,人们的智慧和网络连接后产生的影响力将会被放大。实际上,“在场”与“缺场”体现了数字化生存时代自我身份认同的“二元性”,通过“二元性”的身份塑造,自我才能获得职业的存在感和获得感,才能形成自我身份认同。
(二)业缘与网缘:自我身份认同的二元形式
在一定意义上,数字化生存时代自我生活的两个世界——生活世界和网络世界——有一定的独立性,但更多层面上则表现出相互渗透和融合的特征。生活世界中自我的生存状态和网络世界的生存状态具有明显的区别,前者主要面向现实的世界,获得的是真实的体验;后者主要面向虚拟的世界,获得的是虚拟的体验。因此,不同状态下自我的生活体验是不一样的。但从另一个层面上看,生活世界和网络世界又经常纠缠在一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正是由于身处两种不同的世界,才构成了自我的“业缘”和“网缘”,从而形成了社会对其身份的认知。从“业缘”的视角看,自我要塑造职业的核心竞争力方可安身立命;从“网缘”的视角看,“网缘”是“业缘”的一种延伸,是自我职业能力和形象塑造的数字化表达。“业缘”和“网缘”构成了数字化生存时代自我社会身份认同的“二元性”,通过“二元性”的身份塑造,社会才能形成对自我的身份认同的判断,才能形成自我身份认同。
(三)现实与虚拟:自我身份认同的二元世界
在数字化生存时代,从人的生存状态看,存在生活世界和网络世界“二元世界”并存的局面,因此也决定了自我身份认同实践的二元性。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已经把人们带进了一个数字化生存时代,但这并不意味着人们真实的生活世界的终结。即便越来越多的人生活在“网上”,但作为种的存在,仍然使我们无法和传统的生活世界完全割裂。在数字化生存时代,“虚实相生”构成了自我身份认同的实践的独特景观。从“现实实践”的视角看,自我的身份认同中包含着主体客体化和客体主体化的双向过程。主体客体化是指自我在传承知识、培养能力、引领价值的过程中获得的社会身份认同;客体主体化是指社会的反馈。这个过程就像一面镜子,使自我形成对自身的反思,进而形成自我评价和职业认同。作为实践的一种特殊的数字化表达方式,虚拟实践同样包含着主体客体化和客体主体化的双向过程。借助互联网,主体客体化的过程中形成了网缘关系,扩大了影响力,构成了社会对自我身份认知的重要渠道。在客体主体化的过程中,网友的评价和反馈构成了基于“网缘”关系的个人自我评价和身份认知。在数字化生存时代,“现实实践”和“虚拟实践”构成的独特的“二元性”就像两个不同的战场,通过两种实践,才能在真正意义上形成自我身份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