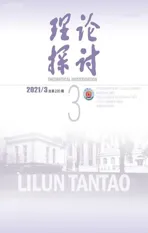公共领域对话语空间及舆论方向的影响与作用
——以大光明电影院事件为例
2021-12-28◎易丹,彭瑾
◎易 丹,彭 瑾
四川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成都610064
一、引言
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提出“公共领域”概念,指17世纪后期在英国、18世纪在法国开始出现,并于19世纪传遍欧洲、美国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它是一种特殊的文化形态、历史形态,是由个体集合而成的公众领域,其功能是透过众声发言,形成公众舆论,对政治和社会权力进行监督和批评[1]108。资本主义社会中“私有化的经济活动必须依靠公众指导和监督而不断扩大的商品交换为准绳;其经济基础在自己的家庭范围之外;它们是第一次带有公共目的”[1]18。这一特有的商品交流与信息交换属性,成为“公共领域”产生的前提。以报纸、杂志等传播媒介为链接,私人社团、学术协会、阅读小组、共济会、宗教社团等民间机构将人们聚集在一起,在阅读报纸、周刊、杂志等私人活动中形成了一个松散但开放和有弹性的社交网络。自20世纪80年代起,就近代中国的社会形态能否以“公共领域”模型加以研究,国内外学界开展了激烈争论和不懈实践[2]。这些讨论将公共领域从欧洲历史中抽象出来,视其为与现代性问题相关联的普适性解释架构,认为近代中国的传统书院、知识分子社团和民间报纸杂志等,逐渐发展成人们发表对时局看法和政治见解的重要场域。在此之前,与皇家叙述相对的,要么是士大夫的清议制度,要么是知识分子间的私人讨论,民间叙述从未以公开的方式在公共场所由公众执掌。
20世纪初,俱乐部、咖啡馆、沙龙、影剧院等现代公共场所在上海的出现,为公众聚集和议论的社交网络提供了依存的物理空间,使公众得以在“市场经济和行政国家‘之间’或‘之外’” 无所顾忌地讨论社会问题。通过满足各自生产与分配特定需求的立场间的交织与互补,以及多方观点对结局的集体性约束,这些独立于政治建构之外的公共交往与公共舆论既对政治权力保持批判,又构成政治权威的合法性基础以及行政的民意基座。例如,著名的大众综合娱乐场所张园“在当时除了是上海的观光游乐中心之外,也是各种政治舆论公开表达的中心,是上海的‘海德公园’”[3]。由本地报纸和杂志构成的传播平台与这些公共空间无缝衔接,扩散和放大公众议论,并将其上升为针对当局行政的舆论压力。从物理空间发生的事件延伸至话语空间,形成特定社会的“公共领域”,按照哈贝马斯的逻辑,这是现代性的一个重要指标。
由此,考察电影院在这样的公共领域中扮演的角色,它的物理空间、影片放映和观看行为以及随后发生的议论、抗议甚至行政操作等,就成为非常有价值的学理活动。1930年,以上海大光明电影院为核心发生的所谓“不怕死”事件,提供了一个非常有价值的个案。对这桩舆论事件的再现与剖析,将还原当时各种社会力量参与公共话题、形成公共舆论的真实面相,为今天的公共舆论疏导与治理提供历史参照。我们可以考察和验证“公共领域”模型是否适用于中国的社会现代化进程,同时也揭示作为中国此一时期最发达的大都市,上海是否形成了现代性的公共领域,是否表征了中国此后必然踏上的文化现代化发展之路。
二、从公共空间到话语空间:众声喧哗的舆论风波
1930年2月21日,上海大光明影院上映好莱坞电影《不怕死》。该片讲述一美国植物学家(罗克饰)到旧金山中国城稽查贩毒集团的故事。剧中的中国人形象形貌猥琐,品行不端,女裹小脚,男抽鸦片,贩毒、盗窃、抢劫、绑票无所不为,位于中国城的花店就是贩毒窝点的所在。剧情中喜剧效果的设置充斥着令中国人不快的侮辱性情节,结果引发一场抵制辱华电影的轩然大波[4]。激化矛盾的标志性事件是公映第二天下午[5]1,剧作家洪深挺身而出,跳上大光明舞台,向观众发表演讲,斥责该片是一部赤裸裸的辱华影片。洪深呼吁:“中国人, 不能默受这样的侮辱与诬蔑, 我们不应当再看这张影片。”[6]在他号召下,数百名观众相继离席。洪深“冲向售票处,身后跟着一大批观众,大约有三百多人,他们高声喊着退票的要求”[7]。见局面失控,大光明电影院经理高永清下令英国经理茄尔丝将洪深强制带入经理室,扭拽中洪深受伤,后被带至爱文义路巡捕房扣押3个多小时,才由明星电影公司老板托外国朋友保释出来[5]58。洪深被捕引起上海文化界一片哗然,“不怕死”风波以大光明电影院为起点,延伸为一场众声喧哗的公共话语大讨论。以《申报》《新闻报》《民国日报》等为首的上海报界,不仅报道了当天冲突事件及随后法庭审判的新闻,还连刊各界评论文章,形成一场1930年代极为显眼的文化评论风暴。
(一)事者之言说
不少观众在事后纷纷发文声讨辱华影片。洪深在《申报》《民国日报》等媒体连续发文,以当事人、戏剧家、留美海归者的多重身份向民众揭露辱华影像对事实的歪曲,“扮演者所御之衣帽,以现在美国之华侨已绝无此种服饰”“贩土绑票及夺警察之枪械等等,无一而非将华人侮辱”。在长约一万二千尺的影片中,辱华内容竟达三分之二。对此,他警醒读者,“文艺(小说戏剧电影)能利用了技巧来麻醉大众,它们的影响大众的观念和意识,虽不是明显的有形的,但是深刻与远大,可以隐隐中转移了大众的心理,比那报章杂志的正面攻击更加难于防备。譬如这张‘不怕死’,凡是看了的人(尤其是外国人),至少是对于中国人不会增加一点好感的”[8]“无论美国人怎样恭敬你,待你有礼貌,和你亲热,那鄙视华人的心理,不知不觉地会显露出来”。基于知识分子和电影业者的敏锐直觉,他直指“任何中国人,尤其是同情于我们海外侨胞的,决不会觉得这张片子,是把中国人做的有面子,有光彩的”[4]。“此片于戏弄之中,寓鄙贱之意,于侮辱之外,又附会而诬蔑,其流弊不堪设想”。他很担忧这类电影持续的破坏性影响,“罗克的作品,在美最受未成年人的欢迎,这班正在中小学读书,最易受影响的儿童,此刻先有了对于华侨的不良观念,将来影响到中华民族的前途,有多么大呢”[8]。呼应洪深的评论,电影人兼报人姚苏凤发文,客观地说:“按到过旧金山的人说,(唐人街)确是糟不可言”,但对影片《不怕死》的态度,“最好是大家不去看;至少,也该有些愤慨的表示”[9]。还有一位自称“电影的信徒”的影迷,他说自己花了金钱费了时间去看电影,“目的不过是要做一会‘ 白昼的梦,来苏散疲弱的神经’”,然片中华人个个“愚蠢如豕”、残忍好杀、贩卖鸦片、被罗克玩弄打死;华人盗魁名为“龙”,是侮辱中国人的象征;对华人面目丑陋、行动蹒跚、脑筋愚蠢、身体臃肿、个性恶劣、屋子湫溢的描绘举不胜举,他“简直发誓不再看外国影片了”[10]。有报纸头版头条刊发影迷文章《爱国同胞大家起来:打倒“不怕死”的罗克,欢迎“不怕死”的洪深》,呼吁读者一致联合,从此勿观罗克主演之电影,并要求政府永远不准引入不良影片[11]。
在激荡的话语空间里,愤怒的矛头不单单指向太平洋彼岸的好莱坞制片商和演员,也直指近在咫尺的电影院。早于洪深被捕之前,已有35名观众在《民国日报》发表联名抗议信,一面向尚未观看电影的大众痛陈,“塌尽了中国人的台,扫尽了中国人的脸……把中国的国体丧失极了”“使人误会以为中国是一个野蛮的国家,一个未开化的民族,是一群毫无德性的人民”,一面向电影院喊话,“大光明的戏院院主,如果不自动停止映演这张完全侮辱华人的影片”“请注意我们中国人也有热血,我们中国人也会不怕死”[12]。文人钱云疾呼:“同胞们争口气,我们大家不要踏进这映不怕死侮辱我们华人的两大戏院吧。如果你还想尝试那不怕死的话,那你简直没有心肝。”高发康疾呼:“凡是热血同胞,革命同志应自今日起立誓不再踏进大光明及光陆两院看戏,与印度甘地不合作主义同为无可奈何之一种办法。”[13]这些话语都把抵制辱华影片的矛头对准电影院,他们认为,影院挂着外商的旗号,实际是华人的产业,利用租界内特殊地位,以华人身份欺辱华人,是可忍孰不可忍。就这样,电影院作为文化载体的公共空间,成为文化抵制的众矢之的。
(二)资本之态度与党派之立场
在这场公共舆论旋涡中,貌似讨伐一片、众声一致的沸腾话语之下,隐含着不同的利益诉求和党派论调。针对电影和电影院的诸多议论和批判,实则成为不同意识形态在上海公共领域里的微妙博弈。
作为民族电影资本的代表,这一时期的本土电影人多是接受西学、怀有国族情怀的知识分子。他们无奈于好莱坞长期强势霸占上海电影市场、国片发展空间十分狭窄的局面,于是,借“辱华”甚嚣尘上的风口浪尖,推行政府电影审查制度。这确是在关税不自主的情况下,实现民族大义、商业利益、产业发展多重诉求的可借之机。明星电影公司老板郑正秋发表长文,从民族屈辱和国片发展的双重维度陈述抵制辱华片的依据与路径,呼吁将华界已推行的电影检查制度覆盖到租界以内, “单说中国领土以内养活了多少外国人,造成了多少外国实业家,每年外人在中国赚去的金钱是多少……(外国)影片上映不受中国电影检查会检查,就在银幕上对着中国人尽情的侮辱;这个理,恐怕太讲不通去吧”[13]。郑正秋之子郑小秋声援洪深在大光明的抵制演说,成为洪深案中原告重要证人,其公司律师成为洪深诉大光明的辩护人。明星公司还号召全体员工上街,形成群众示威运动,要求禁映该片,要求大光明公开向洪深道歉并赔偿损失[5]。
与民族资本话语相呼应,左翼、中共地下党、国民党等不同政治背景和派别人士罕有地表达出相对一致的声音,但在这些声音里,又鲜明或隐蔽地发挥着不同的语调。
在左翼话语中,除了声讨影片本身,还把电影院、资本家乃至政府作为批判靶心。邹韬奋发文,标题即以《大光明中大不光明》表明立场,“论到这件事的性质,简直是十全奴性的十足表现,卑鄙龌龊鲜廉寡耻到了极点”。辱华片“捏造污蔑,固属可恨”,而大光明股东高永清依仗公司的美资背景和租界管辖,欺辱本国同胞,“无耻之尤,应为国人之同弃”[14]。田汉指出,受侮辱而知反抗是弱小者“最宝可贵的生机”,赞同成立“不看同盟”。他举例,罗克拿木棍给华人甲做武器打华人乙,又递木板给乙反打甲,实际上是帝国主义贩运军火给相争军队而从中渔利的隐喻。他以马克思阶级论的立场称赞,以洪深为代表的理性观众在“人家的麻醉剂”前,能保持警惕,辨别味道,这种觉悟是被压迫者走向解放之路的希望[15]。田汉毫不掩饰地表示,洪深大闹大光明是在南国社配合下的一场有计划的行动(1)据田汉回忆,22日洪深在大光明电影院看完下午场《不怕死》后,便到南国社找田汉商量,提出要“去影院讲话,要观众不要看”,并言明已“跟明星公司的律师谈过了,一旦被捕,请他出庭辩护”,于是田汉找南国社社员音乐家张曙、电影演员金焰、青年记者廖沫沙陪洪深同去,“在洋经理扭打洪先生的时候”“也狠狠地回击洋经理”“在洋经理腿上打了好几拳”。[16]。事件发生后,以南国社为首的左翼戏剧团体立即发表联合宣言,“帝国主义对华侵略,在经济上,在文化上,无所不用其极,而近更假借电影之表现,在国际上,作丑恶之宣传,作迷惑之麻醉,淆乱黑白…… 而我国政府,对于此种问题,事先未曾注意加以限制,遂使大光明以华人开办之剧场,乃发生此种怪剧……剧界同人,深愿为洪先生之后盾,作一致之援助,对无理之大光明戏院,蛮横之捕房,作严重之抗争,务使此片销毁,不再映现于世界各国”[17]。值得注意的是,左翼话语中夹杂的马克思主义阶级论的宏文已公开地发表在各大报刊中。黄素呼喊那些仍在“客观地”讨论电影艺术的人们醒一醒,把罗克放在“解剖台”上,先认清他和美国电影艺术的阶级性。“罗克的喜剧底成功是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艺术底成功,因为现代的艺术本事产生于资本主义的机构用以宣传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停留于讨论影片本身,而“单不提到政治,单不提经济组织”,只能掩盖事实。“受着刀子的宰割,毒药的麻痹”,却“有闲情逸致来讨论那刀子那毒药的本身的价值”,实在“痴得可怜”。他揭露,影片是帝国主义给白人洗脑的宣传工具,“是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国家进攻弱小民族的一种武器”,罗克是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最忠实的走狗,最相当的代言者”。在侵略面前只有一条路——积极反抗。“社会不良我们便得改良社会,政治不良我们便得改良政治,经济组织不良我们还得推翻这资本主义的经济组织”[13]。
与左翼话语近似,右翼言论同样声讨影片和影院,但其立场又有不同。对事件关注最久、观点最集中的国民党党报《民国日报》,一边厉声声讨辱华片的破坏性,一边竭力宣扬电影检查制度的必要性,在话语层面给政府的上海市电影检查委员会打气撑腰。右翼《时事新报》更试图将舆论引向热爱党国和元首的轨道上去,“我国人民至今国家观念尚不发达,外人看透此点”是辱华片得以长驱直入的源头。其社论写到,“代表国家者为君主,至此代表国家者则为全民,人民尊爱国家,不啻尊爱其个己;尊爱个己出乎本能,尊爱国家则亦不啻出乎本能也……在消极方面凡有冒犯一国让家之尊严者,全国人民竟可抛弃一切利害是非以图报复,在积极方面,一国人民对于国家之敬爱,实无时无地不谋尽量之展现:闻国歌而肃立,见国徽而脱帽,见元首像片而欢呼致敬”[13]。
众声喧哗的舆论氛围制造了空前一致的行动动力,很快,电影《不怕死》从大光明电影院、光陆电影院撤档,大光明电影院甚至停业易主;洪深诉高永清损害名誉案胜诉;政府电影检查制度得以切实执行;国产电影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产业发展空间;左翼利用文化论争与舆论引导夺取了一定的话语空间。
三、由公共领域产生的现实权力与变革力量
诚如哈贝马斯所论,公共领域(影院)作为主体间性施展的空间,除了物理载体的意义以外,其开放性和公共性还为人们提供了平等参与公共议题的言说场域,并最终构建了公众舆论的话语空间。在“不怕死”事件中,物理空间聚集所激发的话语空间鼓噪,从客观上促成了国民政府、民族资本、左翼知识分子、中共地下党等形成基于民族认同的一致战线。这是现代都市才可能出现的现象,是现代性在公共空间的凸显。电影院一类的新兴公共空间,使上海的现代公众意识得以释放,主体间性得以加强,共识得以达成。而由公共空间延伸向媒体空间的公众辩论,最终转化成公共舆论,促成了相关制度的形成和实施,进而引发了政策和法律的长期推行,正是现代性在上海日常社会中全面展开的一种特定表征。
不过,在这场喧嚣的舆论风波中,公共领域的言论操作中包含的权力场争夺更耐人寻味。作为一个半殖民城市,1930年代的上海的文化特殊性在这场话语狂欢中的呈现更值得深思。而影响上海文化内涵与走向的多元角力,也为今天的舆论治理提供了历史参照。
(一)权力集合推动社会治理
辱华影片激起华界与租界有识之士(包括民众与官员)一致反感和反抗,可被看作西方殖民主义制造的长期地域性压抑的集中爆发。地域同一性所产生的反射同一性,促成上海不同权力话语达成临时一致,共同对外,产生变革力量。例如,尽管租界工部局与国民政府电检会对外国电影的审查标准各执己见,但“不怕死”事件发生后,双方对抵制辱华片达成共识,并在上海全境有效贯彻。外国影片在华内容审查得到制度化规范,《电影检查法》《电影检查法实施规则》《电影检查委员会组织规程》相继出台,国民政府开始推行全国统一的电检制度。仅1931年2月至1934年3月,上海市电影检查委员会检查进口片1,923部,其中,42部好莱坞影片被禁,另一些则被要求删改后上映。例如,赫孔公司《人海潮》删去戴小帽蓄辫之华人侍者镜头,哥伦比亚公司《野人国》删去华侨在木厂聚赌的场景,才得以在华上映[18]。而像《上海快车》《颜将军的苦茶》《将军在黎明时死去》(旧译《糊涂将军》)等辱华影片,根本未能在中国上映。至于这种电影审查制度最终推行到国产片之中,成为国民政府在电影领域的意识形态管控工具,已是后话。
(二)借助舆论占据话语空间
长期以来,在对上海的认知与阐释上,西方世界与中国左翼均视其为罪恶的渊薮。对帝国主义侵略和殖民的束手无策,一直是左翼抨击国民政府的话语核心。在左翼看来,国民党竭力鼓吹的都市繁荣,恰恰以对劳苦大众的残酷剥削为代价。阶级分野与对立,是与帝国主义侵略同样严重的社会矛盾,然而,当民族认同成为联络不同政治立场持有者的情感纽带时,左翼话语的火力方向跟国民政府保持了一致对外。马克思主义信仰者(包括中共地下党)已能娴熟地利用合法舆论,以理性、机智的手法表达自身的立场与诉求。在上海的公共领域之中,中共地下党对“不怕死”事件的话语参与,无疑扩大了其影响。有美国学者认为,洪深对大光明与《不怕死》的控告、民众参与对辱华影片的抗议,“标志着(左翼)将在30年代与上海电影界联系在一起的积极行动阶段的开始,同时中共地下党也在准备涉足其间”[19]。毫无疑问,左翼的幕后参与使事件朝着有利于扩大进步势力的话语空间、有利于新生政党向获得表达机会的方向迈出一大步。
(三)利用舆论强化宣传管控
原本由于国民政府“对于租界一切问题,无权过问,而本市中外电影商人及电影院又十九皆在租界以内,逆知监督指导,困难必多”[20],1929年7月成立的上海市电影检查委员会专事电影检查实效甚微。而此事一发,利用行政命令、主流媒体舆论引导、外交斡旋等多重手段,国民政府将自身塑造为捍卫民族情感的正义化身,试图把民众朴素的爱国情绪同化为爱政党、爱领袖的具体行为。事实证明,作为这场群众运动的幕后推手的国民政府,在此后夺得和贯彻了更为广泛的电影审查权。隶属国民政府的上海市电检会当日便以影片“辱我华人处,令人发指”,向大光明电影院、光陆电影院发出训令:“亟令仰该戏院克日将《不怕死》影片停映,听候查办。”[6]随后,连续采用行政、市场、外交多重举措包括:致函上海《申报》《新闻报》《时事新报》《时报》《民国日报》等各大报馆,要求拒登两院一切影片广告;申请海关及京沪、杭甬铁路管理局查扣《不怕死》拷贝;会同上海市国民党部宣传部电请各省市政府,在罗克未正式道歉前,禁映所有其主演之影片;罚款大光明、光陆两影院[6]。与此同时,国民党各地党部纷纷上呈抗议要求禁映,要求罗克向中国道歉,国民政府行政院责令各省市政府查禁该片。这显然已经超越了话语范围,将强势舆论直接转化为行政举措。
(四)舆情影响司法加速裁判
洪深于事发翌日聘三名律师诉大光明老板高永清侵害名誉和人身侮辱。半月后(1930年3月13日),上海临时法院第七法庭开庭,场面壮观。“旁听席中,约有四五百人之多”“该法庭已无立足之地”“几至全沪注意”“学界与电影界尤为重视”“皆暂抛数小时之职业或学课,特赴法院,以观此轰动全沪民众之巨案之审讯情形”[21]。经两次庭审,7月,法院当庭宣判洪深胜诉。8月,派拉蒙公司发声明回收中国《不怕死》全部拷贝[22]。罗克本人的正式道歉声明刊于《申报》,称“自己完全无意触犯贵国的民族尊严,伤害贵国人民的感情……我渴望做的事就是,如果我以任何方式触犯了中国的民族荣誉和尊严,我愿向中国和中国人民表示我诚实的歉意”[6]。10月,大光明电影院上呈政府上海市电影检查委员会正式道歉,“前以失于检点,开映罗克主演之《不怕死》影片,其中有侮辱国人之处,深用疚心”,并承诺对上海市电影检查委员会各项办法“俱可遵办”,以后映演诸片自当随时于事前声请检查,以免再有错误。在轰然如山来的舆论压力之下,无论自愿与否,司法正义、行政效率、道德反省、市场响应等都得以提速。
四、结语
近百年前,大光明电影院引发的话语激荡,参与塑形了上海的文化公共领域,改变了产业初始量度,最终影响了文化管理与产业发展的历史方向。随着当今世界经济、社会、科技极速发展,在“去魅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哈贝马斯那里,公共领域理论也不断随之修正、发展。就今天互联网对世界的深刻影响,哈贝马斯敏锐地指出互联网碎片效应所引发的新问题,即随着古典自由主义公共领域的形成,构建知识分子的形象——“有赖于警醒世人的新闻界的存在,报纸、大众传媒有引导社会大众将兴趣转向那些与政治舆论有关的话题,也有赖于一个读者群的存在——这个读者群对政治感兴趣,受过良好教育,对于舆论形成中的冲突习以为常,也肯花时间去阅读高质量的、独立的报道”——这一基础已不再牢固。互联网的碎片效应改变了传统媒体的角色。与此同时,公共注意力的商业化已经引发了公共领域的瓦解。媒体对用户个人隐私进行经济掠夺,以有效地操控他们,有时甚至是出于邪恶政治目的。诚如哈贝马斯的新近论述,自印刷媒体被发明以来,每个人都是一个潜在读者。而在互联网时代,所有人都变成了潜在的作者。在这样一种公共领域解构的社会现实中,在我们学会如何以文明方式经营社交网络之前,新的社交问题将引发层出不穷的社会舆论,打破旧有公共领域的平衡,洗涤“应然的”权力结构体系。在这一变动不居的过程之中,如何正向引导、树立我们的舆论环境、有利于社会的和谐发展,将是我们面对的时代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