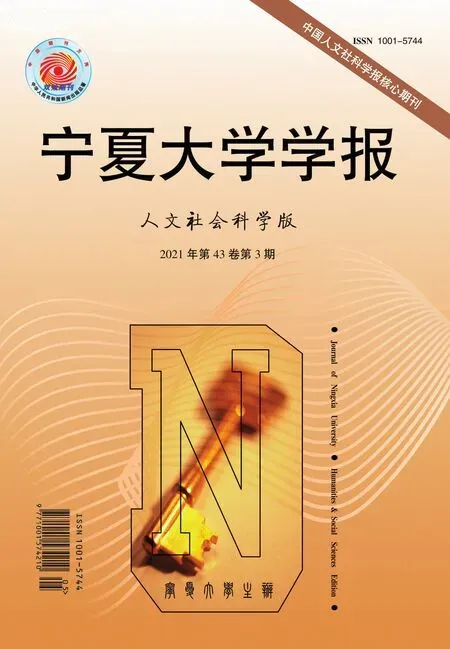《尔雅义疏校补》稿本考录
2021-12-25王诚
王 诚
(浙江大学 古籍研究所/汉语史研究中心,浙江 杭州310058)
清沈锡祚手稿本《尔雅义疏校补》一卷(以下简称《校补》)收入《清代稿本百种汇刊》,由文海出版社印行。沈锡祚,字福庭,归安(浙江吴兴)人,清末学者,事迹不详。据笔者搜考,沈氏有《合校水经注》批校本、《说文解字句读》批校本等存世,除《尔雅义疏校补》外,还与绍兴孙祖同(伯绳)合著有《释名疏证补(附补遗)》。
在考录《校补》之前先简要介绍《义疏》的刊刻版本。《尔雅义疏》(以下简称《义疏》)于道光六年至九年(1826—1829年)初刻入阮元《学海堂经解》(即《清经解》),道光三十年(1850)又由陆建瀛单刻刊行,两种刻本无大差别,均为经过删定的十九卷本,称为“节本”。学界一般认同罗振玉的观点,即“节本”由王念孙删定,但崔枢华提出“节本《义疏》不是王念孙亲自删成,而是在王氏批校的影响之下,由别人删订而成的”[1]。咸丰五年(1855)高均儒从严杰之子严鹤山处觅得《义疏》原稿的严钞本,交由杨以增刊印,事未竟而杨去世,又由胡珽于次年刻成,为《义疏》杨氏本(或称杨、胡本),是为“足本”(中国书店曾有影印[2])。同治四年(1865)郝懿行之孙郝联荪、郝联薇校订、重刻杨、胡本,此即“家刻本”,也是“足本”(上海古籍出版社曾有影印[3])。光绪五年(1879)至十年,郝联薇又据家刻本重加校刊,辑入《郝氏遗书》。《校补》所据版本为陆建瀛单刻本。手稿为行草书,字迹潇洒流畅,偶有一二涂改。沈氏“杂引群书字义,以补原疏之阙,或纠其缪”[4]。全卷仅三十余条,但条条凿实,有理有据。本文对其逐条考辨并加以迻录,分为校勘和补证两大部分内容,供《尔雅》及《义疏》研究者参考。
一 校勘
沈氏对《义疏》的校勘包括诸多方面,既有《尔雅》原文、《尔雅》郭璞注,也有《义疏》所引《说文》、贾谊《新书》、《文选》注、慧琳《一切经音义》等。
(一)《尔雅》校勘
1.《尔雅》异文
《释木》:“洗,大枣。”锡祚按,大枣亦作犬枣,《梁纪》以“蹲鸱”对“洗犬”,疑唐以前《尔雅》“大枣”有作“犬枣”者。(P14)
按,明梅鼎祚《梁文纪》:“若其珍异,则修筵斯溢,千品万类,不可详悉。西母灵桃、南楚萍实、东陵之瓜、北燕之栗、湖畔之柿、江阴之橘、张掖白柰、恒阳黄梨、河东洗犬、陇蜀蹲鸱,并怡神甘口,穷美极滋。”“蹲鸱”即大芋,因状如蹲伏的鸱,故称,又上下文都是珍奇果品,故“洗犬”盖指大枣。此条首尾有墨框。据核,足本《义疏》比节本多出一段:“又按,《白帖》以‘洗犬’俪‘遵羊’,又以‘蹲鸱’对‘洗犬’,‘犬、大’形淆,可知唐本‘大’一作‘犬’。《释文》不收,陆德明盖未见此本也”[5]。推测沈氏后来见到足本,故拟删去。
2.《尔雅》误字
(二)郭注校勘
(1)《释水》:“瀵,大出尾下。”注:“今河东汾阴县有水口如车轮许,沸涌出,其深无限,名之为瀵。”锡祚按,《列子·汤问篇》殷敬顺《释文》引郭注“水口”作“水中”,“许”下有“大”字,“无限”作“无底”,“名之为瀵”作“名曰瀵”。(P14)
按,殷敬顺是唐人,故《列子释文》所引盖据唐本。
(2)《释木》:“柀,煔。”锡祚按……又郭注“可以为船”下,徐锴《说文系传》引有“又耐埤”三字。(P14)
按:《说文·木部》:“柀,檆也。”《系传》:“《尔雅》‘柀,檆’注曰:‘生江南,可作船,又耐埤。’”《国语·晋语八》:“拱木不生危,松柏不生埤。”韦昭注:“埤,下湿也。”
(3)《释鸟》:“鸟鼠同穴,其鸟为鵌,其鼠为鼵。”注:“穴入地三四尺……共为雄雌。”锡祚按,司马彪《续汉·郡国志》刘昭注引作“穴地入三四尺……共为雌雄”。又“穴地”《山海经》第二郭注作“穿地”,余与刘昭注所引同。(P17)
按:《尚书注疏》引《尔雅》郭璞注、《史记正义》引《山海经》郭璞注皆作“穴入地”。不过,《宋书·索虏列传》:“德祖于城内穴地,入七丈。”或可为“穴地入三四尺”的佐证。
(三)《说文》校勘
(1)《释天》:“春猎曰狩。”疏:“狩者,《说文》云‘犬田也’。”锡祚按,今本《说文》“犬田”系“火田”之讹,严氏可均《说文校议》、段氏玉裁《说文注》皆据《韵会·二十六宥》所引正。(P8)
按:《说文·犬部》:“狩,火田也。”段注:“火,各本作‘犬’,不可通。今依《韵会》正。《释天》曰:‘冬猎杀狩。’《周礼》、《左传》、《公羊》、《穀梁》、《夏小正》传、《毛诗》传皆同。又《释天》曰:‘火田为狩。’许不称‘冬猎’,而称‘火田’者,火田必于冬。《王制》曰:‘昆虫未蛰,不以火田。’故言火以该冬也”。
(2)《释兽》:“狻麑似虦猫,食虎豹。”疏:“《说文》:虓,一曰师子。”锡祚按,今本《说文》“一曰师子”下有夺文。唐释元应《一切经音义》卷廿二引作“一曰师子大怒声也”。(P19)
按,此为沈氏据《玄应音义》校《说文》。《说文古本考》云:“盖古本当如元应书卷廿三所引,‘大’当为‘又’,今本夺‘一曰怒声也’五字耳。”《说文义证》《说文句读》都指出当作“一曰师子大怒声也”。
(四)《新书》校勘
《释亲》:“族昆弟之子相谓为亲同姓。”疏:“《贾子·六术篇》:从曾祖昆弟又有子,子为族兄弟。”锡祚按,《汉书·礼乐志》如淳注引《贾子》作“族昆弟”,今本作兄似误。(P5)
(五)《文选》注校勘
(1)《释诂下》:“关关噰噰,音声和也。”疏:“《南都赋》及《归田赋》、《笙赋》注并引‘噰噰’作‘嘤嘤’,疑因《释训》‘丁丁嘤嘤’相涉而误也。”锡祚按,《归田赋》“交颈颉颃,关关嘤嘤”,李善注引:“《尔雅》曰:‘关关噰噰,音声和也。’《释训》曰:‘丁丁嘤嘤,两鸟鸣也。’”(据胡氏仿宋本)是李氏所见之《尔雅》与今本同,又《笙赋》“嘤嘤关关”,李注引《尔雅》曰:“关关嘤嘤,音和也。”又《南都赋》“嘤嘤和鸣”,李注引:“毛诗曰:‘鸟鸣嘤嘤。’《尔雅》曰:‘关关嘤嘤,声之和也。’”此皆涉正文而误。(P2-3)
按:《笙赋》《南都赋》李善注引《尔雅》“噰噰”作“嘤嘤”,涉正文而误,但《归田赋》李注引《尔雅》不误。郝疏所述不确。
(2)《释言》:“琛,宝也。”疏:“《文选·思元赋》旧注:‘琛,质也。’质与宝异,琛质之训与《尔雅》又乖,疑未能定也。”锡祚按,毛氏汲古阁、叶氏海录轩并胡氏仿宋本所刻之《文选·思元赋》“琛”字注皆作“宝也”,惟明刻《文选》俗名三黑口本则训琛为质,此因宝质字形近而讹,不足为据也。(P5)
按:郝懿行谓“疑未能定”,是其所据版本的问题。沈氏核《文选》诸版本,唯明刻本作“质”,认为是“宝”“质”二字形近而讹。
(六)《一切经音义》校勘
《释地》:“邑外谓之郊,郊外谓之牧,牧外谓之野,野外谓之林,林外谓之坰。”疏“王砅”应作“王冰”。锡祚又按,《一切经音义》卷二十二引《尔雅》云:“邑外谓之郊,郊外谓之也野,野外谓之牧,牧外谓之林,皆各七里,林外谓之坰,坰无里数,设百里之国邑,王者之界也。”此系连注并引,与今本及疏中所据李、王诸家引本又复不同,录之以备参考。(P10)
按,此条郭注云:“邑,国都也。假令百里之国,五十里之界,界各十里也。”沈氏指出慧琳《音义》所引不同于今本及他本,比《尔雅》原文多出部分是《尔雅》注的内容。
(七)郝疏校勘
沈氏对郝懿行疏的校勘大致包括文字讹误、词语倒误、书证误引和他书异文三个小方面。
1.文字讹误
(1)(卷一第二十七叶)疏“王砅”。锡祚谨按,《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之《黄帝素问》:“唐王冰注,晁氏《读书志》作‘王砅’,盖欲附会杜甫诗而改之。”疏引作“砅”系承晁氏之误。(P4-5)
按,《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子部五医家类“黄帝素问二十四卷”条已指出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中的“砅”字之误。《义疏》中“王冰”皆作“王砅”,沈氏谓其承晁氏之误。
(2)(卷九第二十叶)疏:“按今‘荼’字古作‘荼’。”锡祚按,“今荼”应作“今茶”。(P14)
(3)(卷十五第十一叶)疏:“口中吐白廾。”锡祚按,“廾”系“汁”字之讹。(P15)
按:以上两处误字在家刻本、杨氏本中均已改正。
2.乙正倒误
(卷十三第二叶)疏:“麆,本今作麤。”锡祚按,“本今”应作“今本”。(P12)
按,此误家刻本、杨氏本均未改正。
3.纠正误引
(1)(卷十四第十二叶)疏:“《齐民要术》引《博物志》:一名英桃。”锡祚按,樱桃一名英桃,系《齐民要术》注引《博物志》(注系孙氏所作,见《四库全书简明目录》)。(P12)
(2)(卷十七第十九叶)《尔雅·释鸟》:“鹣鹣,比翼。”疏:《说文》“鹣鹣”,众家作“兼兼”。锡祚按,《说文》无鹣篆,古只作“兼”。《水经注》卷三十六“兼比翼鸟,不比不飞”,疏内所引《说文》系《释文》之讹。(P16)
4.他书异文
(卷十六第七叶)疏:“其久病心腹之疾皆愈。”锡祚按,“疾”字卢氏文弨校本贾谊《新书》作“积”。(P15-16)
二 补正
沈氏对《义疏》的补正主要是补充书证材料和纠正郝疏错误两方面,此外,还涉及对字际关系的说明以及辨正字音和考证地名,下面分别考录。
(一)补充书证材料
包括为《尔雅》训释和郝懿行《义疏》补充书证。
1.为《尔雅》训释补充书证
(1)《释诂上》:“祖,始也。”疏:“‘祖’,古金石文字作‘且’。《书》‘黎氏阻饥’,《史记集解》据今文《尚书》作‘祖饥’,《索隐》据古文作‘阻饥’,《诗》‘六月徂暑’笺:‘徂犹始也。’”锡祚按,《书》“黎氏阻饥”,《史记·五帝本纪》作“始饥”,《汉书·食货志上》作“祖饥”,孟康曰:“祖,始也”。(P1)
2.为郝疏补充书证
(1)《释诂上》:“禋、祀、祠、蒸、尝、禴,祭也。”疏:“《月令》‘季秋大飨帝尝’,郑注:‘尝者,谓尝群神也。天子亲尝帝,使有司祭于群神。’然则郑意亦以此为祭名,而不以为时祭之尝矣。唯禴未闻,可姑阙焉。郭以为皆四时祭名,恐未然也。”锡祚按,《易·既济》“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禴祭”,王弼注曰:“牛死之盛者,禴祭之薄者。”又“禴祭”,《汉书·郊祀志下》引作“瀹祭”,颜师古注曰:“东邻,谓商纣也;四邻,周文王也。瀹祭谓瀹煮新菜以祭,言祭祀之道莫盛修德,故纣之牛牲不如文王之藻也。”据此是“禴”亦凡祭之通名也。(P3-4)
按,郭璞注:“《书》曰:‘禋于六宗。’余者皆以为四时祭名也。”而郝懿行认为“祠、蒸、尝、禴四者……盖不独时祭有此名,而凡祭亦被斯名也”,他找出了前三者为祭通名的证据,唯独找不到“禴”为祭通名的证据。沈氏为他找到了两个例证,证实了他的观点。
(2)《释诂下》:“豫,安也。”疏:“豫者,豫、誉古字通……故《文选·曲水诗序》注引《孙子兵法》曰:‘虽优游暇誉,令犹行也。’暇誉即暇豫也。”锡祚按,《晋语》:“暇豫之吾吾,不如乌乌。”正用豫本字。(P4)
按:沈氏补充了“暇豫”之“豫”用本字的例证。又如《国语·晋语二》:“主孟啖我,我教兹暇豫事君。”韦昭注:“暇,闲也;豫,乐也。”《说文·象部》:“豫,象之大者。”段注:“此豫之本义,故其字从象也。引申之,凡大皆称豫……大必宽裕,故先事而备谓之豫,宽裕之意也。宽大则乐,故《释诂》曰:‘豫,乐也。’《易》郑注曰:‘豫,喜豫说乐之儿也’”。
(3)《释宫》:“有木者谓之榭。”疏:“古无‘榭’字,借‘谢’为之。”锡祚按,《荀子·王霸篇》“台谢甚高”,杨倞注:“谢,与榭同”。(P7)
(4)《释器》:“罍,器也。”疏:“《正义》引《异义》:罍制,《韩诗》说‘金罍,大夫器也。天子以玉,诸侯、大夫皆以金,士以梓’。”锡祚按,《汉书·文三王传》“孝王有雷尊,直千金”,与《韩诗》说合。(P7)
(5)《释鸟》:“鴽,鴾母。”疏:“古盖读‘無’如‘模’。”锡祚按,無、模古通,《说文》:“無,丰也。从林。或说规模字。”(或说系指“無”为规模字,严氏、段氏诸家皆误读,唯桂氏馥《说文义证》、胡氏秉虔《说文管见》、王氏筠《说文句读》不误)《韩诗外传》卷五:“儒者,儒也。儒之为言無也。”借無为模,与或说正合。(P16)
(6)《释虫》:“蟫,白鱼。”疏:“衣鱼,一名白鱼。”锡祚按,《列子·天瑞篇》“朽瓜之为鱼也”,又苏颂《图经》云“衣鱼生于瓜子”,据此是蟫即朽瓜所化也。(P15)
(7)《释兽》:“猩猩,小而好啼。”疏:“《王会篇》:都郭生生,欺羽生生,若黄狗,人面能言。”锡祚按,《水经注》卷三十六:“平道县有猩猩兽,形若黄狗,又状貆豘。人面,头颜端正,善与人言,音声丽妙,如妇人好女。对语交言,闻之无不酸楚。其肉甘美,可以断谷,穷年不厌。”(“丽妙”据《王会篇》王氏应麟补注本所引乙正)。(P19-20)
(8)《释畜》:“駮,如马,倨牙,食虎豹。”疏:“《说苑·辨物篇》云:駮之状有似駮马,今君之出,必骖駮马而亩。虎所以不动者为駮马也。”锡祚按,此说亦见《管子·小问篇》:“桓公乘马,虎望见之而伏。桓公问管仲曰:‘今者寡人乘马,虎望见寡人而不敢行,其故何也?’管仲对曰:‘意者君乘駮马而洀桓,迎日而驰乎?’公曰:‘然。’管子对曰:‘此駮象也。駮食虎豹,故虎疑焉’”。(P20-21)
(二)纠正郝疏之误
(1)《释诂上》:“身,我也。”疏:“身者,郭云:今人亦自呼为身。按,今时唯狱词讼牒自呼为身。”锡祚按,《越绝书·外传本事》:“嫌以求誉,是以不箸姓名,直斥以为身者也。”南汇张氏文虎《舒艺室随笔》云:“《蜀志·张飞传》:飞据水断桥,嗔目横矛,曰:身是张益德也。”此所谓自呼为身也。(P1-2)
按,郝懿行认为“身”作第一人称只用于司法文书,但沈氏举出例子否定了郝说,证明自呼为身并没有特定的场合限制。
(2)《释亲》:“夫之弟为叔,夫之姊为女公,夫之女弟为女妹。”疏:“《正义》:‘女妐,谓婿之姊也;女叔,谓婿之妹。’然则《尔雅》及郭注‘女妹’并‘女叔’之误。”锡祚按,钮氏树玉《段氏说文注订》云:“《尔雅》当本是‘女叔’,故郭注云:‘今谓之女妹是也。’是郭注本未误,其改当出郭注后。”此说确不可以易,若郭注亦作女叔,其义便不可通。(P6)
按,郝懿行认为《尔雅》原文及郭注中的“女妹”应作“女叔”,沈氏引钮树玉的说法,《尔雅》原文的“女妹”确应为“女叔”,但郭璞注中的“女妹”并不误。
(3)《释山》:“小山岌,大山峘。”疏:“《说文》云:‘馺,马行相及也。读若《尔雅》小山馺大山峘。’此言馺读若岌,则非《尔雅》本作馺矣。疑馺字误。”锡祚按,“岌”系《说文》新附字,作“馺”非误。陈氏瑑《说文引经考证》云:“馺,马行相及也。读若《尔雅》小山馺大山峘。今作岌。郭云:岌谓高过。钱詹事曰:郭说未然,峘即恒之讹,恒义为绵亘,故以恒得名,山相及即绵亘之象,当依《说文》作馺,用相及之意训,此亦读若不破字。”又按,《广韵》下平十七登“恒”下即列“峘”字,引《尔雅》此文,是恒之为峘,犹馺之为岌,皆后人因《释山》而改。乃上平二十六桓复收峘字,并引《尔雅》文,定为后人所增。至《释文》引《埤仓》作垣,亦误。(P10-11)
按,郝懿行怀疑《说文》读若中的“馺”当作“岌”,但沈氏指出“岌”是《说文》新附字,不会出现在说解中,同时引钱大昕的观点,认为《说文》有“读若不破字”的体例,所以许慎所据为《尔雅》古本,古本作“馺”。
(4)《释木》:“柀,煔。”疏:“宋本及《释文》俱作煔,不成字,盖黏字之误,徐铉作,亦非。段氏《说文注》依《尔雅》改作黏是也。锡祚按,《说文》:“柀,檆也。”徐铉据补檆篆于下,严氏可均《说文校议》、钮氏树玉《说文新附考》、钱氏坫《说文斠诠》均据《尔雅》此文订正,今通行之孙氏仿宋小字本《说文》并毛氏汲古阁本以及祁刻《说文系传》,皆从木作檆,惟段氏玉裁注本讹檆为(其所著《汲古阁说文订》并未举及此字,故知是讹),并误忆《尔雅》亦作柀黏,遂注云:“依《尔雅》正为黏。”此盖一时失检耳。至煔篆《说文》收在炎部,郝氏竟指为不成字,亦未免疏于考核也。(P13)
(5)《释兽》:“魋如小熊,窃毛而黄。”疏:“《说文》:‘魋,如小熊,赤毛而黄。’《释文》:‘魋,徒回反。’引《字林》云:‘兽如熊,黄而小。’郭注本《说文》。”锡祚按,《说文·鬼部》“魋”篆系徐铉新修十九文之一,训为神兽。段氏注本补入《隹部》,注云:“依《尔雅》文惟改窃作赤,疏中所引是也。”乃竟认为许氏原文为郭注所本,则大误耳。(P13)
按,“魋”其实是徐铉十九个新修字符之一,原属《鬼部》,段玉裁误据《尔雅》补入《隹部》,郝懿行倒果为因,反而认为郭璞对“魋”的解释本于《说文》。
(三)说明字际关系
按,郝懿行只指出,“矢”“侯”为异文,而沈氏根据《说文》古文清楚说明了“矢”是如何变为“”的。
(2)《释宫》:“垝谓之坫……椹谓之榩。”疏:“椹者,斫木质也。榩者,《诗》云:‘方斫是虔’……《文选·捣衣诗》注引《尔雅》作‘砧谓之虔’。‘砧’‘榩’俱俗体字。”锡祚按,按椹亦俗体,《说文》所无。钮氏树玉《说文新附考》据瞿镜涛云:“《周礼·司弓矢》‘椹质’,《说文·弓部》引作‘甚质’。砧即甚之俗字,或作枮。《释宫》释文:椹,本又作砧。”据此知砧即椹,而古只作甚,又《广韵》下平二十一侵椹重文作枮,知砧又枮之俗字。(P6-7)
按,沈氏在郝懿行的基础上补充说明“椹”“砧”“枮”都是“甚”的俗字。
(3)《释天》:“在壬曰玄黓。”疏:“元黓者,《天文》篇云:戌在壬曰元黓。”锡祚按,“黓”字《说文》所无,古只借“弋”为之。《文选·张衡〈西京赋〉》“建元弋”,薛综注:“元弋,北方第八星。”又《汉书·文帝纪赞》“身衣弋绨”,如淳注曰:“弋,皂也。”贾谊曰:“身衣皂绨。”师古曰:“弋,黑色也。”是弋本有黑义。其证“黓”即“弋”之俗体耳。(P8)
(4)《释畜》:“騉駼,枝蹄趼,善升甗。”疏:“《西京赋》薛综注:……昆駼,如马,枝蹄。”锡祚按,胡氏仿宋本《文选》作“跂蹄”。《说文》:“跂,足多指也。巨支切。”枝系跂之借字。(P21)
(四)考证地名
《释地》:“东陵,阠。”疏:“东陵有二处,‘阠’字不见所出。”锡祚按,钱氏大昕《养新录》云:“《释地》‘东陵阠’,先儒皆未详其地……予按,《说文·手部》‘扟’读若莘,是‘莘’与‘阠’通矣。《庄子·骈拇篇》‘盗跖死利于东陵’,陆氏《释文》:‘东陵,陵名。今名东平陵,属济南郡。’又《春秋》成二年传‘师从齐师于莘’,杜注但言齐地,今据下文‘华不注’‘华泉’皆在济南府,莘与华不注、华泉相去不远,亦当在济南,则《尔雅》之‘东陵阠’疑即《左氏传》之‘莘’也,古本当从手旁,后人改从阜旁耳。”(《齐乘》:东平陵城,城在济南东七十五里)”。(P9-10)
按,沈氏引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依据文献考出了先儒未详的“东陵阠”之所在,认为“阠”即《左传》之“莘”。
(五)辨正读音
《释草》:“莙,牛薻。”疏:“《说文》:‘莙,牛藻也。从艸君声,读若威。’《释文》:‘莙,孙居筠反。’若依孙炎当读为君,如从《说文》当读为威。”锡祚按,莙字《颜氏家训·书证篇》引《音隐》瑰反,又《墨子·明鬼篇下》“不能敬莙以取祥”,毕氏沅校注云:“言敬威以取祥也。”是读威系古音。(P12)
按,“莙”字孙炎和《说文》的读音不同,沈氏认为《说文》读为威是“莙”的古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