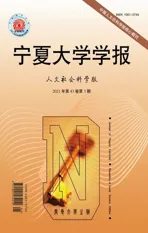历史真实与文学想象
——科伦·麦凯恩的传记小说《舞者》研究
2021-12-25霍舒缓
霍舒缓
(南开大学 文学院,天津300071)
传记创作有着悠久的历史,“早期的、传统的论述更倾向于突出传记的真实性,强调传记的历史属性,而当代批评家们则刻意凸现传记的虚构性,力图把传记拽向文学一边”[1]。随着时代的发展,现当代的传记创作过多地关注了文学性而逐渐淡化其历史性,契合了后现代时期的文学创作倾向和特点。事实上,传记小说同时具有传记的纪实特点和小说的虚构特点,是在后现代传记创作观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混血”体裁,文学性与史实性、真实与虚构成为其基本特征。在传记小说的创作过程中,虚构和纪实成为必要的表现手法,而且两者之间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科伦·麦凯恩(Colum McCann,1965—)是当代最负盛名的爱尔兰作家,他的长篇小说《舞者》(2003)成为当代传记小说的优秀作品。这部小说围绕从苏联叛逃至西方世界的芭蕾舞明星鲁道夫·纽瑞耶夫(Rudolf Nureyev,1938—1993)跌宕起伏而又星光四射的一生展开。出身贫寒的纽瑞耶夫依靠自己的天赋和努力登上了芭蕾舞台,并以精湛的舞技和散发的艺术魅力征服了西方人,但他的负面新闻却接连不断,政治、金钱成为他避不开的话题。麦凯恩在小说中真实地反映了苏联20世纪中叶人们生活的悲苦和艰难,也揭示了缺乏自律的放纵和挥霍对个人名誉的影响,小说语言优美而极具诗意化。就小说叙事层面而言,历史真实和文学想象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体现了传记小说虚实相生的特点。
一 真实与虚构的融合
麦凯恩在小说扉页写道:“本书系虚构作品。除若干知名人物使用的是其真实姓名外,书中名字、人物和描绘的事件都源自作者的想象。”在这部小说中,主角鲁道夫·纽瑞耶夫和在书的第三部中出现的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以及他的搭档玛格·芳婷(Margot Fonteyn)等是在现实中确有其人的艺术家,可是除了这些世界知名的人物之外,围绕在鲁道夫周围的书中人物又都是作者虚构出来的,比如鲁道夫的启蒙芭蕾舞老师安娜,以及十分赏识他的安娜的丈夫和女儿等等,这些人物都是作者为了塑造人物形象,增强小说可读性虚构出来的。“在非虚构小说,新新闻体、‘纪实小说’等等诸如此类的叫法里,小说技巧会使人激动、紧张,激发人的情感,而传统的报道或史学著作并不追求这些,但对读者来说,保证故事是‘真实的’又给它增添了吸引力,这是任何小说所不可比拟的。”[2]最突出的小说技巧就是虚构,但传记小说家是“戴着锁链写作”[3]。小说技巧给了作者很大的创作空间和主动性,但是虚构必须以一定的历史事实为基础,虚构与真实相互交融、相互统一是其根本。在《舞者》中,麦凯恩出色地运用后现代小说创作技巧,以一定的历史真实为基础,打破了传统传记的创作手法和特点,将真实历史与虚构故事融合在一起,使其成为独具特色的传记小说。读者在小说中看得到历史的真实,却又感受到想象带来的新奇。在麦凯恩精心的刻画中,纽瑞耶夫成为作者真正点燃想象力的人物。小说的主题是舞蹈,舞蹈和动作成为小说重要的叙事主题因素,舞蹈、手势和身体在小说中有着重要的隐喻意义,成为主人公治愈创伤的场域,也是未来的寄托。
科伦·麦凯恩在《战斗中:美国作家与拳击》一书的前言中谈到“文字是有力量的”[4],并将这个信条贯穿到小说创作中。这部小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其复杂的叙事结构,在这样的叙事结构中,有多个主体来主导叙事而不是单一主流的叙事模式,类似于中心辐射型的叙事模式。麦凯恩在《舞者》中加入了大量的传记叙事,文中主人公的入场和出场都围绕着舞步,在身体的旋转中强调叙事的流动性。这是类似于万花筒形式的动态叙事模式,视角不断地转换,个人身体的运动与环境的感知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从认知科学的层面来看,身体运动和感官刺激有着紧密的关系,使得视觉感知发挥重要作用。麦凯恩在《舞者》中对身体运动的叙事以及伴随运动的感知,让我们总结出了运动叙事学的美学意义。舞者作为主题和形式的代表,让运动的身体处于中心位置。鲁道夫·纽瑞耶夫是非常出色的舞者,这更凸显了身体运动的中心地位。作为小说中的传记人物,鲁道夫自身就有着表演者的影响力,他出现的房间会突然充满磁性,每个人之间似乎都有了联系,这实际上是身体的表征。在这种情况下,房间内观众的情感驱使他们彼此之间产生了联系,身体的反应解释了深层次的心理和精神上的错位。
曾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提出“新传记”概念的英国女作家兼文学评论家伍尔夫(Virginia Woolf,1882—1941)认为,“真实的事实和虚构的事实两者并不兼容。传记作家努力地将两者融合在一起。事实上虚构的生活专注典型事件,使得生活看起来更加真实……因此,传记作家的想象力得到拓展,借助小说家的艺术手段来展现生活”[5]。我们惊叹于作者在《舞者》开篇对战时苏联冬天的描写以及士兵境况的描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苏联冬天,士兵们为了生存,必须保住任何一丝暖气,“如果要拉屎——虽然并不经常——只能拉在裤子里。他们任其留在那儿,直到冻硬了,等找到有遮掩的地方,再把它拿出来丢掉……他们还学会把暖暖的尿液袋夹在腿间……”[6]。麦凯恩对战场场景描写时显示出来的高超技艺让我们在佩服的同时也难辨真假,苏联冬天的冷和“二战”战场士兵的悲惨境况都是事实,作者在事实的基础上作出的具体叙述则属于小说家的创作领域。就整部小说而言,我们很难区分出哪些部分是真实的,哪些部分是虚构的,除了一些具有时代特点的历史大事件,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纽瑞耶夫的叛逃。此外,麦凯恩自己在《舞者》的致谢部分也承认,“我时而将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历史人物浓缩成一个角色……有部分与知名人物相关的事件是真实的;其他则是虚构的”[7]。麦凯恩对细节的描写,让我们分不清真实与虚构的界限在哪里,这就是虚构的真实。作者通过具体的细节描写,在虚构中赋予主人公以真实性,这是麦凯恩对文学真实性的理解和实践。传记小说解构了传统认识中真实与虚构的对立和矛盾,成为一个有效的文本策略。麦凯恩在谈到《舞者》的创作灵感时提到了爱尔兰。
我从一个在都柏林的朋友那里听到了这个故事……大致是有一天他的父亲带了一台电视机回家,当他插上电源插头时,鲁道夫·纽瑞耶夫的形象出现在电视上,从那时起鲁道夫·纽瑞耶夫成为他的偶像。对于一个7岁的都柏林工人阶级男孩来说被俄罗斯舞蹈家所吸引是一件相当不可思议的事情,这位舞蹈家在布什科里亚(Bashkeria)长大,在列宁格勒接受训练,然后叛逃到巴黎。这个节目可能是从德国某个地方传过来的,也可能来自英国广播公司。所有的这一切都在柏林这个工人阶级的公寓里碰撞,散发开来。[8]
麦凯恩在这里谈到的具体的故事来源以及对7岁男孩和工人公寓的强调都在证实小说故事的真实性。此外,《舞者》的叙事模式避开了时间线性模式,而是采用了一系列的小故事,虽然这些故事都与鲁道夫有关,但是彼此之间有着独立性,共同建构鲁道夫的形象。
后结构主义历史学家海登·怀特在文本历史的内在文学性方面作出了重要的论述。海登·怀特在《作为文学虚构的历史文本》一文中阐述,“如何组合一个历史境遇取决于历史学家如何把具体的情节结构和他所希望赋予某种意义的历史事件相结合。这个作法从根本上说是文学操作,也就是说,是小说创造的运作”[9]。即作者在传记小说的创作过程中历史事件都是无序的,他需要对这些事件进行剪裁、拼贴,历史事件属于过去,我们不可能亲历和感受,所以只能进行建构使其更加饱满,从侧面反映出作者的创作意图。在建构的过程中,以“虚构”为主要特征的文学创作是其主要采取的表现手法。正如歌德在自传式的创作中对历史事件的处理特点一样,“当历史事实对自传事实造成泰山压顶之势时,他用‘浓入’法;当历史事实对自传事实若即若离时,他则用‘淡出’法。前者的用意是透视历史事件留下的心影心响;后者的目的在于提供一个历史背景。最后的宗旨只有一个:‘说明’‘人与其时代的关系’”[10]。正确处理好历史和文学的关系,准确把握事实和虚构成分之间的疏密在传记小说的创作过程中至关重要;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历史与文学、真实与虚构之间的关系不是针锋相对而是相互渗透和融合的特点。《舞者》中所记述的历史真实事件分别是1939—1945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1961年纽瑞耶夫投奔到他心中的西方自由之地、1962年他和英国皇家芭蕾舞团合作并搭档玛格·芳婷(Margot Fonteyn)以及他的同性恋身份等等。与纽瑞耶夫有关系的各种事件镶嵌在小说的各个部分,这些历史事件在麦凯恩精心的安排和布局下,《舞者》烙下了他独特的创作风格,给我们呈现出一个麦氏纽瑞耶夫。
二 后现代文本特征
传记小说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学体裁,它与真实历史现实的关系复杂交错。传记小说尽可能地通过组织事实证据来表现传记人物的真实生活,表明特定历史情景下,特定个体的特征和品质。麦凯恩对自己用小说这个媒介来写传记的目的非常自觉,而且在陈述中解释了他的创作思想。传记小说的标准是创造性地使用材料,这基于创作者对传记人物特点的看法和理解。创作者所选择的具有代表性的历史真实事件在小说中必然有着转喻以及象征的地位。真实的历史事件材料方便小说中细节叙述的展开,支撑着小说的内在真实性,这样虚构的情节或人物对话就给人真实感。真实和虚构相辅相成,使得《舞者》有着高度的复杂性,揭示了一个比真实叙述更为尖锐的真相。麦凯恩在小说题材的传统框架下,从事实中创造“传记”,利用小说结构技巧和叙事特点,来想象人物真实性。小说中意识流的运用,目的是为了揭示历史人物的复杂内心以及自我的多样化。外部世界的内化以及内在心理世界的潜在话语共同组成了完整的现实生活。
在《舞者》中,就传记创作而言,麦凯恩没有虚构,纽瑞耶夫在历史上是真实存在的,但他在写实的同时也在进行着小说创作。对麦凯恩而言,“读者可以在扑朔迷离的天地中进行摸索,而小说家却不能。他必须驾驭自己的作品。在这儿投下一线光亮,从那儿又留下一丝阴影。他还要不断自问,用什么办法才能使情节取得最好的效果?他事前应心中有数,要置身于小说之上,动笔之前,要始终考虑到因果关系”[11]。故麦凯恩明显带着小说创作的意识在写作,他独特的叙事策略成为后现代作品最好的注脚。首先,多视角叙事是该部小说最大的结构特点,通过视角的不断转换,从各个侧面来描绘主人公传奇的一生,而每个叙述视角都有自己独特的不可替代性。围绕纽瑞耶夫身边其他人的叙述,我们可以得到一个更加立体、更具层次感的主人公,而不是扁平人物。法国叙事学家热奈特(Gérard Genette,1930—)在《叙事话语、新叙事话语》(1972)一书中,从叙事学家托多罗夫视角的分类总结出三种叙事视角:第一类全知的叙述者,即“叙述者>人物”;第二类叙述者只了解自己,即“叙述者=人物”;第三类叙述者比人物知道的少,即“叙述者<人物”。热奈特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零聚焦”“内聚焦”和“外聚焦”叙事。麦凯恩作为当代有成就的小说艺术家,深谙叙事视角对小说艺术审美层次的提升。
小说《舞者》中多视角叙事策略和多样性的运用和把握,体现了麦凯恩高超的语言运用能力,使人物的性格得到多方面的展现。在小说的开篇,作者采用的是“零聚焦”的叙事手法。在无所不知的叙述者娓娓道来的具体描述中,给我们展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苏联冬天的战场场景和士兵的境况,为出身贫寒的小说主人公(为士兵表演舞蹈)的上场做好铺垫和氛围烘托。此外,在小说的三个部分中,第一人称的叙述者是热奈特“内聚焦叙事”的不断变换,比如鲁迪儿时的玩伴、姐姐塔玛拉、芭蕾舞启蒙老师安娜的女儿尤丽娜和丈夫、智利女朋友罗莎玛丽亚,后来还有他在伦敦的专用芭蕾鞋匠阿什沃夫、法国的女管家奥黛尔,甚至他的同性恋朋友等等。虽然这些人物的叙述都以鲁迪为中心从自己的视角来叙述,但是他们同时也在描述各自的生活。这种叙事视角更能体现出叙事的客观公正性,强化了叙事的真实性。此外也为作者的间接介入提供了机会和平台,通过文中其他人物的叙述,作者可以适时地加入评论性的语句,从而使主人公形象更加饱满的同时也增加了阅读难度,提高了读者的阅读兴趣。事实上,这种小说写作技巧是一种“事实”,因为“无论什么事件,其经历者通常会不止一人,当然是同时。小说对同一事件的描述可以采用不同的视点——但一次只能用同一种视点。即使是采用那种‘无所不知”的叙述方法、从全知全能的上帝般的高度来报道一件事,通常的做法也只是授权给一到两个人物,使之从自己的视点叙述故事的发生发展,而且主要讲述事件跟他们的关联”[12]。小说中还出现了极少出现的“你”的视角,事实上这里的听众是虚拟的,即使口口声声的“你”也是“我”在叙述,如《舞者》第二部分出现的以“你看见他……”为句子开头的长篇对主人公的叙述,这是麦凯恩为了营造虚拟的对话效果而创作的,似乎是想把读者拉入故事的讲述中。麦凯恩精湛的小说创作技巧和语言能力在这里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和展示,也为小说增强了可读性,更富审美属性。
除了多视角的叙事策略外,就作品结构而言,麦凯恩还在《舞者》中穿插了各种文本形式,比如日记、书信、报道访谈、报纸杂志评论等。当代传记小说增强了传记小说的纪实性,打破了传统传记创作的纪实性和小说创作虚构性之间的沟壑,也体现了叙事的客观公正性,体现出小说的“非虚构化”,但这是一种伪真实感,虽然是类似一种新闻报道式的描述。“它所体现的言语和所表现的非言语性的事件,都是杜撰出来的。但一封杜撰出来的书信跟一封真信真假难辨。”[13]此外,日记和书信体裁省略了许多描写性的语言而强调内心生活,读者能够处在一个优越的地位来窥探人物的内心,人们在书信这个私密空间中方便尽情地倾诉自己的个人思想和情感。此外,纽瑞耶夫内心独白也是一大亮点,麦凯恩在这部分虽然着墨不多,但是却充分运用了后现代小说的意识流技巧,把主人公纷繁复杂的思维特性刻画出来。如在小说的第二部分中:“舞鞋。许可证。把参加音乐学院音乐会的衣服洗干净。公交车上的那个男孩。警觉性。”[14]我们可以看出主人公思维意识的跳跃性、不连续性和联想性,这打破了传统小说的叙事模式,文本的展开依靠的是心理逻辑。作者通过在艺术形式和技巧方面的新颖处理,表现出反传统传记纪实创作的特点,使文学的表现形式更为丰富。
麦凯恩在小说致谢部分写道:“在为这本书所做的调查研究中,我有幸阅读了大量文献,虚构的、非虚构的、新闻报道、诗歌以及网络资源”[15]。从小说素材的积累来看,这些材料增强了小说的叙事效果和表达深度。这种作品结构范畴是后现代主义,打破了传统小说创作材料的体裁。后现代主义文学实践是对传统文学形式以及叙事本身进行解构,在形式上不断创新。后现代主义小说,打破了传统的线性叙事,挑战了故事情节,文本成为开放性的文本,这也是后现代注释的“不确定性”。麦凯恩在《舞者》中创作思想方面的实践和创新是对传记文学的拓展和丰富。在一次访谈中他说:“我认为内容推出形式。语言、选择的语言,最终将决定小说的形式。若先有形式,有了模型,那是有问题的。”[16]为了使纽瑞耶夫的形象更加丰满和立体,麦凯恩巧妙构思了小说结构并充分发挥了小说技巧在创作中的作用。作者对主人公几乎没有正面描述,而是侧面地通过他周围的小人物或大人物的眼睛和口吻来观察和叙述。多视角叙述手段的选择,源于作者意图塑造一个形象立体的主人公。
《舞者》无论在小说结构还是叙述形式上都体现了后现代文本的特点,即多视角、片段化结构、文学体裁的多样性。麦凯恩利用眼花缭乱的后现代小说技巧成就了主人公的立体形象,反映出在西方金钱社会中主人公的迷失,解构了西方世界的自由精神。各种不确定性和各种可能性,让读者在不断翻转的叙事手法中视点不断游移,积累阅读美感。
三 传记小说的审美体验
读者的积极参与是文学作品生命力的重要部分,文学作品的评价标准之一是作者是否“从作品表现的思想、感情中得到共鸣,从中享受到乐趣”[17]。读者基于之前对传统传记的阅读经验形成了自己的“期待视野”,即“读者接受文学作品时自身所具有的某种思维定向和先在结构”[18]。而一部作品的好坏取决于“期待视野与作品间的距离,熟识的先在审美经验与新作品的接受所需求的‘视野的变化’之间的距离,决定着文学作品的艺术特性”[19],且成正比关系。所以小说家为了取得一定的艺术效果,不得不打破传统的写作手法,给读者一个对先前经验的否定。《舞者》作为当代传记小说与传统传记有着明显的不同。读者对于一部传记小说的阅读经验即“期待视野”,首先是强调历史真实的传统纪实传记,再者完全是借助虚构手法创作的小说读本。但是麦凯恩为了达到自己的艺术目的,超越了传统,给读者布下一个迷魂阵,他反复切换叙述者和叙事视角,写作技巧上的精巧成为其亮点也突破了传统的传记体写作。小说在整体谋篇布局上打破了传统的线性叙事特点,取而代之以片段化的结构特点。这种结构方式迫使读者跳出传统,努力获取其意义。
麦凯恩在《舞者》的创作过程中,为了获得独特的艺术效果,在小说字体设计方面也是独具特色。不是所有的文字都是统一字体,而是不断穿插有另外一种形式的字体。这出乎读者的意料,即打破了传统的期待视野。正是因为有了期待视野的存在以及不断被打破的过程,读者获得了审美的愉悦。此外,读者之所以在作者所精心构建的迷魂阵中能保持清醒,主要得益于“读者了解的不单是事件的琐碎细节,而且理解了事件作为组合的熟悉模式中的因素的功能。读者之所以理解了这些事件是因为它们被置放进某种情节结构的范畴之内。事件变得令人熟悉起来,不光是因为读者现在对事件获有更多的信息,而且也是因此这些信息作为情节结构符合读者所熟悉的文化中的一部分”[20]。作品是借助读者这个中介才得以不断延续、不断变更,读者在此过程中不断进行着自己的吸收和批判。一部作品存在的意义得益于某一代的读者,只要能被读者所接受,那么作品的生命力就是存在的,过去和现在、新与旧沟通的媒介就是读者。这点也成为通俗和经典文学作品之间的划分标准。
麦凯恩在《舞者》的小说整体结构布局中,契合了沃尔夫冈·伊瑟尔(Wolfgang Iser,1922—2007)理论的关键部分“空白”或“空域”。“文本视角通过叙述者、人物、情节以及内化于文本的虚构读者等透视角度勾勒出作者的观点。空白促使读者对这些模式化的视角进行协调——换言之,它们引导接受者在文本内部完成基本活动。”[21]《舞者》片段化结构之间的空白即使文本本身没有特别说明也是要联系起来的,这样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在各个部分之间不断来往穿梭,通过不断的否定和肯定,最终获得意义。读者的视点是漂移不定的,在各种文本视角中间转换,文本之间的各种不连贯在读者阅读过程中形成各种冲突,各种观念和认识不断地被怀疑和否定,读者阅读期间不断协调渐渐形成阅读的连续性。《舞者》被分为四部分,这些部分之间几乎是独立没有联系的,而各个部分之间的视角不断切换,叙事策略被运用得淋漓尽致,几乎在叙述时用到了所有的人称。读者的阅读行为“在审美经验的主要视野中,接受一篇本文的心理过程,绝不仅仅是一种只凭主观印象的任意罗列,而是在感知定向过程中特殊指令的实现”[22],在不断地来回反复中,读者将片段衔接起来,以形成统一完整的结构。这样读者在阅读实践过程中重新定位调整自己的认识和理解,读者的期待视野进行调整,增强了文本的审美价值。
奈达尔认为,在写作过程中语言、叙事和修辞都对历史事实进行了修改和修正。“所以读者和传记作家都必须认识到修辞、叙事手法和风格不但组织事实,而且也改变事实,以便创造一个文本世界里的生平。”[23]这就是传记小说的实质,即“文本世界里的生平”,亦真亦幻,真真假假。传记小说推翻了历史与文学、虚构与真实的壁垒,作者以小说家的创作意识进行传记写作,这必然烙下了小说写作的技巧与艺术。正因为如此,与传统传记文本相比,后现代时期的传记小说《舞者》给读者以新的阅读体验的同时,也证明了其艺术价值和审美意义。传记小说作为一个整体逐渐向小说题材靠近,小说家的想象与真实人物之间的互动让我们不禁考虑到真实和虚构的界限在哪里。传记小说家在基于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模拟想象传记人物真实的生活,但是传记人物内心的复杂活动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语言建构起来的。实际上,传记小说是一种文学创作技巧,目的是描述更为完整和复杂的现实生活。评论家对传记小说的关注点,一般集中在虚构文学和真实人物之间的冲突和融合。这种叙事模式从本质而言集个体的主观性、当下的时代意识形态和审美模式于一体。
四 结论
事实上,就小说价值而言,忠实于还原历史的现实不是首要任务,因为小说家只是存在的探索者,这点与历史学家的任务不同。传记小说《舞者》主人公鲁道夫在事业巅峰时期背弃苏联,投奔到他心目中的自由之地——西方。但随着叙述的深入,主人公对西方自由精神产生怀疑,除了在舞台上的时间他能真正感受到自己,其余的时间他感到的是空虚和随之而来的孤独。他陷入西方金钱社会编织的陷阱,关于他的负面新闻层出不穷,吸毒、滥交、酗酒、双性恋等等。到底哪里才是自由?鲁道夫当初为了逃脱苏联的政治桎梏而奔向西方自由世界,可是纸醉金迷的西方世界真的自由吗?性别与政治以及自由成为麦凯恩小说中的重要主题。
麦凯恩带着富有同情心的想象力在吸收了关于历史人物和他的世界的已知事实的基础上,为我们无法了解的经验创造了一个体验的场所。传记小说将心理学和现代小说的创作技巧融入文体中,事实和想象的话语模式在小说中共存。麦凯恩基于历史真实和个人生活真实的基础,有选择性地筛选出小说素材,借用比喻性的事件来暗示人物的内心活动。他将传记事实作为创作的核心,按照后现代小说特点和弗洛伊德的心理研究理论,丰富传记人物的精神生活。在《舞者》中,事实和虚构巧妙地通过小说创作手法结合在一起,这个文本由小说虚构和历史真实共同建构。
此外,麦凯恩通过自己高超的叙事技巧,多视角叙事、片段化结构以及多种文本体裁的混搭,叙述了鲁道夫桀骜不驯的一生。在叙事中,他尽量隐去作者的看法,使小说主人公的形象更具真实感,历史和文学以及事实与虚构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麦凯恩的叙事技巧似乎给了小说非同一般的吸引力,虽然通过其他人的眼睛里描绘的鲁道夫尽管是虚构的,但是却给人更为深刻的历史真实感。从另一个方面证实了传记小说是纪实传记和小说虚构的混合体,历史真实与小说虚构之间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麦凯恩的作品风格有自己的独特之处,对于人物和事件的取材,他倾向于兼具虚构和真实新闻报道式的材料。为了《舞者》取材,他曾在俄罗斯生活过一段时间,也曾细致地观察过芭蕾舞演员的日常训练,这充分体现在小说中麦凯恩对芭蕾舞技精确的描述,给人以虚构的真实感,也是多种文本体裁并存的原因。与传统的传记创作相比,传记小说更注重文学性,着重强调文学的创作技巧,但从宏观层面来讲传记小说消解了历史与文学、事实与虚构的界限,这是传记创作一种成功的尝试和革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