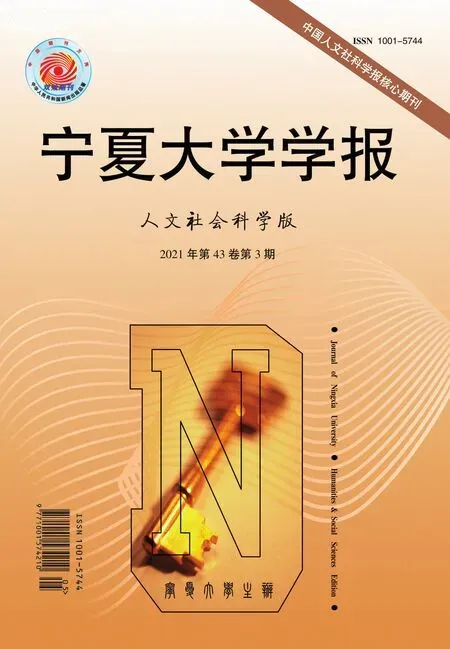民国时期的宋词兴盛论
2021-12-25刘学洋
刘学洋
(南开大学 文学院,天津300071)
“词盛于宋”是文学史的共识,宋词也与唐诗并称为“一代之文学”。虽然明清词学家们就已经在极力鼓吹“宋之词家,号为极盛”[1],但在以学词为导向的传统词学认知下,宋词鼎盛的主要意义在于为他们提供了绝佳的学习对象,至于它的具体内涵及其繁荣原因等外围问题反而所谈甚少。民国词学逐渐向现代转型,宋词开始纯粹地作为文学史的一种遗产被加以研究,“词盛于宋”也成了文学史、词史等新式著作必不可少的内容,得到了比较系统的论述。民国时期关于宋词兴盛的诸多解说,有导夫先路之功,不过由于时代缘故,它所暴露的不足也值得深思,全面地梳理、分析其得失,不仅有助于深化对民国词学的认识,对当下的宋词研究也具有启发意义。
一 量化宋词之盛
较之于唐五代,词在宋代迎来了极速增长,名家辈出,异彩纷呈。然而在民国以前,对于宋代究竟有多少词家却无人能给出一个相对精确的结论,如清初宋征璧《唱和诗余序》云:“词至南宋而繁,亦至南宋而敝。作者纷如,难以概述。”[2]虽然称赞宋词之盛,但对于具体数量也只能含糊略过。在晚清词籍刊刻盛行以前,宋词文献整理以毛晋《宋六十名家词》、朱彝尊《词综》等用力最勤、搜罗最丰,而后者收宋词亦不过三百余家,仅为冰山一角。或是受到词体小道观念的影响,他们对词籍文献并未过多在意,也没有穷尽宋词文献的意识,陈廷焯云:“倚声一途,既有朱氏《词综》,两宋精华,约略已具,而蒿庵犹病其芜。更欲集全宋词,则亦不过壮观邺架,于本原无涉,亦可不必。”[3]他主张求精而非求全,认为没有编辑全宋词的必要,在这种文献认知下,更不可能会大费周章地统计宋词的总数,宋词之盛在量上也就无从谈起了。
民国词学家则注重用计量的方法来清理宋词,为“词盛于宋”提供了更为直观的认识。清末王鹏运、朱祖谋等人开始专力于词籍校勘,蔚然成风,披露了大量珍稀的旧椠,辑出了诸多宋人佚词,代表成果有王鹏运《四印斋所刻词》、吴昌绶《双照楼景刊宋金元明本词》、朱祖谋《彊村丛书》、江标《灵鹣阁刻词》、赵万里《校辑宋金元人词》、易大厂汇刊《北宋三家词》等等,这些丰赡的词籍整理成果,为民国词学家认识宋词之盛奠定了文献基础。在1940年唐圭璋《全宋词》出版以前,王易《词曲史》、薛砺若《宋词通论》等都对上述大型词集丛刻进行了排比统计。薛氏指出:
原集已失,仅散见于各选本,尚无人为之汇辑成集者;或其词仅附见于诗文集者;或仅存三五篇什,及零章断句者;或其词已只字无存,仅从别人记述中,知其曾为某词者;或其词虽盛传人口,而迄不知为何人所作者;若细为搜求,则两宋作家,何止千数?兹从宋、元、明、清及近代重要的选本,……以及重要的丛书本,如上面所举的毛、王、吴、江、朱、赵等家所刻词,并笔记、方志、小说、金石书画题跋、永乐大典内,共搜得可以考证的作家,(去其复见及名号两出者)约八百人[4]。
他有很明确的文献搜求意识,就是要对宋词的创作实绩作出更加精确的判断,不再用“词家纷如”这般含糊之语一概而过,这也是词学史上首次对宋词总数作出了比较具体的回答。虽然后来唐圭璋《全宋词》在此数量上还有补充,但薛砺若等人在当时的条件下,不惮其烦地爬梳典籍、筛比文献,以求得宋代词家之总数,能够更加具体地展示宋词之盛。他所表现出来的求实精神是值得钦佩的,由此也能看出民国词学研究开始由传统的印象批评向实证理性的转变。
而且,经过细致梳理,薛砺若还发现宋初词坛存在一个六十余年的沉寂期。
宋初太祖肇兴,日事戎马,未遑文教,故在开基十余年中,词坛现象,异常寥落。太宗登极,颇能留心礼乐。本人又精通音律,宋代乐曲,乃由此渐臻繁缛。当时各国降臣废主之擅于歌词者,亦渐次奔赴辇下。此时词坛现象,虽较开国之初灿烂多了,然只系几个五代作家的尾声,不能代表宋人自己的创作。直到晏、欧出现,遂使此长期——约六十年——的岑寂状态,为之一变[5]。
南宋王灼曾注意到“国初平一宇内,法度礼乐,寖复全盛。而士大夫乐章顿衰于前日,此尤可怪”[6],但只是提出疑惑,没有详细论证。后世词学家叙述词史时对此也是不以为意,如“词者,滥觞于李唐,滋衍于五代,而造极于两宋”[7],五代词与宋词之间的这一低谷被淹没在宋词极盛的繁荣景象中,造成了词史书写的缺位。薛砺若在《宋词通论》“晏欧以前的作家”中逐一列举了现存宋初词人,包括徐昌图、苏易简、潘阆、钱惟演、王禹偁、寇凖、陈尧佐、陈亚、林逋、丁谓、陈彭年、李尊勗。宋初六十年却只有十余位词人,与宋代逾千数的词人总量显然是极不相称的。他用实际数据证实了宋词的兴盛并非贯穿始终的,在宋初是存在一个沉潜的阶段,这极大地推进了对宋词发展历程的认识,也为后来学者开示了“宋初词坛沉寂”的新课题。
其实,如果单就数量而言,宋词兴盛是有些“勉强”的。民国词学家们在统计了宋词总量后发现,“以数量而论,非但不及唐诗,且远不及宋诗”[8]。唐圭璋在《全宋词》缘起中指出:“所辑词人已逾千家,篇章已逾两万,已自昔视为卑卑小道之词,今亦足抵全唐诗之半。”[9]号称“极盛”的宋词也不过唐诗的半数,而宋代仅陆游一人即存诗九千余首,即使是明清词,在总数上也远过宋词,清词保守估计都在二十万首以上,词人逾万家[10]。数量虽然不足以代表全部,但也是衡量兴盛的重要参照,明清词学家没有对宋词进行过量化分析,他们往往简单地用“词盛于宋”带过,也就回避了宋词数量与极盛地位之间的矛盾。民国丘琼荪对此指出:
宋词的可贵在质不在量,若宋人的诗,反较唐诗为多,明、清人的词,大概也要比宋词为多。若以词与诗较,不论在当代或异代,终见得非常之少,其原因何在呢?曰:声律的限制有以致之。词的声乐,在宋代已十分普遍,民间亦非常流行。因了声律的限制,非率尔操觚者都可歌唱入乐,也非贩夫、走卒、村童、野老等所可信口诌成。且白描的词,更不易协律,又非一般人所可染指。又因声律的关系,字句多长短,平仄又很严,调子又很多;除极普通极圆熟,而又较短的调子外,简直不易记忆。非有声谱放在旁边,或有现成的词可作依傍,或正有人在旁歌唱或吹奏等,洵属不易下手。要下手亦非通晓声律者不办,决非稍通文墨的人都可从事的。……大凡民间的作品,不免粗鄙些,自然没有人为之选录,为之汇集,为之刊布,就此淹没无闻。这又是词少的一个原因[11]。
他从多个角度解释了宋词在数量上相对偏少的原因,抓住了词体的入乐性质和民间词的文献缺憾,是比较切合实际的。丘氏的这段话同时也说明了宋词有其特殊性,不能简单地用数量来衡量评判,“在质不在量”是指它广受宋人喜爱,产生了众多的词学名家,群星璀璨,创制了大量的名篇佳作和词调体式,风格多样,取得了极高的艺术成就,为后世所瞻仰追步。宋词能号称“极盛”以及能继唐诗而起成为“一代之文学”,显然是有更深层的原因和内涵。
二 宋词作为“一代之文学”的界定
“一代之文学”的美誉无疑是宋词兴盛的最好体现,二者是相辅相成的。因而如何界定宋词的这一文学史地位,也能反映出对“词盛于宋”的理解与认识。
一般认为,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自序中提出“一代有一代之文学”[12]以后,唐诗、宋词、元曲逐渐成为文学史上的惯称。事实上,这一说法历史颇为久远,金末刘祁有云:“予观后世诗人之诗皆穷极辞藻,牵引学问,诚美矣,然读之不能动人,则亦何贵哉?故尝与亡友王飞伯言:‘唐以前诗在诗,至宋则多在长短句,今之诗在俗间俚曲也。’”[13]他以感动人心为标准推出了唐诗、宋长短句和金元曲,主要还是立足于审美角度,但已具备了将宋词视为“一代之文学”的雏形。元代罗宗信明确指出:“世之共称唐诗、宋词、大元乐府,诚哉。”[14]似乎元人已经正式确立了宋词的典范地位,但其实元明时期也还有不少人将宋代道学奉为一代之独艺,如虞集云:“尝论一代之兴,必有一代之绝艺足称于后世者:汉之文章、唐之律诗、宋之道学,国朝之今乐府,亦开于气数音律之盛。”[15]清人结束了在词与道学之间的游移,把属于哲学思想范畴的道学排除出去,将词视作宋代文艺的唯一代表,如顾彩云:“一代之兴,必有一代擅长之著作,如木火金水之递旺于四序,不可得兼也。古文莫盛于汉,骈俪莫盛于晋,诗律莫盛于唐,词莫盛于宋,曲莫盛于元。”[16]易学大师焦循也提出“一代有一代之所胜”,其论宋词部分云:“唐人诗以七律五律为先,七古七绝次之,诗之境至是尽矣。晚唐渐有词,兴于五代,而盛于宋,为唐以前所无。故论宋宜取其词。……词之体,尽于南宋,而金元乃变为曲。”[17]他们都一致推举宋词作为宋代文学的代表,宋词的文学史地位在清代已经基本确立下来了。不过他们的观点还比较笼统,并没有说明为何宋词能取代诗文成为宋代文艺的最高典范,因为诗文在传统文人心目中无疑具有绝对的正统性。概而言之,明清文人已经逐步形成了文学代胜的观念,但宋词为何能成为“一代之文学”,他们却并没有作更深入的讨论。
图6为500 kV交流双回路输电线路塔-线耦全体系模型中的导、地线绝缘子,绝缘子与杆塔挂点之间的连接关系,图中分别标明了悬垂绝缘子、导线和地线等.
民国词学家在分析宋词兴盛时,往往也结合它“一代之文学”的地位,互相参照,主要从纵向与横向两个方面予以解读。
从纵向说,他们认为,只有宋代才是词的时代,亦即词独盛于宋。如薛砺若说:“前乎此者,尚未暨于纯熟自然之境,后乎此者,则又为余声末流,渐成绝响了。”[18]宋词在整个词史中都是最突出的部分,具有历史独特性。胡云翼对此有详细的分析,云:
词在宋代是一种新兴的文体,这种文体虽发生在宋以前,但到宋代才大发达,任宋人去活动应用,任这些词家,把词体怎样去开发充实,自由去找词料,自由去描写——总之,自由去创作词。这种词是富有创造性的,可以表现出一个时代的文艺特色。所以我们说宋词是时代的文学。宋以后因词体已经给宋人用旧了,由宋词而变为元曲,所以元词明词便不是时代的文学了[19]。
胡云翼所说的“富有创造性”是指宋人填词无所依傍,可以最大限度地展现宋人的创造性,题材内容、手法风格都是新开拓的,极具新鲜感,不像宋诗有唐诗矗立于前,总免不了以唐人为宗。宋以后法式渐定,趋于套路化、陈旧化,元明清人填词都难逃宋词窠臼,以宋人为宗法典范。而且,他还注意到词作为音乐文学的特殊性,云:“中国文学的活动,以音乐为依归的那种文体的活动,只能活动于所依附产生的那种音乐的时代,在那一个时代内兴盛发达,达于最活动的境界。若是音乐亡了,那么随着那种音乐而活动的文学,也自然停止活动了。凡是与音乐结合关系而产生的文学,便是音乐的文学,便是有价值的文学。……歌词之法随有宋之亡而亡,元曲代兴,此后作者填词,只能亦步亦趋模拟宋词的格调,已失却音乐文学的意义,变成死文学了。”[20]直接否定了宋以后词存在的意义。通过多重条件限定,宋词成为文学史上唯一正统的存在,这一“空前绝后”的历史特性也就构成了它作为“一代之文学”的必要条件。
从横向上看,宋词最能体现宋朝的时代精神。薛砺若云:“当时风气所播,无论是帝王、卿相、武夫、文士、方外、隐逸、名媛、歌妓,以及市侩、走卒、野叟、村夫,都能制作几首歌曲,都能咏唱各种新调,他们肺腑中的真情、隐痛、欢愉,都由这种新体诗歌流露出来,所以词在两宋,不独能代表宋人的文学,且为宋人的灵魂。”[21]又云:“在此三百余年中,由鼎盛而暨于式微,由昇平而遽遭乱离,由一统而渐成偏安,终至于覆亡,其间承平晏享之乐,……故国河山之恸,中原糜烂之惨,所侵蚀于诗人胸臆,及影响于一般人之生活者,均可由全部宋词中寻其端绪。”[22]词在宋代具有极高的普及度,它盛行于社会的各个阶层,无论是达官贵人,还是贩夫走卒,都能参与到词的活动中来,这种广泛的适用性是宋词兴盛最完美的注脚,更是作为精英文学的正统诗文不能及的,引车卖浆之流显然无法措手高雅的诗文。正是由于宋词风靡上下,拥有庞大的受众,使其能够最全面地反映宋人的生活图景和精神世界,他们的喜怒哀乐、国仇家恨在宋词中都有所展现,这也是宋代其他文体无法比拟的。
他们从纵横两个维度分析了宋词的词史地位及其对于宋代文学的独特意义,在双重因素的交叉下,很好地阐述了宋词能成为“一代之文学”的缘由,这些也都是“词盛于宋”的重要表现。而且,纵横结合的研究思路同样适用于认识其他朝代的代表文学,还具有一定的方法论价值,能够更好地理解文学代胜论。
三 宋词兴盛原因论
注重词史现象的分析是现代词学的重要新特征,作为“一代之文学”的宋词繁盛的原因,也是民国学人们热衷于探讨的一个新兴话题,纷纷尝试解开词体在宋代能够风行天下之谜,主要可归为以下三个角度。
第一,从词体艳科与入乐的娱乐性切入,并结合时代背景来分析宋词兴盛的原因。词在唐宋时期本是为尊前宴享而设,娱乐是其核心使命,并非一般的案头文学,民国词学家也紧紧围绕宋词的这一性质来探讨宋词之盛。
刘大杰说:“人类的情欲与浪漫的情绪毕竟是不能完全压住的,任你如何阻住它,它总得要找出路。词这一部门恰好是宋人情欲的出路。文要载道,诗要讲诗教,但词是一种新兴的歌辞,本来就是妓女口中的玩意儿,生来便具有淫靡艳丽的素质。载道也无从载起,讲词教也无从讲起。因此道学家便轻视了这一支文学界的游击队,认为它出身卑贱而把它放弃了。所以在宋代有道学古文家,有道学诗人,而不见有道学词人。一来是词这种东西本不便装进道学,二来也是道学家看不起词。于是词在这种环境之下,便成为浪漫才人发泄情欲的良田,为士大夫脱去道学面孔以后,表现私生活的避难所,为民间流行的乐府与歌谣,而日趋于繁盛发达之途,形成最自由最浪漫的新体诗了。”[23]刘氏注意到词的艳科属性可以不受传统儒教思想的约束,正好成为诗文等严肃文学的补充,为文人提供了表达私人情感的途径,卸下所有的道德伪装,自由地享受、释放个人情欲的快感,从而吸引了大量文人的介入。
2.指出词的音乐功能是宋词兴盛的重要助推力
胡云翼说:“音乐是发生词的渊源,也就是发达词的媒介。原词为歌辞,多可歌。故当代词人的词,每新声一出,便传播于秦楼楚馆了。本来单独的文学效力,在社会里面,远不及音乐的效能来得大。因为有音乐的关系,因此宋词也跟着音乐而得着较大的普遍性。譬如‘有井水处,皆歌柳词’,若不是可歌,那能这么普遍呢?因为在音乐方面,需要歌辞很多,要许多人供给歌辞;而那些歌妓舞女,则每以得名人学士的赠词为夸耀。这些文人,也乐得替她们作词,以博得青楼一粲。”[24]他使用的是后世所习称的“词”概念,单纯是文本意义上的歌辞,宋词是还能够入乐歌唱的,音乐充当了文人与歌妓之间的媒介,一方面促进了歌辞文本的传播,另一方面也刺激了词的生产,从而带来了宋词的繁兴。实际上,词体的音乐性更大的意义在于它的实用价值,刘大杰云:“当日词的用处是广泛的,朝廷的盛典,士大夫的筵宴,长亭离人的送别,倡楼妓女的卖唱,都是歌的词,再如传踏、鼓子词及诸宫调的歌唱部分也是词,再就是白话小说话本里面,也杂用着不少的词。在这种地方,宋词能够普遍于民间,能够流行于下层阶级,他那种音乐的实用功能,却有很大的关系。”[25]他跳出了后世对于宋词一般的文学性认知,更侧重于宋词入乐的歌唱特点,这是决定宋词实用功能的关键因素,实用也就意味着具有广阔的市场和需求,正如龙榆生所说“歌词为当世酬应娱乐必需之品。文人既娴曲调,既不妨随声填写。作者既众,造诣益高”[26]。
艳科与音乐共同指向的都是宋词的娱乐性,这与当时的社会文化也是密切相关的,只有适宜的物质环境才能带来娱乐业的发达,民国词学家也都注意到了它背后的时代环境。刘大杰指出:“宋代虽与外患相终始,但始终是沉溺于酣歌醉舞的空气里,北宋的汴京,南宋的杭州,是两个极度繁荣的大都市,在商业经济的发达中,在君臣上下奢侈淫靡的生活中,在文人学士的蓄妾挟妓的浪漫生活中,在各种娱乐艺术蓬勃生长的空气中,词的用处愈是广泛,词的发达愈是迅速,词人与作品也愈是增多了。”[27]繁华的社会生活为宋人追求享乐提供了物质基础,这也是以娱乐为主的宋词能够拥有市场的重要前提。余毅恒也说:“宋代开国之初,鉴于五代兵伐之扰挠,生灵涂炭,亟思有以与民休息,故尚文而轻武。国家闲暇,般乐饮酒,濡染倚声,沿成风气。”[28]宋代优待士人、提倡歌舞的大氛围更是直接助长了唱词之风。可见,他们对于宋代的经济状况和政治文化都有清晰的体认,道出了宋人趋于享乐的社会原因,这正是以娱乐为主的词体能在宋代广受欢迎的核心动力。
第二,归之于帝王的提倡。如胡云翼说:“宋词之发达,到这般田地,得君主们的帮助也不少。”[29]邹弢云:至宋“而此学最盛。国家提倡,风气开通。”[30]这是民国时期一种十分普遍的认识。诚然,它的确能够找到一些材料依据。如况周颐云:
元以词曲取士,于载籍无征。唯宋时词人遭遇极盛。淳熙间,御舟过断桥,见酒肆屏风上,有《风入松》词。高宗称赏良久,宣问何人所作,乃太学生俞国宝也,即日予释褐。(《中兴词话》)是真以词取士矣。淳熙十年八月,上奉两殿观潮浙江亭。太上谕令侍宴官各赋《酹江月》一曲。至晚进呈,以吴琚为第一。(《乾淳起居注》)是以词试从臣,且评定甲乙矣。政和癸巳,大晟乐府告成,蔡元长荐晁次膺赴阙下。会禁中嘉莲生,进《并蒂芙蓉》词称旨,充大晟协律。(《能改斋漫录》)李邴少日作《汉宫春》,脍炙人口。时王黼为首相,忽招至东阁,开宴,延之上坐。出家姬数十人,皆绝色。酒半,群唱是词侑觞,大醉而归。数日有馆阁之命。不数年,遂入翰苑。(《玉照新志》)是皆以词得官矣[31]。
这些事例都说明了宋代皇帝对词的喜爱,并且对一些文人的仕途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由此他们认为帝王对宋词兴盛起到了推动作用。从本质上说,这种观点其实强调的是王权对于文艺发展的影响,历代的文学发展确实与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专制时代君主的意志一定程度上是可以影响文艺的发展,所谓上有好者下必甚焉。但仅仅凭借个别皇帝的喜好与数例因词受擢的词本事,就推断出宋代帝王是有意提倡词体,从而推动了宋词的繁荣,这明显是无法成立的。
词体的娱乐性决定了帝王不可能大张旗鼓地宣扬词体,因为词在宋代是典型的卑体小道,难登大雅之堂,只是供人享乐之用,君王充其量也是私下喜好而已,绝不可能上升到国家意志层面,作为明文规定加以推广。至于所谓的“以词取士”完全是照搬自唐诗,《御制全唐诗序》云:“盖唐当开国之初,即用声律取士。聚天下才智英杰之彦,悉从事于六义之学,以为进身之阶,则习之者,固已专且勤矣。”[32]暂且不论唐代以诗取士是否真的与唐诗繁荣有必然的联系,但至少可以肯定的是,诗赋是唐代科举的重要内容之一,“以诗取士”是有一定的制度根据。而宋代却从未将词纳入国家抡才大典之中,“以词取士”只是个别文人的终南捷径,不具备普遍性,也不可能引发群体性的趋向,诱使文人纷纷投入以词干谒的队伍中。而且,从具体的实例中也可以看出其中端倪,如被词学家们反复提及的俞国宝释褐之事:
(淳熙间)一日,御舟经断桥,桥旁有小酒肆,颇雅洁,中饰素屏,书《风入松》一词于上,光尧驻目称赏久之,宣问何人所作,乃太学生俞国宝醉笔也。其词云:“一春长费买花钱。日日醉花边。玉骢惯识西湖路,骄嘶过、沽酒垆前。红杏香中歌舞,绿杨影里秋千。东风十里丽人天,花压鬓云偏。画船载取春归去,余情在、湖水湖烟。明日再携残酒,来寻陌上花钿。”上笑曰:“此词甚好,但末句未免儒酸。”因为改定云“明日重扶残醉”,则迥不同矣。即日命解褐云[33]。
细读俞国宝之词,表面虽在咏春事,但却传递了一种悠闲自得的心态,能够如此惬意地游春赏景正反映了国事祥和太平。皇帝看中的正是此词的雍容风度,所改“儒酸”之句,更能表现出一种长期沉醉于大好春光的情态。俞国宝此词无意中流露出颂世色彩,正好迎合了当权者的虚荣心,他因此而得以一步登天。所以,“以词取士”更准确的表述应当是“以颂世词取士”,词这一文体不是决定性的因素,君主更在意的应当是词中颂圣的主题内容。
此外,大晟府被词学家们视作国家提倡词学的重要举措。如碧痕云:“词称诗余,本文章之小道。三唐引绪,五代分支,宋起大晟乐府,人才一盛。周片玉辈,移宫换羽,按时兴歌,于是词家旗帜,五色纷飘矣。”[34]但实际上,大晟府仅存在了二十余年,所修之乐也非填词之乐。王国维曾考证指出:“楼忠简谓先生(按:指周邦彦)‘妙解音律’,唯王晦叔《碧鸡漫志》谓‘江南某氏者,解音律,时时度曲。周美成与有瓜葛。每得一解,即为制词。故周集中多新声。’则集中新曲,非尽自度。然顾曲名堂,不能自已,固非不知音者。故先生之词,文字之外,须兼味其音律。唯词中所注宫调,不出教坊十八调之外。则其音非大晟乐府之新声,而为隋唐以来之燕乐,固可知也。”[35]周邦彦等人填词也不用大晟新声,可见宋词所用的音乐是独立的,大晟府对于宋词的繁荣并没有直接的关联。
将宋词兴盛归结于君主的提倡,是对集权时代君主意志的夸大,民国时人刚刚告别帝制时代,难免对其产生特殊的情结。词在宋朝走向巅峰应是当时的时代精神、城市格局功能、社会政治经济等多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并不是靠个人喜好就能绝对左右的。王易注意到其中的矛盾,云:“顾或谓唐以诗赋取士,君亦声色是娱,有以促诗乐之发展。讵知发展为因,取娱是果。”[36]把宋代帝王对词的喜爱看作整个宋词兴盛的结果与表现,应该更为恰当。
第三,引入进化论来考察宋词的兴盛。唐诗珠玉在前,还与宋词并列为“一代之文学”,宋词很自然地就与唐诗构成一种前后的递嬗关系。民国词学家对于二者的认识主要有二:一是,认为诗至晚唐五代已趋陈旧,宋词兴盛是代之而起的结果。如张龙炎云:“晚唐以下,诗运已颓,故词为宋代独胜之文学也。”[37]二是,认为唐诗已臻极致,宋人只能转而另寻他途,从而造成了词的成功。如儿岛献吉郎说:“宋之诗人,有创作之心,欲与唐人抗衡,自觉绝句恐难驾乎唐贤之上,于是诗学上另辟一新天地,遂产生一种长短句之新体诗也。”[38]究其本质,这两种观点其实都是认为宋词的繁荣是以唐诗的终结为起点的,是文学进化的自然结果。王国维有云:
四言敝而有《楚辞》,《楚辞》敝而有五言,五言敝而有七言,古诗敝而有律绝,律绝敝而有词。盖文体通行既久,染指遂多,自成习套。豪杰之士,亦难于其中自出新意,故遁而作他体,以自解脱[39]。
他认为任何一种文体都有其时效性,与生物一般有一定的寿命,鼎盛过后必然走向衰败,然后或主动或被动地让新兴的文体所取代,旧文体的积弊衰微正好是新文体崛起的契机与动力,文学史形成了循环的发展状态,不断向前进化,词体之兴正是诗体之衰的结果。
然而,这种认识存在一定的局限,它在认可宋词兴盛的同时也意味着对宋诗的否定。如郑宾于说:“诗是违反时代的文体,词是适合潮流的创作。”[40]唐圭璋亦云:“词经过温、柳二氏之专攻,乃得重兴绝业,蔚为大观;诗则降为别支,词则俨然正统矣。”[41]在他们看来,文学向前进化的同时也在不断淘汰旧文体,诗在晚唐已经穷途末路,宋代是词的独尊时代,这实际上完全抹杀了宋诗的价值,同时也有些盲目地抬高了词体的地位。众所周知,宋诗在文学史上有着极高的成就,诗学史上的宗唐、宗宋之争充分表明其影响力是丝毫不弱于唐诗的。唐诗的巅峰并不意味着诗体已经再无拓展空间,宋诗乃至后来的明清诗都依然有它的生命力,皆能反映时代精神而自成一格。刘麟生对此曾辨析,云:“词能增加一种诗体,并不能改革旧诗体,也不能打倒旧诗体。譬如宋代的文学当推词为第一,但是宋诗确有他的立场,不因为词的发达,便没有诗的进化。词笔轻倩,自有引人入胜的地方,可是叙事起来,远比不上诗。他的范围较小,是我们爱词的人不能不郑重声明的。”[42]宋词的兴盛与诗的发展并不冲突,也没有绝对的兴替关系,将宋词兴盛归之于诗体过时的看法也是有失公允的。
总而言之,民国词学家是探讨宋词兴盛的引领者,筚路蓝缕,鲜明地体现了民国词学研究的新理路与特点,也为当下的宋词研究开启了方向,所采用的诸多研究视角和暴露的缺陷偏颇都具有一定的参考借鉴价值,尤其是揭示出宋初词坛的沉寂以及对宋词兴盛的原因等话题,仍然值得今天的词学研究继续深入拓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