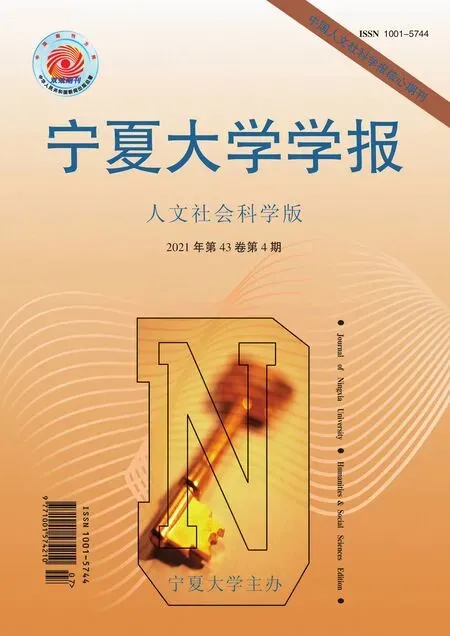陈洪绶对孟称舜戏曲的多维批评
2021-12-23杜翘楚
杜翘楚
(中国人民大学 文学院,北京 100872)
陈洪绶是明末清初知名的画家,除了其杰出的绘画成就,也被赞“书法遒逸”,在诗歌创作方面,被王士禛评为“颇有致”[1],但陈洪绶在戏曲上的成就却鲜为人知。陈洪绶不仅有良好的戏曲素养和浓厚的戏曲兴趣,还与诸多戏曲家和伶人保持密切交往,更值得一提的是,他创作了数量可观的戏曲插图(目前可知陈洪绶所作插图有《张深之先生正北西厢秘本》插图六幅,《李告辰本西厢》莺莺半身像,《李卓吾评本西厢》中第一幅莺莺像与《张深之本西厢》小异,其余十幅中,画《遇艳》一幅,题:“亸着香肩,将花笑捻。洪绶”。但学界对其真伪存疑),还为其好友孟称舜现存的十种剧作的四种作了评点,分别是一部传奇《娇红记》和三部杂剧《眼儿媚》《花前一笑》《桃源三访》,并为《娇红记》亲作长序,画娇娘像四幅,且在第二幅肖像题有七绝一首。就目前所见,仅有一篇文章《陈洪绶与晚明曲家》论及陈洪绶与越中曲家孟称舜、祁豸佳家族与张岱兄弟的交往情况,文章呈现了陈洪绶与晚明戏曲家的密切关系和深厚情谊[2]。对于陈洪绶的戏曲评点成就,朱万曙的《明代戏曲评点研究》给予了关注,尤其对陈洪绶评点《娇红记》创造性地提出了“怨谱”这一概念给出了高度评价:“这在中国古代戏剧理论史上是一件值得大书特书的事情,它表明悲剧理论从感性阶段步入了理性阶段,已经出现了对悲剧和悲剧风格作出高度概括的理论概念,表明悲剧风格批评走向了成熟和自觉。”[3]但总体来看,陈洪绶的戏曲渊源、与孟称舜的交游情况以及陈洪绶对《娇红记》和另外三部杂剧的批评特色,还缺乏深入研究,故本文略作论述。
一 陈洪绶的戏曲渊源
陈洪绶能歌一事,屡见记载。他在《奉觞叔祖大人五十寿序》提及:“十八九岁时,知声能歌曲,叔祖便与击鼓按拍。”[4]其诗云:“老渴今年二十七,未有当筵不唱歌。但使年年如此日,随他日月去如梭。”[5]虽未发现关于陈洪绶演戏的记录,但他对曲律的喜爱却可见一斑。据赵尊岳《明词汇刊》的《宝纶堂词跋》载:“今集所传,盖犹嗣君幼字鹿头者求诸四方友朋,以辑存者也。诗词并潇洒,翛然尘表,惟律以词格,终一闲未达耳。集中附南北曲《鹧鸪天》四阙,删之。”[6]惜今不存陈洪绶所做南北曲《鹧鸪天》,否则将对其曲律成就有更深入的了解。
陈洪绶与诸多戏曲家都保持着深厚情谊,且交游过程中常出现观剧活动。祁彪佳《祁忠敏公日记》丙子(居林适笔)九月十一日记云:“邀朱仲含叔起同陈章侯来举酌,演拜月记,席半,出游寓山,及暮乃别。”[7]陈洪绶与祁氏家族的关系十分紧密,除祁彪佳外,陈洪绶与祁豸佳、祁骏佳、祁奕远叔侄几人也极其要好,在其诗集中常见他们之间的交游往来。祁氏家族以书画、戏曲等方面的卓越成就为人称道,祁家蓄养家班,培养名伶,故陈洪绶与他们的交往过程中也常受到戏曲熏陶。此外,陈洪绶与张岱往来密切。张岱《陶庵梦忆》卷四《不系园》记载与陈洪绶等好友观剧唱曲的聚会场景:“章侯唱村落小歌,余取琴和之,牙牙如语。”[8]又提及与陈洪绶招待鲁王的经历,“是日演卖油传奇,内有泥马渡康王,中兴事巧合,睿颜大喜……设二席于御座旁,命岱与陈洪绶侍饮,谐谑欢笑如平友……”可见在晚明名士间的交游活动中,观演戏曲为其中重要环节。除祁家诸人、孟称舜、张岱外,陈洪绶与曲家王翃也是知交。王翃“好制曲,作《纨扇记》”。“游山阴,与陈章侯善……旁精词曲,有《博浪沙》诸传奇,颇忼慨自喜”[9]。大量的观剧经历和与戏曲家的密切交流对陈洪绶戏曲见解及品位的形成必然有比较正向的影响,从陈洪绶对孟称舜戏曲的评点也能反映出他对《西厢记》《牡丹亭》《琵琶记》《拜月记》等剧作颇为熟稔。
除了观剧活动,陈洪绶还为好友剧本作过题词。张岱创作过一出杂剧《乔坐衙》,剧作已失传,但陈洪绶为其写的题词则保存到陈的文集中。“乔坐衙”是当时的一句俗语,意为装模作样、装腔作势,陈氏题词中有“使宗子其人得闲而为声歌,得闲而为讥刺当局之语,新辞逸响,和媚心肠者,众人方连手而赞之美之,则为天下忧也”[10]之语,可见《乔坐衙》是一出讽刺剧,而陈洪绶在赞叹其“才大气刚,志远学博”之余,也为其不得施展抱负而寄情声歌感到不平。崇祯十二年(1639)十二月,陈洪绶还代马权奇书《张深之先生正北西厢秘本序》于杭州西湖定香桥畔,并作插图六幅。卷首序后列参订词语友三十二人,包括会稽孟称舜子塞。
与戏曲家有密切联系之外,陈洪绶与伶人的交往也见于记载。比较出名的例子即顺治七年(1650)四月三日,陈洪绶的好友林仲青请他到家中作送春之会,席中有顾烟筠吹笛弹弦索,汪抑仙拉胡琴击箫鼓,秦公卓笙管,王璈、老文唱流水。陈洪绶赋七绝一首有“送春邀我两红裙,急管繁弦争暮云”两句,则顾烟筠、汪抑仙应是两名应席的伶人。陈洪绶还写过一篇《好义人传》,传主是苏州的一名歌者梁小碧,与陈洪绶的好友王玄趾私交甚笃,被讥为“痴绝人”。后留都失守,王玄趾投水殉节,梁小碧在家中设其灵位,请王玄趾的弟兄遗孤及至交好友共同祭奠,更时常以饼饵果蔬馈赠他的遗孤。张岱、陈洪绶二人都为这位伶人作传,陈洪绶借小碧的节义讽刺“甲申至乙丑几六年所,不闻有一草莽孤臣于清明寒食,以一盂麦饭望北风而浇之者”[11],既表达了对伶人的崇敬之情,也反映出对故朝的忠贞节义。在陈洪绶为《娇红记》所撰序中,也特别指出了伶人对人性情的影响:“伶人献俳,喜叹悲啼,使人之性情顿易,善者无不劝,而不善者无不怒。是百道学生之训世,不若一伶人之力也。”[12]可见陈洪绶对待伶人的态度是宽容甚至欣赏的。
综上,陈洪绶能够贡献出高水准、多维度的戏曲批评,得益于他作为晚明名士所受到的戏曲熏陶。他不仅在年少时就表现出对乐曲的喜爱,更在与友人的交往中积攒了大量赏剧经验,且不乏与伶人的接触。在陈洪绶所处的文人圈子中,他们品位相投,戏曲创作与评点的实践可谓频繁。以上种种,都成为陈洪绶戏曲批评生成的土壤。
二 陈洪绶与孟称舜交游考
孟称舜将自己的四部戏曲作品交由陈洪绶评点,一来可见二人的深厚交情,二来可见孟称舜对陈洪绶戏曲鉴赏能力的认可。由于孟称舜的诗文多已散失,故二人的交游情况只能从陈洪绶的文集中加以辑录。天启七年(1627),陈洪绶在杭州,有《邀孟子塞》诗一首并自注时间为丁卯九月:“吾思孟十四,的的是吾兄。诗与文皆淡,神和品共清。不能常痛饮,每想数同行。今到西湖上,何为游不成。”[12]子塞乃孟称舜的字,可见二人在天启七年之前就已经相交且相互赏识。陈洪绶有《自书诗册》留存,该诗册有陈为好友朱士服所书的二十四首诗,诗册后有陈洪绶的跋语:“己巳秋暮,与朱士服、王子玙、吕吉士、王子樽、王公旭、孟子塞、赵楚木、赵介臣、王子仙、王士英、王子监、吕衡伯、吕无波水嬉二日,醉后为士服作书,记忆旧诗,便想往时得意失意之句。”[13]可见在崇祯二年(1629),陈洪绶又与孟称舜有交游经历。陈洪绶有《致三兄短札》纸本藏于南京博物馆,内容为:“弟已诺朱、孟二兄商刻文一事,不得留三兄话,歉不可言。相爱如三兄,当不相责也。恒如在金家庙,可招之归。晚际可期一晤否?草草弟绶顿首。公振告辰李吾兄知己。”[14]据辑录者考订,朱、孟二兄当指上文提及的朱士服与孟称舜,刻文一事或指李告辰于崇祯四年(1631)刻《北西厢记》,内收陈洪绶画的插图《莺莺像》及题词。崇祯四年,孟称舜的史论文集《孟叔子史发》成书,陈洪绶为其作序,写道:“予与友善,称相知。逮仁人善士,非与史发之流传不在是与?其识论高卓精详者,予与社中诸君子悉评之,不赘。”[15]这里“社中”表明陈洪绶和孟称舜有共同参加的集社,但是枫社、复社还是其他集社还待进一步考证。崇祯六年(1633)夏,孟称舜的《古今名剧合选》刻成,陈洪绶分别为《柳枝集》中《眼儿媚》《桃源三访》和《花前一笑》杂剧三种作了评点。崇祯十二年(1639)腊月,陈洪绶为《娇红记》题签、评点、制序,并作卷首插图四幅,孟称舜作四首《题娇娘像》词。
除以上有明确时间节点的交游事件外,陈洪绶还有诗《期孟十四》:“同是沉沦客,游踪不可期。君当无慨叹,我亦少伤悲。急到湖船饮,而评山馆诗。来书吾细读,字字有余思”[16]。《东龙潭与孟子塞流觞》:“修禊流觞事,吾尝到处思。岂来五泄矣,而不一为之。得句羞前哲,行歌想后期。天教狂到老,复至更奚疑”[17]。东龙潭在陈洪绶的家乡诸暨附近,说明孟称舜曾到访诸暨,且诗中首句“修禊流觞事”表明二人相聚时间是在三月初三。二人在这次交游之后,又再次在诸暨相聚,一同游览了西龙湫,有陈洪绶诗《与孟子塞游西龙湫》首句“东泷已足慰”[18]为证。另有诗《寄孟十四兼问赵五》,首句“来髯”为来风季,说明孟称舜与陈洪绶的挚友来风季相识,二人有共同的交友圈。
除此之外,孟称舜之子孟远还撰写《陈洪绶传》,录于《宝纶堂集》卷首,末云:“远先人与先生交甚厚,其天性孝友,经世之大节,时时言之。余少犹得从先生游,读其文,见其咏歌之志,何异《离骚》、《天问》?所谓书画者,亦一时兴会所寄耳。”[19]从孟远所述,可知陈、孟二人相交甚厚,且友谊已延续至下一代。
另据陈洪绶戏曲评点所透露的信息,也可见二人的惺惺相惜。如《节义鸳鸯冢娇红记序》中批驳了时人印象中孟称舜“迂生”“腐儒”的形象,认为孟称舜“为人则以道气自持”,是一个“情深一往,高微杳渺之致”的人。在肯定了孟称舜真情至性的同时,也对孟称舜的文学成就进行褒扬,“子塞文拟苏、韩,诗追二李,词压秦、黄”[20]。又如陈洪绶的《桃源三访总评》提及:“《桃源》诸剧,旧有刻本盛传于世,评者皆谓当与实甫、汉卿并驾。此本出子塞手自改,较视前本更为精当,与强改王维旧画图者自不同也。”[21]陈洪绶对孟的创作情况可谓十分了解,且应是忠实读者。再如《娇红记》第三十六出对[醉落魄]一曲的眉批:“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22(]本文所引《娇红记》曲文及评点内容皆出于此)。该曲是对申氏兄弟赴考前的心理描写,而孟称舜屡举不第,此处评点体现陈对孟的读书、应考经历较为熟悉。另外在四剧的评点中,陈对孟的作品颇多溢美之词,虽有有失公允之嫌,但也能看出二人创作观念、审美情趣的一致。
三 陈洪绶对孟称舜戏曲的多维批评
陈洪绶对孟称舜戏曲的批评,不仅包含四部剧作的评点,他还为《娇红记》题签、制序,作卷首插图四幅,有题像诗《题娇娘像》一首。从戏曲批评的角度看,陈洪绶一人就尝试了序、图像、题像诗、评点多种批评形态,对于研究陈洪绶的戏曲批评提供了比较多样的例证,也利于多角度理解《娇红记》这部作品。从戏曲刊刻的角度看,彼时陈洪绶的书画盛名早已卓绝宇内,这部《娇红记》汇集了他处于创作高峰期的书画作品,再加上刊刻名手项南洲的精雕细刻,为后世留下了一部精美的戏曲刻本。就批评者与剧作家的互动来看,二者不仅有书画、题词方面的互动,还有戏曲创作与戏曲评点的互动。剧作家孟称舜在自己的戏曲图像上亲作题词,在戏曲史上也属罕见。
陈洪绶的四幅娇娘像及自题诗和孟称舜的题像词,既是两位友人之间的双向批评,又组成了一个经典的语—图互文案例,且从诗、词、曲、画四个维度对剧作女主人公进行描摹,是对人物形象的多重再现,有利于读者捕捉娇娘这一别具一格的女性形象。首先,二人的批评互动集中在王娇娘这一人物上,突出了孟称舜在人物创作上的匠心。在强化申、王二人至情至性的爱情观念之外,孟称舜显然对于刻画这一有着“与其悔之于后,岂若择之于初”的内心自觉,追求“同心子”的女性角色特别关注,且倾注了更多心血,如他在《娇红记题词》中所赞“性情所种,莫深于男女。而女子之情,则更无藉诗书理义之文以讽喻之。而不自知其所至,故所至者若此也”。其次,陈洪绶所画四幅娇娘像,成功从戏曲所呈现的动态的女性形象之中,提炼出了四个具有代表性的静态形象,建构出了一个悲剧女性角色。四幅画中的娇娘身姿秀丽,装扮繁简各异,但都呈眉目低垂、弱不自胜之态,与剧作中王娇娘令人肝肠寸断的悲情遭遇和其本人的悲剧形象相得益彰。从题像词和画作本身可以看出四幅图分别代表着娇娘在感情上的四种状态:第一幅是未与申纯邂逅之前,少女思春的情态,孟称舜题像词其一谓“晓向花前闲信步,似笑如颦万种情难诉”是也;第二幅是已心有所属却与申纯分别,“目送芳尘无限意,情多几为伤情死”的状态;第三幅娇娘已相思成疾,“羽扇轻持娇不胜,春去秋来,总害春前病”;第四幅乃娇娘的诀别,“忆昨别离何草草,掩镜徘徊,还恐花相笑。人面不如花色好,愁容那似欢时少”。孟称舜除了用语言呈现陈洪绶画作中娇娘的装扮、样貌、神情等细节之外,还加入景语与情语,与戏曲内容相互呼应,给予人像更丰富的情韵。后世对四幅娇娘像中的第三幅给予更高评价,但陈洪绶却在第二幅画像上自作题画诗《题娇娘像》:“青螺斜继玉搔头,知为伤春花带愁。别离几经多是恨,汪洋不浊泪中流。”书画一体,线条流丽,如达化工之境。题画诗的书写策略与题像词一致,先关注于真实可感的外貌描写,再逐步与戏曲所反映的人物情绪相融合。曲、词、诗、画融为一体,为读者理解主人公形象提供了极大帮助。
关于陈洪绶对孟称舜剧作的评点形式,与孟称舜的评点基本一致。孟称舜在《古今名剧合选》上的眉批比较特别,每剧的剧首眉批相当于该剧的“总评”或序文,而陈的四剧评点总评也以眉批的形式出现。在三部杂剧中,偶有简略的夹批,且多与音韵有关。在评点内容上,下文将从评点语言、评点视角、审美标准、艺术观念等几个方面进行剖析。
1.具象化的评语
陈洪绶的评点中,常出现具象化的语言,一些评点词汇实乃陈洪绶的发明。首先,是“栽根”一词。如《娇红记》第三出对“要配好鸳鸯,则除他人材呵,得似你才郎样”的评点是“也便栽根”。同一出飞红的两句曲词“一个待眉传雁字过潇湘,一个待眼前鱼书到洛阳”的眉批亦说:“妒处也栽根”。此词在《娇红记》评点中出现了四次,含义大致等同于“伏笔”,即为后文情节做好埋伏,致使再次出现不突兀,且与前文有所呼应。“栽根”一词尚未发现于其他戏曲评点,当是陈洪绶的独创。佛家有“佛果栽根”一说,陈洪绶早年就有读佛经的经历,其诗《理严华经》中“二十翻此经,亦曾废寝食”可以为证,且陈洪绶终其一生与佛教有不解之缘,晚年甚至不得不避乱山中,剃发为僧。陈洪绶的七言律诗《结社念佛》的第二句“善根夙种有良缘”,就有栽种善根的说法,或许他在戏曲评点中的用词受到了佛教语言的影响。
其次,是“过峡”一词。《娇红记》第二十三出的评语:“此折过峡,生出千峦万峰。”该折主要讲丁玲玲向申纯索要娇娘绣鞋一事。第三十二出对[尾声]“还再则与你走向银塘照双影”的评语是“过峡”。申纯提议与娇娘再到另一处观赏,引出后文险被奶奶发现,娇娘与飞红嫌隙,打发申生回家等一系列波澜。“过峡”本指两山之间的低洼处,这里大致含义相当于事件的转折和情节的拐角处,并引起后文的矛盾冲突。过峡的出现,让故事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在《儒林外史》的评点中,对第四回《荐亡斋和尚吃官司,打秋风乡绅遭横事》的卧闲草堂评也用了“过峡”一词:“此篇是文字过峡,故序事之笔最多。就其序事而观之,其中起伏照应,前后映带,便有作文之法在”[23]。小说与戏曲评点所用之“过峡”,意思大抵相同,当兼有转折与引起后文两种作用。
再次,是“枝”字含义的多用。第一种意思即量词,表示曲子的数量。如《娇红记》第二十三出[念奴娇序]及后面三个[前腔]的眉批:“四枝各写情款,曲尽烟澜。”又如《桃源三访》第一折[胜葫芦]的曲批:“此下数枝,着意追想,尽情惆怅,与会真首折同妙。”第二种意思指不同的事物,划分语言的层次。如《泣赋眼儿媚》第二折对[含笑花]的眉批:“数枝兼从前词演出。”这里的数枝,指的是额角飞鸦,翠钿等等。又如《花前一笑》第一折[得胜令]的眉批:“枝枝于郊游中说出,一肚皮感惋情怀妙。”这个“枝”既可以指代描摹的不同事物:三月泪花红、五夜漏声钟、云暝秋江、花香草店,也可以理解成递进的情感层次。
陈洪绶多发明此类具象化的评点语言,或许与他本人的画家身份有关。“过峡”与“栽根”二词都运用了拟物手法,其含义与字面上所呈现出来的画面是相符合的,对读者理解评点有很大帮助。其他评点者也常常会用比喻等修辞进行评点,但如何像陈洪绶一样用常见意象表达不同的评点态度,如何能让读者领会评点精神而不陷入自我陶醉的境地,则是体现评点者功力的所在。陈洪绶的画家身份还体现在评点的举例上,如他在评《娇红记》时举过李伯时的例子:“李伯时画马,识者愁其坠马腹中,以其神态俱似耳。作者描情至此,当是夙缘前业。”这里陈用来赞扬孟对情愫细致入微而生动的刻画。又如《桃源三访》的总评:“此本出子塞手自改,较视前本更为精当,与强改王维旧画图者自不同也。”种种与绘画有关的特殊联想,也反映出评者对该领域的熟悉。戏曲和绘画一样,都属于再现的艺术,故如何描人、描情、描景、描事成为评点大家格外关注的角度。在戏曲评点中,也往往可见将戏曲描写与绘画技法类比的种种例证。如《三先生合评元本西厢记》卷二第二折第四套李卓吾的总评:“无处不似画,无处不如画。”[24]卷三第三折第二套李卓吾的总评:“吴道子、顾虎头只画得有形象的,至如相思情状,无形无象,《西厢记》画来的逼真,跃跃欲有,吴道子、顾虎头又退数十舍矣。千古来第一神物!”[25]孟称舜在《古今名剧合选序》中提到戏曲“因事以造型,随物而赋象”的特色,又以画马作为戏曲创作的例证,“其说如画者之画马也。当其画马也,所见无非马者。人视其学为马之状,筋骸骨节,宛然马也。而后所画为马者,乃真马也”[26],认为戏曲创作者应该化身曲中之人,置身于戏曲场景,才能创作出为人信服的戏曲作品,而这正是戏曲创作难于诗与词的所在。可见陈洪绶、孟称舜等晚明的戏曲评点者已经在评点中触及了文体特征等关键问题,且能自觉地援引书画的批评语言,让戏曲评点更加具体可感。
2.主客观结合的评点视角
陈洪绶的评点语言往往简练、质朴、谦和,可以透露出评点者与戏曲家密切的交往和深厚的情义。其评点多以第三方的评点者视角,但有时也会加入作为读者的主观阅读体验。在评《娇红记》时,可以看出陈洪绶最后已经抑制不住悲恸的情绪,被深深带进王、申二人的情感悲剧之中无法自拔,如第四十八出[破齐阵]的眉批:“古云长歌之悲甚于痛哭,他人不堪闻,何况仆哉?”第三十八出结尾的四支曲子,陈评道:“读此我亦萧萧头白。”第五十出的一处眉批则将自己的写作体验直接写在了评点当中:“各人还他口气,一字不滥用,近日作文正苦不知此法。”这种偏向私人化的评点也侧面反映出为朋友所作评点所特有的轻松而质朴的状态。
主客观相结合的评点视角,与陈洪绶和作者孟称舜的关系有关,二人私交甚多,艺术理念又相仿,故陈洪绶的评点状态也是自由、松弛的。这种情况在其他评点作品中时有发生,说明当时的评点者或许还没有严格的身份自觉。但从另一个角度去看,主观评点可以看作评点者对其身份的跳出,而引起不自觉身份跳出的文本内容值得读者特别关注。身份的跳出可能由于该处文本恰戳痛处,引发身世之悲,这对了解评点者的经历有所帮助;也可能由于该处文本的写作方式有所转变,或者艺术处理更有新意,这会增强读者的阅读敏感,对辅助文本理解也大有裨益。另外,有些主观视角是从单纯的读者视角出发的,阅读此类评点,会引发共鸣,增进读者对文本情感的理解。
3.宗元的审美标准
以元曲为创作目标和审美标准是晚明戏曲创作、评点的一大普遍现象,孟、陈二人也对元曲高度评价并引以为典范。孟称舜不仅在自己的戏曲创作中实践了对元曲的模仿和再创作,在其戏曲批评中也提及对元代戏曲创作的推崇。如《误入桃源》总评:“元人高处在佳语、秀语、雕刻语络绎间出,而不伤浑厚之意。”[27]又如《燕青博鱼》总评:“元人之高,在用经典子史而愈韵愈妙,无酸腐气;用方言俗语而愈雅愈古,无打油气。”[28]孟称舜在自己的原剧作《桃花人面》的基础上加以重新修改,创作了《桃源三访》,“《桃源三访》的改动背后,体现了作者杂剧观念中宗元的自觉性。正因为自觉,孟称舜才会不遗余力地斧凿于旧作,不惮劬劳地操刀于新篇。”[29]在陈洪绶的戏曲评点中,常以西厢作为其评价标准,对孟的作品不时有溢美之词。如《桃源三访》第一折对[胜葫芦]及后几曲的评点“此下数枝,着意追想,尽情惆怅,与会真首折同妙”,对《娇红记》第十四出开头宾白的评点“一缕空描,实甫低头”等等,该种比较有十余次。元人的语言本色、当行,广为明人推崇,在陈洪绶的评点里,对语言口吻颇为重视,故语言自然当行实为最高标准。如《泣赋眼儿媚》中第一折对[山石榴]的眉批:“是妓人语致”,这是对语言当行的赞美,又如对《娇红记》第三十一出[猫儿坠与玉枝]的批语:“白描丽情,委折如诉。文章化境,岂人所为”,是对语言自然朴实、浑然天成的认可。《桃园三访》较于《桃花人面》,语言上更加追求质朴自然是其中的一大变化,而通过陈洪绶对《桃源三访》改动的认可,也可见陈、孟二人对于元曲宾白自然的青睐。
4.崇尚“情真”的艺术观
陈洪绶所评的四出剧目,均是讲述才子佳人恋情的爱情主题,且从陈对《娇红记》评点的分布情况来看,他也是牢牢抓住王、申二人的情感主线,不会在其他支线上给予过多关注。陈洪绶在《娇红记总评》中称赞《娇红记》“此曲之妙,彻头彻尾一缕空描而幽酸秀艳,使读者无不移情,固当比肩实甫,弟视则诚”。在第四十五出《泣舟》眉批中评论道:“十分情十分说出,能令有情者皆为之死。”相较他在《娇红记》序言中关注天下之教化以及男女情感的“出于正”,陈洪绶在评点中却削弱了这种理义的观念,反而专注于感情本身。
从评点来看,陈洪绶对“真”的推崇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历数《娇红记》中对“真”的强调,如“怨则真怨,喜则真喜,真宰自为,非关想象”,“呜咽之语,字字传真”,“情真意真”,“真啼真痛”,多从表层情绪直导深层情感。对于如何描写情真,陈洪绶颇为强调情绪的层层铺垫,反对无凭无据的生硬变化,如强调“两情未交,正须步步研实方妙”。这种对“情真”的推崇也与晚明评点对“情真”“情至”的欣赏是一脉相承的,从这个角度看,陈洪绶不仅出色地完成了评点工作,还是评点队伍中的领潮者。
一部被盛赞为“情史中第一佳案”的《娇红记》,却被孟称舜冠以“节义”二字,历来研究者都有不同解读。就性情与理义的关系来看,孟称舜认为义夫节妇的出现并不是理所当然,是人的真性情使然:“天下义夫节妇,所为至死而不悔者,岂以为理所当然而为之邪?笃于其性,发于其情。”他还认为,“性情所种,莫深于男女。而女子之情,则更无借诗书理义之文以讽喻之。而不自知其所至,故所至者若此也”。陈洪绶所作《节义鸳鸯冢娇红记序》,实乃为其好友孟称舜的一次辩驳。与王业浩的《鸳鸯冢序》和马权奇的《鸳鸯冢题词》有异曲同工之妙的,在于对孟称舜追求至情、真情的肯定。对于冠以“节义”二字,陈洪绶与马权奇均从男女情爱上升到天下教化的角度加以论证。在陈洪绶的《节义鸳鸯塚娇红记序》中,为孟称舜进行了一番重申:“盖性情者,理义之根柢也。”“夫子删诗,不废郑卫,况子塞所著所选,又皆以情而出于正者乎。”“而申、娇两人能于儿女婉娈中,立节义之标范,其过之不甚远也哉。”[30]陈洪绶所说的节义,自然可以从理学、伦理、道义的角度去理解,申、王二人的感情,是具有极高道德性和具有教化意义的“无邪”的真情,是一种理想化的感情模式。但从陈洪绶的评点细节对比来看,他的关注点紧紧围绕深情、真情和悲情展开,却从未提及序言中所关注的“节义”“教化”等问题,如此来看该序言更像是对好友创作出发点的顺从。
四 结语
陈洪绶的戏曲批评是窥探晚明戏曲世界的一个重要窗口。首先,他作为当时备受推崇的大画家,其所创作的大量戏曲图像也是戏曲批评的一种方式。周之标在《吴歈萃雅·选例》中提及:“图画止以饰观,尽去难为俗眼,特延妙手,布出题情,良工独苦,共诸好事。”[31]戏曲图像已经超越了装饰的范畴,而具有再现、浓缩情节、还原人物形象、彰显精神内涵等作用。画者的对象选择和图像构思,均体现出其对戏曲文本的理解,甚至还有二度创作的意味。在晚明的戏曲刊刻作品中多次出现陈洪绶的戏曲插图,且出自刊刻名手,也反映出当时对戏曲刊刻质量的追求,体现了戏曲刊印、传播的繁荣。其次,陈洪绶作为一个戏曲评点者,为我们展现了晚明戏曲批评中的一些审美特征。对元代戏曲的推崇,主“情”主“真”的审美取向,均在陈洪绶的评点中再次得到验证。陈洪绶所常用的一些评点词汇,对于丰富评点语言、解读戏曲作品具有重要意义。而“怨谱”一词的提出,使陈洪绶的戏曲评点又上升到了一个理论的高度。从对悲剧性有局部的感性体认,到晚明陈洪绶可以对悲剧作品的悲剧风格用理性思维加以总结,说明对悲剧风格的评论“已经走向了成熟,具有了较高的理论水平”[32]。再次,陈洪绶作为孟称舜的好友,二人在戏曲批评上跨越曲、诗、词、文、画的批评互动和二次创作,也是晚明戏曲批评领域一个值得注意的重要现象。得益于陈洪绶的绘画经验,他的评点话语被赋予了更加具象可感的特色;得益于他的戏曲熏陶,他的图像评点能将动态的人物形象准确地浓缩于静态的人物小像之中。此种评中有画、画中有评的多维度戏曲批评,纵观戏曲史,也罕有人能望其项背。从陈对孟《娇红记》的序言和评点语言来看,其风格的平实自然,态度的真诚恳切,与其他的戏曲评点语言有较为明显的不同,可以引入评者与作者关系对戏曲批评的影响这一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
要之,了解陈洪绶与同时代戏曲家和伶人频繁的交往活动之后,就能够理解陈洪绶的戏曲批评可以把握晚明戏曲批评潮流的原因。通过考证陈洪绶与孟称舜的交游过程,有助于掌握二人的深厚情谊,理解陈洪绶的戏曲批评思路。同时总结陈洪绶戏曲批评的特色有利于了解陈洪绶在戏曲领域的价值,深化对孟称舜戏曲作品和晚明戏曲批评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