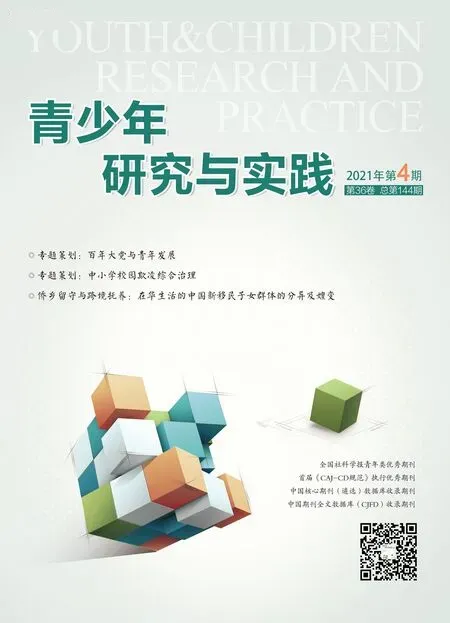随迁子女回流对学习适应的影响研究
2021-12-22乔世延吴彥芳邓锐坚
乔世延,吴彥芳,邓锐坚
(南京农业大学,江苏 南京 210095)
在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中,全国人户分离人口为4.92亿,其中流动人口高达3.75亿。相较以前,流动人口出现了“家庭化”的结构特征,即举家迁移[1]。为了不让自己的孩子成为留守儿童,许多进城务工人员选择将孩子带在身边,流动儿童成为流动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据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010年,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生中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有1167.17万人,到2019年,上升至1426.96万人[2-3]。然而,在当前户籍制度下,大量流动儿童仍面临回到户籍所在地入学的困境。尽管国家教育部门颁布了许多促进随迁子女入学的政策,但是都没有在根本上改变“户籍优先”“在户籍所在地就近入学”的教育体制。自2014年以来,北上广深等大城市严格控制人口规模,实行教育疏解政策,全面提高异地入学门槛,随迁子女不得不返回户籍所在地入学,进而产生大规模的回流儿童[2]。这些流动儿童原本很少回老家,突然回到陌生的老家上学,会措手不及。又由于城乡两地教学理念、教学环境、教学内容等方面的差异,回流儿童通常会面临学习上的不适应。生命历程理论指出,儿童时期的经历在某种程度上会影响其整个生命历程的发展[3]。儿童时期的回流经历必然会对其个人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考察回流经历对儿童学习适应的影响显得尤为重要。
目前,关于流动儿童的研究众多,主要集中于早期的流动经历对于随迁儿童学业表现、心理健康、社会融合等方面的影响。尽管学界对于流动经历的影响存在争议,但是近年来的实证文献倾向于认为,农村儿童与父母随迁到城市后的学习和生活经历,有助于提高流动儿童的认知能力和身心健康发展[4-6]。与普通的流动儿童不同,回流儿童经历了曾经随父母进入城市,后来又返回家乡的动态过程。文献中对回流儿童群体的关注不多,现有相关研究以定性研究为主,少数为定量研究,这些研究主要关注回流儿童回流后的适应问题。张宝歌通过对回流儿童的调查发现,学习和生活环境的转换,导致他们对自我产生怀疑和对农村环境失望,加上城乡教学的差异性和父母教育方式的转变以及老师的不够关心,使得他们对学习失去激情进而产生不适应性[7]。丛玉明等将本地儿童与回流儿童对比研究发现,环境的多变使回流儿童很难形成长期稳定的人际关系,进而不利于他们的自尊发展[8]。王敏则通过某中学的案例研究发现,返乡之后的回流儿童在文化适应、人际交往适应、心理适应方面均存在不同程度的问题[9]。黎煦等基于农村寄宿制小学的实证研究发现,回流降低了贫困地区农村儿童的认知能力,并初步分析出学校教育和家庭关怀的缺失是回流儿童认知能力下降的重要原因[10]。同时,来自城市和农村环境的双重排斥会对农村儿童的心理健康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造成回流儿童的抑郁风险增大,降低了他们的自尊和抗逆力水平[11]。
本文在已有的研究基础上,利用课题组的调查数据,关注回流经历对于农村儿童学习适应的影响,着重分析回流儿童的学习适应现状及存在的问题,考察回流儿童与非回流儿童在学习适应上的差异,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改善回流儿童学习适应状况的建议。
一、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一)数据来源及特征
本文所用数据来源于课题组在劳动力流出大省安徽、湖南、江西三省的调查,具体为在安徽省的六安市和滁州市、湖南省邵阳市、江西省抚州市开展的农村实地调查。调查抽样原则如下:课题组分别在上述4个地级市随机抽取一个乡镇;然后从各个乡镇随机抽取若干农村学校;最后,考虑到学校规模大小的差异,按照每所学校总人数30%的比例抽取样本。在儿童年龄上,采用国际儿童公约的界定,即18岁以下为儿童。在流动的地域范围上,采用教育部的定义,不把县域内流动纳入流动儿童的范畴[12]。结合回流儿童的年龄范围和流动范畴的界定,将回流儿童局限在小学期间曾经跟随父亲或母亲到户籍所在市以外地区流动半年以上,且已回流到户籍所在地入学半年以上的18岁以下的农村儿童。根据本文的研究目标,在剔除无效样本后,共收回有效问卷398份。其中,回流儿童问卷195份,非回流儿童问卷203份。
表1描述了本次调查样本的基本情况,回流儿童中男女比例基本持平,非回流儿童中男生占比略高。回流儿童年龄主要集中于11—14岁。一方面,抽样中11—14岁占比较高;另一方面,回流儿童在小学五六年级时,因在随迁城市达不到中高考的门槛条件而返乡入学,所以11—14岁是回流高峰期。

表1 受调查农村儿童基本特征
为了更好地了解回流儿童的困境,课题组对回流儿童的返乡原因做了统计,发现回流儿童回到家乡上学的原因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如父母在乡村振兴背景下返回家乡就业或无法承担城市入学的高昂学费,回流儿童无法适应城市的学习环境,大多数随迁儿童就读的农民工子弟学校教学质量不如家乡的学校等,这些都是导致儿童回流的重要原因。
(二)变量设定
自变量为是否是回流儿童,因变量为学习适应。目前,关于学习适应的测量指标并没有统一的界定,从狭义而言,学习适应是学习过程中所表现的适应行为及特点[13]。从广义来看,学习适应是根据环境及学习的需要,为了克服学习困难的各种适应活动及其结果的总和[14]。综合来看,学习适应包括学习过程中的自我调整和对周围学习环境的适应。本研究结合目前学界大多采用的周步成编制的学习适应性测验[15],将学习适应分为学习态度、学习环境、学习成效、学习动机四个维度来考察回流对农村儿童学习适应的影响。其中,学习态度是学习者对学习比较持久的内在反应倾向。学习动机则是引导、激发和维持学习活动的内部动力。学习态度虽然受到学习动机的制约,但在学习活动中受到周围环境的影响,是可以改变的[16]。学习环境指学习的外部环境,是学习者学习适应的重要方面。学习成效则着重考察学习者的学习适应效果。问卷整体的克朗巴哈系数为0.715,大于0.6,有良好的信度。学习态度、学习环境、学习成效、学习动机分别由三个变量组成。以学习态度为例,学习态度基于问卷中“您是否主动规划课程学习”“您是否主动参与课程学习”以及 “您是否体会到学习乐趣”三个问题测度,回答“是”赋值为1分,“否”赋值为0分,从而学习态度总赋分为0—3分,分别对应差、较差、一般、好。学习环境、学习成效和学习动机的测度方法与学习态度一致。同时,控制变量包括儿童的个人特征、家庭特征变量。
表2报告了回流儿童与非回流儿童样本组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从父母双方最高受教育程度来看,回流儿童父母的最高受教育程度要高于非回流儿童父母,且差异在1%水平上显著。从父母居住安排来看,非回流儿童父母在老家居住的情况要略多于回流儿童父母,但是均值差异不显著。从学习态度方面来看,在主动规划课程学习和体会学习乐趣均值上,非回流儿童均显著高于回流儿童。此外,学习环境方面,在对教学环境和课堂教学的满意度均值上,非回流儿童显著更高。学习成效方面,非回流儿童在学习成绩的提高和学习目标的实现上比回流儿童更好,且均值差异显著。然而在学习动机方面,回流儿童表现优于非回流儿童,但是只在有强烈学习意愿方面显著。描述性统计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回流儿童在学习适应总体上比非回流儿童差,但这是并未控制其他变量时的结果,因此需要进一步的计量分析。

表2 主要变量的含义及统计性描述
(三)模型选择
为进一步验证回流对农村儿童学习适应的影响,借鉴李放的研究[17],我们设立了有序Logit模型进行计量分析:

Ym表示被解释变量:农村儿童的学习适应状况。m=1,2,3,4分别表示农村儿童的学习态度、学习环境、学习成效和学习动机。j=0,1,2,3表示差、较差、一般、好4种适应程度。Xi为影响因素变量。本部分的核心解释变量为农村儿童是否有回流经历。此外在模型中还加入了控制变量,包括农村儿童的个人特征和家庭特征。
二、实证结果与分析
表3是有序Logit模型的分析结果,模型一、模型二、模型三与模型四分别是关于回流对农村儿童学习态度、学习环境、学习成效、学习动机方面影响的计量分析,且模型都在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

表3 有序Logit模型计量分析结果
从模型一可以看出,回流对农村儿童的学习态度有负向的影响,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回流儿童到农村学校后,难以适应教育模式、教育理念等方面的差异,逐渐产生厌学情绪,表现出不积极参与课堂、不主动规划学习等行为,从而失去对学习的兴趣。
从模型二可以看出,回流农村儿童对学习环境的适应要显著差于非回流儿童。回流儿童在城市上学时,被本地学生看作随迁子女被歧视;回到老家以后,因为城乡地域文化的差异,短时间内也无法融入当地农村儿童的生活学习圈,来自城乡的双重排斥不利于回流儿童的人际关系发展。同时,回流儿童刚刚回到农村上学,对于周围的一切都感到陌生,在与老师同学的关系和对老师的教学方式适应上相比非回流儿童更差。除此之外,回流儿童在返回农村上学后,也会对相比城市落后的农村教学环境产生不适应。
从模型三可以看出,回流对农村儿童的学习成效有显著负向的影响。这与他们的学习态度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学习态度是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信念支撑,好的学习态度有利于激发出好的学习表现[18]。与非回流儿童相比,回流儿童的学习态度更差,因而可能在学习成效上表现更差。同时,城市和农村教材版本不同,教学知识的差异导致回流儿童融入农村学校的教学比较困难,学习成绩短时间内出现下降。
从模型四可以看出,回流对学习动机有正向的影响,但并不显著。在城市上过学的回流儿童能深入体会到城乡之间的差距,虽然回到农村上学,但是他们向往到城市发展。即使回流之后各方面表现差于非回流儿童,但是仍然希望通过教育改变自己的未来,故学习动机并未被削弱。学习动机是学习的内生动力,可以激发出良好的学习态度,两者本应一致,但是在本研究中却出现了偏差。这主要因为回流儿童遭遇了现实的困境。回流儿童在学习、人际关系、生活环境上产生了一系列的不适应,环境变化带来的负向效应会抵消一部分学习动机增强所带来的正面影响,进而影响回流儿童的学习态度。
在控制变量中,总体来看,儿童的年龄对学习适应有正向显著的影响。随着年龄的增长,儿童心智发育会更加成熟,即使面对回流入学的困境,也能及时调整适应学习变化。父母受教育程度越高,就越注重培养孩子正确的学习态度、行为习惯等,同时在孩子的学习过程中潜移默化地激励着他们学习,所以父母受教育程度对农村儿童学习适应有正向影响。此外,如果父母双方都在外地,缺乏对子女的监督与照料,亲情的缺失就会加剧农村儿童回流入学的不适应。
三、稳健性检验
农村儿童是否回流并不是随机产生的,可能受多种因素包括其个人特征和家庭特征等变量的影响。若不对这些内生性因素进行有效的处理,可能无法正确地估计回流对农村儿童学习适应的影响。对此,本文参考唐宁和李放[19-20]的研究,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来检验有序Logit模型估计的稳健性。首先,将样本分为处理组(回流儿童组)和控制组(非回流儿童组),计算每个农村儿童回流的倾向得分,再根据倾向分数匹配后的样本来计算平均处理效应(ATT),以此来判断回流对农村儿童学习适应的净影响。本文采用核匹配方法来分析回流对农村儿童学习适应的影响,来报告处理组在学习态度、学习环境、学习成效、学习动机上的平均处理效应。结果如表4所示,四个变量的ATT数值方向与有序Logit模型估计值方向相同,且在学习态度、学习环境因素上效应显著,只是影响程度变得更小,说明倾向得分匹配法有效地缓解了由样本自选择问题带来的内生性,得到回流对农村儿童学习适应的净影响。

表4 回流对农村儿童学习适应的平均处理效应
为了检验匹配质量,需要对解释变量做平衡性检验,分析结果见表5。匹配后各个变量的标准偏误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最高下降了95.6%,最低也降低了36.3%。全部变量匹配后的组间差异检验p值都增加了,且均大于0.5,说明匹配有效地解决了回流儿童组与非回流儿童组的系统差异。

表5 回流组与非回流组平衡性检验结果
为了检验匹配结果的稳健性,分别采用半径匹配、最近邻匹配方法报告处理组的平均处理效应,如表6所示。从不同匹配方法ATT结果可以看出,四个变量得出的结果与核匹配方法大致相同,虽然数值和显著性水平有差异,但没有影响到最后的结论。

表6 稳健性检验结果
四、研究结论与启示
由于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壁垒以及城市教育资源有限等原因,大量流动儿童不得不返回户籍所在地入学。事实上,回流不仅意味着流动儿童学习空间位置的变动,还会对其学习适应产生影响。本文在安徽、湖南、江西3省农村儿童调查数据基础上,分析了回流对农村儿童学习态度、学习环境、学习成效、学习动机4个方面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回流农村儿童在学习态度、学习环境与学习成效方面与非回流儿童相比都处于劣势。初步分析认为主要是学习环境改变的原因,回流儿童在返乡之前已经习惯了城市的生活学习方式,回到差异较大且相对落后的农村后无法尽快融入新的环境。比如方言带来的交流壁垒,使用城市普通话反而被本地学生嘲笑;参加集体活动时被本地学生隔离孤立甚至被欺负;师生关系的转变导致回流儿童对老师的教学方式不认可等,引发严重的心理冲突。这些状况都不利于形成良好的人际关系,从而对其学习适应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同时,城乡教学体系和教学理念的不同,也增加了回流儿童的学业衔接困难。尽管回流经历给回流儿童带来了一系列不利影响,但回流儿童还是有强烈的学习动机,希望通过教育程度的提高改变自己的未来。因此我们需要加大对回流儿童的关注,帮助他们提高学习适应能力,促进回流儿童的健康发展和社会公平。研究还发现,农村儿童家庭文化资本匮乏,具体表现为农村儿童父母受教育程度较低以及父母双方都在外地,缺乏对农村儿童的感情支持和学习指导,这些都会进一步导致回流儿童学习的不适应。从这点来看,父母要经常关心回流儿童学习生活状况,积极引导他们融入农村生活环境。
根据研究结论可以得出以下几点启示:第一,尽量减少回流儿童现象的产生。大量流动人口迁移潮中出现了举家迁移的结构特征,政府应该加大户籍制度的改革力度,完善教育公平,为随迁儿童的教育创造各种有利的条件,降低异地入学高门槛,打破流动儿童在城市升学的障碍。第二,对于回流儿童来说,回流带给他们的重大困境是家庭结构的变化。农村父母外出务工时,在选择是否将子女带入城市就学时要理性决策;如果子女不得不返乡就读,让孩子至少在父母的陪伴下一起回流入学,增强孩子对农村学习生活的归属感。三是学校应该努力构建回流儿童关爱与教育体系,为回流儿童的课程学习做好衔接,老师要多关注回流儿童的学习和心理状况,关注年龄较小和父母双方都不在家的回流儿童,努力消除回流儿童与本地儿童的文化交流障碍,使之能够尽快融入回流后的学习和生活场景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