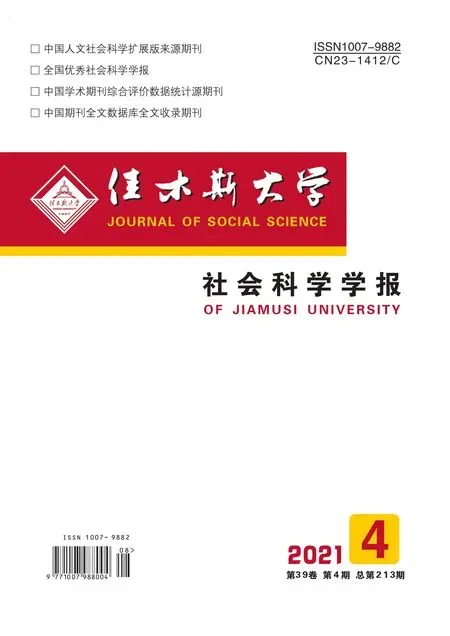萧红小说《小城三月》的空白书写*
2021-12-07李韦函徐晓杰
李韦函,徐晓杰
(佳木斯大学 人文学院,黑龙江 佳木斯 154007)
“空白”这一概念最早由德国接受美学的代表人物W·伊瑟尔提出。W·伊瑟尔认为,所谓“空白”就是指“文学文本中未被写出的部分,它们存在于文本中已经写出的部分向读者暗示或提示的语言和情节结构中。”[1]207空白的存在,使读者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获得了展示其价值意义的空间;同时,读者也获得了作品意义完成者的身份地位。由此,空白是一个积极的、引导阅读得以顺利进行的建构性力量,读者在阅读整合的图式结构中完成其审美想象对文本的建构。W·伊瑟尔“空白理论”的问世冲击了文学研究的传统思维模式,其最根本的原因是把读者提到了文学研究的中心地位。作为接受美学的代表人物W·伊瑟尔始终按现象学的思路,把阅读过程作为文本与读者的关系来掌握和描述,认为文学作品是文本与读者的结合。我们运用W·伊瑟尔的“空白理论”重新解读萧红的《小城三月》时,这部作品作为审美对象在读者的阅读过程中就动态地被建构了。
一、情节空白 尽显风流
在W·伊瑟尔的“空白理论”中,空白出现在文本的各个层次,具有多种表现形式。萧红在《小城三月》中对情节的设置布满了“未定点”和“空白”,这就有待于读者在阅读中对“未定点”加以确定和对“空白”加以补充。《小城三月》开篇即言明“我有一个姨,和我的堂哥哥大概是恋爱了”,这给读者带来的暗示是:作品在讲述翠姨跟堂哥的恋爱史。然而文本没有顺应读者原有的期待,反之将二人的恋爱过程作为空白和模糊点加以隐藏,巧妙制造陌生感,符合两个人恋爱的朦胧性与内心遮蔽性,进而,在形式上和意蕴上对读者进行了邀约。读者带着最初由文本引导形成的期待视野进入文本,却在阅读过程中受到阻碍。这时,一旦读者在文本激发的作用下发挥出填补空白的主动性与再创造的能力,就得以根据文本提供的线索充分再现未言部分,将被中断的故事情节还原。在此过程中产生的新的审美快感与审美经验则是文本为不同时期的不同读者提前准备好的礼物。
作者往往运用其最擅长的内聚焦叙事来设置情节的空白。《小城三月》就以孩童的非全知视角来描述翠姨与堂哥间或明或暗的简短交集。这些寥寥的交集建构起审美对象的图示化框架和召唤结构,情节之间的未定点则构成情节空白,引发读者联想与想象。比如作品写到:“不过有一天晚饭之后,翠姨和哥哥都没有了……我想一定是翠姨在屋里……我跑进去一看,不单是翠姨,还有哥哥陪着她。看见了我,翠姨就赶快地站起来说:‘我们去玩吧。’哥哥也说:‘我们下棋去,下棋去。’他们出来陪我来玩棋,这次哥哥总是输,从前是他回回赢我。我觉得奇怪,但是心里高兴极了……不久寒假终了,我就回到哈尔滨的学校念书去了。可是哥哥没有同来……以后家里的事情,我就不大知道了……我走了以后,翠姨还住在我家里。”[2]35-36文本通过叙述者的介入完成情节上的跳跃,即“我”撞到翠姨与堂哥的会面,导致会面被中断。又以叙述者的离开为故事情节留下空白,即“我”回哈尔滨的学校念书,留下翠姨与堂哥在家里,他们两人到底说了什么、做了什么,读者无法知晓。可见,情节上的中断或“空白”恰恰是“一种寻求缺失的连接的无言邀请”[3]71。
文本舍弃对爱情桥段的全部精彩描述,利用叙述者的非全知视角的局限故意将二人的你来我往隐藏起来,仅提供读者一些含糊的线索,将创作故事情节的权柄交由读者。这样做产生的效果是最大限度地激发欣赏者的审美快感,把文本转化为读者的经验和新的期待视野。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参与文本审美对象和意义生成的再创造过程,于是作品中最为精妙绝伦的描述正是每一位读者脑海中关于爱情模样的美好向往的汇集,而所谓的“不着一字,尽显风流”也正是萧红试图通过“空白”来展现爱情的风情万种。
二、形象空白 入木三分
鲁迅曾站在以作品为中心的立场批评萧红的作品中“叙事和写景,胜于人物的描写”[4]2,暗示作品中人物形象略显苍白。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起,文学研究的思维范式开始从“作者中心”和“作品中心”转向“读者中心”。时代不同,对文学作品的理解也会不同,文学批评也应摒除先见,重新审视萧红对人物形象的刻画。
萧红在《小城三月》中对人物形象的刻画同样布满了“未定点”和“空白”。这在翠姨形象的描写中得到体现。翠姨住在外祖父的后院,与外祖父家隔着一道带着缝隙的板墙。每每外祖母招呼翠姨过来,有时翠姨会先从板墙缝中和“我”打了招呼,再回屋装饰一番,“才从街上绕了个圈来到她母亲的家里”[2]5。这里借空间设置的叙事手法给人物形象留有空白,人物的刻画也达到了出神入化。翠姨是“我”外祖母的亲生女儿,平日里却没有和“我”一样住在前院,后院与前院之间的板墙虽然薄薄的不似水泥墙般厚重,甚至带着裂缝,但它却是翠姨内心的壁垒。这道板墙时刻提醒着她,使她举止不能出格,于是她“走起路来沉静而且漂亮,讲起话来清楚的带着一种平静的感情”。同时,板墙还是翠姨同新的文化、新的思想之间的隔膜。翠姨对所有读过书的人都会油然产生敬佩的情感,对读书的态度是渴望又好奇。一道板墙,透着裂缝,让翠姨看得到彼岸世界却不能直接伸手触到。对她而言,与堂哥和“我”这样的人相比,从蒙昧世界到知识世界的路途总是遥远的,可能需要绕过一条大街,有时比一条街还远。
文本没有直接描写翠姨对所爱的执着,而是生动地勾画了她为买绒绳鞋所付出的努力。这份执着不仅仅是一双鞋,还是觉醒的自我、萌发的爱情和新的文化。翠姨虽早早地就爱上了绒绳鞋,却没有在它刚流行起来时就果断买下来,这意味着翠姨行动的滞后性,同时还象征着翠姨意识觉醒的滞后、爱情追求的滞后、知识获取的滞后以及命运抗争的滞后。数次跑遍商场却仍然买不到绒绳鞋,翠姨意味深长的那句“我的命,不会好的”深刻地象征着翠姨身上带有“林黛玉”一样的弱质性格和发自本能的悲剧命运感。
由此,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将这些图式化的框架联系起来,一个丰富立体的翠姨人物形象就被建构出来:温雅、弱质性格、执着、有觉醒意识、有悲剧命运感、有求知欲,这些互相矛盾的因素决定了翠姨觉醒后的所有抗争都未能转化为向外的积极力量。最后,被逼得无路可走的生命只得以软弱无奈的姿态寂灭。
“空白”不仅不是文学本身的缺点,而恰恰是它的特点与优点,它为读者留下足够的空间和余地,这不代表作家可以随意地制造空白。具有审美价值的空白不是凭空产生的,它一定要经过作家独具匠心的设计,有规律地呈现在读者面前,这样才能营造高级的美感,激发读者对美的感知,给阅读过程带来新的审美体验。萧红塑造人物形象的空白设置恰恰是一种以读者为中心的超越时代局限的创新意识。形象空白是最具美学价值并且经得住漫长历史考验的刻画手法之一。
三、意蕴空白 大言无声
《小城三月》篇幅虽小却含有丰富的意蕴。这意蕴同样需要填补“空白”来揭示。《小城》开头和结尾都在描绘时值三月的小城的景象,都使用了草、花、树的意象,只是情感色彩发生了变化。开头更多地渲染春天的热闹,“三月的原野已经绿了……河冰发了……天气突然的热起来……小城里被杨花给装满了,在榆树还没变黄之前,大街小巷到处飞着……春来了,人人像久久等待着一个大暴动,今天夜里就要举行,人人带着犯罪的心情,想参加到解放的尝试……春吹到每个人的心坎,带着呼唤,带着蛊惑……”[2]1;结尾则突出春天的短暂:“翠姨坟头的草籽已经发芽了……这时城里的街巷,又装满了春天……但是这为期甚短……接着杨花飞起来了,榆钱洒满了一地。在我的家乡那里,春天是快的……春天的命运就是这么短……她们白天黑夜地忙着,不久春装换起来了,只是不见载着翠姨的马车来。”[2]45-46
看似还是一样的季节,却不再是同一个春天了。具体有何不同,文本没有给出自己的阐释,只提供读者以情感变化的暗示和未言的空白,这体现萧红巧妙的笔法和文本更深层的意蕴。空白是吸引与激发读者想象来完成文本、形成作品的一种动力因素,如果文本为读者提供了全部的故事,没给他留下想象空间,那么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就会不可避免地要产生厌烦。 我们带着阅读动力去层层剖析《小城三月》的多重意蕴,在审美欣赏过程中就会体悟到人类同自然一样循环往复的宿命。小说结尾的意象比开头多了一座翠姨的坟墓,也就是说翠姨终没抵过寒冷的严冬,一场抗争的结果是生命的终结与消寂。
《小城三月》是萧红在病榻上的绝笔之作,她在生命的最后时光中,发出了灵魂之问:翠姨是从蒙昧中觉醒的向往新文化的人,新思想到底能不能赋予她生命的意义,使她获得自由的人生。也许答案被藏匿在文本蕴含的深刻意蕴之中,也许其实文本也并没有提出这样的问题。而一旦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提出了疑问,文学作品的无声呐喊就被具体化了,读者自身的哲学思考和审美体悟也随之产生。意蕴层空白的精妙之处就在于此,它体现着大言无声的哲学思考与审美体悟。
萧红在《小城三月》中正是通过对情节、形象以及意蕴的空白书写,使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将文本编织的图景片段衔接起来,从而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多层次的图景结构,文本的意义也就在阅读主体中被建构了。
W·伊瑟尔的“空白理论”与海明威的冰山原则不谋而合,海明威在《午后之死》中提出:“一座移动着的冰山显得高贵,是由它那浮出水面的八分之一决定的。”[5]263就像深海处的冰山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温度的变化而改变体积,文本的“空白”也不会是一成不变的,它会因历史、政治、文化的因素不同,各时期读者也会根据自己的经验世界和逻辑思维不断地参与文本的建构,多元、多维、多重的文本阐释会为读者的审美体验带来无穷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