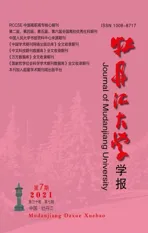多元族裔家庭的身份流变
——以任碧莲的《爱妾》为例
2021-12-07赵雅婧
赵雅婧
(长治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山西省 长治市 046000)
任碧莲(Gish Jen,1955-),出生于美国的纽约长岛,1977年毕业于哈佛大学,1983年获得爱荷华大学作家坊小说创作艺术硕士学位。被认为是美国当代文学界的重要华裔作家,她的作品标志着美国华裔文学在20世纪90年代的一个重要转折,她的系列作品没有停留在观照华裔华人如何获得美国人的身份归属、获得主流社会的认可上,而是以反本质主义身份观的立场提出了多元文化下文化身份的自由选择,解构了美国主流社会的霸权身份观[1]。她的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典型的美国佬》(Typical American,1991)、《蒙娜在希望之乡》(Mona in the Promised Land,1996)、《爱 妾》(The Love Wife,2004)、《世界与小镇》(World and Town,2010)和短篇小说集《谁是爱尔兰人?》(Who’s Irish,1999)。
《爱妾》是任碧莲写作生涯中对族裔性和文化身份议题探索较为成熟的一部优秀小说。该小说的主要人物来自美国波士顿郊区一个国际化的多种族家庭。第二代华裔男主人卡内基·王娶了白人女子布朗蒂,大女儿和二女儿是他们收养的亚裔女孩,最小的贝利是他们的亲生儿子,贝利继承了母亲布朗蒂的金发和白皮肤。卡内基的母亲王妈妈去世前留下遗嘱要中国的亲戚兰兰来美国照顾三个孩子。这个多族裔混合的家庭因为文化背景、社会环境以及对彼此的猜忌,家庭成员间生发了各种冲突矛盾,他们对自己的伦理身份和文化身份属性产生了焦虑困惑。作家用“中国儿子”与“美国儿子”、“收养的”与“亲生的”、“主”与“仆”、“妻”与“妾”这几对隐喻的关系体现了多族裔家庭在多元文化环境下追寻身份归属的超越性探索。[2]
一、王家人的身份困扰
王妈妈作为第一代华裔,靠着自己的聪明才智果断投资房地产,成功实现了发财致富的美国梦,可是骨子里却是一个传统观念和族裔意识很强的老太太。她安排华裔女孩与卡内基相亲,她反对卡内基娶白人为妻。她给儿子取名卡内基,希望儿子可以子承母业,做个像工业巨头卡内基那样成功的企业家。然而卡内基却与母亲的想法思维和价值观背道而驰,十分排斥母亲的管教方式和对他人生的各种安排。他对打理发展母亲的房产业不感兴趣,他故意选择离家很远的中西部上研究生以远离母亲的控制,他不学中文、不见母亲安排的华裔女友。卡内基觉得自己跟母亲是完全不一样的,他认同的是主流白人文化和美国的价值体系,他是地道的美国人。然而卡内基这种有意去掉自己的中国属性去极力迎合白人主流文化的做法其实并没有赢得主流社会的接纳,西方强权主流社会依旧在以族裔、血缘来判定一个人的身份属性。比如卡内基遭遇白人种族主义者的挑衅时,他却只能搬出妻子布朗蒂的白人身份和家族财富作为其炫耀的成功资本来对抗种族歧视。因此,可以看出,卡内基这种以牺牲自己的祖先文化,有意疏离“中国”血缘的文化记忆,其实是西方霸权文化对少数族裔的文化殖民。[3]卡内基作为第二代华裔,其成长过程中的家庭教育自然受到王妈妈强烈的中国传统文化和思维的熏陶,这种来自中国文化的记忆已经潜移默化地根植在他内心。他的故意叛逆和与母亲的对抗冲突,其实是两种文化在他身上的冲撞抗衡。他自小就徘徊在两种文化身份之间,是做母亲期待的孝顺“中国儿子”还是做以个人为中心的“美国儿子”?卡内基在内化美国主流文化对华人“他者”的凝视过程中,并没有主动积极地建构自己的文化主体地位。所以,他身处在被两种文化双重“他者化”的尴尬境地,自然会对自己的身份属性感到迷茫和焦虑。
大女儿利齐是卡内基婚前在教堂台阶上收养的亚裔女孩儿,二女儿温迪是卡内基和布朗蒂婚后专程去中国领养的,缘由是为了跟利齐作伴。虽然两个女儿是收养的,但是布朗蒂待她们视如己出,关心疼爱。但是外貌特征上的差异很容易让外人认为她们不是母女关系。后来,布朗蒂意外怀孕生下了金发碧眼的贝利。两个养女就此认为妈妈布朗蒂会更疼爱亲生的弟弟,尽管布朗蒂对她们的爱丝毫没减。两个养女从小就常被外人问到“是从哪里来的”,这些好奇的目光和提问让她们深受伤害,时刻提醒着她们身属被收养的“他者”地位,这些无形的种族主义压力让她们无法拥有正常的家庭身份,让她们始终感觉到自己身上的“异类”烙印。兰兰的出现让她们在某种程度上感觉到了一些熟悉感和亲切感,她们越发喜欢跟与自己种族一样的兰兰待在一起。同时,由于青春期出现的一些叛逆性,利齐与母亲布朗蒂之间的正面矛盾和冲突越来越激化。“收养的”与“亲生的”,对于这个无法更改的既定现实,女儿们却为之伤神,为之焦虑,长期对自己的家庭身份的焦虑和族裔身份的困扰使她们与母亲布朗蒂逐渐产生了情感认同的障碍。
布朗蒂有苏格兰、爱尔兰和德国血统,是一家投资公司的副总裁。王妈妈是个偏执于族裔文化保护和传承的人,十分看重家庭的族裔性,所以自始至终都在反对布朗蒂进入王家。尽管布朗蒂身上具有传统中国文化孝顺儿媳的优秀品质,也会说中文并一直在努力了解中国文化,生活上十分关心照顾王妈妈,可是在王妈妈心里只是把布朗蒂当成了“种族符号”,从来没有认同布朗蒂的儿媳身份。布朗蒂的白人身份成为了她正常融入王家家庭身份的一个障碍。王妈妈阻止不了卡内基娶布朗蒂为妻,又担心卡内基在白人文化的同化中越走越远,就留下遗嘱她死后让中国的亲戚兰兰过来照顾三个孙辈,这样最起码可以制衡家庭中的白人文化,同时也能教会孙辈说中文。[4]兰兰的到来,确实给这个家庭带来了极大的冲击。兰兰温柔节俭谦恭,兰兰逐渐被卡内基和女儿们喜爱。布朗蒂跟孩子们和卡内基的隔阂越来越深,家庭好像被分裂成两个种族派别,布朗蒂跟儿子一派,兰兰和家庭亚裔成员一派。在卡内基的生日宴会上,“所有那些长着黑头发的脑袋,只有两个长着金发。……随便什么过路人都会以为卡内基和兰是这家的男主人和女主人,而我和儿子是客人。”[5]布朗蒂感到自己被割裂出来,迷失了女主人的身份和地位,她开始疑惑“这还是我的家吗?”“这是谁的家?”布朗蒂怀疑兰兰是王妈妈安插在中国的卡内基的爱妾,兰来这里是要取代她的位置。
任碧莲设置这样一种微妙的“主”与“仆”,“妻”与“妾”的隐喻关系,渲染了布朗蒂对自己身份的焦虑和迷茫,折射了白人群体担心多元文化下各族裔文化共存会挑战以盎格鲁-撒克逊为根基的美国价值体系, 并逐步改变美国人的生活方式。[6]
二、王家人的身份找寻
王妈妈在世时,卡内基拒绝自己的华裔特性,不学汉语,不听从母亲的文化教导不接受母亲的价值观念。王妈妈去世后,他对母亲的思念和家园失根的感觉越来越强烈。他开始学习汉语,在网上了解中国传统文化,悉心保存母亲的遗物,执行母亲的遗嘱。他变得喜欢中国的历史和传统,开始认真审视自己的华裔特性,他深深感觉到了自己血液里的民族文化基因的觉醒,对中国诗歌产生了狂热的兴趣,开始努力寻找族裔传统和文化集体记忆。
从拒绝中国文化到拒斥做纯粹的美国人,卡内基的文化认同几乎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他情不自禁地接近兰兰,甚至认为没有娶一个华裔妻子可能错失了很多。他试图在兰兰身上寻找丢失的族裔身份和文化身份,他痴迷中国文化,从兰兰那里了解中国烹饪精华和传统文化思维,他珍重母亲留下来的中式家具和遗物,他对自己的族裔血统和文化身份属性进行着不断的思考审视。为找寻自己失落的文化之根,他联系香港那边的亲戚,寻找母亲留下的家谱,把丢失的历史和过去重拾起来。小说结尾颇具戏剧性,因为家谱显示兰兰是王妈妈的亲生女儿,而他只是王妈妈在美国的养子,这个消息犹如晴天霹雳,让他心脏病复发,被送去了医院。他的族裔血统也许不是华裔,也许是菲裔、越裔、日裔或者其它亚裔。这个戏剧性事实颠覆了卡内基长期以来的华裔血统和种族身份认知,他领悟到文化认同和身份建立是自由选择的结果,与血统种族无必要关联。卡内基作为出生在美国的第二代移民,徘徊在中西两种文化的夹缝间,他的文化认同和身份探索一路伴随着叛逆、迷茫、找寻和不断的重新认知和选择。
两个养女出身背景不详,这种先天的身份属性缺失和孤儿的心理自卑,使她们对自己在家庭中的地位格外在意。美国社会对待卡内基一家这种跨种族无血统关联的混合家庭依旧持有异样的眼光和狭隘怀疑的态度。两个女儿承受了来自外界和内心巨大的双重压力,她们对身份归属的焦虑可以从跟母亲布朗蒂的交流中窥见一斑。利齐把自己比作布朗蒂的小肚子,表明在利齐的潜意识里十分想成为布朗蒂的亲生女儿的愿望,她对布朗蒂说你不会把我当做小肚子给甩掉吧,反映出利齐担心母亲因为有了弟弟而不爱自己的担忧。温迪把自己比作布朗蒂的“肺或是其它重要器官”反映出她特别希望成为布朗蒂生命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兰兰到来后,两个女儿选择亲近跟自己外貌特征一样的兰兰,而逐渐疏远了母亲布朗蒂。难道族裔和血缘真能成为阻止家庭和谐的藩篱?随着王家矛盾的不断升级和故事的进展,母亲布朗蒂带着利齐离开了王家,兰兰成为了王家新的女主人。这时两个女儿才发觉自己深爱着母亲布朗蒂,兰兰尽管可以做可口的菜肴满足她们的胃口、给她们讲中国的故事满足她们对异域文化的想象,但是兰兰永远取代不了布朗蒂的位置,布朗蒂对她们的了解远胜过兰兰对她们的了解。两个女儿最终理解了家人间的爱和包容是可以超越种族和血缘的藩篱的。这也是任碧莲在作品中通过家庭这个窗口表达:在多元文化背景下,各族裔只有相互包容和理解才能实现族裔间的和谐共融的思想。小说中塑造的两个美国化的亚裔养女表达了作者反本质主义的文化身份观,文化身份并非固有的本质,[7]身份不是僵化固定的而是发展变化的,具有流变性。一个人的族裔血统决定不了这个人的文化身份。各少数族裔是美国的组成部分,为美国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少数族裔有权保留自己的族裔文化特征,族裔性不能成为影响他们美国人的国族属性的事实。两个女儿虽然是亚裔,她们在美国家庭长大,就是美国人,是无需置疑的文化身份。
布朗蒂虽然是白人血统,却会说汉语十分认同中国文化。她曾建议卡内基一道去中国旅游,更好地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她跟着兰兰学做中国菜、学习如何不浪费、了解中国思维。当女儿利齐把从兰兰那里听到的“怪异”的中国故事讲给她听时,她总是把这些“怪异”的故事说成是“迷人的”故事。布朗蒂曾经为自己敢于挑战世俗眼光,跨种族、跨族裔领养孩子组建美国新型混合家庭感到自豪。当兰兰越来越被卡内基和两个女儿所吸引,家庭似乎被分裂为两个外貌特征不同的种族派别时,布郎蒂也不禁为儿子贝利遗传了自己的体貌特征感到欣慰。她跟兰兰之间的纠葛和冲突越来越激化,为了捍卫自己的婚姻和家庭,她舍弃了高收入、高地位的公司副总裁的工作而辞职在家,她想办法给兰兰介绍对象,急于把兰兰赶离王家。布朗蒂跟兰兰之间的这种魅惑的“主”与“仆”,“妻”与“妾”的关系,实则反映的是对“白人土著主义”的挑战和颠覆。少数族裔不再是被歧视被边缘化的他者,多元文化时代各族裔应持有平等的话语权和社会权利。在小说的结尾,布朗蒂带着贝利离家出走。卡内基心脏病突发做手术时,布朗蒂、兰兰、利齐、温迪和贝利都守在了候诊室。对卡内基的关爱让一家人重新凝聚在一起。每个人都认识到家庭不是由血统和种族身份决定的,而是由成员的主动情感选择决定的。兰兰也在逐步融入美国社会,接受美国文化影响,她也发现虽然自己跟王家人的种族特征一样,她只是了解卡内基的胃口,但是她永远无法了解卡内基的内心,她跟卡内基之间还没真正开始就危机显现。两个女儿通过自我的情感选择,认为布朗蒂才是她们的妈妈,血统世系不会撼摇她们的母女关系。
三、多元文化下族裔身份的流变
文化身份的找寻和建立一直是华裔文学作品中的一个重要议题,任碧莲的作品突破了以往华裔作品中聚焦中西文化的二元对立和美国白人主流文化对华裔的身份异化,而是强调在多元文化的背景下,各少数族裔文化与白人主流文化差异共存,少数族裔不需要抛弃自己的族裔传统去迎合主流文化,族裔身份不代表一个人的文化认同和文化身份,每一个美国人都有自由选择文化身份的权力。
小说中的王妈妈是第一代华裔,具有强烈的族裔文化身份的意识,终生都在竭力维护家庭的族裔文化传承,而这在多元文化共存的美国是不现实的,从卡内基的成长之路就可以看出,卡内基是一个十足的“黄香蕉”人,他在美国的教育体制下长大,认同美国的文化和价值,他不会讲汉语,不了解中华文化和历史。王妈妈去世后,他开始把对母亲的深深思念转化为对中华“根”文化的追寻和热爱,他重新审视了自己的华裔身份、开始认同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不断更新着自己对中西两种文化的认知。尽管家谱显示了卡内基的养子身份,他也许是非华裔,但是多元文化下血统不再能决定一个人的文化身份选择,文化身份不是生来固有不变的,而是主观选择的变动不居的。
既然文化身份不是恒定不变的,就没有必要再追寻“我是什么人”[2],王家的两个养女也就没有必要受“我是哪里来的”这类问题的困扰。在任碧莲看来,“我来自哪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想成为什么样的人”。“美国的由来就是有一群英国人决定不再做英国人,身份的变化一开始就是美国文化的特点。”[8]“每个所谓‘族裔集团’的族裔都是每个人自由选择的。”[1]两个养女最终认识到族裔身份和血缘不能影响她们的美国人身份,族裔和文化身份的混杂性是多元文化下个人身份建构的普遍现实,从而走出了文化身份与族裔身份分裂迷失的认识困境。
布朗蒂是混血白人血统,王家家庭中的每个成员代表着不同的族裔身份。这一家庭组合本身就是多元文化在家庭内部的反射。布朗蒂曾深为她自己选择组建的这种新型家庭引以为傲,她抛弃了传统狭隘的种族偏见,主动选择接纳收养非血缘关系的两个亚裔养女。然而兰兰的出现让布朗蒂在王家感到被孤立,布朗蒂甚至开始认为她跟王家人不同的族裔身份也许是使她婚姻失败的主要原因。虽然她刻意追求亚裔美国生活方式,认同中国文化,对待两个养女视如己出,但是肤色及外表在当今美国社会仍然制约着话语关系和人际关系,当家庭出现矛盾纠葛时人们很难跨越种族鸿沟。[9]当布朗蒂离婚后,卡内基才认识到他内心爱的人是布朗蒂,兰兰只不过为他寻求族裔文化带来了中国气息。小说结尾,布朗蒂、兰兰和孩子们一起为卡内基脱离生命危险而相拥欢呼,这表明了爱和包容是能把不同族裔的群体凝聚在一起的,爱才是家庭的凝聚力。
霍米·巴巴在《献身理论》一文中指出,坚持文化的固有原创性或纯洁性是站不住脚的。[10]《爱妾》中人物族裔身份的不确定性和混杂性无疑是对传统观念中民族和文化的地道性、纯洁性的质疑,[2]血统和种族对于身份属性不再具有决定性作用。《爱妾》中王家人在经历了种种家庭摩擦和对自身身份属性的迷茫之后,每个人开始坦然接受文化身份的偶然性和流变性,也意识到多元文化下真正意义的家庭应该是摒弃种族和肤色差异,以爱和包容来定义家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