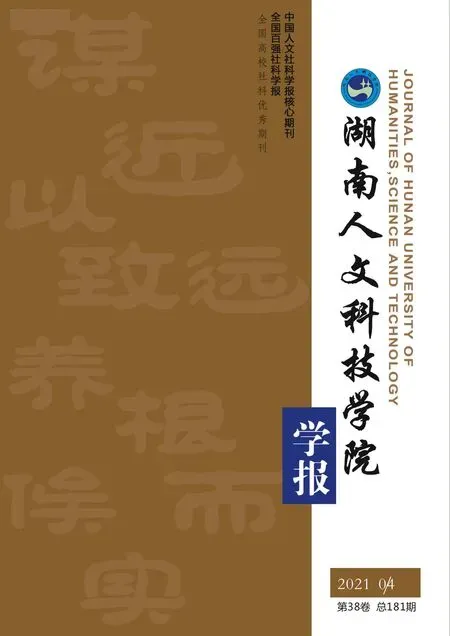生长在原罪土壤上的善之花
——论《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仪式叙事
2021-12-06马硕
马 硕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 文化产业所,广东 广州 510635)
与陀思妥耶夫斯基晚年交往甚密的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在其葬礼上说,这位伟大作家对俄罗斯的意义不仅在于文学,更在于精神。诚然,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人与宗教、善与恶、解脱与困境等方面的思考,不但为存在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基础,更为人如何直面灵魂提供了积极的引导。从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许多学者都认为郁郁寡欢的童年、坎坷的青少年、成年后严重的疾病与一生中不断经历亲友死亡,让这位天性热爱思考的伟大作家更深刻地看到了生命的本质。然而,这些经历可能只决定了他思考的内容而非思考本身,真正触动多米诺骨牌的实际是其生命中的各种仪式,正如波诺马廖娃所说,“断头台、苦役、奥普吉那小修道院,这些他曾经历过并最终带他进入悔改的地方,都成为他生命中重要的里程碑,将他最终带到高度凝聚的福音精神”[1]。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他的作品与友人的信件中多次提到人对精神的依赖,他始终认为人不可能只靠面包活着,人是意义的动物,而意义的过程往往就是仪式的过程,所以,陀思妥耶夫斯基会不厌其烦地回忆与兄长米哈伊在德拉邱索夫学校经历的野蛮的入学仪式,与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成员经历的判决、行刑仪式,与同服苦役的狱友在西伯利亚经历的圣诞节庆仪式等。基于这一认知,他以极为隐蔽的方式表达了他从这些仪式中受到的心灵触动。苏珊·李·安德森认为,《卡拉马佐夫兄弟》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哲学思想表达最为充分的一部作品,尽管与《罪与罚》的取材相似,但作家在自身经历的社会仪式影响下,让作品中人的困境、感性与理性的滥用有了更强有力的依托[2]。陀思妥耶夫斯基敏锐地感知到人性的复杂与仪式密切相关,尽管仪式参与者在一些社会仪式中并没有选择的权力,但正是这些仪式在很大程度上承载并决定了人的思考。人性中饱含着对欲望的需求,以及对信仰的疑惑,对自我的怀疑和鄙弃,在这样的意识下,作家搭建了一条从失乐园通往伊甸园的天梯,凭借世俗仪式及宗教仪式的见证,使人性的善恶在这部作品中呈现出深刻的意义。
一、仪式素中的深层叙事线索
《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仪式叙事分为三个层级,第一个层级即仪式素,指小说中与仪式行为、过程相关的描写,其中明显的仪式素如佐西马长老的葬礼、对德米特里的审判,较为隐蔽的仪式素有阿辽沙的忏悔反省、伊凡的辩论,最容易为读者忽视的仪式素有人物见面的问候、宴会上的致礼等。仪式可看作是《卡拉马佐夫兄弟》的叙事支柱,费多尔与德米特里终其一生都在社交仪式中寻找自我价值,凭借他人的肯定获取微不足道的尊严,如果说他们是世俗仪式的命运承受者,伊凡与阿辽沙便是通过截然不同的信仰指向了神圣仪式的两端。姜训禄在《仪式在俄国象征主义戏剧场面中的功能和形式》一文中提到,“仪式的核心功能体现在其中包含的理想结构以及现实世界与理想世界的统一”[3],即是说,仪式起到了这样一种功用,它通过空间、环境、符号将代表实用行为的社会现实与代表仪式行为的精神思考相连接,成为衡量“真实”的一种方式。
陀思妥耶夫斯基显然深谙仪式的重要,他在《死屋笔记》中谈到,仪式不仅能使参与者感受到敬畏的情绪,更能在仪式过程中不自觉地感受到与他人的联系。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这种从仪式中渗透出的敬畏与联系观念有了更强烈的表现,仪式素成为剖析人物思想的重要渠道,基于这样的思考背景,陀思妥耶夫斯基分别从葬礼仪式和司法仪式出发,阐释在宗教的环境中,人如何对理性和感情做出审判。这样一来,仪式素在文本中便成为了一种媒介,它一端连接着人,另一端则连接着上帝。从基督教的教义来看,人有原罪,所以需要得到上帝的救赎,然而所谓的平等只是一种相对的概念,职业、生活方式都会为原罪添加等级,最终被打上难以磨灭的印记。巴赫金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艺术观察的基本范畴不是行程过程,而是共存和相互作用”[4],这样一来,就引发了一种潜在的审判仪式,人的存在价值不在于个人主体对于欢乐的感受,而在于对周围人、周围环境的改变和影响。
如果说在修道院由佐西马长老主持的公开裁决是“上帝的审判” 的象征,那么,德米特里因被怀疑弑父在法庭上的判决便可看作是“人间的审判”。然而,陀思妥耶夫斯基似乎并不认为这两次判决仪式能够代表真正的道德宣判,对善与恶的思考始终困扰着这位伟大的作家,恶究竟是原生行为还是后天行为?善是否因信仰上帝而约束自我,恶是否因不信上帝而放纵自我?因此,他又凭借两次葬礼来对应这两次判决仪式,用佐西马长老的葬礼否定神圣,又以伊留沙的葬礼肯定道德。纪德也认为,“很少见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在陈述自己的思想之后不马上加以否定的。在他看来,思想一旦得以陈述就好像立即散发死物的臭味,好似佐西马尸体散发的恶臭,而人们恰恰期待着出现奇迹,其时这种恶臭使得他的弟子阿辽沙·卡拉马佐夫夜间守灵变得不堪忍受”[5]75。从这个意义上来看,葬礼仪式是文本中高于司法与教会审判的第二层审判,它的存在价值就在于仪式参与者情感真实的自发态度,特别是在道德的错误与法律的罪恶存在界限时,仪式能够强化判决的效力。
老卡拉马佐夫是所有审判的核心,他厚颜无耻、薄情寡义,对最亲近的妻子和儿子也无法履行自己的责任和义务,只有纵欲、享乐才需要认真对待,他甚至不如巴尔扎克笔下的老葛朗台。然而,费多尔的错误只能引发周围人的唾弃,却不引发法律的判罚,因此,费多尔几乎成为了一个恶瘤,有道德错误却无犯罪行为,使他能够依靠自己丰厚的财产分外逍遥。在这个前提下,费多尔的生存令人嫉恨,于是,在他遭到暗害之前,不少人都暗自希望他能尽快死去,哪怕是“如同天使一般的阿辽沙”也承认有过如此的念头。正如有人问孟子,杀人犯是否该杀,孟子回答该杀,然而“为士师则可以杀之”(《孟子·公孙丑下》),也就是说费多尔应该以什么样的方式死去,如果被杀,又该被谁所杀,这才是问题的关键,并困扰着周围人的道德观念。一个人对于他人的审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自我价值的建构,费多尔的生存和死亡如同一面照妖镜,反射出一群内心深处生长着丑陋的恶之花的人们,所以说,仪式在这里起到了法律所不能替代的作用。
在厌恶费多尔的人群中,德米特里始终处于舆论的中心,从伦理道德的角度来看,当德米特里叫嚣报复、甚至真的殴打了父亲时,德米特里便从受人同情的位置跌到了罪恶的深渊,尽管费多尔绝对撑不起一个父亲的称号,法律在这时却将注意力放在了费多尔大逆不道的行为上。如此看来,即使是在基督教所宣扬的“人是上帝的子民,因而人人平等,大家皆是兄弟姐妹”的语境下,也有着事实的不平等。为了化解冲突,佐西马长老主持了严肃的调和仪式,它通过教会与平民的争论从正反两面为思考信仰提供了真实性。但这场必然失败的调和仪式扩大了争论中的冲突,在对一种信念的坚守上,卡拉马佐夫家的成员们几乎各自为营。从表面上看,他们所坚守的信念代表的是一种人生态度,但深处则是一种关于人性本质、生存价值观念的展现,因此,这场仪式便有着提供线索、摆明证据的意义。在强大的心理压力下,德米特里率先展开了对父亲的判决仪式,他认为父亲不仅严重失职,甚至采用不光彩的手段对付自己时,伦理道德已经自上而下的消失了。不可否认,如果费多尔并非德米特里的父亲,德米特里的行为便有着正义的基础,只会被大众称赞叫好。
审判仪式更为深刻的含义还在于,基于对自己和他人的憎恨,老卡拉马佐夫从内心中不能接受仪式的秩序,更以荒谬的举止将自我放置在不可救赎的位置上,这样一来,他受到周围人厌弃的情况便更为突出,如果他的死亡不是被儿子所弑,便可以说这是来自上帝惩罚,罪有应得。吊诡之处也正在于此,如果上帝不允许杀戮,那么,费多尔的死亡就不能代表上帝的惩罚,如此一来,上帝对正义和道德的审判将置身何处?所以最终的审判只能从神圣仪式滑落到世俗仪式,只是陪审团在思考德米特里的行为是否恰当的同时,他们首先将自己代入到了当时的情境之中,于是,尽管大众诟病费多尔对子女的冷酷无情,却并不妨碍他们强调父母对于子女的天然支配和统治权力,期待子女情感回报的同时,期待德米特里能够以德报怨地热爱自己的父亲,因为这种期待掩盖了人性中自私的一面,代表了一种神圣的道德观。
“上帝的审判”与长老的葬礼遥相呼应着“人间的审判”与伊留沙的葬礼,这四场仪式的存在犹如一张网的四角,彼此制约又彼此联系。受人尊敬的佐西马长老在生前占据着神圣的职位,而葬礼上尸体发臭的不体面几乎是对神圣的全盘否定。所以,他所代表的神圣仪式便不应成立,德米特里的放纵也有了可以存在的理由,这是因为正确被否定后的结果是错误,那么其对立一面的错误也有可能被翻转——德米特里一切恶行的背后都有令人同情的根源,如果他的结局已经无法通过“上帝”进行裁决,来自人间的裁决也将未必公允,正如拉帕波特所说,“仪式的发生在这里是复杂量化信息的一种简单的质性表达”[6]。需要重视的是,无论德米特里的案件是赢是输,德米特里的实际生活都已经被毁,他的爱情和命运被加上了沉重的十字架,无论生死也许都需要用一生去负重前行,这种思考显然十分深刻,它绝非是为未来寄托希望,而是在有限度的宽容中赋予人以更为苛刻的荆棘。
二、神圣与秩序的仪式化书写
如果说《卡拉马佐夫兄弟》中仪式素展示了人物内心对善恶的理解与选择,那么文本中的仪式化书写则是对其叙事背景与线索的进一步挖掘。仪式化并非仪式,它是一种建立在仪式内涵与主题基础上的提炼,具有仪式行为或思维方式的特征,因而有着更广泛的适用性。小说中的仪式化书写不再困囿于对某一仪式细节呈现,而是立足于文本表现的某一个,或几个的主题,更集中地阐释其内容的内在含义。《小说仪式叙事研究》中提出,“如果将文本中的仪式描写看作小说叙事中的第一个层次,仪式化书写则可以看作第二个层次,它是对仪式描写的深化”[7]。立足于这部作品中的审判仪式与佐西马长老、伊留沙的葬礼,其中的仪式化书写主题便可从神圣与污秽这两方面进行归纳。
文本中最基本的神圣主题来源于宗教文化,它从信仰的大背景上将凡俗的人间世分割为可以被上帝救赎及不可被救赎的两端,因为上帝与宗教在其创立之始便被赋予天然的神圣色彩,所以与上帝产生联系的人也相对应的被笼罩在神圣的光圈当中,如佐西马长老、佩西神父、费拉庞特神父、阿辽沙,以及参与宗教仪式时的信众。在这些人群当中,神圣还需要通过个人的行为进行区分,其中持戒是保持神圣的一个重要方面,正如民众在诋毁佐西马长老之时议论到:“他不严格持斋,吃甜东西,常拿樱桃糖酱就着茶吃,而且很爱吃,是太太们给他送来的。一个苦行修士应该喝茶么?”[8]与之相反的是费拉庞特神父,他行为举止怪异,但却因为严苛的受戒行为受到信众的崇拜。在佐西马长老的声望跌入谷底之时,看似与世无争的费拉庞特神父却以极其夸张的语言和行为自我表现,其目的显然是替代佐西马长老而成为神圣的替身。从本质上来看,人物在努力营造神圣性的同时,它的实质价值已经在这一过程中被瓦解,取而代之的是人以神圣之名要达到的某种现实目的。王贺白不无深意地指出,“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来, ‘上帝缺席’的世界比‘上帝介入’的世界, 一方面更真实, 如伊万控诉的荒谬世界;但另一方面却是上帝更大的爱与期待”[9]。或许正因为此,阿辽沙在经历了长老尸身腐臭后的骚乱,费拉庞特神父闹剧一般的行为以及和佩西神父的争执之后,才会令人不安的“吃着腊肠喝着酒”,甚至随着拉基金去让人不齿的女人格鲁申卡家做客。
长期在教会中生活的阿辽沙性格纯净而真诚,他不但在卡拉马佐夫家里有着良好的名声,甚至在城镇中也是如此,阿辽沙被大家认为是最不“卡拉马佐夫”的一位成员。长老对他的亲近与教导更让阿辽沙心中对神圣有着独到的理解,并努力在一切行为中践行这种仪式化的神圣。正是因为阿辽沙突然之间的反差过于巨大,以至于拉基金如同伊甸园的毒蛇一般引诱着无知的夏娃,文本中对宗教的神一面也从笃信转向了质疑,当代表着神圣的两位人物依次出现让众人无法理解的状况时,神圣的意义和价值瞬间烟消云散。在这一层面的仪式化书写中,宗教神圣为人们带去的只是一种习惯性的猜测、认知以及寄托,掌控宗教话语权的教会借助着各种各样的仪式,用以加强人们对超能力的信仰,进而对教会规定的善恶标准做出回应。李泽厚认为,“世间的习俗、经验、规则披戴上神秘光环,成了神圣教义。神圣性使它获有了普遍必然性的语言权力,具有非个体甚至非人群集体所能比拟可抵御的巨大力量,而成为服从、信仰、敬畏、崇拜的对象”[10]。这说明,从宗教教会建构的一套话语体系之所以能够成立,就在于一个人通常都需要找到自我存在的意义,并从中得到归属感。这样看来,代表着超能力的神圣与其说是一种由上而下的思想控制,不如说是由下而上的需求所致。文本通过营造教会的精神指引,以及对教会人员固执却无力的仪式化书写,表现出的是宗教伦理道德所遭遇的危机,神圣性不断衰落,对信仰的倚赖导致信众内心深处价值观的摇摆。可以这样认为,凭借这种仪式化书写,否定了当时普通民众的道德观,他们向往神圣却又轻易否定神圣,呈现出民众复杂而功利的心态。进一步看,文本对宗教神圣不断强化之后,发现它对人性救赎已经不再有效,便为转向另一种更为现实的神圣之路指明了方向。
神圣的第二个层级来源于不可违抗的法律强制力,它所代表的不仅是民众的情绪,更是国家的意志。在审判德米特里时,费丘科维奇的辩护可谓精彩异常,他打压了检察官的气焰,暴露了两位证人的道德问题,让审判庭的气氛从一开始的紧张到后来的轻松愉快,以至于法庭上许多人在辩护律师发言后不自主地站在了德米特里一边。就在大家都认为德米特里可以躲过一劫时,卡林捷娜的突然一击,让法律的天平终究无法客观公正。处罚的结果让在场的每一个人都惊讶不已,哪怕是认定德米特里有罪的,也不得不说这样的惩罚过于严苛。文本对人物情绪的不断渲染,让这种有罪与无罪的观点冲突愈演愈烈,等大众持有德米特里无罪的情感升华到最高点时,却在法律的有罪判决中瞬时倾塌,大众同情的溃败凸显出法律的权威,而在仪式中反复争议的过程又凸显出法律的严肃性,正是这样一种严肃的权威,让法律本身具有了神圣的力量,让处于其中的每一个人都产生了必须服从的心理感受。
这种神圣力较之宗教的神圣来说更为现实,也更为直接。从德米特里的角度来看,让他抛弃不堪过往的,并非是他良心的发现或是道德的提升,而是他被法庭审判折磨之后,终于意识到他已经不再受到尊重,自由和肆意的行为必须付出极大的代价。换言之,法律的制定与执行受到国家机器的支撑,判决仪式有着具体且实在的力量,这种力量以强制惩罚的方式,构建了它的神圣性,并让处于其中的人们真实地感受到,法律秩序所构建的神圣不可抗拒。更进一步说,甚至上帝的神圣性也需要通过人间的秩序得以实现,法律不仅是宗教的有力补充,在一定程度上更凌驾于宗教秩序之上。
对法律神圣性的宣扬表现出的是对宗教神圣性的否定,教会无法调节的矛盾最终需要暴力的参与,然而,与其说这是作品对教会与教义的嘲讽,不如说是作家在面对人性丑恶的欲望时发出的质疑。法律判决之所以存在神圣性,可看作是对权力的彰显,正如福柯所指出的,“人的身体是一个工具或媒介。如果人们干预它,监禁它或强使它劳动(德米特里被判罚服苦役二十年),那是为了剥夺这个人的自由,因为这种自由被视为他的权利和财产。根据这种刑罚,人的身体是被控制在一个强制、剥夺、义务和限制的体系中”[11]。但是,这同时也凸显出另一个问题:上帝如果在精神层面上无法为如德米特里般的迷途羔羊作出指引,那么他神圣的价值和意义应该如何得到体现?
显然,宗教与法律之间存在着神圣的另一个空间,既神圣性的第三个层级,它产生于个人对其意识的维护过程当中,它在一定程度上是接通前两种神圣性的渠道,达到宗教与法律之间的互通。何怀宏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个重要思想在于“人可能永远达不到基督,然而,当人不能够向他人完全奉献自己的爱时,他便感到痛苦,而正是这种罪孽,这种痛苦也许永远无法摆脱,但人能感受到这种痛苦,能意识到自己的罪孽,这又意味着一种希望”[12]。进一步说,个人意识所表现出的神圣性也是对前面问题的回答,当上帝的神圣力量无法使人遵守相关的秩序之时,法律便通过强制的管制与惩罚达到规训的目的,而试图超越凡俗规则羁绊的人,又终究需要回到信仰的神圣殿堂之中。从这个角度看,个人意识并非信仰,但思想的执着会将这种意识不断拔高,以至于个人行为会完全被信仰支配,最终形成一种类似于宗教信仰的个人信仰。事实上,这种个人意识的力量是如此强大,使其在维护与践行个人意识的过程中,会自发显现出一定程度的神圣性。
如果说阿辽沙代表了第一种宗教信仰的神圣性,德米特里彰显了第二种法律强制的神圣性,那么伊凡便是第三种个人意识神圣性的最好体现。他的生长背景决定了他始终处于社会层级的中间,若想要达到某种目的,个人的努力比任何祈祷都要管用,而毫无背景的现实,又让伊凡深刻地明白自己的不利处境。显然,宗教关怀并没有让他感受到实质的温暖,对向往着权力、地位、爱情与世俗尊重的伊凡来说,如何能够让自己从众人中脱颖而出,才是精力需要投放之处。从卡拉马佐夫的三兄弟来看,伊凡才是唯一真正垂涎于父亲财产、并试图通过努力以最大限度得到这些财富的人。基于此,他将父亲与兄弟都看成不同层次、不同阶段的对手,在整个文本中,看似彬彬有礼的伊凡心机最重,他几乎是以步步为营的策略先接近费多尔,再坐观德米特里渐入疯狂,更挑唆麦尔佳科夫从思想到行为逐步走向毁灭。然而,如果伊凡是个天生的恶人,那么文本中关于人性的一切复杂性都会被消解,整个叙事也会沦为善恶的简单对立,关于第三种的神圣性也无从谈起。正是因为伊凡对上帝不以为然,对法律却又心怀敬畏,因此他才需要另外一种“一切无可无不可”的信仰,对自己的欲望以及欲望背后的行为做出有力的支撑。对于这一点,伊哈布·哈桑也曾提出:“没有信仰,我们就找不到意义,也不能把零碎的片断归拢在一起。”[13]由此可见,伊凡将利己的犬儒主义推向了一个精神层面,并从中归纳总结出一套规避宗教信仰与法律规范的理论体系,在他接二连三地与修道院教士辩论,为阿辽沙演说,与麦尔佳科夫争论上可以看出,伊凡在这一过程中逐渐让自己的个人信仰走向了成熟,他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将其观点奉为圭臬,以绝对捍卫和坚决践行的姿态彰显这种理念的神圣性。
在麦尔佳科夫承认自己是杀人凶手之后,伊凡与魔鬼有一段极为理智的交谈,尽管他并不相信上帝,但是在梦魇中看到魔鬼,显然是暗示着上帝同样存在的事实,如果上帝是存在的,也就说明他一贯信奉的利己主义不但虚幻,而且需要遭到谴责。所以,在伊凡看到魔鬼之时,正是他从自我信仰的神坛上跌落,并混迹于魔鬼之列之时。既然上帝在隐约露面,伊凡也不得不直面麦尔佳科夫,宣称自己才是真正凶手的原因与内涵,杀人无疑有罪,但伊凡长久以来的奋斗绝非要将自己置于一个罪犯的位置,在他看来,只有直接的犯罪才属于罪恶,但父亲被杀的事实,不得不使其反思这桩恶行背后的原因。叫嚣着要杀人的人并未施恶行,而真正杀人的凶手却自称是一把刀,那只握在刀柄上的手正是伊凡本人,原因就在于他无所谓善恶,无可无不可的观点,在另一面来看便对罪恶的怂恿,对善行的背叛。
这部作品的背后是关于人的思考,人在精神层面与物质层面的需求在很多情形下是相互排斥的,但社会基本关系中的道德体系却有着基本的模式和标准。显然,这样一部有着庞杂含义的小说,其仪式化书写也是纵横交错、层层递进,但其中对于“神圣”的关注,显然是这部作品中极为关键的主题,在对这个主题的观照过程中,作品所要呈现的仪式感也随之呼啸而出。
三、觉醒于欲望之后的真、善、美
如果说仪式素与仪式化书写仍然没有摆脱文本的藩篱,那么仪式叙事中的最高层级——仪式感,则可以看做是以文本为桥梁,建立起一种从作家到读者的共感。仪式感的概念通常需要分成两个部分进行理解,第一个部分是作家本人与作品人物在参与文本叙事过程中形成的情绪感受;第二个部分是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对叙事理解的不断深化,进而升华出的感官意识。在谈到作品的仪式感时,通常是指由作家的思考为起点,经过叙事发酵,最后再传递给读者的一种严肃、庄重、激昂、崇高的情感。仪式感是一部作品的关键,缺乏仪式感的作品如同缺失了灵魂,使读者不能得到真正的慰藉。
应该说好的作品都具有仪式感,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这个层面上来说,几乎有着与生俱来的仪式感,他在行刑仪式后《给哥哥的信》中谈到:“头被砍掉,我的心还在跳动,我的精、气、神依然存在,我依然有爱,有痛苦,有同情,有记忆。归根到底,这一切仍然是生活,太阳会照到每一个人身上!”[14]7陀思妥耶夫斯基这种强烈的情感表达,为其笔下的人物与叙事也同样注入了深刻隽永的仪式感。从《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可以看出,阿辽沙原谅一切,永远抱有希望的言行营造出的是真挚的仪式感;格鲁申卡和德米特里在判决之后的行为,表现出的是怜悯交融着救赎的仪式感;德米特里在最终审判后的服从表现出的是庄严的仪式感。不同的仪式感让读者感受到人性善的多元,也让读者体悟到欲望在人性走向毁灭中所产生的力量。
代表着真善美的阿辽沙无疑是最具仪式感的一个人物,他绝非不谙世事,事实上他深知身边人如父亲、兄长、格鲁申卡和拉基金的丑恶,甚至还能看清自己心底偶尔涌出的邪念,对于这一切,阿辽沙从不避讳,也正是他的清醒和诚实,使他成为了一个与众不同带有神圣色彩的人。阿辽沙深受佐西马长老的影响,认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应该是和谐而友善的,然而污浊的现实显然与其理想相互抵牾,当劝善不能达到目的之时,阿辽沙便投身于世俗世界当中,期望参与并了解社会后,最终完成对善行的鼓励,对恶行的劝诫。陀思妥耶夫斯基坦言,阿辽沙是其深爱的主人公,因此,作家在赋予他苦难与挫折的同时,也赐予了他信念和力量。值得注意的是,阿辽沙经历的两次关于信仰的心理波动,皆因仪式而起,神圣的长老没有神圣的瑞相,这无疑是信仰的破产,但阿辽沙在依留沙葬礼上的诚挚发言,才是他真正坚定和明白自己信仰的时刻。卢梭强调,“在到达思想的对象之前,必须先经过感觉的对象”[15],阿辽沙的成熟,伴随着失望、痛苦、迷茫还有彷徨,其内心充满了苦难的感受,才让其在重拾信念时得到了他人加倍的尊敬。阿辽沙身上的仪式感在文本中几乎一以贯之,这种对人性善意的坚持,正是这部作品为读者拨开人性乌云、让阳光投射之处,可以这样认为,阿辽沙内心对人的真诚与热爱,正是作家内心的情感投射。
仪式感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唯有它才能打动读者的心灵,使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得到净化、提升甚至感同身受的情感共鸣。仪式感并不在于对高尚道德由始至终的赞颂,也不在于作家对叙事一板一眼、严肃认真的描绘,如果阿辽沙遇见挫折,或者遭遇自己所不能理解的事情,仍然保持他的纯净和高尚时,那么这个人物无疑是失败的,更遑论仪式感,正是因为阿辽沙与普通人一样,有好恶,有厌倦,有怀疑,有冲动,甚至在与丽莎聊天时还会撒些无伤大雅的小谎,才让这个人物真实可信。阿辽沙与其他人唯一不同的是他更有耐心,更会反思自我,这种对待言行的严肃态度,不畏惧弱点和缺陷的执着性格,是阿辽沙之所以能够得到父兄信任,身边人尊敬,让读者心怀赞叹的原因。仪式感的价值在于人物对苦难的态度,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作家日记》中写到:“有一种思想威力无穷,可以战胜不幸、饥荒、苦难、瘟疫、麻风病以及所有诸如此类地狱一样的痛苦;人类如果没有这样的思想,就无法忍受这些地狱一样的痛苦,这种思想就是约束力。”[14]90或者可以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说的“约束力”,正是他在小说中所表现出来的仪式感。
相较于阿辽沙,德米特里呈现出一种悲剧色彩,在判决仪式的面前,他的身心都受到了摧残和束缚,尽管他的性格中存在令人同情又无奈的弱点,却无法成为他得以赦免的缘由。德米特里幼年失去母亲后又被父亲抛弃,应得的遗产更遭到父亲的欺诈,天生孔武有力的他几乎没有得到正常的教育,导致德米特里崇尚武力而非上帝。德米特里的罪恶源自他的爱情,因为深爱格鲁申卡而被金钱拉入了深渊,格鲁申卡与他有着极其相似的性格,内心善良却怀疑一切、否定一切。叶捷琳娜的教养对于德米特里来说,是一种令他窒息的束缚,甚至由此隐约觉察到,叶捷琳娜看似正直的性格背后隐藏着极深的心机。在这种环境下,尽管德米特里让身边的人感到憎恶和厌倦,却在很大程度上打动了读者。从人物的际遇中看到的一种悲剧人生,使读者由怜悯生发出善意,这种从同情到理解的善意事实上净化了读者本身。
同样,游戏人生的格鲁申卡也代表着另一类需要拯救的灵魂,她深知自己的魅力,色相几乎是她唯一能够出卖的东西,以至于格鲁申卡过分地运用了这种权力,周旋在卡拉马佐夫父子之间。应该说,格鲁申卡了解女性在男权社会中的艰难处境,她的圆滑难以引起他人的理解和同情,特别是她在叶捷琳娜家中的表现,几乎与无赖无异,社会对女子温柔善良的要求以及应该具有的品行等方面,在她身上几乎没有任何踪影,因而真正被其吸引的两位男性也只有令人厌烦的费多尔与德米特里。然而,正由于此,她的存在才有着比德米特里更为深刻的悲剧含义,如果说德米特里的悲剧性是可以感知的,格鲁申卡的悲剧性就是容易被忽略的,她几乎成为了罪恶的代名词,不仅成为卡拉马佐夫一案精神上的 “替罪羊”,更成为对魔鬼“献祭”的一种象征。那么,当格鲁申卡因德米特里被抓捕而看到了自己的荒诞,她决定与其相伴,共同接受被流放的判决便可以看做是魔鬼得到的救赎,暗示着执着于自我的生活是罪恶的,只有为成全他人的利益而做出的选择,才是真正的幸福所在,正如阿甘本对身体的精辟论述:“身体是一个双面性的存在,既是向至高权力屈服的载体,又是诸种个人自由的载体。”[16]接受了判决后的格鲁申卡,明白了最重要的自由来自于灵魂而非身体,使这个人物从此具有了一种在悲剧中重生的色彩,同时也说明在一些特殊仪式的干涉下,人性之善的确能被激发,尽管姗姗来迟,却并不缺席。
四、结语
《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仪式叙事从三个层面反映出不同的表现维度,仪式过程与仪式行为的展演,反映出俄罗斯乡土社会中的神权与人权,作家对“神圣”的仪式化书写,则是对信仰的反思和扣问,并在这种仪式化书写中形成整部作品关于怜悯与救赎的仪式感。鲁迅在《穷人》小引中说,凡是人的灵魂的伟大的审问者,同时也一定是伟大的犯人。陀思妥耶夫斯基对道德与罪恶的思考早已超出了神圣和世俗的桎梏,善与恶的边界并非“无可无不可”,当宽容缺失了原则,复仇就未必需要指责,自由也未必是美德。显然,陀思妥耶夫斯基正是看到“犬儒主义”的伊凡的最后结局,才以伊留沙的葬礼为最终的审判画上句号,这个看似与整个叙事并无太大关联的仪式,指向的是约定俗成的大众道德体系——人作为社会中的一份子,自私是可耻的,没有信仰是可怕的,坚定和友爱才是值得赞扬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从仪式的角度勘探作品的叙事特点,在分析其由表及里的艺术魅力的过程中,其真实和深刻性往往能够得到更为全面的展现,正如纪德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评价:“伟大的作家之所以伟大,是因为其著作不仅符合一国一时的需求,而且为时代各族种种不同的饥饿提供充足的食粮。”[5]1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