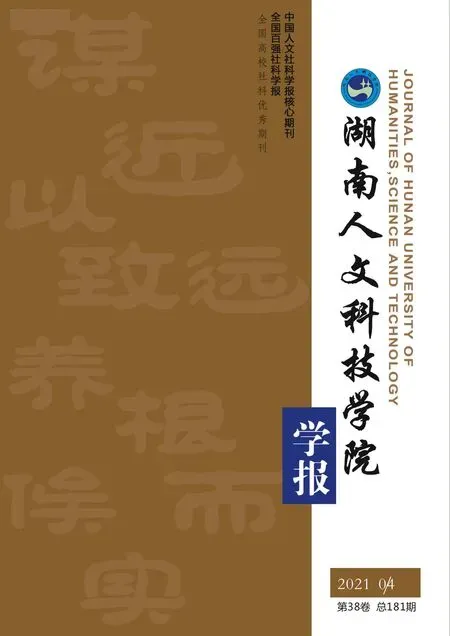仓促的表演与杂糅的主题
——评阿来的长篇小说新作《云中记》
2021-12-06傅钱余
傅钱余
(重庆文理学院 文化与传媒学院,重庆 永川 402160)
文学如何书写灾难?通常来说,或从宏阔的社会历史视角去聚焦群体的生存遭遇,或从微观的个体精神去挖掘人们的灾难经验。不论从哪个角度,作家的情感立场相对其他一些题材来说都会受到一些限制。人类在灾难中的痛苦、挣扎以及幸存者对待生活、生命的态度成为文学对灾难的常见叙述。著名作家阿来以汶川地震为题材的长篇小说《云中记》,选择了一个比较独特的视角——以一个祭师的安魂之路去呈现“对死亡、对自然与人更加本质性的关系”[1]。阿来本人应该有着强烈的悲悯,这样的情感动机和独特视角本有可能创作一部颇具艺术突破性的灾难书写文本。然而让人失望的是,《云中记》并没有很好地呈现出作家所谓的“本质性”思考。
一、《云中记》的人物——木偶阿巴和没有面孔的众人
祭师阿巴是《云中记》的聚焦者,小说交叉运用全知叙述和人物叙述来呈现阿巴的地震记忆和回村之路。虚构的云中村是靠近雪山的一个藏族村落,有着上千年的历史,有着绵延传承着的古歌、仪式和生活方式,甚至像桃花源一样是一个宁静美好的“仙境”。文学营造一个理想化的居所,这无可厚非。然而,当理想居所是刻板的文化花园时,只能说叙述者在偏狭的心态下失去了对社会文化复杂性的深度关注。《云中记》,要“献给地震中的死亡者”“献给地震中消失的城镇和村庄”,然而实际上却成为献给“游客”的一场表演。云中村,成为了一个旅游村、民俗村,叙述者想象着那些读者(游客)顺着陡峭的山路,或骑着云丹牵的马,或坐着中祥巴驾驶的热气球,或陪着阿巴缓缓爬行,来到一个精心打造的民俗文化村——作为景观地标的石碉、藏族文化样式的民居、淳朴友好的高山原住民和神秘莫测的传统祭祀仪俗。看!阿巴,一个祭师,一个表演者,一个导游,正摇铃击鼓、歌颂着阿吾塔毗、带领游客跳着山神节的圆圈舞。
说阿巴是一个木偶,意在说明祭师阿巴不过是作者生硬完成写作意图的一个工具,缺乏真实性和生动性。小说从阿巴爬山返乡开始叙述,止于阿巴与云中村坠落消失,中间穿插阿巴对云中村和自己的回忆。叙述者将阿巴设定为一个坚定地返回村庄祭祀鬼神的人,这种概念式的写作如果拿捏不当,往往会用力过度失去真实性。关键的问题是,叙述者避开了对阿巴回乡动机的真正回答。为什么阿巴在搬迁到移民村四年之后,突然这么决绝地要回去?阿巴的回答是:“还有死去的人,还有山神”“几年了,他们还是叫我们老乡”。阿巴甚至用“他们为什么不叫他们自己人老乡?”来证明云中村移民们受到了区别对待,无法融入当地社会群体。然而,第一句话并没有揭示出原因,阿巴可能是一直保持着对云中村的思念、对亡者的记忆,那么就必然有深刻的内心情感,但叙述者没有呈现;第二句话并没有事件来证实,只能是阿巴的一种感受。
总之,即使不能简单用“动机”这个词来限定阿巴的回村心理,但只有异常丰富、复杂、激越的情感洪流才能产生超越常规的行为,不痛不痒的一句“还有死人”显然不足以支撑阿巴的安魂意识。正因为阿巴在回村时内心世界的复杂性和体悟性不够,导致阿巴的整个召唤亡魂、祭祀山神过程沦为了一场仓促而冷漠的表演——对悲痛的表演、对文化的表演。小说一共387页,但坚决返乡的阿巴的安魂过程总共不到20页,绝大部分的内容却是阿巴在山上与云丹、地质勘察队、央金姑娘、中祥巴等人的会面和交谈。这些内容虽然也触及一些值得思考的现象,然而小说的核心主题被设定的是安魂,并不是批判。
阿巴上过中学,曾经是村里的发电员,有出村拜访邻近祭师、参加县里培训、移民搬迁等经历。丰富的经历和多重的身份本应该带给阿巴看待灾难、自然、人世更高的眼光,也应该带给他更复杂的内心世界。但是从阿巴的叙述中,读者只能听出一句话:“我要回去,鬼魂没有人管,我要和云中村一起消失。”作为小说故事之基础的回村原因,本可以成为一个非常有亮点的地方。因为这里既有阿巴返乡与外甥工作职责之间的冲突,还有阿巴与云中村幸存的人以及移民村乡亲的关系,更重要的是阿巴在此过程中丰富的内心对话。然而小说在此弱化了对阿巴精神世界的呈现,也很少提及阿巴与云中村幸存的人以及移民村乡亲的关系,花了较多笔墨来处理阿巴与外甥之间的冲突。即便是这样的处理,叙述者也显得仓促了一些。外甥仁钦爬上了云中村,见劝不了阿巴,含泪下了山,后来因为移民回流被降职。随后不久,他力挽狂澜轻而易举解决了游客危机,轻而易举又官复原职。显然,叙述者意识到了其中的矛盾,然而解决矛盾的方法却如此简单粗暴。
因此,祭师阿巴只是作者概念化写作的一只木偶,既没有真实感也没有生气。核心人物已如此,其余人物更显苍白。他们是一个又一个没有面孔没有五官的人,身上仅仅贴着某种单一的标签。仁钦,贴着公正勇敢、一心为民的基层干部标签:他心怀乡亲,不顾母亲的生死,积极投入到对幸存者的寻找中,甚至像传说中的大禹一样过家门而不入;他有着钢铁一样的意志,三天三夜高强度的体力耗费和精神压力没有一丝疲倦,佯睡待阿巴睡着后去废墟寻找母亲,没有找到母亲也没有留下眼泪;他敢于担当,劝不回舅舅受到上级处罚而毫无怨言;他决策英明、管理到位,果断地以发展乡村旅游带动乡亲们致富,又狠抓细节工作、服务工作;他还善于沟通、会人情世故,请一顿饭便解决了全国知晓的旅游危机……。这是一位近乎完美的基层干部,和阿巴一样,几乎没有七情六欲,没有太多的情感变化,没有太多的矛盾纠结,一身都闪着金光。对没找回母亲的悲痛,也只是在返回云中村的那晚放肆哭了一回,而那一夜他的主观目的都是劝阿巴下山。当然,他还煞有介事地养了一盆花,被看作是自己母亲魂魄所寄的鸢尾花。然而,这朵鸢尾花的作用,更倾向于是引出女朋友的登场。女朋友的父母一直不同意两人交往,然而仁钦一被罢免他们就从中发现了仁钦的“有情有义敢作敢当”,并同意将女儿嫁给仁钦。可见女朋友的出场其实际目的是试图证明仁钦的品质高尚。
即便如此,这个似乎完美的基层国家干部,却被众多细节所颠覆和解构。当中祥巴向仁钦申请热气球旅游项目时,他“露出了笑意”,还主动向县里请示。然而,该项目一被网友抵制,他立马变了脸色,义正言辞地骂道:“你从哪里来,还是滚回哪里去吧!”他的原因是“网上直播影响很坏,大多数人反对,政府也反对”。显然,这里的仁钦既没有担当也缺乏智慧,甚至缺乏基本的常识。热气球项目之所以不行,不是因为“大多数人”反对,而是性质问题,哪怕没有人反对也是对苦难的消费,也应该停止。仁钦在项目之初,没有和乡干部们商议,一个人拍了板,事情受到抵制之后又将责任全部推诿给中祥巴。申请项目时,叙述的是“仁钦”笑了、请示,而项目被抵制后用词是“政府”也反对,甚至毫不顾忌地用出了“滚”这样的字眼。这样的细节举不胜举,游客被宰后的旅游危机中,仁钦想到的是请客吃饭、开记者招待会、电视台拍摄道歉过程,而乡民宰客问题和乡政府的管理问题却忽略不提。如果消费苦难是可耻的,那么把道歉过程通过电视台直播至少是缺乏诚意的。为了体现仁钦的努力,当他向不满意乡厕收费的妇女鞠躬送礼时,叙述者还说了一句话:“旁边就有人嘀咕:地震时可没看她捐过款。”叙述者的意图或许是,许多根本没有捐款的人打着施恩人的幌子颐指气使。常理而论,地震灾难后非常多的捐助途径,旁边的人何以确定她没有捐助?就算她没有捐助,难道就不应该得到道歉吗?此一事彼一事,叙述者补充的这句话不但画蛇添足,而且充满着浓浓的泼妇气息。
总之,漏洞百出的细节描写并没有成功塑造一位正面的乡村干部形象,只是给一个人形木偶上贴上标签,这个标签还被自己的阵阵喷嚏吹到地上。仁钦作为小说用墨第二多的人物尚如此标签化,其余人物可想而知:心胸狭窄的小人洛伍、见利忘义的央金和中祥巴、满嘴科学腔的余博士。这些人物的作用都是反衬:洛伍反衬了仁钦的英明和大度,央金和中祥巴反衬阿巴对村庄的纯粹、余博士反衬阿巴的传统智慧。然而,这些人物完全失去了真实感,仅仅成为了一个个符号。
二、《云中记》的主题:不协调的拼盘
细读小说《云中记》,作品至少在三个主题上游移不定——主旋律、乡村现代化、文化表述。当然,这三者并非水火不容,处理得好可使作品成为蕴涵丰富的佳作。然而,小说却流于表面地描述,重点不突出,主题之间关系不紧密,形成一个不协调的意图拼盘。它像一匹脱缰失控的马儿,不沿着既定的路线奔跑,反而闯入了一个个陌生地点。每一处,这匹马都驻足片刻,远眺一下风景,然后绝尘而去。
小说在三十余页叙述阿巴爬山返村的经历之后,通过阿巴的视野开始回忆地震刚结束的场景。在这长达十几页的叙述中,一开始就是解放军来救灾了,然后是仁钦指挥救灾的情况。这部分内容以一种讴歌英雄的主旋律口吻叙述,解放军们不知疲倦,不肯吃灾民的东西,不肯喝灾民的茶,不多说一句话;仁钦则是临危不惧、果断英明,不但带领解放军寻找幸存的人,还指挥村民自救。于是,村民们激动、感恩,有碰到解放军就吻手喊“菩萨”的“吻手妈妈”,有大声说出“国家好”“党好”的村民们,有坚定说出“不是我,是国家,是政府”的基层干部仁钦,还有响彻在帐篷里的诵读声“我们都是汶川人!全中国人都是汶川人!今天,我们都是中国人!”
在大地震中,确实涌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他们值得浓墨重彩地讴歌。但是,讴歌如果缺乏实质性的内容,没有更为生动具体且具有感染力的描述,就会变成一种轻浮的腔调。文学不应该沦为喊口号,应塑造真实的形象以体现“向上向善”的力量,从而打动人的心灵。或许,小说意不在此,因此旋即又转入了阿巴的祭祀追忆。然而,小说从第259页开始直到尾页这长达128页的篇幅中,重点又变成了讴歌主旋律——讴歌敢做敢为、有情有义、干练果断的国家基层干部。不难看出,安魂和主旋律并没有很好地融合在一起,并没有用力在灾难之后的“重生”。如果能从对村庄的追忆和对逝者的安抚中走向对重生的主旋律歌颂,尚可说道。如果那样,追忆和安魂就是为了凸显云中村的重生,可小说的处理是云中村的消失,意图是阿巴坚定的文化守候和生命体悟。这造成了两个主题之间的割裂,失去了应有的整体性。
进而言之,灾区重建的情节为了突出仁钦这个人物形象,叙述仁钦如何在种种困难局面中力挽狂澜。小说呈现出了重建中的诸多问题——卫生问题、宰客问题、恶性竞争、消费苦难等,显然这已经超越了重建这一范畴,走向了农村现代化这一更大的议题。或许叙述者试图靠近新农村建设和乡村振兴这一更具时代性的重大主题,然而叙述过程中对这个主题再一次浮光掠影般走过,并未深入挖掘这些问题背后的阶层差异、区域不平衡、文化习惯、民众心理等深刻问题,仅仅满足于从表层肤浅地描绘问题。同时,小说对乡村的叙述流入了一种简单的二元对立:游客总是嫌弃这嫌弃那,并总是以施恩者自居,地震后举国人民真诚的支援却在小说中沦为了一些高高在上自以为是的游客;移民村的村民们几乎被刻画为冥顽不灵、自私可笑、见利忘义,不是恶性竞争就是欺诈游客;乡政府的干部也被简单地分为好坏两类,好干部仁钦和坏干部洛伍,前者好到近乎完美,后者坏到每一个行为都透露着恶意。自然而然,最开始好干部失势、坏干部得势,但是邪不胜正,最后好干部翻身打倒了坏干部。
作品设定的云中村是一个藏族传统村落,村中几乎没有其他民族的居民。实际的汶川县,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区域,有藏族、羌族、汉族、回族等各族居民。据《2019汶川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这四个民族的人口占比大约是20.4%、39.5%、38.7%、1.1%[2]。在这样的人口分布下,叙述者将云中村设定为一个单一民族的聚居区,且全村信仰藏族原始宗教——苯教,这显然是刻意为之。其目的当然不能简单归结为作者的民族身份是藏族,既然作者要呈现对死亡、对人与自然的本质性思考,那么这一地域空间的设定显然是为了呈现藏族的文化精神以及藏族文化中看待死亡和自然的独特观念。由此观之,表述藏族文化就是该小说的核心主题之一。关于文学的民族书写,果戈里曾有一句名言:“真正的民族性不在于描写农妇穿的无袖长衫,而在表现民族精神本身。”[3]阿来本人也坚决反对民族风情式创作,他曾说:“这个时代的作家,应该在处理特别的题材时,也要有一种普遍的眼光。普遍的历史感,普遍的人性指向。”[4]
然而,《云中记》不但仅仅停留在对“无袖长衫”的描写,而且先入为主地设定了一种所谓的“本质性思考”。虽然作家在创作之前必然有一定的构思和安排,但当作品仅仅是为了图解某种预设的理念时,便往往缺乏了艺术性和感染性。《云中记》的基本情节被设定为一个传统的藏族招魂仪式,套在安魂仪式里的,是阿巴通过回忆叙述自己成为祭师的“过渡”仪式。过渡仪式,是人类学的一个术语,指的是许多仪式往往意味着从一种身份到另一种身份的转变,因此仪式本身其实是两个身份的过渡阶段,如结婚仪式、成年仪式等。人类学在研究仪式时,一个重要的方向是探讨“过渡仪式”的阈限阶段的象征意义,即个体既失去了之前的身份又没有具备即将取得的身份的这个中间时刻[5]。在《云中记》中,阿巴成为祭师的阈限阶段,本可以成为一个烘托主题的聚焦点。然而,叙述者的处理却陷入了神秘化的窠臼。阿巴成为祭师的三个阶段分别是失忆、喇嘛指点、非物质文化培训班。阿巴对于非物质文化培训经历并不是特别认同,他一直无法说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他说自己是“非物质文化”。刻意避免“遗产”和“传承人”显然有其用意,意味着以祭师为中心的活动不是行将消失的文化遗产,亦不需要形式化地传承,因为文化本身鲜活地存在于生活世界中。那么,叙述者显然认为阿巴的失忆和喇嘛的指点是阿巴成为祭师的关键,前者尤其重要。
如前所言,为了说明灾难的不可避免,先安排了一场滑坡,然后阿巴神奇地失忆,十多年中唯独喜欢听摇铃击鼓声,最后也在击鼓声中莫名记起一切,然后在喇嘛的指点下几乎顿悟式成为了祭师。虽然对于宗教信仰者来说,确实有许多天启神示的超常经验,但是将这种经验像通俗韩剧一样安排为失忆和恢复记忆的桥段,容易给读者造成较大的距离感,从而失去了可信性。更何况,阿巴在回忆失忆的十多年中,还一直在强调自己当发电员时多么骄傲,这进一步瓦解了信仰。因此,试图通过仪式将阿巴塑造为传统文化、传统信仰的实践者,然而实际上呈现出来的却是一种神秘化的表演场景,缺乏对文化、信仰、民族精神的深层次把握和呈现,小说文化表述的这一主题亦缺乏突破。
三、《云中记》的意蕴——浅表的“本质性关系”
作者一再强调《云中记》表达了“对死亡、人和自然的本质性关系”。阿巴是作者体现他的“本质性”思考的核心人物,他虽然受到了喇嘛的指点和嘱托,但他坚持认为自己所秉承的苯教传统对待死亡的态度不同于体现在喇嘛身上的佛教。佛教认为人死后灵魂可以存在并且会轮回转世,而阿巴认为人死后灵魂也可以短暂存在,但到一定时间就会“大化”——消失至无影无踪。同时,阿巴通过对立于移民村人以及与仁钦、余博士的交谈,也几乎是要呐喊出“大化”不同于理性的无灵魂论。那么进一步可以推知,小说要呈现的是一种非功利性的死亡观念,不祈求来世;云中村的消失(死亡)和阿巴甘愿陪云中村死亡这一行为,似乎是要阐明死亡并不意味着一种悲痛的失去,对世界而言,万事万物从生到死是必然的自然现象,人也好、文化也好,在自然面前都是渺小的。或许,这才是阿巴回到云中村并与之消失的根本缘由,安魂不过是其死亡之前要做的一件事,他要通过仪式让这些无处可依的亡魂归于“大化”,然后一起消失。
自然而然,从这样的死亡观就可以联系上人和自然的态度。小说中,云中村人尊重自然,不伤害动物,但是许多利欲熏心的偷猎者上山来猎鹿,导致鹿群的消失。地震后,偷猎者没有再来,云中村人也搬迁至移民村,于是鹿群又回来了。云丹听阿巴说鹿茸很大,还说那可以卖很多钱,但阿巴拒绝了。这里的对立之意一目了然,从动物获利的工具思维伤害了动物,导致了物种的濒临灭绝。人类需要依靠动物才能生存,但动物却不必依靠人类生存。阿巴回村之后,与鹿群建立了和谐的关系,鹿群开始时有所害怕,慢慢产生信任,最后自由自在地在村里的院子里吃绿叶。此时,人与动物共融共存,人与自然和谐存在。至此,可以总结小说的“本质性”思考:人类的渺小和死亡的必然性,人只能顺应自然规律;人不能把自然当作工具,应与自然和谐共存。
当然,不能否认上述思考的正确性,人确实只是地球的一个物种,而地球上还一直存在着其他物种,人类与其他物种应该是平等而和谐的。然而,在21世纪的今天,这样的观念早已经成为了几乎无人不知的常识,人的渺小也已经是几千年文学史不断重复的主题。将时代常识作为本质性思考,显然是不够的。已有学者指出:小说叙事者真正要传达的意图,只是人死如灯灭这种常识,而对着遇难者、屈死者讲这样的大道理,太不近情理[6]。
文学创作还有一条出路,在不断重复的主题中,赋予新的表达方式,但《云中记》并没有超越少数民族文学写作常见的模式。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少数民族文学作家热衷于民族文化的表达。这种文化表述式的写作思路,确实呈现出了中华文化的多元性。然而,当我们反思少数民族文学在新时期以来四十余年的发展历程,会发现大量的作品缺乏对民族文化价值的深层挖掘和审美表达,往往停留在对山林秘境、风俗仪式、神秘现象等的浅层次表达上。民族文化是一种点缀和饰品,是作家们加工而成的文化景观,不是一个真实而生动的生活世界。更有甚者,照搬文化典籍中的风俗描述,不加区别、不作审视、生硬地搬弄到作品里,以彰显自己的民族文化身份,试图以民族风情获得读者和文坛的认可。
《云中记》的叙述者没有虚构,没有捏造,忠实于文化典籍。苯教研究专家拉巴次仁在总结苯教的自然观念时指出:万物有灵是苯教思想之源,具体表现为对山水树木、日月星辰、自然奇观、动物、祖先及智人的崇拜。它以人为中心,并不苛求来世的富贵[7]。然而,文学创作不是文化研究专著,也不是宗教介绍书籍,文学不在于罗列观点,而是要打动读者、感染读者、启发读者思考。这就要求作品的真实——真实的情感、真实的情境、真实的行为、真实的信仰。即使给出土的恐龙骨架披上仿真的皮肉,它也只能支立在博物馆吓唬一下游览的孩童。叙述者是博学的,书中出现了鸢尾花、香樟树、金盏花、苔藓、樱桃、接骨草、大黄、绣线菊、花楸树、桦树、瓦松、蕨苔、核桃花、荠菜、楤树、芫菜、胡萝卜、菠菜、蔓菁等数十种植物。这些植物几乎都是用的学名,但小说的聚焦者却是一个仅上过初中、且并未离开本地的祭师。可见,云中村成为了叙述者精心制造的云中村,而不是一个具有泥土气息的传统村庄。
总之,关键的问题不是人类与自然是否应该和谐共存,而是如何共存?如果能顺着这个思路继续深掘,去呈现藏族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智慧,那么《云中记》或许会具有一种“本质性”的思考。这需要深入到藏族传统的生活世界,去把握真实的人,体会真实的信仰,感受真正的生活方式,那么《云中记》会成为云中村的生活场景,而不是叙述者虚构的一个注定消失的村庄。
四、《云中记》的情感与语言——矫揉造作、干瘪单调
主题的犹豫使结构安排失衡,使得重点不突出且主题之间缺乏紧密的联系,这造成了《云中记》意蕴层面的浅表通俗,并没有真正揭示出某种本质性关系。其根源是叙述者情感的虚伪和造作,其体现是叙述语言的干瘪和单调。
如前所言,《云中记》的核心是阿巴回村的招魂仪式。但是,这个招魂仪式并没有深入到群体的生活世界,没有从生活中去挖掘仪式和信仰本身的巨大内蕴。著名社会人类学家涂尔干认为:“仪式是在集合群体之中产生的行为方式,它们必定要激发、维持或重塑群体中的某些心理状态。”[8]仪式之所以不断重演,绝不是因为其仅仅是一种传统,而是因为它被相应的群体需要,与相应群体的生活和心灵息息相关,蕴含着群体的某种情感。阿巴的安魂过程中,既缺乏对死者的追忆和同情,更缺乏对待仪式本身的一种虔诚的态度。他不知道自己信不信鬼神,不知道鬼神存不存在。如果说阿巴的行为仅仅是出于一种对即将消失的云中村及地震罹难者的一种责任感,那么通过安魂仪式的方式就显得空洞而做作了。比如在叙述阿巴最后的祭祀山神的仪式中,总篇幅约16页。如此多的篇幅中,绝大部分文字都是在叙述阿巴是如何做的、唱了哪些老歌、这些老歌中又隐藏着什么神话故事。而关于阿巴的内心体验的文字却出奇的少,似乎只有一句“悲怆之情充满了阿巴的心!”语言的匮乏在此可见一斑。在乡土、地域和文化的题材里,老歌、俗语、民间故事、神话传说等往往被用来作为呈现乡土味、地域气、民族情的重要材料。然而,程式化地罗列或者哗众取宠地捏造非但不能达到呈现地方性知识的目的,反而使文学作品失去基本的审美性。《云中记》对阿巴祭师的描写,停留在表层的装束、行为、仪式、老歌等层面,因此也就难以引起读者的共鸣,无法打动读者的心灵。
阿巴的安抚亡魂和祭祀山神,整个过程就基本上是摇鼓击铃和抛洒食子,没有多角度的聚焦,没有细致的描绘,也没有丰富的心灵呈现。在安抚第一家——罗洪家的亡魂过程中,阿巴追思了他们家的勤俭持家,也追思了他们家的吝啬(从不给别人借钱、没有售出的药材已经腐烂);第二家多少人口不知道,除了幸存者阿介其他人都发羊角风“口吐白沫抽搐而死”,对阿介的回忆内容是他异于常人的孤独和同样异于众人的自杀;第三家、第四家,分别死了两个和一个人,全家没有名字没有回忆;第五家没有名字,爱看电视的孩子被卫星接收器的大锅切断了双腿;第六家,搬到县城的裁缝,没有名字,地震前老房子蹋了一个角,阿巴说“他们也没有回来看上一眼”;第七家,阿麦家,因为爱生孩子,有七个儿子和两个女儿,地震后大儿媳和二儿子成了夫妻;第十二家,呷格家,会种麻纺麻,与阿巴一样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然而却不吸收乡亲到作坊工作被大家怨恨;第十五家,祥巴家,追忆内容最多,不走正道,除了中祥巴,其余全部死亡,中祥巴也被列入失踪名单,形式性死亡。剩下的家庭中,除了阿巴自己家,其余的几乎只字未提。整个云中村三百多口人,有名字的不过几户,其余的几乎没有被提及。提及的几户中,既刻意地贯穿着一种简单的因果报应思想,亦潜藏着一种高高在上的猎奇眼光。当然,文学不是户籍资料,不需要也不可能巨细无遗记录每一户的详尽情况,文学常常以某种典型去呈现更具普遍性的意义。那么有名字的罗洪家、阿麦家、呷格家、中祥巴、央金等具有代表性吗?能升华到更深刻的意蕴层面吗?恐怕答案是否定的。央金和中祥巴消费苦难的行为既不能代表云中村民的态度也不能证明阿巴对村庄的深情。
记忆内容的贫乏体现了叙述者情感的空虚。在具体对每一家亡魂的安抚中,阿巴看起来只是在完成一个任务,缺乏真正的同情和悲悯,也没有深刻的人生体悟。每一家的记忆,除了干瘪地说明总人口数、收入来源以及幸存人数,再也没有更多的信息,也没有情感的波澜。阿巴击鼓摇铃,一家一家地呼喊“回来回来”,然后将一把把的粮食撒向一个个院落,仅此而已!这些死去的人是阿巴朝夕相处的乡亲,在叙述者设定的这个人情淳朴的村庄必然有着紧密的联系和深厚的情谊,然而阿巴几乎没有追忆这些,他更多追忆的是自己当发电员时如何辉煌和得意、自己如何成为了祭师以及外甥仁钦又是如何有作为。他甚至神秘化了自己成为祭师的过程——在山体滑坡中神奇存活、失忆多年神奇恢复记忆、受到一个喇嘛的神奇指点,最后神奇地成为了祭师。这并不是在追忆村庄,而在神化自己、炫耀身份。一个为村庄招魂、为文化发声的祭师,却在这里滑入了个体的功利世界。有的学者会认为,这里是叙述者刻意为之的冷静叙述,然而,不能将冷漠当成冷静,冷静背后是深层而抑制的强烈情感,冷漠背后则是空虚而偏执的情绪。
情感的冷漠与语言的单调如影随形,这在其他人物的语言中亦如此。洛伍随勘测队上山时,对阿巴的态度是一次又一次“粗暴地摇晃”,因为他心中有“怨恨”,但对怨恨的处理不到位,以至于“怨恨”成为一种想当然的表演;地震后解放军的营救和志愿者的帮助,本应该具有强烈的感染性,然而却仅仅是“样板式”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人物出场时一般交代了基本的身份信息,但是下一次出现又会重复交代一次。虽然回忆和重复叙述可能是小说为了制造民族味而有意为之,但在枝节的重复和语言的干瘪下,重复成为了一种没有支撑的技巧,既不能成功塑造形象,也无法真正承载构设的主题。
四、结语
笔者相信阿来在创作《云中记》时,有着强烈的悲悯情感,有着激流一样的创作激情。然而,情感动机和创作意图毕竟不同于作品本身。《云中记》并未在独特的文化视角下,或呈现出深刻的地震记忆,或深入聚焦村落重建与乡村现代化问题,或表述真实的民族生活世界。小说都涉及到了这些主题,然而却像一个行色匆匆的游客,拍了几张照片就迫不及待地离开了。结果,小说成为了一个拼凑的主题果盘,既缺乏深刻的哲理思考,亦没有动人的情感,人物形象标签化缺乏生气,语言干瘪生硬缺乏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