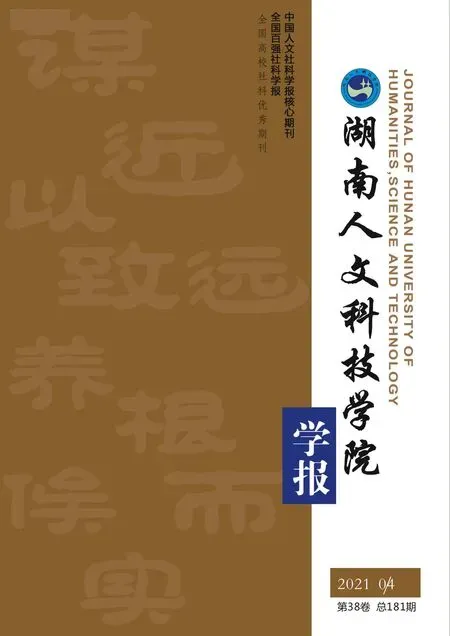女性主体性建构与生命启示
——红柯小说《靴子》的另种解读
2021-12-06张海玉于京一
张海玉,于京一
(山东大学 文化传播学院,山东 威海264209 )
《靴子》(1998)是红柯1990年代新疆系列短篇小说的佳作之一,其新疆书写延续了红柯一如既往的诗意风格与自然气质。多数学者从爱情叙事的角度,将《靴子》归结为旅店少女为醉酒客人洗靴子而萌生情愫的一则爱情故事。郑悦认为,《靴子》中女孩为男性脱下马靴后在心灵上完成了爱情的归属,女性在牺牲自我、成全对方的同时完成了作者对于爱情的想象[1]。李丹梦认为,《靴子》“作者大约是要表达对雄性力量的顶礼膜拜”,而这样的顶礼膜拜反映了红柯神话中一如既往的情爱格局,即“女人大多天然地崇拜男人、依附男人、栽培男人、浇灌男人”[2]。但透过对《靴子》一文的考察梳理,它显然并非单纯表现年轻女人与已婚男人的禁忌之恋与情爱故事。与以往短篇小说频繁出现的“奔马”“雄鹰”“羊”“树”等动植物意象,以及“炉子”“汽车”“扫帚”等西部日常用品的叙事装置类似,红柯以“靴子”作为叙事线索贯穿小说全篇,不仅串联起男女两性之间的情感交流,更透过人与物之间的沟通对话来“重建人的自我”,使故事人物发现并主动建立起与自然世界最原初、本质的生命关联。如曹斌所说,“物与人交流,实际上是作家运用直觉、意识流、自由联想、幻觉对人的生命意识的放大,用以显示生命主体的崇高”[3]。
“靴子”作为游牧民族的必备生活用品,被赋予了深刻的象征意义,成为连通脚与大地的媒介,即人与自然达成交流与融合的信物。首先,红柯借由醉态化的感官叙事,呈现年轻女人在视听触等多重感官带动之下,主动与“靴子”所寓意的自然世界建立生息相通、物我共融的生命联系。其次,红柯借助“手”“脚”(及外在装饰“靴子”)等性意象,进行大篇幅热烈直率的性爱描绘,展现超越伦理与道德观念,完全听从自然本性的原始生命力与欲望本能。最后,红柯通过表现年轻女人在两性关系中由被动到主动的主体意识建构过程,思索女性主体出场对于西部文学主体性地位建立的意义与价值。
一、醉态化的感官叙事:观看·倾听·触摸
杨义在《李杜诗学》中曾经提出,李白创造了一种“富于内在精神体验的醉态思维,散发着西北胡地健儿的率真豪侠的气质”[4]68,它要求作者“把自己的精神调动到摆脱世俗牵累而对生命进行自由体验这样一种巅峰状态,去体验宇宙人生的内在生命本质和清风明月般动人的美”[4]67。同样经历过西部地域文化与自然环境磨砺锻造的红柯,在创作中始终保持微醺状态,作品弥漫出一股任侠狂逸的酒气与豪气。醉态化的审美思维方式放大了人与物的感官体验,视觉、听觉、触觉三种互通共融的感觉方式,在《靴子》中成为诱导年轻女人“她”展开内心世界对于物象世界的主观想象,并与之建立声息相通、物我共融的生命联系的有效路径。如李丹梦所言,“红柯似乎有种根深蒂固的想法,只有化为切身的感官经验,形而上的探索才能落到实处。自然的拟人化因其对感官的诱导、解放和延伸而成为主体建构的关键与必需”[5]。红柯在《靴子》中打造了一个实体的旅店“窗口”,为“她”主观化的感官体验提供交流的路径,“当人类满足于自己房屋门与窗功能的完美无缺,忘了自己与自然生死相依的难以割断的关系时,人类就会切断自己与自然家园的联系,迷失返回自然的路径”[6]。从这个意义上说,窗户无疑为“她”打开了一扇心门,通向生命敞开、精神成长的自然之途。驻足窗前与行走草原代表了年轻女人不同的生命态度与体验,而通过视、听、触等感官方式,年轻女人完成了自我意识的转变及生命原力的觉醒。
(一)观看及延伸而出的眺望
观看是人类无意识的行为表现,位置、距离甚至视角的变动都会影响观看者的感知印象,折射出观看者细微复杂的心绪与感受。小说《靴子》中,年轻女人无疑占据了一个绝对化、无意识的观察视角,小说充斥着女人的“看”以及情绪浮动下的“回避看”。
首先,观看之物为外在环境。在“她”的视角之下,旅店的整体环境与个人空间得以呈现:她的房间在走廊尽头,里边是床,外边是一大堆热水瓶和脸盆,还有水桶和拖把[7]174。狭小闭塞的空间与拥挤杂乱的室内摆置构成了女人平淡生活的日常。房门、走廊、门板构成的室内空间与公路、骑手、草原构成的自然世界两相对立,无形中喻示着年轻女人“她”与自然世界的隔绝。其次,目之所及为具体的物象——醉酒壮汉与窗外景物。观看醉卧在床的男人实则是观察他沾满泥巴还有牛粪的长筒马靴。“她用手绢捂着嘴”[7]169“她的手躲在背后,她不敢动”“她的手从背后蹿出来,飞快地在衣服上抹几下”[7]170等等身体反应的详尽刻画传达出“她”隐晦的心理表征:对于“脏东西”、污秽之物的嫌弃。“回避看”并刻意与醉汉保持距离的行为表明“她”无法将醉倒在床的壮汉与草原骁勇强悍的骑手建立联系,而从习以为常的生活理念出发对壮汉的行为举止做出价值判断——肮脏、狼狈、毫无骑手风范。年轻女人在看,同时也在被看。作为“她”的对立面的旅店老板与醉汉,发觉女人行为的抗拒——手的不自然状态。因而醉汉以一句粗糙朴实却深刻传达男性生命观念的话:不好就砍掉,作为对女人的劝诫。旅店老板的“你年轻你不懂男人”[7]170看似玩笑话却也暗藏生命的箴言。“她”对于手的珍惜爱护与对于醉汉靴子的不以为意,甚至与醉酒壮汉、旅店老板看法与态度的迥异均映射出两性殊异的生活方式与生存状态所构成的生命观念的差异,这成为他们理解与沟通难以逾越的鸿沟。而红柯企图跨越这一鸿沟,寻找沟通两性生命存在的合理方式,一种西部生命所共有的价值观念与精神内涵。
最后,站在窗前的年轻女人与窗外所见之物互为镜像。在拉康的镜像理论看来,窗户幻化为一面镜子,主体透过窗户观看外界,外界及万物成为一种镜像,自我在对于他者观察与想象的过程中获得对主体的建构与认同。年轻女人“她”由初始无意识甚至回避、拒绝的观看转化为带有情感色彩的注目远眺。《靴子》中详细描绘了女人“她”多次探头窗外的场景,女人视线延伸所及之处,已经不自觉带有追寻远方、好奇探望的情感色彩。“她”不仅看到壮阔的大地天空与自然风景,还频繁看到动物车马的投影。关于投影的想象是年轻女人对于自然之我的联想,在承载万物、超越时空的大地与天空面前,万事万物都形如尘埃,唯有以释放性的生命存在奔腾活跃于大地与天空之间,自然生命才能实现真正的联通与共存。
(二)倾听并回应自然召唤
外界环境中的未知声音所具有的迷惑性与号召力,往往能够搅扰变动心理状态下的人物心神,诱导听者自发追寻声音源头,并展开与声音相关的联想与臆断,且在倾听行为中被潜移默化地带领、改变,甚至塑造个体的情感认知与主体意识。
小说《靴子》中,旅馆内部与辽阔草原构成了两个截然不同的声音场域。室内,醉汉“一边喝一边嚼茶叶,咔嚓咔嚓像马吃草”[7]169“那人呼呼大睡,胸腔和喉咙里全是滚烫滚烫的睡眠声,跟茶水一样煮的很酽”[7]172。这些声音显然造成了“她”心理世界的震动,成为搅扰“她”毫无声色的生命世界的有力“噪音”。年轻女人从窗户探头出去的行为,既是对缺乏声色与波澜的生命世界的回避与疏离,更是对于窗外不断走动的马靴声的回应。“她明明听见有脚步声,一下一下走过来,往公路上走,她听得清清楚楚是笨重的马靴声。她连靴子上的铁刺都听见了,好像往石头上钉钉子。铁咬石头,咯铮咯铮”[7]171。笨重的马靴声是年轻女人对于远方世界的想象之声,更是其内心世界冲破生命束缚、渴望自由的回响。它来源于自然世界强大的召唤力量,一步步靠近年轻女人,从天山到大路再到女性心灵深处。“她”的情绪起伏与身体行为是回应生命召唤的过程。“房门嘭一下开了,门板在墙上撞了一下”[7]171,女人内心世界的冲撞,具象化于小旅馆内部空间的突破与响动。窗外不断靠近女人的幻听靴音,以及室内醉汉穿着靴子走向远方的真正靴音,都以某种召唤性的力量深深嵌入女性的情感世界与自我认知上。靴音在这里成为一种精神性的引领物,如草原上的旷古长歌般响彻了年轻女性的生活世界。
(三)触摸靴子,与自然交融一体
年轻女人与“靴子”的接触行为,无形之中成为了解男人生命存在的窗口。在红柯眼中,作为草原日常生活用品的靴子因为与大地的紧密联系而具有了神性。靴子的神性表现在精神世界与生命理念相关的生命启示与指引,它是手抵达脚的媒介,更是一种传输生命经验与建构自我意识的媒介。男人必须“迈步向前”“靴子成了大地的神物,骑手双手扶地,把脸颊贴在草地上,骑手向靴子跪拜,靴筒里装着一个高贵的灵魂”[7]176。唯有穿过戈壁沙漠,踏步行于草原,与自然相融共生,生命的动态与激情才能予以尽情释放。同样,年轻女人的生活状态与心理图示透过女性之手得以展现。年轻女人与醉汉初次见面时捂手、擦手、手背在身后等闪躲与拒斥的手部动作到后文手与靴子的主动交融契合,无疑暗示了女性对于自我意识与生命观念的毁弃与重塑。红柯以细腻诗意的笔触描绘出了手与靴子接触的动态美感:
她弯着腰,张着双臂,可她没跳,胳膊和胳膊上的手在她犹豫的功夫,就扑上去,去脱那人脚上的靴子。[7]172
她的手无比豪迈地顺着黑沉沉的膛线,轻轻晃着,猛一抽,把马靴抽下来,咚,扔在地上。[7]173
她不用刷子了,她的手跟鱼一样从水里摸上来,顺着靴筒滑动,水跟手一起滑,到顶上只剩下一只湿手,跟牛舌头一样,舔啊舔它的牛犊子。[7]175
靴子在女人手里变成新的,靴子有了光泽,女人用布打了一遍,又打一遍。一双马靴就出来了。[7]176
“扑上去”“摸上来”“无比豪迈”等手部表现,以及不厌其烦地脱鞋、洗鞋、擦鞋的接触行为,足以表明年轻女人刻板闭塞的生命“偏见”的摒弃,并不再以观望想象的客体姿态对醉汉做出情感认识与价值判断。相反,年轻女人在有意打破习以为常的生命结界,尝试走出原有的生活空间与认知范围,主动认识并了解男人所生活与体验的自然世界,并以一种顺从甚至虔诚的姿态进入到草原生命的交汇与启迪中。而拘囿闭塞的生命也由此朝向敞开,与自然及其众多的草原生命融为一体,在交融契合中实现生命的通透体验。
年轻女人观看与倾听并响应旷野的召唤,以及女人之手与男人靴子通过触摸实现“契合交欢”,都为女性主体意识建构、生活态度转变、最终走出生命的结界、踏上自然之途提供了契机与辅助。极致张扬的感官书写,为人与物的彻底沟通打造了一条精神通道,实现了故事人物对于生命存在与人生本相的本质透视,这是红柯叙事的可贵之处。
二、物我交融的性爱书写:以靴子为中介
红柯在《真正的民间精神》中谈及现今爱情小说的创作非常之少,在现代文明社会,“求爱、求欢、性,其最美妙的因素离人类太遥远了”[8]。因而在红柯西部小说中,他着力表现对远离世俗与社会属性的超凡爱情的诗意描绘与赞美,传达出西部大地男人与女人情感的真挚与热烈,并企图超越世俗的两性爱情,回归人类情爱的本真状态。如李泽厚所言,“性欲成为爱情,自然的关系成为人的关系,自然的感官成为审美的感官,人的情欲成为美的情感”[9]。生活于边疆大地的男人与女人,他们爱恋、情欲的自然产生既是两性必需的生理需求与情感交流,也是一种超越伦理与道德观念,完全听从自然本性的原始生命力与欲望本能。表现男人与女人的情爱关系就是表现自然与人的关系以及人的自然化生命形态与生命理念。《靴子》中存在多处性爱场面的隐晦描写,“隐晦”并不表示刻意模糊与掩饰,而是红柯巧妙地以性意象作为表现手段,物我契合。在红柯书写中,一切欲望尤其是性欲本能被充分合理化、肯定化,充溢着他对人类本能欲望与自然天性破除遮蔽束缚,回归本真展现的赞美。
(一)以性意象接触暗喻两性阴阳交融
“手”“脚”(及装饰物“靴子”)等性意象的触摸暗喻着男女两性的阴阳交融。埃利希·诺依曼在《大母神: 原型分析》曾说,“在自我和意识仍然弱小、未经发展而无意识占支配地位的任何地方,都可以清楚地看到女性的基本特征”[10]。女性之手,天然具备柔软、干净、魅惑的自然属性,被女性所特别呵护与珍视。而女性之手的手势、姿态呈现,以及与外物的接触抚摸,都使得手不仅是观看审美的对象,更成为实现欲望的工具与欲望的象征之物。小说《靴子》中,女人之手不再作为他者审视观看的客体物,在红柯的叙述装置下成为表现年轻女人拘囿闭塞的生命观念的象征物,同样也是联结两性关系的性爱中介。西方性心理学家哈夫洛克·霭里士曾经表明脚与鞋所具备的性隐喻义:“在足恋者,足或履不是一个工具,而是一个真正的象征,是不惜顶礼膜拜的东西,是一个理想化的对象,摩挲时固须极其虔敬之诚,想象时更不免忘餐而废寝。”[11]这样的隐喻义跨越中西时空始终捆绑在对女性身体的文化阐释上。中国宋朝始兴的“小脚文化”以及对女性脚和鞋子的迷恋,也始终伴随着男权色彩的性欲窥伺。红柯一反其道,不写女人之脚与鞋子,而对草原骑手的马靴进行重彩浓墨地描绘,并企图恢复人之脚与鞋的本然意义——行走需要。“靴子”意象也摆脱了中国自古以来脚与鞋所具有的性政治与社会含义的复杂隐喻与象征符号,而被赋予了单纯而崇高的神性色彩。小说《靴子》通过表现女人之手与醉汉之脚(靴子)脱鞋、洗鞋、擦鞋的动态接触过程,来展现男人与女人的性爱交融。女人“手”由初始的不知所措、抗拒嫌弃到与靴子的主动接触并享受融入,暗示年轻女人已经蜕尽了刻板坚执的生命偏见,真正达至了个体本能欲求与自然世界契合的理想生存状态。
(二)自然“拟人化”与生命个体建立情感联系
自然被“拟人化”成为欲望对象,与生命个体建立情感联系。红柯笔下的群山、戈壁、大漠、草原、河流等自然景观意象并非仅仅发挥地理背景设置、叙事线索推进的结构功能,它在红柯小说中经常是拟人化的灵性所在,充满生机与活力,与靠近它的自然生命建立着真正的情感依赖。而自然作为雄浑的、野性的、激情的性爱一方,往往能够与女性生命个体建立情感联系,甚至实现性欲的交融与姌和。譬如,在红柯小说中出现的“河流”自然意象,《雪鸟》中“男人把丫头护送到河源,男人就不再是保镖和劳力,男人就是这条河”[12]223“他这么一嚷嚷,就改成一条充满生命气息的大河,女人非但没有受到损害,生命的意义反而得以张扬”[12]224;《靴子》中年轻女人提着红塑料桶到峡谷的河边打水,“水面很平稳,水却很紧,她脸憋得通红,身体往后倾,手一点一点从水底吐出来,然后是半圆形的粗铁丝,桶出来时哗啦啦像下白雨。桶水淋淋站在岸上。她缓缓气。她嘴张得不大,可她的呼吸又深又长,胸脯高起来,落下去,大峡谷捏她就像捏一个皮球,捏摸够了一松手,她又丰满起来。她站在大峡谷里,她丰满结实苗条。她的丰满从胸到腰到臀上,腰又圆又细,腰更结实更苗条”[7]174。在此,河流是自然的化身,被具象化为一个人。在性爱双方的依恋、交姌与互融中生命实现了解放与意义的张扬。
“靴子”作为两性精神引领的神物,并没有超越红柯书写的“物”的表现范畴。它始终围绕着两性关系发展而发挥作用,并“把女人当成大地最美妙的地方”[7]176,以此彰显出红柯西部书写中对于母性与生殖文化的极致推扬,在小说中实践“人类回归大地母亲的夙愿”[13]。“靴子”对于大地母亲的回归,一方面表现出女性与自然所天然具备的生命联系,一切草原生命在自然怀抱中息息相通,归为一体,生命能量也在自然生命中不断传递、更新、再造;另一方面反映出红柯一如既往的女性生殖崇拜,两性交姌同样是为着创造生命的需要,是生命得以延续、种族得以繁衍的人类本能。《美丽奴羊》中处女地紫泥泉与科学家妻子同样是大地上最美妙最有生殖力的地方,孕育出了明亮滚圆的美丽奴羊以及世世代代的草原娃娃。《雪鸟》中跳进河中的女兵不但没有丧失生育能力,反而生出了一个又一个壮实的男婴,“给大地带来了丰收”[12]223。
“永恒的男性与永恒的女性之爱包含着呛人的血腥味”[14]。红柯一改现代社会身体叙事的复杂含义与文明底色,祛除工具与符号的附加意味,将隐秘化甚而羞涩化,带有形而下色彩的性欲本能赤裸裸呈现出来,置于崇高甚至神圣的地位,张扬自然社会中身体与欲望的动能与自由,身体欲望的释放承载着精神解放、心灵自由的形而上启示。
三、主体的自我确认:被动到主动
在红柯笔下的男女两性主体关系中,“女性只是属于‘男性/自然’编码下的次生品,闯荡自然是男性的专利”[15]164,此种刻板单一的男性主体性伴随着女性角色的出场以及主体性作用的发挥在逐渐弱化。两性关系逐渐演化为一种新的主体间性,“生存不是在主客二分的基础上主体构造、征服客体,而是主体间的共在,是自我主体与对象主体间的交往、对话”[16]。主体间通过交往、对话,在对另一主体存在的认同下达至对自我主体性的确认。
小说《靴子》中,年轻女人与醉汉初次见面时,醉汉狂驯桀骜的言行与女人畏缩怯懦的举止仍然显示出男性高高在上并审视打量女性的姿态。年轻女人既不了解自然世界及其他生命存在,也无法达至对自我主体性的肯定,遑论生命存在的意义。在经历了与“靴子”即自然亲密的接触之后,年轻女人从抵抗、不解到充分理解男性生命理念与存在之义,实现了由女孩到女人的精神蜕变与主体确认。《靴子》故事结尾,男人与女人进行了一番意味深长的对话,他们均脱落了手、脚(靴子)等象征符号,重新回到人的初始状态,展开了面对面的情感与生命交流。此时,年轻女人已经在两个主体的情感价值交流中获得了比较平等的位置,男女两性达到了高度的谐和与充溢,他们不仅能够自如交谈,互相打量对方,更能够实现情感、精神的双向发展。年轻女人已经抛开了外在的束缚——肉体上的矜持含蓄、谨小慎微以及心灵的束缚禁囿、无法放松,而是像蛹一样裹着拉舍尔毛毯,“光身子睡觉感觉特别敏锐”,感觉的敏锐实则是心灵与外物实现通感,获得了精神上的持久放松与轻快,也意味着女性主体身份与意识的清晰。
女人在美妙的时光里身体就没有重量。她深切地体味着她的轻盈与飘逸。她像是踩着水像是在漂。从房子到走廊,近在咫尺,从走廊到门口,近在咫尺,从门口到无边无际的野外,近在咫尺;而她的行走如同歌手在草原上拉着长调,无边无际地向四野蔓延。[7]177-178
年轻女人“她”在突破生命拘囿的蜕变中获得了至轻的身体感受,“轻盈与飘逸”得益于旧的舍弃与新的发现,走近与融入自然,一任生命的舒展与精神的畅快。红柯笔下的人物拥有一种辽阔的大地意识,草原与大漠的辽远广阔与遥不可及化为人物的“心灵世界”与“生命气息”,不仅小说叙事有很强的空间感,人物处身其中的空间感受也极其强烈,女性主体“近在咫尺”的生命感受,是她精神复苏、得以领会生命启示的一种证明。
刘文祥在分析当代西部文学的主体性变革时,曾言及女性的出场对于西部文学建构的意义,正如女性由被动走向主动的主体建构过程,“西部文学也在告别父权、告别他者的目光中生长出属于自身的主体性: 它表明一种姿态,西部文学不愿意继续被别人阐释,而是要自己阐释自己”[15]168。始终处在刻板偏执的西部印象审视打量下的西部文学,似乎很难找到一个合适的书写定位。蛮荒、落后、粗野等等西部专属词汇并不能涵盖西部的全面,“如果我们承认时光在流传,世界在改变,那么,我们就应该承认‘西部特色’也将是一个日新月异的所指。”[17]而摆脱文学、文化偏见的唯一方式便是摆脱掉自我的“他者”身份。就像小说故事里未经世事的少女一般,如果始终深陷于他者眼光中,永远臣服于男性话语之下苟安于既定的生命状态,她将永远无法清晰地认知自己。西部文学同样,必然要摆脱掉来自主流文学、文化的他者眼光,摒弃以外界期待、认可、命名作为依据进行书写的自我“他者”身份,发掘西部地域特色与族群身份特征对于西部文学的书写意义,从源头建构西部文学的主体性身份。
四、结 语
红柯以炽烈的诗性语言与淋漓的酒神气质,在小说《靴子》中呈现了一幅西部女性生动鲜活的心灵图示。两性关系,尤其是女性的情感与精神走向成为红柯叙事主题的关键。红柯曾言,无论男人或是女人,都需要一种“狂飙突进的酒神精神”[18]要“与奔马与鹰融为一体”[19]。事实上,西部凛冽偏塞的环境不只属于骑手与奔马,同样是生活在天山脚下的女人的精神家园与灵魂栖息地。不同于目的化地体验生活,“对人起巨大影响的是无意识的,是环境,是一种氛围”[20]。红柯笔下的年轻女人“她”已经融汇进作家塑造的代表西部生命力量的人物群像当中,而且被赋予了独特的性格神韵与精神内涵,在不断发见与蜕变中实现了真正的自我。
透过《靴子》中作者有意味的性别建构与女性关照,我们可以发现,两性关系书写以及女性角色出场在红柯新疆叙事中有了更深层的含义。首先,红柯崇尚阴阳调和、万物合一的两性关系与生命状态,尤其对女性生殖给予极度推崇与肯定。其次,男人与女人皆能够顺应自然规律,各得其所,共同发展,实现人性的圆满与完善。最后,它深层次地表现出人与自然和谐一体的关系及原始生命奔流涌动的自然化生命形式,甚至指向“一种浸透着浓烈的血性力量和原始生命激情的少数民族文化”[21]。这种野性、刚烈的地域文化形成于西部艰烈而蛮荒的自然环境中,以一种非理性的姿态塑造出西部人民特有的生命意识,遵从自然化的生命法则,透过身体机能的强力描摹与肉体欲望的放纵呈现来张扬生命的野性与强悍,达至精神与灵魂的充溢与舒展。它是内地人所无法接受甚至难以企及的。
透过红柯颇具风格的两性书写与女性关照,我们能够看到一种迥异于文明社会的完全自然化的生命存在,它强调物我交融却非机械化的生命物化、坚守生命意义回避世俗的物欲横流、执着于大地皈依与心灵宁静,这是西部文学书写的价值与意义所在。而红柯前期小说保持了一贯的非理性生命书写的风格,窥一斑而知全豹,透过对《靴子》的考察与梳理,利于读者走近红柯的西部,了解红柯的感性与单纯,以及一个自然化的西部对于红柯的精神意义与文学意义。
注释:
①新疆系列小说是指红柯1990年代从新疆回到陕西之后创作的小说,包括《奔马》(1996)、《美丽奴羊》(1997)、《鹰影》(1997)、《阿力麻里》(1998)等作品。学者李敬泽认为自1996年红柯在《人民文学》发表短篇《奔马》后,继1997、1998年接连创作的短篇小说给1990年代文坛带来了风暴和惊喜,他们代表了红柯小说创作的最佳水平。
②“行走”作为新疆游牧民族生活与生产的重要方式,传达出边疆人民特有的生存观念与生命理念。透过不断地“行走”,边疆人民与雄浑辽阔的自然世界建立了深厚的生命联系与情感交流,形成他们勇武强悍、自由好动的生命品格与精神气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