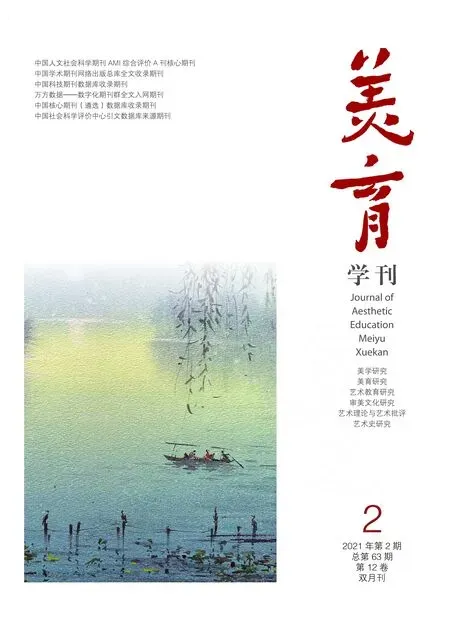现代主义艺术真实观辨析及其审美价值重构
2021-12-04汤克兵
汤克兵
(重庆师范大学 文学院,重庆 401331)
自马奈以来,现代绘画不同程度地反对再现古典艺术中的题材乃至肢解图像本身,诸如线条、色彩、形状等媒介材料显露出它本来的面目,绘画基底的物理属性逐渐成为绘画的表达媒介和主题。由于现代主义绘画排除了隐喻与影射,脱离外在可指称的世界,只能通过媒介来自我指涉。为此,现代主义批评家克莱门特·格林伯格认为视觉艺术的本质及其美学意蕴在于媒介的“纯粹性”。然而,格林伯格对媒介的理解仅限于纯粹知觉层面的媒介“特异性”(自我指涉),也就忽略了媒介的“语境性”(他者指涉)。其实,现代艺术媒介论无需在自我指涉和他者指涉之间进行区分。如果要走出艺术媒介自律论的循环论证陷阱,就必须回到艺术的真实性问题域:绘画媒介自身如何成为绘画的主题?绘画媒介的“可见性”是否等同于绘画艺术的真实性?本文从媒介现象学视角来理解现代主义艺术的美学观念:艺术的真实应该是媒介的真实,即媒介的可见性与真诚性的统一。绘画的平面性或雕塑的三维性既是某种可见的感知物,同时也是一种令人揣测的亚媒介空间。艺术家通过对艺术媒介的巧妙操纵,让藏匿在媒介中的讯息发出声音(媒介真诚地“说话”),并由此以全然不同的方式来重构主体与真实的关系,这正是现代主义艺术将对媒介表现力的探索视为一种新的实践范式与审美意涵的原因所在。
一、绘画媒介的可见性与真实性
传统绘画为了再现外在世界,往往要隐藏绘画的媒介性要素。艺术家通常把世界看作是一幅透过窗口看到的“图像”,世界仿佛如实投影在窗玻璃上的样子,这种“科学化”的观看方式,即“所知”对“所见”的理性宰制实际上遮蔽了世界的本来面貌。诸如线条、色彩、形状等图画标记就只是可供心理投射或筛选的一堆材料而已。而现代主义艺术通过对客体图像的肢解或重组,绘画中不可还原的平面性、颜料与笔触意识,以及长方形状等这些被遮蔽的媒介重获“可感”,变得“可见”。当充满意义的“图像—符号”被剔除,点、线、色块这些非模仿性的要素及其载体特征就获得了自由,其外形和感知进入整体的可见显示阶段,并最终成为艺术“表达”的媒介。
按照象征派诗人古斯塔夫·卡恩的解释,艺术的基本目标是将主观的事物客观化(意念的具体化),而非将客观的事物主观化(经由某种性格所看到的自然),也就是把自我提升到自然之上。例如,同样是称赞德拉克瓦的绘画,波德莱尔认为是颜色和形式把主题的气氛表达得恰到好处;而卡恩看到的却是颜色形式的主观性和表现力,相当于或甚至超越所描写的主题[1]61。同样是强调媒介的表现力,波德莱尔“先入为主”强调主题至上,而颜色和形式只不过是其附属因而变得不可见;卡恩则主张媒介的可见性,即目光能够捕捉到艺术媒介的自主性。在这里涉及一个基本问题:我们观画的时候,是欣赏绘画的肌理、线条、色彩等要素,还是逼真的外在形象?即艺术媒介的自主性到底指什么。
所谓艺术媒介的自主性,即现象学所说的回到事物本身的意向性。从形式上来看,现代主义艺术整体上呈现出一种“去图像化”的强烈意识,正如海德格尔所言,“为着把这幅画当作纯粹的物体要素来加以观察,首先就需要我们的自然观察方式的某种变易,需要一种去图像化(Entbildlichung)的观察方式。运用这种观察方式,感知的自然的倾向才可进入图像的把捉的方向”[2]。绘画物性的凸显,旨在强调绘画的自主性,但是,绘画又不能等同于物。因此,媒介的物性力量,对于审美想象尤其重要。
克莱门特·格林伯格的解释似乎远离了波德莱尔式的象征性主题,因而更接近卡恩的媒介自主性解释。于是,他认为现代主义艺术的核心任务是强调艺术媒介的“纯粹性”, 这样才能使得媒介的物质特性具备独立的审美价值。他认为艺术的独特魅力源自媒介的异质性。由于媒介的重要性与异质性,每一种艺术都将成为“纯粹的”,并在其“纯粹性”中找到其品质标准及其独立性的保证。体现在绘画领域,则是突出绘画的“平面性”原则。“平面性”是绘画艺术独一无二和专属的特征,并在此基础上将“平面性”的实现脉络从马奈、塞尚追溯到马蒂斯和立体主义,而且认为以波洛克为代表的抽象表现主义以及随后的色域绘画(color-field painting)仍然是对“平面性”的延展与深化。[3]“平面性”作为绘画的界限,不仅强调了绘画的视觉经验,而且是使得绘画自我敞开的 “场所”。
事实上,格林伯格关于现代主义绘画的媒介论解释并非独创,而是受惠于艺术家汉斯·霍夫曼。汉斯·霍夫曼将艺术的真实与媒介的物性表达联系起来,他认为“任何深刻的艺术表现都是对真实一种有意识的感觉的产物。这牵涉到自然的真实和表达媒介内在生命的真实”[4]174,而表达媒介乃是给予情感与概念其可见形式的物质方式。探索媒介的性质是了解艺术本质的一部分,也是创造过程的一部分。[4]172-173据此我们可以作出这样的推断,汉斯·霍夫曼以及后来的格林伯格等人的现代主义“媒介论”,试图建构一条由媒介物性表达不断向真实性推进的演化路径,即如何使绘画最终成为一种纯粹的视觉艺术。按照格林伯格对现代主义绘画的本质定义,“一张钉起来的画布”也可以是一幅绘画,尽管不必然是一幅成功的画。在一幅画变成一个任意物品之前,即使图画的平面感与画布的物理平面合二为一,几乎接近一张空画布,也会伴随着绘画媒介的物质性与图画的视觉特征相互抵牾、最终融合的过程。因此,媒介与主题的融合意味着绘画媒介的物质特性可以直接成为绘画主题:绘画作为实物与绘画作为图像之间的等同性。
二、媒介真诚性作为审美判断的前提
格林伯格的媒介纯粹性论断,依据的是康德的自我批判逻辑。因此对媒介的理解仅限于纯粹知觉层面的媒介“特异性”(自我指涉),也就忽略了媒介的“语境性”(他者指涉)。这种艺术媒介自律论更容易掉进循环论证的陷阱。当绘画不需要通过再现或表现某种外在或内在的对象来获得其本质,而是通过自身媒介的真实呈现的时候,那么何以保证媒介的呈现与观看品质之间的有效统一呢?格林伯格并没有给出解释。不过,T. J. 克拉克某种程度上将媒介的意义生成语境化,或许能够给我们提供一些启示。
克拉克认为,现代主义艺术媒介就最为典型地成为否定(negation)和疏离(estrangement)的场所。如此,媒介不仅是某种艺术身份的物质载体,而且也是意义生成和拆毁的隐喻性场所(site),同样也是身份被疏离的社会场所。[5]换言之,现代艺术家在对题材、色彩、颜料、光线、线条、空间、画的表面和布局进行不同程度的肢解和破坏的同时,实际上也迫使艺术家思考绘画媒介自身的真诚性与纯粹性,即在外在现实的不确定性这个前提下,媒介如何被阐释为是对符号的巧妙操纵,并由此以全然不同的方式来重构主体与真实(现实)的关系。
当艺术彰显其独特的媒介特征,媒介自身既是表现方式的物质载体,同时也获得了其独特的符号意义。我们知道,现代主义与装饰艺术都强调几何造型,然而现代主义在根本上不同于甚至对立于装饰性艺术。装饰性艺术只能以它“目的”上的优点而存在;它只能借着自身和指定物体间的关系来获得生命。它基本上是附属的,必然不完整的,所以必定要先满足心灵,才不至于让注意力分散到为其辩护和使其完整的形象。[6]与装饰艺术必须要融入周围环境不同,现代主义绘画艺术基本上是独立的,它和一切环境都不协调。现代绘画艺术存在的理由就是它本身,因此绘画必须创造性地利用它自身的媒介来思考绘画的问题。由此,艺术媒介——语言,或作为语言的形式结构,是受媒介决定——的独立性开始变成美学理论的一环:材质决定了“真实”,而待修饰的那块平面的性质更决定了“实在”。[7]275
如果媒介或形式结构发生变化,内容和意义也就跟着变化。现代艺术对“新”的追逐就在于艺术家运用不同的造型语言(艺术媒介),或将内在情感主题化(表现性),或思考绘画本质问题(构成性)。从艺术家的创造性以及艺术形态的丰富性来说,现代艺术风格或形式的变化建基于艺术家对材料或形式的探索与对捉摸不定的情感的表现。所以,艺术真实或者艺术家寻求的真实仍然是“每种艺术表达方式的真实”,无论是绘画还是雕塑“都受到了其本身界限的限制,并且必须通过适用于这种艺术表达方式的方法来进行理解”[8]。
从绘画的纯粹视觉性来说,可见的只有扁平的表面、颜料与笔触以及由此构成的形状,而附着其上的情感或思想是不可见的,或者说是模糊和不确定的。因此,在既不参照外在事物的外观,又避免沦为装饰的前提下,现代主义艺术理论为保证其审美品质就要赋予媒介的真诚性和有效性。正如艺术史家琳达·诺克林所说,从绘画的事后发展来看,大概属现实主义求实或求真概念的转化,这一概念从原来的“忠于个人对外在物理界或社会界的感知”之意,转变成意指忠于材质——即忠于物体表面平面性——及(或)忠于个人内在强大的“主观”情感或想象力而非忠于外在现实。[7]290在琳达·诺克林看来,装饰艺术的平面性的特征影响了现代主义绘画,最为鲜明的例子是,后印象派(尤其是高更)与法国象征主义艺术深受装饰艺术的影响,而且都强调“以平面来表现真实”,并自觉地以“忠于物性来谋求装饰中的真实”作为艺术准则。所以,现代主义绘画中的“平面性”暗示的是绘画媒介之真,而非画家所描绘的外在世界之真,更不是这一媒介所“反映”出的这一世界之真。[7]293
更为基本的是,艺术家意识到绘画媒介并非被动地作为彰显主题的附属,相反,绘画媒介的物质特性可以构成绘画主题或优先于主题并且具有积极因素。比实际题材或主题更为重要的形式和构图是构成绘画表现力的最大潜在要素。艺术家的直觉感受组织线条、色彩、形式和结构,从而使作品具有一种画家个人的意图的效果。[9]关于这一点,法国纳比派的主要理论家莫里斯·德尼早在1890年的评论中就有类似的精妙见解,他提醒我们最好记住,“一幅图画——在其变成一匹战马,一个裸女,或某件轶事之前——基本上是一块平面,上面涂有以某种秩序搭配起来的颜色”[1]118。
如此看来,当绘画意识到其构成性问题,绘画就回到了媒介本体论的问题域。绘画的真正“主题”乃是对其自身的揭示或自我指涉:“基本上是一块平面,上面涂有以某种秩序搭配起来的颜色”,观察者(艺术家和观众)理所当然地就把“平面”当作一个猜想的亚媒介空间(总觉得媒介背后隐藏着什么),而这正是现代主义艺术将对媒介表现力的探索视为一种新的实践范式与价值取向的原因所在。媒介的可见性背后,即是一个亚媒介空间,更是一个与创作情景与意图关联的语境化空间,它指向不可见的意义本身。因此,“媒介的纯粹性问题出现在一个媒介变得自我指涉的时候,这时它放弃了其作为交流或表现媒介的功能。此时,这个媒介的某些特定代表性形象就被经典化(抽象画、纯音乐)而变成体现了这种媒介的内在本质了”[10]。
三、绘画主题即媒介的符号化过程
检索现代主义艺术的风格演化逻辑发现,各类艺术的主题即是媒介的符号化过程。在塞尚的绘画中,可以确定的是“看见”不仅包括看到色彩的笔触,而且还包括这些笔触构成的对象(类似于理查德·沃尔海姆关于“看进”的“双重性”理解);而且艺术拥有充实而连贯的世界,而世界则是在观看中,确切来说是在感知中出现的;然而,与此同时我们也越来越无法确定,观看过程中如何产生了对事物的区分与联系。因此表象的任务是双重的:既要彰显外在世界的固定性和实体性,又要承认观者并不知道自己的视觉是如何使对象认知成为可能。在艺术史学家克拉克看来,“塞尚的绘画将视觉意识形态——作为独立活动的视看观念,具有它自己的真实性,以及进入事物本身的独特方法——推向了其边界和临界点”[11]。克拉克所说的“边界和临界点”即是绘画中基于光学几何学知识的直线透视问题。在传统透视绘画中,观者与风景之间总要暗示一种空间上的连续性,这样才能顺利地将观察者与理想化的客观事物秩序联系起来。然而这种“一目了然”的视看关系并没有实际地呈现出视觉活动的复杂性。通过细节简化与视点调整,塞尚实际上是既保持了描绘事物的坚实感,同时又突出了图画平面的二维特征。如此一来,正如梅洛-庞蒂所强调的,绘画的媒介特征与可见主题的感知经验之间不再泾渭分明。因为“光线、照明、阴影、反射,所有这些被研究的对象并非完全都是现实的存在,因为它们都如幽灵一般,具有的只是视觉上的存在”[12]。
传统绘画的媒介被掩藏于主题之下乃至要“不可见”,可见的是图像的对等物和可操纵的符号。只有当连贯而逼真的图像被打乱变得陌异时,目光才能投向媒介并让其可见,这样才有可能获得对媒介载体性质的认识;或者说,符号遮蔽了人们射向承载着符号自身载体的目光,只有当符号被移除时,符号的媒介真相才会立刻表现出来。因此,在马蒂斯看来,感受只有在媒介的表现过程中才能被感知,对生命的感受与表现方式之间是不能分开的,“表现方式并不包括面部反映出来或猛烈手势泄露出来的激情”,“而是整张画的安排都具表现力的”。[1]180
尽管画家承认作为表现方式的媒介与绘画主题不可分割,但媒介自身仍然是情感表现的支撑,并没有达到要与绘画主题融合的意识。以毕加索和布拉克为代表的立体主义进一步拉近两者之间的距离,绘画的媒介与主题开始融合。这意味着绘画试图摆脱既有观念或意识形态的束缚,专注于探索艺术媒介自身的特性,并制造绘画“平面”的组合效果。立体主义者承认绘画空间是一种特殊的“平面空间”,他们对绘画空间的拓展,显然是对文艺复兴时期阿尔贝蒂以来的绘画观念(如何在二维平面上创造出三维的效果)的反转,即绘画对象必须接受平面“挤压”,然后再将它们“合乎逻辑”地画在二维平面上。基于几何学的透视法对固定视点的限制,相当于胡塞尔现象学意义的“侧显”,因为观者总是从某个固定的视角来看事物的。也就是说,多维性的隐失其实是必然情形,不可能所有的面都必须同时呈现出来。然而,“毕加索意图用多维性、不同的相互补充的景象的同时呈现,来消除我们的视角的局限性。因此,我们也能理解那种把空间性归结为平面性的趋势,立体的各个不同面似乎必须被折叠起来,必须仅仅保持在一个一目了然的平面上”[13]。毕加索力求把不同的视点统一起来,立体对象仿佛被拆开后在平面上延展开来的样子,这样一来,我们并不是什么也看不到(看似只有变形和扭曲的东西),然而事实上是我们看到的更多,我们可以同时(一目了然地)看到事物的多个“侧显”,这个看似无序与杂聚的视觉混合物,实际上是未经“视觉意识形态”调节前的景象(笛卡尔所谓上帝的直觉)。绘画主题必须与媒介自身的本质协调,即主题从或隐或显的绘画平面构造组合中以形象的方式被“看”出来,而不是外在观念的强行附加。在立体主义的拼贴实验阶段,绘画平面上的报纸、字母、木头纹理图画等拼贴要素本身就是实用物品的碎片。然而,由于平面既作为实际基底存在,又是一个符号性的表面,所以绘画表面存在一种现实物与艺术表达之间的张力。如此看来,这些“碎片”能够用双重眼光来加以观照,“一种将它们视为与线条和色彩并驾齐驱的形式元素,另一种将它们视为它们从中分离出来的那些实际内容的表达”[14]。随着材料碎片的任意聚集,媒介的可塑性变成了未加修饰的、异质的“现实”(其本性乃是分散的、混杂的、偶然的)的一种譬喻。真实材料配合着颜料所建立的抽象结构,起着接近“真正现实”的主题作用,媒介与主题的积极融合和交互影响构成布拉克所说的“新的统一体”。同样,马列维奇的至上主义“方块”是纯粹抽象的表达,是描绘直接感觉(而非感觉的外在反映)的“新符号”。方块是空间与节奏本身:“方块=感觉,白底=这感觉之外的空无”。媒介的真实性同样是被完美地策划出来:《黑色方块》不仅作为一幅画中之画,而且也作为一种对隐匿的绘画载体的突然昭示,这种载体从通常的、表面的绘画世界之中,且因为艺术家极为彰显地使用强力而脱颖出来。[15]只有当“平面”否定一切感知内容与叙事逻辑,媒介的这种极端物质性才能显现,同时这种极端物质性也才能和它所对应的绝对精神性相统一。
我们把焦点转向抽象表现主义,美国“行动画派”的绘画主题与“行为”之间的关系也得到重构,绘画的媒介即是自己的行动轨迹。以杰克逊·波洛克为代表的“行动派画家”试图挣脱“架上画”的“画框”限制,将画布挂在粗糙的墙上或放在地板上,最大限度地将身体运动与情感的自发性有机地整合在画布上。在《蓝杆》系列画中,波洛克发明的滴色画法任由各种纵横交错的颜料与脚印、烟头和碎木屑等杂物混融,远离了形象与空间的构造。此时作为真实对象的画布就成了绘画的载体,画面成了画家身体痕迹的记录。正如批评家哈罗德·罗森伯格(Harold Rosenberg)所说,“在某一个时刻,帆布开始在一个又一个美国画家眼中成了表演的舞台,而不是复制、重新设计、分析或者‘表达’一个真实或假想事物的空间。帆布上产生的不是一幅图像,而是一个事件”[16]。由于艺术家的绘画行为成了生活中偶发的“事件”,绘画作品具有“与艺术家的存在相同的形而上的本质”,因此也就打破了艺术与生活之间的界限。如此一来,绘画作品很有可能被看作是一件现实生活中的普通物品。同样值得注意的是,战后50年代的欧洲绘画艺术也从再现转向了对象本身的物理真实,开始脱离现代主义绘画的平面性规则。绘画的事实不仅停留在色彩与线条的表现力层面,而是材料与现实的直接相遇,艺术媒介的物性渐渐成为现实。意大利艺术家阿尔伯托·布里(Alberto Burri)与卢西奥·丰塔纳(Lucio Fontana)强调画布作为材料物品的整体实在性,可以直接体验,而不需要形式上的先入为主。艺术家并不把原材料的物质性所揭示的“本体”现实看做理想的或超自然的世界,而是看作单一的、真正的现实,所有东西都是由这种现实构成的。材料的实在性既作为表达内在“真实”的基础,同时又是抽象的空间概念。[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