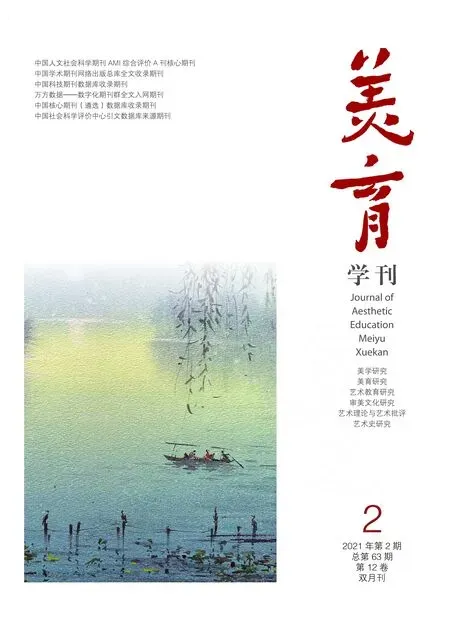宗白华美学建构中的英美思想传统
2021-12-04张泽鸿
张泽鸿
(淮阴师范学院 文学院,江苏 淮安 223300)
在中国现代美学史上,宗白华美学具有“反体系”的特征,这不仅仅是因为宗氏本人曾自喻其美学为不成系统的“思想散步”,更是因为其美学文本彰显的东方诗性特征和直觉(体悟)思维,在美学范畴的运用和话语表述上比较松散和感性,这无疑弱化了其美学文本在概念、判断和推演方面的逻辑力量。倘若借用本雅明和阿多诺的观点来看,宗氏的散步美学著述是一种具有反体系特征的“星丛式”文本。所谓“星丛式”文本,既表征了宗氏美学思想结构的散逸性和诗性,也体现了其美学思想来源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宗氏美学具有理论的多面性,从本体论看,它是生命(机体主义)美学;从艺术学看,它是艺术形上学(艺术哲学);从经验论看,它是创造论诗学。
从宗白华美学与艺术学研究所吸纳的西学资源来看,除了德国和日本的艺术学经验(1)参见拙文:《“德国经验”与“中国问题”——宗白华与现代中国艺术学演进之考察》,载《社会科学战线》2013年第12期,《“日本经验”与草创期的中国艺术学建构》,载《社会科学战线》2018年第8期。之外,还有来自近现代英美哲学传统的重要影响,这一点尚未引起目前学界的足够重视。国内学术界大多认为宗白华对英美哲学传统涉猎不深,受其影响有限,其实这是一种误解。简言之,宗白华与近代英美思想家如怀特海、佩特和帕克等人有较深的思想关联。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欧陆理性主义是宗白华吸收和借鉴英美思想传统的逻辑基础,而怀特海等英美学人的思想往往被视为一种大陆化(德法化的)英美思想。从近代英美哲学和欧陆哲学的分野来看,英美哲学以盎格鲁—撒克逊的思想传统为基础,侧重于分析哲学和逻辑实证主义,而到了怀特海等人,这种分析哲学传统与欧陆理性主义有合流的趋势。因此,宗氏接受英美学者的思想也是有所侧重的,既侧重于欧陆化的一面,也寻求与东方思想的互通。
宗白华在大约写于1925—1928年的《美学》讲稿的附录部分,列有“关于艺术论之参考书”共计12种,其中包括《阿波罗艺术史》、克罗齐的“艺术表现说”、帕克的《美学》、佩特的《文艺复兴》、罗斯金的《威尼斯石头》、葛赛尔的《罗丹之谈话》、立普斯的《美学》以及黑田鹏信的《艺术学纲要》、瑞恰兹的《文学批评原理》等。[1]494笔者认为这是考察宗白华美学与艺术思想形成的重要来源和依据,从中可以见出,英国的怀特海、佩特、鲍桑葵,美国的帕克以及英美“新批评派”的瑞恰兹等人都或多或少地影响到宗白华学术思想的建构和发展。在20世纪20至30年代,现代美学家帕克的《美学原理》曾被当时任教于中央大学的宗白华当作《美学》讲义的主要参考书。帕克强调的“艺术即表现”以及艺术品要求生命贯注的观点[2]12-24,被宗白华所认同和吸收。这里仅以对宗氏思想影响较大的怀特海、佩特和帕克为例,来分析和论证宗白华与他们之间的思想脉络,以期见出英美思想传统在宗氏美学思想建构中的影响维度。
一、怀特海机体主义对宗白华生命美学的影响
宗白华的美学是以生命为本体的境界论美学,这种生命本体美学的营构深受英国现代哲学家、新实在论(Neo-realism)的代表人物怀特海(2)怀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1861—1947)是20世纪英国著名的哲学家,他在哲学、数学、逻辑学、教育学等领域著述颇丰。他是新实在论的代表人物,“过程哲学”(又称历程哲学、机体哲学)的创始人。1929年出版的《历程与实在》(Process and Reality)一书是其过程哲学体系的奠基之作。机体哲学的影响和启发。20世纪的英美哲学主要是以反形而上学的实证主义和分析哲学为其主流,在这个思想传统中,怀特海可谓是一个重要的反传统者,他不囿于分析哲学和实证主义的方法论局限,试图建立一个集宇宙论、人生论与价值论于一体的“新形上学”体系,这就是所谓的“过程哲学”(或曰“机体哲学”)。这个全新的机体主与哲学曾对现代中国哲学家产生了很大的吸引力。(3)受到怀特海机体哲学影响的中国现代哲学家主要有贺麟、方东美、宗白华等。
怀特海的“过程哲学”(process philosophy)又称为“有机哲学”(philosophy of organism),它是一种主张世界即是过程,要求以机体概念取代物质概念的哲学体系。过程哲学涉及自然科学、美学、伦理学和宗教学等领域,“博大兼备,综贯诸家”。怀特海的《历程与实在》曾被誉为20世纪的“纯粹理性批判”。怀特海曾说,他的哲学“东方意味特别浓厚”,其著作中“含蕴有中国哲学里极其美妙的天道(Heavenly order)观念”。[3]290这也是怀特海及其哲学在20世纪中国颇受欢迎的重要原因。
怀特海认为,世界是由“实际实有”(actual entity)构成的,所谓“实际实有”又称为“实际事态”(actual occasion)(4)贺麟在《怀特海》一文中曾将actual entity 译为“实有”,将actual occasion译为“实缘”,颇切怀氏本义,可惜未见学界广泛采用。参见《贺麟选集》,张学智编,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01页。,它是“构成世界的终极实在事物,在实际实有背后不可能找到任何更为实在的事物”[4]18。实际实有就是“点滴的经验”,是“经验的搏动”。这强调了两点:其一,实际实有是经验者与经验的交织体;其二,实际实有是不断变化和运动的。“实际实有”之所以是变化生成的,是因为它们内部有推动力,怀特海称之为“创造性”(creativity)。实际实有的变化运动体现为:它不断吸收其他的实际实有,并被其他实际实有所吸收。怀特海认为:“把实际实有看做是变化中的不变主体,这一观念要完全抛弃。这一点对于机体哲学的形上学学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实际实有既是进行经验的主体,又是它的诸经验的超体。它是主体—超体,两者中任何一个都不能片刻被忽视。”[4]29由此可见,一个实际实有在创造性的推动下生成演化,它既“摄入”(prehend)其他的实际实有,又被其他实际实有所摄入,它总是以一个双重身份而存在,即既是主体又是客体,怀特海以“超体”(superject)一词来指称它。怀特海认为,每一个实际实有都有一个物质极和一个精神极,因此,即使是最低级的实际实有在理论上也有一定的自由、一定的经验,因此它是“有机”的。实际实有构成不同的群集,群集再聚合成更大更高级的群集,直至构成整个宇宙。而所谓的“过程”(process),就是由实际实有构成群集,再由群集构成更大群集直至整个宇宙的动态历程。怀特海指出:“实际世界就是一个过程,该过程就是诸实际实有生成的过程。因此实际实有便是创造物。”[4]22由于宇宙的基本单位“实际实有”处于变化的过程之中,因此整个世界表现为一种创造和活动的过程。这一宇宙论是对传统的唯物论、唯心论和二元论的彻底颠覆。怀特海认为,心物之间并无严格的不可逾越的鸿沟,只不过“高级的近心而低级的近物”[3]297,宇宙是一个“由物到心”层层连接的由浅而深的整体。每一个实有都有“心物两极”,心物相连相通,因此“从物极看来,它在时空之中;从心极看来,它自有它的目的、意义和价值”[3]302。怀特海认为,“身和心”的统一是构成一个人的明显的复合体,我们的身体经验是存在的基础。“人体是自然界的一部分,由于有了它,人的经验的每一瞬间都密切配合。在身体的现实存在和人的经验之间存在着流进流出的因素,因此每一个因素都分有其他因素的存在。人体提供了我们对自然界的现实事物的相互作用的最密切的经验。”[5]157即身体为情感和感性活动提供基础。同时,身体的存在还需要生存的环境,因此,“身体和环境就存在同一”[5]142,正如身体和心灵的统一才成为人一样。在怀特海看来,不仅人的身体跟自然界有关,人的精神和自然界也不能截然分离,因为我们是“身心一体”的生活于自然界之中。因此我们应当把精神作用看作是属于构成自然界的因素。
不仅如此,怀特海反对“自然的两橛化”(bifurcation of nature),认为自然是“有机的全体”,将自然和生命的分开是不能被理解的,只有两者的融合才构成真正的实在,亦即构成宇宙。怀特海指出,如果我们不把自然界和生命融合在一起,当作真正实在的事物结构中的根本要素,那二者同样都是不可理解的;而真正实在的事物的相互联系以及它们各自的特征构成了宇宙。一方面,怀特海认为自然界与生命是融合的,另一方面,是生命概念包含自然界概念,而不是相反。按照怀特海的宇宙创进理论,“生命之向未来转化属于宇宙的本质”[5]133,因此把自然界看作是一种精致的事实是荒谬的,宇宙处在不断的转化和绵延之中,生命的特征就是永远处在“绝对的自我享受”“创造活动”和追求“纯粹理想”的过程之中。这就是怀特海“机体主义”思想的主要内涵。
近代以来“空无所有”的空间学说已被一种“力场”、一种“不断活动之场”的观念所取代。[6]82怀特海强调,整个空间宇宙就是一个“力场”,一个不断运动的“场”。在这个“场”中,“物质”与“能”是同一的,所谓“能”就是一种纯粹的“活动”。自然界就是各种活动的相互关系的舞台,一切事物、活动以及活动之间的相互关系都是变化的。[5]124因此也可以说,自然界充满着“生命力”,实在事实在不断产生。而“过程则被当做活动及其各种不同因素之间的内部关系的复合”[5]128。从怀特海的机体主义思想来看,他主要强调了世界即过程(流动)、宇宙生命是有机体,这彰显了三个递进的意涵:物质(自然)与精神一体化、人的身心一体化、整个世界是生命的一体化。一言蔽之,所谓机体主义就是一体俱进的生机世界。
宗白华非常欣赏怀特海的机体主义思想,早在20世纪20年代,他就曾说:“叔本华发现盲目的生存意志,而无视生命本身具条理与意义及价值(生生而条理)……至今怀德特之哲学乃显以一‘全体性的生机哲学’,调和‘价值界’与‘数理界’。”[1]586在宗白华看来,近代哲学从康德、黑格尔到叔本华,他们的哲学(真)虽然触及道德(善)与艺术(美),但是没能完全贯通一体,将三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旁观统贯”,实现生命整体的观照。近代哲学家中唯有怀特海真正打通了真善美的三界割裂,实现了理论与价值的融通。宗白华扬弃叔本华的盲目的“生命意志”,转而寻求怀特海的有机哲学(过程哲学)与中国生命哲学的会通。因为怀特海过程哲学的基本观点就是认为“自然是活的”,他提出的“超体”概念具有自然与生命统一的审美化色彩,他要求用“自然界和生命的融合”[5]132来弥补我们关于物质自然界概念的缺陷,并强调以“审美直觉来补充逻辑”[7]对于当代生活的重要性,建构起真正的机体主义宇宙观。
正因为机体主义哲学有着对宇宙生命精神的肯定,因此怀特海对诗和艺术也非常推崇,因为浪漫主义以来的美学坚持艺术是表现生命情感的观点,因此,怀特海认同艺术表现生命、“哲学类似于诗”[5]238的诸观点,认为哲学应该从诗人那里听取教训;希望“能将宗教经验和艺术思想与哲学调和,共冶于一炉而得能够充分满足人类精神生活”[3]295。怀特海的这些观点对于信奉东西方浪漫主义生命哲学的宗白华来说无疑具有极大的吸引力,但怀特海并非浪漫型的哲学家,他对生命机体的论证主要理据来源是近代数理逻辑。美国当代哲学家M.怀特在《分析的时代》中曾精辟指出,克罗齐的“历史与艺术”、柏格森的“实践和本能”与怀特海的“生命、过程和有机体”等,都是充满浪漫色彩的主导概念,他们或者以此来建构关于宇宙的天体图式,或者表示对人类存在的大彻大悟。[6]12,79他们对“直觉”和“事物的整体性”有相似的偏好,并反对20世纪开始流行的分析哲学趋势,而怀特海是20世纪超出这些门户之限的哲学家,他超越柏格森的地方在于,他试图用近代物理学和数学的成果来论证关于过程及活动的哲学。怀特海认为自然由诸“显相”构成,它们之间有一种“相互内在”的原理(doctrine mutual immanence),每一“显相”都是另一“显相”(5)自然界的一切“显相”(occurrences)可以大略分为六类:第一类是人的存在,即身体和心灵。第二类是除人之外的所有动物的生命。第三类是包括一切植物的生命。第四类由单细胞生物构成。第五类包含一切大规模的无机组合(inorganic aggregates)。第六类由现代物理学的微观分析所发现的体积极小的显相所组成。参见怀特海:《思维方式》,刘放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215页。的本质因素之一。换句话说,“自然是活的”,自然充满生机,自然中所有的一切作用都是互相影响、互相依赖并且互相转化的。
宗白华吸收了怀氏机体主义的部分思想精髓,并将其融汇到其早期的美学和艺术观念中,但他舍弃了怀特海的基于数理逻辑而建立起来的“实际实有”“经验的流动”诸概念,从而将怀氏的机体主义过程哲学改造成生命流衍的浪漫主义哲学,二者的区别也是明显的:前者是理性的、科学的、现代的,后者是偏非理性的、审美的、古典的。宗白华在美学上是一个本质主义者,他所理解的艺术必然是显现真理的本质,如宗氏认为:“一个艺术品里形式的结构,如点、线之神秘的组织,色彩或音韵之奇妙的谐和,与生命情绪的表现交融组合成一个‘境界’。”[8]59宗氏认为艺术的模仿不是徘徊于自然的外表,乃是要“深透”自然真实的必然性。因为艺术与哲学为邻,它是抵达真理的特殊途径,从本质而言,艺术不过是披上了一件“美丽的外衣”的“真理”。另外,艺术品须能超脱实用关系之上,自成一“形式的境界”,自织成一个超然自在的有机体。“这个艺术的有机体对外是一独立的‘统一形式’,在内是‘力的回旋’,丰富复杂的生命表现。于是艺术在人生中自成一境界,自有其组织与启示,与科学哲学等并立而无愧。”[8]62艺术同哲学、科学、宗教一样,共同启示着宇宙人生的真理,艺术主要是借助于幻象的表征和主体的直观。宗白华这种具有古典主义和本质主义倾向的艺术观念都是受到了怀特海“精神与自然也不能截然分离”的机体主义之影响。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怀特海本人是英美分析哲学传统下的思辨哲学家和唯实论者,他的机体主义本质上是一种理性思辨哲学,而不是非理性的生命哲学。宗白华在嫁接、融会怀特海与儒家思想(《易经》生命哲学)的时候,似乎不太注重对二者做严格的区分,这是一种的“六经注我”“熔众家于一炉”的哲学方法。
二、佩特的唯美主义与宗白华的艺术哲学
宗白华的美学也是一种以艺术审美分析为主的艺术形上学,这种艺术形上学思想与宗氏特别推崇佩特的音乐唯美主义有密不可分的关系。现代艺术学起源于西方,在德语中的名称是“一般艺术学”或“艺术科学”(science of art)[9],英美学界没有类似德语国家的“艺术学”概念,他们大多使用“艺术哲学”(art philosophy)或“艺术理论”(the art theory/the theory in art)等术语。宗白华的艺术学理论主要是受到德国“艺术科学”的影响,但英美学界的艺术哲学和艺术理论也对他的艺术形上学有潜在的启示和影响。
在19世纪70年代,欧洲大陆兴起了一股唯美主义美学思潮,尤其在英法两国最为盛行,代表人物有佩特和王尔德等。唯美主义宣扬艺术至上,标举“为艺术而艺术”,强调艺术的形式主义和审美的非功利性。青年时期的宗白华也曾宣称自己信奉一种“唯美的人生观”,他的唯美人生观和艺术理念,应当说与英国的唯美主义以及魏晋名士美学都有密切关联,后来又逐渐转向魏晋风度的一面。这里简要分析宗白华在一些具体的美学观和艺术观上对佩特的认同感。
沃尔特·佩特(Walter Horatio Pater,1839—1894)是英国美学家、艺术理论家,也是唯美主义美学的代表人物。其代表作《文艺复兴——艺术与诗的研究》被视为唯美主义的宣言。在美学观念上,佩特热烈地崇拜美,把美看作是一种至高无上的价值。在他看来,美是一种脱离现实社会的现象;美只在于形式,与本质、内容、经验无关。在艺术观念上,他反对古典式的模仿说,认为艺术就是对于艺术家个人的印象的永恒不断的“编制和展开”[10],艺术就是把艺术家的主观印象表现为形式上的美。由于佩特对艺术的形式高度重视,认为艺术应当从形式开始而追求“纯粹”,艺术形式占据主导地位,艺术形式能渗透到主题和内容的各个部分,因此,艺术总是从形式到思想感情,而不是相反。佩特说:“艺术总是努力于不受单纯的信息的支配,力图变为纯粹感觉的艺术,力图去除对于其主题及材料的责任;在理想的诗歌和绘画的范例中,作品的组成要素完美地结合在一起,材料与主题不再仅打动理智,形式也不再仅打动眼睛和耳朵,而是形式与内容结合或者说统一在一起,每一种思想和情感都与其可感觉到的相似物或象征物相伴而生,它们为复杂的感知过程,即‘想象性推理’提供单一的效果。”[11]174成功的艺术作品只要具有一种特定的形式也就具有了一种内在的精神。同时,佩特也主张内容与形式的密不可分,不过这种统一是以形式占据主导地位为前提的。
佩特推崇音乐的审美理想,他认为音乐的形式与内容是完美融合的,音乐可以作为一切“艺术的典范”,因为“在音乐中,我们不可能将形式与素材或材料区分开来,将主题与表现手法区分开来”。[12]他还强调说:“音乐最完美地实现了这一艺术理想,实现了这一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统一。在其最圆满的时刻,目的与方法、内容与形式、主题与表达方式之间不再有差别,他们的本质互相完全渗透融合,因此,所有的艺术或许都有可能被认为倾向于且渴望着达于这种完满的状态。与其说在诗歌中,不如说在音乐中,能够真正发现完美艺术的典型或尺度。因此,尽管每种艺术都有其不能言传的因素、不能翻译的效果和达于‘想象性推理’的独特方式,但是艺术仍然可以被描述成一种在音乐的规律或规则的支配下,以达于只有音乐才能完全达到的境地的持续不断的努力,对新旧艺术作品进行把握的审美批评的首要功能之一,就是评价艺术品在这个意义上,与音乐的规则接近的程度如何。”[11]174-175因此,在佩特看来,音乐可以实现内容与形式完满统一的艺术理想,是一切艺术渴望达到的完满状态。
深受佩特的艺术思想影响,宗白华曾多次援引佩特的观点强调“一切艺术趋向音乐的状态、建筑的意匠”,因为音乐和建筑的秩序结构最能直接地启示宇宙的和谐与节奏感。这个观点显然来自佩特,佩特有言:“所有艺术通常渴望达于音乐的状态。”[11]171宗白华最为欣赏这句话,他将这个观点结合到中国艺术的审美特征研究中,由此提出了一种“乐舞为众艺之魂”的观点。宗白华认为,音乐(时间艺术)与建筑(空间艺术)的结合就是“舞”(时空一体、动静结合),舞是最高度的韵律、节奏、秩序、理性,同时是最高度的生命、旋动、力、热情,它被视为“宇宙创化过程的象征”。“舞”作为最紧密的“律法”和最热烈的“旋动”,能使幽深玄冥的生命体验境界“具象化、肉身化”。宗白华进而指出,舞是“中国一切艺术境界的典型”[8]369。中国的书法和画法都趋向于“飞舞”,庄严的建筑中也安排有飞檐来表现“舞姿”。在“舞”的艺术形式中,建筑严谨的秩序流动而为音乐,浩荡奔驰的生命收敛而为韵律,动静合一的“舞”的确可以表现出“宇宙的创化”精神。
佩特认为绘画与音乐具有相通性,并且绘画追求音乐的典范之美,以达到音乐的原则为最高的理想。他在其《文艺复兴》一书中论述乔尔乔内画派时说:“所有这样的艺术真正追求的是音乐的法则或状态。”[11]185一方面,一些最令人愉悦的音乐似乎总是接近于形象和绘画;另一方面,绘画、建筑、十四行诗、浮雕艺术等所有这些艺术通常渴求符合音乐的原则;“音乐是其中的典型,或者说是理想化的完满艺术,是所有艺术、所有艺术特质或部分艺术特质的巨大的‘另一种努力’的目标。”[11]171宗华受到佩特的启发,在他的艺术研究中,也力求打通艺术门类的界限,寻找它们之间具有统摄性的共同规律。譬如他反复强调中国艺术的“灵的空间”“生生而条理的节奏”“音乐化的宇宙”等,其实都是以“音乐”为主导的艺术美的共通性法则。在这里,宗氏试图以乐、舞为核心,建立中国艺术哲学(形上学)体系。
三、帕克的表现主义与宗白华的创造论诗学
宗白华的美学常常以非思辨性的诗性文本为载体,擅长透过讨论文艺创造问题来表征一种审美精神,因此,他的美学研究在方法论上表现为一种诗化的倾向,并建构了一种基于直觉体验的生命创造论诗学,这个创造诗学与帕克的表现主义美学有思想渊源关系。
在文艺创作论上,宗白华先后提出了生命创造(生命表现)、“心源”创造、“虚实结合”的创造、“移情”创造等学说。西方文化史上的“创造”概念原本是神学家们用来描述上帝和世界之间的关系的[13],从无到有的“创造”是属于上帝的能力,上帝不用凭借任何东西“创造”了世界;而艺术作为一种人工技艺,它是人借用各种现有的材料因素“制作”(making)出来的,而不是凭空“创造”的结果。美学史上后来也用“创造”来指艺术的生产过程,因为人类本身就有“一种创造的天性”,艺术的“创造并不意味着抛弃这个世界,而的确是在其中生存”[14]。由此,“创造”论摆脱了神学的色彩而走向人学。艺术不是源于神启,创造不是代神立言,艺术生产并非是艺术家以“诗性直觉”的方式继续神的创造性劳动,而是艺术家面对宇宙人生的一种自觉的审美建构活动。宗白华认为,艺术在于表现生命、传达情感,艺术品要表现宇宙人生的生命精神。一切艺术创造问题,归根结底就是如何将无形式的材料造为有形式的,能“表现”主体心中另一个真实的世界。他说:“大自然中有一种不可思议的活力,推动无生界以入于有机界,从有机界以至于最高的生命、理性、情绪、感觉。这个活力是一切生命的源泉,也是一切‘美’的源泉。”[1]310因此,艺术的功能在于创造真实的生命世界,表现生命精神之美。宗氏的创造论一方面源于他的生命本体美学,另一方面又受到中国现代“唯生论”艺术观以及西方表现主义艺术观的双重启发。
宗白华关于“生命表现”的文艺思想是接着克罗齐和帕克的表现主义美学说的。宗氏在20世纪20至30年代的《美学》与《艺术学》讲稿中,将克罗齐的“作为表现的艺术”理论和帕克于1920年初版《美学原理》(ThePrinciplesofAesthetics)列为重要的参考书[1]494。亨利·帕克(Dewitt Henry Parker,1885—1949)是美国现代哲学家和美学家,主要美学著作有《美学原理》《艺术分析》《经验与实体》等。从唯心主义出发,帕克认为存在即经验,把世界等同于“经验”,并且把经验还原为“自我”,认为任何“经验”都是独一无二的。不存在一般的经验,只存在以“自我”为中心的经验。因此,帕克认为艺术与“经验”有密切联系,“艺术即是表现,不单单是事物或观念的表现,而且还是自身具有价值和独立意义的具体经验的表现。艺术是纳入令人愉快的、有高度组织性的感官媒介中并且在那里化为传达和思考的对象的那种经验。它的价值在于抱着同情态度在想象中去把握和保存生活”[2]46。这个艺术即经验的表现,艺术的价值在于以同情态度去把握人生的观点,不仅启发了美国实用主义美学先驱杜威的“艺术即经验”学说的产生,也对宗白华的艺术创造论和艺术鉴赏论影响甚深。
帕克的艺术观念主要在于提出了“艺术即是表现”的理论,同时他指出,“虽然每一件艺术作品都是一个表现,但并不是一切表现都是艺术作品”[2]12。这就是艺术与表现的本质区别。在艺术即表现的基本学说中,帕克还指出艺术要贯注生命、表现生命,他说:“我们对任何艺术作品提出的最后的要求,都是要它有生命。对我们来说,能够有生命的东西就可能是美的。但是,任何作品只要没有把艺术家的生命贯注到作品里面去,或者不忠于它自己的内在逻辑,就不能够把我们的生命吸引到作品里面去。”“一件艺术作品的最能创造生命的要素之一就是形象。在艺术中,处处都有通过形象把观念加以充实,使之具体而鲜明的倾向。”[2]64艺术的生命精神必须通过形象(意象)这个基本要素才能完成。帕克强调艺术要表现生命感,以及艺术生命基于形象建构的观点都对宗白华的艺术观产生了深刻影响。
宗白华有一个关于艺术的非严格定义:“艺术就是艺术家的理想情感的具体化,客观化,所谓自己表现(self-expression)。”[1]189艺术的源泉是“一种强烈深浓的、不可遏止的生命情绪”。艺术是自然中最高级、最精神化的创造,艺术是人类精神生命贯注到自然(物体)中,使自然精神化、理想化。“美”与艺术所表现的“是生命内部最深的动,是至动而有条理的生命情调”[8]98。正如帕克将整个世界视为“生命的经验”,宗白华将世界视为“生命的情调”。宗白华强调艺术是“生命的创造”,而不是单纯的模仿和再现对象世界,这种生命的创造本质上是将生命体验对象化。他认为:“艺术家要模仿自然,并不是真去刻划那自然的表面形式,乃是直接去体会自然的精神,感觉那自然凭借物质以表现万相的过程,然后以自己的精神、理想情绪、感觉意志,贯注到物质里面制作万形,使物质而精神化。”[1]313模仿并不等于表现世界的真实,必须经过艺术家的心灵体验,再借助物质材料表现出来,是物质的精神化(生命化),这才是真正的艺术品。在宗白华看来,模仿是只能得其表面,体验与表现的结合才能创造出艺术的生命。
帕克认为艺术是对经验的表现,宗白华认为艺术是对生命体验的再创造。艺术家需要特别的才能和眼光,能在普通人的视野中见出不一样的世界,“一个人的面目中,藏蕴着一个人过去的生命史和一个时代文化的潮流。这种人生界和自然界精神方面的表现,非艺术家深刻的眼光,不能看得十分真切”[1]314。艺术家可以在平凡的一枝花、一块石、一湾泉水中表现出一段“诗魂”。宗白华还说:“诗人具有别材别趣,尤其具有别眼。包括宇宙的赋家之心反射出的仍是一个‘诗心’所照临的世界。这个世界尽管十分客观,十分真实,十分清醒,终究蒙上了一层诗心的温情和智慧的光辉,使我们读者走进一个较现实更清朗、更生动、更深厚的富于启发性的世界。”[8]407这里的“诗人”是指广义上的一切艺术家,他借用了尼采的日神精神与酒神精神来说明醒与醉、静与动等不同类型的观照法对人生境界进行观照和表现。日神与酒神,醉与醒,构成了“艺术世界”。艺术创作中的诗人心灵要在两个极端来回穿越,诗人一方面“善醒”,即“他能透澈人情物理,把握世界人生真境实相,散布着智慧,那由身心体验所获得的晶莹的智慧”[8]407,另一方面诗人更要“能醉,能梦”,在“由梦而醉”的过程中,诗人方能暂脱世俗,而坠入变化迷离、奥妙惝恍的宇宙人生的体验境地之中。艺术家在茫茫宇宙、渺渺人生中体验到一种无可奈何的情绪、无可言说的沉思、无可解答的疑问,令人“愈体愈深”,因此艺术的体验境界堪比宗教的体验境界,这是一种欲解脱而不能、“情深思苦”的至境。
从艺术创作心理看,这样一个因体验至深而难以言传的境界,已不是清晰的逻辑文体所能完全传达出来的,因此,艺术家往往用象征或比兴的手法来“传神写照”。艺术家“凭虚构象,象乃生生不穷”,通过对声调、色彩、景物的调和运用,推陈出新,创造出迥异于日常生活的新境界。如唐代诗人戴叔伦所说:“诗家之景,如蓝田日暖,良玉生烟,可望而不可置于眉睫之前也。”[15]这是说“艺术意境”要和主体保持适当距离,在“迷离惝恍”之中构成“独立自足、刊落凡近”的审美意象,这样的意象才能象征那难以言传的“情和境”。中国的艺术家最善于体会造化自然的微妙的生机动态,创造出“浑沌贞粹”的境界。
宗白华认为,中国诗人善于“传神写照”,将审美经验予以意象化,此即所谓“造境”。这是帕克的“将经验予以表现”说的中国化表达。宗氏曾言:“古代诗人,窥目造化,体味深刻,传神写照,万象皆春。王船山先生论诗云:‘君子之心,有与天地同情者,有与禽鱼草木同情者,有与女子小人同情者,有与道同情者——悉得其情,而皆有以裁用之,大以体天地之心,微以备禽鱼草木之几。’这是中国艺术中写实精神的真谛。中国的写实不是暴露人间的丑恶,抒写心灵的黑暗,乃是‘张目人间,逍遥物外,含毫独运,迥发天倪’(恽南田语)。动天地泣鬼神,参造化之权,研象外之趣,这是中国艺术家最后的目的。所以写实、传神、造境,在中国艺术上是一线贯串的,不必分析出什么写实主义形式主义,理想主义来。”[8]323艺术的根基在于对万物形象之描摹,并从形象中感受其“灵魂”,灵魂寓于线条、色调及体积之中。
综上所述,由于宗白华本人对英美哲学传统的兴趣不是太浓厚,他早年的西学背景和学术兴趣主要还是欧陆哲学和唯理论,因此他在接受英美哲学思想的时候,必然是有所侧重和抉择的。总的来说,怀特海的机体哲学、佩特的诗化哲学和帕克的经验主义,都比较符合他的学术趣味,是其建构美学思想可以汲取的重要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