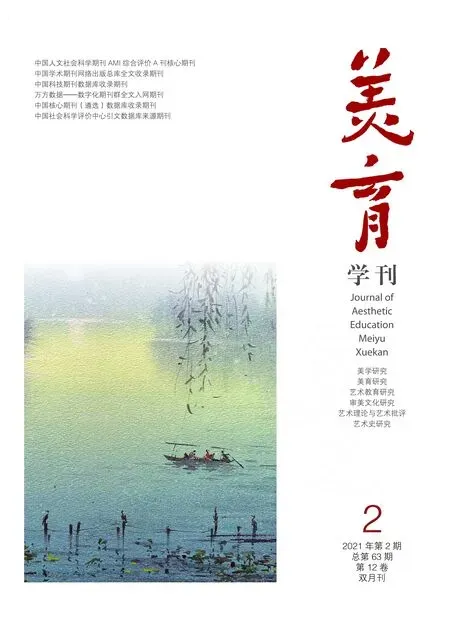日本明治时期大学的美学课程及其讲座的诞生始末
2021-12-04郑子路
郑子路
(江西师范大学 美术学院,江西 南昌 330022)
19世纪后半期以降,随着“西学东渐”的扩展与推进,“美学”这门“新学”逐步进入了东方人的视野。在日本,最早对“美学”进行介绍的是启蒙思想家西周(1829—1897)。他将“美学”译为“善美学”(《百一新论》)、“佳趣论”(《百学连环》)、“美妙学”(《美妙学说》《奚般氏心理学》),并在《美妙学说》中对自身的美学思想进行了一次体系化的构建。(1)《百一新论》刊行于1874年,是西周于1866年至1867年在京都洋学私塾的特别讲义。《百学连环》则是1870年西周在东京“育英舍”的讲稿,今天我们所能见到的版本是听讲生永见裕的笔记。《美妙学说》的发表时间不明,有1872年(麻生义辉)、1877年(大久保利谦)、1879年(森县)等几种不同的说法。笔者认为森县([日]森県:「西周『美妙学説』成立年時の考証」『国文学:解釈と教材の研究』第14巻6号,1969年,第206頁)的说法比较准确,应是1879年1月13日西周在“宫中御谈会”上的讲稿。理由主要有二:(一)从该书强调美学的功利性以及措辞表现来看,受众为天皇和各大臣的可能性很高;(二)对于“美学”的译法与1875年至1878年刊行的《奚般氏心理学》相同。西周的这次尝试虽然谈不上严谨,也并不完备,但却是日本最早的、立足于本国文化的美学体系建构,标志着日本近代美学的开始。随后,在文部省翻译局的嘱托下,另一位启蒙思想家中江兆民(1847—1901)于1883年至1884年翻译出版了法国人维隆的著作,命名为《维氏美学》(Eugène Véron:L’esthétique,1878),第一次使用了“美学”这个汉字译名。尽管在最初的对于“美学是什么”的认知阶段,启蒙思想家、文艺评论家们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甚至一度还造成了一种“文学家、文艺批评家比学院派研究者更具影响力”[1]的现象,但真正促使美学在日本生根发芽并最终得以延续下来的,却是各大学对于美学学科的开设,即所谓的学院派美学的成立与发展。
一、日本讲座美学的诞生
日本的近代化教育,始自1872年(明治五年)的“学制颁布”。该年8月,明治政府颁布了首个关于学校制度的教育法令,效仿法国的学区制度,将日本全国分为数个学区,在学区内设置各级学校,旨在推动全民教育。在这之前的江户时代,虽然并没有明确的学校制度,但各藩均设有针对武士子弟的藩校、家塾或乡学以及针对庶民子弟的寺子屋。而作为名义上的中央政府的江户幕府,也设置了诸种高等教育机构,用以培养各类顶尖人才,如为培养儒学人才而设置的“昌平坂学问所”(后改名为学问所、昌平学校)、为培养国学人才而设置的“和学讲谈所”、为培养医学人才而设置的“医学馆”、为培养西学人才而设置的“藩书和解方”(后改名为洋学所、藩书调所、开成所)等。现存于西周家的书写于“藩书调所”时期的《西周哲学讲义案》,可以看作是“日本西方哲学研究的第一声”[2]40。
1877年4月12日,由天文方、昌平坂学问所(亦称昌平黉)、蕃书调所、昌平学校、开成所等旧制机构合并改编而成东京大学,正式成立。成立之初的东京大学设置有法学部、理学部、医学部、文学部四个学部,文学部中设有第一科“史学、哲学及政治学科”与第二科“和汉文学科”。1881年9月,哲学科单独成为一科,下设心理学、世态学(社会学)、西方哲学、印度哲学、中国哲学、审美学等课程。1886年3月,日本文部省进一步颁布《帝国大学令》,由四个学部组成的东京大学增设工科,成为五大分科大学。文学部也由此升格为由哲学、和文学、汉文学、博言学(言语学)四科组成的文科大学,“审美学”也随之由一门课程升格为哲学科下单独开设的一门专业。从东京大学的创建到升格为文科大学的这段时期,是日本讲座美学的第一阶段,也可称之为史前期。在此阶段,美学并未从哲学中独立出来,仅作为西方哲学课程的一个组成部分,由从美国学成归国、主攻斯宾塞(Herbert Spencer,1820—1903)派社会学的外山正一(1848—1900)以及特聘的数名外国教师(お雇い外国人)讲授。
外山正一13岁进入蕃书调所学习英文,16岁赴英后又于18岁赴美留学,在密歇根大学获得了哲学和理学学位。归国后,他开创了日本首个社会学讲座,并历任东京大学教授、文科学长、大学总长、文部省大臣等职。他终身致力于进化论、斯宾塞学说的介绍,创设罗马字学会,推动音乐、绘画、演剧的改良,是日本近代诗的先驱。通过他晚年发表在《哲学杂志》第11卷154号上的论文《关于人生目的的我信界》(「人生の目的に関する我信界」),我们大致可以了解到他对于人生以及哲学的思考。作为当时为数不多的留学生,外山主讲哲学、史学和英语,与主讲逻辑学和东方哲学史的井上哲次郎(1856—1944)、主讲心理学的元良勇次郎(1858—1912)、主讲伦理学的中岛力造(1858—1918)共同组成了东京大学哲学科最初的教授团队。据《东京大学百年史》记载,东京大学的审美学课程就是由外山于1881年首次开讲[3]588。虽然,1893年讲座制正式确立后,外山转为负责社会学讲座,但负责哲学及哲学史第一讲座的井上哲次郎却认为,“在起初的数年,外山将穆勒(John Stuart Mill,1806—1873)、斯宾塞、贝恩(Bain Alexander, 1818—1903)等人的哲学史作为教材,讲授哲学和逻辑学,与日本哲学研究的兴盛不无关系”[4]35。作为东京大学哲学科早期毕业生的高山樗牛(1871—1902),也在后来追忆外山的文章中评价道:“作为学者,外山博士的博学是日本人中极为罕见的。”[5]562
但是不得不说,与在文艺改良运动以及教育改革方面取得的成就相比,外山在美学方面并没有太多值得夸耀的成绩。1890年4月27日,他在明治美术会发表了名为《日本绘画的未来》的演讲。但演讲稿登报后,却遭到了刚从德国留学归来的年轻军医森鸥外(1862—1922)的猛烈批评。这次“论争”史称“画题论争”,与随后的“审美生活论争”一样为历代史家所重视。但与其他论争不同,画题论争完全是有效地运用了美学原理论的森鸥外(1862—1922)的独角戏。无论森鸥外如何地挑衅或变换方法攻击,作为学界领袖的外山始终保持沉默。这或许是外山的策略,但外界观感普遍认为是森鸥外取得了该次论争的完胜。由外山兼任东京大学最初的美学讲师,一方面固然是出于他个人对于文艺的强烈热爱以及自身所具备的较高的美学素养,另一方面也凸显了当时日本美学界人才的匮乏。
针对这样的情况,东京大学积极地在海外物色人才,并于1882年起将审美学课程改为由外籍教师担任,主要有美国人斐诺洛萨(Ernest Francisco Fenollosa,1853—1908)、英国人库珀(Charles James Cooper,生卒年未详)、美国人科诺克(George William Knox,1853—1912)、德国人巴斯(Ludwig Busse,1862—1907)、俄国人凯倍尔(Raphael Koeber,1848—1923)等。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878年作为东京大学文学部首位外籍教师赴日任教的斐诺洛萨,以及自1893年起在东京大学任教长达21年之久的凯倍尔。其他几位外籍教师由于任期较短,所以与他二人相较,并没有留下太多的记录和资料。据现有的资料可知(2)[日]伊藤吉之助·池上鎌三:「第八章 哲学科」『学術大観 総説·文学部』東京帝国大学,1942年,第324頁;『早稲田文学』1891年11月号,第68-72頁;『早稲田文学』1892年10月号,第18頁;井上哲次郎:「ラファエル·フォン·ケーベル氏を追懐す」『哲学雑誌』第438号,1923年,第60頁。:库珀、科诺克和巴斯在东京大学任教的时间分别为1880年4月至1881年7月、1886年9月至同年12月、1887年1月至1892年12月。库珀使用《纯粹理性批判》的英文版,将康德哲学作为教学中心,开创了日本康德研究的先河[2]63-64;科诺克从汉密尔顿学院毕业后进入神学院学习,并于1877年作为基督教的牧师被派至日本,先后在筑地大学校和东京一致英和学校担任英文、神学和心理学的讲师。1886年,他接任斐诺洛萨,在东京大学短暂地教授哲学和审美学。在东京大学讲授审美学期间,他使用的参考书是威廉·吕布克(Wilhelm Lübke,1828—1893)的《美术史大要》(HistoryofArt,1881),主张将事实、法则与原理的调和作为“圆满的美”;巴斯先后求学于莱比锡大学、因斯布鲁克大学、柏林大学。1887年起,执教于东京大学,教授哲学和审美学,着重于新康德学派的先驱洛采(Rudolf Lotze,1817—1881)的美学理论,提倡新形而上学,主张将自然科学的立场与观念论的世界观进行调和。归国后,他先后转辗于柯尼斯堡大学、明斯特大学,著有《洛采氏伦理学一斑》(「ロッツェ氏倫理学一斑」)(《哲学会杂志》1888年第12号)等。
二、斐诺洛萨的美学讲义
斐诺洛萨出生于美国马萨诸塞州,出生那年正好是“佩里黑船”叩开日本国门的1853年。1874年,年轻的斐诺洛萨以第一名的成绩从哈佛大学哲学系毕业,并短暂地在波士顿美术馆工作。1878年,经动物学家默尔斯(Edward Morse,1838—1925)介绍,赴东京大学任教。在哈佛大学学习期间,斐诺洛萨极为推崇斯宾塞的社会进化论,一手创建了“斯宾塞俱乐部”,并深受黑格尔哲学的影响。来日后,他最初担任的课程是经济学与哲学,后又成为逻辑学和审美学的教授。在课堂外,斐诺洛萨不但热衷于收集和研究日本美术作品,还担任了文部省美术事务官、东京美术学校理事等职,与助手兼翻译的冈仓天心(1863—1913)一起赴欧考察美术行政以及相关的教育制度,积极地为日本传统美术的保存和振兴奔走,直接促成了东京美术学校的创立和《古社寺保存法》等美术相关法令的制定,被看成是日本美术的恩人。
对于日本的传统美术,斐诺洛萨起初并不看好,但因为一次偶然的际会——1880年在奈良、京都等地的旅行中意外地发现了日本佛教美术中暗藏的古希腊的艺术传统——而转变立场,开始狂热地拥护日本画。1882年,他在龙池会的演讲被大森惟中(1844—1908)整理成《美术真说》一书,在日本得到广泛传播,启发了当时的人们对于“美术(3)当时“美术”与“艺术”尚未分化,Liberal arts的译名也尚未确定,菲诺洛萨使用的“美术”可以看成我们今天所说的“艺术”。是什么”以及“美的自律性”的思考。在这次演讲当中,斐诺洛萨否定了“将技术的优劣作为判断美术是否善美的主要因素”的“技巧精良说”、“将是否能引发人们内心的愉悦作为判断美术是否善美的主要因素”的“快乐说”、“将对自然和实物的模仿作为美学的关键”的“自然模仿说”,认为美术的本质并不在于作品与外界的外在关系,而应当在“事物的本体”中谋求。美术的本质在于“妙想(idea)”,即“在各个分子内面保有始终相依的关系,并时常产生一种完全唯一的感觉”。在妙想之外,作为美术的要素存在的是“旨趣”和“形状”。这三者相互组合,构成了诗歌、音乐和绘画。在他看来,“诗歌以旨趣的妙想为主,形状的妙想为次。音乐则相反,以形状的妙想为主,以旨趣的妙想为次。绘画则不可偏废,旨趣和形状共同组成了车的两轮”。并且,他还以该定义为基准,提出了“绘画构造”的“十格”理论,即“图线的和谐”“浓淡的和谐”“色彩的和谐”“图线之美”“浓淡之美”“色彩之美”“旨趣的和谐”“旨趣之美”“创意”“技巧”[6]37-42。
1889年,东京美术学校正式开校。“美学及美术史”课程由已成为日本美术指导者的斐诺洛萨亲自担任。对于斐诺洛萨在东京大学的哲学讲义,现在只能通过三宅雪岭(1860—1945)、坪内逍遥(1859—1935)、井上哲次郎等人的回忆,间接地了解到他的讲义在内容上统合了穆勒、斯宾塞的英国经验论与康德至黑格尔的德国观念论,虽然讲的是进化论,但却并不是像普通的进化论者那样只讲进化论。他将黑格尔哲学中的进化论思想与自然科学的进化论融会贯通,并在此基础上努力寻求突破,并非刻意去迎合当时流行的物质主义,而是追求一种理想主义。[7],[4]70而他在东京美术学校的讲义,则由冈仓天心翻译、大村西崖(1868—1927)编成,现收录于《冈仓天心全集》第八卷,所以相较于东京大学的讲义,可以更加忠实地了解到他的所思所想。他认为,世界并不存在“确定的美学”,现在的当务之急也并非去辨别东西方美术方法或者相关主义的不同,而是应该促成对于美术普遍适用的“真正的美学”的诞生。以此为目标,他通过与东方的“六艺”以及“琴棋书画”等概念对比,进而阐述了西方文脉中美术概念的形成史:
古希腊时代的画师们并不知道有“美术”这个词,也没有意识到有对这个词进行说明的必要。只有一个意思相近的词汇——Music。然而,这个词的意思也很难分辨清楚,只是表达为了成为高等社会的人类所需要的技艺,包含了诗歌和音乐。到了罗马时代,开始有了Arts一词。希腊也产生了Techne一词。这便是英语art and technic的起源。它所包含的是以人工进行制造的创作之意,不仅包括我们今天使用的美术,还包括诸种手艺。大约在两千年前,出现了Artes liberales一词,用来表示Liberal arts。它作为高等技艺,与作为谋生手段的技艺区别开来。……并且在自由七艺之上又出现了Arts poetica(poetry)一词。……到了十三世纪到十六世纪之间,美术的复兴运动以意大利为中心。……当时的画师、雕刻师、建筑师们并不知道自己的技艺有多高超,也在不知道什么是美术的情况下创造出了一批绝世之作。……到了十八世纪初,因为诗歌、绘画、建筑、雕刻需要能将其总括在一起的名称,所以在法国开始出现了Beaux arts一词,该词到了十八世纪末被译为英语Fine arts,也就是美术一词的起源。[8]450-452
在斐诺洛萨看来,正是因为美术一词的出现,所以随之也就产生了分析其性质、为其下定义的美学这门学问。美学与美术一样,都是“需要高尚智识的技术”。“美术哲学的本务”便是对美的本质和本体进行探寻,当下具有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以下几种:第一,王尔德(Oscar Wilde, 1854—1900)等人主张,美术的普遍定义不在于模仿自然,而是在于区别于实物的“非代表性”;第二,惠斯勒(James McNeill Whistler,1834—1903)主张,不管描绘什么题材,只要线条和色彩和谐看起来美即可;第三,传统的保守主义观点认为,绘画必须要模仿自然;第四,伊斯特(Sir Alfred Edward East, 1844—1913)将美术分为以实用为目的而进行创作的“有限美术(Finite art/Decorative art)”,以及从材料到形式毫无限制的自由的、独立的“无限美术(Infinite art/pure fine art)”;第五,邓因(其人未详)从社会学、历史学的角度主张,“美术的盛衰与时代紧密相关”;第六,罗斯金(John Ruskin, 1819—1900)主张,美术因“power(作家的技巧)”“imitation(以笔墨刀锯模仿自然)”“truth(富含宗教及道德的精神)”“beauty(无关本体和性质而给人以愉悦)”“relation(事实上可画的内涵)”等五个原因而给人以“快美”。另一方面,对于美术的定义,斐诺洛萨认为“在三十五、六年前发生了一场大革命”。这场“大革命”,即是在美术的定义中谋求音乐以及“装饰艺术(Decorative art)”的地位。经过这场大革命,现在的美术主要由包含了“不依靠实物而是具有其他产生美的要素”的“六美术”——诗歌、音乐、绘画、雕刻、建筑、装饰——组成。美术衰败的原因就在于“流于技巧(skill)”“固守宗派和主义(school ideal tradition)”以及“一味追求对自然的模仿(nature-likeness)”,而拯救其衰败的办法则是“独创性(originality)”“真诚的情感(true love of subject)”以及“艺术形式上的真理(truth of art form)”。[8]453-470
斐诺洛萨的“美学及美术史”讲义与西周的相比,可以看出明显的进步。在内容上,西周介绍的美学只不过是对他人学说的忠实性转述与启蒙性介绍,而斐诺洛萨的讲义却包含了深刻的个人见解与批判性介绍。与稍显滞后于时代的西周的论述相异,斐诺洛萨的讲义不仅包括历史事实的整理,而且也充分地理解和把握住了当代发展的动向;在方法上,西周是按照鲍姆嘉通的定义与方法,将人类的精神分为“知”“情”“意”三个部分进行介绍。而斐诺洛萨则明显受到了黑格尔和斯宾赛的影响,将美学看作是美术哲学或美术的辅助学,在东西方的对比当中介绍西方的诸种学说。从这点来看,完全可以将斐诺洛萨看作日本比较美学的先驱。这也是著有《东西艺术精神的传统与交流》的山本正男(1912—2007)为什么会在其著作中将斐诺洛萨作为最早实践“东西艺术精神交流”的典型,并在第一章“明治时代的美学思想”中介绍了斐诺洛萨后,又专设一章用以讨论斐诺洛萨[9]。但是,在高度评价斐诺洛萨的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斐诺洛萨在“全面欧化”以及“废佛毁释”的大潮中,具有刻意抬高日本美术品价值的主观意图。这些相关发言受到特殊的时代及社会背景影响,未必就是客观的。另外,也正是因为他一贯站在排斥着重对实物进行模仿的写生主义的立场上,大力赞扬具有浓烈的装饰性与悠久的历史传统的狩野派美术。所以,“著有《破除汉字》、创建罗马字会,宣称‘只要是废除汉字的政策什么都赞成’”[5]563的外山正一,会在《日本绘画的未来》中讽刺道:“当下谈论我国绘画的人大致分属两个流派。其中一个流派即是,听信外国人的赞扬,认为当今世上的活美术只存在于日本的妄信一族。”[6]149
1890年,斐诺洛萨回到美国,担任了波士顿美术馆东方部的部长,开始以东方美术专家的面貌,积极地向西方世界介绍东方美术的历史与发展。斐诺洛萨的代表作是他去世之后在有贺长雄(1860—1921)和大村西崖努力下,在日本出版的《东亚美术史纲》(EpochsofChineseandJapaneseArt,1921)。这本“集三十年的苦心探求,不吝财力与劳力,牺牲了所有的快乐”[10]40而成的遗著,主要具有以下几点特征:第一,与着重于工艺上的技巧、以材料对美术进行分类而不问美学上的动因的西方主流著作相比,该书立足于“渗透在各个时代全体美术工艺中的国民性创意”[10]4;第二,该书并非只研究美术文献的美术文献史,而是以美术作品分析为主的实证性研究;第三,该书虽然通过东西间的对比展开讨论,但由于“美术是可以依据世界标准而进行评判的事物”,所以该书“将重点放在东西方美术的共通性上,在世界主义的视域下,撰写东方美术的历史”[10]8;第四,该书将中日美术关系比作“希腊美术与罗马美术”进行统一性论述的同时,也强调日本文明的特异性。
那么,对于在《东亚美术史纲》中自称“曾经在波斯顿作为哲学家尝试从实证的角度研究美术,到了日本又以考古学家的身份成为美术界的权威”[10]14的斐诺洛萨,我们究竟应该如何客观地评价?在该书附有的序言中,曾任东京帝国大学总长、文部大臣的滨尾新(1849—1925)激赏地评价道:“在我的记忆里,斐诺洛萨君不但是美学的泰斗,而且还是美术批评的大家与美术运动的推动者。在我国从美学以及哲学的角度论述美术,就是始于斐诺洛萨。……他基于美学上的观察,以哲理为依据,考究实物,特别是对东西方的美术作品进行比较研究,极大地显示了他见识的广博与作品批评的正确性。这是普通批评家遥不可及的。”[10]2-3但是另一方面,与斐诺洛萨长期共事的冈仓天心却在讲义录《泰东巧艺史》中,较为冷静地说:“最近,斐诺洛萨以及毕格罗(William Sturgis Bigelow,1850—1926)等对我国美术具有慧眼的外国学者陆续来到日本,推动了日本美术的发展。斐诺洛萨既是黑格尔主义者,也是斯宾赛主义者。他认真地研究东方美术,只是由于当时资料较为匮乏,所以他的结论往往有很多无法论证的地方。但即便如此,他传授体系化研究方法的功绩仍不容抹灭。”[11]正如井上哲次郎所说,“斐诺洛萨虽然作为进化论者推崇斯宾赛,但与此同时他也信仰黑格尔的哲学,尝试对两者进行有机统合。但是在来到日本几年之后,他开始对日本美术产生兴趣,进而埋头于此,以至于抛弃哲学,成为了日本美术的研究者”[4]60。比起在美学上对西方理论的研究与传播的贡献,斐诺洛萨在日本美术史学上的地位则显得更为突出。他将美学作为艺术哲学具体地运用到美术批评与美术史研究当中,让当时的人们广泛地认识到了这门学问的价值。后来的坪内逍遥就曾在书中说,“近来某位美国的博识在东京屡次谈到美术的真理,驳斥了世间的谬说”[12],坦言自己是效仿斐诺洛萨写就了日本首部文艺批评理论著作《小说神髓》。而且在因有效地运用了美学的武器而在文艺批评界崭露头角的森鸥外那里,也可以清楚地看到斐诺洛萨的影子。当然,斐诺洛萨在日本备受推崇,也与其发言在当时迎合了日本人的情感需求不无关系。他重视日本传统美术作品的立场,是在激烈的欧化主义的浪潮中感受到不安的人们所赞成的,而他将日本乃至是东方美术置于世界文明的体系之中的做法,又与高举“脱亚入欧”旗帜希望尽早进入西方文明国行列的洋才派的努力相一致。总而言之,斐诺洛萨是外籍特聘教师中最具影响力的一位,正是他一手开创了日本美术史学与艺术社会学的源流。
三、凯倍尔与美学讲座
以1886年《帝国大学令》的颁布为分水岭,日本的讲座美学可以分为前后两个不同的阶段。如上文所述,在第一阶段内,审美学尚未从哲学中分离出来。而以文科大学的成立为契机,东京大学的审美学讲义开始步入正轨,并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1890年,扩充为“审美学·美术史”讲义;1891年,改称为“美学·美术史”讲义;1893年,升格为文学院20个讲座中的独立一科,成为世界上最早设置美学讲座的大学;1914年,进一步增设“美学·美术史”第二讲座。(4)[日]東京帝国大学編:『学術大観 総説·文学部』東京帝国大学学術大観編集委員会,1942年,第440-446頁;東京大学編:『東京大学百年史 部局史一』東京大学百年史編集委員会,1986年,第588頁。另外,关于各大学美学讲座的相关情况,东京大学美学艺术学研究室曾对东京大学、京都大学、东北大学、九州大学、庆应义塾大学、早稻田大学、同志社大学、关西学院大学做过调查,调查结果以极为简洁的形式发表于日本美学会编《美学》(藤田一美:「諸大学における美学講座等開設に関する資料」『美学』第22巻3号,1971年,第68-70頁)。但在1900年大塚保治(1868—1931)从欧洲留学归来担任讲座教授以前,“美学·美术史”的讲座教授一直处于空缺状态。大塚就任以前的这一阶段,可以称之为讲座美学的第二阶段或准备期。在此阶段,审美学在制度上得到了确定,并且也随着讲座制的正式导入,教学研究开始有效地运转了起来。所以,培养一批以美学为专业的日本年轻学者,也就成为这个时期学院派美学发展的当务之急。肩负起这个重担并出色地完成了任务的,则是作为外籍特聘教师在日任教时间最长的凯倍尔。
凯倍尔与斐诺洛萨都是对日本讲座美学产生了深远影响的外籍教师。他出生于俄罗斯,父亲是德国人,母亲是俄罗斯人。6岁便进入莫斯科音乐院学习钢琴,后在德国耶拿大学跟随著名哲学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奥伊肯(Rudolf Eucken,1846—1926)学习哲学。在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后,凯倍尔先是任教于卡尔斯鲁厄的音乐学院,担任伦理学、音乐史以及音乐理论等课程的教学工作,后成为自由撰稿人,闲居慕尼黑专注于哲学著述。因为他在当时通行的哲学教科书中撰写了爱德华·哈特曼(Eduard von Hartmann,1842—1906)的章节并且著有专论哈特曼哲学的书籍,所以为哈特曼所熟知。当时,恰好井上哲次郎委托哈特曼寻找一名接替巴斯到东京大学任教的哲学研究者,所以也就因此际遇,得到了哈特曼的推荐,来到东京大学任教。1893年就任后,他终身居住于日本,不仅在课堂内为师生们讲授哲学、美学等科目长达21年,而且还在课外为少数有志者开设了希腊语、拉丁语和德语的学习班。如果说,凯倍尔来日前的主要成就在于学术方面,是作为学者对于哈特曼和叔本华哲学体系的研究——《哈特曼的哲学体系》(Dasphilos.SystemE.v.Hartmanns, 1884)、《叔本华的哲学理论》(DiePhi’osophieA.Schopenhauers,1887),那么1893年来日后,他的主要成就则体现在教学上,是作为一名教师,以自身高尚的人格和广博的素养为日本学界培养和输送了一大批优秀的学子——夏目漱石、阿部次郎、大西克礼、深田康算、九鬼周造、和辻哲郎、天野祯佑、安倍能成、岩波茂雄、波多野精一等。正如凯倍尔身边的人回忆得那样,“先生因为忙于讲义等缘故,并没能出版学术上的著作。仅仅是来日后不久,在哲学会做过一次关于叔本华与哈特曼的逻辑性关系的讲座”,“据我所知,先生在公开的场合做过的演讲只有两次。一次是在为了纪念斋藤信策而召开的青年会上,另一次则是在哲学会上”(5)[日]桑木嚴翼:「ケーベル先生に就て」『哲学雑誌』第438号,1923年,第66頁;姉崎正治「ケーベル先生の追懐」『哲学雑誌』第438号,1923年,第72頁。另外,杂志《思想》也推出过“凯倍尔纪念号”(『思想·ケーベル先生追憶号』第23号,1923年)。,可见他将主要的精力放在了对学生的教育与指导上。
从大学退任后,凯倍尔本想回到欧洲移居到地中海岸旁的小镇,但由于战争的爆发,他不得不在横滨的俄国领事馆内度过了人生最后的十年。在此期间,他为杂志《思潮》《思想》撰写了一批散文,并先后在岩波书店结集出版。论文集的内容既包括发表在杂志上的散文,也包括他为了纪念席勒和哈特曼而发表在杂志Wahrbeit的论文以及在哲学会等地的演讲稿。另外,作为凯倍尔散文的主要翻译者的久保勉(1883—1972)还在《凯倍尔博士小品集》(KleineSchriften, 1918;KleineSchriften,NeueFolge, 1921;KleineSchriftenⅢ,1925)的基础上编有《凯倍尔博士随笔集》(岩波文库,1928)以及回忆录《与凯倍尔先生同行》(『ケーベル先生とともに』岩波書店,1951)。由于凯倍尔并没有留下像斐诺洛萨那样详尽的讲义记录,所以我们只能通过相关的学史资料,了解到以下内容:
他用英语讲课,不使用翻译。在内容上,他的“美学美术史”讲义主要分为三个部分:首先作为西方美学史的概要,从柏拉图讲起,追溯了亚里士多德和普洛丁的思想,在指出西方中世思想的重要性后,由莱布尼茨、鲍姆嘉通而过渡到德国观念论。其次,依据德国观念论的考察方法,辩证地分析了美和艺术的本质;最后,着重讲以“审美认识”与“直观”构筑的体系化美学,并对艺术进行了特别的研究。因为该门课程学名是“美学美术史”,所以在美学的讲述之外,也有很多涉及到西方美术史的内容。有的年份,作为美术史的替代,也讲述音乐美学。据《东京帝国大学学术大观》(昭和十七年)所记,凯倍尔的讲义“对比真正意义上的美学讲义,在今天看来,也丝毫不会显得粗略。虽然当时在大学课程上并没有美学讲读,但他在家中购买了柏拉图、谢林、尼采等人的原著召开讲读会,成为了实际意义上的美学讲读。除此之外,他还召开了以一般诗学以及浮士德论为题的特殊讲义,并作为讲师在东京音乐学校教授音乐学”。[3]590
果然比起讲义的具体内容,更能让学生乃至日本学界感佩的,恐怕还是凯倍尔的人格,即井上哲次郎所说的“凯倍尔对于钱财看得很淡,不旅行,也没有妻子家眷。正因为如此,他得以用隐士的态度埋头于自我喜爱的精神上的学问。……这种具有超越意义的隐士作风自不用说是高尚的,对于金钱的淡泊也着实让人敬佩”[13]。并且作为一名教师,他与年轻的学生们平等、友善地相处,以自身高尚的人格魅力与广博的学识素养,培养出了一大批杰出的学者。这一点正如桑木严翼所说,“当下在学界活跃的人们,大部分是出自先生门下”[14]。这些凯倍尔的学生们,在日后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成为哲学界、美学界的主导者。其中,夏目漱石(1867—1916)就曾专门撰文称赞他的老师凯倍尔为东京大学文科教授中人格最优秀的人物:“如果到文科大学去问,这里人格最高尚的教授是谁?一百个的学生中有九十个,都会在说出屈指可数的日本教授之前,先回答是凯倍尔”[15];1899—1902年就读于哲学科、长期与凯倍尔居住在一起的京都大学美学讲座的开创者深田康算(1878—1928)说,“按照年月来数的话,我从认识先生到现在已经度过了23年,在我到目前为止的生涯中几乎有一半的岁月都是与先生共同渡过的”[16],他专门讴歌道:“在我所见到的范围内,凯倍尔是唯一一个在现实生活中活出了‘高尚灵魂’(Schöne Seele)的人”[17]。除此之外,也如三木清(1897—1945)所说,“教养的观念主要就是漱石门下的弟子们在凯倍尔博士的影响下形成的”(6)[日]三木清:「読書遍歴」『読書と人生』新潮文庫版,1974年,第26頁。,以阿部次郎(1883—1935)的《三太郎的日记》以及《人格主义》为代表的、流行于大正至昭和时期的“教养主义”以及“教养派”的成立就与凯倍尔有着密切的关系。
在以凯倍尔为代表的外籍教师的教导和培养下,东京大学美学专业的毕业生们开始逐渐地成熟起来。他们纷纷走出国门,到美学的发源地西欧学习和生活。学成之后,又陆续回到祖国,走上讲坛,成为了独当一面的美学研究者。作为其中的代表,大塚保治于1900年结束留欧后,出任升格为独立部门的东京大学美学讲座的初任教授;深田康算、阿部次郎、矢崎美盛(1869—1931)也分别于1910、1923、1925年归国后,出任京都大学、东北大学和法政大学的美学教授……与此同时,庆应义塾(今庆应义塾大学)、东京专门学校(今早稻田大学)等各大私立名校也相继开设了美学课程,一时群星璀璨,涌现出了坪内逍遥、森鸥外、冈仓天心、大西祝(1864—1900)、立花铣三郎(1867—1901)、大村西崖、金子筑水(1870—1937)、高山樗牛、岛村抱月(1871—1918)、植田寿藏(1886—1973)等一大批杰出的美学家、文艺理论家。在他们的牵引下,日本学院派美学开始迈向了新的发展方向。
(在撰写过程中,湖北大学梁艳萍教授和山西大学臧新明教授在资料提供、术语校正等方面,给笔者提供了较大的帮助,特此鸣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