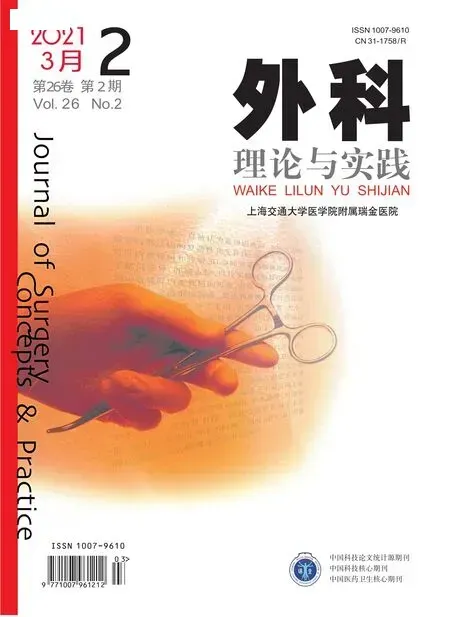肝门部胆管癌腹腔镜手术根治性切除的争议与共识
2021-12-04李敬东朱建交张立鑫熊永福
李敬东, 朱建交, 张立鑫, 熊永福
(川北医学院附属医院肝胆外科肝胆微创研究室,川北医学院肝胆胰肠疾病研究所,四川 南充 637000)
肝门部胆管癌(hilar cholangiocarcinoma,HCCA)是指起源于肝总管、左右肝管及其汇合部胆管黏膜上皮的恶性肿瘤。HCCA最常见的病理类型为分化程度不同的腺癌,约占90%,其他组织类型少见[1]。根治性手术切除是HCCA公认最有效的治疗方法。手术方式及切除范围主要依据临床分型与病理分期。2020年3月23日发布的《2020年NCCN肝胆肿瘤临床实践指南(V1版)》指出,根治性手术切除率仅30%~40%,术后局部复发及远处转移率较高[2]。目前腹腔镜手术日渐普及,病人创伤小,恢复快。但HCCA根治性治疗是否开展腹腔镜手术,国内仍具有很大的争议,国外更是鲜有学者认可和尝试。本文归纳了HCCA腹腔镜手术根治性切除的争议和已达成的共识。
HCCA腹腔镜根治性切除从2010年以来,仅有少数报道,且多以病例介绍为主[1]。随着腹腔镜外科技术的成熟、腹腔镜胰十二指肠切除术(laparoscopic pancreaticoduodenectomy,LPD)的广泛开展和腹腔镜肝切除的精准化发展,国内有较多中心选择性开展HCCA腹腔镜根治性切除[3-7]。目前,会议报道单中心开展例数最多的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刘建华团队150多例。另外,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的秦仁义团队、浙江省人民医院的张成武团队以及笔者所在团队都已累计50例以上。据不完全统计,国内至少有20个以上的肝胆胰中心选择性开展腹腔镜HCCA根治性切除。其手术方式、手术原则与开腹手术类似,有的中心还尝试腹腔镜下行肝动脉和(或)门静脉切除重建。从技术角度证明开展腹腔镜HCCA根治性切除的可行性。
由于HCCA根治性切除是胆道外科最复杂的手术,绝大多数病人只有一次手术机会,且多需半肝以上切除或围肝门切除加尾状叶切除,血管受累很常见[8]。手术的彻底性直接关乎疗效,所以国内很多学者坚决反对应用腹腔镜强行完成HCCA根治性切除。但随着学术交流的深入,目前部分反对的学者也在呼吁理性看待并探索新事物。这是否如20世纪90年代初出现的腹腔镜胆囊切除术,以及近年的腹腔镜胃癌、结肠直肠癌手术和LPD等。
技术可行性的争议与共识
一、切缘
切缘状态与病人术后生存期相关,切缘阳性者一般预后较差[9]。Otsuka等[10]研究发现,术后切缘阳性影响早期HCCA切除病人的生存。切缘阳性病人术后复发率较R0切除病人高,术后生存率低。也有报道,术中首次切缘阳性+再切除切缘阴性病人与首次切缘阴性病人的术后生存差异无统计学意义[10-11]。关于HCCA化疗的研究,R1切除术后化疗生存率与R0切除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然而仍应争取R0切除,因为长期生存率的主要决定因素是病人肿瘤的生物学行为[8,12-13]。R0切除是HCCA治疗最有效的手段。
关于肿瘤上下切缘、环周切缘界定,存在腹腔镜与开腹手术方式的争议。有学者认为腹腔镜触感较差,不易判断胆管的切缘,特别是肿瘤上切缘,影响对肿瘤可切除性的判断,且在术中难以决定手术的具体方式等。随着对HCCA肿瘤生物学行为认知的深入和影像检查技术的进步,术前三维重建等多种手段可协助判断肿瘤的可切除性及切除方式和切缘。HCCA大体病理类型分为硬化型、乳头型、结节型及弥漫型。其中硬化型最常见,约占70%,常侵犯胆管周围组织,致胆管环状增厚,侵犯周围血管及神经,肉眼难以分辨边界,触感也完全不可靠。弥漫型向胆管上、下方向浸润,发展较快,难有手术切除机会,更不易靠触感去确定手术切线。乳头型和结节型有可能通过触感辅助判断手术切线,但在现代影像检查技术的辅助下,术前都能得到清晰的影像检查结果[14]。对于血管的侵犯,即使借助多排螺旋CT、三维重建检查等,仍较难准确判断。术中只能根据具体情况作血管切除重建或R1切除等。此问题无论是开腹手术还是腹腔镜手术都存在。所以,笔者的观点是,触感在现代外科手术中,并不是一个可靠的判断方式。
二、淋巴结清扫
HCCA最常见的转移方式为淋巴结转移,在肿瘤较早期就可出现。Aoba等[15]回顾性分析320例HCCA术后淋巴结转移数量、位置和淋巴结阳性率对预后的影响,发现淋巴结转移者预后差于无淋巴结转移者。所以,规范的淋巴结清扫是HCCA根治性切除术的必要步骤。淋巴结状态可用于疾病分期及预后判断,指导辅助治疗。美国国立综合癌症网络(National Comprehensive Cancer Network,NCCN)第8版TNM分期,更新淋巴结转移分期,重点关注淋巴结转移数目而非阳性淋巴结部位。以区域淋巴结转移数目进行分期,N1为1~3枚区域淋巴结转移,N2为≥4枚区域淋巴结转移,与第7版N1和N2的概念不同[2]。
肝十二指肠韧带周围淋巴结(第12h、12a、12b、12p、12c 组)、肝动脉旁淋巴结(第 8a、8p 组)及胰头后方淋巴结(第13a组)共同构成复杂的淋巴网。淋巴染色发现,肝十二指肠韧带周围淋巴结是最常见的转移部位,且是向胰腺周围和更远处淋巴结扩散转移的关键部位[16-17]。目前国内学者非常重视淋巴结清扫,支持HCCA腹腔镜根治性切除的认为,腹腔镜具有较好的放大作用,在狭窄的空间也能直视,有利于淋巴结清扫,这在LPD已充分证实。清扫肝十二指肠韧带周围、肝动脉旁和胰头后方都很容易,且可直视下清扫第16组淋巴结。彭兵团队回顾性分析胰腺癌5年长期生存率与淋巴结清扫数目和阳性率等,并与开腹手术比较,证实腹腔镜与开腹手术差异无统计学意义[18]。已有手术视频和报道证实,术中淋巴结可能受到的损伤,主要受器械影响,避免淋巴结破碎,开腹能做到的腹腔镜同样能做到[19]。由于腹腔镜的放大作用,对淋巴结清扫可达到开腹的标准。这已被进展期胃癌根治术中淋巴结清扫的报道证实[20]。
尽管国内部分学者也承认腹腔镜的放大作用,对一些特殊部位的暴露优势,但在淋巴结大量融合、与肝动脉和门静脉粘连的情况下,腹腔镜较难完成整块淋巴结清扫,而可能是一个个淋巴结摘除。在腹腔镜气腹的密闭空间,超声刀的气化作用将淋巴结打碎,不能排除增加腹腔内播散转移的可能。美国国立肿瘤数据库(NCDB)统计分析2010年至2012年1 524例腹腔镜胆囊癌术中清扫淋巴结数≥3的数目与开腹组对比,腹腔镜组少于开腹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34%比47%,P<0.01)[21]。这让部分学者认为腹腔镜HCCA淋巴结清扫的质量可能不如开腹手术。综上,目前对腹腔镜HCCA根治性切除淋巴结清扫的技术可行性仍有质疑。
三、血管侵犯
HCCA易侵犯周围血管,联合血管切除重建可使肿瘤根治性切除率提高,生存获益,已达成共识。Mizuno等[22]和Nimura等[23]分析行联合血管切除重建的HCCA病人,发现R0切除可使病人生存获益,提示血管侵犯影响预后。Matsuyama等[24]回顾性分析98例HCCA联合血管切除重建术病人的临床资料。结果发现,联合门静脉切除重建者R0切除率可达80%,术后5年生存率51.2%,术后并发症发生率未见明显增加。联合门静脉、肝动脉切除虽可提高R0切除率,但5年生存率并未提高,与术中联合血管切除重建者的肿瘤生物学特性有关。因此,选择实施大范围肝切除并联合血管切除重建手术时应仔细慎重,需经验丰富的胆道外科医师实施,以使病人获益最大化。
支持腹腔镜手术的国内学者也承认,腹腔镜HCCA根治性切除术中受侵的门静脉和肝动脉重建非常困难。仅有学术会议上零星报道,对重建的质量和术后是否存在严重并发症无详细说明。中华外科杂志2019年发表的腹腔镜HCCA根治切除术操作专家建议指出,对于有明确血管侵犯的,推荐中转开腹手术治疗[25]。
四、神经浸润
神经浸润是另一个导致HCCA预后不良的重要因素[26]。文献报道,胰腺癌、胃癌、胆道肿瘤、前列腺癌、头颈部癌、结肠直肠癌及宫颈癌发生神经浸润的概率分别为70%~100%、6.8%~75.6%、56.0%~88.0% 、12.4%~83.6% 、5.2%~90.0% 、15.7%~38.9%及8.6%~31.3%,说明胆胰癌具有嗜神经性[27]。
2009年,Liebig等[28]提出神经浸润更准确的定义,为肿瘤接近神经并至少包绕33%以上的神经周径或肿瘤细胞浸润神经鞘的三层结构 (即内膜、束膜和外膜)任意一层,这也是目前神经浸润的病理诊断标准。研究表明,神经主要围绕肝动脉及其分支分布,而围绕门静脉和胆管相对较少。腹腔镜手术肝门骨骼化清扫,神经丛的廓清主要沿动脉进行,且用超声刀为主。这引起主张开腹手术学者的质疑,认为很少有腹腔镜医师能用超声刀打开血管的鞘膜,真正做到神经丛廓清,这可能是术后局部复发的主要原因之一。腹腔镜外科医师在行神经丛廓清时,由于担心血管鞘膜被超声刀热损伤,引起术后动脉瘤,所以可能打开血管鞘膜不完整,易导致神经丛转移灶残留。开腹清扫时,一般采用锐性的剪刀,无热损伤,直视下直接进入血管鞘膜,清扫既彻底又安全。笔者认为,胰腺癌、胃癌的腹腔镜手术开展时间较长,特别是胃癌,同样具有神经丛转移的特性。但国内、外的研究表明,应用超声刀清扫,并无确切的证据证实,术后局部转移复发缘于神经丛清扫不彻底。开腹组长期生存率与腹腔镜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如的确证实超声刀不能精准进入血管鞘膜,腹腔镜下也完全可应用剪刀、电剪或电钩进行神经丛血管鞘内廓清。当然,这些争议还需高级别的研究来解决。
五、尾状叶切除和肝切除的范围
由于肿瘤位置和生长特性,HCCA极易侵犯尾状叶的胆管,特别是左侧的尾状叶。故国内、外指南均指出,除HCCA的BismuthⅠ型和Ⅱ型特殊类型可不辅以肝尾状叶切除外,均应作规范肝尾状叶切除。腹腔镜HCCA根治性切除的原则应与开腹手术一致。由于腹腔镜操作的局限性,腹腔镜医师建议常规做解剖性肝叶切除联合尾状叶切除(大范围肝切除),不宜采取保留肝实质的手术 (联合5段和4b段切除等)。腹腔镜能从不同的角度达到狭小的操作空间,有利于处理位于肝后的肝短静脉。学界公认腹腔镜肝尾状叶切除与开腹手术相比,更能直视下操作,具有较大的优势,可明显降低手术难度,减少出血量。反对意见认为,2013年前腹腔镜肝尾状叶切除仅有零星病例报道,2019年腹腔镜HCCA根治性切除术联合尾状叶切除最大宗的报道来自张成武,仅14例[29]。说明腹腔镜整块切除半肝和真正的全尾状叶并非易事,而不是部分尾状叶或分块切除。
六、胆道重建
胆道重建是HCCA根治性切除术的收官之战,也是难度最大的操作,其位置深、显露差。切除病肝残留的肝断面胆管开口多,有的胆管开口相距较远,难以整形,有的胆管壁菲薄易破。因此,肝门胆管空肠Roux-Y吻合非常困难。即使开腹手术也难以做到精确的高质量胆肠吻合,术后胆漏比例高。有学者认为,腹腔镜下此吻合难以完成,术后更易发生严重并发症。这种情况确实存在,特别是气腹增加吻合口的张力,提高吻合的难度。笔者认为,开腹与腹腔镜手术同样面临操作难度大的问题。对拟行腹腔镜HCCA根治性切除的病人更应精心术前准备。术前通过规范减轻黄疸(经皮肝穿刺胆道引流或内镜鼻胆管引流)、抗感染和营养支持治疗提高欲保留肝侧肝胆管的质量,减少胆管壁炎症和脆性。腹腔镜首选大范围肝切除联合全尾状叶切除,尽可能减少肝断面胆管开口的数目,降低手术操作难度。改进胆肠吻合的方法,提高胆肠吻合的质量,如腹腔镜的降落伞方法,以及应用4-0或5-0可吸收PDS-Ⅱ缝线。
技术安全性的争议与共识
HCCA根治性切除涉及所有肝胆外科技术的复杂操作,手术时间长,并发症发生多,如术后出血、胆漏、肝功能衰竭、腹腔内重度感染等。开腹手术一般持续5~6 h至10 h以上不等,一般耗时于淋巴结清扫、血管重建、胆肠吻合等步骤,而腹腔镜的手术时间目前普遍长于开腹手术,大多在8 h以上,且在未涉及血管重建的前提下。有学者认为,手术时间的延长将伴随着腹腔感染的增加,加上上述腹腔镜操作的特点,缝合难度较大。止血大多采用超声刀结合双极电凝等电外科平台。因此术后出血的发生率往往高于开腹手术,且胆漏的发生率也同样高于开腹手术,所以技术的安全性方面值得商榷。目前,专家已达成共识,腹腔镜根治性切除对Ⅰ型、Ⅱ型和少部分Ⅲ型HCCA技术上是安全的。
合理性和必要性的关注
腹腔镜HCCA根治性切除是一个新的手术技术,但并未改变手术的原则,只是手术的入路和操作的习惯有一些改变。对新技术的评价一般分为5 个阶段:想法(idea)、开发(development)、探索(exploration)、评价(assessment)、长期研究(long-term study)[30]。联系到腹腔镜HCCA根治性切除,目前最多达到探索阶段,且HCCA病例较少,能切除的病人更少,所以要完成一个多中心随机对照研究相对困难。腹腔镜密闭状态下,CO2气腹对免疫的影响,以及trocar种植转移和腹腔内播散转移发生率较开腹手术增加。对于腹腔镜HCCA根治性切除的合理性和必要性还需高级别的临床和基础研究来提供支撑。
专家评论
刘厚宝教授(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普外科)
肝门部胆管癌手术是胆道外科复杂的手术之一。往往需要联合大范围肝脏切除、围肝门切除、复杂的胆道成形与重建以及血管重建等,手术难度高、风险大。近年来,随着微创外科技术的发展,腹腔镜和机器人手术在胃肠外科、肝胆胰外科已广泛开展,机器人或腹腔镜肝切除术、胰十二指肠切除等复杂手术在很多临床中心常规开展。但腹腔镜或机器人肝门部胆管癌手术目前仅在国内少数临床中心开展。在手术的安全性、根治的彻底性和术后的远期疗效等方面存有争议。如血管鞘的完整剥离、淋巴结清扫、胆管切缘、胆道重建质量等是否能够达到开腹手术的效果,术后出血、胆漏等并发症发生率是否高于开腹手术等。目前在手术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方面还缺乏客观、长期随访的结果,因此有必要进行多中心的临床对照试验或真实世界的临床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