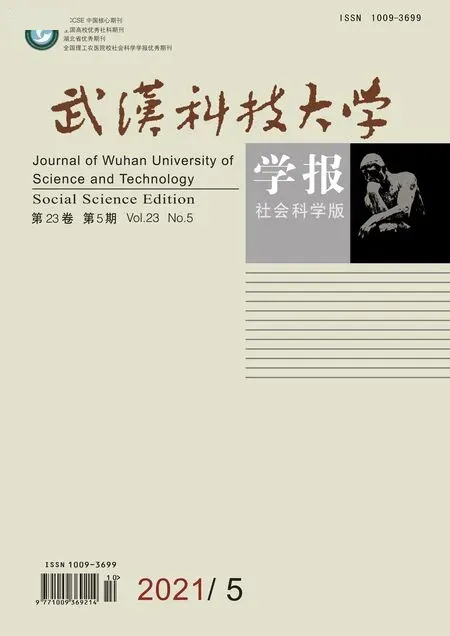孔颜之乐:是“乐道”,还是“自乐”?
——以朱熹的解读为中心
2021-12-04乐爱国
乐 爱 国
(厦门大学 哲学系,福建 厦门 361005)
孔子讲“乐”。《论语·学而》载,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论语·雍也》载,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关于孔子所言“贫而乐”,历来解读各不相同,有些《论语》版本在文本上为“贫而乐道”①,而汉唐诸儒多把“贫而乐”之“乐”解读为“乐道”,并为清儒所采纳;直至现代杨伯峻《论语译注》解“贫而乐”为“虽贫穷却乐于道”②,钱穆《论语新解》解为“贫而能乐道”③。与此不同,朱熹将“贫而乐”之“乐”解读为“超乎贫富之外”的“自乐”。与此相关,对于“回也不改其乐”所言“颜回之乐”的解读,历来也各不相同,多数把颜回之乐也解读为“乐道”,而二程把颜回之乐解读为“自乐”,尤其是程颐不赞同把颜回之乐只是简单地解读为“乐道”,反对把“道”当作一物而乐之。朱熹并不反对将颜回之乐解读为“乐道”,而是强调心中有“道”,心中有“仁”,自然而乐,既是“自乐”又包含了“乐道”,是“乐道”与“自乐”的统一。因此他讲“唯仁故能乐”“私欲克尽,故乐”,尤其要求像颜回那样着实做工夫,“博文约礼”,从而真正感受颜回之乐。
一、从“贫而乐”的不同解读说起
据定州汉墓竹简《论语》④所载,“未若贫而乐”,其“乐”下无“道”⑤(《论语·学而》)。但是,据《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西域文献》Pel.chin.2618写本,论语卷第一(4-2)、魏何晏《论语集解》载,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道,富而好礼者也。”其下有郑玄注曰:“乐谓至(志)于道,不以贫贱为忧苦也。”接着又有孔安国注曰:“能贫而乐道,富而好礼者,能自切磋琢磨。”⑥
关于《论语》文本上应当是“贫而乐”还是“贫而乐道”,清儒讨论颇为深入。臧琳《经义杂记》说:“《古论语》‘未若贫而乐道’,《鲁论语》‘未若贫而乐’。”⑦武亿《金石三跋》说:“《论语》石经字旁注者,于‘贫而乐’下注‘道’字,《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不如贫而乐道,富而好礼’,郑玄曰‘乐谓志于道,不以贫为忧苦也’,皇侃《义疏》亦作‘贫而乐道’,此古本皆有‘道’字之徵,今率从脱文矣。《旧唐书》云:石经脱‘贫而乐道’‘道’字,使后人因循不改,未必非此书之作俑,信然哉!”⑧认为《古论语》文本上应当是“贫而乐道”。陈鳣《论语古训》根据郑玄注曰“乐谓志于道,不以贫贱为忧苦也”,说:“郑注本无‘道’字。《集解》兼采《古论》,下引孔曰‘能贫而乐道’,是孔注《古论》本有‘道’字。司马迁从孔安国问《古文尚书》,《史记》所载《语》亦是《古论》,《仲尼弟子传》引《论语》曰‘不如贫而乐道’正与孔合。……郑据本盖《鲁论》,故无‘道’字。”⑨也就是说,孔安国注《古论语》,其文本为“贫而乐道”,郑玄注《论语》,其文本为“贫而乐”,但“贫而乐”之“乐”被解读为“志于道”,即“乐道”。
何晏《论语集解》的《论语》文本为“贫而乐道”,后来皇侃《论语义疏》以何晏《论语集解》为底本,疏曰:“孔子更说贫行有胜于无谄者也。贫而无谄乃是为可,然而不及于自乐也。故孙绰云:‘颜氏之子一箪一瓢,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也。’”⑩可见,皇侃将《论语》文本的“乐道”等同于“自乐”,并与颜回之乐联系在一起。
北宋邢昺《论语注疏》也以何晏《论语集解》为底本,但在文本上并不采其“贫而乐道”,而采“贫而乐”,但是疏曰:“此章言贫之与富皆当乐道自修也。”把“贫而乐”之“乐”解读为“乐道”,而且还说:“子贡言:贫而乐道,富而好礼,其此能切磋琢磨之谓与?‘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者,……谓告之往以贫而乐道,富而好礼,则知来者切磋琢磨,所以可与言《诗》也。”显然,在邢昺《论语注疏》中,“贫而乐”之意在于“贫而乐道”。
宋代的《论语》文本大都与邢昺《论语注疏》一样,采“贫而乐”。苏辙《论语拾遗》说:“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夫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亦可谓贤矣。然贫而乐,虽欲谄不可得也;富而好礼,虽欲骄亦不可得也。”
二程对“贫而乐”与“富而好礼”有过讨论。程颢说:“贫而能乐,富而能好礼,随贫富所治当如此。……若贫而言好礼,则至于卑,富而言乐,则至于骄。然贫而乐,非好礼不能;富而好礼,非乐不能。”程颐说:“贫无谄,富无骄,能处其分也。乐与好礼,能自修也。切磋琢磨,自修各以其道也。告之以乐与好礼,而知为自修之道,知来者也。”这里只是讲“贫而能乐”,并没有将之解读为“贫而乐道”,认为“贫而能乐,富而能好礼”,是贫者和富者各自所修之道。对此,朱熹说:
无谄无骄,程叔子以为能处其分,与伯子所论乐与好礼互相发明者,皆善矣。然以乐与好礼为随贫富所治,叔子亦以为能自修,则似皆未安也。夫好礼以为修治可也,乐则岂修治之谓耶?
朱熹赞同程颐所谓“贫无谄,富无骄,能处其分也”以及程颢所谓“贫而乐,非好礼不能;富而好礼,非乐不能”,但对程颢所谓“贫而能乐,富而能好礼,随贫富所治当如此”以及程颐所谓“贫而乐,富而好礼”为“自修各以其道”感到不妥,认为“乐”与“好礼”不同,“好礼”属道德修养,而“乐”并不属道德修养,也就是说,“乐”只是“自乐”,并非具有道德内涵的“乐道”。朱熹《论语集注》说:
谄,卑屈也。骄,矜肆也。常人溺于贫富之中,而不知所以自守,故必有二者之病。无谄无骄,则知自守矣,而未能超乎贫富之外也。凡曰可者,仅可而有所未尽之辞也。乐则心广体胖而忘其贫,好礼则安处善,乐循理,亦不自知其富矣。
子贡货殖,盖先贫后富,而尝用力于自守者,故以此为问。而夫子答之如此,盖许其所已能,而勉其所未至也。
在朱熹看来,“贫而无谄,富而无骄”,虽能“知自守”,但“未能超乎贫富之外”;“贫而乐,富而好礼”,则是能够“忘其贫”“不自知其富”,超乎贫富之外。朱熹还说:“昔子贡无谄无骄之问,盖自以为至矣,而夫子以为未若乐与好礼,何哉?无谄无骄,则尚局于贫富之中;乐且好礼,则已超然乎贫富之外也。然其所以至此,则必尝有所用其力矣。”又说:“《集注》谓‘超乎贫富之外’者,盖若为贫而乐与富而好礼,便是不能超贫富了。乐,自不知贫;好礼,自不知富。”也就是说,只有真正“超乎贫富之外”才能达到“贫而乐”“富而好礼”。据《朱子语类》载,
问:“‘贫而乐’,如颜子非乐于箪瓢,自有乐否?”曰:“也不消说得高。大概是贫则易谄,富则易骄。无谄无骄,是知得骄谄不好而不为之耳。乐,是他自乐了,不自知其为贫也;好礼,是他所好者礼而已,亦不自知其为富也。”曰:“然则二者相去甚远乎?”曰:“也在人做到处如何。乐与好礼,亦(自)有浅深。也消得将心如此看,且知得是争一截。学之不可已也如此。”
朱熹认为,“贫而乐”,正如颜回之乐并非乐于箪瓢,是“自乐”,是由于“不自知其为贫”,犹如富者之所以能够好礼,在于“不自知其为富”,同时,无论是“贫而乐”,还是“富而好礼”,都有由浅入深、由低到高的过程,学者既不可“安于小成,而不求造道之极致”,又不可“骛于虚远,而不察切己之实病”, 因此,“贫而乐”作为“自乐”,又并非如颜回之乐那样的高度,但应当由此而达到颜回之乐的高度。
清儒在《论语》文本上大都采“贫而乐”,与邢昺《论语注疏》一致,同时又依郑玄所谓“乐谓志于道,不以贫为忧苦”,从而把“贫而乐”之“乐”解读为“乐道”, 而不同于朱熹解读为“自乐”。
由此可见,对于《论语》“贫而乐”的解读,大致有两种意见:一是孔安国注《古论语》,文本上为“贫而乐道”,或郑玄注《论语》,文本为“贫而乐”,但“贫而乐”之“乐”被解读为“乐道”;二是程朱的解读,不仅其《论语》文本为“贫而乐”,而且“贫而乐”之“乐”被解读为“自乐”,是“超乎贫富之外”之乐,而不是“乐道”。这样的不同解读,事实上又与各自对颜回之乐的不同解读相关联。
二、“颜回之乐”与“乐道”
汉唐诸儒不仅在《论语》文本上采“贫而乐道”,或把“贫而乐”解读为“贫而乐道”,而且把颜回之乐也解读为“乐道”。何晏《论语集解》引孔安国注曰:“颜渊乐道,虽箪食在陋巷,不改其所乐也。”皇侃《论语义疏》曰:“颜回以此为乐,久而不变,故云‘不改其乐’也。……所乐则谓道也。”认为颜回之“乐”在于“乐道”。这与《论语义疏》解“贫而乐道”,与颜回之乐相联系,是一致的。此外,宋李昉《太平御览》引晋皇甫谧《高士传》:“颜回字子渊,贫而乐道,退居陋巷,曲肱而寝”。 邢昺《论语注疏》疏曰:“‘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者,言回居处又在隘陋之巷,他人见之不任其忧,唯回也不改其乐道之志,不以贫为忧苦也。”又疏“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曰:“此章记孔子乐道而贱不义也。”疏“发愤忘食,乐以忘忧”,曰:“其孔子之为人也,发愤嗜学而忘食,乐道以忘忧。”由此可见,汉唐诸儒,直至北宋邢昺,大都把《论语》所言孔子之“乐”、颜回之“乐”解读为“乐道”,这与他们讲“贫而乐道”是一致的。
北宋周敦颐对颜回之乐做了思考,说:“颜子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而不改其乐。夫富贵,人所爱者也。颜子不爱不求,而乐乎贫者,独何心哉?天地间有至贵至爱可求,而异乎彼者,见其大而忘其小焉尔。见其大则心泰,心泰则无不足,无不足则富贵贫贱处之一也。处之一则能化而齐,故颜子亚圣。”二程曾回忆说:“昔受学于周茂叔,每令寻颜子、仲尼乐处,所乐何事。”这里讲颜回、孔子之乐,合称“孔颜之乐”。
对于颜回之乐,二程有过深入的讨论。程颢说:“颜子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箪瓢陋巷非可乐,盖自有其乐耳。‘其’字当玩味,自有深意。”程颐说:“颜子箪瓢陋巷不改其乐,箪瓢陋巷何足乐?盖别有所乐以胜之耳。”二程还说:“颜子箪瓢,非乐也,忘也。”“颜子非乐箪瓢陋巷也,不以贫累其心,而改其所乐也。”认为颜回之乐不是乐于贫贱,而是忘记了贫贱和富贵。或问:“颜子在陋巷而不改其乐,与贫贱而在陋巷者,何以异乎?”程颐说:“贫贱而在陋巷者,处富贵则失乎本心。颜子在陋巷犹是,处富贵犹是。”也就是说,颜回之乐,与贫贱和富贵无关。为此,二程明确讲“颜子陋巷自乐”,认为颜回之乐是“自乐”。据《河南程氏外书》记载,鲜于侁问伊川曰:“颜子何以能不改其乐?”正叔曰:“颜子所乐者何事?”侁对曰:“乐道而已。”伊川曰:“使颜子而乐道,不为颜子矣。”显然,程颐不赞同把颜回之乐只是简单地解读为“乐道”。
后来,朱熹将颜回之乐与孔子“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结合起来。据《朱子语类》载,子善谓:“夫子之乐,虽在饭疏食饮水之中,而忘其乐。颜子不以箪瓢陋巷改其乐,是外其箪瓢陋巷。”曰:“孔颜之乐,大纲相似,难就此分浅深。”这里明确将孔子之乐与颜回之乐统一起来。当然,朱熹也讲孔子之乐与颜回之乐的细微差异,说:“虽同此乐,然颜子未免有意,到圣人则自然。”“唯是颜子止说‘不改其乐’,圣人却云‘乐亦在其中’,‘不改’字上,恐与圣人略不相似,亦只争些子。圣人自然是乐,颜子仅能不改。”
朱熹赞同二程所谓颜回之乐不是乐于贫贱。据《朱子语类》载,贺孙问:“《集注》云,颜回,言其乐道,又能安贫。以此意看,若颜子不处贫贱困穷之地,亦不害其为乐。”曰:“颜子不处贫贱,固自乐;到他处贫贱,只恁地更难,所以圣人于此数数拈掇出来。”明确认为颜回之乐在于“自乐”,而与贫贱无关。至于程颐不赞同鲜于侁把颜回之乐解读为“乐道”,朱熹作了解释。朱熹说:“鲜于侁言,颜子以道为乐。想侁必未识道是个何物,且如此莽莽对,故伊川答之如此。”“伊川说颜子乐道为不识颜子者,盖因问者元不曾亲切寻究,故就其人而答,欲其深思而自得之尔。”在朱熹看来,程颐不赞同把颜回之乐简单地解读为“乐道”,是针对鲜于侁轻率地将颜回之乐说成是“以道为乐”而答,并要求其“深思而自得之”。
为此,朱熹做了进一步解释,说:“程子盖曰颜子之心,无少私欲,天理浑然,是以日用动静之间,从容自得,而无适不乐,不待以道为可乐然后乐也。”又说:“程子之言,但谓圣贤之心与道为一,故无适而不乐。若以道为一物而乐之,则心与道二,而非所以为颜子耳。”在朱熹看来,程颐不赞同把颜回之乐简单地解读为“乐道”,是要强调颜回之乐“不待以道为可乐然后乐也”,讲的是“圣贤之心与道为一”,反对把“道”当作一物而乐之;如果是那样,就是心与道为二,那就不是颜回之乐。朱熹还说:“道是个公共底道理,不成真个有一个物事在那里,被我见得!只是这个道理,万事万物皆是理,但是安顿不能得恰好。而今颜子便是向前见不得底,今见得。向前做不得底,今做得,所以乐。不是说把这一个物事来恁地快活。”也就是说,“道”不是外在的东西,不能把“道”当作一物而乐之,“才说乐道,只是冒罩说,不曾说得亲切”。据《朱子语类》载,
问:“程子云:‘周茂叔令寻颜子仲尼乐处,所乐何事。’窃意孔颜之学,固非若世俗之着于物者。但以为孔颜之乐在于乐道,则是孔颜与道终为二物。要之孔颜之乐,只是私意净尽,天理昭融,自然无一毫系累耳。”曰:“然。但今人说乐道,说得来浅了。要之说乐道,亦无害。”
由此可见,朱熹反对的是把颜回之乐简单地解读为“乐道”,把“道”当作一物而乐之,并不完全反对讲“乐道”。他还说:“且如‘伊尹耕于有莘之野,而乐尧舜之道’,未尝以乐道为浅也。直谓颜子为乐道,有何不可。”据《朱子语类》载,
或问:“程先生不取乐道之说,恐是以道为乐,犹与道为二物否?”曰:“不消如此说。且说不是乐道,是乐个甚底?说他不是,又未可为十分不是。但只是他语拙,说得来头撞。公更添说与道为二物,愈不好了。”
问:“伊川谓‘使颜子而乐道,不足为颜子’,如何?”曰:“乐道之言不失,只是说得不精切,故如此告之。今便以为无道可乐,走作了。”
可见,朱熹并不完全反对把颜回之乐解读为“乐道”,而是反对把“道”当作一物而乐之。他还注:“回也其庶乎,屡空。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论语·先进》,曰:“子贡不如颜子之安贫乐道,然其才识之明,亦能料事而多中也。”这里明确讲“颜子之安贫乐道”。如上所述,朱熹认为“贫而乐”并非如颜回之乐那样的高度,概是认为颜回之乐不止是“超乎贫富之外”的“自乐”,而且其中也包含了“乐道”。
三、“私欲克尽,故乐”
朱熹对于《论语》“贫而乐”的讨论,不仅讲贫者应当乐,而且进一步讨论如何才能实现“贫而乐”,所以强调“超乎贫富之外”而达到“贫而乐”。同样,对于颜回之乐的讨论,朱熹也不仅仅只是讨论颜回是否是“乐道”,而是更多地思考颜回为什么能够于箪瓢陋巷之中而“自乐”。
朱熹说:“颜子之乐,非是自家有个道,至富至贵,只管把来弄后乐。见得这道理后,自然乐。故曰:‘见其大,则心泰;心泰,则无不足;无不足,则富贵贫贱处之一也。’”也就是说,孔颜之乐并不是把“道”当作一物而乐之,而在于心中有“道”,自然而乐。他又说:“这道理在天地间,须是直穷到底,至纤至悉,十分透彻,无有不尽,则于万物为一无所窒碍,胸中泰然,岂有不乐!”还说:“惟其烛理之明,乃能不待勉强而自乐循理尔。夫人之性,本无不善,循理而行,宜无难者,惟其知之不至,而但欲以力为之,是以苦其难而不知其乐耳。知之而至,则循理为乐,不循理为不乐,何苦而不循理以害吾乐耶?”在朱熹看来,孔、颜心中有“道”,因而“自乐循理”,同时又“循理为乐”。
二程虽然认为颜回之乐是“自乐”,尤其是程颐不赞同把颜回之乐只是简单地解读为“乐道”,但是又特别强调颜回之“自乐”在于不失本心。或问:“陋巷贫贱之人,亦有以自乐,何独颜子?”二程说:“贫贱而在陋巷,俄然处富贵,则失其本心者众矣。颜子箪瓢由是,万钟由是。”又说:“若颜子箪瓢,在他人则忧,而颜子独乐者,仁而已。”认为颜回之乐在于其心中有“仁”。对此,朱熹做了解释。据《朱子语类》载,
刘黻问:“伊川以为‘若以道为乐,不足为颜子’。又却云:‘颜子所乐者仁而已。’不知道与仁何辨?”曰:“非是乐仁,唯仁故能乐尔。是他有这仁,日用间无些私意,故能乐也。而今却不要如此论,须求他所以能不改其乐者是如何。缘能‘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这四事做得实头工夫透,自然至此。”
在朱熹看来,颜回之乐并非“以道为乐”,也非是“乐仁”,而是“唯仁故能乐”,在于“他有这仁,日用间无些私意”,因而在“克己复礼”“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中,自然能获得快乐。所以,朱熹又提出“私欲克尽,故乐”。据《朱子语类》载,
问:“颜子‘不改其乐’,莫是乐个贫否?”曰:“颜子私欲克尽,故乐,却不是专乐个贫。须知他不干贫事,元自有个乐,始得。”
伯丰问:“颜子之乐,不是外面别有甚事可乐,只颜子平日所学之事是矣。见得既分明,又无私意于其间,自然而乐,是否?”曰:“颜子见得既尽,行之又顺,便有乐底滋味。”
在朱熹看来,颜回之乐在于“私欲克尽,故乐”,在于“无私意于其间,自然而乐”。朱熹还说:“私欲未去,如口之于味,耳之于声,皆是欲。得其欲,即是私欲,反为所累,何足乐!若不得其欲,只管求之,于心亦不乐。惟是私欲既去,天理流行,动静语默日用之间无非天理,胸中廓然,岂不可乐!此与贫窭自不相干,故不以此而害其乐。”所以他说:“人之所以不乐者,有私意耳。克己之私,则乐矣。”又注《论语》,子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曰:“圣人之心,浑然天理,虽处困极,而乐亦无不在焉。”显然,在朱熹看来,人之不快乐,在于有私欲,只有去除私欲,“浑然天理”,自然而有快乐。需要指出的,朱熹不仅认为颜回之乐在于“私欲克尽,故乐”,而且还解曾点之乐,说:“曾点之学,盖有以见夫人欲尽处,天理流行,随处充满,无少欠缺。故其动静之际,从容如此。……直与天地万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之妙,隐然自见于言外。”同样他也认为曾点之乐在于“人欲尽处,天理流行”。
重要的是,朱熹对于颜回之乐的讨论,不仅要弄清颜回为什么而乐,更是要求像颜回那样着实做工夫,从而真正感受颜回之乐。他说:“‘乐’字只一般,但要人识得,这须是去做工夫,涵养得久,自然见得。”
据《朱子语类》载,
问:“颜子乐处,恐是工夫做到这地位,则私意脱落,天理洞然,有个乐处否?”曰:“未到他地位,则如何便能知得他乐处!且要得就他实下工夫处做,下梢亦须会到他乐时节。”
问:“濂溪教程子寻孔颜乐处,盖自有其乐,然求之亦甚难。”曰:“先贤到乐处,已自成就向上去了,非初学所能求。况今之师,非濂溪之师,所谓友者,非二程之友,所以说此事却似莽广,不如且就圣贤着实用工处求之。”
在朱熹看来,“孔颜乐处”虽然可以解释为“私欲克尽,故乐”,但重要的是要像他们那样着实做工夫,“就圣贤着实用工处求之”,才能真正感受到其中的快乐,体会“孔颜乐处”。朱熹《论语集注》注颜回之乐,曰:
颜子之贫如此,而处之泰然,不以害其乐,故夫子再言“贤哉回也”以深叹美之。程子曰:“颜子之乐,非乐箪瓢陋巷也,不以贫窭累其心而改其所乐也,故夫子称其贤。”又曰:“箪瓢陋巷非可乐,盖自有其乐尔。其字当玩味,自有深意。”……愚按:程子之言,引而不发,盖欲学者深思而自得之。今亦不敢妄为之说。学者但当从事于博文约礼之诲,以至于欲罢不能而竭其才,则庶乎有以得之矣。
显然,朱熹注颜回之乐,强调的是“博文约礼”,着实做工夫。据《朱子语类》载,
问:“叔器看文字如何?”曰:“两日方思量颜子乐处。”先生疾言曰:“不用思量他!只是‘博我以文,约我以礼’后,见得那天理分明,日用间义理纯熟后,不被那人欲来苦楚,自恁地快活。你而今只去博文约礼,便自见得。今却去索之于杳冥无朕之际,你去何处讨!将次思量得人成病。而今一部《论语》说得恁分明,自不用思量,只要着实去用工。”
对于朱熹《论语集注》注颜回之乐,强调“博文约礼”,门人黄榦说:“博文约礼,颜子所以用其力于前;天理浑然,颜子所以收其功于后。博文则知之明;约礼则守之固。凡事物当然之理,既无不洞晓,而穷通得丧与凡可忧可戚之事,举不足以累其心,此其所以无少私欲,天理浑然,盖有不期乐而自乐者矣。”应当说,黄榦的这一解读合乎朱熹之意。
四、余论
由此可见,对于《论语》颜回之乐的解读,历来都与“贫而乐”的解读联系在一起。汉唐诸儒大都把“贫而乐”解读为“贫而乐道”,因而也把颜回之乐解读为“乐道”。二程把颜回之乐解读为“自乐”而不赞同把颜回之乐只是简单地解读为“乐道”,反对把“道”当作一物而乐之。朱熹继承二程,把“贫而乐”与颜回之乐都解读为“自乐”,并强调由低到高的过程,因而并不完全反对把颜回之乐解读为“乐道”,而是肯定颜回的“自乐”中包含了“乐道”,不止是“超乎贫富之外”的“自乐”。尤其是在朱熹看来,“道”之在于人心,颜回之乐就是乐于心中之道,就是克己复礼;一旦私欲克尽,“浑然天理”,心中有“道”,心中有“仁”,自然而乐,因而是在“乐道”中“自乐”,是在着实做工夫、“博文约礼”中“自乐”,以实现“乐道”与“自乐”的统一。
应当说,朱熹对于“孔颜之乐”的解读,不是仅仅停留于汉唐儒家所谓的“安贫乐道”,而是进一步讲孔颜如何在求道中获得快乐,讲“私欲克尽,故乐”,讲心中有“仁”,心中有“道”,自然而乐,并要求“就圣贤着实用工处求之”,以实现“乐道”与“自乐”的统一,这样的解读无疑是深化了汉唐儒家的解读。
现代学者对于颜回之乐的解读,既有解为“乐道”者,如唐文治《论语大义》所言:“颜子之乐,乐道而已。”蒋伯潜《论语读本》解曰:“大凡一个人,处富贵则欢乐,处贫贱则忧愁;只有乐道之士,富贵贫贱,都不足以动其心。”也有继承程朱而不是简单地解为“乐道”者。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赞同程颐所谓“使颜子而乐道,不为颜子矣”,说:“程颐的这个说法,很像禅师的说法,所以朱熹编《二程遗书》时,不把这段语录编入遗书正文里,而把它编入《外书》里,似乎是编入‘另册’。其实程颐的这个说法,倒是颇含真理。圣人之乐是他的心境自然流露,可以用周敦颐说的‘静虚动直’来形容,也可以用程颢说的‘廓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来形容。他不是乐道,只是自乐。”后来,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修订本)又说:“‘孔颜乐处’就在于‘仁’,‘所乐’的‘事’也就是‘仁’。”又认为,“孔颜乐处”所乐的是“‘与人同’,与物同,甚至与‘无限’同”的精神境界。既认为孔颜之乐“‘所乐’的‘事’也就是‘仁’”,又认为孔颜之乐是精神境界,应当说,这与朱熹的解读有着许多相似之处。
如前所述,杨伯峻《论语译注》解“贫而乐”为“贫穷却乐于道”,但是,解颜回之乐却主要讲颜回有修养因而能够“不改变他自有的快乐”。与此相类似,钱穆《论语新解》虽然也解“贫而乐”为“贫而能乐道”,但解颜回之乐则主要讲颜回之贤而能“不改其乐”。李泽厚《论语今读》解“贫而乐”,强调“非以贫而乐”,又在解颜回之乐时讲“儒学之不以贫困本身有何可乐”;而且还引述朱熹《论语集注》所注言,并且说:“马王堆帛书《五行篇》有:‘君子无中心之忧则无中心之智,无中心之智则无中心之悦。无中心之悦则不安,不安则不乐,不乐则不德乐。’‘乐’在这里虽然并不脱离感性,不脱离心理,仍是一种快乐;但这快乐已经是一种经由道德而达到的超道德的稳定‘境界’(state of mind)。”这里特别强调颜回之乐不仅仅是“安贫乐道”,更在于讲由道德修养而达到快乐。显然,这与朱熹解颜回之乐是心中有“道”自然而乐,在“乐道”中而达到“自乐”,“乐道”与“自乐”的统一,是一致的。
注释:
①参见李方:《敦煌〈论语集解〉校证》(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39-40页)。
②参见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13页)。
③参见钱穆:《论语新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21页)。
④据称,这部《论语》是公元前55年以前的本子,是时有《鲁论》《齐论》《古论》三种《论语》存在。参见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定州汉墓竹简整理小组:《论语·定州汉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7年版,第1页)。
⑤参见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定州汉墓竹简整理小组:《论语·定州汉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7年版,第10页)。
⑥参见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国国家图书馆:《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第16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294页)。
⑦参见臧琳:《经义杂记》卷2(载《续修四库全书》第17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52页)。
⑧参见武亿:《金石三跋》(载《续修四库全书》第89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619页)。
⑨参见陈鳣:《论语古训》卷1(载《续修四库全书》第15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317页)。
⑩参见皇侃:《论语义疏》(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