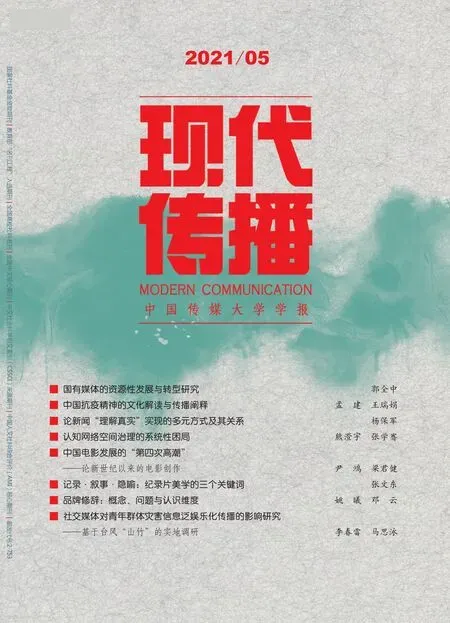芬兰媒介素养教育政策的整体框架与逻辑理路*
2021-12-02袁利平王垚赟
■ 袁利平 王垚赟
一、引言
长期以来,芬兰依托本国完善的教育体系和高质量的教育水平使其在各种国际教育评估中赢得了较高声誉,其高水平的媒介素养教育也得到了世界公认。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芬兰就不断探索和发展媒介素养教育。在七十多年的发展进程中,芬兰通过一系列国家政策不断推动媒介素养教育朝着多样性、综合性、全民性的方向发展。为保障媒体的多样性和多元化,2018年7月,芬兰政府通过了“媒体政策方案(Media Policy Programme)”决议,制定了延伸到2023年的系列目标,具体包括促进创新、改善媒介素养和技能,建立媒介政策网络等。2019年12月,芬兰教育文化部出台了国家媒介素养教育新政策——《芬兰媒介素养:国家媒介素养教育政策》(Media Literacy in Finland:National Media Education Policy,以下简称《政策》),明确了芬兰媒介素养教育的背景、发展目标等,强调了有待进一步完善之处以及相关的社会、文化、技术领域的发展趋势。从芬兰媒介素养教育发展的宏观整体视角来看,其具有连贯性、一致性和创新性的国家政策是芬兰媒介素养教育取得成功的关键所在。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系统梳理芬兰媒介素养教育政策的演进历程,全面分析其组成要素与逻辑理路,并在此基础上挖掘其价值取向,或许能为我国发展和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媒介素养教育提供一定启示。
二、芬兰媒介素养教育政策的演进历程
在七十多年的不断探索中,芬兰更新和出台了许多国家政策,为其媒介素养教育提供了制度保障和方向引领,持续推动媒介素养教育不断向纵深发展。从芬兰媒介素养教育的发展史来看,其政策演进主要有以下四个阶段:
(一)起步探索时期(20世纪50—70年代)
随着大众文化的兴起和发展,西方媒介素养教育从20世纪50年代就开始从保护主义范式逐渐向内容辨析范式转型。①媒介素养教育由保护精英文化、抵抗和防御大众文化逐步转变为认可大众文化的存在价值和积极意义。芬兰媒介素养教育正是发轫于这样一个日趋开放多元的时代进程中。自20世纪50年代,芬兰启动了现代化媒介素养教育探索,并将其视为博雅教育(liberal education)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媒介素养教育兴起的第一个十年,芬兰主要关注了电影对个体和社会的影响,并主张通过对电影的批判性解读促进人们理解和辨别媒介内容。从60年代开始,为增强学校教育的社会化取向,芬兰将媒介素养教育的关注点从电影转向了报纸,并成为这一领域的先驱。1964年,芬兰报业协会(Finnish Newspaper Association)为“历史和公民课程”教师开设了报刊课程(press course)以提高教师的专业性。②进入70年代以后,由于媒介环境日趋复杂化和差异化,芬兰对大众传媒教育(mass media education)掀起了大规模讨论。为抵御媒介的消极影响和增强个体自主性,芬兰越加重视媒介素养教育并将其作为一个跨学科主题(cross-curricular theme)纳入了学校课程体系。在这一时期,芬兰媒介素养教育主要关注的是电影、报纸、电视等传统媒介,显现出反思和批判等特征并进入了主流学校教育体系,为此后媒介素养教育的快速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二)理论奠基时期(20世纪80—90年代)
20世纪80—90年代,随着大众传媒的普及和计算机信息技术的发展,媒介素养教育日益受到各国关注。在国际媒介素养教育实践和理论的影响下,芬兰媒介素养教育随着本国媒介环境的改变而不断发展。80年代开始,芬兰青年运动开展、音乐录影带盛行以及制作录像的便利化促使学界兴起了对媒介素养教育的讨论。③媒介文化的相关研究开始渗透到媒介素养教育领域并对其产生深刻影响。《想象中的孩子:芬兰电影中的儿童形象》(Imaginary Children:on the Picture of the Child in Finnish Films)成为80年代芬兰以媒介研究作为切入点影响媒介素养教育的代表作。20世纪90年代,随着芬兰逐步走上信息化发展道路,通信技术和信息技术在教育机构日渐普及并引起了芬兰教育研究者的注意。传播教育(communication education)开始成为90年代芬兰媒介素养教育的主流。与此同时,芬兰涌现出了众多与媒介素养教育相关的概念,如大众传媒教育(mass media education)、视听教学(audiovisual teaching)、媒介通信教育(media communication education)等,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芬兰媒介素养教育及其研究的最新进展。这一时期,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媒介环境的改变,芬兰积极开展媒介和媒介素养教育的研究,不仅为媒介素养教育实践提供了理论支持,而且为媒介素养教育科学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三)体系形成时期(2000—2018年)
2000年以来,随着相关研究的开展,各国对媒介素养重要性的认识不断深化,媒介素养教育成为欧盟政策制定中的一个重要议题。④在欧盟超国家层面政策的影响下,芬兰出台了专门针对改善儿童和青少年媒介素养的国家政策指南,并将提升媒介素养融入了其他领域的政策之中。一方面,芬兰将媒介素养教育纳入文化、图书馆等相关领域的政策文件中,如2004年,芬兰在出台的文化政策中强调防止媒介暴力的影响并提出了具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另一方面,芬兰教育文化部(Ministry of Education and Culture)于2013年出台了专门的国家政策指南《良好媒介素养:国家政策指南2013—2016》(Good Media Literacy:National Policy Guidelines 2013-2016,以下简称《指南》)。《指南》从国际、欧盟和芬兰三个层次展示了媒介素养教育的发展现状,分析了芬兰媒介素养教育的现存挑战和发展趋势,并制定了目标和原则。⑤此外,包括芬兰图书馆协会(The Finnish Library Association)、芬兰媒体业联合会(The Federation of the Finnish Media Industry)在内的社会各界也积极参与媒介素养教育发展。这一时期,芬兰初步形成了媒介素养教育的政策体系,并逐步确立了跨部门合作和全社会参与的媒介素养教育发展模式。
(四)内涵深化时期(2019年以来)
2019年,芬兰教育文化部在前期调研的基础上出台了《政策》。《政策》是对2013年《指南》的更新和完善,并在发展目标、政府职能和目标群体等方面不乏创新和突破。第一,《政策》基于对芬兰媒介素养教育现状的分析制定了综合、优质、系统的发展目标。其中,综合表现在行为主体、地区发展等方面,优质贯穿于理论研究和实践推进的全过程,系统则主要体现为媒介素养政策的一致性和连续性。第二,《政策》明确了教育文化部、司法部(Ministry of Justice)、交通与通信部(Ministry of Transportation and Communication)等政府部门的职能,涉及部门政策、资金支持、具体措施等多个方面。第三,《政策》将媒介素养教育的对象从此前的儿童和青少年扩大到各个年龄段的全体公民,并对老年人和特殊需要人群给予了关注。这一时期,芬兰的媒介素养教育政策既有继承,也有创新。继承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延续跨部门合作和全社会参与的传统,二是坚持理论研究和教育实践相结合。创新则集中表现于媒介素养教育目标群体的扩大,这与芬兰公平、非歧视的教育传统相契合,凸显了媒介素养教育促进个体发展和社会融合的功能。
三、芬兰媒介素养教育政策的多维构成
连贯性和整体性的媒介素养教育政策为促进芬兰媒介素养教育发展、改善全民媒介素养提供了制度保障。发展综合、优质、系统的媒介素养教育以增强公民媒介核心素养是芬兰媒介素养政策的核心内容。作为一个有机政策整体的芬兰媒介素养教育政策,其核心内容涵盖了媒介素养教育实施主体、发展目标、师资培训、资金支持等多个维度,充分发挥了其跨部门合作和全社会参与的优势。
(一)多元主体:媒介素养教育的政策理念
多元主体参与贯穿芬兰媒介素养教育政策制定和实施的全过程是芬兰媒介素养教育多元化发展的重要支撑,也是芬兰应对媒体环境变化、落实全民性理念的必然选择。构建媒介素养教育的多元主体模式既与媒介素养教育的核心内涵相一致,也是芬兰对媒介素养教育历史传统的继承和发展。一方面,媒介素养教育和媒介素养教育本质上具有跨部门合作性和跨学科整合性。⑥多元主体参与媒介素养和媒介素养教育的本质属性相契合,能够有效促进媒介素养教育跨部门、跨学科的研究和实践,推动其朝着多元化、个性化的方向发展。另一方面,如上文所述,从20世纪50—70年代的起步探索阶段开始,芬兰媒介素养教育已经呈现出多元主体参与的特征。在半个多世纪的发展进程中,这一特征被不断放大和强化,成为芬兰媒介素养教育取得成功的关键。
政府力量主导和社会各界参与是芬兰媒介素养教育多元主体模式的基本内涵。政府机构是芬兰制定和执行媒介素养教育政策的主导力量,起着决定性作用。在芬兰教育文化部的引领下,司法部、交通与通信部等其他国家部门和机构也结合实际,以不同的出发点和侧重点参与媒介素养教育理论研究和实践推进。如芬兰司法部关注媒介素养促进民主的作用,交通与通信部则侧重于将推进媒介素养教育和促进互联网安全使用相结合。与此同时,高校、非政府组织、媒体业以及其他行业的企业或组织等社会各界也发挥各自的优势,积极参与媒介素养教育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并在科学研究、知识普及、资金保障等多个方面为发展媒介素养教育提供支持,成为政府力量的有益补充。如芬兰高校面向公众开办媒介素养教育研讨会和展览,芬兰报业协会持续二十多年开展报纸周(newspaper week)活动。
(二)阶段发展:媒介素养教育的政策方略
明确的阶段性培养目标在教育发展中起到了方向引领作用。自21世纪初媒介素养教育被纳入芬兰国家核心课程体系后,芬兰在各个教育阶段都将提升媒介素养作为重要的教育目标。根据2018年发布的《幼儿教育和保育国家核心课程标准》(National Core Curriculum for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and Care),该阶段媒介素养教育的主要目标是促进儿童在社区积极地表达自我和学习批判媒介。在芬兰2014年发布的《基础教育国家核心课程标准》(National Core Curriculum for Basic Education)中,媒介素养则被纳入横向能力(transversal competence)下的培养目标。横向能力(也被称为“21世纪技能”)是难以在课堂上显性化教授或通过纸笔考试测量的,但它们对于学生应对全球化背景下的挑战和实现未来发展来说是不可或缺的。⑦芬兰在基础教育阶段将媒介素养作为横向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将其融入众多学校课程教学中。此外,在芬兰高中教育、职业教育等不同的教育阶段发展目标中,媒介素养均占有一席之地。⑧
通过对芬兰基础教育阶段媒介素养教育的发展目标进行分析可以发现,芬兰媒介素养教育在媒介使用技能之外,更强调学生个性化认知能力的发展。这一阶段,芬兰主要通过“媒介技能与沟通”(media skills and communication)这一跨学科主题实施媒介素养教育。这一主题被纳入芬兰语、社会科学、历史、视觉艺术等学科教学中,并根据不同年级和学科的特点制定了具体的学科教学目标。“在低年级媒介素养教育中,芬兰更倾向于在良好的媒介环境中培养学生对媒介的认识和使用能力;在高年级则更强调对媒介和媒介内容批判性思考和分析的能力。”⑨总体来说,芬兰基础教育阶段的媒介素养教育旨在培养学生的自我表达能力、信息管理技能、使用媒介和批判性地认识媒介内容的能力。
(三)能力建设:媒介素养教育的政策保障
加强教师媒介素养教育专业能力建设是芬兰实现媒介素养教育目标、应对媒介环境变化和发展优质媒介素养教育的重要保障。首先,媒介素养教育目标的实现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教师媒介素养教育专业能力。芬兰媒介素养教育涉及多个层次的目标,既包括实践层面的使用、消费媒介和创作媒介内容,也包括思维层面的理解、选择和批判媒介信息。⑩这对教师能力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其次,芬兰新旧兼具、多样化的媒介丰富了教育内容,同时也增大了教育难度。社交媒体、手机游戏等新媒体和报纸、电视等传统媒体并存,向芬兰媒介素养教育提出了挑战。如何应对日趋多样化、复杂化的媒介环境是芬兰教育研究者和教师需要共同思考的问题。最后,发展优质媒介素养教育要求教师依托传播学、教育学等领域的研究成果,涵盖多样的教学主题并采用专业的教育方法。
职前教育和在职培训是发展教师专业能力的两大主要途径。在职前教育方面,芬兰高校不仅将媒介素养课程纳入教师专业培训课程,也支持包括硕士、博士在内的媒介素养教育专业人才培养,如拉普兰德大学(University of Lapland)教育学院开设的媒介素养教育硕士项目(MA in media education)。该项目的课程设计主要依托教育学、社会学和心理学进行,包括教学中的媒介、社会中的媒介以及媒介与社会心理健康三大主题,具有多元文化、多样和融合的特点。在在职培训方面,芬兰教师能够获得多样化的媒介素养教育专业培训渠道,包括教育文化部、芬兰报业协会在内的政府部门和社会组织为增强教师媒介素养教育专业能力提供了培训项目或课程。此外,芬兰教师也能够获得接受国际培训的机会,如2019年欧洲委员会(Council of Europe)为教师开设的线上媒介素养硕士课程。
(四)多渠筹措:媒介素养教育的政策支撑
充足的资金是媒介素养教育不断发展的前提条件,也是开展媒介素养教育教师培训、提供教育资源、开展教育研究的重要保障。随着芬兰媒介素养教育日益受到公众认可并成为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之一,其边界不断向社会拓宽,由此对资金提出了更高的需求。长期以来,芬兰媒介素养教育在政府力量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参与下不断推进。教育文化部、国家视听研究所(National Audiovisual Institute)等政府部门和机构是芬兰媒介素养教育重要的资金来源。与此同时,媒体业的企业及其组织、基金会,非政府组织,乃至高校都为芬兰媒介素养教育发展提供了资金保障。此外,21世纪以来,随着媒介素养教育进入欧洲的政策议题范围并逐渐成为欧盟国家的基本职责,在欧盟层面开展的众多媒介素养教育相关项目或计划也成为芬兰媒介素养教育的资金来源。
政府、社会组织、私营部门、高校是芬兰媒介素养教育主要的资金筹措主体。首先,芬兰政府通过直接和间接两种方式为媒介素养教育发展提供保障性资金支持。一是直接开展媒介素养教育项目。如教育文化部“儿童与媒介项目”(Children and Media Program)为推进媒介素养教育科学研究、课程研发等多个领域提供了资金支持。二是将媒介素养教育纳入其他领域的补充性政策。如媒介素养教育是芬兰图书馆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政府对图书馆政策的财政投入也将被用于促进媒介素养教育发展。其次,芬兰社会组织和私营部门积极推进媒介素养教育发展。包括芬兰报业协会、电视台、游戏公司在内的多个主体通过提供赞助和免费产品、开展媒介素养教育项目等方式丰富媒介素养教育的资金来源。最后,芬兰高校通过设立教职、提供研究资金等方式推动媒介素养教育发展。
四、芬兰媒介素养教育政策的逻辑理路
芬兰媒介素养教育的质量是举世公认的,这离不开芬兰国家层面政策的支持和保障。芬兰媒介素养教育政策所具备的核心要素是芬兰媒介素养教育取得成功的关键,其逻辑理路主要体现在政策体系、政策主体、参与主体和教育对象等方面。
(一)广泛参与的政策主体
广泛参与的社会各界为芬兰发展媒介素养教育提供了全方位的支持和保障。从媒介素养教育的资金投入、学术研究、师资培训到公益活动、学习材料等各个方面和环节,芬兰社会各界都在其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首先,非政府组织凭借专业性、灵活性和已有的实践基础成为芬兰媒介素养教育积极的实施者和推动者,为芬兰媒介素养教育全民化作出了重要贡献。芬兰参与媒介素养教育的非政府组织既包括以儿童和青少年为主要关注对象的组织,如芬兰家长联盟(Finnish Parents′ League),也包括着力于提升成人媒介素养的机构,如芬兰终身学习基金会(Finnish Lifelong Learning Foundation)。其次,高校为芬兰媒介素养教育发展提供了人才支持和知识贡献。拉普兰德大学和坦佩雷大学(University of Tampere)为培养媒介素养教育的专业人才提供了硕士教育,坦佩雷大学还将媒介素养课程纳入其他专业的硕士课程中,如信息科学、青年工作等专业。芬兰高校也是开展媒介素养教育跨学科研究和知识普及的中坚力量。最后,私营部门是推动芬兰媒介素养教育发展的重要力量。除了提供资金支持、组织教育活动、提供教学材料外,芬兰私营部门还通过资助高校教职、出台战略报告等促进媒介素养教育发展。社会各界参与能够多渠道筹措资金,优化整合资源,极大地丰富芬兰媒介素养教育的多样性。
(二)多元包容的政策客体
多元包容的教育对象是芬兰媒介素养教育全民性和公平性的突出表现。在儿童和青少年之外,芬兰将成人纳入媒介素养教育目标群体,并对老年人和特殊需要人群给予了关注。首先,儿童和青少年是芬兰媒介素养教育的主要目标群体。长期以来,芬兰学校提供了多种形式的媒介素养教育活动,并在学科教学以外组织了不同主题的媒介相关活动,为学生营造了良好的媒介素养教育环境。其次,成人是芬兰媒介素养教育的重要关注对象。在现代社会,信息的获取、使用和创造是日常生活必不可少的内容,而这些都依赖于多样化的媒介。因此,媒介素养是信息时代公民的必备素养和公民能力的重要组成元素。将成人纳入媒介素养教育的关注对象是芬兰提高信息时代公民媒介素养、发展公民能力的关键选择。最后,芬兰媒介素养教育对老年人和特殊需要人群等弱势群体给予了关注。在北欧地区,老年人成为信息社会边缘化群体的问题一直受到关注,虽然使用新兴信息技术和通信技术的老年人不断增加,但仍有部分老年人被信息社会排除在外。而由于身体或认知方面的不足,特殊需要人群在理解、使用和创造媒介信息上受到限制,但同时多样化的媒介也为其沟通和获取信息提供了渠道。因此,将老年人和特殊需要人群作为媒介素养教育的关注对象并满足其个性化需求既是时代发展的要求,也是芬兰关乎社会公平的重要选择。
(三)连贯一致的政策体系
首先,芬兰媒介素养教育政策的连贯性。20世纪50年代以来,芬兰始终坚持跨部门合作和全社会广泛参与的模式,不断丰富和拓宽媒介素养教育的跨学科属性,促使媒介素养教育朝着全民性、包容性、综合性的方向发展。一方面,教育文化部出台的政策一致支持媒介素养教育。芬兰教育文化部将媒介素养教育作为有机组成部分纳入其他政策中,图书馆政策、青年政策等都认可并支持发展公民的媒介素养。如芬兰在2016年修订的图书馆法案中强调图书馆应当帮助公民获取和使用信息,发展多样化的素养技能,其中包括媒介素养。另一方面,其他政府部门出台的政策一致支持媒介素养教育。芬兰其他政府部门基于各自的视角积极参与媒介素养教育发展。如芬兰竞争和消费者保护局(Finish Competition and Consumer Authority)提供了以消费为侧重点的媒介素养教育,包括辨别广告、将媒介作为支付和交易的手段等。其次,芬兰媒介素养教育政策在连贯性和一致性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发展。随着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媒介技术不断更新,芬兰媒介素养教育政策的关注点数次转变,从批判性地认识和解读电影到关注大众传媒教育,再到发展公民能力,芬兰媒介素养教育不断创新。
(四)协同合作的政策环境
协同合作的政府部门在芬兰媒介素养教育政策制定、实施和评估的全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导向和引领作用。跨部门合作贯穿于芬兰媒介素养教育政策制定、实施和评估的全过程。以2019年《政策》为例,首先,芬兰在媒介素养教育政策规划和制定过程中广泛收集了多个政府部门和机构的意见。芬兰国家档案馆(National Archives of Finland)、竞争和消费者保护局、交通通信部、司法部等部门和机构都为《政策》起草给出了意见。其次,芬兰媒介素养教育政策的实施和推进同样得到了多个政府部门支持。不同政府部门基于各自职责范围开展媒介素养教育研究与实践。如交通通信部主持开展了芬兰媒介及其政策研究,并将数据和研究成果用于贯彻落实媒介素养教育政策;芬兰国家健康与福利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for Health and Welfare)主要关注的是儿童、青少年以及家长在家庭中的媒介行为及其与健康、生活方式间的联系。最后,芬兰媒介素养教育政策的后续跟进和实施效果评估也在跨部门合作下开展。芬兰国家视听研究所将协调教育文化部和其他相关部门,通过开展调查或组织专家团队进行调研等方式定期研究和评估《政策》在国家、区域、地方各级的执行情况。芬兰媒介素养教育政策制定、实施和评估过程中的跨部门合作有助于整合、利用各部门资源,丰富媒介素养教育的内容和形式,提高政策的实效性。
五、芬兰媒介素养教育政策的价值取向
“作为决策主体主动的选择活动,教育政策不可避免地涉及价值问题”,其价值取向为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提供了指导,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政策的内容和未来发展方向。芬兰媒介素养教育政策的价值取向与芬兰社会多元、平等的价值定位相一致,并凸显着媒介素养教育创新、平等、多元和跨学科的发展方向。
(一)彰显平等追求
北欧国家具有完善的国家教育体系和较高的教育水平,平等是北欧国家教育的重要特质。“在芬兰,教育平等的意义是根据平等的教育机会打造一套兼具社会平等与包容的教育体系。”改善媒介素养是芬兰各个教育阶段重要的发展目标和教育内容,平等是芬兰媒介素养教育的核心追求和重要价值。在个体层面上,媒介素养教育有助于提升个体的媒介素养和技能,增强其获取、理解和使用媒介信息的能力,从而缓解由于信息不平等所造成的个体发展机会流失,促进教育公平。在群体层面上,媒介素养教育提倡人际交流、对话和互动,强调通过积极开展多元、包容的教育活动增进不同主体间的理解和尊重,从而消除歧视,促进社会公平。
促使每一个人平等地拥有发展媒介素养的机会是芬兰媒介素养教育的重要追求,其平等性在多个方面得到了体现。一是教育对象的平等性,在2019年《政策》中,芬兰将包括成人在内的所有公民纳入国家媒介素养教育政策,并对老年人和特殊需要人群给予了关注。将媒介素养教育的关注对象从儿童和青少年扩大为各年龄段的所有人群,也强化了媒介素养教育的全民性。二是行为主体的平等性,芬兰媒介素养教育政策的出台过程充分体现了行为主体的平等性。在2019年《政策》出台前,芬兰国家视听研究所通过网络调查广泛收集了来自政府部门、非政府组织、高校、私营部门等利益相关者的意见。众多行为主体就芬兰媒介素养教育的现状和前景提出了意见和建议,有助于加强媒介素养教育政策的全面性和完善性。三是教育理念的平等性,消除歧视、增强社会平等是芬兰社会的共同追求,也是其媒介素养教育的核心原则。通过尊重文化多样性,改善个体获取、认识和使用媒介信息的能力,芬兰媒介素养教育能够为个体发展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改善个体发展机会的平等性。
(二)延续多样传统
芬兰媒介素养教育兴起于大众文化蓬勃发展的时代,因此从起步阶段起就具有显著的多样性。在此后半个多世纪的历史进程中,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尤其是通信技术、数字技术的发展,媒介的类型、内容和表现形式得到了极大的丰富。芬兰通过一系列政策,继承和发展了媒介素养教育的多样性,并促使其朝向融合、系统化的方向发展。芬兰媒介素养教育的多样性体现了芬兰教育的全民性、包容性和综合性,与媒介和媒介素养本质上所具有的跨部门性和跨学科性具有内在的一致性。此外,发展平等、非歧视的媒介素养教育也要求媒介素养教育政策尊重个体差异和个性化选择,增强媒介素养教育的多样性。
芬兰媒介素养教育的多样性表现在行为主体、教育对象、教育内容等多个方面。一是行为主体的多样性,芬兰政府是推动媒介素养教育发展的主导力量,在教育文化部的引领下,司法部、交通通信部,竞争和消费者保护局(Finnish Competition and Consumer Authority)等众多国家部门和机构都为媒介素养教育发展做出了贡献。芬兰社会各界作为政府力量的有益补充,在媒介素养教育中也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芬兰非政府组织、高校、媒体业企业等主体都积极参与媒介素养教育政策规划、制定、实施的全过程。此外,欧盟作为超国家力量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芬兰媒介素养教育发展。二是教育对象的多样性,芬兰将媒介素养教育的目标群体从儿童和青少年扩大到全体公民。这既强化了媒介素养教育的多样性,也显示了媒介素养教育的公平性和非歧视性。三是教育内容的多样性,不同行为主体往往基于其自身实践提供不同层次、各具特色的媒介素养教育,从而增强了媒介素养教育主题、学习材料等方面的多样性。
(三)凸显跨学科本质
媒介素养是现代社会公民的基本素养。媒介素养的概念已经打破学科界限,不断延伸和融入多个学科和相关领域中。除传播学以外,媒介素养也与艺术学、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学科密切相关。媒介素养所具有的跨学科性和综合性要求媒介素养教育也具有跨学科性。不同的学科能够从各自的视角出发丰富媒介素养教育的理论和实践,如教育学研究有助于改进媒介素养教育的方法、手段、课程等,社会学关注社会舆情危机的处理等。芬兰媒介素养教育从发展初期就具有鲜明的跨学科性。在媒介素养教育政策的起步时期,芬兰已经将媒介素养教育作为一个跨学科主题纳入学校课程体系并延续至今。芬兰媒介素养教育的跨学科性也极大地丰富了其多样性,并成为媒介素养教育创新发展的动力和源泉。
芬兰媒介素养教育的跨学科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学校媒介素养教育的跨学科性,芬兰为不同阶段的学校媒介素养教育制定了不同的跨学科主题,基础教育阶段为“媒介技能与沟通”,高中阶段为“沟通与媒介能力”(communication and media competence)。跨学科主题被融入历史、芬兰语等学科教学中,成为教学目标和学生能力培养的有机组成部分。二是媒介素养研究的跨学科性,芬兰媒介和媒介素养教育的发展引起了不同领域研究者的兴趣,人类学、社会学、教育学等领域的研究者都积极参与媒介素养教育研究。随着跨学科研究的发展,芬兰媒介素养教育形成了不同的研究取向,主要包括技术主义取向、保护主义取向、文化研究取向和批判主义取向。三是媒介素养教育师资培养的跨学科性,芬兰拉普兰德大学、坦佩雷大学等高校依托教育学、社会学、传播学等学科开展媒介素养教育师资培训。
(四)秉持创新理念
创新是媒介素养教育的内在要求和发展动力,也是应对现代社会复杂媒介环境的必备素养。网络媒介、数字媒介等新媒介的产生和发展丰富了媒介的形式和内容,同时也增加了媒介环境的复杂性。新媒介技术在广泛并且深刻地影响日常生活的同时,也要求人们打破传统的媒介思维方式,增强批判性地分析媒介和媒介内容的能力。媒介素养教育不只是要求学习者认识、了解不同的媒介或掌握某些媒介的使用方法,更重要的是促进思维的提升和发展,最终实现个体的自我发展。在2019年《政策》中,芬兰教育文化部指出,“媒介素养是指人们使用、消费、理解媒介的能力以及创造媒介内容的能力。”创新性贯穿芬兰媒介素养教育发展始终,推动其不断发展和进步,是芬兰媒介素养教育的内核。
芬兰媒介素养教育的创新性集中体现在教育对象、学习材料等方面。一是教育对象的创新性,芬兰创新思路,将媒介素养教育的目标群体扩大到全体公民,促使媒介素养教育在理解和尊重群体差异的同时,加强个性化和专业化,朝着更具包容性和创造性的方向发展。二是学习材料的创新性,芬兰媒介素养教育关注学习材料的可获得性和有效性。包括芬兰广播电视台(Yle)、芬兰报业协会在内的众多行为主体创造性地为人们提供了多样且易于获得的媒介素养学习材料,确保学习材料能够满足学习者的个性化需求。三是教育形式的创新性,在学科教学和课间活动以外,芬兰还提供了媒介巴士项目(Mediabus)、报纸周(newspaper week)等丰富的教育形式作为学校教育的补充,帮助学生认识、理解多样化的媒介。
六、结语
媒介素养教育是提高公民媒介素养的主要途径,芬兰媒介素养教育所取得的成就离不开其媒介素养教育政策的支持和保障。从芬兰媒介素养教育政策的演进历程和整体架构来看,媒介素养教育政策为芬兰发展媒介素养教育提供了导向和指引,促使其朝着全民性、多样性和综合性的方向发展。我国已经进入了“全程媒体、全息媒体、全员媒体、全效媒体,信息无处不在、无所不及、无人不用”的全媒体时代,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中,应充分考虑当前社会转型的背景和舆论生态、媒体格局、传播方式的深刻变化,立足国情,不断推进完善媒介素养教育,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质量媒介素养教育发展。
一是加强政府统筹规划。政府统筹规划能够从宏观上明确我国媒介素养教育的发展目标、实施路径和薄弱环节等,是我国落实和推进媒介素养教育的重要保障。因此,我国政府应出台专门的媒介素养教育发展规划,从国家层面完善媒介素养教育法律保障,教育体系设计和政策效果评估,为媒介素养教育本土化研究和实践提供政策指引,促进媒介素养教育规范化和系统化发展。同时,应在政策中给予地方一定的灵活性,允许各地结合本地区实际情况发展各具特色的媒介素养教育,丰富媒介素养教育的多样性。
二是动员社会各界力量。社会力量能够在我国发展媒介素养教育进程中发挥积极的补充作用,尤其是电影、报纸、电视等媒体业相关企业和组织在提供资金支持、开展主题活动、丰富学习材料等方面具有显著优势。高校是开展媒介素养教育本土化研究和培养媒介素养教育专业人才的主要阵地。因此,我国应优化整合资源,在政府统筹规划的基础上,发挥高校、媒体业以及其他行业的企业或组织等多元主体的作用,丰富媒介素养教育的内容和形式,加强媒介素养教育研究和人才支持,为开展全民化和多样化的媒介素养教育提供支持。
三是凸显媒介素养教育的多样性和全民性。发展具有多样性和全民性的媒介素养教育是基于媒介和媒介素养的本质属性,适应时代变化的必然选择。一方面,媒介和媒介素养本质上具有跨学科性和综合性,因此发展媒介素养教育应当注重保障多样性。另一方面,复杂、多样的媒介已经成为全体公民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媒介素养是现代社会公民的必备素养,因此发展媒介素养教育应当注重提升全民性。我国发展媒介素养教育应兼顾教育对象的群体特征和个体特征,尤其是考虑老年人等弱势群体的特殊需求,发展多样化和个性化的媒介素养教育,切实改善全体公民的媒介素养。
四是坚持技能培养与思维发展并重。媒介素养既包含技术和能力层面的内容,也包含思维、认知层面的内容。学习使用、消费、创作、辨别媒介或媒介内容的技术和能力有助于正确认识和理解媒介,同时,发展对媒介的合理认知是正确运用媒介的前提。因此,我国发展媒介素养教育应坚持技能培养和思维发展并重,增强公民使用、消费媒介的能力,同时着力改善对媒介的批判性分析和创造性使用的能力。
当然,芬兰媒介素养教育政策也存在一定的不足之处。一是芬兰媒介素养教育政策制定的目标较为宏观和笼统,并未明确阶段性发展目标;二是芬兰媒介素养教育政策对未来媒介素养教育发展做出了展望,但并未明确具体的实施路径和行动方案,在实践指导上有所欠缺;三是芬兰媒介素养教育政策肯定了多元主体的重要性,但并未对多元主体进行有效的协调和统一,尤其是非政府组织等社会力量,不利于最大程度地整合资源,可能导致媒介素养教育的分散性和非均衡性。
注释:
① 张蕊、高宁:《公民媒介素养教育的西方范式与中国路径》,《东岳论丛》,2018年第4期,第185页。
② Sirkku K,Reijo K.MediaandInformationLiteracyPoliciesinFinland,2014.p.2.
③ Reijo K,Sara S,Juha S.DecadesofFinnishMediaEducation,2008.pp.12-13.
④ 耿益群、王鹏飞:《数字环境下欧盟媒介素养政策演进趋势》,《现代传播》,2016年第1期,第147页。
⑤ Ministry of Education and Culture.GoodMediaLiteracy:NationalPolicyGuidelines2013—2016,https://minedu.fi/en/publication?pubid=URN,2020-03-20.
⑦ 王洁、徐瑾劼、黄开宇:《培养学生面向未来能力的教师专业认识与准备——基于UNESCO亚太地区的实证研究》,《全球教育展望》,2017年第12期,第101-102页。
⑨ Tanriverdi B,Ozlem A.AnalysisofPrimarySchoolCurriculumofTurkey,Finland,andIrelandinTermsofMediaLiteracyEducation.Educational Sciences:Theory and Practice,vol.2,no.10,2010.p.12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