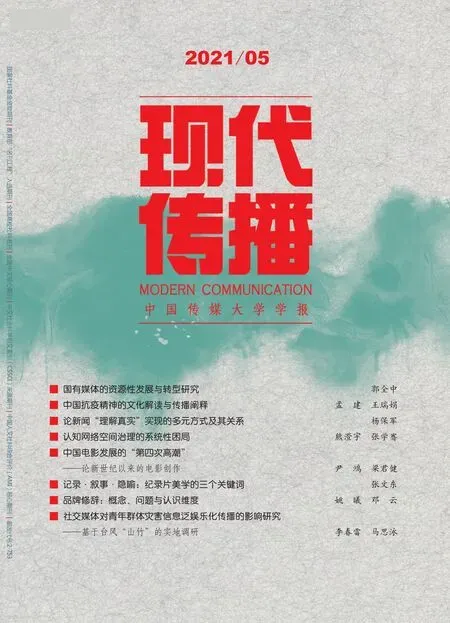溯源与流变:中国纪录片“精英文化”的观念史考察
2021-12-02孙振虎
■ 孙振虎 赵 甜
一、问题的提出
精英文化作为知识分子文化的典型样态,在中国社会文化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国内关于精英文化概念的研究,以学者邹广文的界定为主,指的是“知识分子阶层中的人文知识分子创造、传播和分享的文化”,对社会进行教化、对价值产生规范是其主要作用,精英文化是“‘经典’和‘正统’的解释者和传播者”。①
中国纪录片诞生于革命战争的历史背景,从新闻宣传和报道影像中脱胎,着眼于反映重大社会问题,因此思辨精神、品位高雅成为了其作为“精英文化”而存在的典型特征,“精英文化”所具有的气质是中国纪录片的“外显”属性。从1911年我国首部真正意义上的纪录片《武汉战争》诞生之日起,中国纪录片便从影像作为“影戏”时代记录杂耍的工具的单薄功能中剥离出来,宣传进步思想、反映社会问题成为了中国纪录片承担社会教化使命、发挥价值规范导向功能的指导思想。在以上语境中诞生的中国纪录片,宣传教化是其主要的社会功能,精英性成为了固有的文化基因。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纪录片发展的鼎盛时期,其“精英文化”的气质更是表现得淋漓尽致。纪录片创作者们所代表的崇尚独立精神与自我价值实现的气质交织在一起,使得纪录片常常与“高品位”联系在一起,形成了中国纪录片界“梦一样的现实”②。新世纪初,“阳光卫视”纪录片频道诞生,作为中国首个“严肃高雅的纪录片频道”③,以全球精英人士为服务对象。尽管该频道最终悲壮退场,其追求纯文化理想的实践仍是代表“精英文化”气质的历史性事件。2011年,以“高端的媒体属性、高质的频道受众、高度的传播覆盖”④为宗旨的CCTV9纪录频道开播,并将“高学历、高收入、高职业”的收视群体作为目标受众,“大气、从容、冷静、理性”⑤成为频道主体风格,无不体现着纪录片作为文化产品的精英文化品位。时至今日,纪录片仍被视为“电视文化的守望者”⑥,享有“胶片盒子里的大使”“国家相册”“人类生存之镜”等一系列美誉,承担着“精英文化”的社会使命。
然而,尽管“精英文化”的独特气质已成为中国纪录片的创作与传播的“外显”属性,在纪录片领域对“精英文化”观念的研究却处于相对缺失状态。现有的重要著作和期刊文献,关于纪录片“精英性”的研究占比较小,部分研究仅对纪录片“精英文化”气质的具体现象进行了阐释,但对其本质的研究尚未成体系。因此产生了一种奇怪的现象:一方面,“精英文化”观念已经深刻影响了中国纪录片创作与传播实践,“精英性”几乎成为我国纪录片发展的默认属性;另一方面,这种精英性的界定、“精英文化”观念的产生过程等本质性问题却处于说不清道不明的状态。这种在实践领域内已经“外显”的“精英文化”观念,成为了纪录片研究领域内“内隐”且模糊的观念,始终被提及却难以清晰地被界定。
如何理解中国纪录片的“精英性”? 这种看似自然而然形成的“精英文化”观念,是在怎样的历史语境中被建构出来的?在人人拥有影像记录工具的新型媒介环境下,尤其是大众文化日益占据主流文化版图、泛娱乐化现象愈演愈烈、后现代主义思潮盛行的当下,纪录片所代表的精英文化属性是否仍合乎时宜?我们应该如何在偌大的文化地图中为中国纪录片寻求合理定位,以更准确、科学的观念指导我国纪录片的创作与传播实践,助力其产业勃兴与价值回归?只有对以上问题作出解答,才能找到中国纪录片产业蓬勃发展的路径。
二、当前矛盾:“精英文化”观念惯习与市场需求的不匹配
(一)市场遇冷:“精英文化”观念带来的生存困局
近年来,我国优秀国产纪录片层出不穷,“舌尖”“匠人”“风味”系列纪录片的火爆,在一定程度上提振了中国纪录片创作与传播的信心。然而,相较于整个纪录片庞大的生产规模来说,这些现象级的纪录片仅仅是沧海一粟。《中国纪录片发展报告》历年数据显示,我国纪录片生产的“产品率”多年只徘徊在10%左右,近九成的纪录片无法从文化作品转化为文化产品,实现文化商品层面的流通更是难上加难。调查报告显示,“近10年来,中国纪录片市场规模大幅增长,但以定制市场、委托制作市场为主的格局并没有发生变化,一半靠政府,一半靠市场。完全依靠市场和注意力销售收回成本的纪录片凤毛麟角,健全的市场体系尚未形成”⑦。纪录片的盈利模式相对单一,“收视率普遍不高,广告价格也相对比较低”“衍生品开发环节基本处于缺失状态”⑧的窘况依然存在。《中国纪录片发展研究报告2020》报告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纪录片生产总投入为50.36亿元,年生产总值约为66.60亿元,同比增长3.3%,增幅为近10年来最低值”⑨。中国纪录片真正的繁荣时期还未到来,在影视传媒领域市场化改革倒逼纪录片走向市场的语境下,“精英文化”的固有观念与市场运行规律之间存在有待弥合的空间,这为中国纪录片的发展带来了生存困局。
(二)边缘地位:中国纪录片的发展桎梏
如图1所示,为助推我国纪录片产业发展,广电总局自2010年起便发布了一系列政策规划。2010年发布的《关于加快纪录片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对振兴纪录片产业提出了总要求;2013年“加强版限娱令”下发,明确要求上星频道“按周计算平均每天6:00至次日1:00之间至少播出半小时的国产纪录片”⑩;2015—2017年,《百人百部中国梦短纪录片扶持计划》通知的出台,投入了大量财政资金,旨在激发短纪录片的发展活力;2018年广电总局在面向2018—2022年的规划文件《关于实施“记录新时代”纪录片创作传播工程的通知》中再次明确规定“每个电视上星综合频道全年在19:30—22:30时段播出国产纪录片总量不得低于7小时”。
然而,即便国家已在政策层面着力推动纪录片产业的发展,当前中国纪录片在整体上还是难以摆脱其长久以来的边缘属性。小众传播经常被概括为纪录片传播的特点,业界更将此奉为圭臬,甚至在2011年中央电视台纪录频道正式开播前,该频道“在九个月时间的调研中,首先考虑的就是自己可能‘仅有’的受众群体究竟在哪里”的问题,可见纪录片工作者群体内部早已对纪录片的“小众化”达成一定共识。《中国纪录片发展研究报告》历年调研结果显示,近年来专业纪录频道面临着严重困局:“专业纪录频道在资金、资源与传播空间上受限”,已上星的卫视频道的大部分纪录片还是活在卫视的“睡眠时间”,播出时间多为深夜。湖南卫视、黑龙江卫视以及江苏卫视将“中国梦”题材纪录片安排到凌晨一点至六点排播,浙江卫视和云南卫视自制精品纪录片《西湖》和《经典人文地理》,也未能在播出时间上赢得先机。在一定程度上,中国纪录片所代表的“精英文化”气质,带来了小众传播、边缘化的尴尬境地,即便在国家政策的助力下,一时间也难以实现产业勃兴。
三、“精英文化”观念的形成与发展
由以上叙述可知,中国纪录片所具有的“精英文化”观念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产业发展中市场遇冷、边缘化的焦虑境地,生存困境已成为制约中国纪录片产业发展的巨大阻碍。然而,更重要的问题在于,中国纪录片这种看似自然而然形成的“精英文化”气质,究竟是如何被建构起来的?中国纪录片为何具有“精英性”?只有真正透彻地分析清楚以上问题,才能有的放矢地为中国纪录片改变焦虑困境开出对症药方。
(一)“形象化的政论”:胎记般的烙印
中国纪录片脱胎于新闻纪录电影,“形象化的政论”在该历史进程中是一个无法回避的关键词。“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它就是我国新闻纪录电影的代名词,而且在电视崛起后对电视新闻与电视纪录片创作产生持久的内在影响”。“形象化的政论”作为指导我国纪录片创作的核心理念而被应用,在漫长的历史实践过程中逐渐演变为一种媒介生产惯习。新中国的纪录片由新闻纪录片发展而来,在该思想的指导下,我国的纪录片创作与传播更多重视作品自上而下的宣教作用,无形中形塑了中国纪录片的“精英文化”气质。
“形象化的政论”是1925年列宁与卢那察尔斯基谈话中的观点,列宁明确提出:“它(新闻片)应该是形象化的政论,而其精神应该符合我们优秀苏维埃报纸所遵循的路线”“新闻电影工作者应该向我党和苏维埃的报刊的优秀典范学习政论,应该成为拿摄影机的布尔什维克记者”。1954年初,《人民日报》发表了《进一步发展人民电影事业》的社论,明确指出“新闻纪录片应该是报纸的兄弟”。这样的宣传逻辑继续得到贯彻,1960年陈荒煤在题为《加强新闻纪录电影工作的党性》的讲话中指出:“新闻纪录电影可以说是党报的兄弟。我们能不能及时地、迅速地、正确地反映现实,正确地宣传总路线,都决定于是不是紧紧地依靠党委的领导”。这次讲话,将纪录片作为“形象化的政论”“党报的兄弟”的观念贯彻到了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的创作中,“形象化的政论”成为了新影厂的创作传统。由延安电影团组建的新影厂,是当时我国唯一生产新闻纪录影片的专业机构,我国早期的纪录片创作人才均出自该单位,其纪录片创作与传播的观念决定了我国纪录片发展的历史脉络。
在中国电视诞生初期,电视纪录片与电视新闻之间的界限十分模糊,纪录片所拍摄的题材往往是围绕执政党中心工作以及宣传方针而设定的新闻题材,纪录片与新闻片往往含混为一体,这也导致了“形象化的政论”传统得以沿袭。以陈汉元为代表的我国早期纪录片创作主力也曾表示,其对“形象化的政论”的断言是“确认无疑,而且是刻骨铭心的”,在这种思维的影响下,由这些创作者们拍摄的包括中央新影和地方电视台在内的纪录片都具有了“形象化的政论”的影子。《英雄的信阳人民》《铁人王进喜》《光辉的榜样焦裕禄》《收租院》《周恩来访问亚非14国》《大庆在阔步前进》等纪录片,主题围绕一化三改、社会主义生产建设、阶级斗争等主题展开,纪录片的新闻性超过艺术性,声画分离且依靠解说词的阐述式内容居多,喊口号式的宣教风格成为主导色彩,宣传意味浓厚,画面表现单一,因此被称为“格里尔逊式的宣教纪录片”。甚至在文革时期,拍摄领导人的运动镜头只能由远及近,不能由近及远,因为领袖不能远离人民。被政治意识形态捆绑的纪录片常以宣教工具的面貌存在,政治意义大于影像意义,在新闻纪录片占据主流的时期,“形象化的政论”成为了当时纪录片创作的核心观念。
由此可见,在观念层面,我国的纪录片创作与传播沿袭了苏联时期的传统理念。首先以列宁“形象化的政论”为指导原则,而后在我国的实践中具体落实为“党报的兄弟”,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而存在,“形象化的政论”正如胎记一般深深地烙刻在中国纪录片的身上。然而,仔细分析便会发现,列宁提出“形象化的政论”的论述,原本是针对于“新闻片”的创作与传播观念。“列宁说的‘形象化的政论’是指新闻影片,却被当成是纪录片的唯一定义,这必然导致对纪录片特性、功能的狭隘理解及认知上的偏差。”由于历史的特殊原因,我国早期纪录片与新闻片之间的界限并不清晰,新闻纪录电影作为纪录片的主要形式而存在,“形象化的政论”自然而然地从新闻纪录电影领域拓展到更大范围内的纪录片的创作原则。在纪录片的概念逐渐明确、类型日益多样的发展趋势下,以“形象化的政论”观念指导纪录片创作与传播实践,必然会出现方枘圆凿的尴尬境地。“形象化的政论”“党报的兄弟”这种媒介生产惯习所带来的自上而下的说教传统,无意间将纪录片这种原本极具影像魅力的艺术形式,拔高到阶级斗争的高度。自上而下的宣教作用掩盖了纪录片的艺术魅力。“形象化的政论”带来的宣教特点,使得我国纪录片从诞生之日起便成为了“精英文化”的一份子。
(二)“文人电视”:知识分子情怀的表达
1954年,弗朗索瓦·特吕弗发表了题为《法国电影的某种倾向》的文章,将导演视为影片的真正作者,奠定了“作者论”的理论基础。安德烈·巴赞紧随其后,发表了题为《论作者论》的文章,强调应从作者的角度去品读、解码作品。从《北方的纳努克》诞生起,纪录片作为影像作品的一大类别,其文本始终与作者捆绑在一起,无论是“直接电影理论”还是“电影眼睛派”指导下的纪录片,在坚持真实的同时,始终蕴含着创作者的观念表达。因此,要回答清楚“中国纪录片‘精英文化’观念是如何形成的?”这一问题,就要对作为知识分子的纪录片创作者进行考察。
在传统儒家思想的哺育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历代中国文人的共同目标,“文以载道”也因此成为了书生报国理想得以实现的主要方式。在“文以载道”传统观念的影响下,作为知识分子的中国纪录片创作者尤其重视纪录片这一媒介载体所承担的社会使命。纪录片“所体现的典型的电影特性和它传达意识形态无与伦比的方法优势,让纪录片人不由自主背负起且迷醉于一种责任感、使命感”,这一特征自20世纪80年代中国纪录片走向人文化时期便表现得尤为显著。随着改革开放的到来,中国社会的思想迎来了解放,作为社会精英的知识分子在思想解放的时代拥有了表达的权利。“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成为了中国纪录片创作群体的文化自觉和历史自觉。作为精英知识分子的纪录片创作者们牢牢抓住纪录片这一话语武器积极进行主体价值的表达与言说,对社会现实、国家命运进行思考和发声。自此,纪录片创作者所奉行的精英话语、弥漫于中国社会的爱国主义与进取情绪糅合为一种“不充分的纪实精神”,在80年代理想主义文化空气的熏陶下,成就了“文人电视独领风骚的岁月”。作为“文人电视”文化的承载物,纪录片成为了创作者们作为知识分子表达情怀、实现文人治世理想的关键,其“精英文化”的气质也与日凸显。
《话说长江》《话说运河》作为20世纪80年代纪录片的典型代表,蕴含着纪录片工作者们深重的知识分子情怀。这两部反映我国人文地理概貌的纪录片,由戴维宇导演、陈汉元撰稿,采用章回体的形式拍摄而成,旁白华丽、思想深邃、规模宏大。在《话说长江》的创作中,戴维宇导演特别邀请了虹云、陈铎这两位老艺术家借助中国古典小说章回体的结构形式将长江两岸的风土人情在讲述中娓娓道来,文学意味深厚。《话说运河》第一集《一撇一捺》中“这长城是阳刚雄健的一撇,这运河不正是阴柔深沉的一捺吗?”“巍峨的长城是我们的祖先用自己的骨和肉筑造的,深沉的运河是我们祖先用自己的血和汗灌注的”等工整对仗、饱含深情的解说词便是“文人电视”文化的典型样态。这种文学气息浓厚的创作风格,带来了一批诸如《让历史告诉未来》《唐蕃古道》《共和国之恋》《黄河》《万里长城》的纪录片。从此,民族精神成为主题表征,文学化的影像创作方式成为主流,作为知识分子的纪录片创作者们将自己对家国、民族、社会的关怀注入到纪录片这一影像文本之中。理想气息和人文气质的关照,使得中国纪录片有别于一般的通俗文化作品,承载着“精英文化”的深厚价值内涵。
这种“文人电视”的观念在20世纪90年代继续得到发扬,人类学纪录片的迅猛发展唤醒了纪录片创作者们作为知识分子特有的独立精神。在这一时期,出现了象征独立创作精神的个人小作坊式的创作群体,也造成了“对一些弱势群体和边缘群体进行一些貌似平等、实则借助媒介的力量强行做不平等的窥视似的记录”。《沙与海》《藏北人家》《深山船家》《最后的山神》《老头》《龙脊》《回家》《神鹿啊,我们的神鹿!》《山洞里的村庄》《婚事》等一系列深入边缘地区、探寻古老生活方式与反映社会矛盾的纪录片,都是创作者以知识分子视角关照社会现实、表达治世情怀的代表作品。导演杨荔钠在拍完纪录片《老头》之后,直言不敢再回头看这些老人们,因为片中对老者死亡挣扎时刻的展现,暴露出其由于过分追求独立精神而造成的近乎冷漠的、自上而下式的精英审视视角。同在这一时期出现的《半个世纪的乡恋》《德兴坊》《毛毛告状》《大动迁》,分别反映“慰安妇”问题、住房问题、底层群体生活困境、改革开放与城市拆迁矛盾,无一不体现创作者们对于社会现实的深切体察。冯乔《我想有个家》《刘金海与成功教育》《我的潭子湾小学》的“教育三部曲”,主题的表达没有停留在单纯的记录层面,而深入到了知识分子对于教育问题的关照与思考层面。
新世纪以后,中国纪录片的类型更加多元,但与同时期消费主义主导下的电影、电视剧、综艺等大众文化产品不同,中国纪录片在一定程度上仍保留着长久以来的文化品格。2000年,中央电视台纪录片栏目《见证》开播,在选题方面多以关乎国计民生的重大题材为主,风格相对严肃厚重。2003年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唯一的新闻纪录片栏目《纪事》开播,以打造“行进中的影像中国”为宗旨,再次引领了新闻纪录片的创作热潮,但其叙事语言仍有文学化的意味。与此同时,以《雾谷》为代表的纪录片,通过夸张的手法对假权倨傲的社会现象进行讽刺,开辟了社会学纪录片的新路径。2006年中国广播电视协会纪录片委员会举办的“中国纪录片选片会”上,也专门设置了“社会报道类”纪录片的评选项目,通过纪录片关怀体察社会,成为了为创作者们公认的文化自觉。在美学风格、表现手法方面出奇制胜的纪录片《北京的风很大》引发了极大关注,这种颠覆性的影像表达方式尽显实验性纪录片的特质,但过于先锋的创作理念也容易造成纪录片与普通观众之间的疏离感,纪录片成为创作者们隐喻现实的“圈子艺术”,与日渐崛起的大众文化相背离。除此之外,一系列诸如《故宫》《大国崛起》《复兴之路》《河西走廊》等纪录片的出现,使得纪录片的历史厚度、文化底蕴得到升华,构筑起纪录片创作者们对“大国”的文化想象。2012年现象级作品《舌尖上的中国》引领了美食类纪录片的创作风潮,但美食并不是该类纪录片的核心,透过美食展现东方生活价值观才是要义所在。2014年至2016年涌现的《爸爸去哪儿》《奔跑吧兄弟》等一系列娱乐纪实电影显现出粉丝经济的强势,学界和业界对于这种快消式的纪实影像形态定义存疑,这种对娱乐纪实电影的警惕也在一定程度上映射出创作者们对纪录片与娱乐元素相结合的潜意识中的抗拒心态。事实上,在纪录片形态日益多元、“纪实+”产业面貌日渐凸显的今天看来,对粉丝经济的良性引导和运用也不失为助力纪录片产业发展的一个途径。此前的这种抗拒心态恰好反映出创作者们对纪录片文化品格的高要求。2017年,中国首部获得公映许可的慰安妇纪录片《二十二》的出现,也正是体现了创作者们对于社会问题的深刻揭示。近年来,《生门》《我的诗篇》《摇摇晃晃的人间》《四个春天》《三矿》等社会现实题材纪录片崛起,发挥纪录片“打造社会的锤子”的功能,以期影响现实生活,成为了创作者们关怀社会的具体方式。
由此可见,在作为知识分子的纪录片创作者眼中,纪录片从来都不是单纯的影像记载工具,而是表达文人情怀、实现社会关照的载体。即便是在全面拥抱消费文明、泛娱乐化现象愈演愈烈的当下,中国纪录片创作者们仍坚守着一定的文化品格,“文人电视”是创作者们对纪录片社会功能的共同期待。最新的关于纪录片从业者的调查显示,“重情怀轻回报”仍是当下纪录片创作群体的显著职业特点。这种饱含文人治世理想的纪录片创作与传播观念,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来自知识分子自上而下的审视感,难以放下身段满足普通观众对于精神文化消费品的需求。因此,中国纪录片作为“精英文化”载体的地位不断被拔高,成为了曲高和寡的艺术形式。
四、结论与展望:“精英文化”观念的思考
中国纪录片的影像技术和拍摄手法习于西方,这种最初被西方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用来探讨文化与社会问题的影像文献手段,在功能主义的媒介范式影响下与中国历史语境相契合,成为了由作为知识分子的创作群体推动、对主流价值观进行阐释、具有社会教化和价值规范作用的“精英文化”的典型样本。“形象化的政论”和“文人电视”的创作与传播观念,共同形塑了中国纪录片“精英文化”的独特气质。中国纪录片“精英文化”观念的本质是人文理想的影像化呈现,无论是“形象化的政论”带来的说教传统,还是“文人电视”体现出的知识分子的社会关照,都存在一定的审视态度,这使得中国纪录片不断被推向神坛,成为了曲高和寡的影像文本。
纪录片并不是一种静态的、固定的文化形式,反而正是文化研究学者威廉斯所说的“活文化”,是一种“‘普通人’在与日常生活的文本与实践的互动中获取的‘活的经验’”。从“精英文化”向“大众文化”靠拢,改变长久以来自上而下的审视视角,拉近与普通观众之间的距离,是当前中国纪录片创作与传播的必然路径。
具体而言,有以下两种实践转向:一方面,纪录片应直面大众娱乐消费的需求,以精神文化消费品的身份走向大众。在全面拥抱消费文明的当下,市场话语的强势入侵带来了整个文化生态向大众文化迈进的趋势,满足人们娱乐休闲的需求,成为文化产品的一个归宿。在大众文化日益占据主流文化版图的今天,“精英文化”观念为中国纪录片的发展带来了生存困境,抛却旧有的严肃沉闷、呆板说教的“高冷”面貌,以轻松愉悦、清新生动的创作特点吸引观众,走出精英话语的固有框架,成为市场话语下的大众文化产品,是中国纪录片走下神坛的关键一步。近年来,《早餐中国》《宵夜江湖》《人生一串》《十三行》《可以跟你回家吗》《此画怎讲》等一系列具有后现代主义解构精神的纪录片赢得广泛好评,为中国纪录片提升自身影响力、传播力带来了借鉴经验。
另一方面,融媒体时代的到来,赋予了普通人通过影像进行自我表达与记录的权利,中国纪录片的创作与传播有望成为一种参与式文化。关于布迪厄强调的“文化资本”一词,我们不难理解:在人类社会的绝大多数时间内,底层百姓的文化活动是难以在历史上留痕的,占据文化资本的群体也就占据着被记录的机会,普通人因为缺少文化资本,其日常实践始终都处于“发生即消失”的状态。随着媒介技术的发展和媒介形态的变革,记录工具的普及已宣告着“人人都能成为记录者”时代的到来,影像纪录作品的创作早已成为超越影像本身的参与式文化。以《浮生一日》为代表的众筹式纪录片的出现,将大众群体纳入到纪录片创作与传播的过程中,在充分激发观众作为纪录片创作者的参与热情的同时,使得纪录片创作打破了“被精英知识分子垄断”的刻板印象,成为普通观众也可参与的大众文化。此外,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爆发时期,清影工作室《手机里的武汉新年》、人民日报《凌晨四点的武汉》、上海广播电视台《温暖的一餐》以及大象点映《余生一日》等以UGC短视频素材为来源制作的疫情题材纪录片广受好评。作为当前大众参与式纪录片创作的典型样本,它们充分动员大众参与纪录片创作,显现出纪录片走下神坛后融入大众生活、承担起其社会责任的巨大潜力。
纪录片本该且必然是大众生活与大众文化的一部分,亟需撕去“精英文化”的价值标签。在影像作品早已不是感官奢侈品的今天,中国纪录片的创作与传播应“飞入寻常百姓家”,及时向群众日常生活靠拢。这不仅是关乎产业良性发展的现实路径,更是在文化权利维度实现向人民赋权、将视觉权力下放给普通大众的积极尝试。
(本文系中国传媒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中国纪录片的市场化历史研究”〔项目编号:CUC200D017〕的研究成果。)
注释:
① 邹广文:《当代中国大众文化及其生成背景》,《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2期,第47页。
② 何苏六:《纪录片市场化:中国问题与外国方法》,《现代传播》,2005年第3期,第102页。
③ 何苏六:《中国电视纪录片史论》,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37页。
④ 刘文、张国涛:《修行与探索:央视纪录频道的元年盘点》,《现代传播》,2012年第2期,第88页。
⑤ 李艳峰:《新开局 稳探索 向未来——CCTV-9纪录频道的传播运营之道》,《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12年第12期,第72页。
⑥ 韩飞、何苏六:《新旧动能转换视野下的中国纪录片产业发展》,《当代电影》,2019年第9期,第129页。
⑦ 张同道:《2019年中国纪录片发展研究报告》,《现代传播》,2020年第7期,第112页。
⑧ 张红军、毛阅:《中国纪录片产业链现状分析及策略建构》,《现代传播》,2011年第6期,第84页。
⑨ 《〈中国纪录片发展研究报告二〇二〇〉发布》,《新闻世界》,2020年第5期,第52页。
⑩ 引自中国纪录片网报道《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规定2014年起上星频道须播出纪录片》,中国纪录片网,http://www.docuchina.cn/2013/10/17/ARTI1381981117516466.shtml ,2013年10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