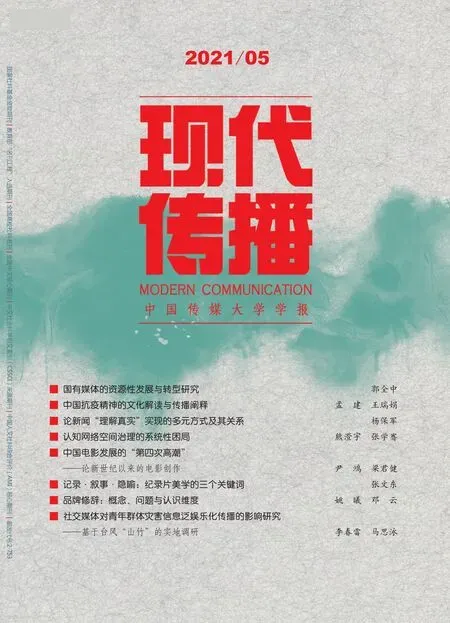时间的亲密涵义
——数字化情感交流中的时间体验及其关系意涵
2021-12-02■粟花
■ 粟 花
一、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以来,情感在私人生活中的重要性显著上升,人们对情感表达和沟通的期待成为当代情感文化的重要特征。年轻人越来越不满足于老一辈通过行动表达爱的传统做法,他们更加青睐通过语言直接表达感情,并从流行文化、大众媒体和西方婚恋习俗中借鉴了许多表达情感的语言和方式。数字媒介的发展助推了这一情感文化的趋势,手机短信、即时聊天工具和层出不穷的社交平台为年轻人的情感交流提供了丰富的表达和互动资源。然而,情感表达和沟通的语言化、数字化给亲密关系带来的影响的相关研究,还很少有深入的探讨。
人类学家阎云翔是最早研究这一现象的学者之一,他认为,对个体情感的重视和对情感表达的期待,是中国社会个体化的表现,但是通过语言还是其他方式表达情感,对关系本身无关紧要,“重要的是两个当事人是否有办法能够相互表白”①。阎云翔的这一评论是针对美国学者波特夫妇的观点进行的反驳,后者观察到中国农村夫妇很少用言语表达感情,由此推断感情对农民来说并不重要。阎云翔的驳论准确地指出波特夫妇的西方中心主义视角,因为存在大量非语言的情感表达方式,足以证明爱情在中国农民生活中的重要性。②然而,这一论述也将交流媒介对亲密关系的影响悉数抹去。如果波特夫妇用语言交流直接对应情感关系的本质,算是一种(语言)媒介决定论,阎云翔的批评则将情感本质化,认为交流形式无涉于关系本身,媒介是透明的。这两种观点都很难帮助我们进一步探讨当前强调语言表达的情感文化对亲密关系的影响,更无益于理解新媒介在其中扮演的角色。
事实上,朴素的媒介透明观和媒介决定论充斥着我们对交流媒介的想象。一方面,媒介隐形通常是正常交流的前提,交流双方一旦接受到信息便“得鱼而忘筌”。如果不是新技术及其来带的怀旧情绪(如对书信的怀念),人际交流在媒介研究中常常被简单化。因为人际交流不同于大众传播,后者涉及庞大的机构组织和明显的权力关系,让人很难忽视媒介对信息及其接受的影响,而人际交流琐屑庸常,除了在提高技巧(“交际”)、强调效果(“沟通”)、鼓励参与(“互动”)之时,极少受到关注,遑论其媒介的运作。但另一方面,无论是艺术表达还是文化评论都常常将交流媒介作为思考文化变迁的方便工具,如将车马的缓慢对应爱情的持久与深刻,将网络的迅捷看作关系的淡漠与短暂。然而时间的快慢、感情的深浅、关系的长短之间的简单对应,或许符合人们的直觉,却暗藏流行的技术决定论,与波特夫妇将语言表达和情感关系的直接对应并无二致。
如何理解以语言为表达媒介的情感文化对亲密关系的影响?如何理解新媒介在其中的作用?如果迅捷是数字化交流最重要的特征之一,那么快速的数字化语言表达对亲密关系意味着什么?要避免在回答这些问题时落入媒介透明观和媒介决定论的陷阱,需要深入亲密关系中的交流实践,在联系宏观的情感文化与微观的媒介实践的同时,也要区分交流形式和亲密关系的分析层次。本研究扎根于情感交流的经验数据,结合亲密关系变迁的社会理论和媒介人类学的概念工具,通过分析城市青年在恋爱中赋予媒介时间性的意义,来探讨这些问题。
本文的经验数据来自于2011、2012、2014和2018年进行的半结构式深度访谈。访谈对象为城市青年,目的是了解参访者在恋爱交友过程中的媒介使用,而情感表达和沟通是其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参加访谈的总人数为70人,在访谈时绝大多数受访者居住在北京,年龄介于20—35岁之间,以在校大学生、研究生、城市白领为主。访谈时间平均为一小时以上,此文中的数据为其中一部分。由于数据收集的时间跨度较大,在此期间城市青年使用的交流媒介发生了一些变化,尤其随着4G网络的普及和流量费用的降低,智能手机逐渐成为城市青年主要的交流工具,并出现许多形态各异的手机应用。这个历时的变化为本文的分析增加了难度,但也为本文的论点提供了更有力的佐证,因为城市青年使用的媒介虽然种类多样,且用法各异,但却体现了一些相似的逻辑和总体性特征。本文的发现虽不具有量化意义上的代表性,但使用者在合理化自己的媒介使用、解释自己和他人赋予媒介的意义以及在恋爱中协商媒介使用的规则时,所诉诸的文化观念和体现的交流逻辑,却可为讨论媒介化的亲密关系提供更具普遍意义的洞见。
二、现代亲密关系中的情感沟通与媒介使用
沟通是现代亲密关系的突出特征,它被赋予了极高的情感价值,也是亲密关系中矛盾和悖论的重要来源。互联网与数字技术在革新交流方式的同时,也反映和加剧了现代亲密关系面临的困境。这些矛盾和困境在社会理论中有较多论述,在新媒介研究中也有不少提及,但这些理论大多基于西方语境的讨论,且常常夹带具有西方文化特性的交流观念。这些理论为本文提供了部分分析思路,也是本文试图拓展的学术对话。
以语言为媒介的自我坦露(self disclosure)式沟通,是西方学界定义“亲密”概念的一个重要指标。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在论述现代社会亲密关系转型时,着重强调了这种沟通方式与亲密关系的紧密联系。他认为,伴随着晚期现代性的不确定感和社会变迁,传统习俗对个人生活的影响式微,亲密关系朝着“纯粹关系”的方向发展,不再依据外在的规范来建立和维持,其存在的唯一依据是双方从关系中获得的满足感,而维系关系的关键在于双方进行自我坦露式的沟通,并在此基础上欣赏对方的个体独特性。③琳恩·杰米森(Lynn Jamieson)曾批评这种“亲密”概念的文化特性④,并指出自我坦露式的沟通理想主要来源于心理治疗话语,其作用被大大高估了,因为现实中的亲密关系具有多样性和多维度的特点,不单依靠推心置腹的交流。⑤虽有这样的质疑,但情感分享和沟通在现代西方的亲密关系理想中长期占据核心位置。
近年来,越来越多西方学者注意到,脱离传统约束、仅靠情感沟通维系的现代亲密关系充满了矛盾和悖论。乌尔里奇·贝克(Ulrich Beck)与伊丽莎白·贝克-格恩斯海姆(Elisabeth Beck-Gernsheim)认为这些矛盾和悖论的核心是爱情、家庭与个人自由之间的持久冲突。从传统纽带中脱嵌出来的个体享有选择自己生活的自由,但同时也失去了传统纽带带来的确定性和认同感。为了逃离自由带来的孤独感和不确定性,个体转向亲密关系寻求安全感和归宿感。因此,个人自由和亲密关系之间形成永恒的张力,人们渴望接近对方又希望相互独立,坦诚的沟通并不能解决二者持久的拉锯战;相反,在沟通中分享真实的自我也意味着暴露冲突和不同,如果自我的感受就是决定关系走向的最终裁判,那么这样的沟通也可能意味着关系的结束。⑥因此,情感沟通不仅无法解决晚期现代社会亲密关系的困境,而且本身也是压力的来源。
随着移动互联网和社交平台的广泛使用,不少学者认为数字媒介反映或加剧了上述亲密关系的矛盾和困境。齐格曼·鲍曼(Zygmunt Bauman)对“液态爱”(liquid love)的论述颇为典型,他认为个体化瓦解了传统人际关系的稳定性和安全感,使亲密关系趋于液态化,变得短暂易逝,而移动电话和社交媒介则是这种“液态爱”的症候。对鲍曼而言,手机和互联网带来的迅捷联系体现了晚期现代社会中个体既渴望人际纽带又恐惧社会羁绊这一矛盾的心理,然而联系只是“虚拟的”关系,可以随时进入、退出、删除,像购物一样用户友好,但这样的交流快速而肤浅、急促而短暂,无法形成真正的情感联结。⑦雪莉·特克尔(Sherry Turkle)对“群体性孤独”的论述同样注意到数字媒介环境下的交流特点,她相信不间断的连接对亲密关系具有摧毁性力量,因为它使人们既无法独处也丧失了与他人建立亲密关系的能力⑧,因此她呼吁人们“重拾交谈”,认为只有面对面交谈才能建立真正的人际纽带。⑨
无论是鲍曼的宏观论述还是特克尔的实证分析,都将数字媒介带来的交流特点作为洞悉现代亲密关系困境的透镜,并对数字化交流的即刻性——快捷短暂或者随时在线表达了担忧。二者都认为这些时间特点无益于建立深刻的情感联结。然而,即刻性既无法反应媒介使用者对时间的全部体验,更无法确证使用者对情感深度的感知。在这点上,以计算机为媒介的传播(CMC)实证研究提供了不少有用的发现。该领域从质疑电子邮件、即时短信息等数字化媒介所能传递的情感范围,转向强调使用者的主观能动性,越来越突出媒介在情感交流中的作用和潜力。⑩约瑟夫·沃瑟尔(Joseph B.Walther)提出的超人际模型是具有代表性的理论,该理论认为数字媒介的特征为交流者加强印象管理、拉近与对方的关系提供了许多可能性,例如文字信息不必受实时互动的时间限制,所以交流者可以精心撰写和编辑信息,避免口不择言。而且交流者只需面对文字信息,因而可以避免被交流情景中的其他因素分散精力,将所有的认知资源集中于信息编写。这些媒介特征加上使用者的交往动机,使数字化文字媒介所能传递的情感的丰富性毫不亚于面对面交流,甚至超越身体在场的交谈。简言之,数字媒介除了即时传输的特点,也有延时交流的可能,尤其是文字消息,媒介化交流的时间特点在很大程度上受使用者的影响。
其次,特克尔对重回交谈的呼吁也暴露了其批评中所预设的沟通理想和亲密观念。对面对面交谈的理想化是二十世纪西方尤其是美国传播观念的一个典型特征,它可以追溯到苏格拉底对文字的批评和对对话的偏爱,并在二十世纪大众传播技术发展的过程中,成为西方知识分子反思传播伦理的重要工具。在亲密关系语境中,以自我坦露为特征的理想化交谈模式伴随着心理学和精神分析的发展,在西方中产阶级中逐渐扩散。这也是吉登斯论述“纯粹关系”的文化语境。特克尔对媒介化交流的批评同样根植于这一文化脉络,她的精神分析视角与心理治疗话语影响下的沟通理想和亲密观念相互印证。如果面对面交谈作为一种交流形式是思考媒介化交流的方便依据,那么面对面交谈作为情感交流和亲密关系的重要基石则具有鲜明的文化特性。
如果中国青年对情感表达和沟通的偏好多少受到西方流行文化的影响,他们是否在实践中认同西方对亲密关系的想象以及相应的沟通理想尚未可知。为了在分析中避免重复西方的交流观念,更为了发现中国城市青年对交流和媒介的理解,本文借助媒介意识形态(media ideology)这一概念作为分析工具。媒介意识形态的概念是语言人类学家在研究媒介使用的过程中对语言意识形态(linguistic ideology)概念的延伸。它指的是在特定的文化中人们对媒介和媒介化交流所持有的理解和预设。这些理解和预设逐渐成为媒介不可分割的部分,并影响着人们对新媒介的使用,使他们更可能排斥一些媒介而青睐另一些媒介。例如,一些美国青年排斥用手机短信发送分手消息,因为他们认为提出分手的一方应该给被动分手的一方直接表达情绪和意见的机会,而短信无法提供这样的机会。同样,毛里求斯的穆斯林普遍欢迎祝祷光碟,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们认为录音比文字更能真实地复制宗教权威话语,这一媒介意识形态又与伊斯兰传统中的诵读罗格斯中心主义和毛里求斯穆斯林对宗教权威话语的本真性理解有着密切的关联。换言之,在媒介的物质特性和个体使用者的媒介实践之间,嵌套着使用者的媒介意识形态,这些媒介意识形态与特定的文化相关,引导个体使用者感知特定的媒介特性、选择恰当的媒介交流、并读解交流中媒介使用的意义。采用这一分析性概念有助于区分媒介特征和使用者体验,并帮助研究者提高对文化的敏感度。
三、数字化情感交流的时间性和关系意涵
本节聚焦中国城市青年在恋爱中的情感交流,着重分析他们的语言和媒介意识形态,以及从这些意识形态中反映出的时间体验。总体而言,研究发现他们虽然赋予了语言表达和沟通以重要意义,但这些意义不同于西方社会对面对面交谈的推崇和对情感沟通的理想化。相对于面对面交谈,文字形式的媒介在情感表达中受到偏爱,它们被用来协商口语交流的规则、判断情感表达的真实性、调节关系中的情感冲突,是年轻人重要的情感交流工具,其时间性的不同维度也被赋予了重要的情感和关系意涵。
(一)以文字协商规则:延时性和距离感作为情感表达的助力
恋爱中的青年使用文字媒介的一个普遍用途,是表达难以说出口的亲密情感。对于他们来说,口语和文字媒介意味着不同的交往规则,在口头交流中不得体或令人尴尬的情感表达,通过文字媒介表达不仅合宜,而且可驭。文字媒介在时间上的延迟性和空间上的距离感,是他们在交流过程中协商恋爱关系和交往规则的重要资源。
无论是文字形式的手机短信、QQ即时消息、微信短消息、微博留言、电子邮件还是手写的书信、小纸条,都被情侣们赋予了情感表达的重要意义和功能,这些意义和功能大多是在与口头交流的对比中获得的。例如,大学生谢芳这样解释自己的媒介选择:
打电话如果说煽情的话,说不出口,或说出来别人也接受不了。所以短信、传小纸条比较好,会在短信、纸条等文字表述中直白地表达。
嘴上表达觉得肉麻和尴尬的内容,写在纸上不仅得体而且更加深刻和细腻。对谢芳和其他参访者来说,文字媒介相对于面对面和电话聊天,总体而言允许人更直白地表达情感,约束口头表达的交往规则似乎并不同样适用于文字媒介。换言之,参访者对文字媒介的偏爱主要来自于他们对交往规则的感知以及对协商规则的渴望。相对于口头交流渠道,文字媒介给他们提供了更多的协商空间,而数字化的书写虽可以即时传输,但仍赋予他们足够的时间寻找恰当的措辞。
参访者对情感表达得体与否的担忧在恋爱关系发展的初期尤为突出。因为在关系过渡时期,恋人身份和交往规则都不确定,双方在交往中的身份呈现可能与对方的期待不一致,因此最可能出现尴尬的局面。一些参访者担心贸然表达情感可能会让对方对自己产生不好的印象,如果对方表示反感,自己就会丢面子,如果是面对面交流他们可能感到无地自容,但文字媒介可以将这种尴尬最小化。文字媒介的使用改变了交流情景,也改变了使用者在对方面前呈现自我的视觉和听觉结构,使发信者不必在制造信息的同时就暴露在对方的评判之下。文字交流使他们能够在情感表达时蒙上面纱,但面纱不是为了遮掩内心的情感,而是为了保护那个违反交往礼仪从而暴露在社会评判之下的脆弱自我。
礼仪作为常识是实践中的伦理,作为形式是行动中的美学,劳拉·布冯(Laura Bovone)在回顾戈夫曼(Erving Goffman)对社会互动的研究时如此总结道。尤其当道德的宏大叙事不再是社会共识,礼仪作为行为举止的规范仍保留着传统价值的残余,它与价值观是否得以践行无关,只关乎“一个非道德问题,即是否策划了一个有说服力的价值观得以践行的印象”。由此观之,城市青年在表达爱情时诉诸文字媒介既清晰地表露了爱欲,又在形式上延续了隐藏的伦理。媒介的选择既是礼仪的体现,也是礼仪的违反。正如克劳·延森(Klaus B.Jensen)所言,传播媒介“在成为表征的形式和沉思的对象之前,是交流互动的资源”。对青年们而言,恋爱文化的变迁和关系的暧昧发展都可能带来自我呈现的挑战。而文字媒介的延时性和距离感则成为他们管理自我身份、协商情感表达的重要资源。
(二)以行动确证真诚:书写时间和回复速度作为情感的佐证
用语言表达爱情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确证表达的真实性。在参访者的理解中,表达的形式常常暗示内容的真假。正如朱迪斯·尔文(Judith T.Irvine)对语言使用的研究发现,不同的文化倾向于使用不同的渠道表达情感,因为通过这些渠道表达的情感被认为更加“真实”。虽然尔文所指的渠道主要是语言符号、副语言特征和身体语言,这一论点也适用于交流的媒介技术。不少参访者认为,用语言表达爱情能增加“浪漫”的情趣,但语言表达本身并不可靠,无法确证情感的真实性。浪漫的情话可以“活跃气氛”“促进感情”,但也可能被看作是“花言巧语”“油嘴滑舌”。显然,这些关于情话的观点汲取了传统文化看待语言的一些观念,即语言意识形态,如语言不能准确地表达内心情感(“言不尽意”),也无法充分反映道德水平(“巧言令色鲜矣仁”)。类似的观念有时也被用来描述文字书写,比如有的参访者认为写情书没有必要,因为“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然而,不同与口头表达,文字媒介也常被视为增加情感表达说服力和真实性的途径,其原因不仅在于文字的延时性让情侣们有时间斟酌、修改情感表达,使之更加细致准确,更重要的是,书写赋予文字媒介的使用以一种“做”的逻辑,从而弥合“言”与“行”两种表达渠道,并以可靠的“行”来拯救不可靠的“言”。具体而言,文字媒介的可信度主要是通过书写所花费的时间和劳动来赋予。例如,编辑雅雯如此评价写情书的价值:
也许有人擅长表达有人不擅长,但写信本身就可能有重要的意义,至少他得花时间思考还得写,这比你最后写了什么重要得多。
制造内容的时间和精力比内容本身更能佐证作者的真诚,赋予情感表达以可信度的不是作为口语记录的文字,而是作为行动的书写。
同样,字数较多、篇幅较长的数字短消息,也常常在参访者的阐释中通过“做”的逻辑来判断表达的真诚。例如,一些参访者在判断恋爱交友软件上的个人信息时,认为内容丰富、填写认真的个人信息更有可能体现真诚严肃的交友意图。相反,短小快捷的数字信息很难通过编写信息所需的精力和时间,来赋予其内容以真实性。所以QQ和微信即时聊天中表达的好感和情意很可能被读解为好玩、调情或者“撩”,而不是真诚的“表白”。对青年情侣们而言,“表白”不仅仅是个人情感的表露,它具有重要的关系功能和承诺意味,代表着一段恋爱的正式开始,并常常被仪式化。短小快捷的即时信息既难以佐证表达的真实性,也就难以承担关系开始的仪式感,所以通过短消息首次表露爱意的情侣,通常会进行更多交流协商来确认情感的真实性。
不过,即时聊天中的短小信息并非完全无法通过“做”的逻辑来增加情感表达的可信度,关键在于发送信息的即时性。在情侣的交流中,“秒回”信息通常被认为是“在意”的表现,而不回复或拖延回复则可能意味着缺乏兴趣或者不够关心。回复的速度和话轮的密度对参访的情侣而言,是具有关系意涵的时间维度。例如,大学生婷婷与她的男友住在两个不同的城市,他们常用QQ即时聊天,婷婷强调他们之间的关系并不“浪漫”,因为他们很少“谈情说爱”,但她能从简短的对话中看出他情感是否真挚:
我过年的时候出了一次车祸,就把他急得要命,就一天一个短信一天一个短信地问我怎么样…… 关系一下就好了。有时我睡觉挺晚的,他看见我还没睡觉,看我QQ还在线,就催我:这么晚了,赶紧睡。有时候跟我发条短信就四个字:晚安,孩子。就完了。我觉得就挺高兴的。
发送短信的频率和时机都意味着交流的“用心”,前者由不断重复的问候推断意图,后者因恰逢其时的催促判断关心。由此,内容简短的“言”通过时间特殊的“言说”行为确证了“言说者”的真诚。
(三)以距离克制情绪:实时互动和快速打字作为冲突的来源
媒介的意义还体现在情侣的争执与冲突中。许多情侣认为争执时双方容易口不择言,争吵中的负面语气也可能激化冲突,而文字交流则有助于“减弱”或“修饰”愤怒的语气,使双方保持冷静和理性。他们用文字媒介制造时间和空间的距离,避免情绪失控和冲突升级。例如,大学生晓琪与男友有过约定,一旦他们发生争吵就各自回到自己的宿舍,冷静下来后,先通过短信息交流想法、达成共识,再见面心平气和地讨论。对他们而言,面对面意味着激烈无序的情绪表露,有意识地拉开距离反而能更好地交流,可以在克制情绪的基础上表达自我,在有序互动的前提下解决冲突。
即时短消息的实时互动可能弥合交流的时间距离,让文字媒介不再适合冲突管理,反而成为双方冲突的助推器。例如,雅雯发现自己跟丈夫使用QQ即时聊天时,一旦发生争吵总会越聊越生气,因为双方都只顾自己打字,根本不花时间留意对方说了什么,这时,即时短消息只会带来更多的冲突:
你在写的时候,可能你在打字然后他也在打字。然后他呢,就只顾发泄他的情绪,然后你再只顾打你的字,根本就说不到一起去。这样就会打电话说了。
从即时短消息转向电话聊天,也是从同时打字转向依次说话,后者让争吵双方有时间在发言之前倾听对方的想法。这个媒介转换提示我们口语交流中话轮的接续性和沉默的交流功能,当即时性成为数字书写的典型特征时,使用者必须重新协商文字媒介对情感交流和冲突管理的价值。
打字速度也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副语言缺失对情感表现力的抑制。当情侣通过文字形式的短消息争吵时,单位时间输出的文字数量被他们赋予了进攻和较量的含义。在以下的采访片段中,大学生大华在描述他与女友桑梅通过即时短消息进行的聊天,从中可以看出灵巧的手指在短信吵架中的作用:
两个人……也不可能什么都想得一样。就感觉,思维交锋的时候,咔!特别快特别快,你就得,非得用气势压倒(对方)。然后她就这样,非得发一堆,然后特别快,然后可以压倒我。
在即时聊天对话框中发送的文字可以形成“刷屏”的视觉效果,对冲突中的情侣而言,这一效果近似面对面争吵时以音量、甚至拳头形成的压倒性势态,是冲突一方的力量展示和支配地位。文字数量和打字速度可以说是文字媒介的“副语言”,起到了面对面口语交流中音量和手势的情感表达功能。
在媒介历史中,打字速度常常具有性别意涵。例如,弗里德里希·基特勒(Friedrich A.Kittler)注意到打字机的商业用途激发了19世纪西方社会中的性别竞争,因为男性控制了传统的文字书写,女性只能通过提高手指的灵活性和打字的速度在职场上与男性书记员一争高下,因此打字机被基特勒称为“话语的机枪”。汤姆·斯丹迪奇(Tom Standage)认为女性和儿童之所以受到电报业的欢迎,是因为速度对收发电报的重要性,女性和儿童手指的灵活性使他们在电报就业市场中不再处于劣势。如果打字速度曾增加打字员和电报员群体的性别竞争,即时聊天中的打字速度也给男女情侣的冲突较量推波助澜,一些参访者将快速打字比作“进攻和防守”,而女性在这场战役中并不占下风。但这种女性赋权的意味极易被夸大,因为在情侣的争吵中,打字速度常常被看作是冲突的催化剂,其原因不仅仅与性别权力有关。
事实上,文字输入和互动速度的提高可能导致信息意义的改变,使交流双方的理解产生分歧并导致冲突。交流的速度暗含双方对信息解码速度的期待,也就是爱德华·霍尔(Edward T.Hall)和米尔德里德·霍尔(Mildred R.Hall)所说的讯息速度(message speed)。它为交流者理解信息提供了一个元传播框架。讯息速度常常暗含在交流和传播类型中,例如新闻标题和卡通漫画隐含着快速解码的文化预期,而纪录片和诗歌的解码常需要更多时间。对特定文化中的既有传播类型而言,解读信息所需要的时间是文化知识的一部分,也是人们媒介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然而,对伴随新媒介产生的新交流形式而言,这样的知识尚未形成,使用者需要即兴地创作语法。
一些情侣在短信聊天中产生的冲突来自于对信息速度的不同期待,他们对交流媒介的调整也意味着对信息速度和媒介意识形态的协商。小马和鹏菲都是北京高校的研究生,他们从异地恋开始,先是书信来往,后来转到QQ和手机短信交流。在对他们分别进行的访谈中,两人都提及他们的QQ即时聊天常常开始很愉快但最后却不欢而散。他们都感觉双方在聊天时似乎有不同的节奏,鹏菲所期望的速度比小马更快,而小马则抱怨鹏菲在快速回复中忽略了他的信息的真正含义。对信息速度的不同期待构成了他们不同的媒介意识形态,鹏菲认为QQ聊天是传递快信息的渠道,无需深思熟虑,重要的是即时回复,而小马为QQ聊天中的信息赋予了更深刻的意义,期望更慢的信息交换速度。因为QQ聊天频繁发生冲突,他们调整了交流的话题和渠道,决定把QQ即时聊天作为快速且有任务指向的互动渠道,避免用它来交流与感情相关的话题。
四、结语:时间作为矛盾的症候与来源
显然,在城市青年的媒介使用和媒介意识形态中,数字媒介的时间性是多维的,并且大多具有关系意涵,并指向恋爱中的关系伦理:表白与得体,真诚与游戏,克制与冲突。对情感表达和沟通而言,数字媒介的即刻性在不同的关系考量中可能产生完全不同甚至相互矛盾的意义。如何理解这些丰富而矛盾的媒介意义和时间体验?理解它们能够为探讨数字化情感交流对亲密关系的影响提供什么洞见?本节联系当代情感文化与婚恋关系变迁的语境来回答这些问题。
首先,年轻人期望用语言表达和沟通情感,却用行动的逻辑来确证其真实性。这意味着以语言为媒介的表达文化虽然变得流行,但传统的爱情表达逻辑仍占主导地位,其运作方式类似于罗伯特·墨顿(Robert Merton)所说的“行动的宣传”(propaganda-of-the-deed),即通过投入传播/交流的精力来衡量其可信度。更重要的是,对于青年情侣而言,以交流的行为佐证交流者的真诚更应放在城市青年恋爱文化的语境中读解。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城市青年的恋爱行为越来越同婚姻制度脱钩,以休闲性(casual sex)为目的的交友亚文化,伴随着都市夜生活和一些交友软件的发展在公共空间变得越来越可见,但在主流恋爱文化脚本中,婚姻仍然是恋爱的主要目的。但随着社会财富的不断分化,婚姻的工具性导向也越来越明显。婚恋文化的变迁和多元的恋爱脚本带来的不确定性,使确认恋爱对象的真诚度成为情侣交流中一个突出的问题。相对于语言表达的情意,“行动”传达的诚意显得更有说服力。青年情侣赋予文字媒介的“行动”涵义,包括耗时的消息编写和即时的信息回复,既体现了传统婚恋理想的延续,更是对现实中恋爱意义不确定的担忧和反应。
其次,年轻人希望通过语言协商冲突、解决争执,却发现距离使沟通更为可能。此处距离的功用并非增加对情侣的理想化,或如特克尔与鲍曼所言,帮助年轻人逃避“真正”的交谈和亲密关系。相反,时间与空间的距离帮助他们从急于自我表达,转向思考关系伦理,通过克制个人的情绪表露,成就双方的谅解和沟通。这与西方现代社会亲密关系中通过书信和交谈将个体情感对象化、理性化有相似的作用。但面对面交谈在青年情侣的冲突管理中并不享有高于媒介化交流的独特地位,那些能制造时间和空间距离的媒介反而被赋予更强大的冲突管理功能。这一方面印证了媒介化交流的超人际传播效应,但更重要的是,它体现了青年情侣在表达自我和维持关系之间寻求平衡的媒介策略。正如贝克与贝克-格恩斯海姆所言,随着个性与情感的重要性日益增加,恋爱的困境已不在于外在的束缚,而更在于两个同样在追求自我的个体之间如何能找到建立亲密关系的共同点。在个体化社会的恋爱关系中,情感沟通的难点或许不在于是否能够相互表露真实的自我、达到灵魂的交融,更在于恋爱双方如何能够既表达独特的自我又实现共同的生活。青年情侣赋予媒介的克制调和之意,暗示了传统的冲突管理方式在数字媒介中的延续,更体现了当代亲密关系内在的矛盾。
可见,青年们对媒介时间性的体验与当代亲密关系的内在矛盾密切相关。借用帕蒂·斯堪奈尔(Paddy Scanell)的说法,时间是“远程传输的本质”,当空间被信息技术征服,时间就成为人们理解世界的重要维度。在变迁中的情感和婚恋文化语境中,数字媒介的时间性意味着表达是否可能、情感是否真挚、关系是否和谐,这些涵义均来自于年轻人在现代婚恋关系中的伦理关切。问题在于时间在情侣的数字化情感交流中是多义的、也是矛盾的。延时的交流可能意味着真实的情感,也可能意味着克制的情绪,还可能意味着漠不关心;即刻的互动可能冲淡情感表达的严肃性,也可能激化双方的争执,还可能暗示真诚的在意。时间的多义性给情感交流带来更多的不确定,甚至成为误解和冲突的来源。因此,数字媒介在助推语言化情感交流的同时,也突出了以情感交流为基础的亲密关系所面临的困境,而数字媒介的时间性也成为当代亲密关系之流动性和不确定性的症候与助力。
(本文系北京语言大学校级项目“媒介化的爱情:青年情侣的媒介使用研究”〔项目编号:16YBB26〕的研究成果。)
注释:
①② 阎云翔:《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1949—1999》,龚小夏译,上海书店2006年版,第94、75-97页。
③ Anthony Giddens.TheTransformationofIntimacy:Sexuality,LoveandEroticisminModernSocieties.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2,p.58.
④ Lynn Jamieson.IntimacyasaConcept:ExplainingSocialChangeintheContextofGlobalizationorAnotherFormofEthnocentrism?Sociological Research Online,vol.16,no.4,pp.1-13.
⑤ Lynn Jamieson.IntimacyTransformed?ACriticalLookatthe‘PureRelationship’.Sociology,vol.33,no.3,pp.477-494.
⑥ Ulrich Beck and Elisabeth Beck-Gernsheim.The Normal Chaos of Love.(Trans.)Mark Ritter and Jane Wiebel.Cambridge:Polity Press,1995,pp.2-7.
⑦ Zygmunt Bauman.LiquidLove:OntheFrailtyofHumanBonds.Cambridge:Polity Press,2003,pp.xii,58-63.
⑧ [美]雪莉·特克尔:《群体性孤独》,周逵、刘菁荆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83-220页。
⑨ [美]雪莉·特克尔:《重拾交谈》,王晋、边若溪、赵岭译,中信出版社2017年版,第3-19页。
⑩ Joseph B.Walther.Computer-MediatedCommunication:Impersonal,InterpersonalandHyperpersonalInteraction.Communication Research,vol.23,no.1,1996,pp.3-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