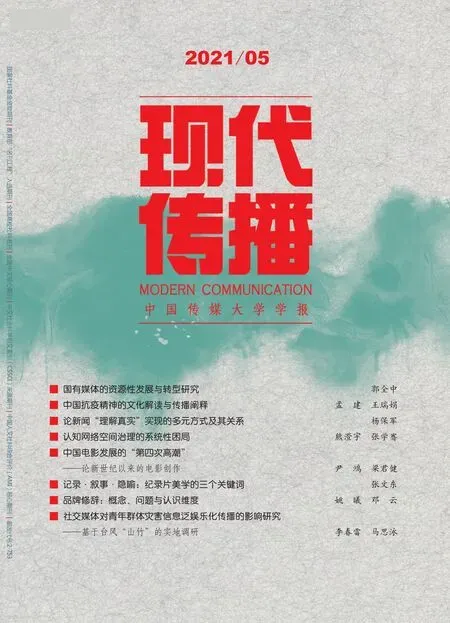社会记忆、身体操演与影视人类学方法及实践
——基于白马藏人影像志创作的反思
2021-12-02卢芳芳
■ 卢芳芳
感官民族志是随着感官人类学(anthropologyofthesenses)的出现而出现,是对视觉中心主义(occularcentrism)、文本中心主义(textcentrism)强势地位的批判。①感官民族志的“具身体现”是指:身体是知觉和理智等精神现象得以产生的媒介,我们通过身体体验世界,也赋予这种体验以意义。感官民族志的“具身性”描写,如何在影视人类学学术实践中得以呈现?本文试图以为期一年的田野调查为基础,从白马藏人影像民族志实践为切入点,根据本土人的仪式操演特征、个体的身体实践传承社会记忆,结合学理与实践,综合探讨感官民族志的“具身性”在影视人类学学术实践中的呈现。笔者试图通过影像志创作探讨如下议题:个体的身体实践如何与集体的社会记忆联结起来?进而涉及到具身感的感官民族志,如何以影视人类学的学科路径呈现?
一、拍摄缘起:社会记忆与感官民族志
传统意义上的记忆传播技术,包括口头、文字书写和身体操演等。保罗·康纳顿强调记忆中被忽视的身体维度,他认为记忆是通过体化和刻写的方式沉淀于身体之中的,这可以与阿斯曼、哈金等人的观念相媲美。意义不能被简化为身体活动范围之外,属于另一个“层面”的符号。习惯是一种知识,是手和身体的记忆。在培养习惯的时候,恰恰是我们的身体在“理解”。②保罗·康纳顿在《社会如何记忆》中,提出身体操演的概念,他指出:“纪念仪式和所有其他仪式存在两个共同特征:形式主义和操演作用(perfomativity)。它们作为记忆手法有效地发挥作用,这主要是因为它们拥有这些特征。”由于纪念仪式明确涉指原型人物和事件,无论人们把这些理解为历史存在还是神话想象,仪式重演特征对于重塑社群记忆是十分重要的特质。③
感官民族志在方法实践上会更多地利用视觉和听觉等技术。从这个角度看,影视人类学学科对于感官民族志的学术实践,具有天然的技术优势。正如学者SarahPink在《做感观民族志》著作中指出:“作为参与式观察的感官民族志,与其被简单定义为参与和观察的杂糅,更应该视为由具身的、置入的、知觉的、移情性等观念构成的学问。”④
聚焦感官民族志的国际影视人类学实践,哈佛大学卢西恩·卡斯汀·泰勒于2006创建的民族志实验室(SEL)可圈可点。该机构旨在促进美学和民族志的创新结合,它使用模拟和数字媒体、装置和表演,探索自然和非自然世界的美学和本体论。利用艺术、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观点,SEL鼓励人们关注世界的许多方面,包括难以用语言传达的有生命体与非生命体。通过SEL制作的电影、视频、摄影、留声机和装置作品已在世界各地的大学和学术会议上展出。在SEL制作的电影和视频被选入柏林、洛迦诺、纽约、多伦多、威尼斯和其他电影节。近十年,其实验室出品的影像志《香草》(Sweetgrass,2009)、《利维坦》(Levithan,2012)、《人民公园》(People’sPark,2012)、《铁道》(The Iron Ministery,2014)、《食人录》(Caniba,2017)等曾在国内展映。有业界人士认为“进行此番影像实验肯定了感官经验在人类跨文化交流中的作用,成为对感官和人类情感的现象学式探索,“‘化身’影像是哈佛感官民族志实验室作品中最为鲜明的特征”。卢西安·泰勒曾提出:“如果(民族志)电影根本不试图说话会怎么样?如果电影不仅构成关于世界的讨论,而且代表了对于世界的感知又会怎样?如果电影不是为了说话而是为了呈现会怎么样?如果一部电影不仅试图描述更是试图去描绘又会怎么样?那么,如果它不仅提供‘简短描述’,而且还提供‘深刻而丰富的描绘’,那又会怎么样?”⑤
影视人类学的研究对象是开放的生活,事先准备的调查提纲难以反映那些日日新的细节;切实的田野调查使田野工作者获得了真正的体悟和体验,加入不可重复的生活过程。例如2018年7月11日,笔者在白马藏族乡以影视人类学视角调研时⑥,忽遇建国以来特大暴雨,大雨引发洪涝灾害,夜间泥石流冲垮村民的二层房屋,从上游冲下的木头堵在村口、冲垮寨门,通讯中断、网络不通。乡政府、村民立刻集结一线救灾,日常以旅游接待为日常生活的村民们瞬间手执门板排水,手握钢锯锯掉堵在河道中的木头,齐心合力守护家园。调研提纲很难预见这些突发场景。影像志的田野调研工作是个漫长、琐碎的过程。在构造“具身性”民族志过程中,笔者与当地人在共同经历中生出的互动性、差异性、共通性一同发挥作用。“融入”与“跳出”又使得自身不断在挂职干部与研究者身份之间来回切换,挂职干部身份的“融入”有助于笔者在当地迅速获得进入现场的合法性,而人类学训练又使得笔者在实践中得以无意识地“跳出”,关注当地人的“主体性”,于无声处产生问题意识与学术关切。
作为个体的身体实践,如何联结集体记忆?如何以影像民族志联结集体记忆、传递反思与生产知识?现从方法论的角度,归纳如下:
首先,通过记录当事人口述历史的影像志是保留集体记忆的重要路径。保罗·康纳顿在《社会如何记忆》中指出:“事实证明,或多或少属于非正式的口述史,是描述人类行为的基本活动。这是所有社群记忆的特征。”他提出“当我们成功地识别和理解别人的所作所为时,我们把某个事件、情节或者行为方式,放到一些口述史的脉络中”。⑦布洛赫也曾经指出:“言语的习俗构成了集体回忆最基本同时又是最稳定的框架。然而,这个框架又是相当松散的,因为它并不包括那些稍显复杂的记忆,而只保留下了我们的表征中一些孤立的细节和不连续的因素。”⑧同样,以口述史为主的影像志的不足之处在于:以言语活动为主的描述难以容纳较为复杂的社会记忆,因为这里涉及诸多非语言细节与稍显复杂的记忆,比如难以描述不具备统一模式的仪式过程,对此,影视人类学者需要对此作进一步探索。
其次,着眼于日常生活实践完成对集体记忆的“浓描”,是联结集体记忆的重要方法。通过记录当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影像志《岷山深处白马人》,笔者试图展现当下平武白马藏人生存的自然环境与他们的日常生活、白马藏人自身对发展的诉求并描述在文旅融合背景下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内部细节。影片的焦点场景包括:白马藏人村寨婚礼的前后过程,猝不及防的特大暴雨泥石流,中国扶贫基金会帮扶的乡村民宿由创意到落地的过程,村民自发组织的文化传习活动,当地春节民俗活动——盛大狂欢“跳朝盖”。这些场景从不同角度、从不同的时间和地点,勾勒出了当地的自然环境、生态智慧与日常生活,反映乡村振兴中政府、公益力量、村民三者之间的博弈共生关系,呈现村落生活中的精神和物质的层面。在这三者之中,当地人的“主体性”得到充分呈现,是影像志重点关注的部分。当地人自身如何看待周围的环境、变化,当地政府又怎样脱贫攻坚、多方帮扶,村民又如何传习文化、如何表达发展诉求等等,则作为背景化处理,试图以影像手段从“具身性”角度,从日常生活实践完成对集体记忆的浓描(thickdescription)。
二、知识生产:文化尊重与乡土实践
影像民族志《岷山深处白马人》作品拍摄于2018年5月至2019年11月,田野作业时间为一年半左右,同时呈现四川平武白马藏人的乡村振兴过程中的文化变迁进程。影像志呈现出在村寨举行的婚礼过程,从前一天宵夜(按当地说法婚礼的前一天叫做宵夜)村民搭舞台歌舞联欢到婚礼开场前的白莫祈福念经,从婚庆公司主持的仪式到身着传统民族服装的父亲挽着女儿走红毯到结束之后逐门逐户喝转转酒,这套民族文化与西式婚礼的结合,展示了传统的新化身,折射出传统与现代的无缝对接;而民宿落地过程,影像志观照到当地族人的诉求与表达,关注当地人以何种方式付诸实践。对于康纳顿提出的身体实践与仪式操演,神圣性与世俗性的呈现,影片则通过“跳朝盖”活动在两个不同村寨的呈现来完成,试图通过影视人类学的最终画面来呈现,传达知识生产与学术关切。对于该动态过程,现从人类学角度归纳总结两点:
第一,学术人员要以人类学的整体观视角进入社区,随时恪守学术伦理,基本工作原则为尊重文化。在此基础上,通过现象的描述呈现出理论反思、知识生产,这样的影像作品本身要有对生活的深刻理解与“深描”(thickdescription)能力,同时具备解释性结构,在建构公共过程中完成知识生产,以影像力量阐释“地方性知识”,运用影像手段完成“写文化”的田野过程,使作品具备“言在此而意在彼”的内在品格与逻辑脉络。
人类学知识的生成是一个涉及诸多不同且不断发展的方法的动态过程;出于道德和实践原因,知识的生成和运用应以合乎伦理的方式获得。“人类学研究者在执行和公开其研究或发布其研究成果时,必须保证不伤害与其一道工作、开展研究或实施其他专业活动,乃至被合理推断为可能受其研究影响的人员的安全、尊严或私密。”⑨未经过当事人许可公开出版当事人隐私,在非虚构写作中实际存在,而在人类学的研究中格外需要避免。这体现在影视人类学研究的过程中,大量的内容根据当事人的需求得以隐匿。在影视人类学科这一直接通过镜头说话的研究中,从若干年田野经历中,应以文化尊重的态度出发,这点在田野工作中常常不期然地呈现。在2019年11月的田野调查中,不期然遭遇一位白马藏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去世,笔者赶往丧事筹备活动时,县电视台提出希望赶来拍摄的要求,族人商量之后拜托笔者委婉拒绝一事。笔者在现场与族人一道商议逝者悼词,亲历送葬场面,但出于伦理考虑,该部分影像并未纳入影像素材之中。值得提出的是:这里决定画面内容是否被呈现的首先是伦理原则,而非事件本身的戏剧性。
“一个真正好的编导,不可能在那儿又完成地道的文化记录,又完成特别炫的文化传播,这时一个导演的脑子里是装不下这两件事儿的。”⑩因此,立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记录的影像志,从学术角度看重点显然偏于文化记录,而非文化传播。拍摄《龙潭洼乡》的李德君老师曾明确提出:“确定影视人类学是一个实践科学而不是一个理论科学,它严格意义上是实践科学,你如果脱离了实践,人类学就说不上。”因此对于影视人类学的方法反思,无论如何不是一个“从理论到理论”的过程,而是从田野作业中产生知识、寓理论对话与作者观点于画面背后的知识生产过程。
第二,在文化尊重原则之上,多角度深描日常生活。影片亦聚焦于民宿落地的乡土实践。在乡村振兴战略中,发展民族特色乡村旅游,带动农民致富,是实现乡村振兴发展的重要抓手。由中国扶贫基金会在平武灾后重建之后介入的民宿修建实践亦是文旅融合的典型选样。在全域旅游背景下,2018年初,中国扶贫基金会选定在白马藏族乡驼骆加寨了投资修建民宿。中国扶贫基金会相关负责人认为:原定在下壳子修建民宿,政府建议建在上壳子(伊瓦岱惹村上寨,简称上壳子),但由于上寨村民反对,没有达成统一意见,最后不得不调回下寨,因为两次反复,导致重复设计、重出施工图纸,造成一了定损失。中国扶贫基金会选择驼骆加寨子,在于看重当地白马藏族文化独具特色,不料落地平武,进展缓慢,然而上寨村民认为“(如建在上寨)破坏了古寨原有的风貌,装修了之后再恢复就难了”,不认同基金会要在原先旧寨的基础上装修的条件,要求对方保留老寨原貌,另外选址另建新寨用于接待游客,建新寨的要求使扶贫基金会难以满足。几经博弈,由于村民与乡政府的意见未达成一致,最终尊重村民决定:确定在下壳子修建,就传统建筑而言,保留传统元素,保护白马藏族文化特色。
这场民宿修建实践中,影片试图呈现:当下村民的主体性在这场民宿修建实践中得到充分展现,在表达利益诉求中,村民们的博弈能力在增强,他们在与外界各色人等的交流中,逐渐获得对老寨文化价值的判断与认知,并合理、合法表达诉求,面对“被开发”的选择,作出符合自身利益的表达。在这场博弈中,政府试图干预基金会的落地选择,而村民的诉求又反作用于最后的抉择,扶贫基金会带着善款,作为外来资源方,既要尊重政府、又要尊重当地老百姓,在这两者满意都之后开展工作。这三方互为主体,互为环境,互惠共生。影像志通过深描日常生活,传递对当地人(包括村民与政府)主体性的尊重。
三、身体实践:具身操演与万物生态观
贝特森提出的关联性模式是“元模式”(meta-pattern),是模式的模式,每个模式是其他模式的全系浓缩,这种模式以小见大、以大容小,它提倡万物关联,看似无关的草木昆虫、山水自然,与人类发生关联,这种思维模式让认知发挥作用,使人回归自然,拒绝高高在上,努力建立新的分类系统,形成新的万物生态观。影视人类学对“具身性”的描写,不仅天生存在技术优势,而且能够通过影像关联“物感物觉”、呈现,万物生态观、关联心智与自然、实现心物互动、形气神相连。
身体实践是维系族群认同的重要手段。在关于“族群的特点到底是什么”的问题上,卢森斯的回答是:家系(genealogyical dimension)。家系总会和亲族及家庭的隐喻交织在一起,这类“家隐喻”和“边界”结合在一起,成为族群认同的主要根基。在笔者观察到的仪式中,通过对每个家庭的动员组织与逐个造访,将个人的身体实践与家族记忆、社会记忆有效连接,节庆活动俨然成为白马藏人族群认同的重要手段。如康纳顿在《社会如何记忆》中提出,记忆或习俗以非文本或非认知的方式流传。身体的社会构成有双重含义。强调操演,尤其是习惯操演,对于表达和保持记忆的重要性,就是强调构成和建构的二义性。无论个人层面的身体实践与集体层面的纪念仪式之间存在差异,还是社会记忆、纪念仪式以及身体实践之间存在一种递进的逻辑关联。“跳朝盖”这一具身操演的群体活动,既是白马藏人表达和传播社会记忆的重要方式,也是演示历史记忆、整合村寨共同体的庆典仪式。
人类学操演的身体实践,被划分为刻写和体化两类,其中的体化实践通过一整套连续的动作得以准确完成,借助习惯的形成与身体的体验,助力记忆过程。在这里,记忆与身体体验密切关联,这与各民族地区的传统、地方性知识密切关联,如侗族“采歌堂”、苗族鼓藏节、景颇族“目瑙纵歌”、普米族“韩规”等,通过广泛的组织动员,族人按照规定的仪式聚集之后、或吟唱、或宰牲、或起舞,这类体化实践无不具备“以身体实践助力记忆过程”的社会功能,借助的同样是“习惯的形成与身体的体验”,来关联心智与自然,共同操演社会记忆。
感官民族志的“具身体现”是指:身体是知觉和理智等精神现象得以产生的媒介,我们通过身体体验世界,也赋予这种体验以意义。影视人类学家拉玛尔(C.Lammer)认为,影片能够将触觉、味觉、嗅觉等感官体验以影音图像表现出来,通过事件记录社会之美,激发观众的感官记忆和想象。笔者通过影像志展示2019年春节期间白马藏人的“跳朝盖”活动,记录该活动之美,通过对白马藏人的仪式生活的深描,描述白马藏人的地方性知识,深刻理解他们的观念。“跳朝盖”作为春节节庆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当下体现,它既是以血缘家族为单位举行的祭祀活动,也是白马人的一种包罗万象的宗教祭祀舞蹈和文化娱乐活动,通过祭神、祭祖、驱鬼仪式和祭祀舞蹈,以求诸神保佑人丁兴旺、六畜平安。通过这一系列关联心智与自然的身体实践,表达出对神山圣域的尊重、对祖先的缅怀、对吉祥幸福的追求,是万物有灵观念的体现,形成“万物生态观”。对于“跳朝盖”活动的复杂社会内涵,学者曾穷石曾经做过概括:“维系白马藏人族群记忆、整合社区共同体、应对社会变迁。”
2019年2月春节期间,笔者前往白马藏族乡伊瓦岱惹村与亚者造组村,观察“跳朝盖”仪式在这两个村寨的不同呈现。伊瓦岱惹村的活动定于大年初五、初六两天,亚者造组村则在安排在初八、初九。从组织的角度观察,笔者发现该活动已经由之前的单位因血缘家族村寨,成为由村委参与组织、神职人员(即白该)在仪式中发挥核心作用、官方与民间合力参与的社区活动。“跳朝盖”的内容是关于族人祖先的业绩和故事——演示白马人自己的民族历史,乃至更为具体的部落和家族的历史。而这些行动本身,则是通过“身体操演”来传递的历史记忆。关于过去的记忆,它既可以通过口耳相传的歌谣、神话传说来重构历史,也可以通过仪式操演来实现,体化实践提供极为有效的记忆系统。而体化实践的特别记忆效果,依赖于存在方式和获得方式,他们不会独立于他们的操演而客观的存在。千百年来,囊括念经、祭山神、出朝盖、全寨集体歌舞乐等诸多动作元素的“跳朝盖”这一身体操演活动,以“体化实践”的方式活泼自然地存在于岷山深处,创造了属于白马藏人雄浑古朴的盛大庆典,体现了鲜明的民族特色和独特的记忆方式与万物生态观。从区域民族研究的角度看,该文化片区相对集中,与陕甘交界的文县、九寨沟的白马人一道,共同创造了独具特色、风格鲜明的白马记忆。2019年2月,平武、文县、南坪三方聚集召开会议,跨省申报“大白马文化生态保护区”,试图打破行政边界,从整体角度传承文化,这是新时代传承族群记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行政努力与县域实践。
关于重演性仪式语言(rhetoricofre-enactment)相关的表达方式,康纳顿归纳为日历类、口头类和手势类。关于重复性仪式语言,他提出“神圣时间”“神圣事件”“神话时刻”这些概念。跳朝盖定于每年的正月初五到正月十六日,但具体到各地、各部落、各寨子、各家族等,皆因地制宜,有各自所谓的“神圣时间”。具体的时间则是一个对时(即24小时),也就是从头天日落开始,到次日的日落时止。跳朝盖程序包括“准备阶段、念经请神、驱邪撵鬼、神人共乐”这几个组成部分。在念经的白莫看来,他认为后面的唱跳都不如这个念经重要,当地白该认为“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念经部分”。通常举行活动的村寨要请来三位白莫,本村没有的话要到外村去请,通常随着仪式在不同的村寨陆续举办,白莫被邀请到不同的场合,赶场子一般忙碌不止。在为他们念经而临时搭建的帐篷里,一旦开始念诵经文就不停止,所需食物被准时送来,并禁止女性进入该场域。
“朝盖”是白马语,本意是指面具,在仪式中,指代“戴着曹盖面具的人”。在曾维益于1991年2月19日至20日记录的《白马藏族跳曹盖实录》中,“跳曹盖”历时24小时,是在春节大年初五太阳落山之时开始,直到初六中午结束。在仪式开始之前,要完成前期的准备工作:购买祭品(一头活羊)、制作“霞道”、组织安排、场地选择。
在“跳朝盖”过程中,白莫第一次念经、朝盖出场的具体时间,均由打卦确定。在午夜准时燃放的鞭炮,朝盖第一次出场时间,则属于“神圣时间”范畴,而这一活动过程,则是对“神圣事件”的具体操演。2019年春节期间,通过对于白马藏族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跳朝盖”在两个村寨不同展演的观察,笔者发现:在没有进行旅游开发的寨子与深度开发的寨子,二者的实际呈现效果存在巨大差异。这也说明:仪式操演在保持稳定性的同时,随着日常生活实践,传统的灵活性与文化再生产能力,随村寨生产生活实际差异,产生了不同面向。在没有进行旅游开发的伊瓦岱惹寨子,笔者观察到:大年初五早上,在长长的念经之后,白莫开始出朝盖,人们聚集院坝,各种彩色经幡迎风招展,人们齐声高呼、相互应答之后,成群结队祭拜山神,到了神山祭拜处,女性止步于木门外,不可近前,男性浩浩荡荡前去祭祀,唱歌列队而归。祭祀神山后,并没有告一段落,而是继续一家一家入户,这活动集合全村所有的男女老少,全部参与其间。每到一家,只见朝盖、白莫们率领村民盛装成群结队而入,鞭炮声此起彼伏,一边大声呼喊一边舞蹈,挥舞手中木剑,每到一家用力拍打木门,这拍打意为祛除邪祟,迎接新年。男性列队在前,女性在后,进屋之后围着火炉绕三圈,继续唱歌跳舞,主事的白莫要在剪纸底下说对这家的祝福语,对每家每户讲的祝福都不同。每家每户要准备好酒(或可乐)人人要喝。朝盖、白莫先进门,女性在门外两侧列队迎接,一边口中念念有词,待白莫做完法事出门后,人们继续唱歌、喝酒、把人扔向天空、彼此祝福。一直走完寨子里的每户人家,之后由一人背着一背篓叶子朝村口走去,倾倒在山下,鞭炮声再起。人们继续列队跳舞,舞步模仿蛙、熊等各种动物,神圣与世俗、庄严与活泼、敬畏与祝福、祭祀与狂欢,诸多元素全部奇妙地混杂在一起,体现在外在生命形态上是刚健清新、古朴稚拙,经文里勾连着天地人神一套体系。这里的人们千百年来都用这种方式,辞旧迎新,祭拜了山神、祖宗、家神、灶神的人们自然而然地感到一阵欢畅。
在影像志所呈现的仪式过程中,人们通过呼喊、舞蹈、“手持木剑拍打木门”、“绕火塘三圈”、再到“将一背篓叶子抛下山谷”“模拟蛙、雄等动物舞步”这一系列规定动作的身体实践,模拟自然,联结祖先,祭拜山神、祝福村民,勾连天地人神,展示万物生态观;将个体层次的身体实践,在不知不觉间与集体层次的社会记忆悄然联结,记忆得以传承,历史再度重演。而背篓里的叶子与自然密切相关,被朝盖背到每家每户,伴随白莫逐家逐户念经过程,直到仪式结束之后,被倒进山谷低处。这个背篓里的叶子被倾倒进山谷的画面被一路跟拍并记录下来,这一组具备隐喻和联觉(synaesthsia)的动态画面显示视觉媒介为人类学的变革提供经验,胜过文本描述。值得一提的是,“影视人类学注重的不是影视本身,而是渗透并且编码于影视中的涉及文化的一系列关系。正像人类学可以解读影视中的这些关系一样,人类学也可以运用影视来建构作品,这些作品以一种更为丰富的知觉(sense)解释文化是如何渗透和形塑(pattern)社会经验的”。通过关注该仪式的身体实践、社会组织、具身操演、非语言细节,以影视人类学的学科路径关照村寨的公共活动,通过影像来展示神圣性的传递,个体的调动,万物生态观的呈现,实现文化翻译,真实描绘族人自发进行的身体操演,以整体性视角把握与村落的关系,连接心智与自然,实现形气神的统一。
而在旅游开发较为成熟的亚者造组村,“跳朝盖”则在初七、初八举办,活动的娱乐性质更为明显,除了吸引游客、自娱自乐,村里自发组织朝盖活动、杀羊,各家各户集资、投工,年轻人除了跳民族传统舞蹈,还有各种游戏,也有网络主播游客在篝火旁趁着活动直播,兜售山货。传统上,跳朝盖的活动,一旦开始就要连续跳三年。影片也呈现出对于“跳朝盖”在两个不同村寨的民俗实践。在没有进行旅游开发的寨子与深度开发的寨子的比较,呈现身体实践与仪式操演的固定性与流变。后者在文旅融合背景下以旅游为目的而恢复传统,作为吸引游客的景观存在。这也折射出社区传统的关联性与当下的市场需求,演化为相互依存的现实存在,这也是神圣性与世俗性在当下白马村落的现实呈现。影像志也尝试回答了如何通过仪式操演来传承记忆这一问题,并试图回到整体性的角度进行深描。
(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所创新工程学科项目“中国西南地区传统村落保护与区域发展影像志”〔项目编号:2019MZS007〕的研究成果。本文得到作者所在的影视人类学研究室庞涛老师的指导,在此致谢。)
注释:
① 参见 D.Howes.ChartingtheSensorialRevolution.Senses &Society,vol.1,no.1,2006。
④ Sarah Pink.DoingSensoryEnthropology.SAGE Publications Ltd.2009.p.63.
⑤ 《“化身”影像:哈佛感官民族志实验室的纪录片尝试》,澎湃新闻,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5363210,2019年12月28日。
⑥ 2018年5月,笔者成为中国社科院遣往四川绵阳挂职团一员,来到平武县挂职民族宗教事务局副局长,希望能够结合专业背景服务当地。在结合本职工作的参与式观察中,逐渐形成《龙州史话——又述平武民族工作及社会发展》影像志(于2019年10月由北京社科智库出版)的基本结构,理出了白马藏人非遗保护影像志的大体脉络。
⑧ [法]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毕然,郭金华译,上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80页。
⑨ 定宜庄、汪润:《口述史读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89页。
⑩ 该段发言出自文化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原主任李松谈“国家影像志”,发言来自2019年于复旦大学举办的“流动的空间——中国影视人类学年会”会议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