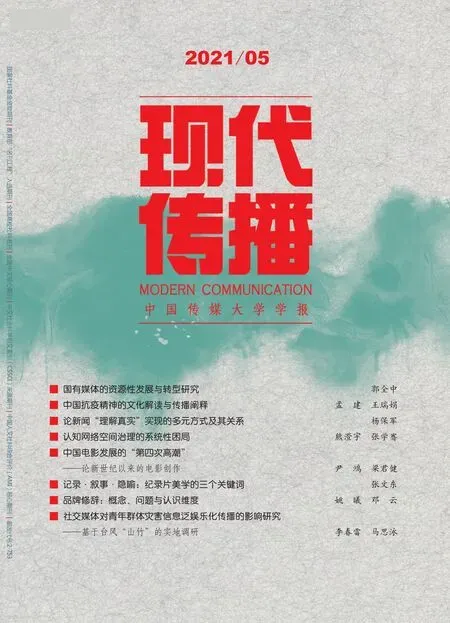美国“公共外交”及若干相关概念辨析
2021-12-02仇朝兵
■ 仇朝兵
1965年,美国前外事官员、时任塔夫茨大学弗莱彻学院院长的埃德蒙·格利恩(Edmund Gillion)在建立爱德华·R·默罗(Edward R.Murrow)公共外交中心时首次提出了“公共外交”这一概念。自从“公共外交”这一概念问世以来,人们对其界定一直存在着分歧。同一个概念,在不同时空背景下,其内涵和外延往往会有所不同;即便在相同时空背景下,由于各自经历不同,人们对其内涵和外延的理解往往也会有不同程度的差异。对于相同或类似的事物,人们也常常会用不同概念进行表述。人们对“公共外交”这一概念及其内涵和外延的理解,也存在类似情况。
近年来,“公共外交”受到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学术界对“公共外交”的研究也取得了较快发展,政策界、舆论界相关讨论越来越多;一些致力于研究“公共外交”的机构或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出现;许多硕士和博士研究生把“公共外交”作为学位论文选题。与这些进展相伴随的是,国内学术界、政策界和舆论界对“公共外交”的理解和界定也存在着很大差异;“公共外交”与“文化外交”“民间外交”“公民外交”等经常被混为一谈;各种新概念,如“城市外交”“公司外交”“高铁外交”等不断涌现,并纳入“公共外交”范畴之中。于是,“公共外交”成了无所不包的东西。这种现象,无助于深化“公共外交”研究,也不利于“公共外交”作为一个学科的发展。
研究“公共外交”首先需要弄清楚人们对“公共外交”的各种不同界定;同时还必须比较、厘清“公共外交”与其他相关及类似概念,如“传统外交”“文化外交”“公民外交”“公共事务”“宣传”“心理战”“政治战”“国际政治传播”以及“战略交流”等的区别与联系等,从而形成对“公共外交”的一种相对明确的界定。明确“公共外交”与这些相关概念在内涵与外延方面的异同,有助于大致确定“公共外交”研究的边界,有助于更加平衡和全面地审视前人在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进一步深化“公共外交”研究。
一、公共外交与传统外交
爱德华·R·默罗在被任命为美国新闻署署长时曾这样界定“公共外交”:公共外交不同于传统外交,它不但包括与政府间的互动,而且包括主要是与非政府的个人和组织之间的互动。另外,除政府部门的观点外,公共外交活动经常会提供许多代表美国个人和非政府组织的不同看法。与默罗的界定不同,多数人把“公共外交”看作一个国家针对其他国家民众开展的旨在推动相互理解与合作的信息、文化交流等活动,而把不同国家政府间的互动归于“传统外交”。曾长期在“美国之音”(VOA)任职的汉斯·N·塔奇(Hans N.Tuch)指出,不同于传统外交,公共外交包括国家间通过政府、外交部门的互动开展的关系。“传统外交经常是——必须是——一种要求保密和隐私的过程(外交中的机密性决不意味着缔结秘密条约或盟约。其意思仅仅是,为达成协议,其过程是秘密的)。相反,公共外交几乎经常是一个公开的过程。公开性(publicity)是其内在的目的;直接诉诸于公众:我们希望人民知道和理解。”①
就具体内容和活动方式而言,公共外交与传统外交有明显不同,但其基本目标可能是相同的或互为补充的。从事传统外交的外交官通过与外国政府代表接触,以促进自己政府的国际事务战略目标中阐明的国家利益。而公共外交则通过政府与外国公众,特别是与经过细心选定的部分外国公众进行沟通,让他们理解这个国家的观念与理想、制度与文化以及其国家目标和当前政策,以促进他们对这个国家历史、文化、价值观、制度和政策等的理解或认同,从而形成对其战略目标的支持,实现自身的国家利益。沃伦·克里斯托夫(Warren Christopher)在任副国务卿时曾表示,通过寻求与其他国家的人民之间的沟通,公共外交补充并加强了传统外交。他认为,公共外交有四个目标:第一,确保其他国家更准确地理解美国及其价值观、制度和政策;第二,确保美国对其他国家的理解及对美国与这些国家之间关系的理解是全面的和准确的;第三,确保这种相互理解在不同文化间得到合作性的个人和组织关系的支持;第四,确保美国政府在制定国际政策时,充分考虑外国公众的价值观、利益和首要关注。②美国公共外交咨询委员会(U.S.Advisory Commission on Public Diplomacy)在1985年的报告中也表示:“通过向外国公众解释美国的政策、向他们提供关于美国社会和文化的信息、让很多人亲身感受我们国家的多样性,以及通过评估外国公众对美国大使及美国的外交政策制定者的看法,公共外交补充和强化了传统外交……公共外交不是传统外交的替代物,它是承认思想和观念在塑造世界上大多数人的忠诚和政治理解方面的重要作用。”③美国前驻叙利亚和阿尔及利亚大使克里斯托夫·罗斯(Christopher Ross)把公共外交视为传统外交的公开面貌。传统外交通过与外国政府的秘密交换来促进美国的利益。公共外交,除接触政府官员外,还通过接触政府外的民众,包括大众和精英,支持传统外交。它与传统的外交活动是相协调和平行的。④
美国南加州大学公共外交研究中心尼古拉斯·J.卡尔(Nicholas J.Cull)教授这样区分“传统外交”和“公共外交”:如果外交是一个国际行为体通过与其他国际行为体的接触实施其外交政策的活动(传统上的政府与政府的联系),那么,公共外交就是一个国际行为体通过接触外国民众来实施其外交政策的活动。它由五个核心组成部分:倾听、支持(advocacy)、文化外交、交流外交(exchange diplomacy)和国际广播。⑤美国国会研究局(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的外交政策分析家肯侬·H.中村(Kennon H.Nakamura)和马修·C.韦德(Matthew C.Weed)也做了类似区分:公共外交是对由职业外交官之间进行的官方互动主导的、传统的政府间外交的一种对外政策补充。美国公共外交指的是与另外一个国家的公民、社区和公民领袖、记者及其他意见领袖等的直接互动的活动。公共外交试图影响其他社会的态度和行动,以支持美国的政策和国家利益。公共外交要求通过人民和思想的交流,建立长期关系并形成对美国及其文化、价值观和政策的理解。传统外交,包括强有力地向外国政府阐述美国的政策,分析和报告外国政府的影响美国利益的行动、态度和趋势等。⑥
从美国公共外交的历史发展来看,“公共外交”始终是服务于美国的传统外交政策的,着眼点同样是美国现实的国家利益。传统外交,指的是政府间的关系,具有一定的非公开性;公共外交,指的是一国政府对其他国家民众开展的活动,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公开性。说“公共外交”服务于政府间传统外交,是传统外交的重要补充,并不是说它的重要性低于传统外交。事实上,在美国的社会制度背景下,公共外交在其国家整体外交中的重要性、对美国国家利益的实现与维护所发挥的作用,可能丝毫都不亚于其传统外交。
二、公共外交与宣传
“宣传”一词源于17世纪罗马教皇为传播天主教信仰而建立的罗马天主教枢机主教委员会,它在现代的同义词是“谎言”“欺骗”和“洗脑”等。出于天主教对新教传播的担心,教皇格利高里十五世(Pope Gregory XV)在1622年发明了“宣传”这个词,建立了信仰宣传办公室(Office for the Propagation of the Faith),以监督教廷在新世界的传教活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协约国英国和美国把对敌国的沟通和说服策略称为“宣传”,于是“宣传”就成了一个贬义词。美国南加州大学安能伯格传播与新闻学院教授尼古拉斯·J·卡尔(Nicholas J.Cull)等主编的《宣传与大众劝说:1500年以来的历史百科全书》一书中这样解释了“宣传”:“进行宣传活动必须是有意识的、故意的。宣传的‘目标’是关键。没有目标,宣传就没有目的和方向……宣传就是为了一个特定目标,故意通过观念和价值观的传播,而非通过暴力和贿赂,来影响公众舆论。”现代政治宣传是有意识用来直接或间接地服务于宣传家及其政治强人的。宣传的目的是说服其对象,只有一种正确的观点,排除所有其他选择。⑦在美国的政治和社会话语中,“宣传”在很多情况下都被视为一种负面的东西,甚至被等同于“谎言”“欺骗”等。因此,美国人更愿意把自己国家的对外信息活动叫做“公共外交”,而非“宣传”。克里斯托夫·罗斯说:“很多宣传包含着谎言,而且不会回避谎言。在公共外交活动中,我们不故意去传播不真实的东西。我们可能会以某种方式表达它们,但我们讨论的是事实。”⑧在20世纪的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宣传与政府对关于其国家和社会的错误信息的传播经常是被联系在一起的,公共舆论倾向于把“宣传”视为欺骗和危险的行为。
美国一直标榜自己对外开展的公共外交活动,是在向世界传播关于美国的真实信息。信息的真实性被视为美国公共外交的生命,也被视为提高美国的可信度或信誉的最佳途径。美国还经常攻击前苏联、中国等国的宣传活动。但从美国开展的某些公共外交活动的具体内容及其形式来看,把它称之为美国人所理解的意义上的“宣传”也不为过。这里讨论的“宣传”,严格说来,指的是“对外宣传”。公共外交和宣传的效果和界定,经常是难以分开的。实际上,在美国学界和政界也经常出现“公共外交”和“宣传”相互替换使用的情况。美国国内对政府资助的信息活动到底是经过巧妙处理的“宣传”,还是正当的“公共外交”,也时常有着争论。甚至在反恐战争时期,“宣传”和“公共外交”也被认为是可以互相替换的,而不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战略性说服手段。⑨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南希·斯诺(Nancy Snow)教授评论道:“公共外交的定义在任何时候都是与民族国家政府的官方目标有明显的联系的,这倾向于意味着一种与宣传后果相联系的更负面的解释。于是,或对或错,公共外交被视为一系列主要大众传播技巧,利用超越理性事实的情感诉求以改变态度,隐匿对信息发出者不利的信息,以及传播促进诸如一国社会、经济或军事目标等特定意识形态的信息。”⑩当人们如此看待美国的公共外交时,它与“宣传”之间的界限也就荡然无存了。也有人用“文化宣传”(Cultural Propaganda)来指代美国的“公共外交”。
既然人们对“公共外交”和“宣传”都没有统一的界定,这就给论者各取所需提供了便利。若深入考察美国的公共外交活动,应该可以看出其中很大一部分内容就是宣传;而且,无论从形式还是从内容或效果看,这个概念本身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宣传”。只是美国希望避免用“宣传”描述美国新闻署和“美国之音”的活动的负面含意。英国莱斯特大学教授G.R.贝里奇(G.R.Berridge)等编著的《外交辞典》中把“公共外交”直接视为描述“20世纪后期外交官进行的宣传活动的一个术语”。
但无论如何,“公共外交”和“宣传”在采用的手段、追求的效果、产生作用的机制等方面,都有许多相似或相通之处。美国本宁顿学院(Bennington College)杰弗里·艾伦·皮格曼(Geoffrey Allen Pigman)教授评论道,“公共外交”和“宣传”有许多相同的目的,其中最重要的是“影响公众态度”或“影响人民的看法”。传统的外交学者曾试图为“宣传”规范地划出边界,防止在公共外交实践中使用它。不过,尽管“宣传”可能有负面意涵,但对于在特定有限条件下实现特定目标,它的使用可能是有效的。在分析和评估当代公共外交的效果时,反馈环节至关重要。而区分有效的公共外交活动与无效的公共外交活动的一个关键因素是信任。从这些意义上看,“公共外交”和“宣传”区别,仅仅在于人们对它们形成的情绪或心理上的反应,特定的历史和特定的社会文化氛围赋予了“宣传”一词负面的意涵。如果抛开情绪性的反应,更中性地理解“宣传”,“宣传”与“公共外交”的某些内容之间的界限也就消失了。
三、公共外交与心理战
“心理战”(psychological warfare)不是一个新鲜的词汇。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就曾针对敌对国家开展心理战。所谓“心理战”,指的是在战争时期针对敌国有计划地运用宣传手段,传播某些观念和信息,以影响敌国军民的心理、情绪和行为,目的是瓦解其士气和斗争意志。“心理战”不同于其他形式的对外宣传,它的对象是敌国而非中立国家或友好国家的人民。由于国家间冲突或战争的多样性,“心理战”也被逐渐广泛应用于战略和政治层面,而不再局限于正式的战争形势下,因而也更多使用“心理行动”(psyops)一词了。心理战既广泛用于各种战争和冲突之中,也被用于和平时期的意识形态斗争之中。
从其手段来看,“心理战”和“宣传”以及“公共外交”中的广播电视活动等基本是一致的,只是“宣传”和“公共外交”的范围更加广泛,它们的对象及其所传递的具体信息和内容有很大差别。“心理战”主要运用于战争中的国家之间或具有重大战略冲突的国家之间,如: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对德国等敌对国家的心理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对法西斯国家的心理战,以及冷战时期美国等西方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宣传活动等。
美国为实现其自身的战略利益和对外政策目标,往往把公共外交活动和心理战行动糅合在一起,二者的部分行动是重合的。这样,也就很难用“心理战”或者“公共外交”来划分美国的很多行动了。从冷战时期美国对其他国家开展的公共外交活动来看,特别是从其对苏东社会主义国家开展的公共外交来看,很难把“公共外交”与“心理战”清晰地区分开来。美国对一个国家采取何种性质的公共外交,取决于美国公共外交对象国的不同以及美国与这些国家关系的性质和状态等因素。
也有人把公共外交视为心理战略(psychological strategy)的基本组成部分。因为,“第一,全球范围内大量公众能够获得的信息量的增加,直接影响了公众的看法和态度,反过来又影响了政府的行为和决策。第二,认知(perceptions)和现实(reality)一样重要。看上去是真实的就会被认为是真实的,在没有言论自由的地方,更是如此。”这种理解只是非常狭隘地理解了“公共外交”,或者说只是把“公共外交”的一部分当成了“公共外交”的全部内容。但毫无疑问,公共外交的某些形式或内容,也可能被运用于心理战的实施。
四、公共外交与政治战
在国际政治竞争或争夺的背景中,“政治战”(political warfare)是一个国家为实现其在世界上的政治规划而使用的工具,但它又不是一系列工具或手段的总和。在波士顿大学安吉洛·M.科迪维拉(Angelo M.Codevilla)教授看来,“政治战”指的是在战争中或像战争一样严重的不流血冲突中,为赢得胜利而动员人们进行支持或反对,是在特定冲突中,一个国家对其正在从事的事情或采取的政策的强有力的政治表达。科迪维拉认为,要想在政治战中取得成功,就必须引导对象国人民把他们自己的生活、财富和荣誉与进行宣传的一方所做的事情联系在一起,使他们理解后者所做的事情。发动或实施“政治战”的一方,既可能采取公开的行动,也可能采取秘密的行动,但它都必须向外国人提供他们应该站在“我们一边”考虑问题的真实、具体的理由,并为其提供具体诱因以大大提高站在“我们一边”的机会。
就其应有的环境而言,“政治战”与“心理战”类似,二者都是主要用于战争中或者类似于冷战这样的冲突中。而“公共外交”应有的范围则要宽泛得多,它既被广泛应用于和平时期,也被用于战争和冲突时期。公共外交所追求的目标,也比“政治战”更加宽泛:“政治战”追求的是在冲突中取得胜利;“公共外交”在特定的情境下当然也有此类目标,但它还包括促进国家间、民族间或不同文化间的相互理解和沟通等。二者的另一差别是:“政治战”采取的行动,既包括公开的,也包括不公开的;而“公共外交”活动是公开的。不过,在特定国家和特定时期,针对特定事件或问题,也很难在“政治战”和“公共外交”之间划出清晰的界限。归根到底,二者都服务于特定国家的利益,都是实现国家利益的手段或工具。
五、公共外交与国际政治传播
“国际政治传播”(IPC)通过报纸、广播、电源、人员交流、文化交流及国际传播的其他手段,以实现某种政治效果。“国际政治传播”是一种比较中性的、没有感情或意识形态色彩的表达,它囊括了“公共外交”“宣传”“心理战”“政治战”等这几个概念所包含的全部内容。国际政治传播可以分为四类:官方的、意在影响外国公众的传播;官方但非意在影响外国公众的传播;意在从政治上影响外国公众的私人传播;以及没有政治目标的私人传播。
“国际政治传播”中第一类也就是所谓的“公共外交”。几乎每一个有能力的国家都会资助和开展这些国际政治传播活动。研究美国的“公共外交”,需要越来越多地增加对美国私人传播之海外影响的关注。美国私人传播的影响是难以估量的,它所产生的效果可能比“公共外交”的影响要大得多。因此,近年来美国政府在对外推行公共外交时,也越来越强调和发挥美国的个人、公司或其他非政府组织在其中的重要作用。
从政策措施与行动效果之间的复杂关系来看,想把“公共外交”与“国际政治传播”截然分开恐怕是不可能的。各种因素在相互交织、相互影响,共同决定了“公共外交”或“国际政治传播”活动的效果。有的政策及其实施可能会产生预期效果,有的可能不会;而有的政策和行动可能产生了其他令人意想不到的效果;而且,无意中产生的效果有时候可能比刻意造成的效果更加深刻。
因此,在公共外交研究中,特别是在评估公共外交之效果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区分“公共外交活动”和“能够产生公共外交活动之效果的活动”之间的区别与联系。公共外交不是在独立的空间中开展并产生影响的,许多本不属于公共外交范畴的活动,能够对公共外交活动的效果产生影响。对于这类活动,在对公共外交活动的效果进行评价时是不能忽视的。“国际政治传播”的外延远比“公共外交”广泛。研究公共外交时,需要适当观照“国际政治传播”领域大量能够影响“公共外交”之效果的活动或内容。
六、公共外交与公共事务、公共关系
在美国,公共外交主要是对外的,是针对外国公众开展的信息、交流等活动,是美国与世界的对话;而公共事务针对的是国内民众,目的是向国内媒体和民众提供信息并影响他们,促进国内公众对政府政策、活动的理解和支持。公共事务项目处理的主要是媒体事务,本质上是反应性的,主要是对一个事件或新闻故事做出反应,或者阻止媒体的行动,公共事务时限通常是由数分钟到数天来衡量的,它要求尽可能及时地做出反应;而公共外交是积极主动的,它应对和处理的问题也宽泛得多,除应对媒体外,它还要应对整个社会的方方面面,既包括向对象国民众提供信息,也包括建立各种关系等,公共外交寻求的是改变目标对象的态度,并说服他们,为实现成功,公共外交的时限可以用数月、年甚至十年来衡量。
美国国务院曾这样区分“公共事务”和“公共外交”:“公共事务指的是向公众、媒体及其他组织提供关于美国政府的目标、政策及活动的信息的活动。公共事务主要是向国内公众提供信息……而公共外交则试图通过理解外国公众、向他们提供信息并影响他们,来推动美国的国家利益。”公共外交不是海外版的公共事务,前者比后者涵盖的内容更加广泛,形式更加多样,手段更加复杂。
在1999年美国行政部门机构改革之前,美国负责公共外交事务的是相对独立的美国新闻署。之后美国国务院设立统管“公共外交”和“公共事务”的副国务卿,承担对内和对外的双重使命。尽管负责“公共外交”和“公共事务”的机构是一体的,而且“公共事务”方面的某些活动确实可能也会对“公共外交”产生某种影响,但在公共外交研究中,仍需注意二者的区别,大致划清二者的边界。
另外,各国,特别是美国在开展公共外交时,越来越重视发挥各种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等私营部门的作用。美国学术界近年来开始把某些非政府行为体的活动也视为公共外交的一部分。这就导致公共关系活动与公共外交活动的趋同现象。皮格曼教授评论道,传统上,公共关系和公共事务被认为是不同于公共外交的,公共事务涉及的是政府与其国内民众的沟通,公共关系涉及的是私人行为体与其受众及支持者之间的沟通。但实践中,这些边界越来越模糊了。这种边界的模糊,对于公共外交研究形成了更大挑战,但也为公共外交研究边界的明确化提出了更高要求。让模糊地带更加清晰,才有助于推进和深化公共外交的研究。
在中国,也经常面临公共外交研究边界被不断放大的情况。比如,把中国外交部对国内民众开展的“公众开放日”活动也视为“公共外交”活动;把“公司外交”“城市外交”等等也纳入公共外交研究的范畴,这种做法,使“公共外交”的内涵和外延无限扩大,表面上呈现出“公共外交”研究的繁荣局面,实际上却忽视或冲淡了对传统公共外交活动及其历史的研究,也不利于“公共外交”作为一个新兴学科在中国的发展。
七、公共外交与公民外交
“公共外交”这个概念突出的是外交活动的性质,“公民外交”突出的则是开展外交活动的主体。在美国,“公民外交”指的是这样一种观念:公民个人有权利甚至责任去帮助塑造美国的对外关系。公民外交官是非官方的大使,他们或者参加海外交流项目,或者招待在美国的国际交换项目参与者,并与之互动。有些公民外交的参与者是有薪水的,而大多数公民外交官是志愿者,他们提供时间、领导技巧、专业知识及其自己的金钱和其他资源,以维持构成美国公民外交基础的地方非政府组织。公民外交活动中一些交流项目的资金至少有部分是美国政府提供的,因而,公民外交也构成了美国公共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
“公共外交”最有效、最深刻的部分是不同国家公民之间直接的思想和文化交流活动。作为个体的不同国家公民间的交流有助于建立持久的友谊和关系,也应该更有助于促进国家间的相互理解和尊重。美国政府资助和支持的交流项目也依赖私营部门合作者和公民外交官,一方面可以提高这些项目的可信度,另一方面可以降低政府开支。由于美国有大量参与到公民外交活动中的非政府组织和个人,他们对美国外交及美国公共外交的影响是不能低估的,他们为美国外交和公共外交动员了大量的社会力量和社会资源,对政府的力量发挥了“放大器”的作用。因此,公民个体或公民组织如何参与并影响美国公共外交活动,也是研究美国公共外交时不容忽视的问题。
八、公共外交与文化外交
贝里奇等编著的《外交辞典》中把“文化外交”界定为“把一个国家的文化成就推向国外的活动”。与文化外交相比较,“公共外交”这一概念强调的更多是活动的对象和形式,“文化外交”强调的更是活动的内容和性质。从形式上看,“公共外交”强调的是一国政府针对其他他国的民众,开展的各种形式信息传播和交流活动,重点在对象和形式;“文化外交”则不局限于此,它不但包括一国政府对他国民众开展的文化交流活动,还包括政府与政府之间的文化关系和文化交流活动。从内容上看,“文化外交”指的是一个国家的政府把其国家的文化传播给其他国家的民众,以推动对其国家理想和制度的理解,进而争取对其政治和经济目标的支持的活动,其内容强调的是文化传播和文化交流;而“公共外交”的内容更广泛,并不局限于文化传播,它既包括文化传播,也包含内外政策的解释说明等。二者的共同之处在于都高度重视文化在国家间关系中的作用,都强调和推动文化交流和跨文化对话。
正是基于文化在公共外交中的核心地位,美国文化外交咨询委员会的报告认为“文化外交是公共外交的关键”。“因为只有在文化活动中,一个国家自己的思想才能更好地展现出来。外交能够以非常巧妙、广泛和可持续的方式促进我们的国家安全……对于塑造我们的世界领袖地位,包括反恐战争,美国的文化财富所发挥的作用绝不会比军事行动的作用更小。植根于我们的艺术和知识传统中的价值观,构成了一种抵抗黑暗力量的堡垒……文化外交,显示着一个国家的精神,可以在美国政治生活中解释其复杂的历史:当我们的国家处于战争之中,外交工具包中的任何一种工具都得以使用,包括推进文化活动。”文化和文化外交的重要性,还体现在“文化实际上就是权力……文化交流是一种学与教、出口与进口、劣势与优势、谦恭与自信之间复杂和平衡的公平交换”。
在研究美国公共外交,特别是涉及文化外交时,需要准确把握“文化外交”和“文化政策”在美国社会文化氛围中的意涵。文化外交是服务于美国利益,特别是其长期利益的,如维护和平、扩展民主及促进经济合作等。美国在其国内社会政治生活中往往避免推行“文化政策”,但在国外,“它意味着一种有规划的方法,以实现美国在教育和智力领域广泛利益的最大化……美国在外国的文化政策目的是培育、纠正、加强以及必要时建立与美国的文化和教育联系。”也就是说,在研究美国公共外交时,有必要深入考察美国的对外文化政策,这有助于从更深刻的层面上理解美国的公共外交。
九、公共外交与战略交流
“战略交流”(strategic communication)是美国军方经常使用的一个概念。美国军方把“战略交流”界定为:操控信息战场,塑造信息以击败敌人的一种手段。而美国的公共外交活动,主要着眼于关系的建立,如增进信任、创造关系网络、建立信誉等。美国国务院用“公共外交”描述的是与外国民众进行了交流,“战略交流”涵盖的是国防部与外国公众、军事对手、伙伴国和非伙伴国政府、其他美国政府部门以及美国人民之间的互动及对他们的影响。
美国国防科学委员会(Defense Science Board)在2004年《战略交流:国防科学委员会报告》中指出,战略交流包括四种核心工具:公共外交、公共事务、国际广播活动和信息活动(IO)。在这里,公共外交被视为“战略交流”的核心工具。奥巴马总统根据美国《2009财年国防授权法》之要求在2010年3月16日向国会相关委员会提交的关于公共外交和战略交流的全面、跨部门战略报告《国家战略交流框架》(National Framework for Strategic Communication)把“战略交流”界定为:(1)言与行的同步,以及所选择的听(观)众如何认识这些言行;(2)旨在与目标受众进行沟通和接触的项目和活动,包括由公共事务、公共外交和信息活动专业人士实施的那些项目和活动。在这里,公共外交也被视为战略交流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而在美国著名国际政治学者、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约瑟夫·奈(Joseph Samuel Nye Jr.)看来,战略交流只是公共外交的一个方面。奈认为,公共外交包括三方面内容:第一个也是最直接的方面是日常交流,包括解释国内和外交政策决策的环境,以及应对危机和反对攻击的准备;第二个方面是战略交流,包括开展一些简单的、类似于政治运动中出现的项目;第三个方面是通过奖学金、交流、培训、研讨班、会议等途径,在多年内与关键的个人发展持久关系。这里需要特别注意,奈虽使用了“战略交流”一词,但他所谓的“战略交流”远不及以上所述的“战略交流”所指代的内容那样广泛。奈在其著作中也未对“战略交流”作更深入的论述。
2010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把“战略交流”视为加强美国国家能力的重要手段。该报告指出:“有效的战略交流对于维持全球合法性和支持我们的政策目标是必不可少的。协调我们的言与行,是整个政府的沟通文化必须培育的一种共同责任。在我们审慎的交流和接触中,我们必须做得更加有效,更好地理解世界各国人民——而不仅仅是精英的态度、看法、不满和关注。这使我们能够表达可信、一贯的信息,制定有效的计划,同时更好地理解我们的行动被如何认知。我们还必须运用各种交流方法,包括新媒体,与外国公众交流。”从该报告对“战略交流”的目标、手段等的分析来看,它与“公共外交”也有许多相同和相通之处。
公共外交属于传统国际关系研究中被关注较少的领域。随着全球化的突飞猛进,国家间的交流变得日益紧密,国家间的关系也日益复杂,公共外交在国家间关系中发挥的作用也越来越突出。公共外交研究已开始成为国际关系研究的重要学术增长点。公共外交与上述其它概念所指代的都是信息传播活动,它们的手段和方式也高度相似,其区别在于活动的对象、具体目标、性质、涵盖的内容以及适用的时空背景等有所不同。但若把它们放在一国整体战略的框架下,或放在其对外交往的历史中来审视,可以看出其总体目的和性质又是相同的,都是服务于其国家战略和国家利益的。梳理、对比和分析公共外交与其他相关概念的差异,有助于更准确地理解公共外交的内涵和外延,从而有助于为公共外交研究确立大致明确的边界,为公共外交及相关问题研究和讨论提供了相对稳定的基础,在一定程度上避免概念的泛化、误用和滥用,进一步推动公共外交研究走向深入。
注释:
① Hans N.Tuch.CommunicatingwiththeWorld:U.S.PublicDiplomacyOverseas.New York:St.Martin’s Press.1990.pp.3-4.
② Allen C.Hansen.USIA:PublicDiplomacyintheComputerAge.New York:Praeger.1984.p.3.
③UnitedStatesAdvisoryCommissiononPublicDiplomacy.1985 Report.inside cover.1985.p.2.available at:https://www.state.gov/1985-advisory-commission-annual-report/.
④ Stephen Hess & Marvin Kalb ed.TheMediaandtheWaronTerrorism.Washington,D.C.: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2003.pp.224-225.
⑤ Nicholas J.Cull.TheColdWarandtheUnitedStatesInformationAgency:AmericanPropagandaandPublicDiplomacy,1945—1989.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8.p.XV.
⑥ Kennon H.Nakamura & Matthew C.Weed.U.S.PublicDiplomacy:BackgroundandCurrentIssues,in Matthew B.Morrison ed.U.S.PublicDiplomacy:BackgroundandIssues.New York:Nova.2010.p.2.
⑦ David Welch.“DefinitionsofPropaganda,”in Nicholas J.Cull,David Culbert & David Welch eds.PropagandaandMassPersuasion:AHistoricalEncyclopedia,1500tothePresent.Oxford,England:ABC-CLIO,Inc.2003.pp.317-319.
⑧ Stephen Hess & Marvin Kalb ed.TheMediaandtheWaronTerrorism.Washington,D.C.: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2003.pp.224-225.
⑨ R.S.Zaharna.FromPropagandatoPublicDiplomacyintheInformationAge,in Yahya R.Kamalipour & Nancy Snow ed.War,Media,andPropaganda:AGlobalPerspective.New York: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INC.2004.p.219.
⑩ Nancy Snow.U.S.PublicDiplomacy:ItsHistory,Problems,andPromise,in Garth S.and Vicoria O’Donnell ed.ReadingsinPropagandaandPersuasion:NewandClassicEssays.London:Sage Publications.2006.p.2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