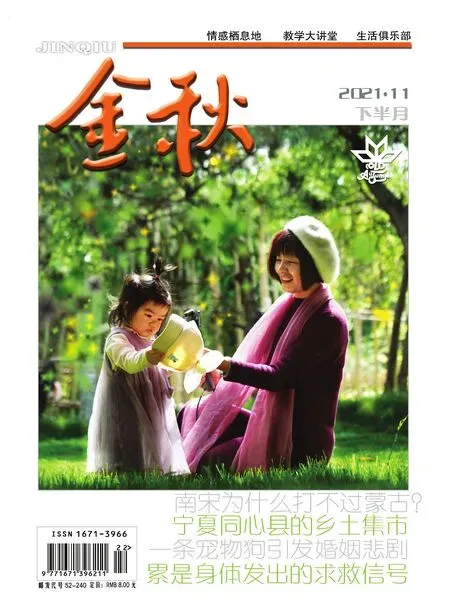回程,谁来接站?
2021-12-02陆晓雅老冯
◎文/陆晓雅 图/老冯
确信妈妈患上认知症之时,我也快到退休年龄了,退休后是成为妈妈全职/全天候的照顾者,还是兼顾照顾妈妈同时做自己原本计划要去做的事情?我内心很挣扎。有时候这种挣扎会在梦境中出现:有一次我梦见和一些人旅行,即将踏上回程(毫无疑问,“回程"象征着我退休后的人生)。有人通知说,回程将不安排人接送站,需要到站后自己解决。于是我开始焦虑,因为我带着老妈,还带了很多的行李,我不知道到站后我一个人该怎么办……
其实,我身边不乏孝顺父母的好榜样。我的一位好友是个非常优秀的中学教师,曾经给我讲过很多生动的教育故事,我本想她退休之后,帮她把这些故事整理出来,让她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方法可以得到传承。但她选择先全力照顾老妈,而且和她当老师时一样奋不顾身,顾不上自己也顾不上自己的小家。在为老妈送终后,她就查出癌症,什么都没来得及做,没能看到自己的外孙女出生就撒手人寰了。
坦率说,我担心自己也会走到这一步。有些认知症患者的病程可以长达十几年,比如美国前总统里根,是1994年向公众宣布他患了“阿尔茨海默病”的,直到2004年才去世。我想,如果为了照顾老妈,我现在就退出社会生活,大概以后就很难重新融入了。我担心,在漫长艰辛的陪伴路上,我的视野会受限,我的能力会衰退,我的社会关系也会渐渐失去联结……在完成了作为女儿的使命后,我会不会变成一个无聊、无趣、无能的“三无”老太太呢?
我早就期盼着退休,因为我已经准备好和朋友在公益领域创业——我知道我仍然具有工作的热忱和能力,仍然渴望发挥自己的创造性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但如果全职/全天候照顾妈妈,我的一部分生命潜能就没有机会发挥了,为此,我大概很难不产生一些负面情绪。带着这些负面情绪,我能照顾好妈妈吗?
好在,现在妈妈的病还在早期,生活尚能自理。她的楼下就是食堂,不想做饭了她就坐电梯下楼去买饭。老妈还有个小时工,每周会过来帮她洗衣和收拾房间。而最为难得的保障,是我们姐弟妹三个人相互支持,同心协力,没有一个人不拿妈妈当回事。
住得最近的弟弟,负责给妈妈买煤气,交水电费、电话费,修理一切坏了的物件,还每周买好蔬菜水果送到家里,甚至炖好鸡汤带过去。我做医生的弟媳妇,则是我妈妈免费的家庭医生兼医疗事务总管,她每周都会为妈妈拿药,周末到妈妈家为她“摆药”一一把一周要吃的药分好,装入分天的药盒。碰到看病、体检之类的事情,少不了她亲自出马,然后认真分析各种检查结果。可以说,老妈的身体状况,尽在她的掌握之中。
我妹妹是家中最小的孩子,也是我们姐弟妹三个人当中唯一在妈妈身边长大的,因此跟妈妈的互动也最亲、最无顾忌。在我们发现妈妈已经不会用热水器,经常是烧一壶水提到厕所“擦澡”后,妹妹和我开始每周给妈妈洗澡。要知道,洗澡对于常人来说没啥难的,但对已经很难理解洗澡程序的老妈来说,用喷头中的热水冲去脑袋上的洗发液,那无异于一场恐怖袭击啊,所以她会特别害怕,帮她洗澡的人还要防着不让洗发水迷了她的眼,或者水冲进了耳朵。而我妹妹就有能力连说带笑、连哄带劝、连拉带拽地帮助老妈完成整套洗澡程序,“香喷喷”地成为“出水芙蓉”,再穿上干净的衣服。妹妹的说说笑笑,可以说是一味非常独特的药,可以软化老妈,让她身体和心理都舒坦。这个独门秘籍,是我和弟弟都不拥有的。
在发现老妈“丢”了存折之后,我成了老妈的财务总管。我们先去银行挂失了存折,然后办了新的折子和借记卡。每个月,我从卡上给她取出一定现金作为日常开销。开始是一个月一次,后来我发现,老妈总是会把钱藏起来,大概是觉得藏起来才最安全,结果总是忘记放在哪儿了。于是她就给我打电话:“给我送点钱来,我没钱了!”在我忙于工作之时,我肯定无法分分钟把钱送到。我改为每周给她发一次零花钱,且都是事先换好的零钱,一大把零钱递过去,她一定觉得钱很多,自己手头很“富有”,这样还能防止她拿着百元大钞出去买东西忘记拿找的钱。我还把一些备用的零钱放在某个隐蔽之处,一旦老妈打电话要钱,我就告诉她;“你上那儿找找看!”
有了弟弟妹妹们的共同努力,我在退休之后实现了自己在体制内未曾实现的梦想:和“青春热线”的资深志愿者杜爽一起,创办了一个公益机构“北京歌路营”,服务于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
创业自然是忙碌的。好在小学六年级的时候,我们的自然课老师就给我们讲过华罗庚,讲他在工厂推广优选法和统筹法,因此我从很年轻的时候就学会了时间管理,很善于统筹和优化自己的工作和生活安排。现在翻看那些年的《效率手册》,我发现除了工作外,“妈妈”绝对是个高频词,不是“看妈妈”“和妈妈去公园”,就是“接妈妈”“送妈妈”——在那段时间里,我经常接妈妈到自己家里住。我先生不用坐班,我出去工作时家中有人和妈妈在一起,总是放心一些。
我住的地方离妈妈家不近,坐公交单程要一个半小时。我听说有人把父母的房子卖了,在自己住的小区另租房子让父母住。这种“一碗汤”的距离(端一碗热汤过去不会凉),据说是亲子间的最佳距离,既便于照顾,又保留各自生活空间。我觉得自己小区内的环境不错,是不是也在小区里租个两居室,把妈妈和比妈妈还要年长7岁的公公一起接过来,请保姆照料他们呢?我甚至还去房屋租赁公司打听过,但想想觉得太过复杂,随着老人身体状况的衰退,我们肯定要请两个保姆,协调两个保姆还不让我头疼死?弟弟妹妹也反对,因为这样老妈离他们远了,照顾起来更加不方便。
妈妈到我家小住,对她对我们都不容易。这也不奇怪,某些正常人还会换了床就睡不着呢,医学上把这种“认床”现象叫做“第一晚效应”。老妈倒是没有“第一晚效应”,不过作为认知症患者,在一个全新的环境中实在是挑战多多:厕所在哪里?哪条毛巾是自己的?可以用哪个水杯喝水?早上几点起床?白天没事儿的时候干点啥?想出去怎么办?这一切,她内心肯定焦虑,但无法说出来。而家里的人呢,也得面对她因为失去认知能力而造成的种种麻烦:她会用我先生的牙刷刷牙,拿我的毛巾擦脸,用我女儿的杯子喝水。鉴于妈妈超强的自尊心,当认知障碍发生时,我们不能说“你拿错了”,只能另外想办法,比如女儿把自己的水杯放到高处,这样就不会被外婆拿到了。
碰到这些“麻烦事儿”,不烦躁、不抱怨并不容易。从认知上讲,不把这些事情当成“错误”,而是接纳她的失能,才能不心烦、不抱怨。不过,除了认知问题,亲子关系的质量也直接影响着互动。
由于我从一岁零九个月就离开了妈妈,妈妈有很长时间在国外工作,她又是那种很少对孩子表达爱和鼓励的人,因此我和妈妈的人生之路,原本是一种弱联结,特别是在情感上和精神上。现在,当妈妈患了认知症,我知道这种弱联结需要改变,但我并不想完全牺牲自己,让妈妈自己的人生之路完全覆盖、淹没掉我的一段人生之路。我们是两代人,也是两个人,我们彼此联结,但也有各自的人生使命。最重要的,是如何改善我们彼此联结的质量,在妈妈人生之路的最后一段,能让她感觉到被爱;在她的人生之路中断之后,我既不会为自己的路没有与她并行而后悔,也不会为自己的路完全被吞噬而委屈——我在照顾她的同时,也努力活出了自己有质量的晚年。
2013年,在我60岁生日那天,我对公益机构的年轻同事说:“拜拜了,我要第二次退休了!”
选择第二次退休,是因为老妈的病已经进入中期,真的需要我投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了。好吧,先不管我的回程有没有人接站,让我在妈妈的回程中与她一路相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