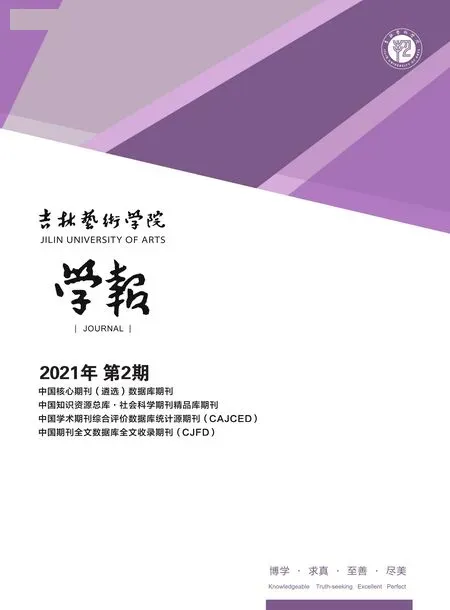潘之恒戏剧表演艺术理论研究
2021-12-01任东岳
任东岳
(天津音乐学院,天津,300171)
中国古代戏剧是结合音乐、舞蹈和诗歌的综合性表演艺术,纵观中国古代戏剧表演理论的发展历程,那些戏剧表演艺术理论的研究著作具有珍贵的历史价值。发展前期特点是较为注重艺人的演出活动、生活和剧场记录等,如唐代崔令钦的《教坊记》中较多地记载乐伎生活、教习和演出情况。宋代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记载勾栏的演出盛景和诸多艺人资料。随着中国古代戏剧艺术的形成和成熟,促进了戏剧表演艺术的兴盛,发展后期较为关注戏剧表演艺术的评论。如元代夏庭芝的《青楼集》主要记述了演员的生活事迹和评价。明代嘉靖和万历年间,由于传奇达到了创作高峰,戏剧演出活动蓬勃高涨,许多戏剧家也投身于演出之中,出现表演艺术与戏剧创作一同繁荣的景象,因此,明代的表演艺术理论主要掩藏于戏剧文学理论中,多散落于文学佳作之中。潘之恒作为这个时期杰出的文人,他的戏剧表演艺术论述在众多作品中脱颖而出,令人瞩目,从而打开戏剧舞台艺术的新局面,成为影响深远的戏剧理论家。
一、潘之恒表演论
潘之恒(1556—1622),字景升,号鸾啸生、亘生等,歙县岩镇(今安徽省)人。自幼聪颖而博览群书,才思敏捷,善与人交,广交当世文人,文采斐然,擅长古文辞赋和诗歌写作,是明代著名的文学家和地理学家。在诗歌、戏剧表演评论和地理辑录方面佳作丰富,著有诗集《鸾啸集》《涉江集》《戊己新集》等,撰有地理游记与辑录《黄海》《名山注》等。关于戏剧表演评论主要集中在杂文著作《亘史》与《鸾啸小品》之中,包含演员小传、观戏心得等,目的是佐理演员积累经验,提升戏剧表演水平,这些精湛的评论与见解成为不可多得的戏剧表演艺术专论。
1.潘之恒之表演技巧层次论
潘之恒在《与杨超超评剧五则》[1]44中提出了演员需要具体的表演技巧,他将其概括为“度”“思”“步”“呼”“叹”这五方面。而这五个方面又可以分为三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是“度”,是潘之恒着重强调的重点。“尽之者度人,未尽者自度”[1]44,他强调“度”分为两个方面,首先便是“自度”,演员沉浸在角色之中,与角色共情共感,但这不是潘之恒所着重强调的表演精巧及所追求的境界,而是追求“度人”的境界,这也是“度”的第二个方面。“度人”指的是通过表演技巧,观众为之共情共感,一起沉浸在剧作家所营造出来的情感世界,与剧中的人物同喜同悲。“度”有传情、共情之意,在表意基础上更要传情,让观众理解动作中隐藏的真情实感,明白人物此时内心的悲伤或欢喜,更深层次的便是要通过言语、动作、情态达到与观众连接情感,共情之境,达到“尽之者度人”的艺术境界。“度”除了是表演基本技巧所要达到的最高艺术境界,同时也是“思”“步”“呼”“叹”所追求的根本目标,处于统领的地位。
第二个层次则为“思”。潘之恒以“西施捧心”为例阐述了演员在表演人物时并非单纯地追求外在形象上的相似,而是要追求神似。“西施之捧心也,思也,非病也”[1]45。其中“思”与“病”只是一字之差,但是这其中所蕴含的情感则大不相同,若只是停留在形似的“病”上,便只能是东施效颦,传达不出人物的精髓,达不到塑造人物时神似的境界。“致其技于真”,而“真”表示要达到外形与内在的高度统一,不但形于真,更要思于真,将二者与人物高度契合才可以达到“西施捧心,思也”的艺术效果与精神追求。
最后一个层次便是“步”“呼”“叹”。“步”表达的是舞台上的形体技巧,“呼”“叹”则是语言技巧,在“思”与“度”的指导之下进一步精进自己的表演技巧。“步”除了要姿态优美,更要“合规应奏”。“邯郸之学步,不尽其长,而反失之”[1]44-45,舞台上演员的形体动作不应“邯郸学步”,一味地模仿别人,只空有其形,未得其神。应形从剧出,立足于具体的人物形象,适宜剧情节奏,最后达到“令巧者见之,无所施其技”的技术追求,同时使观众在观赏时让人有“仙度”之美,动如“若翻燕”,静若“立鹤”,让形体动作具备“美感”,拥有审美的价值,使观众在观看时体验到一种美的审美享受。“呼”“叹”除了要字正腔圆,更要表明达意。台词字正腔圆,在规定情景中准确地传递出人物所要表达的重要信息,明确地传递出导演的中心思想。“呼发于思”,语言的表达皆出于“思”,发于情,语言表达的目的在于抒其情,传其韵,动情感人。“叹”应“缓辞劲节,其韵悠然,若怨若诉”,故演员在语言技巧上应让观众能切身感受到真实的情感,让观众单单听到演员的声音便身临其境,画面感十足。
“度”“思”“步”“呼”“叹”既是表演技巧,也是表演技巧所要追求的艺术层次。潘之恒从实践角度出发,以杨超超的成功演出经验作为主要阐述角度,不但对表演声台行表提出了具体的指导,同时也指出演员在表演技巧上要追求“思”的神似,讲求“尽之者度人,未尽者自度”的艺术境界。由此可以看出,潘之恒的表演技巧层次观对现在的表演艺术具有极大的实践意义。
2.潘之恒之表演情感境界论
中国古代戏剧表演讲究虚实结合,在情感上追求意境的表达,情境交融,主张在虚实之间追求神似。这一观点在潘之恒的表演当中有了比较充分的表达。潘之恒受到汤显祖的影响,强调“非人胜,而情胜也”[1]39,主张在表演中以情写情,以情传神。
潘之恒的《情痴》是在观看汤显祖的《牡丹亭还魂记》之后所评论的一篇文章,他赞叹:“以情写情,有不合文人之思致者哉”。[1]72同时他在文中对剧中杜、柳二人扮演者的表演做了详细的阐述。潘之恒主张只有“以情传神”的作品才能称得上好的作品,同时他也强调“能痴者而后能情;能情者而后能写情”[1]72-73才是一个优秀的演员。“痴”在汉语字典中为极度迷恋某人或某种事物而无法自拔者,要想演好一个角色,便要成为一个“痴者”。而如何达到“痴”的境界,便是要对表演有着很深的执念,只有在情感上极其丰富的人才可以达到“痴”的程度。“能情”有解情之意,同时在文中强调,“而最难者,解杜丽娘之情人也”[1]72,潘之恒认为《牡丹亭》的杜丽娘之所以难演,是因为“解情”,因不知如何解情便无法传情。演员要善于“解情”,善于从作品的细节中发现人物及剧本的表层意象,通过深层次的研读与体会,进一步寻找作品的深层内涵。古代戏曲作品擅长追求“意境”的营造,如若无法“解情”,便无法真正地理解作品中最重要的精髓,最后便“不知其所始,不知其所终,不知其所离,不知其所合”[1]73。“痴情”与“解情”为的是能更好地“写情”,这个写情在表演中强调的是传情,舞台之下要逐渐化身为人物,上了舞台之后便要成为人物,同时还承担着一份传递情感的责任,让观众在观看时为杜、柳二人之间的情而感动,为之泣泪。“惟其情真,而幻荡将何所不至矣”[1]73,只有情真,演员才能更好地揣摩角色的内心世界;只有情真,演员才能完全进入到角色的规定情境当中;只有情真,演员才能与角色合二为一。古代戏剧表演在舞台布景上不追求百分之百的情景还原,在这样半虚半实的舞台环境之下演员快速进入角色,便是考究演员功力的时候。潘之恒主张以情传情,同时更加主张演员在日常生活中的情感积累,在这样的基础上才能更好地进入角色,刻画角色。除了“以情传情”,潘之恒还强调了“以情传神”。他在《神合》中表示:“然神之所诣,亦有二途:以摹古者远,以写生者近情。”[1]47“以情传神”要以“以情传情”为基础,让角色达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形神兼备的表演境界。
“以情写情,以情传神”是潘之恒在表演情感方面的主要理论阐述,强调痴—解—传—神的情感表达,注重演员的内心体验与情感表达,对现在的表演艺术有着极大的借鉴意义。
3.潘之恒之演员综合素质论
何为一个好的演员是潘之恒表演理论的重中之重,也是他表演理论的重要核心。“人之以技自负者,其才、慧、致三者,每不可得兼”[1]42,潘之恒在《仙度》一文中阐述了演员的综合素质观,强调一个演员应该具备“才”“慧”“致”这三个因素。
何为“才”,旨在“赋质清婉,指距纤利,辞气请扬”[1]42,“才”为才华与良好的资质。潘之恒在《仙度》中指出,演员首先需要具备外在的“才”,良好的外形条件,气质清丽,仪态优美,让人赏心悦目,有一种愉悦的审美感受。其次是内在的“才”,有人强调内在的“才”应是天赋,但在本文中更加强调其为后天养成的才华。“才”应是演员需具有深厚的表演功底,同时还要具备深厚的文学修养。他曾赞赏演员顾筠卿,凡是看到古今辞曲,便随手唱来,展现了作为演员深厚的文学素养。演员除了需要保持一个良好的外形之外,更重要的是以“才”傍身,提高自身的素质,以深厚的文学素养作为自身创作的土壤,才是成为一名好演员的基础。
何为“慧”,“意为一目默记,一接神会,一隅旁通”[1]42,演员对角色具备良好的理解能力,擅长把握意图。通过对剧本中的细节、人物的语言去把握作者的创作意图,用心体会角色性情,表演时心领神会,并在此基础上能够举一反三,一隅旁通,从而清楚作品与角色深层次的主旨内涵。在“才”的积累基础上,演员提高自己对作品、人物的理解与领悟能力,善于积累日常的情感,从生活中汲取养分,快速地驾驭角色,化为人物,为自己在表演时扫除障碍,真正做到“一接神会”,在反复实践的过程中达到“一隅旁通”,成为“颖其慧者”。
何为“致”,“其致仙也”[1]42,“致”是演员有出色的表达能力和舞台上的控制能力。演员对舞台充满热爱之情,亦如“见猎而喜,将乘而荡”,在舞台上快速进入角色,“从容合节,不知所以然”,展现无拘无束、从容不迫的艺术美感。演员在表演时完美自然又富于真情实感,对自己的表演技巧有着高超的控制力,在实践中挥洒自如,生动传情,将自己所积累的情感喷涌而出,从而达到“形神合一”的艺术境界,故才能达到“其致仙也”的艺术追求。
可见,“才”“慧”“致”在潘之恒的理论中是不可分割的三个部分,“有才而无慧,其才不灵;有慧而无致,则慧不颖,颖之能离间,在古罕矣”[1]42。“才”是“慧”的基础,有“慧”才能感受到“才”的灵韵,若无“致”便何谈“慧”之聪颖。一名优秀的演员应该具备“才”“慧”“致”这三方面的因素,共同作用于表演之中,方能集大成者,达到“仙”的境界。
二、潘之恒观戏论
艺术的发展都有其独特的环境土壤,时代背景下的社会生产力、思想观念、文化传播等质素,都会影响艺术的创造与发展,而潘之恒对于戏剧表演艺术的深刻见解,同样是多种要素的综合性产物。明代中后期,随着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经济发展迅速,人们对娱乐的需求也与日俱增。戏剧创作脱离教化剧的创作模式,迎来了大量创作时期,达到了中国古代戏剧发展的又一高峰,涌现了一大批杰出的戏剧家,演剧活动空前繁盛,促进了许多家班和职业演员的发展,这为潘之恒探究戏剧表演艺术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刘勰在《文心雕龙》曾讲道:“人稟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2]20,可见潘之恒的人生经历与其戏剧表演理论息息相通。潘之恒成长于财富雄厚的徽商之家,徽商重儒近雅,祖父二辈文化艺术素养颇高,钟爱戏剧艺术,幼时就已跟随家人赏戏,在为演员金凤凰作小传时,曾回忆道:“余五岁时从里中汪太守筵上见之。”[1]145说明家族生活使潘之恒幼年时期就受到戏剧艺术的熏陶。
少年时,多次科举不第,遂放弃仕途之路,以此沉溺于诗歌创作和观戏活动。由于当时演剧活动日益兴盛,潘之恒又喜爱游历山川,踏遍各地观剧地点,结交众多好友,与戏剧作家和演员们的往来也日渐亲密,与李贽、汤显祖、张凤翼、臧懋循、梁辰鱼等戏剧家都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志同道合的好友对他的戏剧表演评论响答影随。特别是与李贽和汤显祖的交往,使潘之恒对戏剧中“情”的理论有了更深的理解,极大地丰富了其戏剧表演理论的发展。在明代中后期,传统思想领域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从理学到王阳明“心学”的嬗变,即从维护传统礼教到关注个体解放的思想变革,影响了戏剧创作领域,出现了晚明剧坛以“情”为主的戏剧创作和审美趋势,而李贽与汤显祖就是这场浪潮的先锋力量。李贽主张以“童心说”为文学创作标准,“童心”就是本真之心,要求文学作品真实地表达个人情感,又进一步提出“化工说”,指出在戏剧创作上也要体现真实自然之情,成为这场浪潮的开端。汤显祖结合李贽的观点,实践于“临川四梦”之中,把“情”当作人物角色的原动力,提高了“情”在戏剧创作中的重要意义。随后,潘之恒在两人的影响下,概括出戏剧创作的目的在于传“情”,而传“情”就不能忽略戏剧表演给观众带来的体验,因此,要重视演员对“情”的理解和塑造,最终概括出表演情感境界论。 在潘之恒的观剧活动中,与当时戏剧家班和演员的联系不可忽略,他经常受到家班的邀请参与观剧活动,又与班主探讨和指导演员表演,与演员们积极交流,因此在戏剧表演技巧方面积累大量经验。如较早创建的邹迪光家班,精通昆山腔的戏剧演出,演艺精巧,风格雅致,在江南一带极有声望,对其他家班的建立带来巨大的影响,他们两人经常就戏剧表演技巧相互交流。可见潘之恒参加邹迪光家班的演出活动,是对他个人戏剧表演见解的肯定,这样的家班演出活动也使他在昆山腔的表演问题上得到更多的收获。除了与家班演员有密切交往外,潘之恒在外游历时,还结识了许多演员。他曾在金陵多次设办曲宴,邀请文人墨客观剧饮酒,演出者是当时颇有名气的演员傅灵修、杨翩等人,为他撰写演员小传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总之,潘之恒自小深受家族尚曲风气的陶染,对戏剧情之惟系,各地游历,结交众多戏剧家、家班、演员等,参与这些丰富的观剧活动,逐渐培养了他在戏剧表演上新颖的观念。
三、结语
在我国古代戏剧史上,潘之恒的戏剧表演艺术理论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对中国古代戏剧表演艺术的贡献不容忽视,也为演员表演创作带来新的生机。
首先,在杂文著作《亘史》与《鸾啸小品》中保存了丰富的戏剧艺术表演史料,主要是对演员资料的记录。中国古代戏剧史上最早的演员称为“优”,是君王用以玩乐和讽谏的“弄臣”,地位和身份十分低微。尽管随着戏剧艺术的兴盛,演员们也无法摆脱社会阶级的差距,而潘之恒对演员资料的记载就显得弥足珍贵。他对演员的记录从嘉靖到万历年间,挑选演员的地域范围极广,南北方都有涉及,遍及苏州、浙江、安徽、山东等地,如金陵歌姬名妓杨美、蒋六和宇四,以及江南昆曲演员谷兰芳、苏州歌妓白姬等人。他不仅对个人的表演技巧作出细致的评价,对演员们报以深切的关怀,也重视演员的精神风貌和风格特征记录。如对昆曲演员王翠翘的记载,王翠翘身为烟花名妓,人生极为坎坷,历经两次婚姻,被俘之后,难以掌控自己的命运,最后跳海而亡,潘氏赞赏王翠翘的志向之“节”,遂认为“有节概可录”[1]177。
其次,促进了戏剧表演艺术理论的繁荣。潘之恒的表演理论立足于实践,从具体的实例出发,从一场场演出出发,细致并有条理地对演员的综合能力和素质进行了梳理、分析。他认为演员需要具备极佳的表演技巧,注重情感体验与情感表达,在“情”的基础上演绎人物,刻画人物,形成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他提出“情”与“境”的结合、“神”与“思”的融合,体现了中国文化独有的意境追求与审美境界。在潘之恒与好友交往中,彼此相互交流和影响,在戏剧表演艺术上都提出了创新性的见解,一同推动了明代戏剧表演艺术的发展。潘氏对汤显祖的《牡丹亭》赞赏有加,曾多次组织排演作品,而他们两人也多次讨论过剧本演出情况,许多观点不谋而合。汤显祖不仅关注场上之曲,也更关注演员的自身发展,这一点在他的专著《宜黄县戏神清源师庙记》中都有体现,他认为演员要专注于艺术表演,培养生活与艺术的融合,达到求真传神的意境。臧懋循是明代文学家,编有《元曲选》一书,与潘氏结识于金陵诗社,一起参与过曲宴活动,他在批评好友汤显祖的“临川四梦”时,提出“使闻者快心,而观者忘倦”[3]62的观点,从戏剧演出达到的最终效果来规范戏剧表演艺术的标准,旨在强调演员的重要性。以上反映了明代戏剧表演艺术的发展越来越重视对演员素质的培养,肯定了好的文本要在优秀的演员表演之下才能更好地展现其优秀的魅力,这也是以潘之恒为代表的戏剧理论家们推动的结果。
潘之恒的戏剧表演艺术理论推动了中国古代戏剧表演艺术的发展,其表演艺术主张的创新性,对明代戏剧表演艺术的发展起到了奠基作用,对后世戏剧表演艺术的实践起到了指导意义,对清代的表演、导演等方面产生了积极且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