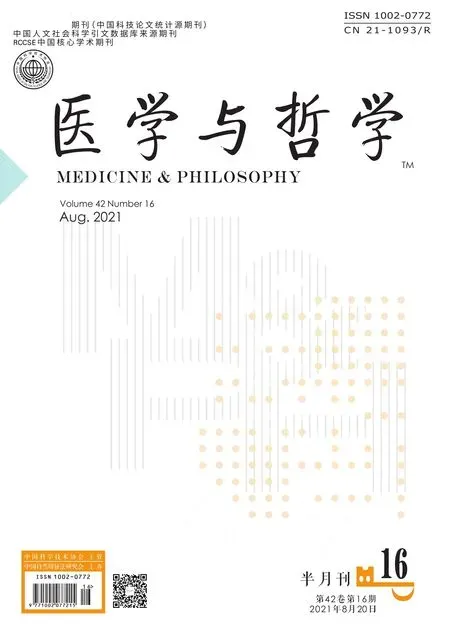安宁疗护服务对象准入标准的国际经验与中国实践*
2021-12-01路桂军王云岭
路桂军 姜 姗 李 忠 王云岭 周 宁
伴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快,慢性疾病和危及生命疾病的患病率正在增加,对安宁疗护服务供给提出了更多、更高的要求[1]。受限于当下居家照护服务供给的短缺,在生命末期,大多数患有终末期疾病,特别是晚期癌症的患者面对疼痛等临床症状,不得不向医疗机构寻求治疗[2-3]。不合理、高强度的临终治疗服务占据了大量的卫生资源,加重了医疗卫生服务系统的负担,众多家庭面临沉重的照护负担。这一现状亟需转变临终照护观念和服务模式,并对国内安宁疗护服务供给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近年来,安宁疗护试点正在全国范围内铺开,许多医疗机构开展了安宁疗护服务,让越来越多的患者从中受益[4-5]。然而,因相关法律法规和实践指南的缺乏,各地准入标准的不同,使得地区间安宁疗护服务供给和利用差异较大。本研究旨在系统梳理国际成熟体系服务对象准入标准,总结先行机构早期实践经验,探索建立符合我国情境的准入标准,促进安宁疗护服务提供流程的程序化和规范化,推动我国安宁疗护事业的发展。
1 安宁疗护的医疗实质及国内外准入标准
2017年2月,原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印发的《安宁疗护中心基本标准和管理规范(试行)》中指出,安宁疗护是为疾病终末期患者在临终前通过控制痛苦和不适症状,提供身体、心理、精神等方面的照护和人文关怀等服务,以提高生命质量,帮助患者舒适、安详、有尊严离世[6]。根据安宁疗护的医疗特征和服务范围可知,安宁疗护服务的本质是对终末期患者的关心照护和帮助支持,旨在减轻患者临终阶段的生理和心理痛苦,提高生命质量。在美国,安宁疗护服务包括以症状缓解、身体护理、医务社工服务为主的核心服务和以物理疗法、职业疗法和言语治疗服务为主的非核心服务两个部分[7]。我国安宁疗护实践中未作此区分。在临床实践中,安宁疗护应用减轻痛苦和不增加痛苦的医疗技术方法,通过对症治疗减轻患者症状负担,不进行以治愈为目标的高风险操作和手术,因此不具备常规医疗手段的侵害性、结局明确可期待、存在不良后果风险等特征。
1.1 国外安宁疗护准入标准
患者进入安宁疗护的标准主要包括预期寿命和特定疾病两个方面。根据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关于安宁疗护准入标准的建议,安宁疗护应该在需要时开始,可持续数天、数月或数年,主要针对的是预期生命不足12个月的患者,包括以下几种情况:(1)患有晚期不可治愈的疾病,如癌症、痴呆或运动神经元疾病;(2)预计将在12个月内死亡的失能患者;(3)原有疾病情况突变引起的死亡风险;(4)因突发灾难性事件(如事故或中风)而导致危及生命的急性病症[8]。
美国Medicare安宁疗护服务要求患者在开始安宁疗护后放弃治愈性治疗的报销,其准入标准包括以下两点:(1)患者放弃原发疾病治愈性治疗;(2)两名专科医师诊断终末期疾病,若按疾病自然进程患者预期寿命6个月或更短[9-10]。关于终末期的诊断,医生应考虑以下几点:(1)主要的终末期条件;(2)相关诊断;(3)目前的主观和客观医学发现;(4)目前的药物和治疗顺序;(5)与终末期疾病无关的病症管理信息[11]。此外,当治愈性治疗不再有益,治疗负担超过受益时,患者也适合进入安宁疗护[12]。
在加拿大,几乎所有安宁疗护医院的准入标准都基于患者的预期生存时间,范围在4周到6个月不等,大部分安宁疗护医院都要求患者的预期寿命为3个月甚至更短,以及要有终末期诊断和医生的转诊[13]。日本安宁疗护服务对患者预期寿命和疾病类型没有限制,所有患者都有资格接受居家安宁疗护,但只有晚期艾滋病和晚期癌症患者才可以接受住院安宁疗护。
1.2 我国台湾地区安宁疗护准入标准
我国台湾地区健康保障体系涵盖的安宁疗护服务对象包括以下几种:癌症晚期(约占90%)、终末运动神经元病、老年和早期器质性神经疾病、终末期脑部病变、急性肾功能衰竭、肺衰竭、慢性肝病或肝硬化、心脏衰竭、慢性肾功能衰竭[14]。2015年12月,我国台湾地区通过了亚洲第一部专门保护患者自主权的“患者自主权法”,规定年龄在20岁及以上且具有完全行为能力的任何人(患者或医疗代理人)都享有医疗知情权、选择权,通过预先医疗计划和预先指示,当患者符合五种临床状况之一时,可以选择接受或拒绝治疗,五种临床状况分别是:(1)身患终末期疾病;(2)处于不可逆昏迷状态;(3)处于永久性植物状态;(4)患有严重痴呆症;(5)其他疾病或痛苦难以忍受,疾病无法治愈,且没有其他合适的治疗选择[15]。我国台湾地区安宁疗护服务对象准入没有生存期的限制,符合条件的患者都有资格接受服务。
以上这些国内外经验表明,安宁疗护服务人群主要是晚期癌症患者,近年来开始关注到疾病终末期的非癌症患者,如心血管疾病、慢性阻塞性肺病、肾功能衰竭、肝硬化、阿尔茨海默症和其他痴呆症、多发性硬化症、帕金森病、艾滋病、类风湿性关节炎、糖尿病等[16]。
2 安宁疗护服务的中国经验和准入标准建议
自2013年起,笔者所在团队在临床实践中,通过对关键概念的梳理[4-5],以及与多方专家咨询和讨论,不断优化和完善服务对象的准入标准,构建了“以患方需求为导向、以关爱帮助为核心”的安宁疗护准入标准体系。科室服务对象数量逐年增长并趋于稳定,2013年收治患者1例,2019年收治患者175例,包括居家服务对象。收治病种范围从终末期肿瘤患者逐步扩大到高龄衰竭状态、晚期心力衰竭、晚期运动神经元疾病等其他终末期疾病患者。截至2021年4月,累计为700余位临终患者提供了以对症治疗为主,其他照护为辅的整合型安宁疗护服务,显著减轻患者痛苦及其亲属的照护负担,达到了患者满意度高、医护人员成就感高的综合效果。
笔者建议在患方接受安宁疗护理念、明确表达拒绝继续疾病治愈性诊疗的前提下,经医疗机构判定患者处于疾病终末期,结合考虑当时疾病状态的中位生存期不足6个月,至少合并下列一条标准,方可进入安宁疗护:(1)疾病终末期,有不适症状;(2)肿瘤晚期,患方拒绝继续肿瘤治愈性治疗,且有不适症状;(3)严重疾病,患方继续治愈性诊疗的风险和痛苦明显大于受益,不能承受并明确表示拒绝治愈性诊疗;(4)身体功能障碍、高龄衰竭老人等,脏器功能严重障碍且无法通过治疗改善,生活质量低下处于痛苦状态,身体状况处于衰竭进程,患方拒绝继续常规医疗诊治流程,寻求减轻痛苦的医疗帮助。
需要强调的是,上述标准中“当时疾病状态的中位生存期不足6个月”可解释为在当时疾病状态下,此类患者的预期生存期不足6个月,而非对该个体生存期的预判,因此不作为严格限定条件。上述标准中患方是指:(1)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患者本人及其授权委托人;(2)未成年人、意识不清者、精神病患者等不能判断自身病情状况和无法清楚表达意愿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法定监护人及法定代理人。同时,如果患者进入安宁疗护一段时间后,经安宁疗护医生和专科医生判断,其病情好转,能够继续疾病治愈性治疗,或者患方意愿改变,患者可以随时从安宁疗护阶段转出,进入专科疾病常规诊疗。
3 医患双方在安宁疗护准入中的角色定位
3.1 患方在安宁疗护准入中的角色定位
每个人都有一直追求医疗抢救,直到抢救无效的权利,因此任何疾病状态判断的指标都不能用来判定某个患者是否应该放弃医疗求生或放弃疾病治疗,只有患方可以表示放弃或拒绝疾病治愈性诊疗或抢救。进入安宁疗护的前提是必须由患方自主提出安宁疗护要求,即患方享有安宁疗护的自主决定权,专科医生可以就患者病情状态与患方沟通,告知其除继续治愈性治疗之外还有安宁疗护这一医疗选择,但安宁疗护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不能主动诱导患方接受安宁疗护,更不可替代患方做出医疗决策。
3.2 医方在安宁疗护准入中的角色定位
安宁疗护服务对象是有症状缓解需求的临终患者,建议标准中提到的医疗帮助即为减轻痛苦的安宁疗护医疗帮助,并非针对疾病治愈性治疗的常规诊疗过程。
关于疾病分期、病情严重程度及进展预后状况、预期生存期等情况,应以非从事安宁疗护的专科医生判定为准。如此可避免患者的专科疾病主诊医生同时也是患者安宁疗护医生的弊端,防止医生在患者病情和医疗方式选择上出现误判和道德风险,预先“利益规避”,以防止“利益驱动”,即规避既是“裁判员”也是“运动员”的风险。因专科医疗资质和诊疗能力的缺乏,安宁疗护机构的医务人员并不适合进行专科疾病的诊断。此外,有关疾病症状、痛苦程度、风险受益等应依据患方的主观判断,不可限制患方的自主权。
4 本土化安宁疗护准入标准构建的价值探讨
4.1 无预期寿命限制,顺应文化情境
与英美等国的安宁疗护准入标准相比较,笔者建议的标准并未对患者的预计生存期做出限定。从临床诊疗实际来说,任何医生都无法对患者的死亡时间做出准确预估。以美国的安宁疗护实践为例,虽然美国将符合安宁疗护资格的患者预期寿命限定在6个月以内,但研究表明,在超过25年的Medicare安宁疗护服务中,安宁疗护的中位停留时间在20天~22天,一半以上接受安宁疗护的患者服务时间少于21.1天[17]。由此看来,以患者生存期作为严格限定条件,除了便于医疗保险管理,在服务提供层面并无实际意义。从国内文化背景和医疗环境角度出发,若明确规定安宁疗护准入需满足预计生存期的条件,而患者实际生存期短于预期,易引起家属不满情绪,甚至激化医患矛盾。若患者实际生存期长于预期,将有可能加剧现阶段安宁疗护供需矛盾,增加安宁疗护相关医保负担。本标准没有特别强调临终时间的概念,更容易被国内大众接受,能够适应现阶段乐生恶死的死亡文化和伦理环境,有利于安宁疗护的宣传和推广,进一步提高安宁疗护接受度,优化医疗资源利用,帮助更多有需要的患者和家庭从安宁疗护中获益。
4.2 以患方意愿为标准,更具可操作性
将患方意愿作为主要判断标准,明确安宁疗护以症状控制为主,不进行原发疾病的诊断和治疗,一方面便于医务人员在临床实践中界定服务范围;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家属明确医疗目标,避免信息偏差和不必要的医患矛盾。此外,本标准以医疗机构非从事安宁疗护的专科医生的诊断为依据,不强制使用姑息行为功能评分量表(palliative performance scale)等患者功能状态评价量表,有助于医生从专业的角度进行诊断,避免受到量表评价不确定性的干扰,简化准入流程,实践中更具可操作性。
此标准明确将“是否进行原发疾病的诊疗”作为常规医疗与安宁疗护的分界线,可以使医方和患方明确安宁疗护的进入与退出时机,帮助患者及时获得合适的医疗照护,打消患方顾虑。换言之,当患者身体功能衰退、症状负担较重且自愿进入安宁疗护时,可及时获得对症治疗和心理疏导等服务;而在患者身体状况改善时,可重新考虑是否退出安宁疗护,继续病因治疗。这也有利于大众正确理解安宁疗护的实质和意义,即死亡不是安宁疗护的必然结果,而是在走向死亡的过程中给予帮助支持,使死亡过程更加平稳舒适、有尊严。
4.3 保障患方利益最大化,实现全生命周期照护
临床实践中,患方若由于各种因素(疾病痛苦、医疗风险、经济条件、生活质量、生活习俗、价值观等)拒绝继续病因诊治,则可能面临两种结局:(1)寻求减轻痛苦、改善症状的对症治疗;(2)放弃医疗,承受疾病痛苦。若患方主动寻求对症治疗,医方也将面临两种诊疗方案选择:(1)接受患方要求,提供减轻痛苦的治疗,即安宁疗护;(2)以不符合收治条件为由,拒绝患方要求,使得患方减轻痛苦的期望落空,失去医疗照顾,从而陷入更加痛苦的境地,这明显违背医学人道主义精神。因此,该准入标准的构建立足于医疗本质,旨在减轻临终患者痛苦,给予患者家庭更多帮助;同时,有助于医务人员开展安宁疗护实践,保障各年龄段、各疾病人群安宁疗护权利,实现全生命周期的照护。
5 结语
自安宁疗护服务开展以来,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空军医院疼痛科不断以该标准界定服务对象,累计为700余位临终患者及其家庭提供医疗、心理和社会等方面的帮助,收到了非常满意的成效。以患方需求为导向、以法律规范为准则、以关爱帮助为核心的安宁疗护准入标准体系的构建,可推进患者家庭的和谐,增进医务人员的成就感,有助于提升社会大众福祉。
在安宁疗护不断试点和推广的背景下,本研究首先介绍了典型国家和我国台湾地区的成熟经验。此外,基于临床实践和专家讨论,本研究首次系统地介绍了安宁疗护服务对象的准入标准,强调了患方意愿的重要性;该标准充分尊重了患方的自主权,有利于医患双方的充分沟通、提高医护人员的执业规范、保护医护人员的正当利益。同时,该标准顺应了我国传统文化,不强调死亡的预期终点,其体现的医学人文关怀精神有利于促进安宁疗护的推广和应用;医学人文精神关怀的体现也有利于促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体系的完善。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与国际经验相比,当前我国对于安宁疗护的法律规范基本处于空白,该标准是在充分的医患沟通基础之上实施的,实际运用过程中,相应的政策法规和规章制度有待于多方共同参与,进一步探索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