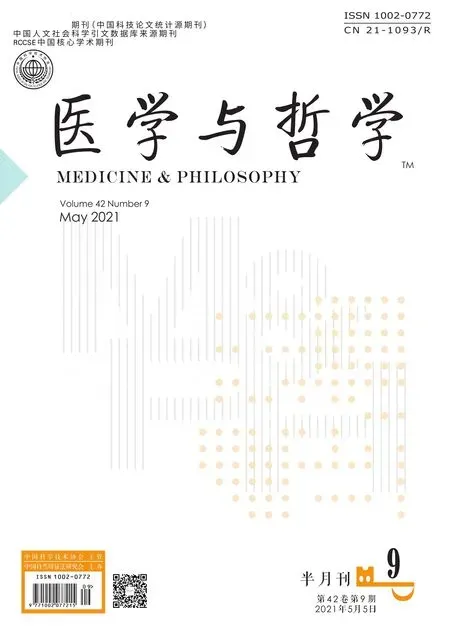关注、凝视和忽视:抗击新冠疫情中女护士处境的人文反思
2021-12-01闫飞飞
闫飞飞
2019年12月,新冠疫情的暴发及其在全球的蔓延,全方位地改变着人类社会发展的未来走向。从宏观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到微观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公民对国家的观念,到全社会对医护人员的感知,无不深刻地受到此次疫情的影响。在抗疫过程中,医护人员发挥的作用得到了国家和社会各界的高度称赞与认可。其中女性医护人员发挥的作用更是举世瞩目,俄罗斯塔斯社2020年3月7日刊登题为《“白衣天使”——中国女性以忘我精神抗击疫情》的报道,突出赞扬了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斗争中中国女性医护人员的贡献。根据《中国妇女报》2020年2月19日的报道,奋战在一线的医生中有50%以上为女性,其中一线女护士更超过了90%[1]。护士这一职业在抗击疫情中发挥的作用得到了全社会各界的关注、肯定和盛赞。美中不足的是,在媒体和社会对女性医护人员报道与关注的同时,公共舆论中依然存在着基于不平等的性别关系而对女性护士身体的凝视和支配,以及对女性护士的职业身份和正当权利的忽视。希望全社会和公共舆论能够正视这些问题,使为抗击新冠疫情作出重大贡献的女性护士群体能够得到更加真切的关爱和尊重。
1 关注:对护士处境的全方位关怀及其衍生意义
1.1 社会各界对女性护士的全方位关注
每逢突发的、带来巨大社会恐慌的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医护人员的作用就会被集聚性地凸显出来,社会各界在此种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暴发期间对医护人员的关注都会呈现出积极的评价。以2003年非典暴发以来护士地位的变化为例,根据中山大学护理学院2004年的一项研究指出,“非典流行后护士与社会人士都认为护士社会地位较以往有明显提高,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其中,护士自我评价非典流行前自身地位在中等以上的占32.98%,非典流行后为63.57%;社会人士认为,护士社会地位非典流行前在中等以上的占76.58%,非典流行后为90.66%”[2]。同样的,在本次抗击新冠疫情的过程中,医护人员,特别是女性护士群体也得到了国际和国内社会各界全方位的关注和赞誉。习近平总书记在2020年护士节前夕发表重要讲话指出:“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广大护士义无反顾、逆行出征,白衣执甲、不负重托,英勇无畏冲向国内国外疫情防控斗争第一线,为打赢中国疫情防控阻击战、保障各国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作出重要贡献,用实际行动践行了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崇高精神。”[3]
从社会各界和媒体的关注视角来看,女医护人员剪短长发甚至剃光头出征抗疫,女医护人员在医院忙碌的身影,女医护人员因劳累席地休息的形象,诸多女医护人员去掉防护服后满脸勒痕的照片,再到社会各界对抗疫女医护人员生理期卫生巾短缺的关注,护士的身体和形象在疫情报道和传播中得到了全方位的关注。媒体报道中对女护士疲惫的身体的报道,正是通过借助于女护士“受苦的肉身”的视觉呈现方式极大地激起了社会公众的同理心,这对于激发全社会抗疫热情有着极大的渲染力。
1.2 社会各界对女性护士关注的衍生意义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此次疫情中由于对前线女医护人员卫生巾短缺的关注,藉由以女护士为主的女医护人员的身体,打破了社会舆论中隐秘的月经禁忌,使之再次公开地进入人们关注的视野。在中国传统的文化和民俗中,月经被认为是污秽且神圣的禁忌,中国学术界对月经进行开创性研究的民俗学家江绍原指出,中国传统文化对月经的认识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天癸(月经,引者注)是一种污秽之物,与疾病、生产、性交及死尸类似;第二,天癸具有使鬼魅和邪术家都畏惧的污秽力量;第三,经血与经衣能解毒治病,如两性病、急病、受毒等;第四,天癸(特别是第一次的天癸)被视为人身的一种精华,与乳汁、大小便等相同,可与其他‘人元’及天地精华合制成丸散丹膏(红铅)而服用,小到壮阳补血,大至益寿延年。”[4]虽然,现代中国社会文化中很少再有这种对月经的污秽且神圣的迷信认知,但是,月经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是社会中的语言禁忌,依然是难以公开言说的或不可言说的对象,是需要使用一些避讳语(如来事、来身上、大姨妈等词)来象征和指代的。作为语言禁忌的月经,使得正常生理期的女性身体成为男性主导下的社会中的一个被遮蔽和忽视的“存在着的无”。社会习俗中存在着这种有关月经禁忌的不可言说性,使得月经和卫生巾等女性生理用品很难进入社会关注的公众话题,更难成为公共政策关注的政策议题。
在此次抗击新冠肺炎的初期,社会各界对抗疫物资的捐赠主要集中在防护服、护目镜、口罩等用品。随着疫情的进展,各种自媒体报道出以女护士为主的一线女性医护人员卫生用品的短缺困境,特别是2020年2月14日《人民日报》官方微博发布的一条“妇联支援一线女医务人员卫生用品”登上热搜,抗疫一线女性医务人员生理期卫生用品的短缺迅速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央广网、中国共产党网、中国妇女报·中国妇女网、中国青年网等各大官方媒体以及各种自媒体纷纷集中关注抗疫一线女性医护人员的生理期卫生用品,社会各界纷纷向一线女医护人员捐赠生理期卫生用品。此次疫情中,藉由以女护士为主的一线女性医护人员的身体所遭遇的困境,出现的这种“捐赠卫生巾运动”,使得月经和卫生巾成为全社会集中关注的公共议题。借着抗疫中对一线女医护人员卫生巾关注的势头,2020年8月底,“卫生巾贫困”再次登上热搜,成为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公共话题。《新京报》2020年12月21日发表《追问2020:普通女性被看见的一年》中指出:“关于‘散装卫生巾’的讨论,则将长期被忽视的‘月经贫困’问题抛到了大众眼前。”[5]可以说,2020年月经和卫生巾的再次“被发现”正是藉由全社会对以女护士为主的抗疫一线女性医护人员的关注而产生的衍生意义。社会舆论开始打破月经禁忌,使之成为可以公开言说的社会议题。正如苏珊·桑塔格[6]在《疾病的隐喻》一书中指出:“疾病并非隐喻,而看待疾病最真诚的方式——同时也是患者对待疾病的最健康的方式——是尽可能消除或抵制隐喻性思考。”同样的,我们也可以说,月经并非禁忌,看待月经最真诚和最健康的方式是尽可能消除或抵制月经禁忌。正确看待生理期女性身体的起点,首先是要消除和抵制这种语言禁忌;社会对女护士的关注,也应该首先从关注女护士的身体和生理周期开始。
2 凝视:对护士性别的物化呈现
在本次抗疫的过程中,护士群体在受到社会全方位关注的同时,也存在着对女护士身体的不正当的对待。其中最受关注和批评的是甘肃日报社主办的全国重点新闻网站、甘肃第一网络媒体“每日甘肃网”官方微博发布的一段甘肃省妇幼保健院15名援鄂护士启程前集体剃光头的视频,此视频一出,立刻引起网络舆论的巨大质疑。质疑主要集中在“为什么非得剪光头?”“是不是强迫?”“是不是形式主义?”[7]我们在这里要集中反思的则是官媒为何要推出这段视频,其背后隐藏的逻辑是什么。
2.1 对女性身体的凝视和支配
“在启蒙运动所奠定的现代性视野中,‘身体’已经获得了其自由主义的哲学基础。从尼采、齐美尔到柏格森,人的本质不再是抽象的形式原则和理性逻各斯,而被充满感受力的肉欲身体所取代。”[8]身体摆脱了抽象原则的束缚,成为彰显人的主体性的一个本质符号,人的身体也成为自我私人领域的最后堡垒。但是,正如女性主义所指出的启蒙运动对人的定位存在着男性父权的意味。现实中身体的呈现并不是启蒙运动思想家所设想的那样平等,相反,在现实中它表现出性别不平等的态势和社会印记。身体确实是私人领域的最后堡垒,但身体一旦跨出自己的私人领域进入公共领域,就会发生扭曲和变形。“我的身体在公共领域是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构成的,它既是我的又不是我的,身体从一开始就被给予了他人,打上了他们的印记,并在社会生活的严峻考验中得以形成。”[9]尤其是女性的身体,在男性主导的社会文化中,女性躯体总是作为景观而存在的,它总是“作为男性凝视(gaze)的对象呈现出来”[10]。根据福柯对凝视的解读,“凝视作为一种观看方式,是凝视动作的实施主体施加于承受客体的一种作用力。在现代社会, 凝视是有形的、具体的和遍在的,凝视象征着一种权力关系, 它是一种软暴力”[11]。在凝视中,凝视主体是强势的、处于支配地位的,被凝视者则沦为凝视主体的客体而存在,被凝视者是弱势的、处于被支配地位的。作为凝视关系中的被沦为客体的被凝视者的身体已经丧失了主体的地位,而处于被定义、被塑造、被安排的地位。
2.2 不平等的权力关系下对女性的物化
在男性的凝视下,进入公共领域的女性身体更容易丧失主体性,女性很难成为主导自己身体的主人,女性身体更容易成为被物化的对象。在公共领域中,对女性物化的一个主要体现是:“在新闻题材涉及到女性时,不是以所报道女性的能力、才华、专业形象等作为报道的关注焦点,而总是过度关注其身材、样貌等物质性信息。”[12]对女性的物化使女性的身体呈现为被看、被用的客体而被重新安排和规划。在男性主导的公共文化中,女性一贯被定位为母亲、弱者,而当女性的身体在遭遇到重大公共危机的时刻,被凝视的女性身体更有可能成为公共舆论的焦点。在重大危机面前,女性只有剔除掉母性和弱者的形象,成为男性,甚至成为比男性更男性的男性形象,似乎才有资格成为对抗重大危机的主体。在不平等的性别权力关系中,女性已经处于弱势的位置,而当不平等的性别权力关系被裹挟进公共舆论之后,作为弱者的女性身体更是处于双重且加倍的被支配和被利用的处境。
2.3 对女性护士身体的凝视和物化
重新回到被官方媒体宣传的被集体剃发的15名护士的视频上:被剃光头的是女护士,他们不是医生,更不是男医生。在当前的医护关系中,护士相对于医生来讲,仅仅是以医生助手的形象被认知,相对于医生来讲,护士更是处于扮演着默默无闻的服务者、服从者和弱者的地位。作为弱者的女护士,在面对此次新冠肺炎这一罕见的重大公共卫生危机中,按照传统的新闻宣传惯例,只有弱者不顾一切地挺身而出,似乎才更能体现面对灾难所亟需的英雄主义和悲情主义。在这种情境和逻辑的支配下,不平等的性别权力关系被掩盖。相较于男性医护人员,参与抗击疫情的女护士需要付出或展示更多的牺牲才能够激起社会的赞誉和同情,在此种逻辑下,女护士只有通过付出或展示一部分身体(剃光头的护士、怀孕的护士、生理期无法更换卫生巾的护士等)才能够证明自己奉献精神的圆满。在社会舆论中,“凝视之眼”聚焦的是女护士疲惫的身体,她们只能凭借疲惫的身体的展示赢得同情性赞誉,社会需要利用女护士的身体来激发起对抗击疫情的共识和团结一心。可以发现一个明显的对比:女护士因身体的展示赢得的是“同情性的赞誉”,医生则因着自己对新冠病毒的医治赢得社会对其专业水平的尊重,很显然,对女护士的“同情性赞誉”正是对其专业水平的忽视甚至轻视。
3 忽视:护士专业身份和地位的失语状态
通过上文的分析,可以发现无论是对女护士的关注还是凝视都集中在女性护士的身体,前者主要通过展示女护士辛劳疲惫的身体来突出护士的奉献精神,后者则主要通过利用女护士的身体(或护士身体的一部分),以煽情的方式激发悲情主义的目的。对女护士的关注和凝视,有一个共同之处:对女护士专业身份的忽视以及与之相关的对女护士的福利待遇和地位的忽视。
3.1 公众舆论中护士的“仆人”形象
护士虽然一直被人们称为白衣天使,但是近些年来公众和社会舆论对护士形象的认知以及护士的职业声望则呈现出下降的趋势。马冬玲[13]以1949 年以来《人民日报》对护士形象的相关报道为文本进行分析发现,在不同时期《人民日报》对护士形象的报道呈现出知识分子形象、劳动者形象、“仆人”形象和性别形象等多元化形象。但是,“不同时期对护士形象的再现也有差异,在市场化不断深入的过程中,护士的职业形象掺杂了从知识分子、普通劳动者到‘仆人’的等级化的形象,而对护士作为知识分子形象的再现日益让位于对护士作为女性形象的再现”。护士从知识分子形象一降而成为女性和“仆人”的形象,公众舆论对护士女性形象的认知,其实是将男性所刻画的女性的外表、温柔、顺服等形象强加到护士身上;同时,公众舆论将护士认知为“仆人”的形象,则是以主人的心态将护士看成毫无怨言、任劳任怨、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仆人”。总之,公众舆论中的护士形象应该是形象好且任劳任怨的“仆人”,护士似乎成了任何女性稍作训练都可以承担的职业,护士职业的专业水准受到了最大程度的忽视和轻视。在此次新冠疫情中,媒体和公共舆论对护士的关注依然主要聚焦于护士舍小家为大家的无私奉献,聚焦于护士身体的“劳累”“辛苦”等,这种传统的宣传模式其实依然是强化着护士的“仆人”形象,而对护士的专业身份多有忽视。
3.2 护士群体对自身形象的期望
相较于公众舆论对护士形象的定位,护士群体对自身形象有何种期望呢?孙妍等[14]在对511名护士对自身形象期望的研究中发现,最被社会公众感知认可的护士的“天使形象”,却是护士自身期望值最低的形象。护士群体对自身形象期望值最高的则是事业家形象,这说明护士“在实际工作中对职业的知识内涵、受尊重程度、职业的发展方向最重视,渴望自己未来的形象是一个护理专家形象”。可以发现,公众舆论对护士形象的认知和护士群体对自身形象的期望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与护士对自我形象的期望相比,是护士对自身工作现状的感知,据2017年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护联网等机构联合发布的《中国护士群体发展现状调查报告》显示,“80.7%的护士在工作中最看重‘获得尊重’。92.0%的护士认为‘护士工作的社会地位太低’。83.3%的护士不能明显感受到患者对护士的尊重,90.0%的护士不能明显感受到社会大众对护士的尊重”[15]。这一数据显示,绝大多数的护士在工作中体验不到职业尊严,无法获得职业满足感。
3.3 警惕公众舆论对护士职业的道德绑架
我们应该反思的是为何公众舆论对护士形象的认知与护士群体对自身职业的感知和期望会呈现出如此大的差距。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官方媒体、自媒体、医护类行业媒体总是会高调宣扬任劳任怨、无私奉献、放弃家庭和子女、服务无微不至、主动要求加班等具备诸种高尚美德的护士形象,这种高调的道德宣传甚至使护士自觉不自觉地在自我工作总结中自我美化,不具备这些高尚美德似乎就不是一个合格的护士。此种宣传势必塑造和强化了公众与患者对护士“完美的仆人”形象的期待,一旦患者和公众面对现实中不完美的护士就极容易产生失望,进而产生各种摩擦和纷争。事实上,上述诸种有关“完美护士”的道德宣传,其实是超出护士职业道德的要求,是对护士职业伦理的漠视。
媒体上的“完美护士”的宣传与护士的基本职业道德,其实是两种不同的道德要求。按照富勒[16]的区分,前者应该是属于“愿望的道德”,而后者则属于“义务的道德”,所谓“愿望的道德”是“善的生活的道德、卓越的道德以及充分实现人之力量的道德”,“愿望的道德是人类所能达致的最高境界作为出发点”;而“义务的道德则是从最低点出发。它确立了使有序社会成为可能或者使有序社会得以达致其特定目标的那些基本规则……它不会因人们没有抓住充分实现其潜能的机会而责备他们。相反,它会因为人们未能遵从社会生活的基本要求而责备他们”。媒体单一性的、刻板化的对“完美护士”的宣传,其实是模糊了“愿望的道德”和“义务的道德”的界限,前者属于美德,后者才是义务。美德不在权利-义务的范畴,护士做到了固然值得赞扬,如果做不到,相对人(患者或公众)也没有权利提出要求。义务才是必须履行的,相对人(患者或公众)有权利要求护士必须履行,同时,义务主体也是权利主体,如果相对人(患者或公众)提出了义务范围之外的要求,作为权利主体的护士也有权利拒绝履行。从这一角度来思考,我们应该重新反思此次抗击新冠疫情中对护士的宣传和赞美,提防对抗疫中护士的高调赞美成为漠视护士日常工作中基本权利的道德绑架。
3.4 疫情之后女性护士地位的不确定性
女护士群体在抗击新冠疫情中发挥的作用得到了社会舆论的极大关注和赞誉。随着疫情在我国基本得到控制,人们(特别是护士群体)开始关心:疫情过后,护士群体的地位和形象会得到实质性的改变吗?每逢重大自然灾难和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期间和危机过后的“非常时刻”内,社会公众对护士群体的评价在短期内都有明显的改善。正如前文所述,非典刚刚过去的2004年的一项调查中显示,在非典流行后护士与社会人士都认为护士社会地位较以往有明显提高。但是,对护士群体的积极认知和评价能够在“平常时刻”持续保持吗?以抗击非典之后医护人员的社会地位为例,2013年为纪念抗击非典十周年,钟南山院士在接受《南方日报》的采访中指出,在非典暴发十年后,“公众、政府部门以至媒体对医务界的一些偏见没有改变,我觉得这是个很大的遗憾。不能非典一走,汶川地震一过去,医生就从‘白衣天使’变成‘白衣狼’”[17]。很显然,在2003年抗击非典的过程中,护士地位仅仅在短期的“非常时刻”得到了急剧的提升,但是,一旦非典过后重新回归到“平常时刻”,护士群体的地位又重新跌落回公共舆论的偏见之中。同样值得关注和追问的是,此次新冠疫情过后,护士群体的地位是否会再次出现急升急降的情况呢?令人遗憾的是,女护士地位的保障依然存在着诸多不确定性,新冠疫情暴发至今,媒体已经报道出多起暴力殴打女护士的新闻。疫情之后,针对护士群体有关自身地位和权益的担忧,公众、政府部门、媒体以及医疗系统内部应该合力塑造健康的舆论环境,制定实质性的政策保障护士的地位和权益,不能让护士群体再次在日常的工作和生活中继续受到忽视。
4 结语
在此次抗击新冠肺炎的过程中,参与抗疫的护士群体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社会舆论对参与抗疫的护士都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和赞扬。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媒体和公众舆论延续传统的宣传模式和思维模式在对护士进行全方位报道和关注的同时,那只对女性护士身体的“凝视之眼”仍然在不断地闪烁,在性别不平等和公共舆论的裹挟和支配下,女性护士成为被物化的客体,女性护士只能通过展示其受损害的身体、像男人一样的身体,才能激起“同情性的赞誉”。在女护士身体的高度关注和凝视的背后,隐藏着对女护士专业身份和地位的忽视,以及对女护士正当权利的漠视。对女护士的关注、凝视和忽视是相互渗透的:对护士的关注和道德赞扬,总是伴随着对女护士的物化性凝视;在凝视之眼下对护士工作高度的道德关注,其实潜藏着漠视女护士职业身份,甚至抹杀女护士基本权利的道德暴力和精神强制,我们应该警惕对“完美女护士”的高调道德赞美蜕变为现实中对女护士的道德绑架,并加强对女护士专业身份的宣传和人文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