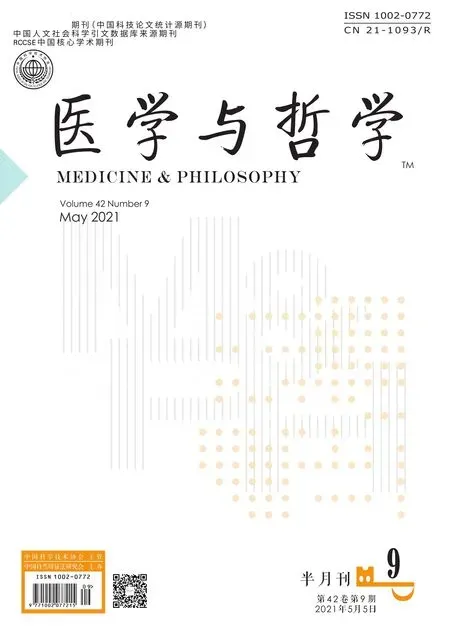近代中国传染病书籍的出版与传播*
2021-12-01贾登红
贾登红
近代中国传染病知识的生成、普及与印刷书籍的出版和传播是密不可分的。一方面,“传染病害人最速,病原亦最多。我医界宜竭力提倡,以引起人民普通之新智识”[1],医学界及出版商、书商等通过对传染病知识的转译、整理与出版,提高了近代中国传染病知识的“能见度”,推动了民间传染病知识的更新;另一方面,借助于书籍发行所形成的销售网络与“读者—文本”之间的互动,此类书籍如同书籍史家所比喻的“书籍酵素”“思想的工具”“心态装备”一般,影响与改变了近代中国及民众对传染病的认知,推动了国民防疫知识的近代化。相关方面代表作有张仲民《出版与文化政治:晚清的“卫生”书籍研究》[2]、董思思《从赤脚医生到仪式专家:传统知识在乡村社会中的延续——一项阅读史的研究》[3]等,他们从书籍史或阅读史的视角切入,或多或少地谈及与梳理了近代卫生知识与医学书籍的出版、传播及阅读等情况。基于此,我们若将“书籍和印刷文字作为一种历史力量的研究”[4],通过对民国时期涉及传染病知识的书籍梳理与回顾,便可大略认知近代中国传染病知识的生成与流布形状,以及印刷书籍对中国卫生政策制定及其走向近代化过程中所施加的影响。
1 作为资本的文化:强国卫民话语下的传染病知识
作为一种专业性知识,近代中国对传染病的认知经历了“先鬼神而后医药”,渐识预防和趋避的一个过程。我国“古无传染病之说,皆以为瘴气,皆以为天行,又皆以为鬼神之祟。故当一种时疫盛行之候,必有符咒祈禳迎神打醮之事”[5]序。“泰西古代医学家,也以为传染病是上帝降下的一种处罚恶人的方法,或系厉鬼作恶的缘故。”[6]一旦发生疫情,民众首先想到的就是去敬拜上香,如他们会用白色的石灰将自己的建筑物围绕起来,并用亮红色的布料缠绕在他们的烟囱和门口,祈求可以恐吓瘟疫,让其不敢靠近自己。“只有当疫情控制不住时,他们才会选择通知当地的政府官员。”[7]清末民初之际,面对西医知识的传入,绝大多数民众还存在恐惧西医等现象,“胼手眡足之民,不知卫生为何事,有终身沉浸于污秽中而不觉查者,一切食息、起居、衣服、器皿无不在足以致疫”[8]231。
其中,对民众体魄影响最大的又以传染病为害最巨,医学人士叶法维就曾痛心地讲道:“传染病患为害惨烈,当其肆虐,死亡枕藉,动摇国族命脉无与伦比。根据各地卫生机关历年报告,因传染病致死者竟占所有病例百分之七十二……现今欧美文明先进各国已能实施防疫,控制其传播,惟我国卫生教育落后,医疗设施简陋,每逢时疫流行,辙遭东西滋蔓,是以繁华城市因之而沉寂,强劲军旅坐此而覆亡,草木含悲,风云有恨,惨矣!”[9]初版自序
当时有识之士纷纷提倡“购买传染病图书,以及传染病虫(如蝇),供人观览”[10],认为要国家强盛,“必先要保持国民身体的健康;要我们的国民的身体健康,必先要预防病害的侵袭;要避免病害的侵袭,必先要知道病害的本性、来源和它们侵袭的途径,并且要知道扑灭病原的方法。侵袭我们身体最多数而最可怕的,当然是传染病”[11]序。故此,唯有认识传染病,才能达到预防、扑灭疫病,实现国民健康、国家强盛的目的。
一些出版商和书商也纷纷涉足于此“市场”,或谋求“文化资本”,或以普及传染病知识为己任,邀请医界人士,编辑出版了各类传染病书籍,推展了知识的传播,例如,有“急性传染病”和“慢性传染病”之分的图书,有专门针对“儿童传染病防治”的书籍,有专论“牲畜传染病”的书籍,有为学校等专业性机构提供传染病防治管理知识的书籍,有为军队防治编写的“卫护手册”,有通史性的“中国医学史”,有服务于家庭防疫的“家庭卫生常识”,有译自苏美等国的“传染病学”专业性著作,有抗日根据地翻印和简易装订的“卫生常识”,有对现实防疫经验总结编撰之书,等等。
这样通过书籍与文字的触角,便将传染病的知识扩散传播到了民众所栖息与生活的各个角落。“在这段历史中,他们各有各的位置,各有各的角色。于是乎,文本史、书籍史,乃至更广泛的交流形式和文化实践史”在印刷书籍中相互发生联系,进而让我们通过书籍史的视角,“就把所有参与话语生产、传播和阐释的人都网罗进同一段历史”[12]。最终,书籍史研究可以作为“一门‘问题史学’,通过过去理解现在,通过现在理解过去”[13]。
2 书写传染病:书籍知识的专业性与大众化之分
黄克武曾说在清末民初,中国的知识处于一个从传统到现代的过渡阶段,简单地说,可谓经学的没落与科学的兴起,或说是“俗世化”的发展。对此,在传染病书籍的印刷出版领域亦可窥视一斑。
当时,鉴于“吾国人种,甲余全球,则传染亦握全球之大多数”[1],对这一问题的不得不重视与关切之缘由,其时出版的各类传染病方面的书籍,也多是直抒其意。有书籍从疫病的严重性入手,告知民众“传染病,为有传染流行性之疾病,其病原体,散布各地,乘机侵袭人类,辗转感染,如火燎原,为祸之烈,莫甚于此。故吾人对于此等疾病,必须及早加以正确诊断,适当治疗,及严密预防,乃始有济于事”[14]1;或从概念分类入手,“人类的疾病可分二大类:一类叫作传染病,一类叫作非传染病,两类之中,与人类最有关系的,为传染病”[15],开宗明义;或从防疫与国家人种强弱视角阐释的,“综观中国人民体格孱弱,精神萎靡,疾病频繁,死亡超格的现状……本社有鉴于斯……促使医药卫生社会化,挽救国家危机,增进民族健康,完成复兴建国大业”[16]。
翻检当时出版的相关书籍,可以发现“书写文本”大致可分为两类。其一,专业性的书籍。此类书籍又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是服务于特定读者群体的,如医生、护士与防疫工作的人员;二是聚焦于特定的传染病,如家畜传染病等。在第一方面,如为“护士应用”编写的《中国传染病概论》一书强调:“此书之编辑,希望能应两种需要。第一为护士学校教员之需要;不论担任教课者为医师或护士,皆须于职务忙迫之时,预备教授大纲,故本书拟将各种应用材料,勉为编入,使所论各病,一一逼真,于学生有兴趣,于教育有裨益。第二系应护生之需要,编辑一种课本,文字简明,而能授以关于中国各种传染病应有之智识。”[17]第二方面,聚焦于牲畜等特定传染病防治方面书籍的出版情况,也可窥见近代防疫知识的拓展与农业生产发展之间的关联。贺克[18]在《家畜传染病学》中称:“今岁,浙江东阳县开办家畜防疫训练班,目的在短期间培植防疫人员,备充该县防疫工作之实施,兹以该会即将开办,由建设厅委贺克主持教务,因编《家畜传染病学》一书,以供应用,该书内容,均经程绍迥博士校阅,可称适当教材。”陈之长则在1936年由吴信法编著、正中书籍出版的《家畜传染病学》序言中讲道:“兽医之学,向为国内学者所忽视。当家畜瘟疫流行时,农民除祈求瘟神之宽佑外,别无他法;其结果不但使农民蒙重大之经济损失,而且致畜牧事业之无从发展。”[19]
其二,注重传染病知识书写的大众性与可读性。1935年编著的《传染病》一书在其“发刊旨趣”中强调:“一切科学,对于人类均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是人人应有的知识,决不可认为太高深、太专门的。医学是科学中之一种,当然不能例外,应使大众化,叫不以医师为职业的人,也感到医学的兴趣,自然而然能了解人体的生理,疾病的来源,以及预防和疗养的方法。”[14]发刊旨趣由程瀚章编撰、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小学生文库”中《传染病》一书也写道:“我们的一般民众,尤其是小朋友们,对于传染病的知识,不是很觉得缺乏吗?要想把这种知识普及到大家脑海里,必得把许多传染病一样一样的详细讲述出来,灌输起来才行。”[11]序
另如开明书店出版的《人与虫的搏斗·虫性传染病篇》宣传语所宣扬的:医学是一门最艰深的科学,不是一般人所能够窥其堂奥的;不要说一般人,即使是守卫天责的医师们,有时候也会感到头痛的。然而人终究是人,人对于种种疾病的抗争,事实上不能够完全依靠医师;人要自己贡献出一点力量和方法来,那就需要一些常识了,尤其是对于传染病。“本集作者基于这个意念,选取了一个巧妙的方法,运用了文学的天才,把艰深的医学写成一个个绮丽的故事,使读者感觉到是读着一部部感人的文学作品,同时却从这里面获得了可以实际应用的医学常识。”[20]
3 知识的“指南针”:细菌、消毒与隔离法的普及
对于传染病书籍的出版,这一时期很多书籍还强调了其文本知识的“指南针”作用,希冀可“使读之者,知一病有一病之原,其传染之法,蔓延之途,皆经先哲苦心之研究,明白告我。禹鼎温犀,神奸无所逃遁,持此以为避疫指南针,则吉凶趋避之途,庶可瞭然,而魑魅魍魉莫能侵犯矣”[5]序。大华书局编撰的“医学卫生问答丛书”发刊要旨中便指出:“谁都知道健康是人生的幸福,谁都愿望自己和家庭身体的健康。可是,大家都免不了病,病了,当然急求治愈。因此,社会上很多的人士,都不免要感到医药卫生常识的饥荒;同时,他们必然渴望得到一个指点迷途的南针。”[21]针对于此,多数书籍从传染病的病原体细菌、消毒法、隔离法等方面入手,普及与丰富了民间的传染病知识。
首先,在19世纪末发现细菌之后,“西方关于病菌致病的学说开始传入中国,并得到一些人的认可”,如“一本完成于清代末年的防疫著作这样介绍了细菌学说:‘传染之原因,皆由细菌,细菌亦生物也,以显微镜测之,有球状者,有棍状者,有螺旋状者,有苦迈(英文字形)……’”[22]余云岫对此曾描述道“其病毒能由甲传乙,使多人生同一之病者也。何谓病毒,病原微生物是也。何谓微生物,细菌与原虫是也。各种传染病,都有独特之病毒,或假人体以传播,或缘器具为媒介,以流毒世间,播害吾人”[5]1。同时,各类图书也多配以细菌的图形,让读者能够“眼见”而识,有切身之感受、深刻之记忆。
其次,对消毒法的介绍。“预防传染病,最重要的当然是消毒法。消毒法,就是把病人和接近病人者的身体或衣服,和病室内或病人接触过的用具上,以及排泄物中所附着的病原体杀灭的方法。”[11]12消毒法又可分为烧毁法、蒸汽消毒法、煮沸消毒法、药器消毒法等类。《山西省疫事报告书》曾记录面对1918年的肺鼠疫时,山西省政府在施行消毒法过程中所面临的巨大阻力,其报告书认为,这是由于消毒行为是“三晋人民前此未闻未见者”,尤以当时的传统迂腐的学究、无业游民更甚,对此多有恐惧,流言丛生,对此报告书指出若“不惜小物,于遮断交通、清洁预防诸政策决定实施后”[8]202,不进行消毒,就取得不了最后针对疫病防疫工作的胜利。由此可见,消毒法对阻断传染病传播的作用与意义。中华书局编撰的《传染病预防消毒及救急疗法》在“编辑大意”中也讲道:“传染病之预防与消毒,为维持公众卫生上最要之事。晚近政府颁布中医条例,亦规定传染病预防与消毒之规则于其中,足见国人对于此种知识,亟须补充,无待辞费,故本书以传染病预防与消毒网要居首。”[23]
最后,关于隔离法的推介。人类至惨痛之事,“莫惨于撄不治之疾而亡于非命”,传染病“一旦流行,小则蔓延几村几县,大则波及几省,甚至全国。人类牺牲之大,难以设想”[24]。在清末民国,囿于国情国力,疫情一旦发生,所能选择的措施多是“有防无治”一条,即对已发生疫病的防疫措施唯有“隔绝”二字。在此,同样以民国年间山西省应对肺鼠疫之事为例来说明。当时,疫情发生后,山西省政府采取的首要措施便是“遮断交通,内地严重检查,先后选白话电示数条,俾官民依照清洁、隔离、埋尸、封室各办法严切执行,并聘请各国医生、牧师、教士分投帮助,派委宣讲多员,乘机利导其注重支点,在使人自防卫、家自引避、村自隔绝,忍一时之痛苦,保万姓之安全”[25]。当然,实施“隔绝”,也是因为“各种传染病,各有一定时日之潜伏期,故无论何种传染病流行时,凡有接触病毒之嫌疑人,须依该病之潜伏期为标准,使之离居。若过期不发,则知其并未受染,即可放行”[5]1-2。另外,一些法律性书籍也从立法的角度,为防疫“隔绝”的实施提供了法律制度方面的保障。如1928年颁布的《传染病预防条例》第三条规定:“人口稠密各地方应设立传染病院或隔离病舍。”第四条规定:“当传染病流行或有流行之虞时,地方行政长官得置检疫委员,使任各种检疫预防事宜。于舟车执行检疫时,凡乘客及其执疫人等,有患传染病之疑者得定相当之时日扣留之。”[26]
上述所论均为近代西医传染病知识在中国的输入与传播情况,在具体的研究与实践过程中,也不可忽视中医在传染病防治方面的作用。如当时由中医改进研究会邀请时逸人编辑的《中国急性传染病学》一书的“赵序”中称:“近今中西医家,对于防疫治疗,亦颇尽心。特中西各自为政,而此等病多发生于僻壤穷乡,西医西药所不能遍及之处,然则是编,较之时令病学,尤为切要者矣。”[27]可以说,从清末至当代,中医与西医在防疫知识之间一直是处于一种竞争与互补的关系之中。
需要补充的是,也不可忽视传染病书籍的发行与阅读情况,毕竟书籍发行得越多,就间接说明阅读的人群也越多,书籍所能起到的作用也就越大。囿于笔者管窥所见资料,现仅从报刊资料及几本图书的发行数据作一粗略推测。据报载,1926年,中西医学研究会为普及医学卫生知识起见,经理事会决议,印行了八种书籍,分别为《医学门径语》《结婚与健康》《传染病客座谈话》《花柳病一夕谈》《青年之摄生》《肺痨病之天然疗法》《素食主义》《卫生格言》,每种计5 000份,“函索者每种须附邮四分,以示限制”[28],总计4万余册书籍免费赠送。除民间的研究会外,政府在传染病书籍的出版方面也是不遗余力,1934年青岛社会局“以时届冬令,气候不均,白喉猩红热等传染病,最易发生,自应预为防范,特饬科印就大批猩红热白喉预防小册,函送公安局代为分发市民,以便预防传染,而重健康云”[29],大大普及了医药知识的传播。
在书籍出版方面,1945年由文通书局出版的美国西塞尔(Cecil)著,叶维法主译的《法定传染病学》在“再版自序”中强调:“本书初版问世后,未及数日即被竞购一空,西北边远地区及驻印国军医务机关,因路途遥远,音讯阻滞,不及订购,纷来函电要求再版。”[9]再版自序后此书在较短的时间内又进行了三次印刷。又如,1949年由时代出版社印刷出版的苏联陀勃罗霍托娃(Доброхотова)撰,朱滨生译的《儿童传染病预防法》,在其版权页上标注1949年2月份印刷了2 000册,12月再版时又印了3 000册,可见社会对这类书籍阅读需求之旺盛[30]。
4 结语
书籍史为我们认知近代中国传染病的生成与传播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视角,如同乔治·萨尔顿强调的:“印刷术的发明是人类历史上伟大的转折点之一,它对科学史尤为重要。”[31]借助于印刷术,口头与手抄本形式的传染病知识被稳定、可靠与持久的书籍形式所取代,为人们提供了一种值得信赖和可反复阅读的知识,使得近代中国的防疫知识主动地趋向于世界传染病防疫知识的主流思潮,普及了细菌学的知识观念和传染病预防、消毒等技能,而非被动地适应,体现了近代中国卫生防疫现代化的积极探索。“人民有完全卫生知识而后国家有完全卫生行政,此传染病预防不易之原理也。”[8]1
总之,传染病书籍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重要“注脚”,如果我们不去解读这个“注脚”,就无法认知很多问题。印刷书籍在对传染病知识的生成与普及过程中,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1912年~1949年中国社会所赖以运行和存在的关于传染病的知识语言和科学认知,形成了对社会的干预,成为改造社会的一种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