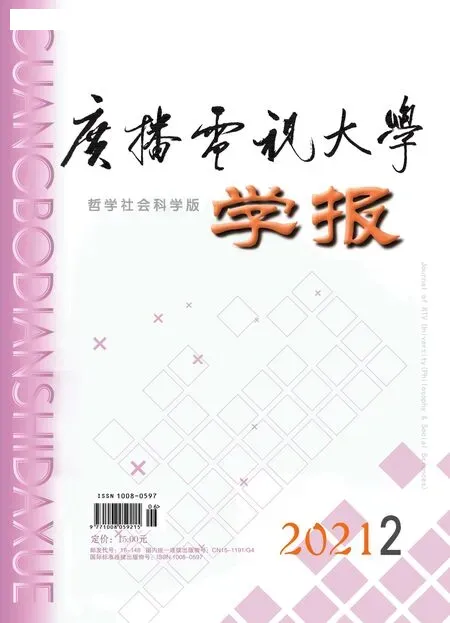元初从征文人南下诗歌的文学与文献价值
2021-12-01梁建功
梁建功
(南开大学,天津 300071)
宋末元初在统一战争中,不少北方文士随同忽必烈南下征战大理、南宋,进入西南、两湖以及江淮等地。在南北对峙一百多年后,北方文士第一次大规模进入南方地区。他们积极保护南方百姓与文化精英,同时引导理学北传,成为南方文化的重要保护者。
除了文化上的贡献之外,从征文士在南下过程中创作了不少诗作。南下潜邸文士以北人之视野察南方之风物,展现了西南、中南地区的自然与人文景观,同时记录了蒙古军队南下的历程。当然,其中还寄寓了诗人在南北统一进程中独特的个体感受。这些北方文士参与到南北统一这一时代巨变之中,他们第一次进入南方,面对异域独特的自然风物以及紧张的战争生活,他们所作诗歌的风貌以及特殊心态值得研究。
一、南下进程与南方景观:从征文人南下诗作的历史记录
自1244年开始,忽必烈开始大规模征召北方文士进入其潜邸,“岁甲辰,帝在潜邸,思大有为于天下,延藩府旧臣及四方文学之士,问以治道。”[1]P57北方文士陆续汇集忽必烈潜邸之中。其中一些北方文士在进入忽必烈藩府之前已经随同蒙古军队南下江汉地区。如1235年姚枢、杨惟中随同阔出南下江汉地区,姚枢在德安解救被俘的赵复,促成赵复北上。而后世将赵复看作元代北方理学的开启者,“河北之学,传自江汉先生,曰姚枢,曰窦默,曰郝经,而鲁斋其大宗也,元时实赖标之”[1]P2994,“静修先生亦出江汉之传,又别为一派”[1]P3020。从征文士真正大规模南下是在忽必烈南征大理与南宋时期,随同蒙古军队南下的士人有刘秉忠、刘秉恕、张文谦、张易、姚枢、郝经等人。其中就现存文献而言,刘秉忠、郝经留下大量南下诗歌作品,其他从征文人留下南下诗作相对较少。本文主要以刘秉忠、郝经等人南下期间诗歌创作为线索,探求南北对峙一百多年来,北方文士以从征方式进入南方过程中,其诗歌所具有的时代与地域特色。这些从征文士所作诗歌中既有关于蒙古军队南下征战过程中军事行动、战争形势的记叙以及对蒙古军队士气的描述,还有不少对南方自然与人文风光的描写。
从征文士南下诗作中很大一部分是对南下征战进程的叙述。
(一)南征途中军情之紧张
从征文士随同忽必烈南下征战大理和南宋,其诗作中有不少对紧张战争形势的描摹。刘秉忠作为忽必烈潜邸时期的主要谋臣,参与了忽必烈早年征战大理以及江汉地区的军事行动。特别是南征大理期间,刘秉忠诗歌中有不少关于蒙古军队征战的记叙。南下大理途中,要“重劝小心防暗箭,深知老将识兵机”[2]卷一乌蛮道中,在深入西南地区之后,刘秉忠发出了“投亡置死虽能胜,履薄临深未敢安”[2]卷一过白蛮之感的感叹。除了直接对紧张军情的描写之外,刘秉中还很善于通过对环境的描摹进而渲染军情的紧张,“风急旌旗高捲日,夜长刁斗寂无声”。[2]卷一满坦北边而郝经在随同蒙古军队南下江汉时,描写了蒙古军队在石门期间的军貌:“部伍条整顿,介胄听将令。遇敌勿妄动,涉险更安静。”[3]P75南方地理形势与北方不同,对于南下征战的蒙古军队有相当大的挑战性,随同蒙古军队南下的北方文人对此也多有感发。
(二)南征行军途中之艰难
蒙古军队南下大理和江汉地区,途径西南以及湖北地区,这些地区山险水急,因此行军之途径多险阻。这些从征文人诗中除了记叙南征时战争形势紧张外,还有不少对南征途中行军艰难的描叙。郝经随同蒙古军队南下江汉地区时,和南征将士一起历经艰险,“甲士斫前路,呀转岗坂竞。登天忽落井,急注缭一经。翻身伏马鬣,植立上石磴。覆地露叶滑,摔面树枝迸。断木余高盘,蹶步复拉胫。楂竹磔青耳,剟刺蹄血凝”[3]P75。而在南征大理期间,蒙古军队需要从甘肃南下,穿越川西、滇北等地,这些地区多高山急湍,地理形势比江汉地区更为险要,同时,行军距离更长。刘秉忠在南下云南期间,所过之处是“脊背沧江面对山”[2]卷一过白蛮,刘秉忠第一次来到西南少数族群聚居地区,其地山川与风物给刘秉忠留下了深刻印象,“鞍马生平四远游,又经绝域入蛮陬。荒寒风土人皆怆,险恶关山鸟亦愁。”[2]卷一西蕃道中。对从征文人来说,南方山水之柔美之处并没有过多地在其诗中得到展现。
(三)南征军队气势之盛
虽然军情紧急,行军路程又十分险恶,但是这些从征文人对蒙古军队南下必将取得胜利充满了信心。他们或者描绘蒙古军队围城时军阵之严整,如蒙古军队在围困大理城时,“天王号令迅如雷,百里长城四合围。龙尾关前儿作戏,虎贲阵上象惊威。”[2]卷一下南诏或写军纪严明,气势胜人,如郝经南下江汉的蒙古军队“如律以次发,不鼓气益盛。”[3]P75南宋军队面对南下元军,“敌人隔林望,坐甲不敢出。”[3]P75不论是征战大理还是南下江汉,所在地区多崇山急湍,地理环境十分险恶,加之这些随征文士都是第一次进入南方地区,其诗中对蒙古军队军势强盛的描述虽有夸张与颂扬之嫌,但是仍然为我们深入了解蒙古军队南下的细节提供了丰富的历史材料。
(四)南征军队仁义之师的形象
刘秉忠、郝经在叙述南征进程时,有不少诗句将蒙元军队描绘成不滥杀的仁义之师。在他们眼中,南征军队“伐罪令行元不杀,远蛮归服感仁声。”[2]卷一过鹤州郝经直接写出“渡江不杀降,百姓皆安堵,”[3]P79之句,白兆地区的居民,“负担来迎降,马首争蒲伏。为闻不杀令,又复治安陆。”[3]P77除了描述蒙古军队南下不滥杀的行为外,他们还对蒙古军队南征的正当性进行论述,指出“彼乃执信使,徼鄙閧偷劫。本以礼义期,谁知重骄跋。”因此“王乃振师徒,扬旗祃太白。”[3]P81刘秉忠、郝经等从征文人不仅仅描绘了蒙元军队仁义之师的形象,还阐释了蒙元军队南下统一南方的正当性,正因如此,他们对蒙古军队南下统一天下充满信心。
从征文人诗中除了对蒙古军队南下历史进程的记叙外,其中还有不少南方意象的描写。从征文士眼中南方的山水与人文景观具有不同的意蕴,这就使得其南下诗作具有独特的风韵。
(一)南方山水与地势之壮丽
从征文士所经地区为西南与江汉地区,这些地区山险水急,使得其诗中的南方山水多壮丽之色。刘秉忠随同忽必烈南下西南地区,其诗中对西南山水的描绘多壮丽之景色,“一泓碧玉垂天影,万丈丹梯壮地形。”[2]卷一乌蛮江上在过玲珑山时,他用“青”与“白”来描摹玲珑山之山色,“摩青块磊谁能凿,透白玲珑自可穿。”[2]卷一过玲珑山郝经随同蒙古军队南下随州时,写随州“山南楚甸坼,汉东随为大。”[3]P75除此之外,诗人在描写云梦泽时,直接感叹“乾坤入涵混,鱼龙深宛转。”[3]P78纵观刘秉忠、郝经诗,其中有不少有关南方山水地势雄壮的诗句,正是这些雄壮诗歌意象的加入使得二人南下诗歌颇有雄浑之风。
(二)南方莲、竹等凄清萧寒之态
莲、竹等是南方代表性的植物,在前代诗歌中多有出现。一般而言,前代诗歌中很少将莲、竹与凄清萧寒之感想联系,但是在郝经等人所作诗中,“莲”成为“野莲”,“竹”成为“荒竹”。他们赋予这些南方植物的意蕴明显和前代有所差异。郝经在描写南方之野莲时,先叙写莲生长之处十分萧寒,“陂塘渺烟芜,秋波淡浮空。”[3]P82而野莲在此萧寒之境中只能“金粉亦自香,霞腴为谁容。”[3]P82这些“荒竹”“野莲”生长于长期战乱的江汉地区,这里百姓逃亡,一片衰败之色,因此竹、莲也随之呈现出荒空之态。
(三)从征文人诗中的南方人文景观
南方有着众多的亭、楼等人文景观,从征文士登楼赋诗,流露出归隐之思。郝经登黄鹤楼发出“我方溷戎马,对面兵尘隔。焉能载酒上,云间觅仙客。”[3]P81的感慨,诗人借助黄鹤楼仙人饮酒飞升的故事表达了自己在战争中对洒脱人生的向往。而刘秉恕登随州白云楼,面对萧瑟的秋风直接发出“黄耳不来家信远,西风肠断白云楼。”[4]四册154之感。可以看出,这些南方人文景观由于其独特的历史文化意蕴,使得它们成为从征文士表达心绪的有效载体。
总体来看,不论是展现山水地势之壮丽,还是表现南方植物之凄清萧寒,从征文士都能将从征途中的独特感受融入其中。从征文士诗歌记叙了蒙古军队南下的进程,是对蒙古军队南下历史的重要细节补充。诗中还描写了具有独特风韵的南方意象,具有十分重要的文学与文献价值。
二、时代与个人:从征文士南下途中情感的两个侧面
随同蒙元军队南下的北方文人是南北隔绝一百多年后第一批大规模南下的文人,在南北统一这一时代背景之下,他们直接参与到了这一变革的历史进程之中,因此探究其南下过程中独特的情感状态对于我们了解变革时代中文士生存状态与心理状态具有重要意义,而这些情感在其诗歌作品中得到充分的体现。
(一)对南征胜利充满信心
考察刘秉忠、郝经等文人南下诗歌可以发现,其中有不少诗句表达了诗人对蒙古军队取得南征胜利充满了信心。这种信心当然来自蒙古军力之强大,除此之外,他们对南北统一、社会秩序恢复以及生民生存的关注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这种信心。刘秉忠在南下大理途中,尽管南征之途艰险异常,但是他对降服大理以及天下最终实现统一却充满了信心,“日月照开诸国土,乾坤包着几山川。”[2]卷一乌蛮“已升虚邑如平地,应下诸蛮似急湍。”[2]卷一过白蛮在攻下大理之后,刘秉忠更是期望百姓能够做新民,过上安定的生活,“南诏江山皆我有,新民日月再光辉。”[2]卷一下南诏而郝经认为虽然“东南天一隅,区宇独限越。我鞭莫及腹,我车莫通辙。”[3]P85但是蒙古军队“干腹出大理,上流下开达。夔门势扼吭,通泰潜捣胁。万里常山蛇,首尾劲相接。”[3]P85正是由于如此战略态势,加之蒙古军队“千麾绕清霜,万蹄碎踣铁。”的实力,所以诗人描绘蒙古军队南下渡江时,“谈笑过江东,兵刃浑不血。”[3]P85这些从征文人的诗句表明,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对南北统一的历史趋势是有清醒认识的。
(二)厌乱思治
查洪德先生指出:“元代是乱世,人情厌乱思治,致力去乱求治,是元代文学的基本主题。”[5]P11从宋金对峙至蒙金、宋元战争,南北一直处于战争的阴影之下,特别是金末元初,北方战火频仍,郝经“金季乱离,父母偕之河南,偕众避兵,潜匿窟底,兵士侦知,燎烟于穴,爝死者百余人,毋许亦预其祸,公甫九岁,暗中索得寒遗一瓿,按齿饮母,良久乃苏。”[6]P294可以说,金末北方战乱给这些文士内心留下深刻的印记。此外,从征文士在南下征战过程中目睹了交战地区残破之景,郝经在南下随州期间,随州地区“居人尽室去,涵养侭一败。荒空二十年,繁伙日芜秽。白垩余屋壁,狐狸窟庭内。穿窗枣枝曲,倚柱岩桂坏。谁种当道棘,乱长侵阶菜。奥室没蒿莱,何处觅粉黛。”[3]P75随州是宋金、宋元对峙前沿,长期的战乱使得这里成为一片废墟,面对江汉地区的残破景象,他发出“反思中原好,桑麻展平镜。衍沃少严邑,生民乐王政。”[3]P76“佇马开天荒,欲复太平代。”[3]P75的感叹。此外,长期征战生活使得他们身心十分疲倦,而自身怀揣经世救民之价值理想,其南下诗歌中自然充满了对天下太平的渴望之情。刘秉忠更是有“凤凰望断麒麟绝,空想萧韶奏太平。”[2]卷一驴湫道中之愿望可以说,金末元初北方近乎崩溃的社会现实是这些从征文士积极拯救时弊的直接动因,他们加入忽必烈幕府之中,并随同忽必烈南征北讨,在南下过程中,他们不仅仅沉浸于随蒙古军队征战的战功获取之中,更多的还是关注战争对百姓所造成深重灾难。止乱救民,恢复社会秩序是他们进入忽必烈幕府的初衷,就当时北方的蒙古贵族而言,忽必烈能够吸纳他们行汉法的意见,这些从征文人从忽必烈身上看到了北方社会秩序恢复的希望。从这个意义上讲的,厌乱思治思想产生与止乱救民的践行有着深刻的社会现实背景。
(三)倦怠、苍老与飘零之感
从征文人多数生活于金末元初这一战乱频仍时期,他们在进入忽必烈潜邸之后随同忽必烈南征北战,几十年的征战生活使得他们在南下过程中不时流露出苍老、倦怠与飘零的生命体验。刘秉忠在南下大理时已经三十七岁,他时常发出“半生鞍马苦劳行,鬓影难求晓镜青。万里又征南诏国,九霄还识老人星。”[2]卷一南诏“军中无酒慰飘零,辜负沙头双玉屏。”[2]卷一江上别寄而郝经也是三十七岁时随同忽必烈南下江汉,此时正值秋季,他看到“高秋江汉波,卉木入摇落。”[3]P83有如屈原“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7]P140之境,生于此秋风萧瑟之地的梧桐“凄迷气日丧,憔悴叶自脱。”“岂能持风寒,况乃失所托。”[3]P83诗人正是借助此秋桐展露自己憔悴与漂泊之感。
(四)归隐之思
从征文士南下期间,多有归隐之思。这种情感的产生与南方山水与隐逸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郝经南下江汉期间,他看到楚地“群山避鄢郢,霜净楚天远。秋色浮雁背,风水芦花满”“鹅鹳不知家,悠悠忘还返。”[3]P78由此“注目浩无迹,驰想首重俛。”[3]P78郝经想到的是曾经在此劝说屈原归隐的渔父,“濯缨谢渔父,瞑卧汀沙晚。”[3]P78在楚地自然与人文环境之下,郝经生发出“何时结茅屋,老吟寄残端。”[3]P78之思。与郝经相似,刘秉忠在南征途中不时发出不如归去之思,“愿戢干戈息征伐,归期先卜两眉头。”[2]卷一灭高国主对诗酒自娱的萧散闲淡生活产生强烈向往,“直将日月销书秩,更假云山作画屏。满地干戈虽有酒,不能长醉似刘伶。”[2]卷一南诏可以说,这种归去与隐逸的思想成为南下文士的一种共通性的思绪。
南下文士在南下过程中期情感是多方面的,从宏观层面对蒙古军队能够完成天下一统的信心到自身在长期征战过程中的疲倦之感,以及由此生发出对闲适隐逸生活的向往都显示出从征文士在时代大变中特有的个体感受。
当然如果回溯这些从征文士的个人经历可以发现,不论是刘秉忠、姚枢还是郝经,他们都经历了金末北方战乱,他们认为“四海一红炉,焦心待时雨。群生日熬熬,无从求乐土”[4]3册P18,因此安定天下,恢复社会秩序就成为这些从征文士的社会价值追求之一。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刘秉忠等人诗中有大量渴望天下太平的诗句,他们希望蒙古军队能够完成天下统一,实现社会秩序的恢复。郝经在宋元对峙之际出使南宋,期望两国“铲去疑阻,以承天休,弭兵息民,申画疆理,通天下之一气,合南北之太和,苏润疮痍,补葺倾败,舒释灵长,缔结欢悦。”[3]P977这种价值追求在元初北方士人中相当普遍,他们加入忽必烈幕府,不仅仅是渴望能够满足个人物质需求,更主要的是能够在忽必烈身上实现个人的社会理想,因此郝经在南下途中直接说出“抚膺还自颂,不负生平学。”[3]P80另一方面,从忽必烈渴望大有为于天下到南北统一,将近四十年时间,这些文士一直随同忽必烈南征北战,长期的战争生活对他们的心灵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也极大地消耗了其生命力,在战争间隙,他们借助异域的山水或者表现内心的灰暗,或表达归隐的思绪。这种战争年代的个体感受与天下统一的时代脉搏相缠绕造就了从征文士诗歌独特的风韵。
三、从征文人南下诗作的文献与文学价值
作为南北分裂一百多年来第一次大规模进入南方的北方文士,从征文人在南下期间所作诗歌具有独特的诗史价值与风韵。这些诗歌产生在南北统一之际,由北方诗人在南方写成,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与全新的地理环境之下,其所作诗歌自然成为记录这一独特时间与空间的文学材料,从征文人所作诗歌的诗史意义也正在于此。
(一) 从征文人南下诗歌具有诗史价值
关于“诗史”的论述,冯至的观点具有代表性,他指出“杜甫的诗一向称为诗史。我们现在也常沿用这个名称标志杜诗的特点,它广泛而深刻地反映了唐代安史之乱前后的现实生活和时代面貌。”[8]P59,也就是说“诗史”的基本内涵是叙事性与纪实性,特别是重大历史活动一直是“诗史”的表现内容。从这两方面来看,从征文人南下期间所创作的一些诗歌具备以上特征。从内容上讲,这些诗歌作品记叙了蒙古军队南下征战的历史细节,包括南下路线,南下过程中所过地区的风俗,蒙古军队军威等等,这些历史细节在一定程度展现了宋元对峙时期,西南、江汉地区独特的社会风俗以及蒙古军队南征时期的风貌。刘秉忠随军南征大理期间,所作《西蕃道中》《乌蛮道中》《过白蛮》《下南诏》《满坦北边》《驴湫道中》《过玲珑山》《过鹤州》等,以及郝经南下江汉地区所作《随州》《石门》《白兆山》《渡江书所见》《渡江书事》等作品都以北人视角来观察南北大一统这一历史进程。正如上文所述,这些作品从行军道路之艰难、军情之紧急等方面来表现蒙古军队南征的困难程度,同时诗人又从军势之威严以及蒙古军队仁义之师形象等方面表达出南征必胜的信心。除此之外,从征文人南下期间个人情感以及对这场南北战争的看法等都在诗中有所展现。诗人在展现上述内容之时,多是进行客观的记叙,叙述南征军队南下进程。如在《石门》中,郝经记叙士兵斫木开路,行军路途狭窄险恶,南征士兵还要面对敌军的威胁,因此行军途中要严格遵守军纪等都在诗中一一呈现。这些诗句展现了个体文人在卷入时代巨浪后独特的生命体验,也成为我们透视变革时代下文士人生存境遇的绝佳材料。
(二)南下诗歌的地域色彩
从征文人南下期间所作诗歌,具有明显的南方地域色彩。这种地域色彩首先表现在西南与江汉地区的自然山水、景物以及地域文化的展现。特别是刘秉忠等人,南下西南地区,这里的自然风物与中原迥异,在刘诗中,成千上百喧啾似鸦雀的“鹦鹉”,万丈的“天梯”,被石磴接引上坡的泉水等西南风物成为其诗中最显著的地域元素。除了西南,江汉地区的风物也经常出现在从征文人的诗歌之中,如宋衜笔下的武当山,“武当却立翠屏新,碧玉溶溶汉水奔”[4]7册P317,郝经诗中“陂泽通江湖,田岸藏町疃。横汇渊薮大,散漫稻畦浅”[3]P78的云梦泽,它们都是江汉地区的标识性自然景观。除了这些自然景观外,当地的人文景观也是展示地域文化的重要载体,特别是江汉地区,邻水高地多有亭台,历代有不少文人在此留下千古名篇。此外,江汉地区自古以来就是南北对峙的前沿,不少重大的历史事件都在这里发生。从征文人在此地征战时,或登楼抒怀,或凭吊古迹。郝经登上压云亭看到“艨艟断江流,甲骑蹙城脚。”[3]P80的景象,登黄鹤楼看到“千帆落山巅,万樯拥舟楫。”[3]P81而杨惟中夜泛赤壁,看到“怒虬松偃映,漱玉水潺湲。明月尊前月,丹崖战后颜。”[4]3册P27的夜景。正是由于这里历代为四战之地,所以宋衜发出“如画江山千古在,城闉几度战尘昏。”[4]7册P317之感,从征文士所作南下诗歌所具有的地域色彩是自然与人文相互交织而成的。
(三) 南下诗歌在元代诗歌史中的价值定位
刘秉忠、郝经等从征文人作为金朝灭亡后第一批进入南方的北方士人,他们南下其间所创作的诗歌作品丰富了元诗的表现内容,是元代军旅诗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他们身为文人,又不同于征战的武将,他们对时代巨变有着更为细腻的感受。因此从不同角度来审视从征文人所作诗歌,我们可以发现,这些诗歌在元代诗坛具有独特的价值。元代诗歌发展史可以追溯到跟随成吉思汗西征的耶律楚材,而从1234年金朝灭亡至1276年临安被攻破,元代诗坛一直被金源文人所占据,其间近四十年时间中,南北对峙,北方文士开始随同蒙古军队南下,西南以及江汉地区成为北方文人南下的集中区域。南北统一之后,北方文人以各种方式南下,可以说从征文人南下开启了元代北人南下序幕,其南下期间所作诗歌自然成为南下北人诗歌创作的先声。这些南下的从征文人不论从诗歌风格还是人格特质来说都有不同特点,如刘秉忠虽为僧人但是其“气刚以直,学富而文。虽晦迹于空门,每潜心于圣道。”[2]卷六附 拜光禄大夫太保参领中书省事制郝经更是为了天下太平前往南宋议和。可以说,经历金末北方战乱的从征文人都抱有救世拯弊的价值理想,这种理想和价值体现在虽前进之途十分艰难,但是仍然对蒙古军队南征胜利以及天下太平充满信心。从这一意义上讲,南北统一之际产生的南下诗歌不仅仅记录了蒙古军队南下的历史进程,同时展现了北人视角下的时代巨变以及他们对这一历史巨变的看法和感受,在元代诗歌史中具有重要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