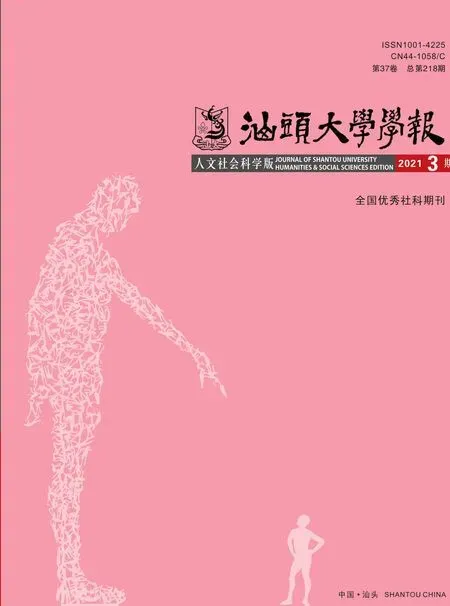身体:魏晋审美领域的新视野
——从先秦、秦汉与魏晋的身体观念比较谈起
2021-12-01沈文秀
沈文秀
(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广东 广州 510631)
不管是中国还是西方,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文化条件下,各个不同的历史时代对于身体的认识也是各有特点的。先秦时期的身体观念中身体被伦理化、规范化。儒家思想观念中人的肉体之身并未得到重视,而是将身体依附于社会伦理道德,希望从人的修身推及社会治国理想;道家思想观念中虽承认身体的肉体性,但身体的肉体性价值却被否定,因为它是人忧患的根源,主张人应该忽视外在的身形而讲求内在精神的修养。秦汉时期,身体的肉体性得到了肯定,认为通过一些方式能使人的肉体之身永恒长存,并将人的身体与天数运化和社会伦理规范相联系;魏晋时期,身体的肉体性得到进一步肯定,但身体具有短暂性与个体性,同时,人的身体成了审美领域的新视野。
一、先秦及秦汉时期的身体观
先秦时期形成了以血缘联系为基础的宗法伦理制度,身体正是这种伦理规范的承受者和体现者,即被伦理化、规范化的身体。儒家的身体观念中,身体承载着社会伦理道德,“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1]316(《孟子·离娄上》)人通过修身来维持社会人际关系,以适应社会的伦理规范,将“安身”“修身”“正身”作为一个人最基本的任务,“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1]2(《礼记·大学》)修身的根本是为了维持社会的伦理秩序,“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1]1(《礼记·大学》)一个人修身最重要的目的不是在于自己,而是要有益于国家社会,“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1]151(《论语·子路》)人的身体与人的前途命运、人格品行以及社会伦理相联系,“相人之形状颜色而知其吉凶妖祥。”[2](《荀子·非相》)“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其生色也睟然见于面,益于背,施于四体,四体不言而喻。”[3](《孟子·尽心上》)因此,“在儒家是以仁德内化入身,以礼仪塑造其身,来修炼内在的德性圆满完善的身体。”[4]道家的身体观念中,虽承认身体的肉体性,但身体的肉体性价值却被否定,老子认为肉体性的身体是人忧患的根源,“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5]121(《老子》第十三章)“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败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5]118(《老子》第十二章)人应该忽视外在的身形,重视内在精神的修养,排除社会中的各种诱惑来养神安心,达到自然无为的精神境界。庄子认为:“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6](《庄子·知北游》)“气”是生命得以存在的本质,生命在于形而上的精神,人应通过“虚静”“心斋”“坐忘”等方式杜绝人的自我成见之心和贪念欲望之心,达到《齐物论》中所说的形如槁木、心如死灰的生命境界。
秦汉时期的身体观念中,身体的肉体性价值得到了肯定,《孝经》(开宗明义章第一)中提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7]一个人尽孝最基本的要求是要保存肉体之身的完整性,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曾说:“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8]对人的身体的惩罚就代表对一个人的惩罚程度。《淮南子·原道训》中认为:“天下之要,不在于彼而在于我,不在于人而在于我身。”[9]两汉葬俗提倡对逝者厚葬,表明身体的肉体性价值受到重视,两汉的神仙方术追求人的肉体修炼以长生不死,以及道教的服食炼丹能长生的观念,都认为肉体性的身体能永恒存在。同时,人的肉体性身体与天数运化和社会伦理规范相联系,如董仲舒认为:“人之形体,化天数而成;人之血气,化天志而仁;人之德行,化天理而义。”[10]188(《春秋繁露·为人者天》)“天地之符,阴阳之副,常设于身,身犹天也,数与之相参,故命与之相连也。”[10]228(《春秋繁露·人副天数》)“行有伦理,副天地也。此皆暗肤著身,与人俱生,比而偶之弇合。”[10]228(《春秋繁露·人副天数》)汉代的观人相面中认为身体的外部特征能体现一个人的前途命运,如王充《论衡·骨相》中认为:“人曰命难知,命甚易知。知之何用,用之骨体。人命禀于天,则有表候于体。察表候以知命,犹察斗斛以知容矣。”[11]36“案骨节之法,察皮肤之理,以审人之性命,无不应者。”[11]38对身体外在特征的观察是鉴别一个人性格品质的重要途径,如“越王为人长颈鸟喙,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乐。”[11]39“秦王为人,隆准长目,鸷膺豺声,少恩,虎视狼心……不可与交游。”[11]39-40从人的身体的各个部位特征就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富贵荣华与贵贱高低,汉代王符在《潜夫论·相列》中认为:“人身体形貌皆有象类,骨法角肉各有分部,以著性命之期,显贵贱之表。”[12]362“夫骨法为禄相表,气色为吉凶候,部位为年时。”[12]364不过,汉代的观相术也在不断地发展变化,王充认为人的命运在出生时已经注定而不可更改,人的外形是对这种命运的体现,而王符则认为可以通过后天的努力来改变这种注定的命运,因而人可以通过规范自己的言行举止,修饰自己的仪容外表以符合察举取士的要求,特别是以“九品中正制”作为选拔人才的时期,对人的一言一行以及音容笑貌都有严格的规定,刘劭《人物志·九征》中有“故其刚柔明畅贞固之征,著乎形容,见乎声色,发乎情味,各如其象”[13]38。容貌形态因关系到人的仕途而受到重视,但人对自己外形的修饰要符合儒家社会政治与伦理规范,要求“其为人也,质素平澹,中睿外朗,筋劲植固,声清色怿,仪正容直”[13]43。可见,秦汉时期对人的外貌特征的观察以政治实用为目的。
二、魏晋审美新视野:身体
魏晋时期,身体成为审美领域的新视野,身体具有短暂性,也最能体现自我本性,魏晋士人更是以自我的身体行为去反抗虚伪的繁文缛节与黑暗残酷的社会政治,追求独立与自由,实现自我价值。
(一)动乱的时代与自由的思潮
魏晋时期,自然灾害频繁发生,人们生存的自然环境恶劣。据邓拓《中国救荒史》[14]中记载,三国两晋大约两百年时间内,共发生旱灾60 次,水灾56 次,风灾54 次,地震53 次,雨雹35 次,疫灾10 次,蝗灾14 次,歉饥13 次,霜雪2 次,地沸2 次,如果按平均计算,每年就会受灾1.5 次。更重要的是,汉末中央政权瓦解,政权频繁更迭,三国战乱不断,相继有曹魏与司马氏集团间的政权之争,西晋时期又出现了“八王之乱”“永嘉之乱”、十六国之乱,东晋时期,先后发生了王敦之乱、苏峻之乱及孙恩、卢循之乱等;不仅如此,当时还有门阀士族之间、中央与地方之间,以及他们各自之间的战争杀戮,导致生灵涂炭。《后汉书·董卓传》《晋书·刘琨传》等书中记载了魏晋百姓的生活惨状。魏晋名士在残酷的政治斗争中惨遭迫害,如魏明帝以“构长浮华”的罪名“抑黜”了何晏、李胜等十余人;司马懿发动高平陵政变,杀害了曹爽、何晏等人,并且祸连三族;司马氏把持朝政后,召竹林七贤入仕,嵇康因拒召被惨杀;曹操以败坏社会伦理道德为由杀害孔融,但实际是由于孔融揭露了曹操假借礼法掩饰自己虚伪面目和除掉异己的野心而丧命。
魏晋时期,传统儒学思想已经演变为虚伪的礼教纲常和繁缛的程式礼节,人的日常行为都要符合“礼法”的规定,要“服有常色,貌有常则,言有常度,形有常式,立则磬折,拱若抱鼓,动静有节,趋步商羽,进退周旋,咸有规矩,心若怀水,战战栗栗,束身修行,日慎一日”[15]64。人的真实本性被扭曲,这不仅是魏晋士人追求解放与自由的障碍,而且“礼法已经丧失了它的真精神,变成阻碍生机的桎梏,被奸雄利用做政权工具,借以锄杀异己”[16]225-226。阮籍在《大人先生传》中就批判:“君立而虐兴,臣设而贼生,坐制礼法,束缚下民。”[15]66“汝君子之礼法,诚天下残贼、乱危、亡之术耳。”[15]67社会的大动乱除了带给人们无限的悲痛恐惧外,也引发了伦理秩序、礼教规范、道德操守等传统思想观念的变化,“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痛苦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16]208。此时期对老庄思想、汉代传入的佛教思想以及本土生发的道教思想等多种思想进行吸收与创新,在追求自我解放与自由的时代思潮中,人们对生命的意义进行重新思考,对于自我的价值进行重新评定。因而,魏晋士人在追求自我人格独立的过程中,就要对这种压抑人性的伦理秩序与礼教纲常进行反叛,嵇康在《难自然好学论》中就提出:“然则自然之得,不由抑引之六经;全性之本,不须犯情之礼律。”[17]266人的自然本性不应该被礼法所抑制,追求个体自我的解放与自由,就要摆脱虚伪礼教对人的束缚,才能实现人的个体生命价值,如《世说新语》[18]中记载:“桓温问殷:‘卿何如我?’殷云:‘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品藻》三五)“桓曰:‘第一流复是谁?’刘曰:‘正是我辈耳!’”(《品藻》三七)“阮籍嫂尝还家,籍分与别。或讥之,籍曰:‘礼岂为我辈设也?’”(《任诞》七)
(二)身体之美:最本真的自我
魏晋时期,频繁的自然灾害与动荡不安的社会,人们处于朝不保夕的生存环境,不再去追求肉体的永恒存在,而是承认生命的短暂易逝。如《古诗十九首》、曹操的《短歌行》、曹植的《赠白马王彪》、曹丕的《典论·论文》、王羲之的《兰亭集序》等魏晋士人的诗作中都流露出对人生短暂的担忧和生命易逝的感叹。魏晋时期的思想观念中,人的身体具有短暂性和个体性,身体最能体现自我本性,梁代萧统在《陶渊明集序》中说:“亲己之切,无重于身。”[19]身体对于魏晋士人实现自我价值有着重要的意义,个体性的身体代表的不是经过“三纲五常”规范后伦理化的我,代表的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我”,通过身体表现出的是“我”的思想情志,体现出的是自我的个性特征。
汉末中央政权瓦解,曹操推行“唯才是举”的选材标准,打破了传统的道德伦理标准,魏晋时期的人物品评也开始由政治实用标准转向了审美标准,身体更是从伦理道德的规范中解放出来。魏晋士人的容貌、形体、肤色等都成为审美的对象,如《世说新语·容止》中记载,“何平叔美姿仪”“潘岳妙有姿容”“王夷甫容貌整丽”“潘安仁、夏侯湛并有美容”“裴令公有俊容姿”“王敬豫有美形”等,在接见匈奴使者时,曹操担心自己外貌丑陋而“不足以雄远国”,让仪表俊美的崔琰来冒充自己,可见他对自我容貌的重视程度。不仅人整体的外在形象受到赞赏,最受关注的是人的眼睛,如“裴令公目王安丰:‘眼烂烂如岩下电。’”“裴令公目王安丰:‘眼烂烂如岩下电。’”“谢公云:‘见林公双眼黯黯明黑。’孙兴公见林公:‘棱棱露其爽。’”人的内在风韵可以通过人的眼睛体现出来。魏晋士人肤色白皙、身材修长、体形清瘦等也是亮点,如“何平叔美姿仪,面至白。魏明帝疑其傅粉,正夏月,与热汤饼。既啖,大汗出,以朱衣自拭,色转皎然。”“嵇康身长七尺八寸,风姿特秀。”士人的眉与鬓发也有特点,如“刘尹道桓公:‘鬓如反猥皮,眉如紫石棱,自是孙仲谋、司马宣王一流人。’”与魏晋之前重“神”轻“形”,甚至忽视人的外形的传统思想相比较,魏晋的形神问题中虽然重视人的“神”,但是并没有忽视人的外形的价值,嵇康《养生论》中认为,“是以君子知形恃神以立,神须形以存”[17]145。“形”是“神”存在的基础,观人之“形”能够知“神”,因而这一时期出现了对“形”的关注,再加上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为了摆脱当时虚伪礼教的束缚,以及追求自我价值的需要,人的身体的外在形象不再受制于传统伦理道德的规范,而是凭借自我个性得到了展示。当然,《世说新语》中也有不同的人物形象,如:“刘伶身长六尺,貌甚丑悴,而悠悠忽忽,土木形骸。”余嘉锡先生认为“土木形骸者,谓乱头粗服,不加修饰,视其形骸,如土木然”[20]。又如,“庾子嵩长不满七尺,腰带十围,颓然自放”。他们的外在形象与魏晋士人追求的仪容之美并不相符,却获得赞赏,是因为魏晋身体审美的意义是以身体展现自我本性,显示自我价值,不管外形是美是丑,“土木形骸”“颓然自放”展现出的都是最本真的自己,而不是被虚伪礼法约束的自我。
(三)身体行为:反叛政治、对抗礼法
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认为对人的身体的各种规范其实就是对一个人灵魂与思想的控制,我国传统伦理道德中对人的身体行为有一系列的要求,以使人的思想行为符合社会伦理秩序的需要。身体作为魏晋士人表现自我本性的载体,从社会伦理的束缚中被解放出来,不仅得到了凸显,而且,他们以自我的身体行为去反抗权力统治下的黑暗政治,去冲破统治阶层所规定的虚伪的礼法制度。
1.女性化的修饰装扮。魏晋士人关注自我外形的同时,也重视自我的装扮修饰,但偏向于女性化的装扮修饰。如曹植、何晏等人都有敷粉之好,《三国志·王粲传》中注引《魏略》中提到,“植初得淳甚喜,延入坐,不先与谈。时天暑热,植因呼常从取水自澡讫,傅粉。遂科头拍袒,胡舞五椎锻,跳丸击剑,诵俳优小说数千言讫”[21]。《三国志·曹爽传》中记载:“晏性自喜,动静粉帛不去手,行步顾影。”[22]何晏不仅有敷粉的喜好,更喜欢穿艳丽的服装,《晋书·五行上》中记载:“尚书何晏,好服妇人之服。”[23]822在中国传统思想观念中,服饰有区分尊卑贵贱等级的社会政治作用,如果人的服饰装扮不符合社会伦理规范,就被视为“服妖”,历代正史“五行志”中都会专列“服妖”一项,如《后汉书》《晋书》中记载穿木屐、宽衣等都是“服妖”现象,但魏晋士人对服装的选择并不是按照儒家礼法的规定,而是以反抗虚伪礼教和追求自我价值为目的,因为魏晋时期,传统儒学思想已经演变为虚伪的礼教纲常和繁缛的程式礼节,人的日常行为都要符合“礼法”的规定,要“服有常色,貌有常则,言有常度,形有常式,立则磬折,拱若抱鼓,动静有节,趋步商羽,进退周旋,咸有规矩,心若怀水,战战栗栗,束身修行,日慎一日”[15]64。当然,在《世说新语》中也有不同的例子,如:“裴令公有俊容仪,脱冠冕,粗服乱头皆好,时人以为玉人。”裴凯粗服乱头与何晏敷粉装扮是大相径庭的两种行为,却获得了“玉人”好评,原因在于这两种行为都是对社会伦理和世俗礼法的反叛,都是对权力政治规训的破除。
2.叛逆、任性与放诞。孝道观念是儒家推崇的社会伦理,“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经,而民是则之。则天之明,因地之利,以顺天下。是以其教不肃而成,其政不严而治”[24]12。孝道应该由对父母的孝延伸到对君主的忠,对一个国家的社会政治稳定有重要作用,因而统治者提倡以孝治天下。“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1]10传统的丧葬礼法有一套严格的规章制度:“孝子之丧亲也,哭不偯,礼无容,言不文,服美不安,闻乐不乐,食旨不甘,此哀戚之情也。”[24]38但魏晋士人在丧葬期间却有着看似不合常理甚至荒唐的身体行为,如《世说新语·任诞》中记载阮籍为母服丧时“散发坐床,箕踞不哭”,“蒸一肥豚,饮酒二斗,然后临决,直言‘穷矣!’都得一号,因吐血,废顿良久”。又如王粲、曹丕、孙楚、王济等名士都爱听驴叫,王子敬、顾彦先平生好琴,学驴叫、弹琴也成为魏晋士人悼亡死者的一种方式,这些身体行为虽与儒家所提倡的丧葬礼法背道而驰,却是冲破礼教束缚的反抗之声。“名教”原指儒家所提出的礼法制度和行为规范,“礼义之经也,非从天降也,非从地出也,人情而已矣”[25]854。礼法的制定要以人的情感为基础,而人的情感的自然表达就产生礼,礼的作用是为了保证人的情感的实现,但魏晋时期,“名教”的虚伪伦理规范束缚了人的自然本性,不合情之礼压抑甚至扭曲了人的真情,“名教”甚至被当权统治者利用为实现其政治目的的手段,如孔融、嵇康被借以“名教”所杀,曹魏代汉、司马氏篡曹等都是以“名教”作为掩人耳目的借口。阮籍在《大人先生传》中就批判魏晋当权者的虚伪礼法:“君立而虐兴,臣设而贼生,坐制礼法,束缚下民。”[15]66因而,魏晋士人在追求自我人格独立的过程中,对这种压抑人性的伦理秩序与礼教纲常进行反叛,他们的一系列叛逆的身体行为其实是他们内心的真情流露,是对当权统治者所吹捧的礼法的有力回击。
魏晋士人对酒的嗜好与依赖是任何时代所不能比肩的,如《世说新语·任诞》中记载:“刘伶恒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在屋中。人见讥之,伶曰:‘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裈衣,诸君何为入我裈中!’”《大戴礼记·劝学》中提出:“‘野哉!君子不可以不学,见人不可以不饰。’不饰无貌,无貌不敬,不敬无礼,无礼不立。”[26]刘伶嗜酒时脱衣裸形的放诞举止,显然与此相背。又如:“诸阮皆能饮酒,仲容至宗人间共集,不复用常杯斟酌,以大瓮盛酒,围坐相向大酌。时有群猪来饮,直接去上,便共饮之。”这与儒家的“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大为不同,与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人生目标也相差甚远。魏晋士人沉醉于饮酒,却常常“醉翁之意不在酒”。《晋书·阮籍传》中记载:“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文帝初欲为武帝求婚于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钟会数以时事问之,欲因其可否而致之罪,皆以酣醉获免。”[23]1360嗜酒成癖、大醉不醒,这极似荒诞的身体享乐行为背后,隐藏的是黑暗社会政治下的保身之计,是魏晋士人对当权者虚伪礼法的曲折反叛,也使其能不受羁绊,表达自我本性与真情。
三、魏晋身体审美的历史局限
自我意识觉醒的魏晋士人在追求独立与自由的过程中,将审美的目光投向了自己的身体,肯定了它的意义与价值,并得到了空前的凸显。魏晋士人看似极为荒诞的行为,隐藏的却是对当权者黑暗政治的压制与束缚的反抗,但不可回避的是,魏晋的身体观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
其一,女性的才情与德行受到肯定与赞扬,而女性的容貌身姿之美并未得到同样地展现。《世说新语》贤媛篇中记载了一些才华横溢的女性形象,如:“谢遏绝重其姊,张玄常称其妹,欲以敌之。有济尼者,并游张、谢二家,人问其优劣,答曰:‘王夫人神情散朗,故有林下风气;顾家妇清心玉映,自是闺房之秀。’”“神情散朗”的评价体现出对女性才华的认可,女子之才在传统的女性审美观念中不值一提,甚至是“女子无才便是德”,但魏晋时期女性之才受到了赞赏与肯定。“谢太傅寒雪日内集,与儿女讲论文义。俄而雪骤,公欣然曰:‘白雪纷纷何所似?’兄子胡儿曰:‘撒盐空中差可拟。’兄女曰:‘未若柳絮因风起。’公大笑乐。即公大兄无奕女,左将军王凝之妻也。”“咏絮才”成了才女谢道蕴的代名词,这种“林下之风”的女性审美标准将女性之才纳入到了人物品评之中,拓展了魏晋女性审美观的内容。当然,《世说新语》中也记载了一些知书达理、相夫教子的女性,如“陶公少时作鱼梁吏,尝以坩鲑饷母。母封鲑付吏,反书责侃曰:‘汝为吏,以官物见饷,非唯不益,乃增吾忧也。’”此则故事被后世奉为教子的典范,女性受到肯定的评价标准是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的“三从”观,以及妇德、妇言、妇容、妇功的“四德”观,而女性的容貌身姿之美在魏晋时期并未像魏晋士人一样有充分展现的空间。
其二,虽然魏晋士人在凸显自我的过程中展示了自我身体,但也给魏晋士人的身体审美设定了一种固定模式。魏晋之前对于男子的要求多是与道德品行等儒家伦理规范有关,如《礼记》中认为:“是以君子恭敬、撙节、退让以明礼。”[25]3《论语·学而》中温、良、恭、俭、让是君子必备的品行,但魏晋人物品评的理想标准是玉人形象,如《世说新语》中记载的以玉来形容人的仪容之美,或形容人的气质之美,“蒹葭倚玉树”“颓唐如玉山之将崩”“傀俄若玉山之将崩”“似珠玉在瓦石间”,玉是一种鲜亮光洁之物,而且色质不随时间的改变而黯淡,不仅以玉比喻魏晋士人的外表,如人的肤色的白皙、容貌的俊俏,更以玉比喻魏晋士人的内在气质,玉人形象体现了魏晋士人追求形神双美的审美理想。出于对“玉人”形象的审美追求,魏晋士人爱好自我的修饰装扮,容貌之美、肤色白皙成为士人关注的一个方面,甚至出现了一种女性化的阴柔之美,如“王丞相见卫洗马,曰:‘居然有羸形,虽复终日调畅,若不堪罗绮。’”卫玠是魏晋时期的美男子,身体瘦弱到了连穿罗绮都嫌太重的程度,这与传统男性身体的勇猛刚健、厚重粗犷的阳刚之美的标准截然不同,但这种“玉人”形象的身体审美标准,是魏晋士人追求人格独立与自我价值的身体审美,如果离开魏晋这一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就与这种身体审美的内在目的相违背。
结语
追求人的自由与解放是魏晋时代的一个思想主题,魏晋士人的仪容笑貌、言行举止等鲜明深刻的人物形象历经时空的流转依然清晰生动,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他们敢于冲破一系列的礼法束缚去追求自我的自由与解放。身体是魏晋士人追求自我独立与展示自我个性的最直接的载体,通过对于身体的凸显和解放去追求自我个体的独立,身体从伦理道德的束缚获得了独立的空间而成为审美对象,并且士人以自我的身体行为去对抗礼法规范,如裸体、醉酒等一系列今天看来都放荡不羁的身体行为,正是士人通过自我身体去反抗礼法束缚来实现自我价值的反映,形成了中国历史上所特有的魏晋风度,而这种魏晋风度也是士人的一种身体姿态的深刻展现,魏晋时期的身体观对后世的身体观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