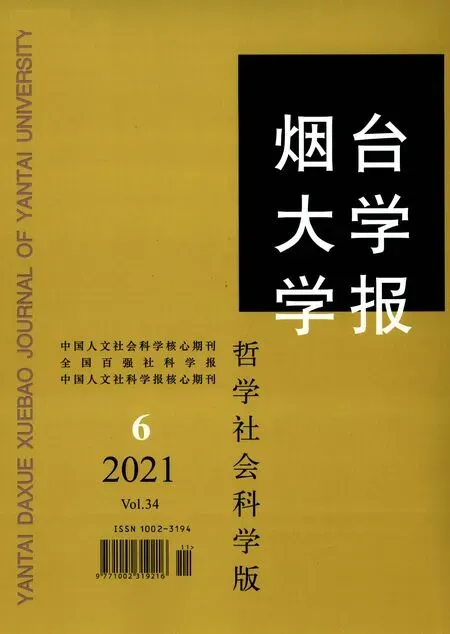北宋前期华北家族制度的建设及其意义
——以徂徕石氏为例
2021-11-30谭景玉
谭景玉
(山东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山东 济南 250100)
学界对宋代家族已有较为丰富深入的研究,但总体上看还有一些缺憾:区域上对北方的研究十分薄弱,时段上对北宋前中期讨论偏少。总之,关于北宋前中期新宗族制度创建阶段的北方家族个案研究比较少,不多的相关研究主要探讨一些仕宦家族的地位沉浮和文化家族的学术文化成就,均较少讨论其家族制度的建设。徂徕石氏是一个初兴于五代,到北宋前期日渐兴盛的官僚家族。学界对其讨论不多,日本学者松井秀一在五代更迭的背景下详细论述了其兴起的过程、家族世系、婚姻圈及通过科举入仕成为新型官僚家族的经过,(1)参见松井秀一:《北宋初期官僚の一典型——石介とその系譜を中心に》,《東洋學報》第51卷第1號,1963年。但对其家族制度建设及意义等讨论不多。探讨该家族制度建设的实践和意义,既可深化对北宋新宗族制度创建过程的认识,又可通过讨论新宗族制度创建之初即出现的区域上的不同,加深对中国宗族区域差异的认识。
一、唐宋之际徂徕石氏的兴起
徂徕石氏大约于唐昭宗大顺年间,由石介的六世祖石光前从沧州乐陵(今山东乐陵)迁至兖州乾封县(今山东泰安)梁甫乡云亭里商王村,即今山东省泰安市高新区徂徕镇北望村一带。包括石介墓在内的石氏祖茔即在该村北。北望村位于徂徕山西麓的平原地带,汶河从西边流过,土地低湿肥沃,虽时有水溢之害,但还是颇利于农业生产。石氏从石光前到石介高祖石逵和其曾祖辈七人,一直未曾析居,因劳力既足,又专力务农,故蓄积日增。
为在五代乱世中保全身家性命,石介诸曾祖练习骑射格斗,逐渐成为能够保卫乡里的一方土豪。后晋开运三年(946)夏四月,“河南、河北大饥,殍殕甚众,沂、密、兖、郓寇盗群起,所在屯聚,剽劫县邑,吏不能禁。兖州节度使安审琦出兵捕逐,为贼所败”。(2)《旧五代史》卷八四《晋少帝纪四》,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修订本,第4册,第1294-1295页。流寇不怕官军,对石家却有惧意;面对“吏不能禁”的数千流寇,仓促应战的石氏家族奋力一战,虽有不小损失,但还是杀其数百人,其实力之强可见一斑。
石氏随时势变化积极谋求仕进,以维系家族地位。五代时,石氏族中有些“敏有材力,习战尚勇”者就投身到藩镇帐下充当亲军或低级军职。石介之四祖父石洪为后晋天福年间兖州节度使桑维翰的亲军厅头军,四曾祖石路岩先后在兖州节度使安审信、后汉泰宁节度使慕容彦超、后周兖州防御使索万进帐下任职。由于北宋偃武修文,石氏家族遂开始重视子弟的文化教育。石介曾祖父路真让孙子石丙随乡先生学习儒家经典。石丙精通三家《春秋》学,大中祥符五年(1012)中第。石介早年更是积极求学,天圣八年(1030)中进士。
后周显德五年(958),石氏分家。当时石介曾祖辈七人,因曾祖第六房无嗣,与第五房合为一院,共分六院。后第四房绝嗣,成为五院。北宋康定二年(1041),第一院分六院,第二院分三院,第五院分四院,第七院分二院,第三院因人丁不旺未能扩大,仍是一院,由此共十六院。该家族经过唐末到北宋前期150年的发展,已形成了较庞大的宗支结构。
二、北宋前期徂徕石氏家族制度的建设
徂徕石氏家族制度的建设是从整修祖茔开始的。庆历元年(1041),石介称石氏“自高祖以降至于六世孙七十丧,咸未改葬”。(3)石介撰,陈植锷点校:《徂徕石先生文集》卷一四《上王状元书》,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68-169页。这里不是说逝者都未下葬,而是未能按礼制安葬。当时的宋人入仕后,基于光宗耀祖、父以子贵之观念,往往会按照身份等级将先祖重葬于祖茔。(4)参见陈植锷:《石介事迹著作编年》,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106页。石介之父石丙经营30年,至其离世仍未完成,便将事情托付给石介。石介四方奔走哀告,筹措葬资,历时17个月,方于庆历元年八月完成其父遗愿。在这一过程中,石介围绕祖茔及祖先祭祀进行了一系列家族制度的建设。
第一,改葬族人于祖茔,完善墓祀制度。庆历元年八月,石介在《石氏墓表》中称:
石氏食此田百有五十年矣,葬此地九十有年矣,自始祖至圭八世,能不失故田,能奉祭祀。今举曾王父而降为三十二坟,用康定二年辛巳八月丁丑八日甲申归于大茔,以附始祖、高祖、曾祖。
石介将其曾祖父以降七十丧合为32坟,附于“大茔”(祖茔)。石介应当只是祖茔整修活动的发起者和组织者,祖茔整修是整个宗族的活动,由此可将族众团结在一起,达到“收族”的目的。石介还对祖茔进行了修整,确立了其范围,补种树木,使之显得十分壮观。他还强调“岁时则与十六院大合祭焉”,并要求子孙世世遵守“祭之以礼”的祭祀制度。这种集合石氏十六院子弟共同祭祀先祖的活动定期举行,可将族众紧密团结在共同祖先的周围,加强族人之间的联系,增强族众的认同感,是收族的重要手段之一。
第二,创建祭堂。庆历二年(1042),石介说:“石氏既用康定二年辛巳八月八日举大王父以下为三十二坟,葬于祖茔,复立祭堂于宅东北位。葬之以礼,祭之以礼也。”(5)石介撰,陈植锷点校:《徂徕石先生文集》卷一九《拜扫堂记》,第235-236页。石介将族人改葬祖茔后,又在住宅东北位置设立了祭堂,时间在庆历元年十一月十七日。石介所作祭堂实际上是在前代家庙基础上演变而来的。根据周代礼制和前代法令,担任节度掌书记的石介只是从七品,不具备设立家庙的资格,但其又非庶人,不能“祭于寝”,于是在综合斟酌古礼、神道及人情的基础上,对传统礼制加以变通,在住宅东北创立了祭堂三楹,“以烈考及郭夫人、马夫人、刘夫人、杨夫人、后刘夫人居焉。荐新及于烈考五夫人而已,时祭则请皇考妣、王考妣咸坐”。(6)石介撰,陈植锷点校:《徂徕石先生文集》卷一九《祭堂记》,第234-235页。此祭堂与唐代建于住处之外甚至是京城的家庙有所不同,与明清时建于住处之外的宗族祠堂也有区别,(7)王鸣鹤等:《中国祠堂通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115-116页。是唐代家庙到明清宗祠之间的一种过渡形态。祭堂平时只是祭祀父母,遇重要祭祀时,则同时摆列曾祖父母、祖父母之位。
第三,创建拜扫堂。石介于庆历二年三月撰有《拜扫堂记》一文,追记前一年祖茔拜扫堂的创建,他说:“岁时必上冢,出必告于墓,反拜于墓,则皆有祭,不可以无次设。乃直茔前十四步为堂三楹,一以覆石,一以陈祭,总谓之拜扫堂云。”(8)石介撰,陈植锷点校:《徂徕石先生文集》卷一九《拜扫堂记》,第235-236页。此“拜扫堂”实即为墓祭提供方便的墓祠,建于茔前,为堂三间,以一间遮盖墓表,以一间陈设祭祀。墓祠原来流行于汉代,东汉末年开始衰落。魏晋至隋唐时期流行家庙,墓祠极为少见。石介在新宗族制度创建阶段庙制不完善的情况下,创建墓祠拜扫堂,在当时是有开创意义的探索与实践。
第四,立石以记谱系。石介在《拜扫堂记》中称:“石氏从周得姓逮于今,二千有余年矣。自沧徙居至于今,百五十有年矣。祀远,唯介之烈考能谈其谱,讨源及流,实为详尽。小子尝受之烈考,终不有识,大惧坠落。又为石高五尺,广二尺三寸,厚一尺,列辞二千三百六十八字,表于墓前,以传千万世。”(9)石介撰,陈植锷点校:《徂徕石先生文集》卷一九《拜扫堂记》,第235页。可知石氏世系尤其是石光前自沧州迁至奉符县(即唐乾封县,北宋大中祥符元年改名)后的世系只有石丙能够讲清,石介从其父那里掌握了家族世系,但担心日久遗忘,于是刻石以记,即《石氏墓表》。该文首先粗略追述了前代石氏名人,以提高家族成员的荣誉感;接下来详列迁至奉符后的世系,作用相当于后来族谱中的世系表。在北宋“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阀阅”的形势下,族谱失去了选官等方面的功能,改以收拢族人和辨明亲疏为目标,尤其注意祖先世系之考证,略远详近。(10)参见王善军:《宋代宗族和宗族制度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14-15页。《石氏墓表》即是如此,对徂徕石氏自始迁祖以降的世系记述得十分详尽。与一般族谱不同的是,《石氏墓表》还记录了石氏诸女及其夫婿的情况,追述石氏先贤却极为简略。
总之,北宋前期徂徕石氏家族制度的建设是在石介主持下围绕祖茔及祖先祭祀进行的,此举使该家族初步具备了家族组织的若干基本要素。石介先是将数代族众按礼制祔于祖茔,并对祖茔进行整修,又在祖茔刻石记录石氏世系,还立拜扫堂以覆盖之,既有效解决了“风雨燥湿,石久必泐,字久必缺”的问题,又可发挥墓祠的作用,为祭祀提供便利。至于祭祀制度,除规定岁时墓祭外,石介还颇具开创性地修建了祭堂,成为唐代家庙到明清宗祠之间的过渡性设施。
三、徂徕石氏家族制度建设的意义
石介支持的徂徕石氏的家族制度建设出现在庆历元年以前,一些做法是颇具开创性的,在北宋新宗族制度的创建过程中具有重要意义。
唐末五代时,战乱连年,家庙制度被破坏,“公卿大夫之家岁时祠飨皆因循便俗,不能少近古制”。(11)韩琦:《安阳集》卷二二《韩氏参用古今家祭式序》,《宋集珍本丛刊》第6册,北京:线装书局,2004年,第490页。所谓“便俗”,就是“祖祢食于寝,侪于庶人”,(12)司马光:《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七九《文潞公家庙碑》,四部丛刊本,第9页b。公卿士大夫同平民一样,四时祭祖于室内。宋初亦是庙制不立,但到仁宗时,新兴的士大夫群体势力迅速发展,迫切需要建立新的庙制。虽从庆历元年十一月开始允许文武官员仿效唐制设家庙,但营建家庙仍只是少数高级官僚的特权。汾州介休人文彦博于嘉祐元年(1056)造家庙,往往被认为是北宋家庙建设的开端。实际上,此前已有石介等一些官僚士大夫对新的庙制进行了探索。咸平年间,淄川人王樵到契丹寻访被掳掠的父母,“累年不获,还山东,刻木招魂以葬,立祠画像,事之如生”。(13)《宋史》卷四五八《王樵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点校本,第38册,第13439页。天圣六年(1028)前后,官员任中师在家乡曹州住宅之侧起作新堂,共有三室,名曰“家祠堂”,“以是升画像而荐岁时”。该祠堂中室供奉任中师之父亲,东室供奉其母,西室供奉其兄长任中正及夫人张氏,其弟任中孚和任中行分别处于侧位。任中师建“家祠堂”,也是因为家庙制度“废于五代之兵兴”,当时人“用常所器服而又祭之于寝,盖亦不知事神之道,使士君子之祭疑于匹庶人之祭”。(14)穆修:《河南穆公集》卷三《任氏家祠堂记》,四部丛刊本,第5页a。前代家庙多设于京师,而任中师所建在其乡里,故不叫家庙,而称“家祠堂”。
任中师所建家祠堂与石介建立的祭堂在创建原因、形式等方面均有相同之处,都是为了与前代家庙制度相区别,但又是在家庙制度影响下出现的祭祀设施。这些都是北宋颁行家庙制度前的有益探索和实践,在祠堂形式上开启了家庙向宗祠的过渡,也得到了当时人一定程度的认可,郓州人穆修就认为任中师的家祠堂“适事中而允时义”。(15)穆修:《河南穆公集》卷三《任氏家祠堂记》,四部丛刊本,第6页a。它们之间也有不同,具体表现在祭祀对象上,任中师的家祠堂与王樵所立祠堂只祭及父辈,而石介的祭堂更进一步,祭及曾祖,在某种程度上开启了宋代士庶均可祭祀三代及以上祖先的先例。
学界往往基于明清以来南北方宗族发展的实况,强调江南的宗族组织形态远较北方发达,具体到宋代,或认为北方地区宗族形态相对松散,在新式宗族组织形态建设方面明显落后于南方地区。(16)参见王善军:《宋代宗族发展的区域差异及其原因》,《安徽史学》2013年第1期。实际上,这些认识缺乏对宋代以后新宗族制度建立过程的通盘考察,具体到宋代新宗族制度的创建阶段尤为不妥。如前所述,宋代华北官僚士大夫对新庙制的探索在很大程度上是走在全国前列的,在新宗族制度创建阶段,华北在某些方面并不落后于南方。任中师、石介等人于庆历初年以前就在京东地区对祠庙及祖先祭祀制度进行了探索,稍后的范仲淹于皇祐二年(1050)在苏州创设族田义庄,欧阳修于皇祐年间创修《欧阳氏谱图》,苏洵于至和年间创修《苏氏族谱》,这些做法可看作是北宋官僚士大夫分别在不同地区,从祠庙及祖先祭祀制度、族田义庄制度和谱牒制度等宗族制度的不同侧面,对新宗族制度创建进行的探索和实践,它们共同推动了新宗族制度的建立。
北宋前期的华北地区对新宗族制度创建的探索和尝试与当时华北学术文化的变革尤其是儒学复兴是同步的。穆修与石介都是古文运动的推动者,主张文风变革。王樵是仁宗庆历以前活跃于京东地区的“东州逸党”的重要成员,博通群书,治学上表现出“不治章句”等倾向。以石介为实际领袖的泰山学派是宋代新儒学创建阶段重要的推动力量,文彦博、范仲淹等都与之关系密切。总之,开拓创新是北宋前期华北学术文化较为突出的特征,宗族制度方面的探索也应视为这种创新的一个组成部分。
北宋前期华北官僚士大夫从祠庙或祖先祭祀入手对新宗族制度进行探索,或许还受地域社会文化传统的影响。战国时,民间墓祭已形成了一定的传统,汉代流行建墓祠,华北尤其是山东地区尤其突出。今存汉代墓祠均出现在山东,分别是山东嘉祥的武氏祠和济南市长清区的孝堂山石祠。田野考古中也多有这种发现,如汉安元年(142)的邹城北龙河文通祠堂,永兴二年(154)的东阿芗他君祠堂,永寿三年(157)的嘉祥宋山许卒史安国祠堂……石介在当时庙制不完善的情况下,继承山东地区的社会文化传统,创建墓祠“拜扫堂”,对金元时期山东宗族的发展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北宋时,华北一带对祖茔营建和祖先祭祀尤其重视。官至兵部尚书的曹州人任中正,临终前深感遗憾者就是未能完成祖茔建设,将其事郑重委托给其弟任中师。安阳人韩琦从嘉祐年间开始数次寻找前代祖茔,并对其祖父以下的茔地进行了精心设计,多次亲往祭祀,到熙宁时还参酌多种礼书编成《韩氏参用古今家祭式》,后人多用之。(17)参见符海朝:《韩琦祭祀活动与祭祀思想之探讨》,姜锡东、李华瑞主编:《宋史研究论丛》第10辑,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402-419页。石介去世后,其妻子饥寒交迫,韩琦与富弼捐俸买田以救助之。这些本为救助石介子孙生活的土地后来成了石氏“永世之祭田,收其入以奉馨香”,(18)《徂徕石氏宗谱》撰修委员会:《徂徕石氏宗谱·祭田叙》,2017年,第52页。这也可反映出对祭祀的重视。华北宗族对祖茔与祭祀的重视不仅受地域文化传统的影响,而且深刻塑造了后世南北方宗族的差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