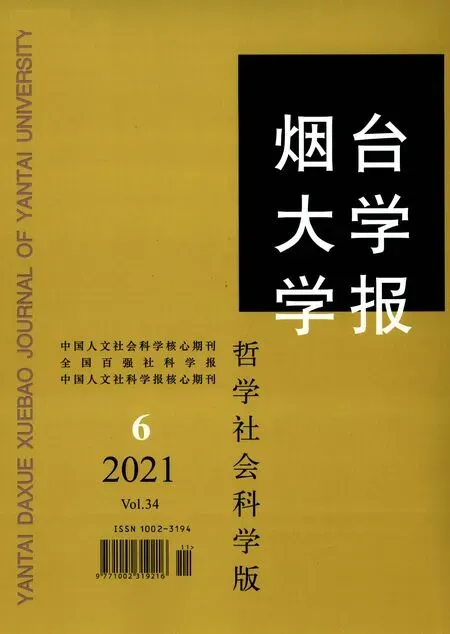中国的“北方宗族”与宗族的“北方类型”
2021-11-30钱杭
钱 杭
(上海师范大学 历史系,上海 200234)
千百年来,中国宗族的组织形式、功能种类从来都要随着外部制度环境的变化而变化;无论是南方还是北方,宗族组织及功能的形成、发展、完善、消失、更新、替代、转型,始终都是通例,更是与时俱进的常态,任何一种具体功能、任何一个阶段性表现都不能构成“中国宗族”这一总类之下的独立类型。根据这个观点,凡位于中国北方地区的宗族,虽然都可称为“北方宗族”,但由于其具体功能往往同时见之于南北方各地,因此并非任一“北方宗族”的任一行为都可自然地归入“北方类型”,还须据其具体功能进行研究后方能确定。
与宗族具体功能不断发生的阶段演变、局部调整相比,“类型”具有基础性、综合性和稳定性特征,其核心内涵,是指宗族世系学的实践形式和标志。(1)有关中国宗族的基本规定及世系学实践形式和标志,可参见拙著《宗族的世系学研究》第三章《宗与世系》的表述:“中国宗族是以父系单系世系为原则构建而成的亲属集团。它以某一男性先祖为‘宗’,以出自或源于一‘宗’的父系世系为成员身份的认定标准;所有的直、旁系男性成员均包含其配偶。在理论上,宗族的基本价值表现为对共同认定之世系的延续和维系。作为社会性组织之一种,宗族成员的范围在实践上受到明确限定。”钱杭:《宗族的世系学研究》,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3页。如果研究者通过对文献的广泛收集和准确解读,能够证明在一个较长时段内某些宗族确实存在与其他宗族不同的世系原则和表达方式,(2)“世系原则”是指对祖先及宗亲范围的认定原则。“表达”(representation)有三层含义:对事实真相进行的或符合或背离的描述;对事实的理想化;描述与理想的深层构成逻辑。参见黄宗智:《民事审判与民间调解:清代的表达与实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中文版序”,第1-2页。在学理上也能大致归纳出清晰的原则框架(包括形成背景、中心概念、逻辑起点),就可将其称为中国宗族的某一“类型”。至于能否以“区域”命名,则取决于两点:一是资料的覆盖范围,二是问题的展示程度。在逻辑上,“类型”的存在应可超越“区域”的划定“空间”(space)。很明显,发现和比较南北方宗族某类具体功能的异同固然重要,但根据中国宗族的基本原理,找到足以象征北方有而南方无的世系原则和表达方式,则更为重要。正因如此,“宗族的北方类型”,应该比“中国的北方宗族”具有更深更广的学术内涵,即使在地理上超越“中国北方”的界域也是可以成立的。
明清以来,广泛分布于中国东南地区(以下略称“南方”)的宗族,其物化要素、组织结构、功能种类、活跃频率等,无一不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以致被当成一个男系亲族组织的“完美(卓越)”标本,用以说明“中国社会统合力的基础”。(3)斯波义信:《解说》,见M.弗里德曼著,末成道男等译:《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附篇”,东京:弘文堂,1991年,第236页。若以此为准绳,秦岭—淮河以北、内蒙高原以南,包含中原在内的广义北方地区(以下略称“北方”)宗族的发展程度,显然只能被认为属于“非典型”“残缺型”,至少是“不发达”“不完备”一类。但是,与南方宗族相比存在差别本身并不是什么问题。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许多中外社会史学者通过广泛收集、细致爬梳各类史料,对明清直至当代中国北方宗族的组织结构、祠堂仪式、谱牒编撰、族墓体制、节庆祭祀、宗教信仰、冲突协调、生产合作、生产互助进行了系统研究,发现在战乱频仍、人口流失、政治高压、经济中心南移的大背景下,北方宗族的日常功能在很多方面都呈现出明显的弱化、淡化甚至隐形化趋势;但与此同时,宗族传统、宗法观念的持续存在,一旦激活亦能获得积极响应和广泛参与的宗族文化活动,也是可以观察到的客观事实。这说明,如就组织形式和功能种类而言,南北方各地的宗族都在发生变化,只不过变化的节奏、侧重的内容各有不同而已;若据此建构起所谓区域类型,既不恰当,也无必要。近年的社会人类学和历史人类学田野调查也指出,北方各地凡有需要且具备基本条件者,宗族活动都可以达到非常活跃的程度,甚至可超过南方宗族的一般水准。比如出于众所周知的政治与社会原因,南方宗族于上世纪60年代初普遍进入隐形状态,而位于中原地区的河南省却有逆势而上的情形,从1961年至1963年4月的短短两三年间,在河南全省108县中,有“九十个县……续家谱一万多宗”,(4)《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6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301页。若以整数计,平均每县续修家谱竟达111宗(种、部)。(5)此数据见于中共河南省委为进行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而统一部署的“九十个县三级干部会议上揭发的材料”(《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6册,第302页),一直被用于证明北方宗族功能中“家谱编撰”一项的阶段性表现强度,但实际上此数肯定有问题。如此大的规模不仅在当时很难达到,即便衡之以中国谱牒的总体发展态势,以及与改革开放后河南省所修新谱的数量相比,也很难令人置信。详见钱杭:《60年代初的河南新谱——以〈前十条〉附件中的“河南报告”为中心》,《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6期。不仅家谱编撰如此,宗族主要功能如族墓体制、祠堂建设、仪式规则等,同样可以观察到“彼伏此起”的现象,这就说明,希望从功能差异中概括出宗族的区域类型将面临一系列困难。
以下,笔者将通过一个特殊的视角来讨论宗族的区域类型,以抛砖引玉。
清康熙初,师从著名经学家毛奇龄的萧山举人张文檒,用“宗族分支,北方称门,南方称房”12字,概括了南北方宗族对“分支”的不同称呼。(6)张文檒:《螺江日记》卷8《房支》,《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100册,济南:齐鲁书社,1995年,第83页上。虽然北方宗族在“称门”的同时也有大量“称房”者,但南方宗族除了“称房”外确实没有或极少看到“称门”的案例。这就从逻辑上建立了一种可能性:张文檒也许已在一定程度上为建构宗族之区域类型,展示了一条“北方所有、南方所无”的重要线索,如果深究下去,或可有重大收获。但为什么只称其为“可能性”?因为在张文檒笔下,“门”只是北方人对“宗族分支”的一种地方性称呼而已,他没有主动暗示,更没有积极尝试,去揭示“门”是否还有其他复杂内涵。在地域广袤、方言众多的中国,同一事物存在区域性“别称”本为司空见惯之事。文人的标准做法即如东汉扬雄撰著《方言》那样,“类集古今各地同义词语,大部分注明通行范围。取材或来自古代典籍,或为直接调查所得”,(7)扬雄撰,钱绎笺疏,李发舜、黄建中点校:《方言》,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前言”,第1页。所获成就,可为进行汉语方言词汇的比较研究提供重要的历史资料。然而若不详加注疏,反复说明,“古今各地同义词语”的汇集本身充其量只是编成一部方言词典而已,撰集者的辛苦工作并没有为人们指出进一步思考的方向,诸如“别称”何以形成?“别称”所指是否单一且始终如一?“别称”是否另有深意?……张文檒的问题就在这里。他在提供了有可能推动区域类型研究的重要线索后却又戛然而止,没再往前迈进一步。这样一来,一个敏感发现和重要创见,却与希望找到“不同的宗族世系学实践形式和标志”这一目标失之交臂了。
近年来,国内外中国宗族史研究者已注意到“北方称门”现象的真实性和普遍性,但能否为实现建构宗族区域类型的目标提供继续前进的关键线索,还需要学者有效揭示问题的核心,努力超越张文檒的思路。2004年,秦燕、胡红安在陕北64种新旧族谱基础上,概括出清代陕北宗族的内部结构,具体析分为“家(家庭)—门(房支)—族(宗族)三个不同层次”。(8)秦燕、胡红安:《清代以来的陕北宗族与社会变迁》,西安:西北工业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66页。兰林友也指出,明清时期晋冀鲁豫京津地区宗族组织的“最小单位是家庭,其中间形态是房(支、门),或派、牌、柱”。(9)兰林友:《论华北宗族的典型特征》,《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期。很明显,三位学者所展示的大体就是张文檒的思路,所引资料中的“门”,因此被直接处理为“宗族分支”的北方别称。之所以如此,首先是因为他们接触到的与“门”有关的样本还不够多样化,其次是或与长期以来研究者对中国宗族世系观念所具一致性和普遍性的强调,降低了对各区域间可能存在某些差异性的敏感程度有关。否则以他们的学术功力,不会不注意到当地人明明可以把“分支”称为“房”,为何还别出心裁改称其为“门”。
另有一些学者通过展示的资料(当然也未达到典型程度),开始把房、门理解为两个不同的学术范畴,从而初步涉及到并有可能启发读者去深入探索房、门两称不同的发生原理和深层差异。1988年,杜赞奇(Prasenjit Duara)在研究著名的满铁《中国农村惯行调查》时,发现了许多重要资料,如河北省邢台县农村宗族中由“已分家立业的胞兄弟或堂兄弟组成”的“门”,栾城县寺北柴村郝氏宗族“分为5门……刘氏一族亦分5门,赵氏分3门”,昌黎县侯家营村“侯姓分为3门”,等等。(10)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王福明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85-89页。1990年,孔迈隆(Myron L. Cohen)详细讨论了他在河北保定杨漫撒村的收获。据记录,该村有19个家族,其中的胡氏家族由75个家庭构成,胡氏男子直接用“‘四大门儿’(字面意思为四扇大门)即‘四大分支’来称他们家族的四大部分。每个大门都可以追溯到在杨漫撒定居下来的四兄弟之中的一个”,(11)以上引文见孔迈隆:《中国北方的宗族组织》,夏也译,载马春华主编:《家庭与性别评论》第4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161页。也就是认四兄弟为现存胡氏宗族的开基始祖。在杨漫撒村,由兄弟后裔构成的宗族还有许氏,但许氏宗族成员并不将这个渊源称之为“门”,而称之为“支”或“派”,称“门”的宗族只有胡氏一个。2010年,韩朝建研究了山西代州鹿蹄涧村的杨氏宗族。该族始祖是北宋杨业,至明初旭、聚、彬、明、肃时,宗族出现分化,旭、明2人留在代州,聚、彬、肃3人迁居外地。旭、明各有4子,构成代州杨氏“八门”。明代推行编户齐民后,“八门”遂为“鹿蹄涧村杨氏的基本构成”。(12)韩朝建:《“忠闾”——元明时期代州鹿蹄涧杨氏的宗族建构》,《历史人类学学刊》(香港)2010年第8卷第1期,第46页。2013年,李永菊也注意到明代河南归德府叶氏宗族始迁祖叶受有二子,分立为长门、二门。据所引商丘《叶氏家乘》乾隆年“旧序”:“吾家自始祖传至二世,一为长门,谱系残缺无考。二门传至四世祖,同胞四人,一无嗣,其三祖分东、西、中三门,此谱固中门之裔也。”(13)李永菊:《从军事权贵到世家大族——以明代河南归德府为中心的考察》,《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4期。2017年,任雅萱根据明代山东中部山区莱芜县宗族的资料指出:“亓世能有两个孩子,分为两‘门’”,“莱芜县芹村吕氏,自三世祖分为大门、二门、三门、四门、五门(明初占籍情况不详);港里吴氏自明洪武年间迁至莱芜县,占军籍,自二世而门始分,按照二世祖的名字命名为大纲门、天赐门、朝佑门;益都县颜神镇康熙朝大学士孙廷铨孙氏,明初占匠籍,自四世分南、北二门,自七世北门又分前、后两宅。”(14)任雅萱:《分“门”系谱与宗族构建——以明代山东中部山区莱芜县亓氏为例》,《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7年第2期。任雅萱在新的文章中指出,明代山东莱芜县亓氏宗族中的“门”是一种为了应对赋役进行的联宗行为,已经超越了宗族内部原有血缘的分化,而是联合的过程,意味着“宗族”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想象因素。见任雅萱:《大户与宗族:明清山东“门”型系谱流变与实践》,《史林》2021年第1期。2021年,田宓介绍了内蒙古地区汉人家谱中的“门”,如曲国贤、曲国孝兄弟二人移居口外沿河村,曲国贤生子曲富银,后回内地,曲国孝则定居口外。曲国孝生子曲富成,曲富成生五子,分为长、次、三、四、五门。(15)田宓:《近四十年来内蒙古土默特地区蒙汉家族的系谱编修与族际交往》,《民俗研究》2021年第2期。
在这几位学者的研究中,部分宗族所称的“门”虽然也常常被使用于“宗族分支”的场合,但只要细心阅读他们引证的资料,就可发现,这些“门”从发生时已与“房”表现出了重要差异:构成“门”之起点的,一定是几位具有同胞关系的平辈兄弟,而不是展示约束关系的异辈父子;诸“门”一旦分立,位于诸“门”之前的若干位上辈尊亲即可淡出祖先世系,从而导致对世系的往上追溯几乎及“门”而止,而分“门”之后世系的向下延续、向旁扩展则不受任何限制。这可以说明两点:第一,我们不能像张文檒那样,把北方宗族之“称门”与南方宗族之“称房”在所指上等而视之,仅理解为对“宗族分支”的两个同义别称;第二,在理论上,房、门显然是两个不同的范畴,分别代表了基于父子或基于兄弟两种不同的世系学原则。用孔迈隆的说法,杨漫撒村胡氏家族的“门”,主要是基于“谱系分支”(genealogical branching)的一种“新的亲属体系计算方式”,它与南方宗族常见的基于“非对称性裂变”(asymmetrical segmentation)的“房”,构成了两种不同的亲属关系模型。(16)“非对称性裂变”又译为“非对称性分支”,相关词汇还有“不对称继嗣”(asymmetric descent)等。对南方宗族“著名的非对称性裂变”更早、更详细的分析,可参见F.弗里德曼:《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之八《宗族内部的权力分配》,刘晓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88页。孔氏的定义虽然还有些问题,但所作的结论则很有启发性,他说:“在中国北方,这两种亲属关系模型可以在同一个宗族共存……杨漫撒村宗族的主要特征表现为父系亲属固定谱系模式和父系亲属团体模式共存。”(17)孔迈隆:《中国北方的宗族组织》,夏也译,载马春华主编:《家庭与性别评论》第4辑,第160-162页。所谓“父系亲属固定谱系模式”,意指基于世代自然延续的世系表达,接近于“大宗世系”;“父系亲属团体模式”,意指可发挥实际功能的世系范围,接近于“小宗世系”。很显然,孔氏称“固定谱系模式”为“新的……计算方式”并不准确。限于体例,这里不作展开,容另文讨论。就笔者的感觉而言,中国东南方的“同一个宗族”和同一个村落中,要出现“两种亲属关系模型”共存的可能性确实不大。因此,这种“共存”和他后面对族墓研究中发现的“兼容”,似乎的确可视为宗族“北方类型”的重要特征。此说是否能够成立,还有待对更多样本做更仔细的分析。
长久以来,纵向性的“族—房”模式,一直被认为是中国宗族的基本制度,具体包括男系、世代、兄弟分化、从属、扩展、分房等六大原则。(18)陈其南:《“房”与传统中国家族制度:兼论西方人类学的中国家族研究》,《汉学研究》(台北)1990年第3卷第1期。“房”的其他功能均派生自以上核心规定。位于“房”之上的“族”,意味着对各房支的聚合、收拢,即所谓“合房收族”。明清时期的族长、房长,尤其是后者,之所以能在实际生活中对宗族所在村落的公共生活、权力分配、冲突解决起着组织者、领导者和调解者的作用,(19)关于族长、房长在南北方村落生活中的实际作用,可参见仁井田陞:《中国社会的同族与族长权威——以明代以来的族长罢免制度为例》,《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第25册,1961年,第29-76页;钱杭:《十七世纪江南社会生活》第二章《江南的宗族与宗族生活》,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91-128页;黄宗智:《民事审判与民间调解:清代的表达与实践》,第52-132页。也是因为他在系谱上的位置及其对有关资源的掌控能力,足以决定其他平辈、下辈甚至上辈族人与这个纵向结构的关系。
“门”与“房”明显不同。据集中展示了“门”及门谱特征的山西沁县族谱所示,(20)参见钱杭:《沁县族谱中的“门”与“门”型系谱——兼论中国宗族世系学的两种实践类型》,《历史研究》2016年第6期。“门”在系谱的表达上有四个特点。其一,谱中可以有“门”,也可以没有“门”;“房”则为宗族自古以来所必有,即便谱中未见“房”字,族中仍然有“房”的事实。其二,“门”形成于兄弟之间,独子不成“门”,诸“门”不分立;兄弟既可一子分一“门”,也可多子合一“门”。“房”则体现了父子原则,独子须单立一“房”,同辈诸“房”必分立、独立。其三,兄弟诸“门”之序,可以不等于兄弟之序;同父诸“房”之序,则必与兄弟出生顺序相合。其四,“门”上下不对称地包容部分同辈分支,在大多数情况下,它是通过对兄弟不同的组合方式,在分支林立的同宗全图中形成一组新的世系起点,起点代表者称“门祖”或“门主”,可以与“房”及房谱的纵向性和分析性实现互补。(21)孔迈隆在杨漫撒村也有类似观察:“许家和胡家告诉我们……有几位兄弟就意味着这些兄弟和他们的妻子的坟墓构成了第二代的坟墓……由于都葬在公共墓园中,这一代的兄弟不能进行宗族谱系的非对称裂变,甚至也不能够分裂成谱系分支。……在中国东南部,原则上在谱系上任何一个点都可以通过裂变形成新的宗支。”见孔迈隆:《中国北方的宗族组织》,夏也译,载马春华主编:《家庭与性别评论》第4辑,第164-165页。
沁县宗族所立之“门”主要体现了系谱上的意义。虽然“房”的概念在沁县很少被提及,但沁县宗族兄弟间所立之“门”及所成之谱,与父子间所立之“房”并不构成排斥的关系,也没有在族内形成一级独立的功能性组织。在那里,“门”及门谱只是用一套不同于“房”及房谱的世系原则和表达方式提高了宗族的凝聚力。其具体表现,是从纵横两个方向,为有效整合同辈兄弟及其后裔提供充分的系谱依据,对可能发生的同姓联宗产生重大影响。笔者从山东莱芜地区的联宗资料中发现,当地并不是所有宗族都立“门”成谱。但由于立“门”的前提是要有若干位同父兄弟,自分“门”起,任何一“门”已不能单独存在,因此,只要由曾经立“门”成谱的宗族发起联宗,即可使参与者的“世系”和“居处”信息达到高度清晰化。这种清晰化,不仅体现在每位入谱者分属“某门某支”的世系位置清晰,而且体现在其当下所在的“某县某村”位置也极其清晰。(22)山东莱芜吕氏族谱续修委员会、吕恒超主编:《莱芜吕氏族谱统修大门大支之一族人村庄表》,《大门谱》第2册,2012年9月,第13页。在从未立“门”的房支之间,虽然也可以通过认定一位共同始祖来确定联宗的纵向起点,但“认定……起点”谈何容易,“门”外房支若与“门”内宗族联宗,势必付出更艰苦、更曲折的努力。(23)参见钱杭:《分“门”与联宗——读山东〈莱芜吕氏族谱〉》,载常建华主编:《日常生活视野下的中国宗族》,北京:科学出版社,2019年,第171页。关于这一点,南方各地的联宗已为我们提供了太多的案例。
总而言之,为中国宗族构建“北方类型”,并使其表现出理论上的特殊价值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需要在“大局观”的引领下,通过对中国南北方宗族各种特有范畴和标志的比较研究,(24)除了南方的“房”和本文的“门”外,可视为“特有范畴和标志”的,还有容、柜、股等。参见韩朝建:《华北的容与宗族:以山西代县为中心》,《民俗研究》2012年第5期;田宓:《近四十年来内蒙古土默特地区蒙汉家族的系谱编修与族际交往》,《民俗研究》2021年第2期。展现出新的样式、能力和手段。必须指出的是,虽然“中国北方的资料开辟了父系亲属体系研究的新领域”,(25)孔迈隆:《中国北方的宗族组织》,夏也译,载马春华主编:《家庭与性别评论》第4辑,第159页。但作为对中国宗族具体表现形式的学术性把握,任何区域类型都不具有可以取代或覆盖其他类型的资格。在研究方法上,更须提倡综合兼容,亦如常建华所说:“以往宗族研究重视功能与结构、制度与世系的思路仍在继续,近来的趋势是从功能向结构、从制度向世系的变化。大致上说,制度论与功能论相联,结构论与世系论结合。”(26)常建华:《明清北方宗族的新探索(2015-2019年)》,《安徽史学》2020年第5期。
在将来的宗族研究中,只要我们对“北方类型”的学术内涵达成基本共识,就可以进一步讨论这一“类型”在其他区域中的具体表现,从而实现构建“类型”的初心了。笔者对此充满期望和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