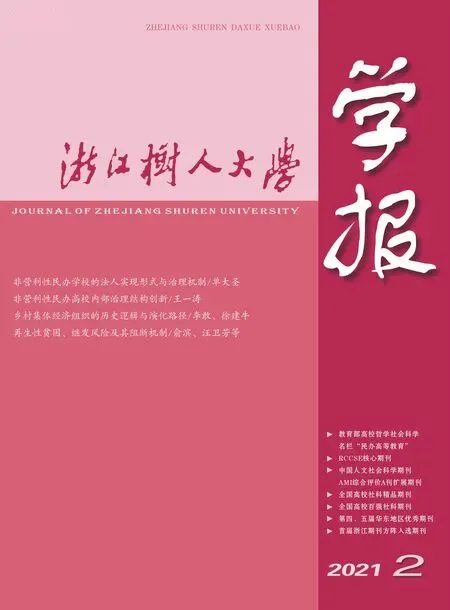南阳汉乐舞画像石与汉代乐舞思想流变
2021-11-30林涵
林 涵
(浙江树人大学 艺术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5)
南阳汉乐舞画像石作为丰富的传统文化艺术遗产,承载了多元思想,在当下图像学研究日渐凸显的学界,其有巨大的价值拓展与延伸空间。南阳汉乐舞画像石中的乐舞资料,是考察汉代生活审美及挖掘汉代独特乐舞思想特征和流变的有效切入点。南阳汉乐舞图像品类繁多,本文选择从画像石资料着手,考察其图像概况、图像元素以及蕴含的汉代乐舞思想的特征和流变,以期拓宽中国传统乐舞思想的研究路径。
一、南阳汉乐舞画像石资料及其图像解析
在中国传统乐舞研究中,古名、道具和画像石形象动作都是重要的评判要素,如朱青生《南阳汉画画面描述所用的术语与专词》中,根据要素对画像石舞蹈图像作的踏盘舞、七盘舞和盘鼓舞等三种乐舞类型的划分,可以说是对中国传统文献遗存中已有乐舞名称的判断和认定,已经具有了以图像对应文字材料的逻辑。其对“七盘舞”的记载和描述如下:三国卞兰《许昌宫赋》曰“兴七盘之递奏,观轻捷之翾翾”(1)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1223页;第769页;第764页。,陆机《日出东南隅行》曰“丹唇含九秋,妍迹陵七盘”(2)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华书局2017年版,第652页。,张衡《舞赋》曰“历七盘而屣蹑”(3)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1223页;第769页;第764页。。又如,张衡《西京赋》对盘鼓舞的记载曰“振朱屣于盘樽,奋长袖之飒纚”(4)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1223页;第769页;第764页。。这些都是对汉代乐舞形态最初的平面记录。
除去上述文献资料,南阳汉乐舞画像石中的乐舞图像是又一处关键的研究资源,目前可见材料主要有:河南南阳东关汉许阿瞿墓志画像石、南阳麒麟岗汉画像石墓宴饮图以及河南唐河汉冯君孺人(久)墓画像石等。除人类乐舞之外,南阳汉乐舞画像石中还存有祥禽瑞兽的舞蹈形象,在人类舞蹈和自然动物舞姿之间建立了同图同场的构图关系,成为人类乐舞的自然辐射和汉代天人关系、谶纬之学的体现,为汉代乐舞提供了拟兽舞姿原型。如南阳市王庄汉墓出土的《祥禽鹄鸟图》画像石,四前一后五只鹄鸟在云纹和星宿图像的围绕中展翅飞翔,说明“鹄”作为汉代重要祥禽之一,已大量存在于绘画、画像石等艺术世界中。
对上述画像石资料进行图像解析,是当下以画像石记录的汉代乐舞思想研究的基础。笔者在对前文所提及汉画像石进行研究的基础上,认为汉乐舞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的特征。第一,在舞蹈形式上兼具两性独舞、双人舞、对舞及三人舞,可以看出汉代乐舞的形式是随具体场合而定的,舞蹈动作有一足踏盘或一足踏鼓,抑或双足踏鼓等。第二,舞者在衣冠上体现了汉代铺排浪漫的文化风尚,如女性舞者在衣冠上多梳高髻、双髻或戴巾帼,以着广口长袖服装居多,又以双层袖为主,还有少数持巾而舞者;男性舞者则以介帻之冠为主。第三,表演现场通常是与宴饮、百戏、升仙等世俗生活相结合的,如荥阳河王水库汉墓保留了麒麟舞、火龙舞和铜器舞等场景,这些舞蹈贯穿墓室壁画的各种场景,舞者或独立表演,或几人组合,用到了琴、笙、竽、笛和琵琶等乐器,以生动的乐舞资料反映了中原文化对生死观的理解,也显示了汉代乐舞在日常生活领域的样态。第四,乐舞画像石图像与汉代社会文化的对应。汉代乐舞常与汉代百戏杂艺中的跳丸、角抵、叠案、掷剑等相组合,兼顾了民间大众化、世俗化舞蹈和宫廷宏大乐舞两种艺术风格,将宫廷和日常、世俗和升仙的多元文化内涵与时代精神相融合,具有广阔的艺术表现空间和艺术呈现场域。
二、南阳汉乐舞画像石的图像意义
以画像石为载体对汉代乐舞图像进行解读,是客观挖掘汉代社会生活、社会文化及民间信仰等信息的有效途径,在弥补史料缺失的同时,有效保留了文字难以传递的信息。因此,对图像的研究,是进一步解读历史文化信息的必要途径。
(一)生活舞蹈和艺术舞蹈的二元构成
无论是战斗舞、娱乐舞,还是农作舞、狩猎舞,其服饰、道具和音乐等形态均是对汉代社会日常生活的真实记录。但同时,舞者中的职业舞伎、俳优和巫师等的舞蹈模态非日常所有,其身体语言的表达进入了更深的层面,形成了特殊的艺术程式和技术体系,也拉开了世俗与艺术的审美距离。
(二)“世俗图”与“世俗舞图”的二相杂糅
汉乐舞画像石的图像存在“世俗图”与“世俗舞图”杂糅的现象,如渔猎图常与汉代山水田园艺术的发展相勾连。《弋射收获图》的上层有游鱼飞鸟、荷花卓荦,弋射者姿态优雅;下层则描绘收获的劳作场景。又如劳作舞,河南南阳方城东关汉墓出土的《阉牛图》中,龙腾、熊舞、公牛扬蹄以及胡人疾步如飞、挥刀阉割的力量感,共同形成了富有紧张感和审美效果的艺术空间。
汉画舞蹈中,羽人格斗舞、角力舞、力士舞和剑客舞等,也是画像石的重要展示内容,如南阳汉画馆藏《武士图》展现的武士舞姿、《蹶张图》中的蹶张形象、《平索戏车、车骑出行、荡舟、狩猎和舞剑格斗图》的舞剑格斗,均显示了汉代的尚武精神。南阳出土的《鸿门宴图》剑舞,既表现了世俗的礼尚往来,又呈现出儒家礼仪;郑州黄淮艺术博物馆藏《施礼四舞俑》、南阳王庄汉墓出土画像《祥禽鹄鸟图》等,则是汉画舞蹈中包含的公共社交类信息的集中反映。
此外,祥瑞舞与巫道舞则保留于汉画像石对宗教领域的记录中。如《踏盘长巾舞图》中的飞驰回望祥禽舞,舞伎与鹄鸟等飞禽共舞,姿态各异,仪态万千,具有汉代庄重而奔放的审美特征。《施礼四舞俑》则以舞者服饰、姿态、表情的区分,形象地展示了汉时舞者装束形态之繁多、艺术表现空间之巨大。
三、汉代乐舞思想的流变
南阳汉乐舞画像石记录了丰富的生活及主流政治的场景,但其更深层的蕴涵是汉代乐舞美学思想的呈现,因此是研究中国乐舞美学思想的重要资料。春秋战国时期,文化多元,百家争鸣,多种思想交融,为中国乐舞美学思想的多元化发展提供了可能。但值得玩味的是,乐舞美学并未因此得到蓬勃的发展,而是进入徘徊期,这种徘徊呈现出世情时序对艺术美学的制约与制衡。秦统一六国,建立大一统王朝,在实现大一统的同时,对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进行了调整,包括对文学艺术思想走向的强势施压,集中表现为文化高压政策,使乐舞美学思想遭受极大冲击:
至秦患之,乃燔灭文章,以愚黔首。汉兴,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迄孝武世,书缺简脱,礼坏乐崩,圣上喳然而称曰:肤甚阂焉!(5)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701页。
“礼乐”思想是儒学的内核,随着秦始皇焚书坑儒,乐舞美学思想亦随之淡褪,隐藏于民间。其甚者,连同“乐之为他者抑或自者”的哲学讨论一并湮灭。直至汉代,“礼乐”思想方在不断的积累与建构中得以复苏,彼时的“礼乐”思想,以儒家审美为主流,适应社会现实,是汉王朝政治需求的反映:
汉兴,拨乱反正,日不暇给,犹命叔孙通制礼仪,以正君臣之位。
汉承秦之败俗,废礼义,捐廉耻,今其甚者杀父兄,盗者取庙器,而大臣特以薄书不报期会为故,至于风俗流溢,恬而不怪,以为是适然耳……汉兴至今二十余年,宜定制度,兴礼乐。(6)班固:《汉书·礼乐志》,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030页。
由此可见,汉初立国后,社会渐趋安定,生产日益复苏,人民的物质生活得以保障,但依旧受到秦朝以来礼坏乐崩后遗症的波及,出现了一系列丧失礼义廉耻的社会现象。在这一背景下,社会诉求发生转变,大众由对秩序的渴求逐渐转向对“礼乐”的渴望,“礼乐”制度与文化逐渐趋于复兴。由于其系联着社会伦理与艺术审美两端,对两汉的文化思想影响深远。
具体来看,两汉时期的“礼乐”思想建立在汉武帝“罢黜百家,表彰六经”的经学思想基础上。经历时代更迭,经学在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的交替中发展,不断进行自我修正与改造。加之董仲舒“天人感应”的“宇宙—道德”本体论的理论支撑,儒家思想遂逐渐适应了汉代政治导向、社会秩序与伦理道德的要求,取代了汉初兴盛的黄老思想,成为社会主流,并由此逐步发展出一套完整的理论系统。随着新兴价值理论体系的产生,思想与学术方面亦随之作出调整,直接导致了经学与谶纬之学的兴盛,而“礼乐”制度中蕴藏着的儒学思想便在政治与伦理的双重系联下得以强化,成为制度的内核。
儒学以政治为依托,在思想界获得了权威地位,并在形式与制度的双重压制下逐渐走向极端。东汉章帝建初四年的白虎观之会,以法定的程式制定经学议题的相关标准,遂将这种形式化推向极致,而谶纬之学正是这种权威之下的一种表现形态。谶纬之学以神学精神为依托,神学精神则肇自董仲舒,在东汉时期达到鼎盛。从《春秋繁露》到《白虎通义》,正是谶纬之学发展脉络的体现,这条脉络中包含了浓厚的天人感应色彩:
占也者,先王所以定祸福,决嫌疑,幽赞于神明,遂知来物者也。若夫阴阳推步之学,往往见于坟记 ……至乃河洛之文,龟龙之图,箕子之术,师旷之书,维候之部,铃决之符,皆所以探抽冥阎,参验人区,时有可闻者焉。其流又有风角、遁甲、七政、元气、六日七分、逢占、日者、挺专、须臾、孤虚之术,乃望云省气,推处祥妖,时亦有以效于事也。(7)③范晔撰,李贤等注:《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703页;第1749页。
博通五经,兼明星纬,士之远来就学者,三千余人。③
董仲舒的“以德配天”,将“天”投射到儒家的伦常礼法制度中,而“谶纬之学”则强力勾连“人事”与“天象”,寻求两者间的平衡。由董仲舒到谶纬之学,“人事”完成了与经历儒家伦常洗礼的“天象”的对应,这一过程实质上是“人事”对董氏“天象”的妥协与顺应,而谶纬则起到了“正当性预置”的作用,即利用“天象”与“神性”的正统性,削弱理性思维与逻辑思辨的觉醒,再加之经历“焚书坑儒”的摧残,理性思维不堪一击。由此,在董氏“天人”体系的权威之下,“人事”与“天象”完成同构,辐射至汉代文化的诸多方面。而两汉“礼乐”思想便在儒学定于一尊、王权绝对化中生成,处处渗透着儒学影响下的痕迹:
后世衰废,于是后圣乃定五经,明六艺,承天统地,穷事察微,原情立本,以绪人伦,宗诸天地,篆修篇章……乃调之以管弦丝竹之音,设钟鼓歌舞之乐,以节奢侈,正风俗,同文雅……礼以仁尽节,乐以礼升降。(8)陆贾撰,王利器校注:《新语校注》,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19-30页。
礼乐者,何谓也?礼之为言履也,可履践而行。乐者,乐也。君子乐得其道,小人乐得其欲。王者所以盛礼乐何?节文之喜怒.乐以象天,礼以法地。人无不含天地之气,有五常之性者,故乐所以荡涤,反其邪恶也;礼所以防淫佚,节其侈靡也。故《孝经》曰: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移风易俗,莫善于乐。(9)班固撰集,陈立疏证:《白虎通疏证》,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93-94页。
两汉时期,先秦儒家所开启的音乐与美学思想被包裹在“礼乐”制度中,其在向社会核心领域迈进的过程中,逐渐丧失了话语主体的身份性及作为音乐的自觉性,取而代之的是与主流社会相适应的社会伦理属性,带有儒家浓厚的政治教化意味与社会关怀意识,与社会政治、人常伦理密切系联,反映了音乐为获取主流地位而与其“本性”“自性”的妥协。
但在不断的发展演进中,“音乐”随着“礼乐”在儒家伦常的教化熏陶下,逐渐将自身融入其中,成为与道统相磨合的典范,从而在道德上获得自我与官方权威的认同。一方面,“礼乐”的日益固化,甚至可被视为两汉盛世的体现,彰显着盛世的海晏河清。另一方面,“礼乐”唯有获取儒家制度与标准的认可,才可能获取合法存在的土壤,拥有继续发展壮大繁荣的可能性,而“音乐”也在这样的制约中受到儒家的牵引,具备了自我发展的能动性。在由先秦到两汉的平稳过渡中,“音乐”随着“礼乐”制度迁延,以顺从与应变的姿态进入儒家文化圈,逐步站稳脚跟,成为文化艺术领域的主流。
四、两个需要辨析的问题
南阳汉乐舞画像石承载了汉代乐舞思想及中原地区乐舞文化的信息,是探讨汉代宫廷雅乐与民间俗乐的重要资料。在前文讨论的问题之外,南阳汉乐舞画像石尚在以下两个方面具有启发作用。
(一)俗乐与雅乐
南阳汉乐舞画像石呈现了汉时儒家的乐论思想及其政治、伦理标准,其将音乐之“雅”与“俗”相对立,并试图将涵盖着伦理教化的神圣性植入雅乐,使之具备预置的正当性。而汉末至六朝,以“雅”“俗”之辨为契机,音乐的“自性”在主体意识渐趋被触发的觉醒中不断复苏。可以说,“雅”“俗”之辨所带来的思辨色彩为乐的审美自觉打下了理论基础,而“俗乐”也渐趋成为六朝审美艺术觉醒的载体之一,其所承载的情感保留了情感生发的原初状态,裹挟着质朴、坦率、真诚,迸发着鲜活的生命力量。这种原初状态,也在客观上触发了包括音乐在内的关于艺术审美觉醒的思考,对后世“主情”派、“性灵”派的发展影响重大。
在心理机制上,中西方对文学艺术的价值批判极其相似:西方在开启美丑“别异”之旅后,随着理性意识以及分析方法论的不断张扬,最终确立了美学中的“丑学”一支。而中国古代,“雅”“俗”之辨则是音乐艺术走向“和”的必然路径。中国古代乐舞思想创生了音乐审美的两个基本范畴:其一,在儒家作为绝对的话语主流之时,以“郑卫之音”为代表的“俗乐”在中原地区几乎丧失了存在的合理性价值,仅仅作为“雅乐”的对比与参照。随后,“郑卫之音”渐趋南下,与以南方文化为代表的楚文化相融合,逐渐形成了与北方中原文化相对峙的浪漫之音。其二,古代传统音乐美学的“雅”“俗”之辨,与古希腊时期“美善统一”的思想相接近。溯源观之,轴心时代,中国的孔子、荀子等儒家代表倡导“雅乐”,贬斥“郑声”,而西方的柏拉图,则将那些荼毒青年、殃及城邦的“诗人”驱逐出自己的“理想国”,两者共同彰显了以音乐为代表的艺术思想,并在生成与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受到社会主流赋予的各种意义,而音乐通过社会所彰显的现实性关照,往往高于纯粹的现象学意义上的学理分析。
(二)“乐之为乐”与音乐边缘化的悖论
由以上对汉乐舞画像石中所体现的中国乐舞美学思想的分析可以看出,音乐在逐渐觉醒并日益实现“乐之为乐”的独立性转型后,慢慢摆脱了儒家伦理纲常的束缚,其地位也相应地由中心向边缘转移。可以说,音乐“自性”与独立性的开始,也是音乐不断边缘化、民间化的开始。具体来说:从先秦到两汉再到六朝,音乐的社会地位经历了“隐—显—隐”的路程,而音乐“自性”则生成了“显—隐—显”的路径。造成这种现象的关键在于礼乐自身的定位。先秦两汉,“礼乐”为获取合法性而依附于儒家伦常,在与儒家的不断磨合中成为艺术的主流,其被依托于社会现实中,文化等级森严。至魏晋六朝,政治更迭,疾疫横行,民生凋敝,无论是士族还是平民,皆处于高压之下,人心惶惶,朝不保夕。这种危机感也对人的内心造成了强烈的冲击,唤醒了人对生命主体意识的自觉关注。而儒家主导的“礼乐”再也无法满足社会的普遍需求,逐渐丧失了现实性意义。于是用于满足个体情感表达的“自性”音乐日益壮大,并在六朝时达到巅峰。隋统一全国后,社会秩序不断得以恢复,儒家“礼乐”的缺失一点点被修补,开始了对六朝艺术美学的反思与矫正。
乐感文化作为中国文化的核心之一,在“诗乐舞”的传统下不断发展变迁,并与其他艺术形式相融合。乐舞甚至可以与绘画、书法等艺术相感通,以音乐之外的艺术形式来表现。而音乐与其他艺术形式的交互渗透,在弱化音乐作为艺术主流的同时,也在客观上推进了中国古代艺术的发展,实现了中国传统艺术的一次大转向。
南阳汉乐舞画像石中的乐舞资料,体现了汉代独特的乐舞思想及其流变,呈现出包含在乐舞之内的传统音乐对其自身定位作出的探索与发展。它徘徊于社会所赋予的职能性与自身的独立性之间,不断在矛盾冲突中作出调和修正,谋求独立的出路。这种矛盾冲突与调和修正,实质上是古代文化潜藏着的美学精神的自我冲撞与洗礼。而乐舞对自身定位的妥协与反省,也正与传统美学中的自我觉醒相契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