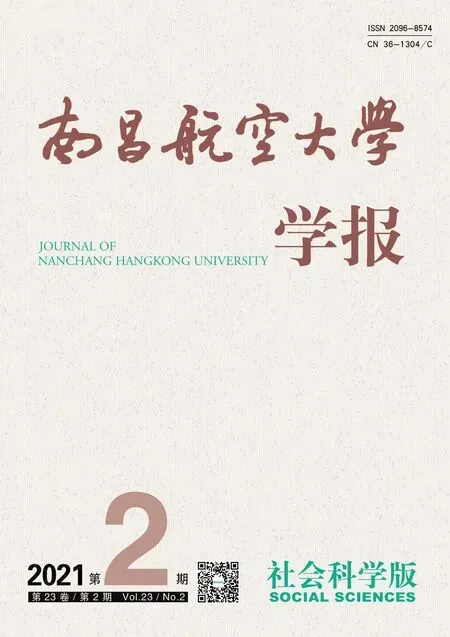生态翻译学视域下《我在故宫修文物》纪录片字幕翻译的多维适应与选择
2021-11-29闻惠敏
闻惠敏,万 涛
( 南昌航空大学 外国语学院,南昌 330063)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近年来,国际文化交流与融合日益加深。作为传播文化的一种有效途径,影视作品在我国实施“文化强国”战略进程中的作用不容忽视。纪录片更是成为了促进我国文化“走出去”的重要载体。纪录片 《我在故宫修文物》以全新视角走进古老故宫,摒弃宏大叙事,平实地记录了文物修复师的日常,近距离展现国家级文化遗产的技艺与传承人的修复工作和喜怒哀乐。该片不仅向观众展示了故宫收藏的稀世 “珍宝”,而且系统地介绍了我国文物修复的发展历史,揭秘“大国工匠”高超的文物“复活”技术,对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挥了积极作用。
在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进程中,翻译的桥梁作用不容小觑。翻译理论林林总总,其中,中国本土创立的生态翻译学理论受到广泛关注。2001年,清华大学胡庚申教授开始尝试将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学说”应用于翻译研究并阐述其可行性,进而提出了建立“翻译适应选择论”的构想。三年后,胡教授在专著《翻译适应选择论》中系统概述了这一新理论的产生背景、理论基础和基本内容。2006年,胡教授在以“翻译全球文化:走向跨学科的理论构建”为主题的国际会议上宣读了《生态翻译学诠释》一文,首次在国际学术场合正式提出了生态翻译学理论学说[1]。
生态翻译学“借助翻译生态与自然生态系统特征的同构隐喻,以生态整体主义为理念,以东方生态智慧为依归,以翻译生态、文本生态、‘翻译群落’生态及其相互关系为研究对象,从生态视角对翻译生态整体和翻译理论本体(翻译本质、过程、标准、原则和方法,以及翻译现象)进行综观和描述”[2]。
生态翻译学将翻译的“语境”扩展到“翻译生态环境”,并将其视为由语言、交际、文化、社会以及作者、译者、读者共同构建的整体。“它既是制约译者最佳适应和优化选择的多种因素的集合,又是译者多维度适应与适应性选择的前提和依据。”[3]生态翻译学探讨翻译过程中源语生态移植、转换为译语生态的规律,从而为源语文本解读和翻译策略选择提供新视角及理论依据。
翻译适应选择论作为生态翻译学的重要概念,将达尔文进化论中的“适应/选择”学说引入翻译研究,从“自然选择”“适者生存”的理论视角,提倡翻译过程应“以译者为主导、以文本为依托、以跨文化信息转换为宗旨,是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而对文本进行移植的选择活动”[4]。
本文以生态翻译学为理论依据,在分析字幕翻译特征的基础上,从“适应”与“选择”的视角,探讨纪录片字幕译者如何适应特定的影视翻译生态环境,在语言、文化和交际三个维度进行翻译适应和选择,帮助目标观众跨越语言障碍,最大程度获取源语信息,从而促进文化的传播和交流。
一、字幕翻译的基本特征
字幕翻译是文学翻译的一部分,但影视作品语言与一般文学作品语言风格迥异。“影视语言的特点在于其聆听性、综合性、瞬时性、通俗性和无注性。”[5]影片中人物的对白是瞬时性的,观众需要根据剧情发展和前后情景来推测影片所要表达的意思。鉴赏影视作品的群体,年龄结构和学历水平的不同,这就要求影视语言要符合大众的文化期待和审美情趣。影片中所涉及的中西方文化差异也对字幕翻译提出了要求,译者需挖掘语言背后的文化知识和内涵以提升译文的表现力。因此,字幕翻译主要具有瞬时性、口语化、文化性三大特征。
首先,字幕翻译具有瞬时性特征。“电影是一种声音和画面相结合的视觉和听觉的综合艺术形式。”[6]在观赏影视作品时,观众接收视觉信息的同时也接收听觉信息,这些信息随着影片的播放转瞬即逝。尤其是在欣赏国外影片时,要使观众听懂、看懂,字幕翻译至关重要。字幕必须与影片的画面、声音同步,这就要求译者需进行适当删减和转换。
其次,字幕翻译具有口语化特征。影视作品的语言主要以口语为主,简洁明了、通俗易懂,译文也应相应地体现口语化特征。观影时,观众需要根据剧情发展和上下文情境进行一定程度的推测,期待一遍就能听懂、看懂,因此语言的通俗易懂显得尤为重要。由于影片观众文化水平不同,社会阶层不同,要求字幕翻译应顾及译语观众的语言水平,以最简练的方式来准确传递源语含义,以符合大众的文化期待和审美情趣。
再次,字幕翻译具有文化性特征。中文影视作品中常出现大量成语典故、民谚格言、双关语、歇后语等文化知识,这对译者的文化素养和翻译能力提出了挑战。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如果不跳出语言层面之囿去挖掘语言背后所隐藏的文化内涵,译文的表现力就会受到限制,这必然导致观众对影片所传递的信息产生曲解或误解,译制片的艺术性和欣赏价值将大大降低。在字幕翻译中,若涉及文化负载词,译者需寻找恰当的技法加以处理。
影视作品主要通过银屏字幕和人物对白来传递影视信息。人物对白题材广泛,涉及生活的方方面面,诸如法律、政治、经济、文化、宗教、文学、艺术、体育、科技等,因此字幕翻译的综合性也增加了译者的工作难度。
二、字幕翻译的多维适应与选择
此前已有相关纪录片系统地呈现了紫禁城的建筑特征及美学价值。与这些纪录片不同的是,《我在故宫修文物》以平铺直叙的手法记录了文物修复师的日常工作,展现修复师的个人特点和精神世界。片中大量的人物对话和旁白涉及北京方言。受影片屏幕时空所限,每个画面的字幕不超过两行,且停留的时间不超过6秒。因此,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需秉持言简意赅原则,根据语境作出适当的翻译移植和转换,使观众结合影片的画面、声音、图像及人物动作等各渠道信息,理解影片传递的涵义。
“一部好的字幕不能拯救一部糟糕的影片,但一部质量低下的字幕肯定会毁了一部好影片。”[7]纪录片字幕翻译直接关系到国家良好形象的树立,这就为纪录片的字幕翻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翻译涉及语言的转换,而语言又承载着人际交往和文化交流的使命。因此,“语言、文化、交际有着内在的、符合逻辑的关联,这也体现了翻译转换的基本内容”[8]。语言、文化和交际三个维度的适应性选择与转换正是生态翻译学“多维”转换的主要概念。
(一)语言维的适应与选择
在语言表达方式方面,中西方存在着较大差异。因此,译者在了解纪录片字幕翻译的生态环境后,需仔细考究源语所表达的含义,并根据目的语读者的语言表达习惯,充分发挥译者主体性,适当调整词汇,转换语言形式,从而避免译文晦涩拗口,造成观众误解。
语言维的转换主要通过词类转换来实现。词类转换是指在一定的语境下,一个词临时改变了常用的词性,从某一词类转变为另一词类的现象。首先,词类转换依赖于一定的语境,大多数词如果不依赖上下文,便无法明确其词性,转换更无从说起。其次,词类转换是“临时”的。从词义上说,词一般包括临时义和固定义,从词类上说也有“临时类”和“固定类”。能进行词类转换的词显示的只是临时义,属于临时类。因此,词类转换是一个词临时、偶然发生的现象。
在所有的词类转换现象中,名词与动词的转换较为常见。汉语善用动词,呈现动态;而英语善用名词,呈现静态。翻译时需考虑英汉语言的不同特征,汉语中的一些动词需转换为英语中的非谓语动词、名词、介词、形容词、副词等。词类转换使得字幕符合英语的行文习惯,让外国观众对影片的理解与源语观众产生相似的效果和共鸣。
字幕翻译中还应注意抽象词与具体词之间的转换。“中国人重直觉与具象,而西方人重理性与逻辑”[9],这一思维方式的差异导致语言的差异。在翻译过程中,汉语中具体的表达方式需转换为英语的抽象表达方式,外国观众才可通过字幕理解影片内容,领略中国古典建筑和传统技艺的独特魅力。 《我在故宫修文物》中的翻译实例充分呈现了上述特征。
例1:我们就挑了这么一对儿比较大型的,另外一个破损也比较严重,本身也是亟待抢修,抢救性修复这么一对儿吧。
We picked this pair, for they are larger, and also because of their bad damage, needing urgent repair and restoration, repairing and restoration for salvage.
“抢修”为动词,译文中处理为名词词组“urgent repair and restoration”,符合英语的静态特点。 “urgent”一词突出了紧迫性,增强了句子的表现力,形象地表达了文物急待抢修的状态。“repair”和 “restoration”两词连用,其中,“repair”侧重于修理, “restoration”则更侧重于复原。译者使用两个意义相关的名词使译文清晰易懂,符合英语表达特点的同时,满足了字幕瞬时性特点对译文的要求。
例2:有那重彩,咱也不敢拿水这么招呼。
We will never use washing method directly on the heavy-colored works.
原文描述的是修复古字画时需用水对其表面进行清洁。由于外国观众不了解文物修复的具体方法和过程,直接译为“water”容易使得观众误以为文物修复步骤简单而草率。译者把具体的“water”转化为抽象的“washing method”,保证译文简洁明了的同时也易于外国观众理解,实现了语言维度上的适应和转换。
(二)文化维的适应与选择
字幕翻译不仅是要实现语言意义的转换,更重要的是让观众理解语言承载的文化内涵,实现两种文化之间的互动和交流,“即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关注语言文化内涵的传递和阐释,在译文中体现跨越文化差异的选择转换”[10]。原片中存在许多具有浓厚文化色彩的词语以及一些特殊的语言形式,加上字幕翻译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这就大大增加了影片字幕翻译的难度。
处理字幕翻译中文化信息主要遵循文化补偿、文化移植和文化协调三原则。任何纪录片的主题故事均发生在一定的文化语境中,观众只有理解了其中蕴含的文化才能更好地理解影片的主题。文化补偿原则旨在翻译时尽可能保留源语的文化特色,运用适当的翻译策略对原文中文化缺省的部分进行修复和补偿,以帮助观众对纪录片有较好的理解。而影视字幕翻译中的文化传递主要是通过文化移植和文化协调来完成的。
由于字幕翻译的瞬时性特点,译者无法完整地译出源语所蕴含的全部文化内容,且死译会使得译语字幕刻板生硬,造成观众理解困难。在文化移植原则下,译者需酌情舍去源语的部分文化特色,恪守本族语的表达习惯和行文规范,使字幕读起来较为生动地道,更容易被观众所理解和接受。不同的语言是不同文化发展的产物,反映其独特的文化底蕴。译者应通过文化协调和语言转换来尽可能减少源语和译语在转换过程中文化信息的流失,同时使译文适应纪录片语言生态环境,从而增强其生命力。
译者在处理字幕翻译中的文化信息时,须注意上述三原则的应用,让翻译字幕与影片画面有机结合,以达到文化交流的目的。由于字幕翻译受时空限制,缩略法在字幕翻译中十分常见。译者根据实际情况将无关紧要的信息压缩、简化,甚至删除,从而减少观众对信息的加工处理,使译文达到言简意赅的表达效果。除删减不必要的信息外,也可使用提炼法将语言中暗含的信息高度浓缩,便于观众理解纪录片传递的信息。
例3:真正咱们好的那个传统的东西,让你接笔完了以后,你根本看不出来。
But for us, with the real good traditional techniques, you can never tell after the restoration.
“接笔”又称补笔,是一种古字画修复技术。文物修复师在进行古字画修复时,不能仅凭想象来添加文字或补充画面,而是要根据原作所想要表达的意蕴或意境,将缺损之处依照字形画意添加笔画、线条或颜色,从而最大程度恢复其原貌。鉴于字幕翻译的特点和纪录片语言的生态环境,译者无法对 “接笔”进行详细的解释,而是提炼出源语的核心含义,舍去源语的部分文化特色,运用外国观众能够理解的“the restoration”一词,通过文化协调和语言转换来减少跨文化交流产生的障碍。
众所周知,中文常用四字词语表达形式。该形式整齐、语音悦耳、言简意赅。然而,英文并不具备这一表达特征。故在字幕英译时,译者需根据语境对四字词语进行释义、改编或再译,以符合译语表达习惯。
例4:你在这儿默默无闻的,一辈子就干这个。
But you will work here unknown to public for a whole life.
“默默无闻”意为做事无声无息、无人知晓,做了好事不声张、不图名利。该词出自 《晋书•祖纳传》:“仆虽无无,非志不立,故疾没世而无闻焉。”译者通过对这一词语和上下文语境的理解,将其释义为“unknown to public”。译文简洁晓畅,准确地传递出了源语对文物修复师默默奉献、不图名利的职业素养的赞美之意。
此外,在字幕翻译中,如果原影片字幕提供的信息不足,观众会不知所云。因此,在许多情况下,需要译者在适应生态翻译环境前提下,发挥其主体性对语义进行增补,加入必要的文化背景信息以及相关解释说明,使得译语字幕更加符合译语文化的生态语境,以便于观众能够更好地理解影片传递的文化意蕴和深刻主题。
例5:那时候是接班,接班进来。
The practice at that time is succession meaning to take over your parents’ working position.
“接班”为我国特定时期的一个特别用词,“指父辈退休后由子女顶替空出的名额,进入父母原单位上班,但不一定继续从事父辈原来的工作”[11]。由于文化差异,英语中没有“接班”的特定表达。如果纯粹按照源语字面翻译,外国观众可能无法理解。故译者经过仔细考量,用了一个模糊词“practice”指代“接班”一事,同时用“succession”来引出 “接班”这一词背后所代表的传承和接替的意义,并通过后置定语对其进行解释说明。译者综合考虑了可能影响译语观众接收信息的各种语言和文化因素,并将这些信息整合在一句之中,形象地传译了源语的文化内涵。
(三)交际维的适应与选择
语言的使用目的在于完成交际活动,因此纪录片字幕翻译不仅要实现两种语言符号及其所代表的文化内容间的转换,还要实现其交际目的。此外,字幕翻译的瞬时性也要求译语必须在和源语大致相同的有限时间内完成信息传递。
字幕翻译里包含大量对白的内容,对白的风格对人物形象的塑造极为重要,因此,对白的翻译应再现人物风格和形象。译者对词汇的选用应围绕这个目标,有时,标点符号的运用也能发挥重要作用。
例6:多好的东西!
What a masterpiece!
该句对白为文物修复师在看到精美文物时所发出的感叹。译文保留了源语结尾的感叹号,表达了人物说话时的兴奋之情。在原片中,人物在说 “多好”一词时,两字之间声音拖长,译者用“What a …”这一句式配合动作和声音的长度准确地传达出当时的场景和人物语气,传译出了说话人对文物精妙绝伦的赞美之情。
例7:行了,齐活。
All right, mission accomplished.
该片出镜人物多为北京人,其对白“京味”较浓。“齐活”是地道的北京方言,意思是工作或任务完成了。简简单单的两个字使人物爽直、利落的性格特征溢于言表。此例中,源语仅有四个字,译文也相对应地用了四个词,生动地传译了人物的语言风格和性格特征,语言与画面交相辉映,使译语观众对文物修复师的形象产生了和源语观众同样的理解和印象。
结语
生态翻译学将翻译理论回归到社会、文化等翻译生态环境之中,对翻译本质、主体、过程等诸方面进行思考。并且,把整合适应选择度作为评价标准,认为翻译过程中整合适应选择度越高,译文的质量就越高。生态翻译学要求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不但要遵循语言维度的适应性选择,还要挖掘语言背后的文化现象及其内涵,进而实现字幕翻译从人物到译者再到观众的信息传递和交际目的。
纪录片字幕的翻译无法做到绝对“忠实”。在翻译过程中,除了要考虑纪录片语言的特殊性之外,还要考虑译语观众的语言和文化因素。纪录片时空的限制要求字幕译者必须采用灵活的翻译技法,使得字幕语言简洁明了、通俗易懂。纪录片字幕翻译的核心要素是语际信息的传递与文化的转换。由于受到多重因素的制约,译者应依据生态翻译学的多维适应与选择原则,灵活运用词类转换、增减提炼、文化移植等技法,保证字幕翻译的正确性与适应性,做到以“信”为本,又不盲目求“信”,从而实现弘扬和传播优秀传统文化、促进文化交流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