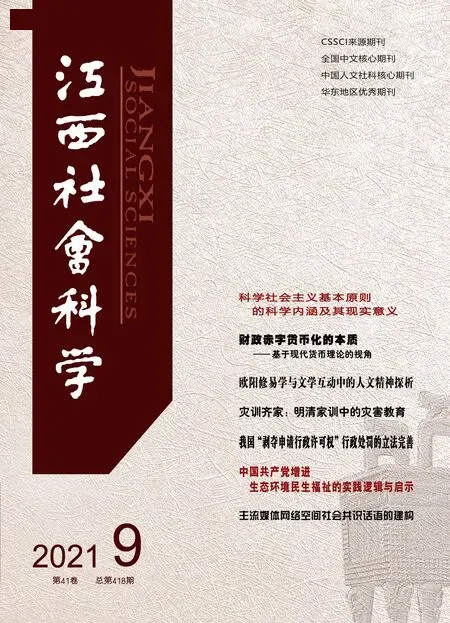作为“外文本”的词本事
——兼论“比兴寄托”说的生成
2021-11-29刘泽华
■刘泽华
词体的短小篇幅与抒情特质让人们在对它诠释时不得不向文本外求助,从而形成“外文本”。外文本的形成途径略有两种:其一为作者本人陈述,包括词题、词序以及其他讲明创作缘由、作品意义的书信、诗歌等;其二为他人叙述,这种外文本又可分为在场叙述与不在场叙述两种,大量的词本事即属于不在场他人叙述。在文本阅读过程中,读者在心里推导出一个作者形象即“隐含作者”,此形象又通过对词文本的演绎被具象化为本事。在阅读中会有更多符合这一隐含作者形象的本事产生,并加入隐含作者形象的具象化编织中,影响读者阅读时的基本态度与评价。在某种程度上,本事所逐渐勾勒出的作者形象代替了作者本身,使“作者”作为符号文本脱离真实主体,参与到二次叙述的“外文本”中发声。词文体在阐释过程中的“外文本”传统是“比兴寄托”形成的重要内因。
在知人论世观念的笼罩下,对作者意图的探求贯穿了整个中国文学批评史,尤其在宋代,以意逆志的“尚意阐释”倾向成为阅读的基本方式。①然而,词作为一种以抒情为主的短小文体,在故事层与话语层方面有着天然的不足②,这让知人论世的传统陷入困境,导致大量真伪难辨的词本事散布于词学批评史中。杨绘的《时贤本事曲子集》被认为是最早的词话,此书即以辑录本事为目的,之后的《古今词话》作为第一部以“词话”命名的专书,同样以勾辑本事为首要任务,自宋及清踵武者如蓬从风。然而,在词学研究中,甚诋其非者亦不乏人,胡仔面对杨湜《古今词话》中所录《贺新郎》本事就有“真可入笑林”[1](《苕溪渔隐词话》,P182)之讥,王士禛斥责鲖阳居士释《卜算子》乃“村夫子强作解事,令人欲呕”[1](《花草蒙拾》,P678),罗忼烈在《宋词本事多不足信》中直言:“本事绝大多数是始作俑者捕风捉影、向壁虚构而来的。”[2](P184)虽然历代学者指出了本事作为史料的不可靠,但这些本事在词学批评史上实有重要意义。
传统词学批评大致可分为词意阐释与词艺探索,词意方面自宋代对本事的编织,至清代形成了自觉的比兴寄托传统。本文试使用“外文本”概念简要勾勒传统词意阐释机制的框架,并对本事在这一机制中的意义加以诠释。
一、“外文本”概念的提出
本文所使用的“外文本”实脱出自“副文本”(paratext,亦译作“类文本”),之所以不使用现成术语,因其外延与词学现象并不铆合,为避免混乱不清,以下首先对二者进行区分,进而明晰“外文本”的概念。
法国理论家克里斯蒂娃(Kristeva)的互文性理论为结构主义诗学打开了新的文本切入点,使学者对文本的关注由本身移向周边,将文本研究从封闭中解放出来。热奈特(Genette)在她的启发下开始了“跨文本性”的讨论,将其定义为“所有使文本与其它文本发生明显或潜在关系的因素”[3](P64)。在《隐迹稿本》中,热奈特将跨文本关系分为五种类型:文本间性(intertextuality,亦译作“互文性”)、副文本性(paratextuality)、元文本性(metatextuality)、广义文本性(architexture)、承文本性(hypertextuality)。[4](P69-75)副文本性,即“由一部文学作品所构成的整体中正文与只能称作它的‘副文本’部分所维持的关系组成,这种关系一般来说不很清晰,距离更远一些,副文本如标题、副标题、互联型标题;前言、跋、告读者、前边的话等;插图;请予刊登类插页、磁带、护封以及其它许多附属标志,包括作者亲笔留下的还是他人留下的标志,它们为文本提供了一种(变化的)氛围,有时甚至提供了一种官方或半官方的评论”[4](P71)。在《门槛》中,热奈特将副文本分为“内副文本(peritext)”和“外副文本(epitext)”。“一个副文本元素,至少如果它包含以实质形式呈现的讯息,则必然具有一个可以与文本本身相对应的并容纳它的位置:围绕文本,并且在相同的体积内与文本保持着更为尊重(或更谨慎)的距离。在同一册内有诸如标题或序言之类的元素,有时还包括插入文本空隙中的元素,例如章节标题或某些注释。我将以‘内副文本’来命名第一个空间类型”[5](P4-5)。对于“外副文本”,即“与文本保持着更为尊重(或更谨慎)的距离”则是“位于书本之外的信息”,如访谈、对话、书信、日记等。
可以看出,“副文本”是指围绕在正文以外的部分,但副文本的出现,很多是由作者所设置,其意图是减少读者的误读,通过副文本来引导读者理解文本,“确保文本的命运与作者的意图相符合”[5](P407),且热奈特的论述是以小说为对象,其本身就具有很强的叙述性。赵毅衡在“广义叙述学”的框架下,进一步提出“伴随文本”,将热奈特聚焦在小说的目光拉升到整个文化活动,其文本类型分为:副文本、型文本、前文本、元文本、超文本、先/后文本。[6]无论是“跨文本”还是“伴随文本”,“外文本”当属其中,但又与其规定的几种类型不尽相同,故本文使用“外文本”一词,而不用现成的、已具有一定边界的术语。③
词体的短小篇幅与抒情特质让人们在对它诠释时不得不向文本外求助,以探明作者因何而感以为词,于是,作者的创作意图、创作背景就难以避免走向文本化,从而形成“外文本”。为了使本身缺乏叙述性的词完成叙述化,在文本的接受过程中,只好通过“场外征用”的方式来乞灵于外文本,对于外文本选择的开放性也导致了二次叙述的不确定性。赵毅衡将二次叙述分为“还原式二次叙述:对情节比较混乱的文本,需要重建文本的叙述;妥协式二次叙述:对情节非常混乱的文本,需要再建文本的叙述;创造式二次叙述:对情节自相矛盾到逻辑上不成立地步的文本,需要创建文本的叙述”[7](P107)。词的二次叙述难以划入这三类中,因为这三类文本都是“情节”混乱,而词却多不具有“情节”。弗鲁德尼克提到“读者把文本当作叙述来读,由此把文本叙述化”,赵毅衡认为他夸大了读者二次叙述的作用[7](P106),可是,当我们审视词的二次叙述时,弗鲁德尼克的观点恐怕是合适的。笔者认为词的二次叙述当属于第四类,即对缺乏叙述性的文本,通过征用外文本等方式,创建文本的叙述,可以称为“填空式二次叙述”。外文本是在词“填空式二次叙述”的阐释机制中存在的,它作为独立存在的文本可能与词的创作并无关系,但在阐释机制中成为词的外文本,这是词的独特性,也是与“副文本”相区别的重要所在。
在词意阐释过程中,外文本的形成途径略有两种:其一为作者本人陈述,包括词题、词序以及其他讲明创作缘由、作品意义的书信、诗歌等。如苏轼的好友刘攽偶然听到他在密州任上所作“乐府短长诗”,觉察其中的皮里阳秋,于是寄诗以戏,东坡读后又以诗作答:“十载飘然未可期,那堪重作看花诗。门前恶语谁传去,醉后狂歌自不知。刺舌君今犹未成,灸眉吾亦更何辞。相从痛饮无余事,正是春容最好时。”[8](P396)“那堪重作看花诗”出自刘禹锡《游玄都观》,刘禹锡意在讽刺朝局,而“刺舌”出自《隋书·贺若弼传》,贺若弼之父临刑前引锥刺弼舌,告诫贺若弼缄口慎言,“灸眉”出自《晋书·郭舒传》,王澄以郭舒病狂,掐鼻灸眉以治之。苏轼的自陈便成了理解这些“乐府短长诗”创作意图的外文本,让读者在理解知密词作时多去思考背后的政治隐喻。
将词题、词序归入外文本,因题序常表现出与正文的疏离。作者为避免读者对词的误读,有意识撰写题序,引导读者阅读,可以说是作为正文的注释出现的,交代写作的原因和背景等,与正文相比具有一定的叙述性。除此原因外,还因有不少题序并非出自作者本人之手,此现象在宋词中尤为常见。宋人少有自编词集者,多为后人或书商编辑,这样在刊刻流传的过程中,导致题序等文本十分不稳定,常有编辑者后加题序的现象出现,使读者产生误解。如秦观《千秋岁》(水边沙外),乾道本《淮海居士长短句》无题,范成大《莺花亭诗序》:“察少游‘水边沙外’之词,盖在括苍监征时作”。《唐宋诸贤绝妙词选》题作“少游谪处州日作”,显然此题为后人所加,毛晋刻《淮海词》便据以题作“谪虔州日作”(“虔”当为“处”之误),俨然是秦观自题,以此观之,此词似作于处州无疑。然而,《独醒杂志》《能改斋漫录》等皆载此词作于衡阳,此录《独醒杂志》卷五云:
少游谪古藤,意忽忽不乐。过衡阳,孔毅甫为守,与之厚,延留,待遇有加。一日,饮于郡斋,少游作《千秋岁》词,毅甫览至“镜里朱颜改”之句,遽惊曰:“少游盛年,何为言语悲怆如此!”遂赓其韵以解之。居数日,别去,毅甫送之于郊,复相语终日。归谓所亲曰:“秦少游气貌大不类平时,殆不久于世矣。”未几,果卒。[9](卷五,P124)
徐培均认为《千秋岁》上片“城郭春寒退。花影乱,莺声碎”云云,所写为春景,秦观绍圣三年(1096)时自处州出发,岁暮抵郴州,他经过衡阳至少当是秋天,与词境不符,故徐培均推断,此词是绍圣三年春作于处州,至衡阳时遇孔毅甫始呈之。[10](P84-85)此推断存在很多疑惑。首先,提前数月拟好词作准备呈交孔平仲(字毅甫),居然在词中还标明实际所作的时间,这样的行为十分奇怪。其次,孔平仲绍圣三年二月方知衡阳④,待到秦观知晓恐怕已过春季。再者,如果是秦观在处州提前拟好,预备呈予孔平仲,直书秋季即可,甚至出示作品前亦可稍加修改,使其符合当时季节。笔者认为,此作实以追忆之辞为主,上片所写是回忆春季离开处州情形,下片先怀念与孔毅甫在京城时金明池之游,后转为感慨时光易去,韶华不再。故上片所写春景无关创作时间,当据《独醒杂志》《能改斋漫录》等系于绍圣三年途径衡阳时所作,之所以有处州之论,甚至将上片所述春景理解为作品创作时的季节,实是后世学者在阐释词意时征用后出的题序所提供的信息,对词作产生了误读。可见,题序不论是作为作者自注还是刊刻过程中所加,都显现出与正文的疏离,并不能与词的正文同等看待,也当归入外文本。
外文本形成的第二种途径是他人叙述,此类又可分为在场叙述与不在场叙述两种。在场叙述如苏轼熙宁七年(1074)离开杭州,至松江时与杨绘、张先等人一同宴饮唱和,席上苏轼作《菩萨蛮·席上和陈令举》(天怜豪俊腰金晚),同时参加宴会的张先作《定风波令》(西阁名臣奉诏行),序云:“霅溪席上,同会者六人,杨元素侍读、刘孝叔吏部、苏子瞻、李公择二学士、陈令举贤良。”[11](P78)此段材料则成为在场者张先叙述苏词创作背景的外文本。同样作为在场者,作者叙述与他人叙述并不互斥,元丰四年(1081)苏轼作《书游垂虹亭》就回忆了此次宴饮:“吾昔自杭移高密,与杨元素同舟,而陈令举、张子野皆从吾过李公择于湖,遂与刘孝叔俱至松江。夜半,月出,置酒垂虹亭上。子野年八十五,以歌词闻于天下,作《定风波令》,其略云:‘见说贤人聚吴分,试问,也应傍有老人星。’坐客欢甚,有醉倒者。此乐未尝忘也。”[12](卷十一,P2254)另一类不在场叙述,包括词话所辑录非上述外文本的词本事。比如同样叙述苏轼、张先等六客之会,庄绰《鸡肋编》载:“苏子瞻与刘孝叔、李公择、陈令举、杨公素会于吴兴,时张子野在坐,作定风波词以咏六客。”[13](卷下,P103)即属此类。因此事苏轼本人及其他在场者都有叙述,所以,他人转述时便少有填空补白,但更多的是作者本人没有相关叙述,这就为词意阐释中的填空式二次叙述打开了缺口,不在场者叙述时或假托权威,或直接借作者本人之口,营造“在场感”,词话中的词本事更多属于此类。
二、二次叙述中隐含作者的具象化
定位了词本事在词意阐释机制中的位置后,笔者想再借助隐含作者这一概念阐发词本事作为外文本的意义。此概念由韦恩·布斯(Wayne Booth)提出,指在叙述者与作者之间还存在着“隐含作者”。申丹进一步分析,认为“隐含作者”涉及编码与解码两个层面,自解码而言“隐含作者则是文本隐含的供读者推导的写作者形象”[14]。就词的阐释而言,在文本阅读过程中读者在心里推导出一个作者形象即“隐含作者”,此形象又通过对词文本的演绎被具象化为本事。如苏词在接受的过程中,产生出忠君爱国的苏轼和风流雅士的苏轼两种隐含作者形象,这两种形象被以词本事的方式具象化。
忠君爱国的苏轼,如杨湜《古今词话》释苏轼《西江月》(世事一场大梦)为忠君之思:“坡以谗言谪居黄州,郁郁不得志。凡赋诗缀词,必写其所怀。然一日不负朝廷,其怀君之心,末句可见矣。”[1](《古今词话》,P30)胡仔对这一解读不以为然,“兄弟之情,见于句意之间矣。疑是在钱塘作,时子由为睢阳幕客,若词话所云,则非也”[1](《苕溪渔隐词话》,P174)。但杨湜以该词末句“把盏凄然北望”作为揭示苏轼怀君之心的抓手并非空无依傍。刘向《九叹》中追念屈原:“留思北顾,涕渐渐兮。”王逸注:“言己所以留精思,常北顾而视郢都,想见乡邑,思念君也,故涕渐渐而下流。”自《九叹》下,“北望”这一行为就沾染了思君恋阙的色彩,如杜甫在漂泊时北望而顾念京都有“愁看直北是长安”之句,李勉守赣州时登郁孤台北望而有“心在魏阙”之叹。解词者根据“北望”的文化内涵推导出忠君爱国的苏轼形象。《复雅歌词》中所录神宗闻《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事,便是该形象的具象化:
元丰七年,都下传唱此词。神宗问内侍外面新行小词,内侍录此进呈。读至“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上曰:“苏轼终是爱君。”乃命量移汝州。[1](《复雅歌词》,P59)
此事不见史载,但当苏轼的爱君形象成为定式后,对苏词爱君之意的阐发以及本事的杜撰就可顺势而为了,这则本事常被理解为神宗对苏轼有着特别的眷顾,如《爰园词话》:“子瞻生平备历危险,而神宗读其‘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之句,曰:‘苏轼终是爱君。’遭际亦略相当,俱能令千古艳羡。”[1](《爰园词话》,P402)神宗对苏轼的怜惜常出现在各类史料中,然而,神宗与苏轼的此种关系恐怕也只是苏轼形象在流传过程中的想象,朱刚的《“乌台诗案”的审与判——从审刑院本〈乌台诗案〉说起》一文便揭示了苏轼因乌台诗案贬谪黄州,实是神宗本无必要的特别责罚,绝非眷顾。[15]这些本事在苏轼爱君形象的流传中也不断加入具象化的过程中,使之更为丰满,成为解苏词之所依。
本事所构建的另一个苏轼形象为风流雅士。如苏轼《贺新郎》(乳燕飞华屋)颇具“本色”,于是,《古今词话》将之演绎为一段风流本事:
苏子瞻守钱塘,有官妓秀兰天性黠慧,善于应对。湖中有宴会,群妓毕至,惟秀兰不来。遣人督之,须臾方至。子瞻问其故,具以发结沐浴,不觉困睡,忽有人叩门声,急起而问之,乃乐营将催督之。非敢怠忽,谨以实告。子瞻亦恕之……秀兰力辩,不能止倅之怒。是时榴花盛开,秀兰以一枝藉手告倅,其怒愈甚。秀兰收泪无言,子瞻作《贺新凉》以解之,其怒始息。[1](《古今词话》,P27)
《西塘耆旧续闻》则借权威之口另陈本事,言陆子逸曾在晁以道家见东坡《贺新郎》真迹,晁氏解该词乃为侍妾而作:
公(陆子逸)尝谓余曰:“曾看东坡贺新郎词否?”余对以世所共歌者。公云:“东坡此词,人皆知其为佳,但后攧用榴花事,人少知其意。某尝于晁以道家,见东坡真迹。晁氏云:东坡有妾名朝云、榴花。朝云死于岭外,东坡尝作西江月一阕,寓意于梅,所谓‘高情已逐晓云空’是也。惟榴花独存,故其词多及之,观‘浮花浪蕊都尽,伴君幽独’,可见其意矣……意有所属也。或云赠王晋卿侍儿,未知其然否也。”[16](卷二,P299)
晁说之与苏轼相识,此本事借晁口言“榴花”为东坡侍妾名,于是,因《贺新郎》有“石榴半吐红巾蹙”句而解作“用榴花事”,假托权威以获得“在场感”是杜撰本事的惯用手法。此则材料真伪难辨,但显然也是将此词的隐含作者推导出一副风流才子面貌,并进一步具化为本事。本事作为不在场者叙述的外文本,为了词意阐释的权威性,除了假托在场者之口获得在场感外,在流传过程中还可能伪装成作者本人自述,如上述《贺新郎》在毛晋汲古阁本《东坡词》中便转化为词序,将《古今词话》所载本事中的“苏子瞻守钱塘”“子瞻问其故”“子瞻作”等改为“余倅杭日”“仆问其故”“仆乃作”。
本事往往具有传奇色彩,易被大众所接受,因此,在传播中反而会将作者本身的意图遮蔽,从而对其他读者理解文本产生误导。如在忠君爱国的苏轼形象成为定式后,《复雅歌词》便可以毫无依傍地将《卜算子》(缺月挂疏桐)释为一首比兴寄托之作:
缺月,刺明微也。漏断,暗时也。幽人,不得志也。独往来,无助也。惊鸿,贤人不安也。回头,爱君不忘也。无人省,君不察也。拣尽寒枝不肯栖,不偷安于高位也。寂寞吴江冷,非所安也。此词与《考槃》诗极相似。[1](《复雅歌词》,P60)
面对《贺新郎》(乳燕飞华屋),项安世竟认为这首词“兴寄最深,有《离骚》之遗法,盖以兴君臣遇合之难,一篇之中,殆不止三致意焉”。另一方面,受到苏轼风流雅士形象的影响,被解作忠君爱国的《卜算子》(缺月挂疏桐)居然也可以敷演出才子佳人的本事,吴曾《能改斋漫录》:
东坡先生谪居黄州,作《卜算子》云:……其属意盖为王氏女子也,读者不能解。张右史文潜继贬黄州,访潘邠老,尝得其详。⑤
此借苏轼门生张耒、好友潘大临来显示本事的可靠,以证明此确有一段为女子而作的风流韵事。伴随着误读,会有更多符合这一隐含作者形象的本事产生,并加入隐含作者形象的具象化编织中,达到对“前理解”的影响,从而引导读者在阅读词时的选择,决定了读者阅读时的基本态度与评价。某种程度上,本事所逐渐勾勒出的作者形象代替了作者本身,使“作者”作为符号文本脱离真实主体,参与到二次叙述的“外文本”中发声。如苏轼的风流雅士形象不断丰满,成为定式,《卜算子》(缺月挂疏桐)的本事不断被编织,《瓮牖闲评》杜撰出东坡在黄州时,有邻家女属意苏轼无果而终;《东园丛说》据以生发出苏轼少时许诺邻家女,待自己登第后来聘,日后却别娶他人的故事来;《野客丛书》则在此基础上演绎为苏轼与惠州温都监女之事。
在二次叙述的过程中,词文本扮演了底本的角色,缺乏叙述性,但包含着多种叙述的可能,读者通过选择底本中的一些要素,来进行填空和再现,构建叙述文本,通过叙述文本将心中的隐含作者具象化。本事在这个过程中是作为述本存在的,面对相同的词文本,本事可能包含着A和B两种不同的作者形象,如上文所述苏轼的两种形象,二者虽然不同甚至互斥,但共享着底本中的一些元素。当一种形象成为定式后又会被借以解读底本,即使面对同一底本,一个形象中也会编织出不同的本事,如上文所述《卜算子》(缺月挂疏桐)一词被《能改斋漫录》《瓮牖闲评》《东园丛说》《野客丛书》不断改写生发,它们之间构成承文本的关系。
为了使缺乏叙述的词完成文本叙述化,在二次叙述中不得不通过征用外文本来完成填空,外文本中的不在场叙述为填空式叙述提供了空间,词文本在这个过程中包含着多种可能,于是,同一文本演绎出不同的作者形象,而这个形象又可独立于文本之外,进而影响词意的阐释。宋代作为词的经典时代,其尚意阐释的倾向让“外文本”阅读深深根植于词学传统中。
三、“比兴寄托”生成的文体因素
在勾勒出词意阐释中“外文本”的阐释传统后,本节进一步审视清代“比兴寄托”词学理念的生成。“比兴寄托”在清代由诗入词,当溯之嘉庆时期常州词派的兴起,为矫浙派末流空疏之弊,张惠言揭橥“意内言外”,主张词“极命风谣里巷男女哀乐,以道贤人君子幽约怨悱不能自言之情”,自此清代后期词坛渐以“比兴寄托”为作词之圭臬,无论解词还是作词,多以社会性、政治性为切口。此习气沿波而下,现代学界如唐圭璋、刘永济、叶嘉莹等解词时依然受其影响,可见此风之固。
学界讨论比兴寄托盛于清代词坛的原因时,多从文体以外的角度入手,或言其时风雨如晦之时局,或言文人经世致用之怀抱。如詹安泰在《论寄托》中认为:“寄托之深、浅、广、狭,固随其人之性分与身世为转移,而寄托之显晦,则实左右于其时代环境。大抵感触所及,可以明言者,固不必务为玄远之辞以寄托也。”[17](P64)将比兴寄托的创作手法主要归因于时代环境。朱德慈在《常州词派通论》中认为是政治气候、经学影响、词风流弊三个方面因素催生了以比兴寄托为基本特征的常州词派[18](P1-21)。诚然,文体的变化总要受到其外部环境的滋养,一种观念形成的外因自不容忽视,然而,更应注重文体自身生成的内在规律。比兴寄托的隐曲幽微,本来自诗歌传统,它不但被嫁接于词,而且还深深植入了解词、作词活动中。“比兴寄托”的词学理念“前后百数十年间,海内倚声家,莫不沾溉余馥”[19](P489),如果词体本身不具备接纳它的可容性,是不大可能形成如此深广之词学传统的。
笔者认为,词在阐释过程中的“外文本”传统即是“比兴寄托”形成的重要内因。“师古”情节以及宋词本身所具有的阐释空间让其成为常州词人宣扬家法的媒介,词文本在批评的过程中展开远超文本本身内涵的扩容,这样的扩容虽不无“兴感”的成分,但兼具学者与作家二重身份的常州词人还是努力征用其他文本以显示阐释的合法性。常州词派主要采用对原有词作进行再阐释的方式来宣扬自己的词学主张,谭献所谓“作者之用心未必然,读者之用心未必不然”[1](《复堂词话》,P3987),一方面否定了作者对文本阐释的权威性;另一方面也揭示出比兴寄托传统最初并非酝酿自作者的创作过程,而是读者的阐释过程,常常征用“外文本”的词学阐释传统成为可以接纳“比兴寄托”的文体条件。如上文所论《卜算子》(缺月挂疏桐)在阐释过程中受到忠君爱国和风流雅士两种形象影响,其中,忠君爱国的诗教正与比兴寄托之旨相侔,自然苏轼的此种形象成为常州词人所择定的理想作者,陈廷焯编选的《词则》即引征鲖阳居士之言,并驳斥他说道:“或以此词为温都监女作,陋甚。从《词综》与《词选》,庶见坡公面目。”[20](《词则辑评》,P2151)所谓“庶见坡公面目”,也就是说,所见之“面目”便是词文本在接受过程中形成的忠君爱国的苏轼。《水调歌头》下亦引征董毅《续词选》评注:“忠爱之言,恻然动人。神宗读‘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之句,以为‘终是爱君’,宜矣。”[20](《词则辑评》,P2150)显然是据《复雅歌词》所载本事,以见常派寄托之论。这样的向外乞灵的填空式二次叙述阐释模式,无疑是对词学自身所具有的“外文本”阐释传统的发挥。
综上所述,词意的阐释因文本叙述性的缺乏,往往需要重建叙述,所以,二次叙述多是以填空式呈现的。在这个过程中,释意者一方面需要将已经存在的外文本作为填空的材料;另一方面释意者也是已经存在的外文本的读者,受到已经存在的外文本构建的作者形象影响,其将心中的隐含作者代入释意中,通过填空具象化为新的词本事。词文本作为二次叙述的底本,常常被解读出两种相悖的意思,作为外文本的词本事在词意的阐释过程中扮演了比词本身更为强势的角色,这样的传统为常州词派“作者之用心未必然,读者之用心未必不然”[1](《复堂词话》,P3987)的阐释策略提供了土壤。通过分析苏轼两种形象的形成与流传,可以看到隐含作者具象化的过程是复杂的,在这个过程中,受到传统儒家的伦理纲常与词被歌伎演唱这一行为方式的影响,同时还渗入了经师解经的方式。在词意阐释时,对作者爱国忠君形象的推导距离比兴寄托观念的自觉也只有一步之遥。当然,清人比兴寄托词学观念的形成无疑是多方面合力的结果,但这其中作为外文本的词本事恐怕是其重要内因之一。
注释:
①周裕锴在《中国古代阐释学研究》中提到:“孟子的‘知人论世’之说虽论及时代背景、作者生平与诗歌意义之间的关系,但在宋以前的诗歌注释中并未引起真正的重视,或者说还未形成一种传统……可以说直到宋代,诗与史再一次携起手来,以诗为史才成为阅读作品的基本方法。”
②宋人已经意识到词体在叙述性上甚至远远不如诗,如刘次庄因“时有一倡,为郡官所据,太守怒之,逐出境外”,作《尘土黄》(翠眉连娟舞蹈袖长),又用五言诗为词作译,用七言诗为词作笺,以释词之义。
③除热奈特、赵毅衡所提出的学术名词外,还当与谭君强提出的“外故事”做出区分。他在《论中国古典抒情诗中的“外故事”》(《江西社会科学》2014年第1期)认为“故事与话语的二项对立,在抒情文本中并不必然地存在”,于是,他主张从抒情诗文本以外的“外故事”来考察诗歌,并将“外故事”分为典籍记叙的外故事、诗人标记的外故事、与叙事文本相融的外故事、记叙评述的外故事。本文所谓“外文本”包括但不限于“外故事”,词文本以外的抒情诗等并非“故事”,但在词意阐释中发挥作用也在“外文本”之列。
④参见李春梅的《三孔事迹编年》(吴洪泽、尹波主编《宋人年谱丛刊》第5册,四川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921页)。
⑤吴曾在《能改斋漫录》中,将苏轼的忠君爱国形象在后世逐渐成为东坡形象的主导,这与南宋时习惯将道学群体比附为元祐党人不无关系,如朱熹云:“一有刚毅正直、守道循理之士出乎其间,则群讥众排,指为道学之人而加以矫之罪……复如崇、宣之间所谓元祐学术者。”(《戊申封事》,郭齐、尹波点校《朱熹集》卷一一,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75页)。姚愈:“臣窃见近世行险侥幸之徒,创为‘道学’之名……反以元祐党籍自比……此皆借元祐大贤之名,以欺天下后世。”(李新传《姚愈论奸伪之徒欺世盗名乞定国是》,《道命录》卷七,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第77页)作为元祐魁首的苏轼自然在道学的“主导叙事”下披上了忠君爱国的外衣,经生解经的阐释方式更易被用作解释苏词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