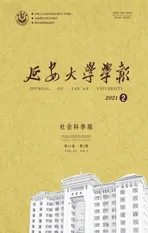《白鹿原》地理空间的文化意义
2021-11-29梁向阳张爔文
梁向阳,张爔文
(延安大学文学院,陕西延安716000)
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寻根文学,将文化作为文学的核心价值取向,取代了持续多年以政治为主导的文学观念,《白鹿原》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当前对《白鹿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从文化心理学出发的人物形象研究、史诗性的主题意蕴研究、从艺术特色出发的文本剖析以及跨文本研究,而对故事发生地本身的空间建构及其所蕴含的文化内涵重视不够,偶有涉及也是从叙事学的角度进行空间形式的梳理,对其文化内涵浅尝辄止。小说中对地理空间的建构,通常代表着作家独特的审美倾向,也体现着作家的创作理想。无论是作家在小说中所描绘的人或物,还是作家内心情感的抒发、主题的表达,都无法脱离地理空间而独自存在。本文将《白鹿原》置于文学地理学的视阈下,对小说中所构建的重要地理空间及其所蕴含的文化内涵予以探究,以期更深入全面的理解这部作品。
一、白鹿古原:传统文化的承载空间
陈忠实是在寻根文学的启发下去寻找民族精神的本质,但他与主流的寻根文学作家有所不同。他认为“文学的根”不该过于关注深山密林而偏离现实生活,更应关注人口密集的地区,寻根文学作品所寻的“根”应该是逐渐式微的主流传统文化。基于这一点,他选取了深受关中儒学滋养的白鹿古原这一客观存在的地理空间作为小说文本发生和主题彰显的承载空间。
《白鹿原》的文本故事环境,对应现实存在的地理空间,其描写的是发生在白鹿原上的故事。白鹿原隶属于陕西关中,位于西安市东南方向,是儒学重镇——关学的所在地,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之一。据《辞海》所记:“在陕西蓝田西灞、浐二水之间。南连秦岭,北至灞岸,东西十五里,南北四十里。相传周平王时有白鹿出此原得名。原上有汉文帝霸陵,亦称霸陵原。”[1]“白鹿”被作为一个原始意象,白鹿原的名字也由此得来。自古以来,白鹿就被视为祥瑞之兽,代表着至仁至德的纯善品德。在这片古原上,白鹿更是蕴涵着人们对所有美好生活的期许和向往。用“白鹿”意象象征传统文化精神,难免有些空灵和晦涩,但不可置否,它较为明确地指向了传统儒家文化。作为原上最传奇的故事,白鹿传说被一代一代的传诵,在稚童刚刚能听懂人言之时便深入心头无法忘记,并以此带来深深地“白鹿执念”。儒家文化的守护人白嘉轩便是“白鹿执念”的代表人物。小说开篇第二章以白嘉轩因在雪地里发现湿地下的白色叶片,询问朱先生后便认为这是千百年后白鹿化作精灵的显现,为获得鹿子霖家的这块“吉兆”之地,迅速谋划出万全之策进行了巧取换地做坟园,由此之后白家便走上了人财两旺的局面。此场换地风波直到小说结尾仍被提及:白嘉轩对着悲惨的鹿子霖流泪致歉,并认为自己“一辈子就做下这一件见不得人的事”。儒家文化的忠实守卫者,为追求“风水宝地”“白鹿精魂”可以暂时舍下仁义道德,这也是传统儒家文化的矛盾所在。
白鹿古原作为儒家文化的载体或象征,构成这一自然地理空间的要素远不止“白鹿”这一个意象,还包括丰富的植物意象、其他民俗意象,更重要的是世代居住于此的人们,以及他们在生活生产中所形成的传统习俗、生存方式和思维模式等等。对于《白鹿原》来说,古原不仅是一个客观存在的地理空间概念,更是一个主观精神的文化空间概念,是白鹿村民们世代形成的风俗习惯、情感认同和价值认同等融汇一体的传统文化集合。陈忠实对此也曾说过:“白鹿原上,最坚实的基础不是别的,而是几千年漫长的封建社会存留下来的那一套伦理规范,几千年文化积淀形成的那一种文化心理,几千年相沿流传的那一番乡俗风情。”[2]26
以白鹿古原为承载的白鹿村,作为关中地区的一个农村社会,较少受到现代文明的侵袭。也就是说,在封闭的白鹿村,传统儒家文化影响下的伦理规范和家族观念是族人们奉行的信仰和价值取向,并在这片土地上世代积淀、传承,与这片具有原始意象的古原水乳交融。
二、祠堂:宗法文化的权威空间
文化实质上是一种价值观念的认同,更多的体现在情感上的认同。千百年来,儒家文化早已渗入到中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作为一套成熟的价值体系,指导着中国人的生活甚至社会发展,在这个体系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便是严谨的宗法伦理。寻根文学作家普遍关心作品中传统与现代的矛盾关系,陈忠实在《白鹿原》中主要对儒家文化进行了挖掘和反思,祠堂作为宗法伦理的典型空间,正是承担了这一任务。
祠堂在白鹿村的位置,在小说第十三章有所提及。批斗三官庙老和尚的大会,会场选在位于白鹿村中心的戏楼上,而戏楼位于白鹿村祠堂前,中间隔着一个广场。祠堂和戏楼相邻,是族人遇事聚会的地点,是白鹿原宗法文化呈现的典型地理空间。由此可以看出,祠堂的地理方位是白鹿村的中心。祠堂对白鹿村中心位置的占据,延续了它早在封建社会就树立起的管理族人的优越感,即族长对族人有着发号施令和控制各种行为的权力。如第十一章,杨排长带着一队士兵到村里征粮,鹿子霖和田总乡约田福贤先后劝说白嘉轩到祠堂敲锣,召集村民交粮。在杨排长的威胁下,“白嘉轩敲了锣。白鹿村的男女老幼都被吆喝到祠堂门外的大场上”。[3]167再如,当白鹿原上出现传说中的“白狼”时,只有作为族长的白嘉轩,才有资格调令族人们停止手头农活,集体筑高墙,安排夜晚巡防。此类事件,体现出祠堂对于族人发号施令和对白鹿村管制的绝对权威。
祠堂作为白鹿村祭祀祖先的场所,它所代表的是封建宗法文化。它的庄严和神圣构成了祠堂作为空间的第二个特征——封闭性。祠堂作为祭祀祖先的宗法空间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这种封闭性最明显和直接的体现就是除了祭祀祖先,祠堂大门常年关闭。除此之外,封闭性不仅在于形式上的封闭,更在于抽象意义上的封闭,即宗法的认同与区别,能进入同一祠堂才是白鹿家族的人,族外人或是不被认同的人始终无法进入祠堂,例如白兴儿和田小娥始终被拒之门外。中心地位的占据和封闭性的认同构成了祠堂在族人心中神圣不可侵犯且具有绝对权威的地位。
白鹿祠堂的命运有三个阶段:修复——毁坏——重修,在一定意义上,这也象征着传统宗法文化在白鹿原上的三个发展阶段。作为白鹿村的族长,白嘉轩实现生活人财两旺后,便有了翻修祠堂的想法。小说第五章写道,“祠堂年久失修,虽是祭祀祖宗的神圣的地方,却毕竟又是公众的官物没有谁操心……白嘉轩想出面把苍老的祠堂彻底翻修一新,然后在这里创办起本村的学堂来。他的名字将与祠堂和学堂一样不朽”。[3]61修复祠堂无形之中增强了族长白嘉轩的名望和功德,也充分地重塑和弘扬了宗法文化,用宗法文化凝聚了白鹿村的族人。《乡约》与祠堂、族规这些传统文化中的家族宗法文化密不可分。《乡约》被族长白嘉轩视为每位白鹿村村民都应遵守的行为准则,就连白嘉轩的“死对头”鹿子霖在读完《乡约》后也发自内心地赞叹和认同。鹿子霖认为如果白鹿村的每位村民都能按照《乡约》做人行事的话,白鹿村就能成为真正的礼仪之乡;白鹿村的徐先生也连连夸赞《乡约》是白鹿村的治本之道,因为它有着重建传统的伦理道德规范的作用,甚至有收拾世道人心的功能。然而社会有其自身发展的规律,现代文明社会必然与封建宗法社会不相容。黑娃在大年初一“进攻”了祠堂,砸了刻着《乡约》的石碑,这是祠堂自修复以来受到的最大的破坏,也显示了现代文明对传统文化的不满和强大冲击。但统治了白鹿原上千年的封建意识形态不可能就此退出历史舞台。黑娃的“革命”只是暂时的胜利,之后白嘉轩再次带领族人翻修了祠堂,将刻着《乡约》碑文的石板拼接起来,由此来警示族人铭记教训。
陈忠实虽然对传统文化进行了反思,但反思的程度远不能与他对传统文化留恋相提并论,于是他在小说后半部分中又设置了黑娃“皈依祠堂”的行为。经历了社会革命的洪流后,身心疲惫的黑娃选择向曾经对抗过的礼教低头。他首先娶了老秀才的女儿高玉凤为妻,之后又拜“关中大儒”朱先生为师,最后回祠堂祭祖。朱先生的亲自陪同,也显示出黑娃此举具有根本性的意义。曾被黑娃的反叛打折腰的白嘉轩亲自主持了黑娃的祭祖仪式,他肯定了黑娃的改过自新,并进行了表彰。此举正合了白嘉轩对宗法文化的自信:“凡是生在白鹿村炕脚上的任何人,只要是人,迟早都要跪倒到祠堂里头的。”[3]590黑娃的回归,是宗法文化的胜利,表明了即使在现代社会传统文化仍然具有权威地位,有着强大的影响力和控制力。
但无论陈忠实如何留恋传统文化,祠堂所代表的宗法伦理的权威空间意义在现代文明的洪流中最终会被淘汰。白孝文的回乡祭祖更好地说明了这一点,他的“回归”和黑娃的“回归”有着本质的不同。白孝文始终都认为从没离开过白鹿原的人是没有出息的,即使他跪倒在祠堂里,也没有丝毫悔改和“仁义之心”,他不过是想在白鹿原上找回他失去的尊严,炫耀现有的光辉,拥有更好的仕途和地位。随着回乡祭祖,黑娃回归了家族伦理文化,但鹿兆鹏在去延安前百忙之中依然对黑娃表示遗憾和不解:“哦呀呀!黑娃兄弟呀……你怎能跑回原上跪倒在那个祠堂里?你呀你……”[3]596不论是白孝文的假意祭祖,还是黑娃的真心皈依不被理解,都表明祠堂的绝对权威和神圣地位在各种新兴势力和多元文化中逐渐逝去。
三、白鹿书院:关中儒学的教化空间
白鹿书院作为一个知识文化空间,与它的山长朱先生有着同样的神秘性。根据小说的描写,白鹿书院具体位置为“坐落在县城西北方向的白鹿原原坡上”。[3]22此处的原坡指由于地势起伏相对于白鹿原而言较高的山丘。还根据书中白嘉轩因为一个迫切想要解开的梦,而半夜动身去白鹿书院找寻朱先生,到第二天天亮才抵达,时间的漫长体现出书院与白鹿村的距离的遥远。除此之外,在田小娥死后出现瘟疫时,部分白家人躲进白鹿书院,可见书院与白鹿村有着能隔开瘟疫的遥远距离。白鹿书院位于白鹿村又高又远的地理方位,显示出其高瞻远瞩、远离世事的旁观者态度,也体现出在此讲学者朱先生作为“关中大儒”具有中庸、理性的特质。
“书院是我国封建社会特有的一种教育组织形式,它是以私人创办为主,积聚大量图书,教育活动与学术研究相结合的高等教育机构。”[4]白鹿书院创始于宋代,河南的吕姓小吏居住在白鹿原时子孙出了四位进士,皇帝为此修祠纪念,吕氏后人便挂了“白鹿书院”的牌匾在此讲学。除此之外,北宋时期,陕西理学家张载创立“关学”并广泛传播、影响深远。由此可见,白鹿书院有着深厚的儒家传统文化底蕴。朱先生重新挂起白鹿书院的匾牌,代表着作为传统文化空间的白鹿书院又重新发挥起它弘扬儒家文化、教化族人的作用,从进入书院的人也无时无刻不体现着有教无类的儒家教育思想。在这里就学的起先有鹿家二兄弟、白孝文、白灵等,后有历经革命的浪潮“皈依祠堂”的土匪黑娃,朱先生自嘲道:“我的弟子有经商的,有居官的,有闹红的,有务农的,独独没有当土匪的,我收下你,我的弟子就行行俱全了”。[3]584
祠堂被毁坏可以修复,书院学子的一一离去却不会再回来。在白鹿村上接受着儒式教育的青年一代先后从白鹿原上的“最高学府”离开,进入“洋学堂”,学习“西学”。这是现代文明对传统教育的冲击,接受了“个性解放”的青年们,从根本上彻底与白鹿原上的儒家文化相背离。白鹿书院随之关闭,朱先生闭关编修县志,同九位先生竭日夜之力、克艰难之苦,临终前卖了书院门前的一颗柏树才得以印书成册,《滋水县志》是朱先生在世上完成的最后一件事,白鹿书院成为动荡时代的最后一丝安宁。但最后白鹿书院因“批孔”被红卫兵洗劫,朱先生在去世后遭遇“掘墓”,小说中设置了朱先生墓穴中“人作孽,不可活”的预测情节,同样表现出陈忠实对儒家文化遭到劫难和衰落的无限惋惜。
朱先生是“白鹿精魂”的化身,更是儒家文化的化身。在传统农业社会为主导的白鹿原上承担着道德模范作用,指引着人们生活生产。他具有不俗的品格和节操:以一首诗化解了白鹿两家的买地纠纷;以一纸《乡约》约束村民的行为礼仪,使“仁义白鹿村”真正践行;他为百姓奔走,饥荒年月发放赈济粮食,救民爱民;战争时期,只身一人去说服方巡抚退兵,使得村民免遭涂炭……可以看出,朱先生是《白鹿原》中陈忠实异常偏爱的“圣人”,同时也是对其所代表的儒家文化的极力肯定。但是在现代文明看来,传统儒家文化也有其矛盾的一面,朱先生作为设塔人之一镇压田小娥的情节反映出这一点。在“亲翁杀媳”的惨剧后,白鹿原上出现了一场前所未有的瘟疫,这场瘟疫带走了许多族人,包括族长的妻子仙草。在巨大的恐惧下村东头的破窑出现了香火不熄、青烟升腾的奇观,鹿子霖趁机带领族人们与白嘉轩商议为田小娥修庙葬尸,以救生灵。白嘉轩在愤怒之中拿不定主意,便去白鹿书院找朱先生解答。一向讲仁义的白嘉轩怒火中烧,并说出了他的举措:“我早都想好了,把她的尸骨从窑里挖出来,架起硬拆烧它三天三夜,烧成灰末儿,再撂到滋水河里去,叫她永久不得归附。”[3]472这看似已经很残忍的行为,在远离世事、推行仁义的朱先生“冰冷”的提议下成为了“让她永远不得出世”“造塔祛鬼镇邪”的“完美”举措。田小娥“生的痛苦,活的痛苦,死的痛苦”。[2]124她死于传统伦理与封建秩序,即使在死后也无法逃脱泯灭人性的封建传统文化的桎梏。
四、保障所:家族文化的对立空间
通过分析作者的观点趋向,可以看出他在情感上对儒家文化倾向于肯定。白嘉轩宁愿承受精神重压和肉体痛苦,依然坚守儒家文化的正统观念。而通过近乎神化的关中大儒朱先生更是作者笔下的理想人物,鲜明地体现出作者的价值取向。如果说白鹿祠堂和白鹿书院体现作者对儒家文化的肯定与宣扬,那保障所存在的意义便体现出传统儒家文化在现代文明中的式微。
滋水县白鹿仓第一保障所,它是社会变革下国民党当政期间应运而生的产物,是国民党政府在白鹿原上权力展示的地理空间,它代表着新兴的政治势力。它冲破了白鹿祠堂和白鹿书院在白鹿原上独揽大权的局面,这充分地说明了空间作为一种政治工具的实质。保障所与祠堂事事针锋相对,这也证实空间实际上是充满着意识形态的客体,始终具有政治性和象征意义。相比祠堂在小说中出现的一百七十多次,保障所在小说中仅出现过六十多次,不及祠堂分量的一半,由此可见,小说重在写传统文化与宗法家族文化,而代表新兴政治文化空间的保障所并不是所要寻的“根”。
正如白鹿祠堂的封闭性与中心位置的占据,显示出它对白鹿村管制的绝对权威,空间在一定程度上展示着着权力的本质,保障所也同样有属于自己的特征。
保障所的选址是破败不堪的民房,位于城镇地带,是更容易接触和掌握现代信息的地理空间,这样选址的意义,正表现了它与传统文化的对立。保障所的选址是鹿子霖上任后在用白鹿仓拨给他的紧张的经费买下的,当他挂出“滋水县白鹿仓第一保障所的招牌之后,这座多年来一直破败不堪的居民小院,完全焕然一新了,在灰暗衰老的白鹿镇上,立即昭示出一种奇异的气质”。[3]95保障所是具有政治性质的空间,它的选址不管是从地理位置上来考量,还是从空间意义来审视,都十分随意、毫无根据。但正是这种随意,体现了它作为现代文明和新兴势力对历史和传统的轻视,只在乎当前形势、阿谀奉承、毫无底蕴的特点。
相对于祠堂的封闭性来说,保障所具有的则是开放性,最明显体现在对于可进入者几乎不作限制上。祠堂对族人的认可在品行和性别上有明确要求,保障所对于来访人的身份地位、性别进行几乎不作限制,最明显的例子便是从未得到祠堂认可的田小娥也可以随意进入。田福贤为了抓获黑娃而诱骗田小娥,此时的田小娥想去找田福贤商议,权衡再三后她转身走进了保障所。由此可见,保障所是可以轻易进入的空间,对身份和时间都没有限制。此外,保障所对于掌权人的选择也具有开放性,这是与祠堂的掌权人——族长的世袭传承截然不同的。鹿子霖作为保障所的第一任乡约,由于长子鹿兆鹏的身份被追捕而撤职。县长岳维山想让名望高的白嘉轩接任,而非鹿家的其他人,但白嘉轩作为深受“白鹿文化”哺育的中国农民,他不愿染指集团政治,拒绝了出任乡约。这体现出保障所对掌权人的任用只讲究政治效益,较为随意。祠堂作为代表宗法文化的地理空间,十分看重传承,一直以来由白家人掌管,而保障所即使由鹿子霖一手创办,也具有随时失去的风险,对任职人员的不同选择来源于这两种空间不同的文化。保障所作为新政权下成长起来的政治空间,代表的是政治文化,具有现代性质,这也正是它与祠堂的根本区别。
小说中保障所集中出现的事件并不算多,也不够典型,多是作为鹿子霖任职的身份背景加以介绍。但作为地理空间的保障所,所发生的事几乎都是负面、消极和不光彩的。比如保障所成立之初,鹿子霖便奉县长史维华之命,让各族族长在村中征收粮食。鹿子霖的儿媳冷大小姐,在封建婚姻的悲剧下她过起了“有男人跟没男人一样守活寡”的无性且不幸的压抑生活,在公公鹿子霖某次深夜醉酒的调戏与幻想中殷勤地向阿公“发射信号”,结果受到鹿子霖毁灭性的羞辱。自此之后,她开始了持续半年的“哑巴生活”,最终在压抑与反压抑的无法平衡中人格与精神分裂。在初冬的某天上午,她发疯的在村巷中喊叫:“我到保障所寻俺爸去呀……我想俺爸了呀!”[3]523并一路喊叫到保障所,让正在与好友聚会的鹿子霖极度难堪与羞辱。此类有违宗法伦理的事件绝不可能发生在庄严神圣的祠堂之中,这同时也与保障所的开放性有关,在一定程度上也表明了保障所与祠堂的针锋相对。保障所与宗法势力、其他政治势力的较量,由此带给白鹿原的动荡不安,足以看出这个新兴政治空间的斗争属性,也展示了其与传统家族势力对立的根本属性。
宏观来看,在白鹿原上家族势力逐渐式微,而新兴政治势力方兴未艾,毫无疑问二者的斗争也将在混乱中持续很长一段时间。“阶级意识的形成意味着家族意识的削弱”。[5]20世纪的中国现代社会,传统家族文化受到阶级斗争盛行的长期冲击。英国著名历史学家阿·汤因比曾提到,中国家族文化的复兴对21世纪人类社会结构的变革将具有深远的意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陈忠实《白鹿原》的出现,则是以家族文化为内核的儒家文化在中国复兴的标志。
关于传统文化,陈忠实在反思,我们也应反思。无论何时,“忠孝仁义”“学为好人”都不是一件坏事,但评判何为“忠孝”、何为“仁义”、何为“好人”的标准会随着社会发展而一直变化。陈忠实在《白鹿原》中给予传统文化极高的赞扬,但其式微我们也应从容面对,“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是我们对待传统文化惯用的方法。对传统文化的保护和发扬确实有利于民族精神的传承,但其糟粕始终会阻碍现代文明的建立,应该进行必要的扬弃。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来源之一。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有利于坚定文化自信,为人民提供精神指引。
新时期以来,我国小说创作空前繁盛,《白鹿原》之所以能够独领风骚、历久弥新,不仅在于这是陈忠实对生活的深入发现和独立表述,还在于他把地理空间的描写和利用发挥得淋漓尽致。这些地理空间不仅是小说谋篇布局的关键,更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渗透着作者对中华文化现代命运的深入思索。总之,从文学地理学的角度去解读《白鹿原》,可以更深地挖掘其博大精深的文化世界,更加全面地了解这部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