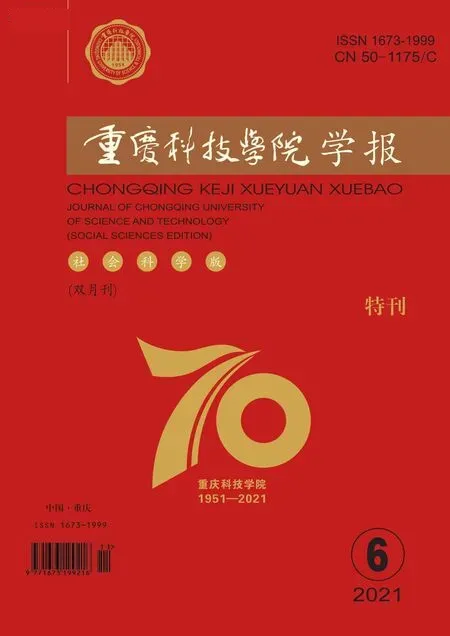救亡与近代中国“祖国母亲”话语的生成逻辑
2021-11-29徐峰
徐 峰
(贵州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贵阳 550025)
“祖国母亲”是现代政治话语中常用的抒情性词语,它是人们十分熟悉的一个隐喻。可能是因安于所习之故,学者至今对这个隐喻的来龙去脉仍缺乏细致的梳理与阐释。现有的研究大致涉及两种分析路径:一种是从文学艺术角度分析“祖国母亲”这个词汇意象所包含的语言、文化及社会认知,梳理其表现类型及历史变迁脉络[1-2];一种是从政治文化角度探寻这一概念的渊源,但多是在西方政治文化语境下溯源,认为“祖国母亲”是从西方移植过来的一个概念,在男权主义传统十分深厚的国度不会内生出将祖国女性化的隐喻[3-4]。这两种分析路径当然都是有启发意义的,但因为研究视角的原因,对“祖国母亲”话语产生的中国语境缺乏细致的梳理和分析。在近代中国“救亡”和“启蒙”的双重话语中,中西思想的激荡与交融为“祖国母亲”概念的生成提供了丰厚的历史土壤。外力作用(西方影响)固然功不可没,但内生动力(中国自身因素)也不容忽视。鉴于前人研究对中国自身因素方面挖掘不够,现单从中国语境分析“祖国母亲”隐喻生成的话语逻辑。
一、进入救亡语境的女子国民身份
鸦片战争后的中国,从自我隔绝状态被动走向世界,国势阽危,万方多难。不屈的中国人试图挽狂澜于既倒,开启了一轮又一轮的救亡实践活动。一般而言,“人虽感患大病,胃气不伤则必愈。天下虽有大变,民心不散则不危”,但彼时的大清王朝“譬之于人,五官犹是,手足犹是,而关窍不灵,运动皆滞”[5]。部分知识精英逐渐明白,大清乃是膏肓之疾,已然无可救治,“欲使中国不亡,惟有一刀两断,代满洲执政柄而卵育之”[6]50。于是革命逐渐提上日程,并成为改变社会的最后一种手段。最后,腐朽的封建统治终被革命的声浪湮没,成为历史尘埃。在此过程中,女子的国民身份也从无到有、由隐到显。
甲午战争后的中国内忧外患,国家处在风雨飘摇之中,随时可能倾覆。晚清的士子特别是青年学生,生活在亡国的忧患中。深重的民族危机让他们开始深刻反省,思考国家何以如此颓丧。19世纪末,少有人将之归咎于统治者的昏聩与制度的腐朽,而往往归责于“君子”。“我国之君子,乃病呓如故,鼾睡如故,眡娗诿諈又如故也。”[7]44“君子”耽于逸乐,浑噩无为,以致国将不国。但是,很快国人的认识发生了变化。由于女权主义的鼓吹,在20世纪初已有人提出,国之耻“非独男子之罪也”,女子对国家积弱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女子积习,其最可鄙最可伤者,略有数端:识见卑陋,眼光如豆,自私自利之间,固结于胸中;妄尊妄大之心,时形于辞色,涂脂抹粉,数时装以自炫,不特人视之为玩物,即己亦自居于玩物而不辞。”[8]归责于女子,虽不免有“甩锅”的嫌疑,但却发现和承认了女子作为国民一员的身份。国族强大,才可不惧西方国家的虎视眈眈,而强大国族,需要有强壮的国民,但彼时的中国“贫窭之媒,流传弱种”[9]。“欲革国命,先革家命;欲革家命,还请先革一身之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母。女子身体健壮,不仅可孕育出良好体格的国民,还预示着民族的优劣,国族的强大。女子作为国民之母的身份引起国人的重新审视。1904年就有人在报上疾呼,希望国人在救亡的时候可以注意到女子“国民母”的身份:“国无国民母,则国民安生?国无国民母所生之国民,则国将不国。故欲铸造国民,必先铸造国民母始。”[10]1907年人们对女子“国民母”的身份认知又进了一个层次。“女界者,国民之先导也。国民资格之养成者,家庭教育之结果也。我中国之所以养成今日麻木不仁之民族者,实四千年来沈沈黑狱之女界之结果也。唤起国魂,请自女界始。”[11]女子的国民身份受到重视,而且在国势岌危之际还要求女子作为国民母的救亡责任大于男子。“夫国家之亡,由于政治之腐败者半,由于社会之腐败者亦半。而亡国之惨,一国之男子固受其祸,一国之女子亦受其祸。故国亡而不能补救,则匹夫与匹妇皆与有罪;而国将亡而思补救,则匹夫与匹妇皆与有责也。不宁惟是,以中国家族制度之不善,为女子者苟无爱国心,不特其自身放弃国民之责任而已,而为男子者亦为其所系累,而不能萃其心力,以为国家社会造福。故女子之关系于国家之兴亡,实比男子为较大;即女子之应尽对于国家之责任,亦比男子为较重也。”[12]20世纪初女界也有接受这种认知,并对国之危亡主动揽责:“今日国危种弱之故,非他人之责,而实我与诸君之罪也”,因为“女人以生产国民、教育国民为独一无二之义务。乃诸君不独不能尽义务,而反为国民种祸根、产劣种……今日之世,种族竞生,优胜劣汰。我制造国民之诸姊妹,偏产此劣种于大地之上,又何怪其将为红黑之续耶?”[13]
所谓女子“种祸根、产劣种”,在当时主要矛头所指的是女子缠足陋俗。晚清以来不同时期对女子缠足都有不同声音,若论抨击最厉害挞伐最深刻,则非戊戌维新时期莫属。1897年8月8日《时务报》刊文《中国缠足一病实阻自强之机并肇将来不测祸说》,大肆声讨缠足:“精颓神丧,血枯气衰,门户难持,呻吟可厌,为之夫者,终身为所累,安有余力以相其夫?是缠足一端固专害中国贤达聪明之妇女也。且数千万贤明之妇女,皆成废疾,不能教子佐夫,而为之夫为之子者亦只可毕生厮守,宛转牵连,无复有四方之志。故自上达下,自内达外,因循颓惰,得过且过,无意自强。是缠足一事,刭天下妇女之足者患犹小,丧天下男子之志者患无穷也。”[7]37这里说女子缠足“丧天下男子之志”,虽有失偏颇,但对缠足之害的检讨还是较为深刻的。1898年6月康有为向光绪帝上书,也痛陈了缠足之害:“尫弱纤偻,为其母裹足,故传种易弱”“与万国竞,而留此弱种,尤可忧危”“中国二万万女子,世世永永,婴此刖刑,中国四万万人民,世世永永,传此弱种,于保民非荣,于仁政大伤”[14]。这里将女子缠足与国族自强联系在一起进行考量,将女子地位提到了一个新的认识高度。女子因缠足而致体弱,进而致种弱,其实这并不构成因果关系,但在当时社会的一般舆论看来,国家的贫与弱就是因女子缠足而致国族体弱导致[7]203。这反映了当时国人认识上的一种偏狭,同时也不乏有精英男子推卸责任之嫌。近代的中国掉队落伍且饱受外人欺凌,国家的强盛迟迟不得实现,精英阶层郁志难伸,然后自我释怀说是女人不争气。在国族主义的大背景之下,中国男人在全球国家竞争中“自己觉得比不上他人,回过头来又把这种羞耻加之于身边的女人”[15]。19世纪末,中国的女权意识在复苏伸张,对女子给了国民的标签,但又给泼了污水,将国族的孱羸归咎于女子体质之弱。
20世纪初有人提出女子相比男子在生理及性格上具有三大优势,而且将这种优势与国家命势联系在一起。其一,是“坚执心”。“苟女子一旦幡然而明”,必“以其爱父母,与夫从一而终之爱情,移爱于国,移爱于同胞”“其结团体也,必致永久不散,死生相共矣”。其二,是“慈爱心”。“吾女子倘成就学业,得参预政治、外务,必有平等、公和、自爱种族之心。”其三,是“报复心”。“中国向有谤女子之言曰‘最毒妇人心’。吾知此毒性矣,为女子之特美性也。中国人之无恨心也,日受外人之涂毒,而不知恨……则其仇恨心必坚决,不顾一身之利害,必辗转设计而对敌之。所谓最毒妇人心,既知其非,必与其始终反对,无忽而仇敌、忽而和好之病矣。”有这三大特性的女子,“苟能人人读书,知大体,爱国爱种,办事之手段,必胜于彼男子也,必优于彼欧美女子也。”[16]原本在国家民族大事上缺位或者多扮演红颜祸水负面形象的女子,一下子在救亡中凸显其重要价值。女界的兴起承载了国人对国族强大的愿景。1905年有人对女界的前途与国家未来给予厚望:“独我女界,负灵明之质,葆美妙之姿,而停辛伫苦,蓄而不发。自今以后,空山乳虎,一鸣惊人,光明旧物还我河山之丰功伟烈,其终握于纤纤之手乎?美矣哉女界之希望!重矣哉女界之责任!”[17]
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救亡实践层面的深入,加上女权主义的兴起,女子的身体也被纳入国族叙事。女子的身体曾长期被视作男子狎玩的对象,即使有女子以身许国,也多是在男权主导的世界最大化开发与利用自己的身体资本。近代的国难强化了女子国民的身份认知,需要女性在救亡中担负一定责任。女子的救亡责任,最开始是男权视角下国族话语的一种叙事,或多或少是男权主导的世界推给女子的责任,但同时这也是女子地位提高的必然结果。在救亡的路上,人们在女子身上寄予了国族强大的美好想象。女子逐渐走进国家政治话语范畴,担负起救亡责任,这为继后的“祖国母亲”话语的生成提供了可能。
二、“母亲”与国家形象的艺术黏结
“祖”与“国”在古汉语中是两个单音节词。“祖”的意思是“始庙也”,即宗庙;“国”的意思是“邦也”,即诸侯的封地[18]。现代政治话语中的“祖国”,是西方在近代历史变迁和政治发展中,逐渐整合了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而出现的一个指称国家观念的政治意象[3]。传统中国的汉语词汇中没有“祖国”这个词,其含义隐藏在“国”的概念中,只不过多指庙堂、朝廷、君王这些偏重伦理道德层次的“国”,很少注意到疆域、领土、主权这些现代政治概念下的“国”;偶有“祖”“国”两个字在一起,但它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祖国”概念,也没有任何情感附加值。最早可见的“祖国”一词出现在郦道元的《水经注》中:“恒水又迳波丽国,即是佛外祖国也。”[19]1842年魏源所著《圣武记》中也出现了“祖国”两字:“久艳东南印度之富,特隔于各回部。至是乘各部自閧,谋由巴社以图印度。巴社者,回回祖国。”[20]这里的“祖国”并无“国家”之意,是指祖先居住的地方。在近代以前,国人没有形成明确自觉的国家意识。甲午战争后,在亡国灭种的生存危机之下,特别是经过拒俄运动的精神洗礼,中华民族的现代国家观念才开始有了一个模糊的轮廓,但仍未抹除专制社会传统的蛮夷与正统思想观念之辨的痕迹。此时经过日语的中介,“祖国”一词在20世纪初的中国开始成为现代民族国家的代称[4]。1903年5月出版的《革命军》中,多次出现了现代政治意蕴下的“祖国”这个词。其中,最为时人称道的一段话是:“我祖国今日病矣,死矣,岂不欲食灵药、投宝方而生乎?苟其欲之,则吾请执卢梭诸大哲之宝旛,以招展于我神州土。”[21]1905年陈天华在蹈海前写的《绝命书》中有一句话:“今日之中国,主权失矣,利权去矣,无在而不是悲观,未见有乐观者存。”[6]47这句话可以很好地解释邹容所说的“祖国今日病矣”。这也是“马关约成,国势日蹙”[22]时局之下,晚清知识分子对国家的一种直观感知。出于对祖国未来的担忧,他们从“革命”一词中找到扶大厦之将倾的灵光。不过,19世纪末20世纪初青年学生口中的“革命”,还不免有空谈救亡之嫌。这一时期,对不屈的中国人而言,爱国与救亡好像一对孪生兄弟,相伴而生,如影随形;同时也是热血青年的使命与担当。
女子的重要地位和她实际的处境,与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及其承载体中华民族在近世的遭遇有其相似性。特别是女子体格柔弱、纤巧,性情温顺、卑抑,这与晚清以来国力逐渐衰弱、外人不断压榨欺凌的中国何其相似。现实中羸弱的女子让人联想到式微的国家,荏弱妇女的命运恰似国家运势的投影。这一时期,女子的身体与国家的存亡及民族的兴衰开始产生一种关联,出于对国族强大的祈盼,女子身体开始被赋予政治上的寓意[23]。国族的强大在于女子的强大,而女子的强大在于体格的强健、人格的独立。晚清以来,社会的激荡将女子的身体裹挟进历史的洪流,实践层面出现了从脚踝、发式、衣着到思想、经济等改造女子的种种尝试,在此过程中有关女子身体的叙事逐渐进入历史的视野。
人是羸弱之人,国是孱弱之国,这两者虽然有一定程度的相似性,但中华民族在世界民族之林中若永远像一直处于受压迫受剥削的最底层的女子,那么国家未来何在?不解决这个问题,则“女子”与“国家”只是有着一定程度上的相似性,并不一定会产生意义上的黏结。现实中人们注意到原本至弱的女子可以反转变成至强之人,“妇女弱也,而为母则强。”1902年2月,化名“中国之新民”的梁启超写道:“夫弱妇何以能为强母,唯其爱儿至诚之一念,则虽平日娇不胜衣,情如小鸟,而以其儿女之故,可以独往独来于千山万壑中,虎狼吼咻,魍魉出没,而无所于恐,无所于避。大矣哉,热诚之爱之能易人度也。”[24]1914年有人对此进行了深度阐释,原本羸弱污贱的“国民母”如何得以变成“至强”之人:“平日之工愁善恐,自居于最懦最弱之地位者,由乎情。其以至弱之位至为母而易居至强之点,亦非由情所牵制乎?夫母之于子爱,情恳挚莫敢与敌。举凡饮食起居寒暖琐屑之事,躬亲操作,旦夕悬心,一若自忘其懦弱者,此无他,以其爱之深而情之笃也。”因此,“人之强弱本无一定之气质”“盖天下可有处于境地之所不可不弱,亦有迫于理势之不可不弱,亦有迫于理势之不可不强”“为火焰及室,则弱女可以踰重垣;子女临山河,则慈母可以登深谷、渡危桥。此由于情之不可遏抑,由势之所不得不然者也。”[25]在20世纪20年代以前,中国社会已经有这种普遍的共识:弱女为母则强。1918年8月20日鲁迅在给许寿裳的信中也提到:“人有恒言:‘妇女弱也,而为母则强。’”[26]弱女子为母则强,强与弱可以相互转化。“弱即强之机,强即弱之渐。此乃循环之道然也,顾有弱可强而强反弱者。”[27]国家运势也应如此。鸦片战争以来沉疴宿疾的中国需要一个契机,犹如女子为母则强一样,才可开启一个强国奋起之路。这一时期,国人注意到女子与祖国之间有很多契合点,而且在女子为母则强的事实上寄予了对祖国强大的渴望,实则已经孕育出“祖国母亲”的话语内涵。
1919年,求学于日本的郁达夫基于自己的留学生活体验创作了白话短篇小说《沉沦》。小说中的主人公“我”,在溺海前的内心独白将祖国拟人化了:“祖国呀祖国!我的死是你害我的!你快富起来,强起来吧!你还有许多儿女在那里受苦呢!”[28]这里“祖国母亲”的隐喻呼之欲出,只不过这里“我们”是祖国的“儿女”,祖国的性别倾向还不是十分明显,可以是“父亲”,也可以是“母亲”。最早明确将“祖国”譬喻成“母亲”的是闻一多。1925年3月,闻一多深感弱国子民在国外承受无处不在的歧视与凌辱,出于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对祖国的深情挚爱,奋而写下了发聋振聩的爱国之作《七子之歌》。1925年5月,《七子之歌》正式在国内综合周刊《现代评论》上首次发表。其时正值国内五卅惨案引发新一轮反帝爱国运动高潮,《七子之歌》一经问世就引起国人强烈的思想共鸣。在这组诗歌中,闻一多以拟人的手法,将中国当时被列强掠去的澳门、香港、台湾、威海卫、广州湾、九龙岛、旅顺和大连“失养于祖国,受辱于异类”的“失地”,比作远离母亲的7个孩子,以第一人称写法哭诉他们受尽异族欺凌而渴望回到母亲怀抱的强烈心声。每首诗歌的最后都以“母亲!我(们)要回来,母亲!”[29]作结,掷地有声,一唱三叹,一种深沉的赤子情怀,一种对厄运的抗争、对祖国的眷恋与执念,溢于言表。《七子之歌》是“祖国母亲”隐喻的发轫之作,可视为汉语中“祖国母亲”隐喻的起源[2]。20世纪20年代,“祖国母亲”这个近代以来中国人常用来称呼自己祖国的话语表述已然形成,特别是《七子之歌》广为流传,“祖国母亲”的隐喻恰到好处地表达了知识精英内心深处的忧国之情,逐渐为人接受。在以后的文学创作中,文人普遍接受了“祖国母亲”的喻示,使其成为文学形象中一个常用词汇。“祖国母亲”的喻示借助文学作品的传播在全国流行开来,由此形成一个政治和民族主义抒情常用的话语词汇。
三、作为情感表达与政治话语的“祖国母亲”
“九·一八”事变后,中华民族再次笼罩亡国灭种的阴影,一时间救亡的呼声响彻云霄。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之际,女子作为母亲、妻子、女儿、国民,需要担负的为自身、家庭、社会、国家的责任并不轻于男性。“妇女是国民之一,且而为数要占二分之一。自然,妇女关系国家兴亡,并不减于男子,恐怕还要胜过男性呢。”[30]一个国家的组织和社会的构成,其主体是国民。国民既有男女两性,则国家的责任也自然应该由男女两性共同承担。这一时期女子的国民身份认同以及救国的责任得到有识之士的推崇,人们对女子的抗战体验有了更透彻的领悟。宋美龄就曾从母性角度谈到女子对抗战的重大意义:“彼等有超特之人生观,能安心忍受一切之现状而植希望之光辉于其上;能运用其困难生涯中之一切,以济任何之艰危与穷乏;能艰苦卓绝而不屈服于困难;能秉持非常之果毅与勇气,以战胜任何之困厄,而实现其衷心之所赠与所信;更蓄有不可思议之潜在力量,埋头吃苦,百折不挠,以完成其任务。”[31]女子牺牲一切,教养子女,只求家庭的复兴,与在侵略者的淫威与蹂躏下不甘屈服、坚韧抗战的祖国又产生了契合点。中国的母性有这样一些优异的特性,国民在这种母教感化熏陶下能以为家的精神来为国,这特性已由母性而培育为民族性,所以在此基础上可以说中国的抗战是一种“母性抗战”[32]。“母性是什么?是爱、忍耐与扶持!是牺牲精神的最普遍最恒久的表现!谁还能责备一个做了母亲的人!一做了母亲,她的全生命就变做乳汁,她是在把全生命哺养她的孩子们哟!”[33]母亲是时代最好的榜样,是爱与牺牲的榜样,中华民族的抗战要具有这种母性精神,在伟大母性的光辉下完成神圣的抗战救国大业。
对抗战的母性认知有着深厚的民族历史文化土壤。传统中国是个男权主义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女子的社会地位低下,政治上无权乃至被漠视忽略。但在中国传统的文化中也一直有女子的身影,而且有时还可与男子的地位比肩。中国最早的医学典籍《黄帝内经》“天年”篇中说,人体生命的开始“以母为基,以父为楯”。人出生的体质根基取决于母亲,父亲对人的体质只起遮蔽与拱卫的作用[34]。《易传·说卦传》云:“乾,天也,故称乎父;坤,地也,故称乎母。”[35]在先民的哲学思维中,苍穹是父亲的形象,大地是母亲的形象。这种思想文化一直延续下来,对抗战时期的国家认知有着重要的影响。抗战时期,祖国在侵略者的暴行下断壁残垣,百孔千疮,大地母亲满身创痛,苦不堪言,这时候祖国是一个受难的母亲形象。
“四年前,一个可纪念的日子。敌人野马,嘶遍了祖国,铁蹄践踏到家乡。从此,祖国呵,被压住了呼吸。母亲被禁了!不能自由地歌唱,深深的,蒙上一层血痕。敌人张开贪婪的血口,铁蹄蹂遍了祖国。四年来,我们一直喘息着,我们失去了,无数的土地,美丽的河山,破碎支离。千万兄弟们,被奴役;千万姐妹们,被杀害。整整的,四年了,今天,我们的祖国,到处窜着,凶狠的野兽。太阳旗,还在飞扬,掩映着,狰狞的魅影!”[36]这是迄今所见最早的一篇在题名中出现“祖国母亲”字样的现代新诗,比那些偶在正文中出现“祖国母亲”意象的诗歌更直接,抒情性更强烈。日本的侵略战争让中华大地满目疮痍,中华子民深受兵燹之苦、黍离之悲。绝大多数国人都有过国难、身难和家难的三重体验,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紧密捆绑在一起,开始同呼吸共命运。大地母亲蒙难,个人遭受灾难,个体的抗战体验很容易与大地母亲的遭遇产生情感上的共鸣。很自然,20世纪20年代在文学艺术作品中出现的“祖国母亲”形象,到抗战时期成为了一种强烈的情感表达与政治话语。抗战时期,“祖国母亲”的隐喻最终得以定型,并在如火如荼的抗战事业中得到进一步传播。“祖国母亲”话语在情感层面表达了中华儿女对侵略者的愤慨,对伤痕累累之国家的痛彻心扉;在政治层面,它又预示着祖国儿女砥砺前行,蓄势积力,争取最后胜利的信心。
在抗战救亡的呼声中,“祖国母亲”这一隐喻通过文学和艺术的传播渠道,形成了一个以“祖国母亲”为核心意象的抒情话语网络,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中国人的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苦难深重的祖国就是我们的母亲,她饱受屈辱,遍体鳞伤,但母亲的隐忍与坚毅一定会带我们度过这段不堪回首的岁月。“祖国母亲”的喻示影响所及播撒了无数抗战的种子,无数民众惊醒了迷梦,受到了心灵的震撼。“祖国母亲”的喻示也让全国人民不分阶级、身份、地域、年龄、职业,普遍知道了抗战的意义和重要价值,激发了他们隐藏于内心的爱国观念和民族意识,使中华儿女团结在救国御辱的旗帜下,为争取民族的自救和解放,为增强抗战力量和巩固中华民族的基础,摒弃前嫌,捐躯赴国难[37]。
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为“祖国母亲”隐喻的传播提供了一个广阔的背景和丰富的情感基础,使其逐渐从文艺符号层面的情感话语变成爱国救亡的政治话语。在抗战救亡中,“祖国母亲”话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它鼓动和激励着革命的意志与精神,而革命声势的裹挟又影响了它的传播与走向。“九·一八”事变后的民族危机催生了“祖国母亲”隐喻的政治化,使其与革命和政治开始有了紧密的联系,并逐渐固化为一个代称“祖国”的常用政治抒情表达词语。
四、结语
“祖国母亲”的喻示产生于近代中国救亡的历史语境。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华民族面临深重的民族危机,客观上激发了潜藏在社会中的抗争与救亡的力量,这股力量与世纪之交逐渐酝酿出现的民族国家意识、女权思潮、革命思想等相互激荡,共同作用,从而凸显了女子的国民身份及救国责任。近代中国深重的国难让女子的身体叙事开始进入公众视野,国人在女子身上投注了有关国族运势的考量,由此在女子命运与国族气运上找到了越来越多的相似之处。妇女卑如尘埃与近代中国饱受外族欺凌的窘迫虽有几分相似,但这两个物象差异太大,原不至于让人产生更多的联想,而经过文学的艺术修饰,妇女的现实处境与国家的屈辱境遇有了修辞上的联系,形成了“祖国母亲”的意象。这一意象所譬喻的并不单纯是两者当时憋屈与沉郁的受难形象,因为女子坚韧的个性,对苦难的免疫力,对困难的承受力,对生活的执著精神,恰昭示着中华民族的复兴及屹立世界民族之林只是一个时间问题。“祖国母亲”的喻示酝酿于20世纪初,20世纪20年代经过文学大匠的艺术创作而成为一个文学词汇,抗日战争时期才真正定型成为一个指称祖国且饱带感情的常用政治话语词汇。
“祖国母亲”喻示的出现也有西方话语的影响,因为近代中国民族国家的大叙事中或多或少有着西方的影响,近代中国的政治表达也离不开对西方的模拟与参照。不过,在“祖国母亲”话语的生成中西方因素只是一种间接影响,直接因素还在于中国自身,在于中国当时特定的救亡语境,在于对传统文化中大地母亲譬喻的一种时代承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