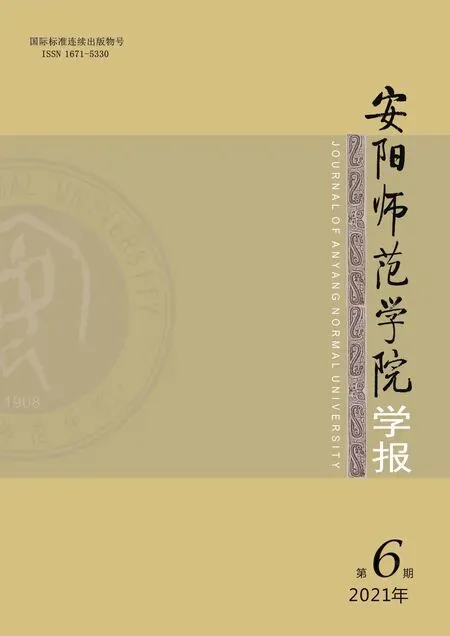罗马共和国显贵群体中收养现象探究
2021-11-28蔡丽娟钟典晏
蔡丽娟,钟典晏
(华中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9)
罗马共和国时期,在“显贵”(nobility)群体中存在着特殊的收养现象[1](P139),公元前2世纪及以后,收养案例明显增多。这一现象受到许多学者的关注,如莫泽尔的《罗马贵族党派和家庭》[2]探究罗马人的家庭与政治的联系,提及了一些影响重大的收养案例。根据他的观察,收养的主要作用是在特定情形下保障家族的继承。萨勒在《罗马家庭中的家父、财产和死亡》中指出,养子的继承与亲生子的继承一样,既包括家父身份地位的传递,也涵盖宗庙祭祀事务的移交[3](P43)。对收养问题进行专门研究的有休·林赛的《罗马世界的收养》,他用一个章节探究罗马社会中的继承法则,并着重探讨养父子之间的继承[4](P97-122)。他明确指出,收养者最为普遍的动机就是子嗣的数量不能满足家族继承的需要;而被收养者可以利用收养者留下的财产和政治资源,为自己的政治生涯奠定基础。显贵群体在这方面的需求尤为强烈,因为家族的延续与继承是他们维持自身政治优势的基本前提。霍普金斯则认为,收养的作用是双重的——无子的显贵借此延续家族;多子的显贵则利用他人的政治、经济资源助力后辈的发展,同时保证原来家庭中的资源供给[5](P49)。这一论点实际上指明了收养的一部分政治作用。林赛则指出,收养是为数不多的、能够在生理关系以外创造亲缘纽带的手段之一,并梳理了“政治性”的收养。但他仍然主张,只有少量的收养实现了政治动机和结果的统一[4](P169)。然而,即便许多收养行为起初并未承担政治目的,它们却在客观上影响了共和国的政治。那么,收养对显贵群体在政治方面究竟有何影响?收养以何种方式帮助显贵维持政治优势?该文试图就这些问题展开讨论。
一、显贵群体的政治优势与内部竞争
“显贵”一词由20世纪的德国学者格尔泽尔提出,用以指代罗马共和国具有执政官权力的人以及他们的后代(本文使用更广泛的定义,见下文)[1](P27-32)。其材料依据则是西塞罗等古代作家的文本。在拉丁文中,nobilis和nobilitas均可指代显贵。Nobilis的词源是nosco(意为“知名”)加上bilis(表示能力),其本身的含义可以归结为知名、出身高贵、具有影响力[6](P1182-1183)。与此相关的另一个词汇是patricius,其词源是pater(意为“父亲”“庇护人”),专指那些自古显赫的氏族贵族,他们在共和国中期的变革之前几乎完全控制着罗马的最高官职。然而,从公元前368-367年的李锡尼-绥克斯图法(Lex Licinia Sextia,规定两执政官位置之一可由平民担任)开始,到公元前342年的格努西亚法(Leges Genuciae,要求每年至少有一位平民担任执政官),再到公元前300年的奥古尼亚法(Plebiscitum Ogulnium,向平民开放部分神职),最后到公元前287年的霍田西阿法(Lex Hortensia,规定平民大会的决议对全体公民具有法律效力),平民逐渐获得担任各种公职的资格,他们占有一个执政官位置成为政治的常态。平民大会的决议最终被赋予普遍的约束力,氏族贵族在各类政务中的权力垄断则不断被打破。如此融合而成的“牙座官”群体及其后代即为“显贵”(牙座官的拉丁原文是curulis magistratus,这些官员有资格使用带象牙装饰的座位,象征着他们在各自的领域内拥有全权imperium,执政官也包括在内)。上述法案陆续通过后,“显贵”这一概念开始取代氏族贵族成为政治关键词。实际上,这一系列法案的通过与其说是全体平民或大众的胜利,不如说是小部分上层平民的胜利——他们凭借平民运动的力量迫使氏族贵族让步,通过改革清除了担任公职的障碍,利用财富和社会影响力取得了与氏族贵族分享共和国最高权力的机会。所谓 “权力共享”(power-sharing)[7](P228)的含义即在于此,这一概念恰当地指明了显贵群体的融合性特征。此外,显贵的开放性也使得政治上的“新人”(homo novus,凭借自己的能力和功绩达到高位的人)[1](P28-34)获得了跻身高位的可能。但这种开放性非常有限,是否吸纳新人的决定权很大程度上掌握在显贵群体内部,新人的出现许多时候被认为是对执政官职位的玷污;显贵家族常常强调——他们比任何人都更有资格担任那些最高的职位,这种观念逐渐为选民所接受[1](P52)。
显贵群体虽然改变了氏族贵族那种完全封闭、世袭的性质,但显贵身份的传承主要还需依靠家族关系。罗马社会将家庭看得十分重要,以至于国家制度都在一定程度上模仿家庭,而罗马人“人生的目的和精髓就在于自有家室和儿孙满堂……一个家族或是一个氏族的绝灭却是一场灾难”[8](P53)。相比于其他阶层,显贵家族的继承具有更加重大的意义:从现实角度,显贵的身份、地位、财产是家族内部代代相传的重要资源,合法继承人的缺席意味着尊贵地位的终止,以及财产的外流;在情感方面,家族宗庙是他们引以为傲的精神源泉,必须谨慎守护,不能使之破败。当然,政治优势的维持也有赖于继承,如果合法继承人过早去世,一切其他的筹划和准备都将付诸东流。公元前179年前后盛极一时的弗尔维乌斯(Fulvius)氏族就经历了这样的厄运:氏族首领在172年面临绝嗣的局面时选择自杀,整个氏族只有依靠另一个分支才得以维系,他们对政局的主导权也旁落他人手中。一般来说,一旦亲生子嗣的状况无法满足需要(包括无子、早夭和能力缺陷等),显贵家族就会考虑将收养作为一种补救措施,用以确保家族宗庙的延续,这方面的探究将构成该文的重点之一。
另一方面,虽然罗马的最高权力长期在显贵群体之间分享,但他们并不是一个利益、志趣高度统一的整体,他们内部存在着权力竞争。根据执政官年表以及莫泽尔对罗马政局的分析,公元前367年至公元前355年期间,亦即显贵崛起之初,他们之间就存在一定的对立。埃米利乌斯(Aemilius)、塞尔维利乌斯(Servilius)两个氏族贵族与李锡尼(Licinius)、格努西乌斯(Genucius)两个平民氏族组成一个较为温和的集团,而曼利乌斯(Manlius)、法比乌斯(Fabius)等氏族贵族则倾向于支持平民领袖李锡尼·斯托罗(Stolo)的激进改革,让平民执政官的出身更加多元化。相对晚近的政坛也充斥着类似的合作与竞争,并且体现了收养的政治作用。平民氏族弗尔维乌斯(Fulvius)的崛起是最佳的例证:他们迁入罗马后,通过与氏族贵族法比乌斯的合作登上政治舞台,公元前322年首次有成员当选执政官(属于Curvus一支,其同僚出自Fabius氏族);公元前180年昆图斯·弗尔维乌斯·弗拉库斯(Quintus Fulvius Flaccus)在当年的执政官去世后担任了递补执政官并主持了下一年的选举,由此缔造了公元前179年的“弗尔维乌斯王朝”——当年的两名执政官在血缘上均出自弗尔维乌斯·弗拉库斯家族,实际上是一对亲生兄弟(分别是Quintus Fulvius Flaccus,是前180年执政官的同名表亲;以及具有养子身份的Lucius Manlius Acidinus Fulvianus)。而且当年的监察官是公元前189年曾任执政官的弗尔维乌斯·诺比利奥尔(Nobilior),这意味着弗尔维乌斯氏族的两个分支垄断了公元前179年的三个最高职位。此后,弗尔维乌斯氏族还在公元前180年、179年的副执政官人选中提拔新人,培植自己的势力,再帮助他们在之后的年份里顺利晋升,以此排斥异己、延续集团势力。这种局面反映了一个上层平民氏族在政治竞争中的暂时胜利,收养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正是因为179年兄弟执政官中的一人被氏族贵族曼利乌斯·阿西迪努斯(Acidinus)收养,改换了社会身份和阶层属性,他们同时担任执政官这件事才符合政制规范。
由此可见,显贵主导的政治是一种权力共享与权力竞争并存的政治。一般认为,显贵对政治的主导很大程度上要靠依附民(client)的支持。在任何需要表决的场合,后者可以帮助显贵建立优势,使其能够顺利地担任公职、主导集会、避免被定罪[1](P100)[9] (P387)。但实际上“没有任何资料表明,平民可以偏离他们自身的利益,根据他们各自或集体依附的上司(庇护人,patronus)的要求投票”[10](P264)。而在公元前2世纪下半叶的不记名投票改革之后,庇护人甚至无法查证其依附民的投票情况。另外,显贵门下的依附民有很大一部分不在罗马,而是身处其他城市,作为一个整体受到庇护,无法普遍参与罗马城中的表决。因此,即便某位显贵比他的对手拥有更多的依附民,他也无法确保自己在权力争夺中占据上风。实际上,显贵的政治优势是从全方位的竞争得来的,而不是由制度或习俗直接赋予的。他们必须想方设法提高自己的竞争力:除了在战场上建立功勋,还需要举办公共活动以笼络人心,尽可能地争取每一位公民的支持;必要时还需相互达成协议、调度政治资源。由于在出身上具有天然的劣势,平民显贵会更加迫切地需要盟友的支持,因而也更加需要血缘之外的纽带,用以攀附那些枝繁叶茂的氏族贵族。实际上,不论出自哪个阶层,当显贵家族的内部条件无法满足竞争的需要时,他们往往选择通过对外构建关系网甚至建立政治集团,整合可供利用的政治资源,进而实现利益最大化。布隆特指出,显贵群体内存在着众多的集团或派系(factions),它们组建的方式包括最基础的家族内部的联合,以及联姻和政治友谊等等[9](P36-37)。
实际上,收养同样能作为一种策略,发挥建立和维系政治集团的作用,即使它不如上述其他几种方式那样普遍(从命名法判断,公元前249年-前50年只有4%的执政官具有养子身份)[9](P49)。随着时间的推移,显贵的收养行为在公元前2世纪逐渐流行起来,时常带有政治上的目的。具有代表性的案例为:大西庇阿(Publius Cornelius Scipio Africanus)的妻子是“马其顿的”保卢斯(Lucius Aemilius Paullus Macedonicus,公元前182年、前168年的执政官)的姐妹,而大西庇阿的儿子收养了保卢斯的次子,即后来所谓的小西庇阿(Publius Cornelius Scipio Aemilianus Africanus)。保卢斯的长子则由公元前181年的外务副执政官昆图斯·法比乌斯·马克西姆斯(Quintus Fabius Maximus)收养,后来成为公元前145年的执政官。这位法比乌斯另外还收养了公元前169年执政官塞尔维利乌斯·凯皮奥(Gnaeus Servilius Caepio)的一个儿子,这个养子和他的亲生兄弟三人于公元前142年至公元前140年先后担任执政官[2](P99-144)[4](P147-148)。四个显贵家族的两代人之间就发生了三次收养,显得非常密集,不容忽视。因此,收养在政治策略上的作用,将构成该文探究的重点之二。
二、收养与显贵的继承
收养的主要作用是保证家族继承。判断一个人是否拥有显贵身份,主要的依据就是他的氏族前辈(最好出自同一家族)是否有人当选牙座官,因此显贵身份显然是通过家族关系传递的,随之传承的还有这一身份带来的政治优势[5](P59)。然而,罗马贵族群体的高死亡率是众所周知的,占比较高的死亡原因包括一般疾病、传染病、战争等,有限的卫生条件加剧了生命的流逝。根据霍普金斯的数据模型,能顺利活到20岁的罗马常住人口只占40%-60%,而其中的三分之一左右活不到40岁[5](P72)。可见即使是多子的家庭也无法避免绝嗣的风险。另外,由于“荣誉阶梯”(cursus honorum)和公职间隔期的设置,高级官职的适龄往往很高;而随着后辈的缓慢升迁,家族前辈积累的政治资本却在不断损耗;而且罗马显贵重视军功,政治生涯通常都从危险性较高的军团长官(tribuni militum)开始。因此,如何保证家族后辈顺利通过“荣誉阶梯”、延续家族的地位与政治优势,成为了显贵们的重大课题。
公元前2世纪的弗尔维乌斯氏族之所以迅速衰落,直接原因就是后辈的早亡——弗尔维乌斯·弗拉库斯家族当时的首领、公元前179年执政官、公元前174年监察官昆图斯有两个儿子在伊利里亚(Illyricum)服役,其中一个不幸战死,另一个患上重症;在李维的记述中,这成了昆图斯于公元前172年自杀的导火索,“忧伤和恐惧交织,击垮了他的意志”[11](P56)。盛极一时的弗拉库斯家族遭受重大打击,此后直到公元前135年才再度出现执政官。不论对昆图斯的自杀作何解读,两个儿子的不幸无疑起了助推作用:亲生血脉难以为继的现实摧毁了早已拟定的政治蓝图;他本就背负渎神的指控,加上这次重大不幸,他的宗教情感也遭受重创。这种艰难的局面与他早年的情况形成了鲜明对比:那时弗拉库斯家族尚处于多子的状态——正是因为他的兄弟卢基乌斯被氏族贵族曼利乌斯收养,兄弟两人才得以同时担任公元前179年的执政官;这次收养发生后,他还有至少一个兄弟留在原来的家中。卢基乌斯·弗尔维阿努斯被收养的起因不甚明了,很可能是曼利乌斯·阿西迪努斯家族的卢基乌斯(养父)膝下无子,为避免绝嗣,向联盟的弗尔维乌斯·弗拉库斯家族寻求帮助。据昆斯特(Kunst)推测,这次收养发生的时间不会晚于公元前205年[4](P147),亦即弗尔维阿努斯担任副执政官之前17年,距离其执政官任期更是有26年之久。如此看来,“兄弟执政官”的促成不可能作为双方家族的初始计划,这次收养起初仅仅发挥着如下作用——实现被收养者对收养者的宗庙、财产与地位的继承,保障家族的延续。
收养根据形式分为三类,显贵家族对继承的迫切性影响着他们对形式的选择。自权人收养(adrogatio)古已有之,而他权人收养(adoptio)最迟在十二铜表法时期开始应用。这两种收养同属于“完整收养”,也是法定的收养形式,区别于后来兴起的遗嘱收养(adoptio per testamentum)。自权人、他权人的概念都是对于被收养者而言,自权人(sui iuris)指的是拥有家父权力的人,他权人(alieni iuris)指的是处于家父的父权之下的人。在自由人的范围内,他权人一般等同于家子(包括女性)[4](P65)。他权人被收养时刚从生父的父权之下解放出来,只身进入新的家庭,不带去妻子、儿女和财产;当收养者去世时,被收养者直接成为自动继承人,在无遗嘱的情况下自动参与遗产分配、身份继承,就像逝者的亲生儿女、处于夫权之下的妻子一样。自权人(sui iuris)的收养程序却更加复杂烦琐,被收养者付出的代价也更大:它的执行需要经过大祭司的调查和库里亚大会的商讨;被收养者经历“人格减等”(capitis deminutio),失去自己的父权,转而由收养者的父权支配,被收养者的整个家庭包括妻儿、财产都发生转移,原来的家庭宗庙随之消失。如此一来,当收养者去世、安排继承事宜之时,要考虑的就不仅仅是被收养者本人,还有他带来的整个家庭。正因如此,他权人在大部分情况下往往是更佳的收养对象,它可以保全双方家族、免去烦琐程序,效果相当于在显贵群体内部进行“后代再分配”。弗尔维阿努斯和埃米利阿努斯(小西庇阿)的事例均体现了这一点。与此相对,自权人收养往往是出于形势所迫,显示出收养者家族引入一个外人来实现继承的迫切需要。在这种前提下,自权人收养的目的大多比较单纯,即对收养者家族宗庙、地位和财产的继承,包括平民或氏族贵族身份的传递。西塞罗曾经详细阐述这一点,并列举了公元前71年执政官俄瑞斯忒斯(Gnaeus Aufidius Orestes)和公元前61年执政官卡尔普尼阿努斯(Marcus Pupius Piso Frugi Calpurnianus)的事例,作为自权人收养的模范[4](P76)。这两起收养事件完全符合自权人收养的四条规范:第一,收养者没有男性后代且没有生育能力;第二,收养者必须要年长于被收养者;第三,收养双方不带有出乎继承以外的动机;第四,收养双方必须出于自愿[4](P76-77)。传统规定的大祭司调查覆盖了这四点,从而尽可能地确保收养仅仅是为了满足家族继承的需要。自权人收养的政治意味较少,还因为双方之一的家庭需要直接融入另一方的家族。如此一来,如果一位收养者的目的在于与收养对象所属的整个氏族拉近关系,那么他完全可以选择对方氏族中处于家子(他权人)地位的人进行收养,而没有必要排除万难去收养一位家父(自权人)。
除了自权人收养,遗嘱收养的目的也相对单纯,即以家族继承为主。遗嘱收养是较晚时期流行的一种很可能不具有法律效力的收养形式,它只发生在立遗嘱人死亡、遗嘱生效之时,内容仅仅包括被收养者继承收养者的财产,通常(并非强制)冠上收养者的姓名作为回报;它不涉及双方的家庭生活,不产生新的父权,不能改变被收养者的阶层属性和部落归属,甚至可以被拒绝接受。因此,遗嘱收养相对于完整收养更像是一种协议,更加灵活,程序简单,女性也可作为收养者[4](P79-86,160-168)。而从具体事例来看,可靠的最早记载出现在共和国后期,最令人瞩目的便是恺撒对奥古斯都的收养,后者设法从中获得了比一般情况下更多的政治资源。由于遗嘱收养传递政治资源的效率较低,在此仅作以上交代。
与道德要求相悖的是,以继承为目的的收养也可能兼有政治意图:在权力共享原则确立后,平民的身份被赋予了一定的政治意义—— “‘向平民转变’(transitio ad plebem)被个人或氏族用作获得保民官等特定官职资格的手段。”[4](P174)这种手段的盛行使得共和国晚期的收养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权力争夺的工具。运用这种政治手段的典型案例当属克洛狄乌斯(Clodius)的收养,出身贵族的他在公元前59年被平民丰特尤斯(Fonteius)收养,并于公元前58年就任平民保民官。而根据西塞罗的说法,这次收养严重触犯了自权人收养的四条规约;它之所以能够实现,是因为当年的大祭司恺撒(Gaius Julius Caesar)和庞培(Pompeius Magnus)的帮助。此次收养中,家族继承只不过是表面上的伪装,政治上的需要才是真正的意图。克劳狄乌斯取得保民官资格后不久便被养父解放,他也从未改换家族宗庙的归属[4](P178)。此外,由氏族贵族转变为平民并不是这种策略的唯一运用方式,根据不同公职或神职的资格要求,显贵可以决定如何利用收养来改换身份,从而达到他们的政治目的。例如,公元前57年,一位科尔内利乌斯·兰图鲁斯(P.Cornelius Lentulus Spinther)通过被曼利乌斯氏族收养而规避了制度上的限制,与一位同族人成为祭司同僚[4](P172)。
总之,不论选择哪种收养形式,收养的过程都包括继承权的相关问题,因而往往伴随着社会身份的转变和资源的再分配,也就比较容易承载着除继承之外的意图。当然,由于政治的非世袭性,此时的收养尚且无法直接传递政治权力,因而其中的政治意图也相对次要;相比之下,罗马帝国早期皇帝之间的收养关系则真正地以政治权力的平稳传递为主要目的。
三、收养与显贵的政治策略
罗马共和国时期,还有一些收养行为以政治意图为重,兼顾继承的需要。虽然它们在数量上不占主要地位,但其对政治具有显著影响,故而具有考察的价值。前文曾经提到,公元前179年执政官弗尔维阿努斯的收养起初并不关注政治权力的垄断,但政治意图在其中占有一定的地位,因为不论是否同属于显贵,是否分享政治权力,氏族贵族与平民之间仍具有相当明确的差异。阿西迪努斯家族不顾宗教、社会等方面的阻力,率先促成氏族贵族与平民之间的收养关系[4](P146),绝不仅仅是出于对绝嗣的恐惧。弗拉库斯家族则有意利用收养关系加固与氏族贵族的联盟关系,为长期掌握政治主导权打下基础。莫泽尔指出,这两个家族之间已经长期进行通婚,这可能为实现跨阶层收养提供了一定的支撑[2](P185)。收养与联姻于此一齐发挥作用,成为联合显贵家族、维系政治集团的有效策略。
一般来说,作为一种政治策略的收养多采用他权人收养的形式。类似联姻,多子的家庭中的儿女尊奉家父或家族首领的意志加入另一个家庭。收养主要可以从两个方面实现显贵的政治目的:首先是利用友好家族的政治经济资源扶植后辈,尤其是在生身家庭境况不佳之时。例如公元前3世纪晚期的保卢斯家族,老埃米利乌斯·保卢斯在公元前216年的坎尼战役中战死,其长子——后来的“马其顿的”保卢斯尚未成年。莫泽尔推断,就是在此种不利局面下,老保卢斯的次子过继给了他在公元前219年的执政官同僚李维乌斯·撒里纳托(Marcus Livius Salinator),得以利用后者的家族资源顺利成长[2](P215)。其次是巩固与友好家族的政治联系及合作。虽然上述这个养子本人没有取得政治上的成功,他的亲生兄长(即“马其顿的”保卢斯)和养父家里的兄弟盖尤斯·李维乌斯·撒里纳托(Gaius Livius Salinator)却在公元前191年共同担任副执政官;他的儿子盖尤斯·李维乌斯·德鲁苏斯(Gaius Livius Drusus)还与保卢斯的亲生子小西庇阿一同担任了公元前147年的执政官。如此一来,通过这次收养,双方家族的政治联合从老保卢斯那一代向下延续了两代人。前文所列举的西庇阿-埃米利乌斯-法比乌斯-塞尔维利乌斯之间纷繁的收养关系,也处处体现着家族间的联合意图。其中一组收养关系涉及三个家族:塞尔维利乌斯与埃米利乌斯两个氏族之间的合作关系从公元前4世纪延续到了公元前2世纪,老保卢斯在公元前217年执政官塞尔维利乌斯·盖米努斯(Gnaeus Servilius Geminus)的帮助下当选了次年的执政官;“马其顿的”保卢斯在公元前168年当选执政官,则受惠于前一年执政官塞尔维利乌斯·凯皮奥(Gnaeus Servilius Caepio)。在家庭方面,如前所述,“马其顿的”保卢斯的长子与这位凯皮奥的长子都过继给了公元前181年副执政官法比乌斯(Quintus Fabius Maximus),从而在第三方的家庭中成为兄弟。法比乌斯收养两个养子的动机很可能是缺少亲生子嗣,而另外两方的意图更多地在于巩固政治合作。然而,这种联合的策略并不总是有效的。事实上,在公元前143年至公元前140年的八位执政官中,凯皮奥家族的三兄弟(包括那名养子)与另外一对兄弟梅特鲁斯(Caecilius Metellus)组成一条战线,而他们的竞争对手正是属于小西庇阿集团的庞培乌斯(Quintus Pompeius)和莱利乌斯(Gaius Laelius)[2](P226)。实际上,显贵之间的关系非常繁杂,每个家族的最终目的都是自己利益的最大化;因此,在某段时间或某次政治路线的争斗中,这些关系孰轻孰重影响到一名显贵及其家族的抉择。收养只是家族间联系的其中一种形式,当它促成的联合关系不足以压倒这名显贵的其他关系时,它作为一种政治策略就很可能会归于失败。
收养固然能帮助显贵维持政治优势,但也可能付出巨大的代价。“马其顿的”保卢斯的第一任妻子来自帕皮利乌斯·马索(Papirius Maso)家族,她在生下两个儿子后被抛弃;后一任妻子也生下两个可以作为继承人的儿子,保卢斯于是将两个年长的儿子过继出去。按常规,这对兄弟没有资格参与原家庭地位、财产的继承,也不承担任何义务。但意外的是,保卢斯两个较小的儿子在他从马其顿归来的凯旋式前后相继夭折,导致他于公元前162年去世时在法律上是无子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小西庇阿兄弟参与了父亲遗物的继承,尽管他们并不能阻止保卢斯家族世系的灭亡(后来冠上Paullus作为家族名或绰号的Aemilius实际上来自早先的Lepidus家族)。这一案例中,收养的策略起初看起来代价轻微,最后却成了保卢斯家族的致命伤。在这一系列事件发生后,小西庇阿将他的养祖母(血缘上的姑姑)和养父交给自己的大部分遗产交给了自己被抛弃后境况不佳的母亲。在生身母亲去世时,他也参与了遗产继承,并将这部分财产让与了他的亲姐妹[12](P627),由此成就了自己慷慨的名声。
总之,收养发挥的政治作用,主要在于显贵家族层面的联合与竞争;而个人也能通过被他人收养,谋求政治生涯更快更好地发展。尽管收养的动机、形式,以及随之而来的家族关系、继承事宜之间存在一定的联系,但这些要素并不是严格对应的,偶然因素和个人行为可以影响收养关系及其政治作用,造成动机、过程、结果之间的错位;本文只能立足于文献中反映的社会规范和已经考证的史实,对显贵群体中的收养现象及其作用进行初步的分析,疏漏之处,请阅者包涵。
综上所述,罗马显贵的收养大部分都以继承为主要目的,意在避免家族灭亡,延续显贵地位。同时,收养也能作为一种政治策略,帮助显贵家族在“权力共享”“权力竞争”中维持政治优势,即使它的结果不一定符合预期。形式上,自权人收养和遗嘱收养的目的较为单纯,即以家族继承为主。而作为政治策略,他权人收养比遗嘱收养有效,比自权人收养简便,故而更受青睐。除此之外,收养现象并不仅仅出现在共和国时期的社会上层,它还构成了帝国早期帝位递嬗机制的重要部分:在尤利-克劳狄王朝期间,“被皇帝过继为子是得到军队、贵族和民众支持的最重要一环”[13]。这两个时代的收养之间的联系与区别,或许可以作为今后研究的一个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