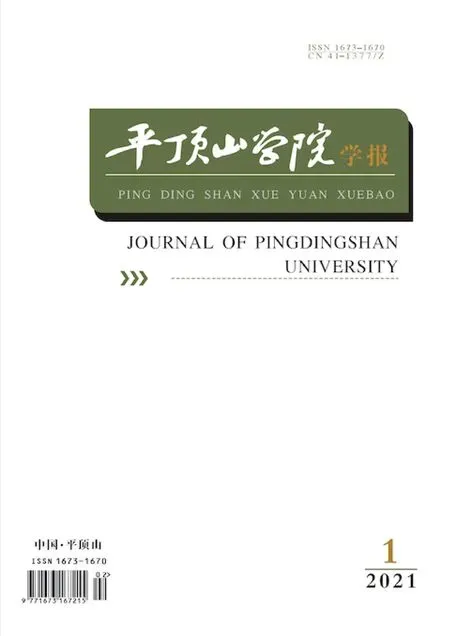现实世界之“重”与可能世界之“轻”
——论王小波《万寿寺》的可能世界叙事
2021-11-28杨深林
杨深林
(湖北工程学院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湖北 孝感 432000)
中国当代著名作家王小波“时代三部曲”之《青铜时代》中所收录的中篇小说《万寿寺》具有极其复杂的文本结构,特别是主人公“我”所在的“现实世界”与“我”创作中的湘西—长安的“可能世界”形成了深刻的互文与指涉关系。《万寿寺》不仅可以从元叙事、戏仿与互文等后现代的经典叙事学层面,或者是从虐恋、狂欢、唯美、失忆、寓言与自由主义等思想层面进行解读,也可以从后经典叙事学之“可能世界叙事学”的角度进行综合解读。
可能世界是“世界的可能的存在方式,是我们假设过去事态、预测未来事态、制订行动方案的思维工具”[1]。现实世界则是世界的实际存在方式。而文学中的可能世界则是叙事虚构世界。从可能世界叙事的角度来看,《万寿寺》中作者所在的现实世界、叙事者“我”所在的文本现实世界与叙事者“我”的幻想虚拟世界之对峙、交织的背后,向我们昭示了不同类型价值观的碰撞,最终凸显作家王小波对诗意世界与个体价值的诗性追寻,特别是他对“消极自由”价值立场的审美性持守。
一、《万寿寺》的虚构世界与现实世界相平行与独立
虚构世界与现实世界有实质的差异却同样真实,并有着自己的独特属性。
(一)虚构世界的认知非完整性
从认识论来看,虚构世界是由符号创立的非现实世界,是人类心理世界的特定产物,虚构世界的不完整体现了人类对现实世界认知的不完整。作为知识分子作家的王小波根据自己的生活经历与对中国历史、现实的思考出发,以知识分子这一特定人群作为主人公,创作了一系列的虚构作品“时代三部曲”来反思与观照中国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万寿寺》为我们创造了一个压抑的虚构世界:“我”作为年轻知识分子对所在单位的压抑与不满,并以写作作为对不合理现实的消极反抗,但最后终归无用,还是得向“无趣”的现实投降。这部小说同样延续了王小波一以贯之的对中国知识分子生存状态关注的主题。
小说中的认知的不完整性体现在主题与叙事两个层面。在主题层面,王小波通过知识分子这一特殊群体的喜怒哀乐来折射20世纪中国人仍处在前现代的生存境遇。20世纪的中国经历了巨大的风云变化,知识分子只是时代大变局中的一小部分人,并不能全面反映中国复杂而多维度的历史与现实。王小波在《万寿寺》中以其自由主义的文化立场对以“万寿寺”为象征的中国传统文化极尽嘲讽之能事,虽切中某些痼疾如礼教的虚伪,却忽视了中国传统文化对人自身及人文理性的张扬,从而对西方文化中存在的过分崇拜器物与科技理性而具有纠偏作用;在叙事层面,王小波竭力建构虚构世界的不完整性最大化,打破传统情节的线性叙事,而是以主人公生活的现实世界与小说建构的虚构世界互相交错与破碎的叙事风格表现主人公对现实的不满与愤懑之情,只能以写作来反抗,生活与小说文本杂糅,呈现了主人公只有对小说反复的改写来抒发自己愤怒而无奈的生活困境。
(二)虚构世界的认知聚焦性
虚构世界体现了人类从特定视角对现实世界的认知,所以其认知广度是受限的,但获得了更为集中的认知强度。虚构世界聚焦于现实世界或心理世界的某一侧面,通过信息筛选或陌生化手法使得世界的某个层面得到最大程度的凸显或强调,使我们从他者的角度重新审视现实世界,或获得被日常生活自动遮蔽的某种洞见。《万寿寺》以第一人称的内聚焦叙事的视角来展开情节,严格遵循从“我”的角度呈现我的所看和所想,淋漓尽致地表现我的内心冲突和漫无边际的思绪[2]27-28, 而对他人的所想或不熟悉的环境则保持缄默。主人公“我”失忆之前是一名标榜“自由派”而生性叛逆的年轻学者,并不喜欢研究所压抑而无趣的学术氛围,于是践行福柯“通过写作来改变自己”[3]180的理论主张,以自己的文学创作戏谑和反抗古板无趣的“学院派”。后来在一次车祸当中轻微失忆,于是小说就从“我”出院后回到单位所在地“万寿寺”开始阅读昔日的创作手稿寻找自己失去的记忆开展情节,向我们展现他对自己手稿的阅读与评价,以及对现实生活的种种不满。同时,他极尽所能地把手稿中以薛嵩与红线的爱情为主题的“湘西—长安世界”写得如此地诗意而自由,更加反衬现实世界的无趣与压抑,最后《暗店街》的主人公花费了毕生精力都没有找到记忆,而“我”只用了一个星期就恢复了“令人倒胃”[3]227的记忆。
中国当代作家中以知识分子生活为题材的作品不在少数,但是能够把知识分子的生存境遇写得如此透彻与复杂的作家屈指可数,王小波是其中之一。王小波的《万寿寺》 跳出了传统的以知识分子生活为主题的小说动辄控诉时代不公(知青文学等),以及向琐碎日常沉沦(《一地鸡毛》等新写实)的两极化的创作套路,而是以一个年轻知识分子的视角向我们展现了坐落在“万寿寺”的学术机构中的知识分子的压抑与无趣的生存现状,揭示了中国特殊群体之一的知识分子生存状态的复杂性:“我”既不是启蒙等“宏大叙事”中为生民立命的时代弄潮儿或弃儿,也非“微观叙事”中对现实生活俯首称臣,被“一地鸡毛”的庸俗现实压垮而沉沦的“小林”式卑微人物,而是一个位卑却有梦想的普通知识分子——“我”以写作来影射中国历史、现实社会,努力追求诗意与有趣的生活,反抗僵化的传统文化与刻板的学术体制。从小说背后我们可以看到,王小波笔下的知识分子形象摆脱了传统写作中“为生民立命”与沉沦于现实欲望与琐碎的扁形形象的局限,创造了一个个体生存困惑与呢喃而同时向历史敞开的圆形形象。王小波的写作“消除了‘公共写作’与‘私人写作’之间赌气般的裂痕,使二者相互关照、相互滋养”[4],体现了他对中国知识分子生存命运的清醒定位与思考。
(三)虚构世界的不可能性
虚构可以创造出逻辑上的不可能世界。有些事实我们可以通过词语创造出来,但在现实世界中无法存在。《万寿寺》中写漂亮的女刺客半夜行刺薛嵩未遂而被捉住,并被处以斩首的极刑。从现实经验来讲,被斩首后人会立即死亡。但是,女刺客的人头没有身体以后不仅没有立即死亡,还活了几天。女刺客人头的皮肤颜色从瓷白到变成有褐斑的几天中,像平时一样有健全的生理功能:它能睡觉做梦,它能思考,甚至同时可以与红线对话。这种人被斩首后脑袋离开身体还能够生存几天才死亡的情况只可能在虚构世界中存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可能存在的。
后现代的“元虚构”文学叙事以“如何写小说”为主题来暴露创作及其修改过程,向我们展示了不可能世界的不可能性,打破了传统写作掩盖虚构世界的虚构本质并不断向真实趋近的假象,揭示了虚构只是一场话语游戏的残酷事实。《万寿寺》中“我”是“自我意识”的叙述者。“自我意识”的叙述者是指叙述者“意识到自己的存在,并出面说明自己在叙述”[2]45-46。作为“自我意识”的叙述者“我”在失忆后阅读自己旧时的小说手稿并加以评论和改写,把小说的创作过程而不是情节作为探讨的中心。但是,面对强大而无趣的现实世界,“我”沉湎于薛嵩和红线爱情的“湘西”虚构世界终归要被打破,“我”恢复了记忆,却“心情惨然”,又要到压抑的“万寿寺”上班,“这好像是千秋不变的命运”[3]235。
简言之,一方面,虚构世界虽然是人类的心灵情感活动的符号建构,但并不能完全割断与现实世界的历史文化关联,而是建立在现实经验基础上的艺术虚构;另一方面,没有叙事虚构,我们无法表征与认识现实世界,对虚构世界的创作与体验会间接地调整我们对现实世界的看法。《万寿寺》虽然以一个失忆者对小说创作过程本身的探讨作为主题,并建构了一个充满诗意的虚构世界,与他生活的压抑无趣的现实世界形成鲜明的对比,但是主人公在评论小说以及讲述自己的生存状态时不断对中国社会历史现实进行戏谑与调侃,这是王小波建立在对中国历史现实与知识分子命运的深切体悟与思考之上进行的艺术变形与虚构。同时,《万寿寺》是关于中国现实的寓言与表征,折射了王小波对中国知识分子生存状态的深邃思考,摆脱了之前同类题材小说中知识分子境遇的单维性,要么是民族—国家宏大叙事中呐喊或怨艾的存在,要么是市场—日常微观叙事中沉沦或清高的存在,使我们从主人公看似波澜不惊的日常生活中窥见千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的根本困境以及王小波对知识分子自身弱点的某种自觉反省。
二、《万寿寺》内部幻想的虚拟世界成为叙事的中心
叙事的虚构世界由文本现实世界与人物的梦想或心理活动的虚拟世界组成。虚构世界是艺术家从特定视角讲述我们零散的生活经验,是把相互之间毫无关联的情节与人物赋予因果联系与意义的有限叙事世界。所以,在虚构文本世界内部,虚拟世界与文本现实世界不再是平行关系,通常构成一个以文本现实世界为中心,虚拟世界围绕其运动的叙事世界。但是也有例外,比如《万寿寺》的虚拟世界则成了叙事中心,而文本现实世界则围绕其运转。
(一)庸俗世界与诗意世界相平行而存在的叙事现实世界
文本现实世界是叙事人物居住和共享的世界,在《万寿寺》中文本现实世界与虚拟世界不处在同一时空,之间也没有直接的因果联系。主人公“我”生活在充满灰色与压抑的二十世纪的北京的庸俗世界,而薛嵩生活在充满理想与自由的千年前的唐朝长安和湘西的诗意世界。
《万寿寺》的文本叙事世界是典型的框架结构,即叙事现实世界对诗意世界的展开起宏观的因果说明作用,基本不干预诗意世界的运行。小说从一开始就引用法国作家莫迪阿诺的小说《暗店街》的一句话“我的过去一片朦胧”[3]3,并在小说中反复出现,从而奠定了小说的框架叙事结构与基调:“我”因出车祸被撞成轻微失忆,在朦胧中开始了自己的寻找记忆之旅。“我”出院后,在自己的原单位历史研究所上班并阅读自己往日的小说手稿,以及与好像与我很熟的未婚女子一起生活的过程中寻找记忆,并发表自己对所生活的庸俗世界的所看所感。同时,“我”所阅读的自己旧日小说手稿是一个与现实世界截然不同的充满自由与理想的诗意世界:前半部分唐朝的薛嵩为追求自己建功立业的理想变卖自己所有家产捐得湘西节度使的官职,于是来到只有荒原与红土的湘西世界。后半部分则讲述自己在长安解救白衣女子(老妓女年轻的时候)以及与白衣女子的情史,以及“我”梦中的千年前的美丽的长安城。小说手稿的诗意世界是“我”对庸俗现实世界的不满,但又无法改变,只能通过小说创作建构的理想世界。因此诗意世界的种种情节与人物的设置都是针对无趣的庸俗世界的有的放矢,庸俗世界起到对诗意世界宏观的因果说明作用,但几乎不直接干预诗意世界的运行。
(二)幻想的虚拟世界
虚拟世界作为文本现实世界的替代性可能世界,是人物的私人世界,即人物的心理表征或祈愿现实世界所应呈现的样子,即与《万寿寺》的文本现实世界相对独立而完整的,由人物的W-世界(Wish-world,愿望世界)与虚构叙事构成的F-宇宙(Fantasy-universe,幻想宇宙)。
在《万寿寺》中,绚烂与诗意的W-幻想世界,即“我”旧时的小说手稿创造的唐朝的湘西—长安的诗意W-世界,以及“我”在阅读后对小说手稿的改写,共同构成了一个F-幻想宇宙。它与“我”生活的无趣与灰色的叙事现实世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个幻想世界不仅与“我”所生活的文本现实世界相平行而存在,而且占据了小说的压倒性篇幅,是主人公对文本现实世界的逃避,是其W-世界不能得到实现的补偿性实现。
《万寿寺》中“我”虽然是年轻的历史研究学者,却并不喜欢这种刻板与量化的学术体制,不擅长也很讨厌写学术论文,更愿意被别人叫作小说家。“我”喜欢自由而充满“诗意”的生活,但是自己无法改变以“穿蓝制服,带白边眼镜”[3]206的领导为代表的强大的“恶意”世界,所以“我”只能通过对唐传奇《甘泽谣》的戏仿,创造了一个承载自己在庸俗现实中不能实现的幻想宇宙。
在文本现实世界中,“我”的W-世界是希望自己可以过着自在和诗意的生活,可以自由地创作,可以发明各种机器,可以修理研究所坏了的热水锅炉。但是僵化的学术体制要求发表学术论文才能评职称,残酷的现实生活逼迫他不能实现自己的愿望。所以“我”的梦想只有在幻想世界中的薛嵩身上得到补偿性实现,薛嵩的生活就是“我”理想的生活:他是具有发明天赋的能工巧匠,可以自由地做自己喜爱的事情。在凤凰寨,薛嵩为了把红线追到手而制造了一个无比坚固但体现薛嵩赤诚与温柔的囚车。在长安城,他为了解救被囚禁在宝塔地下室里的恋人白衣女子,运用金蝉脱壳的计策成功地把白衣女子救出。
总之,叙事世界的动力来自文本现实世界与虚拟世界之间的冲突,造成了某些世界在文本现实世界中得到实现,而其他的世界则因为种种原因未得到现实化而不复存在。《万寿寺》的叙事动力来自“我”对自己记忆的找寻,即“我”生活的文本现实世界与F-宇宙的冲突与博弈,开始是F-宇宙具主导地位,而文本现实世界居于次要地位。随着“我”的记忆逐渐恢复,文本现实世界渐次占据主导地位,而F-宇宙慢慢降到附属地位,轻微失忆的“我”出院之后回到万寿寺上班,阅读旧时小说手稿,并在与白衣女子共同生活的过程中,“我”的记忆在一点一滴地逐渐恢复,从开头的“我的过去是一片朦胧”[3]206中,“我”阅读昔日小说手稿并发表评论,甚至改写小说的F-宇宙占据压倒性篇幅,特别是刺客来犯的情节,穷尽各种方法探索情节的各种可能性与语言的极限。但到文本的最后,“我的过去不再朦胧”[3] 252,“我马上就会想到她是谁”[3]253。随着“我”的记忆恢复,“我”的F-宇宙终归结束,宣告了“我”的W-世界的最终破灭:“当一切都无可挽回的沦为真实,我的故事就要结束了。”[3]257
三、《万寿寺》的虚构世界与现实世界之抵牾:消极自由的审美性持守
王小波自身丰富的人生阅历促使他一直在思考中国知识分子的生存境遇,把自己的思考与生存经验的点滴以文学叙事化,为我们创造了一个个充满丰富想象力与温暖多情的虚构世界。
王小波善于用丰富的想象与精练的语言营构一个充满叙述迷宫与奇情异想的虚构世界。王小波从小就具有文学天赋与爱好,不喜欢写实,“讨厌受真实逻辑的控制”[5],而偏爱想象与叙事。这种美学风格的形成使他在文学师承和知识结构方面迥异于当代大陆作家,也不同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出生的大陆作家的巴尔扎克等偏写实的传统现实主义和雪莱等浪漫主义的写作谱系,而是卡尔维诺、杜拉斯等偏想象与叙事的非现实主义乃至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写作谱系。王小波的“时代三部曲”,无论写过去的《青铜时代》(包括《万寿寺》),还是写未来的《白银时代》,以及写现在的《黄金时代》,虽然是与现实有关联,但绝不是对现实的逼真刻画,而是以“历史狂想主义”的寓言方式折射着中国“知识分子的处境”[6],乃至中国的某些历史现实。
王小波的《万寿寺》向我们呈现了一幅二元对立的世界图景:失忆者生活的现实世界是无智、无爱、无趣的滞重世界,失忆者建构的虚构世界是大智、大爱、有趣的飞扬世界。失忆者的心灵在今与古、思维与想象之间来回穿梭,“我”多么希望永远生活在没有记忆的虚构世界,但是“我”更需要记忆,虽然记忆总会和令人生厌的现实世界发生关联。最后,“我”生活的现实世界压倒诗意的虚构世界,使“我”逐步恢复了记忆,“我”又回到所栖居的悲哀滞重的现实世界,但“我”仍想回到长安城——诗意的世界,他用一句话表达了这部小说的主旨:“一个人只拥有此生此世是不够的,他还应该拥有诗意的世界。”[3]258
从这部小说我们可以窥见王小波对消极自由的审美性持守,反对积极自由对个体的肆意侵犯。按照以赛亚·伯林的看法,积极自由是主体自主决定或被允许做某事的自由,即“去做……”的自由;消极自由是主体自主决定或被允许不做某事的自由,即“免于……”的自由[7]。王小波经常引用罗素的名言作为自己的座右铭——“参差多态乃幸福的本源”[8],他反对呆板单调的独白型价值观,提倡有趣、宽松的复调型价值观。智慧、有趣与爱情的三大主题一直是王小波的不懈追求,特别是对有趣的追求是王小波小说的核心所在。他反对整齐划一、“奉承权威”的无趣生活,提倡个体思考,追求多样化的生活,用王小波的话说就是“人活着必须有尊严。你在任何地方都被当作一个人物来看待,不是一个东西来看待”[9]。
《万寿寺》中的主人公“我”在面对压抑与无趣的强大的“现实世界”时,只有通过创作来建构自由与有趣的“可能世界”来消极反抗刻板的现实世界。这二者的冲突以及“现实世界”强大的境遇,向我们昭示:叙事不仅是我们组织现实生活经验的手段,更是一种文化创造性实践,激励我们改变启蒙仍未完成的“现实世界”,为实现多样态与美好的“可能世界”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