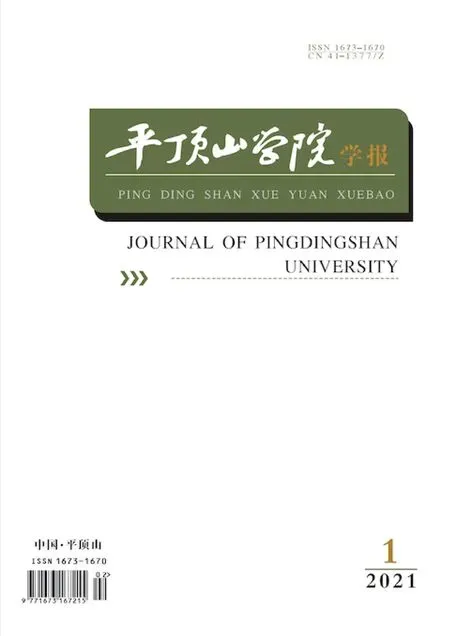民初新加坡华媒视野中的白朗起义
2021-11-28王琦
王 琦
(安徽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安徽 淮南 232001)
白朗起义作为民国成立之初的一次重大政治事件,百余年来一直为学界所关注。围绕着起义性质这一关键问题,目前学界存在两种观点:一是称之为“民国时期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伟大的农民起义”[1];另一个是视之为“一场带有辛亥革命时期历史印记的土匪运动”[2]5。这场起义爆发伊始就受到海内外华人世界的广泛关注,南洋华媒还给予了持续追踪与深度报道。1913—1914年之间出版的新加坡《叻报》《总汇新报》《振南日报》等均不惜笔墨报道此事,其中尤以《振南日报》最为详细。该报系新加坡著名报人邱菽园所创办,在南洋侨界影响颇大。这些新闻报道也使得后世研究者得以从第三方视角去审视与思考这场起义。本文以民初新加坡侨报相关报道为主要依据,分析指出南洋华媒更倾向于将白朗起义视为一场以哥老会为核心的传统秘密社会所发起的反暴政抗争,堪称清末以来一系列会党起义的“余震”与“尾声”。需要说明的是,白朗起义时逢二次革命,起义军与孙袁两派之间的关系是海外舆论关注的焦点,因此,白朗起义与秘密社会、国民党及袁世凯当局三者间的关系也就成了本文探讨的核心问题。
一、白朗起义与秘密社会的关系
(一)“白狼”释名
对于白朗起义军,时人多称之为“白狼”。对此学界有三种解释:第一种认为是对白朗名字的讹传,“白狼者,回人也。原名朗,世人讹传以为白狼”[3]352;第二种认为来自白朗的绰号,“白狼姓白名朗,河南宝丰县人,以其身材高瘦,腿长行快,故因其名而绰号白狼”[3]411;第三种则认为是对白朗行事风格的描述,白朗“二十二岁时,部下己有数百人之众,据鲁山县属一山寨为根据地,武断乡曲,跋扈难制,人因称之曰白狼”[3]320。三种说法的共同点在于均认为“白狼”是他称,词义为中性或贬义。然而在南洋华媒的报道中,“白狼”是起义军自称。“狼匪所用言语甚为奇特,其称官军曰狗,盖彼等以狼自居,官军剿捕之,故以狗名之也”[4]。此后各地的响应者也不乏以“狼”自居者:“拟在蒙古内地组织蓝狼,在奉,吉界内组织红狼,其黄狼匪羽现已组成,潜伏江苏内地,黑狼匪羽刻已派赴四川内地组织。”[5]在广东民间,“近日东莞谣言百出,塘头厦、常平、寮步、茶园等区沿途均有人演说,中有‘白狼生,乌猿死’等谣”[6]。显然,“狗”“猿”均暗指袁世凯及其追随者,是他称与蔑称,而“狼”则是反袁势力的自称与褒称。由此可见,“白狼”之名绝非仅与领导者的姓名有关,而实质是传统秘密社会的一种切口与隐语。因此,“白狼”作为社会边缘文化的一种隐喻符号,象征着底层民众的反叛精神,表明在社会文化心理层面上,白朗起义与中国传统秘密社会存在重要的内在关联。
(二)哥老会与白朗起义的士兵来源
与一般的土匪不同,白朗起义军是一支军事素养较高、战斗力较强的部队。“巨匪帮伙大半系退伍军人,惯于野战,一遇大队军营,彼即远飙,以避其锋。”[7]有研究者将其解释为“裁兵和变兵大量存在白朗军中”,军匪不分,因而“具有土匪军队的特征”[2]58。然而这些“裁兵和变兵”来自何处,目前学界尚未查明。而在新加坡华媒看来,这些士兵大多来自鄂军第八师(该师师长为季雨霖)。季雨霖本系辛亥革命元老,后遭人排挤,黯然离职。第八师被裁后,所部士兵大都流离失所,对当时政权持敌视态度,“鄂省长江上游,为咽喉重地,故乱党图鄂之心愈接愈厉。近以白狼扰乱,势焰甚炽。该党欲乘此时机,与狼联合一气,而乱党之在鄂省则以季雨霖之部下为最多”[8]。之后,这批经历过实战考验的退伍兵大多加入起义军,是起义迅速发展壮大的重要原因之一。“闻其匪势增长之由,盖各处军队多投匪群,就中如湖北第八师被裁兵,有全体化匪之概。”[9]新加坡华媒曾援引一位在皖北参与过前线作战的政府军军官的话,认为“白狼原本为豫之一种土匪,虽为时甚久,不过与各省之土匪相同,专出没于乡村,并不敢扰及城镇,与官兵抵抗。革命以后,散兵无业者多趋之,季雨霖之兵占大部分,且皆带有枪弹,其势乃炽”,“因之随白为匪者益众,军械且更充足,于是敢出汴省,扰至湖北也”[10]。
值得注意的是,鄂军第八师与哥老会存在重要渊源关系。哥老会自清末以来广泛渗透到湘军、新军等军事组织中,辛亥革命之后新成立的鄂军中不少士兵也出身哥老会。关于哥老会、鄂军第八师与白朗起义军三者之间的关系,从一则新闻报道中可窥一斑:“季雨霖之胞弟季雨霆向在哥老会为教学二哥(即会中军师之别名),兹因无家可归,亦投身入白匪中为头目,领有步马队一千余人。”[11]之后起义军在转战各地时又收纳不少哥老会成员,入陕后更是如此。“此次寇陕者不但白狼,兼有洪江会匪杂入其中,盖洪江会匪即红帮会,又称哥老”,“盖白匪入秦,但有三四千人,其势并不大。今陕省帮匪几于遍地皆是,多红帮也。”[12]同时,“狼匪号称扶汉军,一九一一年哥老会起事亦用此名”[13]。由此可见,随着参与度的提升,哥老会对白朗起义的影响愈加明显,从最初的人员组织渗透,逐渐转变为政治诉求的引领。故此,在新加坡华媒看来,白朗起义自爆发伊始就与哥老会关系密切,后者不仅是前者的重要兵源与骨干力量,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前者后期发展的政治走向。
(三)秘密社会与白朗起义的后勤供给
白朗起义的另一大特征就是奉行流动作战的军事策略,故时人多讥之为“流寇”。起义军本身没有制造枪弹的能力,“传言有三十人能造子弹,特欺人语耳”[14],“所有白狼等所用之军火,均系随处收买”[15]。因此,“匪亦颇知宝贵枪弹,每次接战,非至火线内不发,以其购买子弹不易,每排须费洋一元(一排五粒),如被官兵战败,则匪宁牺牲人,不牺牲枪,无论如何,必将枪夺回”[16]。
总的来说,白朗起义的武器供给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外购,而长江中下游沿岸的各大口岸则是主要贸易地。“沿江各埠,白狼羽党甚多,大率扮作商人,或流丐,纷散各地,探听军机。另有一种头目,在汉口、九江、南京、天津等埠,设古玩杂货店,专任代销党中掳掠品。”“按是等组织颇为巧妙,虽侦探林立,亦难索隐。盖其机关之组织,似乎完备,彼且自负,若无需他党之扶助也。”[17]此后白朗率部离豫入陕,远离了长江流域,随即在枪械供给上出现严重的危机。“陕为陆地,常苦转运不便,此次陕军与狼苦战,遂生子弹不足之虞,而匪中缺乏军火,较官军尤甚。盖白狼在陕,决不能如在豫之易买得也。”[18]不仅如此,秘密社会还将此网络进一步拓展到了海外侨界,之后发生的加拿大“江泽案”更是在侨界产生较大的影响。由于此案不见载于国内报纸,现将南洋华媒相关报道节录如下:
此案发见以后,温哥华西字报纸迭次记载,咸言江泽为旅坎华侨某秘密会社中人,平日主张无政府主义甚力,此次杀人劫物之事,亦与某秘密会社有连。又据江泽之主人米拿特言,江泽自在其家服役以来,颇能勤慎,近两年中,性质忽变,常于夜间私往华埠,每逢星期六日,或竟出而不归,微闻其他华人,言江泽新入一秘密党会,此党会为盛倡社会共产主义者,时以此为江之个人主张,于服役初无关系,故亦毫未厝意,而不虞以主张悖妄之故,竟演出此图财害命之惨剧也。闻江之谋杀主妇,蓄意已在两星期以前,故窃得主妇首饰数事,秘密藏匿,然终虞主妇觉察,故不得不出于杀害,其已窃得之首饰,乃欲变卖得金,交付某秘密党会中购办军械,私运回国,以为接济白狼之用。因某秘密党会在温哥华、域多利两处势力甚盛,近更与白狼暗通声气。去年十二月,曾购办军械一次,值银四千元,由域多利埠托某轮船运回香港,展转交与白狼。中国政府闻之,急遣侦探截查,已无及矣。今中国政府已商准港督截留华人由外洋运入之军械,而旅坎之某秘密党会尚未知之,故仍尚续购军械之预备,而江泽且以此故犯此杀人劫物之大罪案,真可谓奇之又奇者矣。[18]
由此可见,白朗起义背后确实存在着一个由秘密社会所建构的庞大社会支持网络,从长江流域蔓延至海外侨界。诸如江泽之类的这些普通“幕后资助人”,应该经历过辛亥革命的洗礼,深受民初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等思潮的影响,甚至还有可能接触过共产主义思想,其观念具有鲜明的时代性,显然不应将之归为传统意义上的农民阶级,更无法将其与乌合之众的土匪相提并论。因此,从社会文化心理、组织人员构成与社会支持网络等诸多层面来看,新加坡华媒视野中的白朗起义是以哥老会为核心的秘密社会所发起的一次暴力抗争,既非农民起义,也非土匪运动。
二、白朗起义与国民党的关系
关于白朗起义与国民党之间的关系问题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焦点,新加坡华媒对此则有一个明显的态度变化过程,即从前期的将信将疑转变为后期的断然否定,强调白朗起义的自发性与独立性,不认为国民党与白朗起义之间存在任何领属关系。
在白朗起义的活动早期,新加坡华媒倾向于认为其与孙、黄等国民党人存在某种政治上的联系,但态度较为审慎。1913年10月间,白朗起义军在枣阳曾与美国籍传教士霍尔姆氏有接触。“匪党之就询讨袁情形者甚多,间有以北京已否攻克为问者。及该教士告以政府获胜,黄兴已逸,则该匪等皆陡然变色,为状若至懊闷者。若辈对于黄兴似颇崇拜。”[19]1914年1月,白朗起义军与政府军在京汉路东的新安店发生激战,“据旁观者之推测,均谓白狼历年乱豫省,均在深山穷谷,偏僻处所,从未敢公然在京汉路试其猖獗伎俩”,“此次敢在铁路两旁肆虐,其中显有主动之人,因而疑及孙、黄暗中勾串,观其举动,人言亦非无因也”[20]。
随着白朗起义的后期发展及社会对其了解程度的加深,新加坡华媒转而态度明确地认为,白朗起义与国民党之间并无领属关系,依据是白朗起义所倡导的政治主张在理论上混乱不堪,在实践上自相矛盾。起义军在入陕后政治态度出现了明显变化,“毅军获白狼旗送京,有扶汉军,公民军,讨袁军三种”[21]。“扶汉”显然源自哥老会等秘密结社固有的本土种族主义观念,是对清末以来会党起义惯例的遵循,体现出历史惯性的某种延续;而“公民”观念则体现出辛亥革命前后外来的共和主义与自由主义兴起之后的民权意识,表明白朗起义试图通过彰显“主权在民”以对抗袁世凯政权所奉行的国家主义理念。因此,在新加坡华媒看来,白朗起义的政治理念混杂着古老的本土种族主义与近代的欧式民权意识。前者具有排他性,后者具有普适性,两种观念的内在抵忤致使白朗部众在思想上是混乱的、行动上是自相矛盾的。主张种族主义,但袁世凯政权多为汉人,难以号召民众,而孙中山等人又认为清亡之后民族主义的目标已达成,无须再加以提倡;提倡民权,却滥杀无辜,焚烧劫掠,杀人无算。同时白朗起义军所奉行的狭隘种族主义又往往凌驾于民权意识之上,难以处理与西北地区少数民族的关系,致使民族冲突不断,逐渐走向衰落。可以说,白朗起义与孙、黄领导的国民党从理念到行动均不相容。故此,新加坡华媒明确指出,“外间多称白匪为孙文、黄兴之羽党,然观其举动,殊觉不类”,“要之,该匪决不受一党之指挥,则固可见”[22]。这无疑是将白朗起义视为一次由秘密社会独立发起领导的旧式会党起义,而起义的失败也说明,自清末以来,以种族主义相号召的秘密社会起事方式在政治语境中丧失了合法性,在政治实践中失去了号召力。白朗起义成为旧式会党起义在历史舞台上的最后一次亮相。
三、白朗起义与袁世凯政权的关系
在新加坡华媒看来,白朗起义沉重打击了袁世凯政权的政治威望与国际声誉。起义爆发后,南洋华媒对袁世凯当局的抨击,前期主要集中于军事领域,抨击各级政府治军无方、作战不力;后期则主要集中于政治领域,矛头直指袁世凯,斥责其治国无能、独裁统治。
在新加坡华媒看来,“白狼匪祸成之者豫督张镇芳,陕督张凤翙也,纵之者督师段祺瑞也”[23]。“张镇芳督豫两年,坐拥五十营重兵,而毫无军事学识”[24],“现在各省之中,职务废驰之最明显者,莫如河南。河南本系完善之区,而近来盗匪滋孽,民不聊生,且因此牵及鄂西皖北,均受影响”[25]。袁世凯政府应对此事“束手无策,并惊动全世界人之耳口哉。近闻欧洲各国因狼匪扰乱之故,以致中国债票价格日低”[26]。对此,南洋华媒颇为感慨,“去年湖口之役,南省纷纷独立。袁氏运筹帷幄,决胜于数十日之内。当此之时,政府威望,遂以倾动中外。噫嘻!昔何神速,今何濡濡哉,因此袁氏声威必有一落千丈之势”[27]。
随着相关报道的逐步深入,新加坡华媒开始思考起义爆发的深层次原因。“白匪伏诛后,汴省官场互相称庆……愚民无知,闻白狼击毙之耗,反为哀惜,而对于官军之胜负,转若漠不相关。”[28]为何会出现这种场面?在新加坡华媒看来,“人民之纷扰,国家之衰弱,皆政府之咎也”。首先是经济原因。“记者以为匪不足患,所虑者各省人民心理,咸以为政体虽革,而官家之积习未改,敲诈人民之风较之往古有过之而无不及……富者拥金不动,贫者流转沟壑……故欲防匪之起,则惟有开辟富源,理财政而后可。”[29]而更重要的原因则是在政治领域。“中国自革命以来,无日不居于风雨飘摇之中,漏舟积薪之上。政府以因循敷衍为职,行一政也,则虚与委蛇,授一吏也,则五日京兆……于是人民信任政府之心益弱,闻乱惊惧,谈虎色变。”[29]如果说经济发展的停滞、社会财富差距的扩大以及民众对政府的政治信任降低孕育了白朗起义的土壤,那么袁世凯政府的独裁统治和对人民民主权利的肆意侵犯则造就了起义的主角。关于袁世凯政府、国民党与秘密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南洋华媒认为:“中国之政党两年来轩然大波起矣,然行径不纯入正轨,尚含有汉、唐、明朋党之余风,其甚者则隐带秘密社会之痕迹”,而“今者国民党解散矣,而秘密会社由此益多”,“由秘密社会而归入政党,政党愈多,则人才愈出,而国家可以减少他顾之忧,由政党而遁入秘密社会,则秘密社会愈盛,则扰乱愈剧,而人民必受连带关系之灾。”原因就在于政党主张合法斗争,而秘密社会更倾向于暴力手段。“政党之对于政府也,必出以明亮之态度,以议院为战地,以法律为戈矛,以一党议员为猛将,所谓堂堂之阵,正正之旗也。若秘密会社之对付政府,则炸弹手枪,以行暗杀,造谣煽乱,以运机谋。”故此,“为政府计,务使秘密会社可返于政党地位,而政党不致复归于秘密会社地位。民国庶几其永固乎。虽然根本之救治法尤在乎正义也”[30]。在新加坡华媒看来,保障人民的结社权利,推动哥老会等传统会党向近代政党转型才是“民国永固”之策。然而,遗憾的是,1914年1月9日,袁世凯当局发布《严禁哥老会令》,强令各会党解散,传统会党向现代政党转型之路受阻。在新加坡华媒看来,一面是袁世凯当局滥用暴力,肆意侵犯人民的民主权利;一面则是非暴力的合法抗争方式已无可能。当民主、自由、法治荡然无存的时候,底层社会固有的“以暴易暴”逻辑便会应运而生。这也从侧面说明新加坡华媒承认白朗起义具有一定的正当性。从这个意义上说,这场反暴政的抗争被冠以“起义”之名,当之无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