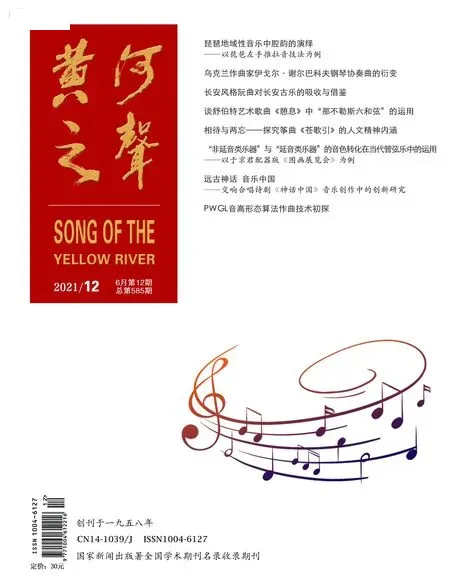民族歌剧《运河谣》中重唱唱段艺术特性探究
2021-11-26张苗苗
张苗苗
一、民族歌剧《运河谣》的创作概述
2012年《运河谣》正式面世,经国家大剧院历时两年打造而成,主创团队(印青作曲、黄维若编制、廖向红导演)实力雄厚,且由雷佳及王宏伟等多位青歌赛金奖歌手共同演绎。纵观我国民族歌剧,其题材大多以塑造英雄形象为主,而《运河谣》一改这一传统,将焦点汇聚于以书生秦啸生及艺人水红莲等为代表社会底层人物,希望以此来凸显人性的善良及感情的真挚。《运河谣》全篇可看作是一首序曲及六个场景的转换,这是主创团队在最初就已经达成的共识,在借鉴西方歌剧创作手法的同时充分展现了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及音乐元素,为此这部歌剧兼具了民族气韵以及流行风貌,而创作者也不再倚重于咏叹调等传统创作方式,反而突出了独唱、重唱及合唱等多种声乐表现形式的独特魅力。
二、民族歌剧《运河谣》中重唱唱段的音乐特点
(一)民间音乐元素的运用
民间音乐元素的灵活应用是凸显这一歌剧民族性特点的重要前提,而《运河谣》则是国家大剧院第一次以民族唱法为基础进行的创作尝试,中国传统民族特色不仅体现在主题内容的选择、故事情节的设计以及演唱唱法的选择之上,同时还体现在整部歌剧的编排及整体音乐风格的设定等方面。以《运河谣》第一场中的《彩龙船》为例,这一唱段融合了苏杭地区独有的采茶调元素,且在调式方面除五声调式之外,还加入了A徵音形成六声调式。分析主人公的对话时可以发现每个小唱段中都有明显的南方音调,其婉转及细腻的特点尤为突出,配合优美的服装及独具特色的舞美,生动的展现了我国江南地区的民风及民俗;以第二场中的《拉纤歌》为例进行分析,引用了民间音乐中最为常见的劳动号子,用以凸显我国劳动人民的智慧及优良品德,进而与观众形成情感上的共鸣;以最后一场中的《大豆白米花生》为例,唱段中明显可见京韵大鼓等元素,与之前的采茶调形成了明显的对比,生动形象的展现了北京当时的繁荣景象。
(二)丰富的音乐织体形式
丰富的音乐织体是民族歌剧《运河谣》重唱唱段的显著特点之一,在理解音乐织体这一词汇时,以时间为切入点,同时也可以从空间的角度展开分析。纵观全剧单声部及多声部织体均较为常用,其中和声与重唱均属于多声部织体的范畴之内,相较于单声部织体而言,丰富重唱唱段使得歌剧作品的层次更为清晰、内容更加饱满,且作品本身的戏剧性也得以充分展现。全剧以水女和声为主线,贯穿始末,且每一场中都有类似于旁白式的说唱部分,也可以看作是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且人物形象差异明显、故事情节较为曲折,这使得音乐织体也变得更加丰富与多样。
重点分析民族歌剧《运河谣》中的重唱唱段,主要分为主调音乐织体以及复调音乐织体这两种,而再进行细分,则又可以将复调织体分为模仿及对比复调这两种。主调织体以一条旋律线为其主旋律,而其余声部均应当发挥出衬托的作用,即只需要突出某个人或某个旋律声部的演唱即可,这一音乐织体在第一场的《彩龙船》以及第二场的《拉纤歌》中均有所体现,作曲家希望通过这样的设计来改变我国民族音乐创作过于注重单声部的现状,进而实现由横向发展向纵向发展的转变,在保留中国传统音乐的独特韵味的同时,追求更为多样的音乐织体以及更为厚重的音响效果,带有民族特色的主调织体音乐也成为了民族歌剧《运河谣》的重要支撑。分析复调织体的应用效果,其演奏形式发生了转变,增加了双线条乃至多线条,交叉并存,歌剧作品的音乐性大大提升,虽然这种织体在歌剧《运河谣》中的应用并不算多,但第二场中《千年修来难同当》这一唱段最具代表意义,主要运用了模拟式复调织体进行男女二重唱,由此也成为了全剧中最为经典的唱段之一。
(三)灵活的声部
声部的灵活运用是民族歌剧《运河谣》得以广为流传的重要原因,分析其剧情及主题,主要围绕四个重要人物开展,为此其合唱唱段最多可能存在四重唱,对于不同的演唱者而言,其自身音色条件存在显著差异,为此在组合时也具备独特的魅力。在创作时,主创团队依据演唱者的声线及故事情节来设计重唱的内容,其主要目的是为了突显人物的性格、塑造其鲜明的形象、准确的揭示人物之间的关系并清楚的表达故事情节。演唱者在处理个人感情以及声部之间的组合搭配时并不需要遵循固定的模式,但由于各片段都是经作者精心编排过的、而并非随意组合而来的,为此演唱者一定要仔细揣摩人物心理,从而加强整个剧目的戏剧性。从声部的搭配角度来看,全剧中只有一段同声重唱,其余的均为男女混声重唱(女高音、男高音及中音),且不同音色以及不同音区的混合在表达人物内心情感变化及戏剧矛盾冲突时都有其独特的意义。呼应式,顾名思义为衬托主声部而存在,其他声部需要进行附和,可以看作是一个声部的引领部分;对比式,即主要通过对比的方式来强调人物特点,对比的内容通常为音色、速度以及节奏等音乐元素;交叉式,即各个声部按照有序的排列进行穿插与交错,通过将人物及故事情节进行叠加来为观众营造一个更加真实的故事场景。
(四)节奏与旋律
分析《运河谣》的创作背景,主创团队以民族唱法为基础借鉴西方歌剧的创作手法,才得以将现代音乐及民族音乐进行完美融合,由于故事情节的发展始终围绕京杭大运河,为此在进行音乐设计及舞美编排时更趋向于突出民族性这一特点。前几个场景中并没有过多的戏剧性变化,主要以船在运河上平静行驶为背景,唱段中包含的江南特色小调,既柔美又细腻,以四四拍或四二拍等多种节奏型为底,以此突出附点音符与切分音符,而调式的选择上则倾向于带有民族特色的五声或六声调式。以第二场水红莲演唱的咏叹调为例,她与秦啸生一同泛舟,何其悠闲,而这一唱段中的四四拍节奏切好与这一律动相近,速度也相对舒缓,以降E五声商调式为主并配合若干分解和弦,实现了音乐旋律的极大丰富,整体的流动性得以增强、音乐的美感得以突出,虽然后几场的情节表现出明显的转折,但整体音乐的抒情性特点并没有因此而改变。
三、民族歌剧《运河谣》中重唱唱段演唱分析
(一)二重唱《灿若星辰的目光》
《灿若星辰的目光》为歌剧第二场的起始部分,在这一场景中,秦啸生与水红莲二人互生爱意,而这一二重唱唱段正是二人交流、倾诉并传达爱意的重要唱段,其歌词充分展现了二人的柔情蜜意,前半部分略显羞涩而后半部分的情感表达则更为直接,这一唱段不仅起到了承上的作用,同时也为后文恶霸拆散二人以及盲女的出现等情节做了铺垫。这一唱段是歌剧中旋律性最强、主旨最为鲜明的部分,无论是曲式结构还是调式调性都填充了大量的民族元素。演唱者在演唱时应当注意唱段中的休止处理,在起始处的强拍上做弱声处理,控制气息并保持其始终平稳,以此来表现出二人情感的微妙变化,前一部分近似低声倾诉,为此演唱时应营造娓娓道来之感,注意切分节奏的处理才能够更好的拿捏情感表达的分寸,既不可过于内敛,又不可过于直白,此处应当以突出女生的主旋律声部为主,为此男生的声部则需要做弱处理。演唱时一定要注意演唱的连贯性,在第一段结尾处做渐强处理,以此来更好地承接后半部分的情绪变化。后半部分逐步迈向全曲高潮,为此演唱时音量应当随之增强,最好能够做到以情代声,在乐曲行至“难同当”一句时做渐强处理,必要时加入前倚音予以修饰并丰富人物的情绪与情感。
(二)三重唱《我是一叶浮萍》
三重唱《我是一叶浮萍》出现在民族歌剧《运河谣》的第三场,此时盲女关砚砚已经出场,秦啸生不得已冒认他人身份与她在一起而无暇顾忌水红莲,而关砚砚对身边人的身份也心存疑虑。三人都处于迷茫无奈之中,且面对不可知的未来,三人将自己比作随水飘零的浮萍,而这一三重唱唱段的篇幅相对简洁且短小,可简单分为三个乐句,每一句的歌词与其音乐结构相对应,三个声部轮流做主旋律。水红莲声部以徽音为起始、关砚砚声部以羽音为起始、秦啸生声部以宫音为起始,乐句间起始音呈逐渐升高态势,用于表现三人情绪的不稳定状态,前后呼应、此起彼伏,此前出现的四个唱段均为这一三重唱唱段做了铺垫。三人深夜无眠且各有所思,水红莲主要表达对秦秦啸生的思念、秦啸生主要表达自身的左右为难而、关砚砚则对身边人心存疑惑,这一三重唱展示出了更加戏剧性的效果。演唱者应当把握好不同声部的情感色彩,演唱时不可过分拖沓,也不可存在明显的顿挫,应当清楚的表达临近两个音之间的五度关系。从而确保演唱的整体性以及声音的统一性,但某一人物的部分为主旋律时,其他人的声部应当做弱处理,以此突出主旋律,且最终三人的演唱均归于主和弦并随着减弱处理而结束。
(三)二重唱《快快回到她身旁》
二重唱《快快回到他身边》是民族歌剧《运河谣》第四场中的经典二重唱片段,故事发展至此,关砚砚已经断定身边的人并非李小管,而水红莲对秦啸生的思念也日益加深,这一唱段为两个女性角色的重唱唱段,她们虽然都在抒发感情,但心中所思所想却完全相同,关砚砚希望他能够尽快回到意中人的身边,由此可见其善良的品性,而水红莲的情感则更多为期盼、哀怨及无奈。虽然这首作品的篇幅并不长,但充分运用了复调的手法,两个人的声部旋律各自独立却又相互呼应,为此演唱者更应当处理好声部之间的联系。分析第一小节可知,引用了此前出现的咏叹调,而水红莲声部此时则起到附和作用,其中频繁的使用了8分休止符,从而使观众在听觉上能够感受到主人公的抽泣与呜咽,进而达到娓娓道来的效果,随后紧跟着两个16分音符,主要是用以表达水红莲急切见到秦啸生的心理以及关砚砚希望他能够回到水红莲的身边,“他身边”这三个字由二人同时演唱,但出发的角度却不尽相同,演唱者在演唱时应当切实从角色的角度出发,进而感受其中的不同情感。
(四)四重唱《天堂有路你不走》
《天堂有路你不走》是民族歌剧《运河谣》中少有的四重唱部分,同样出现在第四场景之中,故事情节的变化也由此变得更加激烈,整个歌剧的戏剧张力也得以突出。在这一场景中,恶霸已然知晓了秦啸生的真实身份,于是才有了“天堂有路你不走”一句,而三人(关、秦、水)慌乱至极进而发出感叹,唱段中的波澜起伏较为明显,恶霸的无耻行径也与三人的焦急状态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与之前的重唱唱段不同的是,《天堂有路你不走》的篇幅相对较长、速度相对更快且其曲式调性的转换更为频繁,为此对演唱者综合能力的要求也相对更高。分析引子部分可知,为更好的塑造恶霸这一人物形象,演唱者出场时便要破口大骂并展示出其洋洋得意,在遇到附点节奏时应当将演唱做轻佻处理以表现其小人得志,而水红莲在开口时便要彰显其坚决与果断的态度,且此时关、秦二人的声部应当以突出水红莲为主,后半部分主要为秦啸生的声部,演唱者应当以感叹的语气来突出惋惜之情与气愤之感,此时水、关二人应当完成衬托的任务,而三人的共同演唱则是为了进一步渲染气愤至极的情绪,“无耻、可恶阴险”的发音应当短促而分明,最后做渐强处理直至整个唱段结束。
结 语
国内音乐界在追求当代歌剧的创新发展过程中不断融合民族元素以彰显其民族特色,其抒情性与戏剧性等特点更为突出,在此过程中,重唱艺术也实现了自身的可持续发展。民族歌剧《运河谣》在创作过程中不仅继承并发扬了我国民族歌剧的优良传统,同时也借鉴了西方歌剧的先进创作方法与演唱技巧,这标志着我国民族歌剧的发展序幕就此拉开,无论是在叙事方式还是在音乐结构等方面,都弥补了我国传统民族歌剧存在的不足,同时也为当代音乐教育及作品创作提供了新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