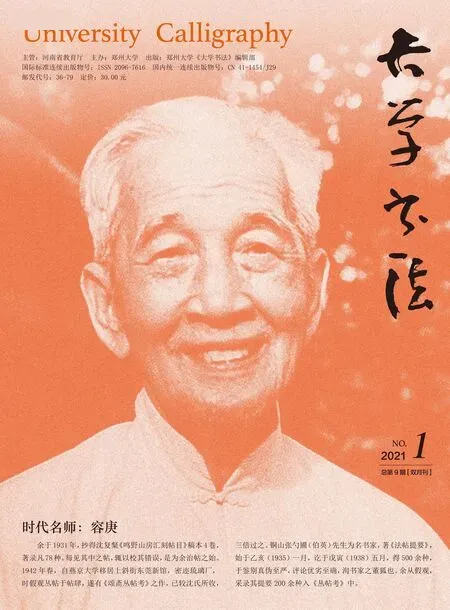书之时可知“自然”
——论《书概》中“自然”观念的审美意蕴
2021-11-26李帅文
⊙ 李帅文
在《书概》中,“书当造乎自然”是刘熙载书论的核心命题。“自然”作为“天人合一”的审美范畴,蕴含于天与人的展开之间,是书法艺术中的本质和内在依据。从《说文》中“仰观象于天,俯察法于地”[1],到当代书坛所提出的“日常书写”,“自然”观随着历代书学思想的发展,其审美内涵有所改变。对于问题而言,当前对《书概》的研究局限于书学观念的逐一阐释,而深入探究“自然”观的审美意蕴有利于对当代书坛“自然”观的反思。本文关注“自然”作为一种书法审美理想与《庄子》之自然观的内在联系,以及其在《书概》创作观中的显现。
一、“自然”的根基
《书概》开篇“以象立意”是对书法原初本质的追溯,以“自然”的形式确立书法本来的面貌和意义,这是书法最原始的审美内涵。“象”与“意”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庄子所说的“形”与“神”。“形”是生命之本,是生命存在的本然形态;而“神”是生命之主,其本质就是自然之道,是自然的意蕴。所以“自然”的哲学基础基于庄子的“通天下一气耳”,即“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2]。“自然”始终是生命力和“气”的集聚与显现。
“与天为徒,与古为徒,皆学书者所有事也。天,当观其章;古,当观其变。”[3]这里引用《庄子》中:“其一与天为徒,其不一与人为徒,天与人不相胜也,是之谓真人。”[4]郭象为其注曰:“‘天’者,自然之谓。”[5]也就是说,人与自然二者是息息相关、不可分割的整体。庄子将天性和人性集于一身来描述“真人”这一理想人格,笔者以为,庄子强调的重点是人有至真,这一“真”是当时人类思维追求超越的精神取向的表现形式,是天、地、人的本然“存在”。刘熙载将“与天为徒”作为学书者所有事之首,意在强调“自然”的神圣性。“观天之章”即提出了如何“与天为徒”,如何追求“自然”的至高境界。“章”即天地万物的运行规律,将自然的外在形象内化为书法的本质灵韵,正如《庄子》之“真人”的内在显现正是“以一种形象化的方式指向一种抽象的哲学境界,这种境界可以理解为超越于现象世界的、先于人为的、知识的、未经人的思维构架改造的本然的存在”[6]。所以“与天为徒”正是以“自然”的本质为内在根据,“观天之章”也是“自然”观的首要根基。
同时,“与古为徒”是刘熙载对《庄子》中“创变”思想的接受,“为人之所为者,人亦无疵焉,是之谓与人为徒。成而上比者,与古为徒”[7]。刘熙载将“与古为徒”纳入学书的方法论:“观古之变”是在传统与创变的不断展开中得以实现的。创变是古人在传统的基础上对自然的顿悟,所以“古”只有内在于“天”才得以显现“自然”的灵韵,否则只是存在于历史与传统的时间范畴。“自然”在书法创作中存在于被遮掩的古法与敞开的万物之中,其根基是天与古的融合、天与人的合一。
二、“自然”的显现:“无为者”的能动性
“书要有为,又要无为,脱略安排俱不是。”[8]刘熙载在这里通过“有为”与“无为”指出书法创作中“自然”的显现。“有为”与“无为”在这里处于张力之中,即书家临池实践之积累与其天赋、性情等生命特征,后者是书写中“心忘于手,手忘于书”的境界,创作前“有为”的积累内在于“无为”的书写,因此,“有为”与“无为”在这里是合二为一的关系。此处又批判了创作中的“脱略安排”,放任和刻意并非“无为”和“有为”,刻意安排有悖于“心手达情”,而脱略放任又犯了“好溺偏固,自阂通规”之忌。庄子所谓“无为”,是“心斋坐忘”“莫若以明”,回归到生命的本真状态,如此才能通达逍遥,与天地精神为友。所以,书法的本真状态和“自然”境界是书写时的自行发生,不是可以明状的对象,而是首先从“无为”的状态中产生。
其次,刘熙载在《书概》中创造性地提出:“书当造乎自然。蔡中郎但谓书肇于自然,此立天定人,尚未及乎由人复天也。”[9]这是对蔡邕自然观的发展,强调了人的主观能动性。“肇”意为发生、始兴,蔡邕意在表述书法始于对自然的象形,且提出书法之形势源于自然之阴阳二气,“阴阳既立,形势出矣”,“自然”在这里是不可揭示的,是在阴、阳的对立统一中发生的。而刘熙载则在此基础上提出的“书造乎自然”正是对“自然”这一真理的去蔽,是书家使书法中的“自然”得以在不断敞开的状态下显现,是排除日常的书写习惯,在“有为”的积累之上“无为”的尽情挥洒笔墨,在心、手、纸端的张力中不断生成。这既是海德格尔认为的“真理作为这种世界与大地的争执被置入作品中”,又近乎庄子提出的“真知”“是存在的澄明、去蔽状态,是原初混沌的同一”[10]。所以“由人复天”是书家能动性的审美体验对“自然”这一真理的去蔽。
刘熙载在《游艺约言》中对“无为”“由人复天”有较为详细的补充:“无为者,性也,天也;有为者,学也,人也。学以复性,人以复天,是有为仍蕲至于无为也。”[11]“性”“天”是人之性灵与自然之天机。正如实现“真人”需要“离形”“忘知”,也就是对有为的“去形”与“去知”以使“性灵”去蔽,所以刘熙载认为:“无为之境,书家最不易到,如到便是达天。”[12]“天”即自然万物的天机,是非具象的、被遮蔽的存在,书家只有发挥“无为”的审美能动性敞开“天”“性”才能使“自然”这一书法审美理想得以在创作的过程中显现其自身,也就是海德格尔在《林中路》中谈到的真理的生成是非静止的,是在不断遮蔽与显现的争执中生成的。所以,书之“自然”即显现于“无为者”能动性的审美与生命体验,如《庄子》中“庖丁解牛”“梓庆削木”等寓言,在心手相忘的自然境界中才能实现“进乎技”,进而达“无为”之道。
三、“自然”观的实践:“书之时可知矣”
《书概》中的“自然”观以“观天之章”“观古之变”为根基,通过“无为者”显现,刘熙载认为:“高韵深情,坚质浩气,缺一不可以为书。”[13]“深情”和“浩气”是创作中的自然流露,是言不尽意的。而此“情”此“气”通过笔墨表现为书法,则是“自然”的外化。那么“高韵深情”“坚质浩气”如何通过笔墨自然流露?刘熙载提出了“不工”与“工”、“生”与“熟”、“疾”与“涩”等具有方法论意义的美学范畴。
《书概》中有“观物以类情,观我以通德,如是则书之前后莫非书也,而书之时可知矣”[14],这里的“类情”“通德”强调了书法艺术语言的功能,更重要的在于其揭示了主体的能动性,否定了“书之前后”的有意识状态,而是书写过程中“无意识”的情感显现。刘熙载引用《易传》“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15],意在表达书法始兴之时已蕴含的自然宇宙观。而在微观层面,刘熙载通过“技”来阐明“自然之道”,如“涩”这一笔法,“惟笔方欲行,如有物以拒之,竭力而与之争,斯不期涩而自涩矣。涩法与战掣同一机窍,第战掣有形,强效转至成病,不若涩之隐以神运耳”[16]。“涩”作为一种笔法现象,在毫端与纸的张力中显现。将“涩法”与“战掣”笔法对比,指出二者的关键在于“隐以神运”,“神运”二字存在于隐匿和遮蔽状态中的“非力运而能成”,是“无意识”的主体思想通过笔端藏露、中侧、提按等微运动之间自然流露的“机窍”。
在书法品评方面,刘熙载在“不工者,工之极也”[17]中指出学书之初需要练就工稳细致的技法,继而追求“不工”的境界,即自然、无定法,是习书境界的升华,是对“离形”“忘知”的实践,超越肉体和生命,归属于自然的状态。又如《书概》中对“生”与“熟”的讨论,“惟能用生为熟,熟乃可贵”[18],习书贵在精熟吗?非也,贵在精熟基础上的“生”,回归到“生”这一自然本真的创作状态,才能达到“人书俱老”之境。所以书之“贵”不在精熟,而在“生——熟——生”这种不断展开、自然生成的过程。刘熙载在书法审美方面以自然为喻,以“灵和殿前之柳”指尚姿致之书风,以“孔明庙前之柏”喻书法之气格,因为“灵和殿”和“孔庙”的在场,所以自然之柳、柏被赋予一种品格。刘熙载提出“取姿致”不如“尚气格”,隐喻了自身的审美取向。类似亦有借怪石隐喻书法之形态:“怪石以丑为美,丑到极处,便是美到极处。”[19]这里“丑”并非是外观之美的反义,而是指在时代语境下对合乎审美规律的极端个性化艺术语言的描述,刘熙载认为“丑”字之中“有丘壑未易尽言”,所以其背后是对法度和一般性审美的超越,体现了作者对书法时风的创见。
四、《书概》中“自然”观念的审美意蕴与反思
《书概》关于“自然”观的方法论表述,指出书法之“自然”境界藏于书之时的“神运”之中,在“不工”“用生为熟”的自然状态中显现“孔明庙前之柏”的气格,这里的“神运”和气格体现了书法中“自然”的本质和依据,即“自然之道”;而“自然”之存在则体现在“不工”“用生为熟”“以丑为美”等表现方式中,即“自然之术”,“自然”只有在书之时技进乎道时才能显现。但由于当代书写工具的改变、书法教程对于书写技法的强化、技与道的“分工”等诸多现代化因素的出现,使得书法之“自然”意蕴日益消解。当代书法提出的“日常书写”(亦有“自然书写”之说)这一概念是指“日常生活中为各种事物的需要而进行的书写”[20],其旨在强调书写内容的自然表达,虽区别于有目的的书写训练,但实质是对书法功用的强化,又弱化了“自然”背后的“灵韵”,使书法本质性内容暴露在日常需要这一层面。而自然作为书法重要的审美意蕴,是建立在“有为”积累之上心与手的“无为”,是笔纸相触的生成,是一种不可言说之物,而当“自然”作为书写这一行为的修辞而出现时,这一审美内蕴随之逊位,从而成为书写技法所能表现出的“伪自然”,这正如本雅明所言:“若想上前观看彩虹,彩虹就会消失。”
作为书法审美的重要范畴,“自然”在各个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展开方式,从“仰观象于天,俯察法于地”[21],到“书肇于自然”,再到书法之法的审美范畴,其根基在于“观天之章”与“观古之变”。在基于先贤古法的创变和顺应天机的规律之中,“自然”才得以确立,显现于“无为”和“有为”的争执之中,在“无为者”能动性的审美体验中,在既工、既熟的基础上追求“离形”“忘知”“隐以神运”,进而在书之时才得“类情”“通德”的审美感知,这正是“自然”的审美意蕴不断趋近书法艺术真理性内容的过程。而这一真理性的显现并非完全可视、可言说的客观存在,而是在心与手不断敞开与遮蔽的张力中顺应客观规律和主体性情而不断生成的过程。所以《书概》在形而上和方法论层面向我们阐释了“自然”这一书法的审美意蕴,对当今书学方法论方面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注释:
[1]王先谦.艺文志:汉书补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8:2906.
[2]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M].北京:中华书局,1983:165.
[3]袁津琥.艺概注稿[M].北京:中华书局,2009:615.
[4]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M].北京:中华书局,1983:176.
[5]郭象,注.庄子[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36.
[6]徐克谦.庄子哲学新探[M].北京:中华书局,2006:71.
[7]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M].北京:中华书局,1983:126.
[8]刘熙载.艺概[G]//上海书画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室.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710.
[9]刘熙载.艺概[G]//上海书画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室.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710.
[10]徐克谦.庄子哲学新探[M].北京:中华书局,2006:72.
[11]崔尔平.明清书法论文选[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94:889.
[12]崔尔平.明清书法论文选[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94:888.
[13]季伏昆.中国书论辑要[M].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2000:367.
[14]刘熙载.艺概[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171.
[15]阮元.十三经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0:74.
[16]刘熙载.艺概[G]//上海书画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室.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710.
[17]刘熙载.艺概[G]//上海书画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室.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710.
[18]刘熙载.艺概[G]//上海书画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室.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710.
[19]刘熙载.艺概[G]//上海书画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室.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710.
[20]邱振中.书法[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37.
[21]王先谦.艺文志:汉书补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8:29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