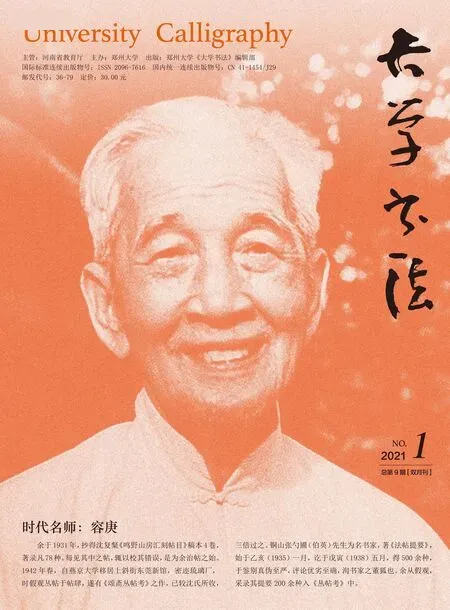从张怀瓘论“兴”看书法艺术的生成
2021-11-26张函
⊙ 张函
书法艺术生成过程就是书法家兴感之际和表达过程。张怀瓘描述王献之书法时曰:“偶其兴会,则触遇造笔,皆发于衷,不从于外,亦由或默或语。”[1]把书法生成解释为两个阶段:首先,是“兴会”的产生,这是书法家触物造端、心物交融而引发的“欲书”冲动,也是王羲之所指的“兴感之际”;其次,是书家个人在内心中有意识地追寻这份“欲”,凭借着书家日常生活中的经验运用想象逐渐把这份由心灵产生冲动的“意”和“象”变得鲜明生动,也就是构思阶段。张怀瓘认为王献之的书法艺术生成完全是在其内心引发并成熟的,是看不见的艺术过程。张怀瓘准确阐释了古代书法艺术生成的原理。“兴会”是书法本体的引发过程,想象、构思是使表达本体的作品之形渐趋清晰明朗的过程。这两个阶段虽然都属于书法家内心的思维活动,但是前者是无意识的,后者是有意识的。书法作品正是基于这样的前提才会展现在我们眼前。
一、从“文学之兴”到“书法之兴”
在古代书法理论中,“兴”被看作是书法艺术生成的基本条件。张怀瓘描述王献之书法时曰:
至于行草,兴合如孤峰四绝,迥出天外,其峻峭不可量也。……偶其兴会,则触遇造笔,皆发于衷,不从于外,亦由或默或语,即铜鞮伯华之行也。[2]
张怀瓘把王献之比作春秋时期的羊舌赤,即铜鞮伯华。羊舌赤具备了敏而好学、勇而不屈、有道而能下人的优点。张怀瓘把王献之的书法比作成羊舌赤,意在说明王献之书法不仅有功夫,而且在技法上纵而不肆,在艺术品质上高而不寒。更重要的是他借助描述王献之的书法来阐释了书法艺术的生成原理。在他的观念中,最完美的书法艺术要在“兴合”“兴会”的条件下才能产生。“兴合”“兴会”只能是偶然出现,并非恒久存在,而且这完全是书家内心的作用。宋代朱长文评张旭的书法曰:“盖积虑于中,触物以感之,则通达无方矣,天下之事不心通而强以为之,未有能至焉者也。”评说颜真卿书法时曰:“碑刻虽多,而体制未尝一也。盖随其所感之事,所会之兴,善于书者,可以观而知之。”[3]张旭、颜真卿作为“神品”的代表,他们的书法艺术都在“感物”“感事”的条件下产生,这就是“兴”,也叫“感”,也可以合称为“兴感”,即与王羲之《兰亭集序》中“每览昔人兴感之由”之意相合。
“兴”的历史由来已久,古代文艺理论的发生原理中关于“兴”的阐释更是多如牛毛。汉代徐干解释“兴”的缘由时称:“艺之兴也,其由民心之有智乎?造艺者,将以有理乎?民生而心知物,知物而欲作,欲作而事繁,事繁而莫之能理也。故圣人因智以造艺,因艺以立事,二者近在乎身,而远在乎物。”[4]“知物而欲作”实际就是“感”。艺术的产生正是在这种“知”和“欲”的牵动下生成的。而作为书法艺术发生理论,“兴”的观念完全在情理之中,因此,也就不需要给予特殊的说明。而“为中国所特有的书法艺术,和乐为中心这一古老深厚的传统有着内在的深刻联系”,并且同乐一样“起源于模拟而又大大超越了模拟,突出地展示了中国艺术重视情感表现的特征”[5]。
在古代书法理论中,“兴”的作用通常会被玄妙的哲学性语言所掩盖,突出的一点就是“书道”的提出。最初对书法的艺术性描述主要表现出一种非人力的神秘色彩,如庾肩吾称书法的出现是“疑神化之所为,非世人之所学”。李嗣真称颂四贤书法是“神合契匠,冥运天矩”的结果。到了张怀瓘则称其为“玄妙”,讲“神将化合,变出无方”“妙用玄通,邻于神化”,把书法的生成归结成神力的结果。随着人们对于书法艺术的不断探索,以及书法在实用之外所形成的非功利性影响,使得人们越来越体会到书法本体“情”的重要。而且任何一门艺术最终都会与人的生命紧密联系在一起,最终艺术形式都只能是人类精神展现的一种媒介。人的生命形式从最基本的物质形态必然要上升到精神形态甚至宗教形态。所以书法艺术在人的最高的生命追求过程中也会达到新的境界,这就是张怀瓘尊书法为“书道”的原因。故而宋代朱长文,在完全能够领会书法艺术真谛的同时,必然产生“书之至者,妙与道参”的观念。在这样一种理论环境下,书法的产生是神秘的,书法最终的归宿是神圣的,只有书法的艺术呈现过程才是具体的。
文字观赋予书法政教色彩并走向伦理,而哲学观则赋予书法神秘色彩。“兴”在书法艺术生成那一瞬间所具有的理论意义就被弱化了。在先唐时期所有关于书法的生成理论中都不曾明确见到“兴会”的影子。即使在唐代,“兴”的偶然出现,也仅仅是为了说明某位书家的一种书写状态。所以,“兴”在古人的观念中既是一种必然,又是无需说明的问题。
二、“兴”的艺术特点
我们在古代书法理论中发现,“兴”贯穿于古代书法艺术生成全过程,“兴”是决定书法能否进入艺术境界的绝对条件。在关于书法艺术生成理论的相关记载中,“兴”作为书法艺术发生的重要因素,其本身也包含三方面特点。
第一,“兴”的产生以“物”“我”共鸣为前提。“兴”既然是主体和客体共同作用下产生的情感冲动,这就表明人的行为活动不能是孤立于社会与自然之外的,而是和社会、自然相互作用的。社会和自然启迪着人类的思维活动和行为活动。客观世界在人类的主观精神活动中往往充当着重要角色。书家的艺术冲动通常缘起于对客观世界的感知,“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6]。这种细腻敏感的心理活动存在于书家的内心之中,他就会有一触即发的感受。书家的这种“感”专注于客观存在的一切内容,凭借着直觉对于所触及的事情,引发了内心的波动,这是书法艺术行为产生的最原始动力。当书家进行书法艺术活动时,往往受到社会、自然的影响,产生新的艺术构思,表现与众不同的艺术作品,传达着更为准确的艺术信念和精神理想。在古代书法理论发展中,对于“兴”的认识则经历了一个由神化到物化的过程,其间不仅把书法的生成说成是“神化”的因素,也注意到了“敏思藏于胸中”这样一个在内心孕育构思的过程,并提出书法艺术的本体是“情”的结论。庾肩吾把“文情”作为衡量书法家能否入品级的基本标准,也就突出了书家内心的认识在书法艺术生成中所起到的最为直接和最为敏锐的作用。这说明古代书法理论在发展过程中延续文字观到书法观的理论模式的同时,也开始逐渐认识到书法本体是情感的表达。唐代张怀瓘指出:
其趣之幽深,情之比兴,可以默识,不可言宣。亦犹冥密鬼神有矣,不可见而以知,启其玄关,会其至理,即与大道不殊。[7]
在他看来,书法的产生是一个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过程,即是人人心中都有却又是人人口中所无的事情,并把这称为“道”。与此同时,张怀瓘把“兴”作为灵感,他说“意与灵通,笔与冥运,神将化合,变出无方”“理与道通,必然灵应”“不由灵台,必乏神气”“志出云霄,灵变无常”“自非造化发灵,岂能登峰造极”等。张怀瓘所讲的灵性实质是心触物有感的结果。
不管是外在的“物”,还是单独存在的“心”,二者的交融来源于直觉式的感知,而“直觉”是艺术欣赏或者是艺术生成的直接条件。这里所说的“感知”是有经验性的活动。这种经验性的“感知”就艺术的发生过程分析,一定是以认识为前提条件的。作为书家只有对客观世界的充分体验和了解才能积攒艺术素材。正是因为内心中已经存在了这样的经验,书家在触物的一刹那间才能唤起事先的美感经验,随物宛转,从而能动了情。朱光潜先生指出“美感经验是形象的直觉,就无异于说它是艺术的创造”[8]。书家“触物有感”的事情在古代时有发生,如王羲之观鹅、夏云奇峰、担夫争道、公孙舞剑器、锥画沙、屋漏痕,等等,或事或物。这些在书法家的眼中即不存在社会的实用性,也不存在自然的科学性,而那时完全成为一种艺术的启迪,引发的不是对于事物的客观判断,而是内心中隐藏的平静情感。张怀瓘称这种感觉是“触遇造笔,皆发于衷,不从于外”[9],朱长文认为是“积虑于中,触物以感之,则通达无方矣”[10]。
第二,书家内心蕴含着“情”也要有所“感”,即移情作用的出现。虽然“兴”是物我交融的结果,但是“心”具有主观能动性。这表明只有生机勃勃的生命存在,“心”的作用才能存在。古人认为书法的本体是观念形态的“情”,而“情”又是以主观意识形式存在于书家的内心之中,只不过这时候的“情”表现为静态的无形的隐性特征,这是指人本身就具有悲、欢、喜、怒、窘、穷、哀、愁、苦、闷等一系列的情绪存在,只是在没有引发之前深藏在心底,就像是一座活火山在喷发前的沉睡。一切艺术的情感因素都是从内心中产生的,并不是外界给予的。朱长文“手与神运,艺从心得”[11]、钱惟治“心能御手,手能御笔”都是强调内心是艺术产生的直接动因。“情”是内心原本就有的,在原始阶段是不确切和隐形的,当有客观的物质或者物情出现在主体眼前,内心对于外界的事物有所动,这就是“感”。有学者认为“感”与“情”是一种形态的两个方面,前者是动态的生成理论,后者是静态的本体理论。[12]
尽管古人常常论述书法艺术生成是“触物以感之”的结果,并且也注意到了书家的“心”与“情”的主导作用,但是为何“触物”就能有“感”呢?而不是通过其他方式,诸如重复训练、科学分析去获得这份感知呢?尤其是“物”自身乃客观存在,并没有思维能力和价值判断,除了拥有生物的基础本能之外,更不可能存在任何情感上的精神迹象。为何这些外在的东西能够激发我们的艺术感觉呢?这就是移情作用的体现。
移情作用是人的一项心理活动,是把自己的经验和情感转移到外物身上。在书法艺术活动中,移情通常存在两种情况。第一种是物我同一。比如怀素观看夏云奇峰,他的注意力已经完全专注于云的形象上。在他的主观认知过程中除了云的形象外一无所有,云的变化完全占据他的头脑,进而由云的自然状态联系到了书法艺术。由云的变化快慢联想到了用笔的节奏,由变化的形状联想到了字形的舒卷,由云的明暗联想到了墨色的枯润等,此时,云的物质性形态转化成为书法艺术的表现内容。所以当出现类似情况时,书家的移情作用往往表现为自然之美。第二是物入我情。如王羲之在兰亭雅集时书写的《兰亭序》。《晋书·王羲之传》记:“羲之雅好服食养性,不乐在京师,初渡浙江,便有终焉之志。……尝与同志宴集于会稽山阴之兰亭,羲之自为之序以申其志。”[13]王羲之的“终焉之志”在前,兰亭集会在后,触景生情。王羲之并没有把会稽山的自然之美移入书写中去,而是借助了“兰亭”这一具体的事件来促生内心中早已存在的“志”。这属于艺术精神的表达。古代书法理论中有关“触物有感”所引发的书法艺术冲动,偏重于第二种“物入我情”的描述。张怀瓘称:“万事无情,胜寄在我,苟视迹而合趣,或染翰而得人。”[14]正是讲移情作用产生的“物入我情”的道理。
第三,“兴”为即刻即逝,迸发于瞬间,不可预知,不可控制,极为自由,故而才能无止无遏。张怀瓘介绍了书法艺术生成时存在的两种现象:
且其学者,察彼规模,采其玄妙,技由心付,暗以目成。或笔下始思,困于钝滞;或不思而制,败于脱略。心不能授之于手,手不能受之于心,虽自己而可求,终杳茫而无获,又可怪矣。及乎意与灵通,笔与冥运,神将化合,变出无方。虽龙伯挈鳌之勇,不能量其力,雄图应箓之帝,不能抑其高。幽思入于毫间,逸气弥于宇内,鬼出神入,追虚捕微,则非言象筌蹄所能存亡也。[15]
一种是“笔下始思”,一种是“意与灵通”。前者完全属于临时应酬的写作状态,没有艺术表现的欲望和冲动,没有经过想象的构思过程,所以最后的完成是心手相违的。而真正的艺术要在主客体触发的一瞬间产生,因景生情,既不是书家用意识去控制出来的,也不是书家冥思苦想出来的,而是在心物交融之际自然产生的。正是因为“兴”全然处于一种自然生成状态,所以“情”也是真诚真实的。因而书法一定不能矫揉造作,应该是书家内心自然而又真挚的情感流露。贺知章“每兴酣命笔,好书大字,或三百言,或五百言。诗笔唯命,问有几纸,报十纸,纸尽语亦尽;二十纸三十纸,纸尽语亦尽。忽有好处与造化相争,非人工所到也”[16]。“造化”是不可预知的神来之笔,“人工”是技术形成的精湛之笔,后者是前者的基础,也是艺术境界形成的基础条件。更为重要的是古人往往能从不同的作品中体会到作者的不同情感,孙过庭体会王羲之书法时曰:“写《乐毅》则情多怫郁,书《画赞》则意涉瑰奇,《黄庭经》则怡怿虚无,《太师箴》又纵横争折。暨乎兰亭兴集,思逸神超;私门诫誓,情拘志惨。”[17]而朱长文在品味颜真卿书法时称:“盖随其所感之事,所会之兴,善于书者,可以观而知之。故观《中兴颂》,则闳伟发扬,状其功德之盛;观《家庙碑》,则庄重笃实,见夫承家之谨;《观仙坛记》,则秀颖超举,象其志气之妙;观《元次山铭》,则淳涵深厚,见其业履之纯,余皆可以类考。”[18]古人在谈自己的经验时也会经常提到“兴”的短暂和自然性质,如宋代的雷简夫在《江声帖》中记:“近刺雅州,昼卧郡阁,因闻平羌江瀑涨声。想其波涛番番,迅掀搕,高下蹶逐奔去之状,无物可寄其情,遽起作书,则心中之想尽出笔下矣。噫!鸟迹之始。乃书法之宗,皆有状也。唐张颠观飞蓬惊沙、孙姬舞剑,怀素观云随风变化,颜公谓竖牵法似钗股,不如壁漏痕,斯师法之外,皆其自得者也。予听江声,亦有所得,乃知斯说不专为草圣,但通论笔法已。钦伏前贤之言,果不相欺耳。”[19]古人认为艺术的“情”虽然藏在人的主观感受当中,却缘起于对客观世界的感知。人所具有的“心”不仅是物质的形态,更多的是一种认知形态。“心”中所藏是可以引发一切所能感知的“种子”的。“心动”就是受到某种可能引起的契机条件,这个条件被称为“物”。这里所讲的“物”,并不局限于具体的形状特征,而是指独立于人主观精神之外的一切可以感知并认识的内容,可以是具象的物质,也可以是抽象的物情。心与物在接触的一刹那间发生的感受就是“感”,是主客观世界共同交汇的结果。主观单方面的“感”是无病呻吟、闭门造车,客观单方面的“感”又会陷入客观唯心主义,所以,艺术本体的产生所依赖的正是主体和客体的共同作用结果。
正是因为古人提倡书法艺术的生成是真挚、自然的流露,也就反对无兴而书、为书而书,这就是“若迫于事,虽中山兔毫不能佳也”[20]。书法艺术的完成不能有任何外界的干扰和功利性、目的性。宋代朱长文强调“儒者之工书,所以自游息焉而已,岂若一技夫役役哉”[21],更是强调书家艺术行为的能动作用,反对为笔墨所累。明代莫云卿评祝允明书法曰:“楷书骨不胜肉,行草应酬,纵横散乱,精而察之,时时失笔,当其合作,遒爽绝伦。”[22]莫氏所评内容有二:一为应酬,二为合作。应酬无论如何都不会让作家随物宛转、与心徘徊的。董其昌谈自己经验时曰:“作书不能不拣择,或闲窗游戏,都有着精神处,惟应酬作答,皆率意苟完,此最是病。”[23]傅山更是认为应酬绝不会有兴会的书写冲动。与应酬相反,古人把兴会所至、任情恣性的作品称为“合作”。[24]清人周星莲比较“兴”与“不兴”对于书法艺术生成所带来的不同效果时说:
废纸败笔,随意挥洒,往往得心应手。一遇精纸佳笔,整襟危坐,公然作书,反不免思遏手蒙。所以然者,一则破空横行,孤行己意,不期工而自工也;一则刻意求工,局于成见,不期拙而自拙也。又若高会酬酢,对客挥毫,与闲窗自怡,兴到笔随,其乖合亦复迥别。欲除此弊,固在平时用功多写,或于临时酬应,多尽数纸,则腕愈熟,神愈闲,心空笔脱,指与物化矣。纵之,凡事有人则天不全,不可不知。[25]
可见,古人把“兴感”之际看作是产生书法艺术的重要条件。与之相反,没有“兴感”出现,刻意书写,或者完全是应用性书写的作品,通常被称为“工”或者“能”。庾肩吾评论“下品”书家“动成楷则”就是指不好的书家把书写的法则规范作为写字的最基本要求,而“中权后殿,各尽其美”的表述意在说明书写的文字要在整齐规范的前提下,保留些书写者的个性特征。庾肩吾把符合书法基本技法的书家收入最低品级,也意味着实用性书写是艺术性书写的基础。唐代张怀瓘列“神、妙、能”三品,其中“能品”即属于“下品”之列。宋代朱长文解释“能品”云:“离俗不谬,可谓之能。”清代包世臣又把这类实用性文字称为“佳品”,释为“墨守迹象,雅有门庭”。类似“下品”“佳品”“能品”的作品在古代以科举铨选居多。士人学习书法首要任务是参加科考,应用第一,功利性因素较大。洪迈称唐代铨选择人之法中书法要求楷法遒美。[26]一旦书写与制度相关联,那么完成的书法作品决不能掺杂任何个性情感,更谈不上“兴感”触发下的书写艺术行为。梁同书称:“高文典册大率多倩人缮写,非不圆润工整而书者之性情不存焉。”[27]所以凡是宋代的“院体”、明代的“中书体”、清代的“馆阁体”等实用性很强的文字,都不能作为阐释书法艺术生成的研究对象。
古代书法艺术理论经历了由文字观到书法观的过程,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文字观的理论一定能准确揭示出书法艺术的本质特点。相反,在面对书法的艺术生成时,古人的描述往往会变得更为感性,更具有个人的经验性特征,甚至于以抽象释具象、以空幻释神奇。唐代苏晋、王翰阐释书法艺术生成,结果“历旬不成”,张怀瓘反复琢磨书法艺术的生成原理,最后得出 “书道大玄妙”“始知极难下语”[28]的结果。以张怀瓘的认识和阐释能力而言,书法的艺术生成原理并非无处着手。万希庄称赞张怀瓘对于书法艺术的阐释性说明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其言曰:“文与书,被公(张怀瓘)与陆机已把断也,世应无敢为赋者。”[29]这说明,张怀瓘对于古代书法的艺术原理是非常明晰的。在张怀瓘对书法艺术的论述中,不难发现他对于书法艺术的产生十分关注,只有明确了书法艺术的生成问题才能以此为标准对古代书法进行艺术性的划分与判断。“兴”作为书法理论,不仅能够揭示书法艺术的产生,还能够以此建立起书法艺术的规范与范式。虽然我们了解到古代书法理论常常运用品级流别的形式进行艺术定位,但是实际上所依据的却是书法艺术的生成形态,前者是果,后者才是因。
注释:
[1]张怀瓘.书断[G]//张彦远.法书要录.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04:267.
[2]张怀瓘.书断[G]//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室,上海书画出版社.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96:180.
[3]朱长文.续书断[G]//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室,上海书画出版社.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96:324—325.
[4]徐干,著.池田秀三,校注.中论[J].京都大学文学部研究纪要(23),1984(3):75.
[5]李泽厚,刘纲纪.中国美学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25.
[6]陆机.文赋[G]//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67.
[7]张怀瓘.六体书论[G]//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室,上海书画出版社.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96:212.
[8]朱光潜.朱光潜美学文集:第一卷[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19.
[9]张怀瓘.书断[G]//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室,上海书画出版社.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96:180.
[10]朱长文.续书断[G]//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室,上海书画出版社.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96:325.
[11]朱长文.续书断[G]//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室,上海书画出版社.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96:325.
[12]李壮鹰.中国诗学六论[M].济南:齐鲁书社,1988:88.
[13]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3099.
[14]张怀瓘.书断[G]//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室,上海书画出版社.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96:207.
[15]张怀瓘.书断[G]//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室,上海书画出版社.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96:154—155.
[16]窦臮.述书赋[G]//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室,上海书画出版社.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96:256.
[17]孙过庭.书谱[G]//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室,上海书画出版社.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96:128.
[18]朱长文.续书断[G]//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室,上海书画出版社.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96:324.
[19]朱长文.墨池编:卷三[G]//卢辅圣.中国书画全书.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230.
[20]蔡邕.笔论[G]//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室,上海书画出版社.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96:6.
[21]朱长文.续书断[G]//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室,上海书画出版社.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96:336.
[22]莫云卿.论书[G]//明清书法论文选.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5:213.
[23]董其昌.画禅室随笔[G]//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室,上海书画出版社.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96:544.
[24]丛文俊.古代书法的“合作”问题及其介入因素[J].中国书法,2006(9),(10).
[25]周星莲.临池管见[G]//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室.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96:723.
[26]洪迈.容斋随笔:卷十[M].孔凡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5:129.
[27]梁章钜.吉安室书录[G].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3:64.
[28]张怀瓘.文字论[G]//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室,上海书画出版社.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96:209.
[29]张怀瓘.文字论[G]//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室,上海书画出版社.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96:2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