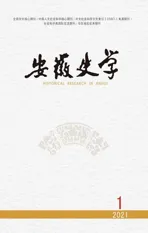抗战时期“发展华中”战略的党内分歧及其化解
——以中原局、东南局为中心的考察
2021-11-26冯超
冯 超
(中国国家博物馆 科研管理处,北京 100006)
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后,中共中央作出“发展华中”的战略决策,新设中共中央中原局,刘少奇为书记,负责领导“长江以北河南、湖北、安徽、江苏地区党的工作”;(1)《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中原局组成及管辖区域的通知》(1938年11月9日),中共滁州市委党史研究室、安徽省新四军历史研究会编著:《中共中央中原局》上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年版,第87页。并将原来的中共中央东南分局改为中共中央东南局,项英为书记,负责“浙江、福建两省和江苏、安徽、江西三省的一部分”(2)陈丕显:《中共中央东南分局、东南局的建立和部分工作情况》,本书编辑组编著:《中共中央东南局》上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版,第48页。地区党的工作。日后,“发展华中”的战略主要由中原局和东南局来贯彻执行。在“发展华中”战略方针下,1939年底刘少奇率中原局机关移驻皖东与新四军江北指挥部会合,此后从皖东至皖南并不广阔的区域内,出现中共中央中原局和中共中央东南局两个中央局机构,且距离较近,工作上的交织与争论使得华中地区长江南北的政治局面迅速发生变化。这种变化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新四军的指挥权,其二是新四军的发展方向。具体看来,对于新四军的指挥权,中原局成立前,新四军主要由项英指挥;中原局挺进皖东后,没有下属部队,因此,江北部队改由刘少奇就近指挥。这客观上造成项、刘分别指挥新四军一部的局面。对于新四军的发展方向,中原局建立前,新四军第一、二支队东进至苏南,第三支队留在皖南,第四支队第八团东进皖东,七团和九团坚持在合肥东南部,基本处于苏南、皖南、皖东地区。中原局移驻皖东后,刘少奇提出发展苏北,要求新四军一部渡过淮河,建立苏北抗日根据地。这一构想改变了新四军最初的发展方向,且与项英的意图有很大差异。这后来成为项、刘分歧的焦点。从1939年底至1940年11月,项、刘、中共中央三方往来大量电文,讨论解决项与刘的战略分歧。可见,项与刘的分歧受到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实际上,项、刘分歧关乎新四军的发展,关乎华中抗战局面的推进。后来的实践证明:刘的战略旨在贯彻执行中共中央的指示,实现了“发展华中”的战略目标;相比之下,项的战略意图未能实现。那么,项、刘分歧的来龙去脉如何?中共中央是如何应对并解决项、刘分歧的?本文依据抗战时期项、刘、中共中央三方电文,结合学界先行的研究,试图梳理解决上述问题,以此探寻抗战时期中共党内分歧的处理机制。(3)对于项英与刘少奇的分歧,童志强、陈兴等已经注意到,但论述稍简,无法全面了解项、刘分歧的来龙去脉。参见童志强:《从高敬亭错案兼论新四军时期的项英——答王辅一》,《江淮文史》2012年第4期,第115—119页;陈兴:《刘少奇在新四军(四)——反对江北部队南调》,《党史文汇》1998年第10期,第35—36页。
一、“发展华中”方针与中共中央、项英、刘少奇三方认识
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中共中央提出“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这一方针提出后,中共中央并“没有真正下决心实施”(4)王建国:《项英在皖南时期主要“错误”辨析》,《抗日战争研究》2011年第2期,第106页。,直到1939年4月后,中央才开始真正意义上重视发展华中。1939年1月,刘少奇到达河南竹沟正式组建中原局,通过调查研究和听取相关汇报,逐渐认识到华中抗战的特殊性。同年3月,刘少奇返回延安。4月12日,刘少奇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作关于华中工作问题的详细汇报。报告具体分析了目前华中地区的军事、政治情况及其特点。毛泽东听取汇报后,发言指出:“六中全会决议发展华中的方针是正确的”,华中地区“现有两万党员,将近两万军队,这是大的成绩,比华北的发展更大”,“现在全国共产党与游击战争的主要发展方向是华中”。(5)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刘少奇年谱》(增订本)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277页。会后的4月21日,中央果断作出《关于发展华中武装力量的指示》。这份指示是发展华中的重要文献。首先,指示明确定位了华中在全国抗战中的战略地位。指示指出,华北中心工作是巩固,“华中是我党发展武装力量的主要地域,并在战略上华中亦为联系华北、华南之枢纽,关系整个抗战前途甚大。”其次,指示重新确立了华中抗战武装的领导中心。指示指出,“新四军在江北指挥部应成为华中我武装力量之领导中心”,明确提高了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的地位。再次,指示调整了江南新四军的发展方向。指示提出,“江南则因国民党之限制及其统治力量之雄厚,致发展迟缓,在将来发展亦有很多困难”,新四军在江南“发展前途又受大限制”,“希望东南局及新四军领导同志顾全全国局势及华中之重要,抽调大员及大批干部到江北”。(6)《中央关于发展华中武装力量的指示》(1939年4月21日),《中共中央中原局》上卷,第119页。上述表明,中共中央认识到新四军在江南发展受限,希望新四军领导抽调大员及大批干部到江北,实际上是要求将重心转移到江北。
中央发出发展华中武装力量的指示后,项英于1939年4月和5月致电中央,提出了江北工作方针以及江北指挥部的人员配置,基本上执行了中央发展华中武装的要求。因此这一时期,项英并没有抵制“发展华中”方针,其支持组建江北指挥部,也派出了一批干部支援江北。但是,项英的工作重心并没有完全转移到华中江北,江北部队的敌后游击战争未能充分开展。1939年5月11日,项英致电中央,认为:“江北不在张扬而在求实利与实效,而在胜利以便发展与强大”(7)《关于江北工作的提议》(1939年5月11日),《中共中央东南局》下卷,第705页。,这一主张影响江北新四军的发展。对此,刘少奇在1943年3月的总结报告中批评道:六届六中全会以后,“津浦路、淮南路以东仍是没大注意开展游击战争,那里的同志仍在东南局原来路线的影响之下。直到1939年冬……才把中心转移到津浦路两侧敌后地区去”。(8)刘少奇:《六年来华北华中工作经验的报告》(1943年3月),《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2018年重印,第275页。在刘少奇1939年3月返回延安后,至1939年底深入皖东这段时间,皖东江北部队处于项英负责的东南局领导之下,然而津浦路、淮南路以东仍是没大注意开展游击战争。这表明六届六中全会后,项英对华中、皖东等地区没有足够的重视。
对于中央“发展华中”的战略,刘少奇坚定贯彻执行。1939年5月18日,身在延安的刘少奇致电中原局代理书记朱理治,指出:“敌人主力已向中原及西北进攻,河南将成为游击战区,鄂中将成为敌人的深远后方。这是我党在中原发展游击战争的最好时机。应动员全党大大发展游击战争,建立我党领导的武装部队,确立我党在中原长期抗战中的巩固地位与基础。”(9)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刘少奇年谱》(增订本)第1卷,第280—281、288、292页。8月下旬,中共中央政治局经过多天的会议讨论,“决定加快发展华中”。(10)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刘少奇年谱》(增订本)第1卷,第280—281、288、292页。9月15日,刘少奇等从延安返回华中。11月初,他率中原局机关到达新四军游击支队驻地皖北涡阳。11月11日,首次提出让游击支队一部“越过津浦路东去创造苏北根据地”。(11)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刘少奇年谱》(增订本)第1卷,第280—281、288、292页。12月19日,刘少奇正式提出:苏北是有最大发展希望的地区。
综合上述材料,笔者得出几点结论:一是六届六中全会后,中央虽然提出“发展华中”的方针,但是一开始没有达到应有的重视程度。1939年4月后,中央的重视程度愈来愈高,原因是刘少奇组建中原局返回延安后,汇报了华中抗战的重要地位。8月后,中共中央决定加快发展华中。二是刘少奇坚决贯彻执行中央“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1939年底,刘少奇率中原局抵达皖东与江北指挥部会合前后,提出发展苏北地区,有力推动了“发展华中”的战略进程。三是项英在1939年12月前,并不抵制中央“发展华中”的方针,但是在具体贯彻执行上力度不够。项英没有完全听从中央的指示,将工作重心转移到华中江北地区。随着中央对发展华中的高度重视,项与刘的战略分歧渐露端倪。
二、新四军主力“北上”、“南下”与项英、刘少奇的认识差异
刘少奇抵达皖东后,纠正了皖东地区新四军发展受限的思想问题,提出大力发展苏北地区。12月19日,刘少奇致电中央并项英、彭雪枫,认为苏北地区是有最大发展希望的地区,建议第四、五支队及皖南部队能够配合皖东北彭雪枫、张爱萍部向苏北发展。在发展苏北的战略下,刘少奇又对新四军的部署提出意见:一是第四支队七团和第五支队八团等在皖东津浦路两侧活动,特别提到江南六团只到扬州、六合活动。二是其余第四支队九团、十四团和第五支队十团、十五团渡过淮河,在皖东北整理后配合彭雪枫部向苏北发展。三是待苏北发展立足之后,部队可向淮阴以南发展,即可配合七、八两团及江南部队向东、北发展。(12)《刘少奇关于目前华中发展地区及工作部署致中共中央书记处等电》(1939年12月19日),《中共中央中原局》上卷,第156—157页。
刘少奇提出发展苏北,不仅需要皖东第四、第五支队的配合,还需要江南部队的大力支持。刘的苏北发展战略需要调动江南部队,这是皖南军部项英意料未及的,便触动了项与刘的分歧。对于刘少奇的苏北工作意见,项英没有赞同。12月22日,项英复电刘少奇并中央,认为刘少奇意见考虑不全面,提出新四军整体方针“绝不能作过左的布置”,“希望中央和军委对四军应有全部计划”,确定新四军行动总体的方针。(13)项英:《对苏北工作的意见》(1939年12月22日),军事科学院《项英军事文选》编辑组编:《项英军事文选》,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3年版,第637页。项英看来,刘少奇发展苏北是局部问题,会造成与苏北国民党军冲突,将打破新四军总体发展方向,出现让新四军各自为战的局面。12月23日,项英再次致电中央,强调江南的特殊情形和困难,提出“在将来任何情况下是以独立开展南方局面,以与北方配合,这在政治上、战略上均应如此。”项英认为江南和苏北同样重要,江南要冲出包围需要集中力量,“否则分散游击,无论政治、军事上不能展开局面”。(14)项英:《对江南工作的布置意见》(1939年12月23日),《项英军事文选》,第639页。12月27日,中央致电刘、项,提出“在华中方面以淮北之苏皖地区为主要发展方向,从四、五支队酌抽部队过淮河是很对的”,“应从江南酌派部队及干部去增强之,以便胡服(即刘少奇——引者注)能从四、五支队抽四个团过淮河”,“皖南方面抽一部分干部及武装过江北,发展和巩固津浦南段地区”。同时,中央要求“东南局地方工作应着重皖浙赣三省边区”,“这样才能使在将来极不利局面下,有江北及皖浙赣三省边界的两条退路。你们应坚决执行这一计划”。(15)《中央关于新四军在华中及江南工作的指示》(1939年12月27日),《中共中央中原局》上卷,第163页。中央电文肯定了刘少奇的意见,强调淮北之苏皖地区为主要发展方向,要求东南局支持刘的苏北发展计划;又尊重了项英的意见,要求东南局重视皖浙赣边区工作,保障新四军的退路。中央看来,江北与江南同等重要,江北与江南两个方向都要稳步发展。
项英、刘少奇关于苏北与江南地位争论的同时,江北指挥部指挥权也是刘少奇需要解决的问题。江北指挥部成立后,在东南局领导下,设立了前敌委员会。1939年底,中原局与江北指挥部会合后,江北指挥部的指挥权发生变化。中原局抵达江北后,需要邻近指挥江北部队,所以“前委”无存在必要。为了解决江北部队指挥权问题,刘少奇于1939年12月31日致电中央并项英,提出“前委”与中原局的关系问题。1940年1月1日,项英致电中央答复了刘少奇的问题。“中原局既到皖东,四军江北前委应取消,统一于中原局”,“军部不指挥江北部队,以便统一”。(16)《项英建议取消江北前委统一由中原局指挥致中共中央电》(1940年1月1日),《中共中央中原局》上卷,第169页。1月4日,中央书记处决定将江北指挥部前委改为皖东军政委员会,归中原局指挥。1月19日,中央决定第四、第五支队归中原局指挥。至此,江北指挥部受刘少奇为书记的中原局指挥,新四军军部和江南指挥部主要由项英指挥,这是新四军指挥权的重大变化。
江北部队指挥权解决之后,项英与刘少奇的分歧加剧,尤其是江南部队北调问题。1940年1月4日,刘少奇致电中央及项英,再次提出新四军第四、五支队或江南抽调一部分队伍去淮河北岸发展,建立苏北根据地,使四、五支队从战略上打破目前所处的危险与困难境地。电文中说:“如同意我的建议,还请江南抽调一、二个团兵力过江北,并派陈毅或袁国平来江北加强领导。”对于刘少奇的要求,中央11日复电同意“从江南抽调一两个团过江北发展”,协助彭雪枫部进入苏北。(17)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刘少奇年谱》(增订本)第1卷,第297—298,310、312页。然而项英断然拒绝了刘少奇的意见。1月14日,项致电刘并中央,表示:“皖南在任何情况下非独立行动,坚持南方不可。一切工作须按全国情形来布置,不能限一方面,也不能各自打算。你的指示确难遵行。”(18)引自童志强:《从高敬亭错案兼论新四军时期的项英——答王辅一》,《江淮文史》2012年第4期,第116页。由此电文可见项英与刘少奇分歧的严重程度。
对于项英与刘少奇的分歧,中央起初是通过加强与东南局的沟通来化解。1940年1月19日,中央专门给项英及东南局发出对新四军发展方针的指示,兼顾项、刘双方的要求。指示中,中央再次肯定新四军向北发展的方针,认为“华中是我们目前在全国最好发展的区域,在华中可以发展”。“新四军能否向南发展,向皖浙赣大活动,抑或应过江向北,要看今后的形势来决定”,“皖南既不能再调部队过江到皖北,我们同意不再调”,“江南陈毅同志处应努力向苏北发展”。“同意四、五支队归中原局指挥,但在苏北扬州一带的部队,则仍归项英、陈毅同志指挥。”(19)《中央对新四军发展方针的指示》(1940年1月19日),《中共中央中原局》上卷,第176页。从这份指示中可以发现,中央居中对项、刘分歧的调解。中央支持刘少奇发展苏北的方针,同意中原局指挥江北第四、第五支队,并要求陈毅向苏北发展;同时,中央对于项英向南发展的主张没有完全反对,同意皖南部队不再调动,苏北扬州地区部队仍归项英指挥。中央调解的背后是要准备新四军在皖北苏北与皖浙赣闽交界地区的两条退路。在中央与项英沟通的同时,刘少奇也与项英积极沟通。1月19日,刘少奇两次致电项英并中央:我致力于贯彻发展华中的任务,从新四军第四、五支队抽调部队去淮河北岸并向苏北发展,是为了完成中央发展计划的布置。希望你尽一切可能帮助我们完成这一任务。不过,中央的调解并没有解决项、刘之间的分歧。
1940年3月,皖东“摩擦”升级,李品仙与韩德勤合谋东西夹击新四军第四、五支队。皖东形势危急,刘少奇与项英的矛盾激化,主题是江北部队南下问题,焦点是叶飞、陶勇两部南调。3月下旬,叶飞、陶勇两部急调来安半塔集,援救新四军第五支队,取得半塔保卫战的胜利后,叶、陶两部活动于江北地区。4月5日,刘少奇率领中原局和江北指挥部东进来安半塔,与新四军第五支队会合。起初,刘希望叶、陶两部配合坚持津浦路西阵地,防备桂系的进攻,后为推进苏北问题的行动方案,刘要求叶部担负“引敌围攻、孤军坚守、待援歼敌”的任务。(20)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刘少奇年谱》(增订本)第1卷,第297—298,310、312页。苏北问题进入关键时期,项英等提出江北部队南调。关于江北部队南调,项英原先并不赞成。3月29日,项英致电刘并中央,提出:江北部队“南调绝无理由可讲”,“故置之不理为好”。(21)项英:《关于蒋顾电令南调江北部队的意见》(1940年3月29日),《项英军事文选》,第663页。但至4月10日,项的态度发生变化,“我仅有三个团转向苏北不容易,俟在皖南反击后暂坚持一时”,“江北部队不能南调”,“但江南基本部队可允不北移,在某种情况下对叶飞部队可允设法南调”。(22)项英:《新四军决心准备还击》(1940年4月10日),《项英军事文选》,第674页。项的态度变化源于江北新四军在津浦路西、路东与国民党顽军冲突后的认识。3月底,刘少奇领导江北新四军先后取得定远自卫反击战和来安半塔自卫反击战的胜利,冲突短暂停止。项英此时认为,“根据各方情形,某方显系全国布置和阴谋,如全国难以到达好转,则阴谋实施不免”,“就江南现有力量”,“在大变中不能支持局面”。因此,项英认为,“对全国及将来估计,是否目前可允江北部队南调,则江南可达六万以上兵力,牵制影响某方甚大。”(23)项英:《建议江北部队南调以便与国方谈判》(1940年4月14日),《项英军事文选》,第676页。项英担心国民党顽军进攻皖南、江南,提出江北部队南调,加强江南和军部的防御力量。刘少奇反对叶、陶两部南调。4月12日,刘少奇致电项英并中央,指出:“中央决定江南部队立即向苏北发展,江南应为箝制方向且江南武装冲突尚未发生,或者还可缓和一短时,请暂缓调动叶飞、陶勇两团。”(24)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刘少奇年谱》(增订本)第1卷,第310、312、313、313页。4月16日,项英又指出,“江北部队不南调冲突仍不免”,主张“调江北之叶、张(张道镛,即陶勇——引者注)两团全部急返江南,以应大事变”。(25)项英:《关于调江北叶张两团回江南的请示》(1940年4月16日),《项英军事文选》,第677页。4月17日,刘少奇致电中央,提出:“为了解决苏北问题,叶飞部不应调回江南,而应速回苏北积极行动。”(26)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刘少奇年谱》(增订本)第1卷,第310、312、313、313页。刘少奇认为,“叶飞部回江南对救援军部的作用并不大,而在向苏北行动的作用及发展前途很大。”(27)引自陈兴:《刘少奇在新四军(四)——反对江北部队南调》,《党史文汇》1998年第10期,第36页。4月18日,毛泽东致电项英:“叶、张两团以留在江北发展为适宜”(2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88页。,不同意项的主张。4月19日,刘少奇致电中央,严肃指出:江北部队南调是国民党阴谋消灭我军的毒辣计划,“我坚决不同意江北任何部队南调”,叶飞部“必须立即在苏北行动,吸引韩德勤向其进攻,我在自卫口号下抵抗至适当时间再去增援,才能解决苏北问题。否则,我即使有足够军力,却无充分政治理由向苏北大胆行动。”(29)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刘少奇年谱》(增订本)第1卷,第310、312、313、313页。刘少奇强调向苏北发展是中央既定方针,不能随便改变。江北叶部如南下,苏北群众组织与统战关系即刻瓦解,苏北问题无解决可能,前期工作也将付之东流。(30)参见陈兴:《刘少奇在新四军(四)——反对江北部队南调》,《党史文汇》1998年第10期,第35—36页。4月20日,项英再次致电中央军委,仍然坚持叶部调回江南,指出“为便于争取苏北,在江南、皖南加强力量有大作用,以牵顾不能增援。”(31)项英:《关于调叶部回江南的请示》(1940年4月20日),《项英军事文选》,第681页。电文中,项英强调了苏北力量有八路军南下部队以及新四军第四、第五支队,苏北顽军力量薄弱,完全可以应对,叶部南下可加强江南力量,牵制顾祝同。
上述电文中,刘少奇、项英意见针锋相对。面对这种形势,4月20日,中央致电项英、刘少奇,郑重指出:“皖北、皖东、淮南、苏北是我军在全国的最重要的战略地区之一”,“绝对不能答允四、五支队和叶、张两团南调”,“叶、张两团及苏北全部均暂归中原局指挥,部队调动应该依照中央的电令”,“至于江南部队如何部署,由项英视情况自行决定”。(32)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刘少奇年谱》(增订本)第1卷,第310、312、313、313页。中央电文措辞强硬,将新四军叶飞、陶勇两部以及苏北部队划归中原局指挥,是对项的新四军指挥权的制约与收束。巧妙的是中央规定叶、张两部和苏北部队“调动依照中央电令”,江南部队部署由项英决定,避免进一步激化项英、刘少奇矛盾。4月22日,项英再次强烈要求叶、张两部南下,“为着仍使我江南部队不遭对方之打击,如以现在皖南三个团(加军直)、苏南三个团仅两个团,而欲求对此两战争地区斗争的胜利,则不可能”。“江北局势因苏韩败退,及皖李现撤兵,已基本稳定”,“并不需要叶、张两团”。“叶、张南调,一方既以缓和战区之压迫,一方即以增强反击力量,其有帮助即在此”,“为使江南能够勉力坚持、取得反击胜利,再度坚决要求叶、张两团南调”。“至四、五支队南调问题”,“可延搁则延搁之”,“无法延搁时便是作战,我亦决心应战”。(33)项英:《关于大江南北战略形势》(1940年4月22日),《项英军事文选》,第683—684页。项英此电虽然提出江南的客观需要,但与中央的指示相背离,引发中央的不满。
这场争论中,刘少奇获得中央的支持,而项英被中央责备并制约。在叶、张两部南调的分歧中,刘少奇要求叶飞部担负“引敌围攻、待援歼敌”的任务,不可南下;而项英出于江南力量的薄弱,要求叶飞部南下,应对江南可能发生的战争。两者虽然皆有自身的战略需求,但中央的“发展华中”战略决定苏北的优先方向,这是项英未能接受的。项英在电文中向中央提出:“甚望顾及各方,江南之愁窥困难,恐较江北有过之无不及。”(34)项英:《关于大江南北战略形势》(1940年4月22日),《项英军事文选》,第684页。争论中,项英也有妥协,放弃了第四、第五支队南调的主张,但其强烈坚持叶、张两部南下。最终中央要求“叶飞部开返苏北,在苏北地区放手发展”(35)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刘少奇年谱》(增订本)第1卷,第314、335、342、344页。,以江北地区为新四军主力的主要发展方向,发展苏北的战略得以贯彻下去。苏北战略如出现意外,华中局面恐受巨大损失,这对于全国局势将产生不利影响。因此,中央侧重支持刘少奇的苏北发展战略,守住华中最重要的生命线。5月4日,中央给东南局发出《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的指示,指示由毛泽东起草,对东南局的工作给予了严厉批评。指示中提到,“他们要四、五支队南下,我们则以无论如何不能南下的态度对付之;他们要叶、张两部南下,我们则以请准征调一部北上对付之。”(36)《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1940年5月4日),《中共中央中原局》上卷,第227页。指示对项英的做法提出批评,要求东南局和军分会诸同志讨论,坚决执行中央决定。在江北部队南调之争中,项英、刘少奇双方都向中央表达彼此的关切。中央权衡利弊后,适度制约项英权限,表明中央此时侧重转向发展皖北、苏北地区。
1940年6月,中央增派八路军黄克诚部及彭明治部抵达华中,进一步加强对发展苏北的支持力度。八路军南下华中后,中央和刘少奇希望江南新四军军部过江北上,统一指挥华中新四军、八路军,因而围绕军部北移,项英与刘少奇产生分歧。8月17日,刘少奇致电叶挺、项英:建议叶挺或军部北来后详细商量华中整个进攻计划。(37)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刘少奇年谱》(增订本)第1卷,第314、335、342、344页。同日,项英致电中央:“皖南部队仍坚持原有根据地”,“力求军事指挥重心逐渐转移江北”。(38)项英:《关于军部不能北移及对江南工作的意见》(1940年8月17日),《项英军事文选》,第694页。10月9日,刘少奇致电中央,提出:“军部在皖南既不可能,建议从速北移”,“皖南阵地即用游击战争坚持,如不能坚持,即放弃亦可”。(39)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刘少奇年谱》(增订本)第1卷,第314、335、342、344页。10月11日,项英致电中央并刘少奇,提出“依据各方形势与条件,军部困难北移”,“仍以军部所在地作基点较有利”。(40)项英:《关于皖南情况及军部北移困难的报告》(1940年10月11日),《项英军事文选》,第700页。10月12日,中央致电叶挺、项英等:“军部应乘此时速速渡江,以皖东为根据地,绝对不要再迟延。”(41)《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关于新四军的行动方针致叶挺等电》(1940年10月12日),《中共中央中原局》上卷,第449页。10月19日,刘少奇等致电中央:“华中的斗争急需建立统一的司令部”,“解决华中统一指挥问题最圆满的办法是军部速即移来,统一华中指挥并可兼指挥江南”。(42)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刘少奇年谱》(增订本)第1卷,第314、335、342、344页。10月28日,项英致电中央,认为:根据目前情况来看,“当以加强江北为主要,以求控制华中一带,要坚持皖南,确难二者得兼”,“为了便于将来我更大发展,坚持皖南阵地有极大作用。如现放弃,将来不易取得这一强固的支点”。(43)项英:《关于新四军皖南部队北移的意见》(1940年10月28日),《项英军事文选》,第703页。项英出于坚持皖南支点的战略作用,不愿北移,但已认同江北的战略中心地位,尤其是力求新四军军事指挥重心转移至江北,反映出项英思想认识的变化。11月17日,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建立。中央决定:叶挺、陈毅、刘少奇统一指挥所有陇海路以南之新四军与八路军。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建立后,新四军指挥重心完成北移,项英与刘少奇的战略分歧趋于完结。在中央决定中,特别提出“项英同志,在皖南部队移动事宜就绪,经重庆来延安参加七大”。(44)《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叶挺、陈毅、刘少奇为华中总指挥部正副指挥及政委的决定》(1940年11月),《中共中央中原局》上卷,第483页。由于种种原因,项英未能离开皖南军部赴延安参加七大,也未能及时率领军部北移。
三、项英与刘少奇战略思维的不同
项英与刘少奇对于新四军的发展方向以及“发展华中”战略的认知分歧,根源于项英与刘少奇战略思维的差异。东南局书记项英“始终认为新四军主力应坚持在江南地区发展,对于向北发展的方针不愿积极贯彻执行”。(45)彭厚文:《论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中共党史研究》2014年第3期,第70页。项英坚持皖南、苏南阵地,试图打开新四军“向南发展”的游击道路,主张:长江以北由中原局领导,北进主力应以八路军南下部队为主,不要调动新四军部队;长江以南由东南局领导,集中新四军主力,向南发展,形成南北配合,遥相呼应之势。项英的战略构想是:坚守皖南支点,待日军侵占闽浙赣后,以皖浙交界天目山为依托,向闽浙赣边方向发展,因此不同意军部北上,也不同意抽调部队北上。(46)参见陈兴:《刘少奇在新四军(四)——反对江北部队南调》,《党史文汇》1998年第10期,第35页;张双智:《皖南事变前中共中央与项英的战略分歧——从新发现的白艾笔记说起》,《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4期,第110—111页。
关于项英向南发展战略的正确性,学术界尚有争论。有学者指出:项英的战略思维有一定的被动性,即向南发展建立在日军进攻闽浙赣的判断上,但根据当时实际,日军并没有这一进攻行动。因此,等待日军进攻会造成错失新四军在皖东、苏北发展的良机。(47)参见陈兴:《刘少奇在新四军(四)——反对江北部队南调》,《党史文汇》1998年第10期,第35页。有学者研究发现:“向南发展”不是项英自作主张,中央有要求项向南发展、坚持皖南的指示。(48)黄开沅:《对项英率部滞留皖南原因的探讨》,《安徽史学》1991年第1期,第19—25页;王建国:《项英在皖南时期主要“错误”辨析》,《抗日战争研究》2011年第2期,第103—105页。也有学者认为:项英坚持的新四军南方战略方案始终是毛泽东和中央全局战略的重要备案,项英接受并执行毛泽东和中央的新四军南方战略支点构想,但表现出相当程度的教条主义态度,“始终以南方战略支点为重心考虑问题,而非以更宏观的视野深入分析、领会中央对新四军战略北移意见的合理性”(49)王骅书、王祖奇:《项英与中央屡生分歧和争论仍长期任职新四军原因探析》,《安徽史学》2013年第2期,第96—103页。,“项英的南进构想,从原则上讲并未错,错在对形势的分析,不能综观全局,在认识上出了偏差”。(50)房列曙:《关于项英“南进”“南调”“向北发展”问题的重新评价》,《安徽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2期,第232—234页。从当时的历史情景来看,项英提出自己的主张,并坚持自己的主张,是可以理解的。但从历史结果来看,项英的南向战略意图未能实现。
相对而言,中原局书记刘少奇坚持贯彻中央的正确方针,推动新四军“东进北上”,完成“发展华中”的战略目的。刘少奇提出发展苏北,是基于对抗战形势的准确分析与判断。刘少奇认为:“苏北地域辽阔,全属敌后,我们有驰骋回旋的广大地盘。国民党江苏省政府主席韩德勤暗中勾结日、伪,积极反共反人民,人民恨之入骨,群众迫切要求我们前去领导他们进行抗日斗争。向东发展,政治上、军事上对我们都有利。因此,苏北是我们的战略突击方向,应集中力量向这一地区发展。”(51)刘顺元:《刘少奇在皖东敌后》,《中共中央中原局》下卷,第95页。刘少奇后来也总结指出:发展华中是按照具体步骤进行的,1940年“是以军事行动为主,打开华中各根据地局面”。(52)刘少奇:《对华中工作的意见》(1943年6月18日),《刘少奇选集》上卷,第288页。这从一个层面表明中原局发展华中是有规划的。刘的战略意图即是贯彻执行中央“发展华中”的战略,打开皖东、皖北、苏北的局面,发展壮大新四军力量,让华中成为像华北一样的抗战重要战略区域。
结 语
项英、刘少奇分歧是抗战时期“发展华中”战略推进过程中的独特现象,也是抗战相持阶段华中苏皖敌后局面发展演变的影响因素。这一分歧是抗战相持阶段中共中央首次面对两个重要的中央局负责人之间的分歧,自然引起中央高度关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决定成立中原局和东南局,显然,这两个中央政治局派出机构是执行中共中央战略方针的重要机构。项英和刘少奇分别作为东南局书记、中原局书记,在执行中央“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中,产生一系列分歧,根源于项英、刘少奇都有自己不同的分析和判断。项英与刘少奇在发展华中、新四军发展方向等具体问题上存在分歧。刘少奇坚持新四军主力“东进北上”,完成“发展华中”的战略;而项英反对新四军主力“北上”,主张坚守皖南,谋求向南发展。项英与刘少奇的分歧实质上是战略思维的不同。中央在处理项、刘分歧中,充分尊重项英和刘少奇的意见,最终经过战略权衡后支持刘少奇,是根据抗战局势的变化作出相应的决策。在这一过程中,中共中央经历江北、江南同步发展向以苏北、皖北为重心的政策转变,把握并权衡中原局和东南局的不同意见,不断调整政策方向的优先点,并在不同阶段采取居中调解、适度制约项英权限、全方位支持刘少奇等方式处理、化解中原局与东南局的分歧,保证了既定战略的贯彻落实。关于战略方针存在党内分歧是正常的,中央能否及时正确化解分歧,统一思想认识,达成战略目标是关键。抗战时期中共中央在“发展华中”战略过程中,正确应对中原局与东南局的分歧,并采取妥当方式化解分歧,最终达成战略标目,是中央领导智慧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