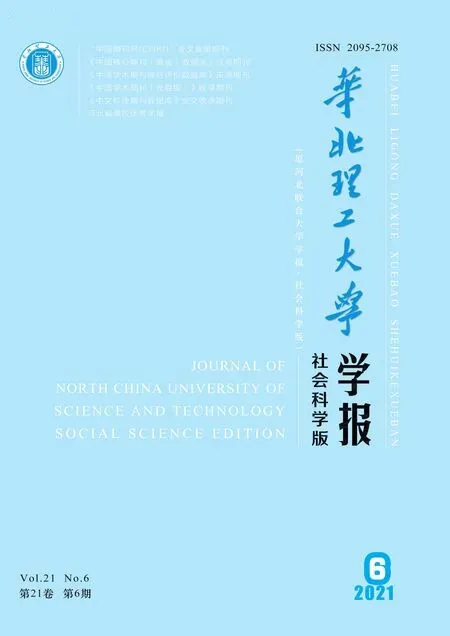从“掩饰”到“真实”On a Chinese Screen译本中的中国形象
——毛姆游记
2021-11-26徐雅静
徐雅静
(安徽信息工程学院 通识教育与外国语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0)
OnaChineseScreen: Sketches of Life in China(以下简写为OnaChineseScreen)是英国作家毛姆(William Somerset Maugham)创作的唯一一部有关中国的游记作品。该游记由五十八篇短文组成,毛姆在本书中描绘了三种古老的中国形象,分别为古老、辉煌、华美的中国形象;黯淡、破败、落后的中国形象;宁静、平和、恬淡的中国形象[1]。毛姆在20世纪初亲身游历中国,在部分篇章中构建了一幅遥远神秘的近代中国图景,但是作品本身仍无法摆脱东方主义思想的桎梏,所以毛姆的OnaChineseScreen可被称作一部极具东方主义色彩的著作。
一、东方主义概述
在《东方主义》一书中,赛义德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探讨了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之间权力与话语的对立模式。赛义德指出,东方主义可以在语言、文化、历史和政治领域找到踪迹。19世纪以来,西方不断培养东方语言文化专家,以塑造“东方他者”的形象[2]。由于欧洲长期以来培养和塑造了对东方的偏见,因而在西方人眼中,东方人一方面有着“懒惰”,“愚昧”的习性,另一方面东方本身有具有一种令人向往的神秘色彩。这两个层面在毛姆的OnaChineseScreen中都有十分具体的体现,毛姆笔下刻画的中国人是丑陋野蛮的,中国社会是贫穷落后的,中国文化是低级庸俗的。东方主义是西方试图制约东方而创造的一种政治教义,它作为西方人对东方的一种根深蒂固的认识体系,始终充当着欧美殖民主义意识形态的理论支柱。在OnaChineseScreen中,毛姆虽然对中国人民充满同情,但该著作在很大程度上是东方主义内涵的集中反映。但是,东方主义的概念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中并没有一成不变。19世纪,西方学者刻意将世界分为西方和东方。在东方主义中,西方和东方都是为西方霸权服务的,这意味着东方和西方之间存在着一种权力关系,支配关系,霸权关系[3]。为实现这一目的,西方学者提出了西方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霸权导致的二元对立观点。然而,随着现代性的推进,东西方依附的观念在今天逐渐淡化。在现代化、全球化、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推动下,中西关系越来越平等。当今的“新东方主义”的出现也跳脱出了经典意义上地缘政治的概念。正是如此,后期译本对中国形象的翻译也没有刻意强调或省去原文中有关东方的描写。
总之,OnaChineseScreen中充斥了大量具有东方主义色彩的段落,四部译文的译者在传达原作东方主义思想的深度上也不尽一致,东方主义的不断发展是翻译不同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四个译本中的中国形象
1919年至1920年冬季,毛姆来到中国,溯长江而上一千五百英里,OnaChineseScreen便是这次行程的产物。这部游记问世后的一百年间,OnaChineseScreen共有三部全译本和一部全文注释本问世。最早的译本《中国见闻杂记》即是胡仲持1943年的注释本,也是唯一一部非全译本。改革开放后毛姆作品的译介重新盛行,陈寿更在注释本的基础上翻译了原作,并把书名译为《在中国屏风上》。2000后,唐建清重译了这部游记作品,对前作中的翻译问题进行了修改。2018年,由盛世教学西方名著翻译委员会翻译的译本出版。唐建清和盛世译本在书名上都沿用了陈寿更的翻译——《在中国屏风上》。
陈寿更译本在译者的话中说到,“这个本子找了1943年胡仲持先生注释翻印本做了参考。”[4]唐建清译本在译后记中提到了陈译本,觉得该译本不甚理想,而他自己的译本多半也是一个背叛者[5]。由此可见,就毛姆在原作中对中国形象的建构而言,不同译者采取的翻译方式不尽相同,故处在不同时期的译本对原作中中国形象的重构也不同。下文则对四个汉译本的中国形象构建作出详细阐述。
(一)“屏风”后的中国形象
屏风作为一种的传统意象,在中国文化中有着重要的文化内涵。屏风一般起到遮挡和修饰作用。书名译作《在中国屏风上》,其内涵实则把毛姆眼中的中国图景绘在屏风画上。对于屏风画上描绘的中国形象,不同的译者有不同的解读方法。该节以胡仲持的译本为例。
OnaChineseScreen最早的译本《中国见闻杂记》是由著名翻译家胡仲持译著,于1943年出版于开明书店。这一译本是唯一一版非全译本,作为注释本,胡仲持在这一版译文中删除了原文中的七篇短文分别为“Dinner Parties”“The Glory Hole”“The Opium Den”“The Beast of Burden”“The Stripling”“Democracy”和“Metempsychosis”。被删除的文章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有辱中国形象的篇章,另一类用译者的话来说是毛姆给当时中国有的“可辱之处”做辩解的篇章。胡仲持在序言中说,他注释的这一版译本是供英语学习者使用的,健全的中国读者并不爱听外国作家对中国的缺点作辩解[5]。以“The Beast of Burden”和“The Opium Den”为例子,前者描写了生活在水深火热中,靠出卖体力为生的苦力形象;后者描绘了一幅“燕子窝”里留着长辫自我麻醉的吸毒者形象。胡仲持在他的翻译中采取直译的方法显然是不被读者接受的,因此译者编注该译本时未对这些段落进行翻译。
除被删去的七篇短文外,注释本中的其他篇章均只选取了毛姆原作中的部分段落和句子进行翻译,没有和原文一一对应。注释本除了减译之外,部分翻译还出现了误译、改编、省略等现象。
例1.注释:黎明是一幅中国乡村的晓景,作者的笔下不但传出了美丽是色调,而且透露了婉妙的诗意[6]。
译者用这一小段概括了原文“Dawn”的全篇内容,使用了改编的翻译方法,可传达的黎明景色却与原著描绘的大相径庭。原文中毛姆认为中国乡野的黎明如“幽灵”一般并在文中用了“I pass out, awaiting me, all ghostly, is the dawn”[7]来描绘黎明。在东方主义思想中,西方视中国是一个贫穷落后的野蛮国家,不仅是“荒蛮之地”还是“未开化”的代名词。可译者却用积极的笔触给读者描绘了一幅美好静谧的乡村图景,显然是与原文不符的。
胡仲持在这一译本中把真实的中国藏在屏风之后,故意删减了有关西方人对中国霸凌的段落,在翻译中也改变了毛姆的原意,刻意美化中国形象,从而建构出一幅古老繁盛的中国形象。
(二)“妖魔化”的中国形象
时隔41年,陈寿更翻译的《在中国屏风上》收录了胡译本删除的七篇文章,并作为第一部全译本于1984年在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不同于40年代,改革开放后各国文学作品如潮水般涌入中国,对毛姆的译介也从1949年之后的停滞阶段进入到了高潮期。不同于之前的注释本,陈寿更在翻译中体现出了原作中的东方主义色彩以及较为强烈的个人情感色彩。
例2.原文:"There are the raucous shouts of the coolies and chair-bearers; the menacing whines of the beggar, caricatures of humanity, their emaciated limbs barely covered by filthy tatters and revolting with disease."[7]
译文:“这里有苦力和轿夫们的沙哑的叫喊;乞丐的胁迫和哀诉,他们瘦弱裸露的四肢,覆盖着污秽的破布和生着令人厌恶的疾病,都是人性的讽刺漫画。”[4]
这一段描绘了山城重庆的街头风貌,码头旁的街头巷尾充斥着衣衫褴褛的苦力和乞丐。在这一篇开头有一段重庆环境的描写"It is a grey and gloomy city, shrouded in mist."[7]原文中毛姆营造了一幅灰暗阴郁的城市风貌,之后也着重强调了中国下层百姓的穷苦生活,毛姆笔下对中国的描写符合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形象,是西方意识形态下的东方。在例2中译者把“revolting with disease”译成了“生着令人厌恶的疾病”。为了迎合原作者设定的基调,译者这里增译了“令人厌恶”,既表达了毛姆对乞丐的厌恶也体现了中国社会环境的恶劣,译者采用这样的翻译方法迎合了毛姆作为一个东方主义者对中国的看法。最后译者又增译了“都是人性的讽刺漫画”,在毛姆对中国描写的基础上,作者在文末概括出了这句话,使译作继续朝着西方贬损中国形象的方向发展,忠实且强化了原作者在文中表达的东方主义色彩,加剧中国形象“妖魔化”。
例3.原文:"You wondered if he thought that down this pass in days gone by his ancestors had ridden, ridden down upon the fertile plain of China where cities lay ready to their looting."[7]
译文:“在过去的岁月里,他的祖先沿着这条道路奔驰而下,驰入中原大地的平原沃野,那里坐落着无数富饶美丽的城市,供他们掠夺。”[4]
毛姆在当地看到一位骄傲的蒙古土司带着川流不息的商队入关经商的场景,他不禁想到在过去的岁月中,周边的部落必定也是沿着这片不毛之地来到中原大地进行掠夺的景象。“fertile plain of China”译成“中原大地的平原沃野”。这里的“fertile plain of China”指代的并不是中国的平原地区,而是把整个中国比作为一片沃土。这一段是蒙古商队入北京城门的场景,译者用“中原大地的平原沃野”来形容北京确实有一定的夸大成分。自马可·波罗来华传教后,西方普遍认为中国是一片富饶的土地,陈寿庚在这一段中把“ready to their looting”译成“供他们掠夺”,“looting”表达读者了对弱国的不屑一顾,而译成“掠夺”也展现了大国的悲哀,译文影射出了当今中国的破败苍凉。从原文来看,这几个短语均体现了毛姆的东方主义思想,极大程度上吹嘘了中国的实际情况,把中国描绘成可随时被掠夺的“宝藏国”,并且在翻译中,陈寿更也毫不掩饰的继续放大了原作中的中国形象。
(三)“解殖民化”的中国形象
OnaChineseScreen的第三部译本由唐建清翻译并于2006年在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这一版整体采用了较为保守隐晦的翻译风格。例4.原文:"In China it is man that is the beast of burden."[7]
译文:“在中国,驮负重担的不是牲畜,而是活生生的人啊!”[5]
唐译本处理这句话时用了感叹的语气,用了三个短句来加强语气,并与原句的强调句式相呼应,表现了苦力的沉重劳役。同时用“活生生”来形容人而不是用“牲畜”或“驮兽”,更加体现了译者的个人情感,即对底层百姓命运的呐喊。另外两个译本则直接把苦力比作牲畜,没有对苦力形象做辩护。
例5.原文:"I hate the country, I hate the people," he said. "As soon as I’ve saved enough money I mean to clear out."[7]
译文:“我不喜欢这个国家,我也不喜欢这里的人。一旦挣够了钱我就离开。”[5]
唐译本把“hate”译成了“不喜欢”;陈译本译成了“恨”;盛世译本译成了“讨厌”。虽然这三种译法都可以表达“hate”的含义,可传达的语气却大不相同。唐译的“不喜欢”的语气最不强烈。同时唐译本把“clear out”翻译成“离开”,而陈译用了“远走高飞”。相对于后者来说,“离开”则表达的较为委婉。毛姆在原作中借助一位在中国滥用权力的洋行老板的话语,反映出他本人对中国的憎恶。唐译本明显在原作强烈东方主义色彩的基础上进行了弱化,重塑了解殖民倾向的东方形象。
(四)“去屏风”后的中国形象
时隔十二年后,最新的一版译本《在中国屏风上》于2018年由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出版,由盛世教育西方名著翻译委员会翻译。盛世译本在文中关于中国形象的翻译中较为忠实的再现了原文特点。
针对例2原文,盛世委员会则译为“街上是苦力们和轿夫们嘶哑的吼声,还有乞丐们哀声连连的乞讨声,他们穿着破破烂烂的脏衣服,四肢残疾,受到疾病的折磨。”[7]盛世译本把“revolting with disease”译成了“受到疾病的折磨”。相比于陈寿更的翻译,盛世译本没有在原文基础上做过多的阐释,仅表达出街头病痛缠身的乞丐形象。后半句盛世译本用了“破破烂烂”,“四肢残疾”来刻画街头乞丐形象。而陈译本用了“瘦弱裸露”,“污秽的”和“令人厌恶的”来形容,尤其是“令人厌恶”一词包含着强烈的个人色彩,故盛世译本的翻译相较于陈译本来说能够更公正客观的展现原作中的形象。
例6.原文:“When he first came to Shanghai he refused to use the jinrickshaw. Presently he always thought of the boy between the shafts as a man and a brother.
“Don’t you think we wight leave it till after luncheon” I said. “Those fellows are sweating like pigs."[7]
译文:他第一次来到上海时,他拒绝使用黄包车。他现在常坐黄包车,不过他总是把拉车的劳力看成是一个平等的人,一个兄弟。
“午饭过后我们再去不行吗:”我说,“拉车的家伙汗滴得跟雨淋了似的。”[8]
这一部分摘自第七篇游记。它描写了英国人亨德森从一开始对车夫礼貌相待到后来对中国车夫拳脚相向的转变。这些转变都表达了他对中国的极大的不尊重。盛世译本把“the boy between the shafts as a man and a brother”翻译为“他把拉车的劳力看成是一个平等的人,一个兄弟”。“劳力”一词已经有了偏颇的含义。其他两个译本用“两根车杠中间的人”来形容车夫,这种翻译仅客观地描绘了一个人力车夫的模样,但缺乏对人力车夫社会身份的评价。
此外,盛世译本把“Those fellows are sweating like pigs”翻译成了“汗滴得像雨淋了(刚从水里捞起来)似的”。陈译本则翻译成“那两个家伙汗得象猪一样了”。“sweating like pigs”是英语习语,意为一个人在剧烈运动后汗流浃背。虽然原文使用了比喻,但盛世翻译委员会避免使用“猪”来指代人力车夫,也较为准确的转述了原文的含义,较为“中性”的描写了人力车夫的形象。
比较盛世译本的翻译,我们不难看出,起初以亨德森为代表的西方人对中国的态度心存敬畏,但在东方主义的影响下,中国作为一个东方形象深深地印在了他们的脑海中。亨德森对中国态度的转变反映了中国社会的衰落,而盛世的翻译可以准确地表达出这些态度的转变。作为四个译本中最具忠实性的译本,盛世译本没有明显的删除或误译部分,相较于其他译本较好地达到了忠实的翻译效果。
三、不同形象变化的原因
前文分析了OnaChineseScreen四个译本中中国形象的特点,从上文得知,不同时期的译本中对同一中国形象的相关描写也有很大不同。究其原因,不难发现这四部译本出版时间间隔较大,从二十世纪40年代到2018年这近80年里,中国的翻译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译者风格对形象的不同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除此之外,随着中西方关系的变化,中西方综合实力差距缩小,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传统东方主义的发展也受到了影响,在新的时期东方主义新的表现形式也间接影响了译者对译本中中国形象的塑造。最后,当今译本的读者受众早已不同于40年代译本的受众,后期译本的译者可以不用太过顾虑中国读者是否能够接受当初没落的古国形象。
(一)中国翻译环境和读者接受度的变化
1976年后,在宽松的文化政策下,大量外国作品的引进使得翻译业开始复苏。此外,毛姆的翻译浪潮在停滞了几十年后再次兴起[9]。与20世纪40年代的胡译本相比,70年代后的三部译本逐渐向原文靠拢。在这四个译本中,胡、唐在翻译中体现出了很强的主观性,弱化甚至消除了敏感词语中的文化歧视内容,用胡仲持的话说,他的译本消除了令国内读者感到不快的内容。在第三篇游记中,胡仲持把“蒙古土司”这一章节注释为“The Mongol Chief”是作者在路上所见的一个蒙古王公的美妙的写照[6]”。前文例3中提到,陈寿更对该章的描述呈现出一个肆意掠夺中国宝物的土司形象,这与胡仲持的注释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译者在前言中提过,之所以删减部分译本是因为当时的中国读者不愿意看到这样一部充斥着中国负面形象描写的作品。近代以来,中国一直受到西方列强的欺凌,这严重挫伤了中国人的文化自信,严重阻碍了中国文化的发展和传播。最早的胡译本出版于新中国成立前,其中的7个注释版本被删除。除了删除篇章,在其他部分的翻译中故意突出了中国的繁荣与和平,与毛姆的初衷背道而驰,在一定程度上照顾了当下中国读者的接受能力。从建国之初到改革开放,再到形成负责任的中国形象,中国的国际地位大幅提升,中华文化逐渐走进世界视野。后来的翻译不仅恢复了删除的原文,还出现了全译本。此外,译者并没有刻意美化中国,而是更忠实地翻译了原作,真实再现了20世纪初的外国人眼中的中国图景。从1987年的第一个全译本开始,陈寿庚就试图从原文所描述的翻译的不同方面来展现真实的中国。然而,他的观点在某种意义上是极端的。但在之后唐建清的全译本中,这一现象得到很大的改善。2018年,盛世西方名著翻译教育委员会在很大程度上展示了在西方想象中中国形象的真实写照。自文学和翻译环境以及社会意识形态转变以来,中国读者不再对原文中的原始形象感到厌恶,现在的中国年轻读者也愿意回顾过去,了解现实;相较于从前,中国读者对具有东方情调的异域形象的描述接受度更高,心态也更为包容。
(二)不同译者对待东方主义的态度变化
东方主义处于不断演化的过程,尽管东方主义的核心内涵并没有发生变化,但是在不同时代发挥的作用却有所差异。新东方主义受制于时代环境的影响而不断变化,处于不同时期的译者对待原作东方主义的态度也不尽相同。尽管这两种类型都把东方和东方形象作为研究对象,但东方主义关注的是东方各民族和东方文化的过去,他们将东方国家最辉煌的时期严格假设为特定的历史时期,东方的衰落就成为一种自然的不可避免的现象。毛姆作为东方学家在其游记OnaChineseScreen中书写东方人,东方学家和东方人是一种书写和被书写的关系[10],二者之间本质上是一种权力关系。因此,在最早的陈译本中,译者开篇一定程度上夸大了中国的繁华和辉煌,营造一种理想的乌托邦社会。在例3中陈寿庚用了“平原沃野”和“富饶美丽”来形容中国城市。当毛姆对中国的态度转为消极的描述时,译者则使用具有讽刺意味的词语和语气来放大中国的衰落景象,甚至偏离了原文的本意,如例2中陈寿更用“灰暗阴郁”来形容重庆,用“令人厌恶”和“衣衫褴褛”来形容中国人。这种鲜明的对比使陈的翻译成为一个带有强烈东方主义基调的译本,陈寿更把原作中体现的东方主义思想毫无遮掩地再现给读者。
21世纪,现代性观念的普及逐渐影响了东方主义的发展。现代性试图将非西方文化纳入东方主义观念,在这一时期,现代性的入侵打破了东方主义的节奏[10]。现代性成为东方主义的延伸,是东方主义的延续,也是对西方意识危机的回应。东方主义在新世纪的表现及其对西方的抗争使翻译文学产生积极的变化。OnaChineseScreen中塑造的中国形象在陈寿庚的翻译中产生了偏离,中国社会和中国人甚至被妖魔化。但唐建清在充满东方主义色彩的中国形象的塑造中却体现出了解殖民化的思想。在例4中唐建清把“it is man that is the beast of burden”译成“驮负重担的不是牲畜,而是活生生的人”,在另外两部全译本中,陈寿更把该词译成了“人就有着这种人所不堪的重负”,盛世译本译成了“中国人成了驮兽”。唐建清的翻译中淡化了“beast”作为“兽”的概念,用“活生生”来形容人,违背了毛姆本身要传达的中国苦力的困苦处境,是对原作中国形象的解殖民化转述。因此,他的解殖民翻译倾向也影响了他对东方形象塑造的态度。
东方主义在发展中不断变化,它在表达过程中也建构了不同的知识和信息。如果东方主义是知识和权力直接因果关系的自觉活动,那么它很容易被抵制和被驱逐。如果译者完全在译文中体现原作的东方主义,也会受到读者的抗拒,这也是之后的译者在翻译具有东方主义色彩的中国形象时逐渐出现解殖民化特点的原因。只有把握当代东方主义在西方自我认知中的无意识、内在性和普遍多样性的特点,东方主义在作品翻译中才能得到延续和发展。
四、结论
毛姆在OnaChineseScreen一书中描绘了一幅幅丰富多彩的中国画面,涵盖了外国官员和领事的状态,也涵盖了中国农民和苦力的生活,这些人物的活动点缀着毛姆眼中的中国图景。该游记的主题和内容在翻译中涉及到了中国形象的认同和建构问题。游记的开篇部分充满了毛姆对中国的向往和钦佩。毛姆曾两次前往远东和南太平洋岛屿,他多次提到来华的目的是追求中国以往的辉煌。但是在东方主义语境下,游记在后半部分对中国的描写中充斥着毛姆太多的傲慢。通过译者的翻译,中国读者也看出了屏风后所彰显出的西方文化的优越感。东方主义者对中国形象的看法一旦形成,不仅会影响西方眼中的中国形象,也会影响中国人对自我的认识。
OnaChineseScreen从第一部注释本问世到最后一部译本的出版前后经历了近一百年的时间。四个译者也从其所处的时代背景出发对文中近代中国形象的建构和翻译做出了自己的努力。由于受不同语境下中西关系,社会现状以及西方文化的影响,最早期的译本中,译者对书中中国的负面形象进行了美化和改编,而在后期的翻译中则能够客观忠实地进行再现。不同译本中,译者使用不同的翻译技巧来构建中国意象,从而使得译文中的中国形象与原作相比发生变异。译文中的这些意象被偏离、弱化和渲染,导致译文与原文中的中国形象产生分歧。研究表明,译者对待东方主义的态度以及读者接受程度和翻译环境的变化对中国形象在不同译本中的变迁均产生了影响。
透过中国形象在译本中的世纪变迁,透过四个译者对毛姆作品中的东方主义思想的传达,透过译者对中国形象的翻译措辞选择,有助于读者深入理解中西方文化冲突的深层原因。同时,译者在新时期对近代中国形象的准确传达也代表目的语读者国家自豪感和民族自信心的不断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