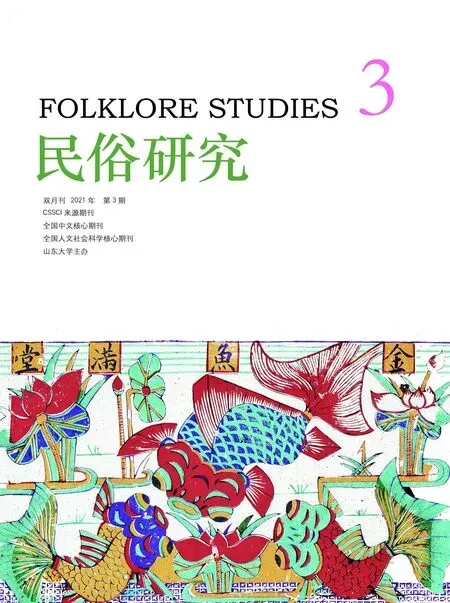权威话语与社会分化条件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社区参与
——以耍歌堂的保护过程为例
2021-11-25陈岱娜
陈岱娜
一、东寨“耍歌堂”引发的冲突
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保护已经走过了二十多年的历史。由于政府与民间社会的大力推动,非遗一词已是家喻户晓。非遗在与民众生活的联系越发紧密的同时,引发的争议也越来越多。在笔者近年长期从事田野调查的南方某省的瑶族社会中,亦不乏这样的案例。例如,2017年12月3日(农历十月十六日),地处山区的东寨迎来了一场非遗展演活动——“原生态”耍歌堂。东寨是一个行政村,包括老排、横青村、大景村、小村、大坑村、大风村、水景村和东星村8个自然村。老排是指位于山上的瑶寨,其他自然村因移民搬迁而形成,被统称为新村。此次耍歌堂活动的仪式中心设立在东寨村委会旧址处的一个空置小屋中。出歌堂的队伍从此出发,围绕大风村的水田行走,最后在离新村村口不远处的田埂上举行表演。此次活动由县政府提供资金,在村委会的组织下,共有近百位瑶族民众参与其中,吸引了数百名游客到场观看。活动结束后,众多游客聚集在村口的停车场等待离去。停车场的一角,村民李达正守着他面包车里的盒饭,见笔者走过,气急败坏地说:“哎,你来看看!我从县城拉了100个盒饭。就卖出不到10个!他们个个都不买!”此时,村口突然冲出一个醉汉李星。他用汽车将全村唯一的进村通道堵住,且一直在现场大喊大叫,口中提到“大家的东寨”“发展属于大家”之类的词句。突然发生的拦车风波导致大批本文曾在2020年11月举行的北京大学社会学第七届博士生论坛暨余天休执教百周年纪念会议上宣读,感谢林叶、邱泽奇、谭同学、童莹等老师提出的建设性意见,以及匿名评审人给予的修改意见。所引材料来源于笔者的田野笔记,时间:2017年12月3日,地点:东寨大风村停车场。基于学术伦理考虑,本文所涉及的县级以下的地名和人名皆为化名。
游客无法离开。目睹此幕的李达情绪更加高涨,激动地嚷道:“要不是我现在腿坏了,我立马冲上去抓个人就打!那些导游,带人来白白看表演,看了就走,什么都不留下!有这个道理吗?你看明年,我就叫一辆货车把石头倒在路上,谁都不要进来!”
一场闹剧最终在村中保安队的介入后逐渐平息,但是冲突背后反映的因耍歌堂产生的村民与游客、村民与地方精英的矛盾则难以轻易解决。2017年,在东寨数场与耍歌堂相关的活动中都出现了村民以拦车的方式公开表达诉求的情况。耍歌堂,瑶语称[ai41ko44tong53]或[tam53ko44tong53],是由全寨村民相约举行,汇聚人心的重要集体活动,也是瑶族文化的核心。耍歌堂是一个集合了祭祀祖先、娱神娱人的歌、声、舞、乐的大型民俗活动,其流程包括告祖公、出歌堂、游神、祭祀法真、追打黑面鬼、乐歌堂和退公等。传统时期,每隔三至五年,以村寨为单位举办一次耍歌堂。2006年,耍歌堂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在当地政府的财政支持与宣传推广,以及地方精英的牵头组织下,耍歌堂在停办多年后重新恢复了生机与活力,举办的频率增加至一年一次。同时,地方精英也借由耍歌堂的模式举办文化旅游演出。每年的耍歌堂有数百村民共同欢庆,各地游客奔赴观看。从表面上看,社区中不同阶层的村民皆有参与耍歌堂的保护,保护成果卓有成效。但是,从活动中频发的冲突可见,村民对耍歌堂的理解与认识存在分歧。普通村民没有正常的渠道表达自己的诉求,只能通过公开地打破公共秩序的方式获取关注。为何看似积极的社区却难以看见“社区参与”的成效?由此,笔者试图追问:社区是什么?社区如何得以有效地参与到非遗保护之中?为回答上述问题,笔者以东寨耍歌堂中出现的冲突事件为线索,通过访谈村中与耍歌堂非遗保护相关的村民,理解地方精英与普通村民对耍歌堂的不同认识与态度,分析耍歌堂保护的社区参与为何陷入困境之中。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非遗保护工作系统中,社区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关键词。《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以下简称《公约》)及由此衍生的相关文件,从非遗的概念、认定的标准、到非遗项目的申报过程,皆有详细的条款指出非遗项目与所在社区密不可分的关系,并强调“社区最大程度参与”的原则。(1)关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保护政策中关于社区参与的条文分析可参见杨利慧:《以社区为中心——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保护政策中社区的地位及其界定》,《西北民族研究》2016年第4期;周超:《社区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法保护的基本理念》,《河南社会科学》2011年第2期。这是因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已意识到若是依靠自上而下的国家干预仅可能取得短暂的效果,而非遗所属社区主体的参与会更具持久性,因此需要警惕对国家的过度依赖。《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填写备忘录》中明确提到社区应尽可能广泛地参与非遗保护。(2)UNESCO, Aide-Mémoire for Completing a Nomination to The Representative List of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of Humanity, For 2016 and Later Nominations. No.28.然而,劳拉简·史密斯(Laurajane Smith)指出《公约》本身并没有提供一个关于社群或次国家群体非遗的优先权框架。(3)Laurajane Smith, “Intangible Heritage: A Challenge to the Authorised Heritage Discourse?”, Revista d’Etnologia de Catalunya, vol.40, no.1(June 2015), pp.133-142.国家或是精英主导的权威化遗产话语(authorized heritage discourse)在非遗保护中仍占据主导地位(4)Laurajane Smith, The Uses of Heritag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6, pp.13-42.,导致遗产实践中主体性的缺失(5)刘朝晖:《“被再造的”中国大运河:遗产话语背景下的地方历史、文化符号与国家权力》,《文化遗产》2016年第6期;Marilena Alivizatou, “The Paradoxes of Intangible Heritage.” in Michelle L. Stefano, Peter Davis and Gerard Corsane, (eds.), Safeguarding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Woodbridge, Suffolk: Boyell Press, 2012, pp.9-21.,并且人们在实际的工作中常遭遇主体是谁的困境。(6)张多:《社区参与、社区缺位还是社区主义?——哈尼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主体困境》,《西北民族研究》2018年第2期。在实践中,社区遗产成为一个自上而下的行动以及一种进行控制和确定权威的工具。(7)Elizabeth Crooke, “The Politics of Community Heritage: Motivations, Authority and Control”,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ritage Study, vol.16, no.1-2(January-March 2010), pp.16-29.在权威化遗产话语与社区的讨论中,大多数的研究集中在分析国家或是机构与社区中精英的关系(8)参见唐璐璐:《社区与权威遗产话语的角力:对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批判性思考》,《民族艺术》2020年第5期;杨利慧:《社区驱动的非遗开发与乡村振兴:一个北京近郊城市化乡村的发展之路》,《民俗研究》2020年第1期。,或强调非遗保护融入乡村社区发展的重要性。(9)张士闪:《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当代乡村社区发展——以鲁中地区“惠民泥塑”“昌邑烧大牛”为实例》,《思想战线》2017年第1期。然而,中国的国情决定了非遗保护是以国家为主导的保护,目前已设立了“国家—省—市—县”的四级保护系统以及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保护制度。在自上而下地执行非遗保护政策的过程中,政府主导的保护所带来的资源流入可能挑起或者扩大社区内部的分化,但目前学界较少讨论这种分化对社区参与的影响,也较少反思社区自身的变迁而仅将社区视为同质性的存在。在“社区参与”一词中,争议主要集中在社区的概念及内涵上。虽然社区的定义繁多,但大多数的定义都认可其应具有两层含义:一是利益或者兴趣的共同体;二是基于某个地域空间的社会群体。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在《社区与社会》一书中,将“社区/社会”作为二分的对立关系而提出:“共同体本身应该被理解为一种生机勃勃的有机体,而社会应该被理解为一种机械的聚合和人工制品”(10)[德]斐迪南·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纯粹社会学的基本概念》,林荣远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45页。。这种基于对比关系的阐释方式,让社区一词逐渐成为一个固定的参照系。社区概念带有隐喻,且相对静止的意涵,导致时下的非遗保护可能出现一种“想当然”的理解,认为社区是均质化的、一成不变的共同体,从而忽视了非遗传承主体内部的复杂关系,以及社区的认同与边界在情境中的变动。有学者认为在中国“社区参与”只是当地政府推进项目的面纱,民众并不能真正地参与到政府的决策中,由此判定社区参与未能达到成效。(11)William Nitzky, “Mediating Heritage Preservation and Rural Development: Ecomuseum Development in China”, Urban Anthropology and Studies of Cultural Systems and World Economic Development, vol.41. No.2/3/4 (Summer, Fall, Winter 2012), pp.367-417.本文的重点不在于讨论政府与社区的关系,而是将目光聚焦在常被视为一体化的社区之中,以耍歌堂冲突为切入口,分析东寨社区作为地域性的利益共同体的转变,讨论社区参与何以可能的问题。
二、作为族群文化的非遗遭遇商品消费
2006年以来,耍歌堂从一个地方文化活动转变为非遗项目,被赋予了外在的文化政治意义,成为具有公共性的非遗。(12)刘晓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地方性与公共性》,《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作为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的耍歌堂不仅是瑶族文化的代表,也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代表,因此,它不再局限于地域社会内部的共享,而是对外面向不同族群的观众开放。在消费文化的影响下,诸如李达等村民认为耍歌堂的对外开放应是有价的。在耍歌堂冲突中大发牢骚的李达长年在外务工。2017年10月,他因腿伤而回村休养了两个多星期,断了收入。此次,他拿出积蓄购买盒饭,希望赚一笔钱来弥补误工的损失,但事与愿违。在地方政府的资助下,观看耍歌堂活动的游客无需购买任何门票。在李达看来,游客没买门票,又不在村里消费,属于“白看”,游客们没有为自己的观看行为付出任何代价。这种认识的产生是基于耍歌堂是一个对外的服务,且它的价值是由其作为商品在交易环境中所产生的交换价值来衡量。(13)Arjun Appadurai, The Social life of Things: Commodities in Cultural Perspective.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3.李达的愤怒出于他认可了耍歌堂商品化的逻辑,是一种市场经济下理性思维的表现。冲突中的醉汉李星是村中的一名货车司机,他在争吵中提及的东寨发展归属问题指向的是村落精英。他认为,举办耍歌堂活动只有少部分的精英受益,而普通村民没有受益。这种思考方式指向了一个问题,即时下村民参加耍歌堂是为了谁?曾经参加过1953年耍歌堂的李古信婆的一句话或许可作为答案:“现在不是瑶民的耍歌堂!是政府出钱,给你们汉人看的!”(14)访谈对象:李古信婆;访谈人:陈岱娜;访谈时间:2018年1月11日;访谈地点:东寨老排。在村民眼中,时下耍歌堂的内在价值被剥离,成为一场对外的具有商业价值的演出。这与传统时期耍歌堂是为了祭祀祖先与自我娱乐的目的已相去甚远。
“耍歌堂变味了”的判断几乎成为东寨人的共识。但是,如何应对这个问题,不同的行动者的认识差异甚大。东寨的文化精英李信宁认为耍歌堂出现的种种争议源于瑶族人外出务工后被“教坏”了的结果。他十分反感部分村民事事以钱衡量的做法,认为需要找回“传统”的耍歌堂,重拾瑶族文化的根,以对抗外来文化的侵袭。非遗保护正是时下最好的契机。李信宁不止一次与我表达他对时下耍歌堂的不满与忧心:“现在就是不对嘛,政府出钱,你拿钱去跳舞,给100块,跳一场两个小时。这不是自己的东西,我希望我们有自己真的想去做的东西。瑶族的年轻人忘记了自己的传统,不知道根在哪里了!”(15)访谈对象:李信宁;访谈人:陈岱娜;访谈时间:2018年1月21日;访谈地点:东寨大风村。李信宁将传统的耍歌堂视为本族群重要的社会记忆,强调其与瑶族身份认同之间的联系。作为局中人,他深知举办传统耍歌堂的难度。为此,他拜访村中的长者,了解和记录传统耍歌堂的具体过程。这些积极的行为与李信宁的身份相关,他的至亲是耍歌堂的传承人,一直希望复办传统的耍歌堂,但不幸于2016年病逝。李信宁的倡议既是对至亲遗愿的回应,同时也是他多年来对编导、参演瑶族歌舞的感悟。他认为耍歌堂的舞台化演出只是权宜之计,必须得遵循传统的方式才是真正的非遗保护。
虽然李信宁积极地争取复兴一个传统的耍歌堂,但是东寨不同年龄与阶层的村民对此的反应不一。大部分村中的长者支持李信宁的倡议,与此同时,他们也表达了自己的忧虑。先生公(16)先生公:排瑶中从事宗教活动的男性。李达华说:“我当然很高兴了!可是难啊!先生公好多不会念以前的经了,我也没真正地学过。会唱(历史歌)的老人好多都走了。”(17)访谈对象:李达华;访谈人:陈岱娜;访谈时间:2018年6月22日;访谈地点:东寨大景村。1940年出生的李太帕婆说:“那肯定是好!不过以前是‘甲头’来收钱。现在都没了,大庙也没了。怎么办?”(18)访谈对象:李太帕婆;访谈人:陈岱娜;访谈时间:2018年6月22日;访谈地点:东寨大景村。“甲头”,是瑶族传统的社会组织瑶老制中头目公的助手。一直都活跃在东寨歌舞队且早在1978年就提出复办传统耍歌堂的李佳恭说起此事时也摇摇头说:“没那么容易!零五年时就有说要弄,当时村里已经组织不起来,何况现在?这可不像集体时期,大队一个通知,各个生产队都要响应,积极性很高。”(19)访谈对象:李佳恭;访谈人:陈岱娜;访谈时间:2018年6月19日;访谈地点:东寨水景村。
李达华从物质文化的角度指出,在技术上难以实现复办耍歌堂。在传统的耍歌堂斗歌环节中,长者会通过瑶歌教导年轻人农业劳作知识及讲述祖先迁徙故事,同时,年轻人通过瑶歌跟意中人倾述情意。当下大部分年轻人已外出务工,即使有的留在村中从事农业劳作,也可从多种渠道获取相关知识;谈情说爱也不再借助瑶歌传情。换言之,耍歌堂的教育功能已经消失。李太帕婆和李佳恭是从社会组织层面分析耍歌堂难以再恢复的原因,“甲头”和“生产队”都代表特定的社会情境中组织村民的方式,然而时下的东寨缺乏影响广泛的民间自组织力量支撑举办传统的耍歌堂。
与长者们虽忧虑但赞成的态度相比,李信宁的说法在东寨的中青年群体中却引起了很大的争议。村中的文艺爱好者李芯妮听到这个消息时,反问笔者:“耍歌堂不是每年都有吗?他(李信宁)是不是想成为传承人?要搞也好,可谁出钱呢?”(20)访谈对象:李芯妮;访谈人:陈岱娜;访谈时间:2018年1月21日;访谈地点:东寨大风村。大学生李宁也表达了自己的忧虑,她担心有些文化精英并没有足够的公信力带领群众。确实,在我的走访中,大部分人表示不愿意为了李信宁而去参与复兴耍歌堂。对此,李信宁觉得很无奈:“你知道现在有些人就是心不好,说搞耍歌堂是为了我搞的,什么叫为了我搞的?这是为了东寨,为了大家能够记住历史,能够团结在一起。以前即便大家是非常的穷,也是要办仪式。现在大家生活好了,有一点钱了,反而想着怎么能赚更多的钱,文化都忘记了!”(21)访谈对象:李信宁;访谈人:陈岱娜;访谈时间:2018年1月22日;访谈地点:东寨大风村。
上述争论的一个点是李信宁与传承人身份的关系。近年来,李信宁在积极申请耍歌堂传承人的称号。因此,当他作为牵头人提出“复办传统耍歌堂的建议”时,部分村民认为他是为了传承人的称号,并不是为了东寨。传承人制度在社区中引发的争议与权威化遗产话语相关。非遗传承人是由官方认定的掌握该文化的权威人士。传承人对所属项目的认识和理解经过官方与学者的文字记录,成为非遗申请文书的一部分,也常成为非遗相关报道、书籍的重要资料来源。种种相关的表述成了合法性的文本,强化了传承人的权威地位。布迪厄曾言:“任何特定的文化能力……,都会从它在文化资本的分布中所占据的地位,获得一种‘物以稀为贵’的价值,并为其拥有者带来明显的利润。”(22)[法]布尔迪厄:《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布尔迪厄访谈录》,包亚明译,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96页。非遗所蕴含的价值是一种文化资本或资源。(23)Janet Blake, “UNESCO’s 2003 Convention on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The Implications of Community Involvement in ‘Safeguarding’”, in Laurajane Smith and Natsuko Akagawa (eds.), Intangible Heritage. London: Routledge, 2009, pp.45-73.在个人层面,非遗不仅关乎文化与政治,其所产生的经济效益也十分重要。(24)G. J. Ashworth, “Heritag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Selling the Unsellable”, Heritage & Society. vol.7, no.1 (May 2014), pp.3-17.这促使民间文化精英各展其能,力图成为传承人。已有研究指出,能否获得传承人的称号是多方力量博弈的结果。(25)刘晓春:《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若干理论与实践问题》,《思想战线》2012年第6期。尤其是提名过程中,个人与非遗专家和官员要有良好关系。代表性传承人的制度导致非遗的利益相关者之间出现了分化和等级化。(26)Christina Maags, “Creating a Race to the Top: Hierarchies and Competition within the Chinese Transmitters System”, in Christina Maags and Marina Svensson (eds.), Chinese Heritage in the Making: Experiences, Negotiations and Contestations. Amsterdam: 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 2018, pp.121-144.对于诸如耍歌堂这种集体性项目而言,权威并不一定局限于一人,不同阶层、身份、性别的村民对耍歌堂的认识也不一致。此外,耍歌堂办得越好,则可能归功于传承人组织得好或者有利于组织者申请传承人称号。因此,传承人身份的设置反而在集体项目中容易引发争议与矛盾。因此,当传承人想要带动社区参与时,难以摆脱他人对其个人利益的质疑。
此外,在我国的非遗保护体系下,国家给予传承人一定的补贴,助其开展传承活动。但是,一个人的补贴对于整个大型节日活动而言是杯水车薪,却极易引起传承人与参与村民之间的嫌隙。耍歌堂作为集体项目需要广大群众的参与,但只有少部分人从非遗保护体系中受益。如在东寨当地,国家级传承人每年可从国家与省的文化部门分别获得两万和一万的补贴(27)国家级、省级、市级、县级传承人除享有国家规定的补贴外,各地传承人的补贴情况因地而异,差异较大。,而且传承人在参与各种文化活动时可积累声望,也常获得外界的赞赏。少部分耍歌堂的核心成员如先生公、长鼓舞的鼓手等可获得每次出场100元至200元的补贴,余下的普通村民可能只有10元至50元的补贴。声名与利益都集中在少部分人身上的情况造成其他的村民越发没有兴趣去思考如何改进耍歌堂,而是满足于当下简单地打长鼓,或者走一下流程,就可以领取补贴的参与方式。村中的精英认为村民这种状态是一心“向钱看齐”且“不思进取”。这种精英与村民各行其是的分化状态在某些场合中容易转化为明面上的冲突。精英是一个与社会分层相关的概念,可以根据个人所控制的资源及其对地方社会的支配能力来判断。李信宁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多次带领东寨歌舞队外出表演,掌握了一定的文化资源,可以被称为精英。但是,精英并不一定是民间权威。(28)关于地方精英与民间权威的区分,可参见李晓斐:《当代乡贤:地方精英抑或民间权威》,《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4期。民间权威可以借助其威信聚合群众的力量于同一件事上。这便要求权威人物的所言所行符合村民们的期待,从而得到大众的认可。耍歌堂成了非遗项目,社区资源再分配引发的分化导致与之相关的精英备受争议。部分精英失去威信,难以成为民间权威。然而,更为重要的是文化价值的转变促使保护一个传统耍歌堂的号召和行动已不是大部分村民们的期待。因此,讨论非遗的社区参与需要回溯耍歌堂的转变,以及东寨社区几十年来的社会变迁。下文从时间的维度分析东寨作为一个“社区”共同体的变迁过程,从而探讨社区参与何以可能的问题。
三、非遗的认同、人地关系与地域信仰的转变
2006年,亚太文化中心组织(ACCU)在日本东京召开以“非遗保护中的社区参与:迈向2003公约的执行”为主题的会议。与会专家对“社区”的定义达成了一个共识:“社区是指那些根植于与他们的非遗实践、传承与所参与的共享历史关系中生产而出的认同感和联系的人们组成的社会关系网络。”(29)ACCU. Expert Meeting on Community Involvement in Safeguarding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Towards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2003 Convention. https://ich.unesco.org/doc/src/00034-EN.pdf.访问时间:2020年10月23日。将社区视为共享认同的社会关系网络或是人群集合的定义有利于规避社区主义带来的某个地方对区域性共享文化的垄断,这点得到了学者的认可。(30)Marc Jacobs, “Participation of Communities, Groups and Individuals - CGIs, not just the Community”, In Janet Blake and Lucas Lixinski (eds.), The 2003 UNESCO Intangible Heritage Convention: A Commenta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0, pp.273-289.此定义强调社区的基础是认同感和联系,但未指出社区定义中地域空间概念的重要性。从中文的语境出发,“社区”一词具有强烈的地域性色彩。中文“社区”一词中的“社”,本是祭祀土地的意思,与土地有密切的关系。(31)彭兆荣、张进:《“社区”的维度与限度》,《思想战线》2019年第1期。对于民俗类的非遗项目而言,地域性并不仅是一个地理空间概念,更涉及地域社会中的地理环境、人与文化的联结。这种关联是社会的、历史的创造,并且需要加以解释。(32)Akhil Gupta and James Ferguson, “Culture, Power, Place: Ethnography at the End of an Era”, In Akhil Gupta and James Ferguson (eds.), Culture, Power, Place, Explorations in Crutical Anthropology. Durham, N. C.: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1-30.
谈及瑶族,人们总会提及一句俗话:“无山不成瑶。”茂密的山林既是天然的屏障,也是传统时期瑶民获取资源的重要来源。东寨老排四面环山,居中轴高处,被密林所覆盖。密林中大多是自然生长的杂木林,有杉树、枫树和果树等。传统时期,瑶民在山中砍伐得到的树木一般用于建房子、做棺材、制作长鼓等,极少用于买卖。普通人家在春分与秋分之前将杉树皮剥下,用树皮盖屋顶。东寨大庙的屋顶由一尺见方的茅草块相交叠合而成,柱子为杉树,杉树头朝上,树尾向下,不砍尾,留树枝,成人字形。瑶民崇拜古树,进山砍树需要在树下压纸钱,或者烧香祭拜树林,不可讲砍树,否则可能会因为得罪树魂而被压伤或者压死。(33)许文清:《粤北排瑶的宗教观念》,广东省民族宗教研究院、中山大学人类学系等编:《排瑶研究论文选集》,广东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79-287页。1950年代,政府大量收购东寨所处地区的杉木,由此自然生长的杉树数量开始减少,同时人工植林的面积逐步上升。瑶民与山林的关系开始有所转变。在“向山要粮”“以粮为纲”的口号驱动下,瑶民大量开发水田,修筑梯田。集体化时期,在东寨大队队长李罗公的组织下,村民修建从老寨山上到山下的引水渠及排水沟以满足排灌需求。由于水利技术、劳动投入及化肥农药使用的增加,水田的产量有所提高,种植水稻成为瑶民重要的生计来源之一。同时,勤劳的东寨人仍坚持林粮间作(34)林粮间作是当地常见的耕作方法。土地轮耕三年后,肥力减弱。在冬季时又在另一面山耕作,开春锄种。瑶民用镰刀和锄头挖去树木和草根,烧做肥料后,翻松泥土,挖出一个个小坑分穴种上玉米、番薯或黄豆等作物。的模式,他们几乎在所有能耕作的山地都种上粮食作物。据与东寨依山相隔的西寨村民房四贵回忆,他年幼时到访东寨亲戚家,总能收到不少番薯、玉米等杂粮。东寨村民们也常谈起1960年代末的故事,当时他们将一担一担的玉米和番薯抬下山,支援周边的汉族村寨,深化了民族间的情谊。
20世纪80年代末,由于村中的年轻瑶民(15至40岁)外出求学与务工,劳动力流失的同时家庭的口粮压力逐渐减少。近些年,即使部分东寨村民选择返乡生活,也大多聚集在县城,从事非农业劳动。因此,不少留守东寨的村民抛弃了耗费劳动的林粮间作的耕作方式,而改为在山地上全面种植杉树,以及就近在屋前屋后的田地上种植水稻,以减少劳动的投入。衫树苗栽下后在三年内要定期除草打理,此外便无需付出其他的人力。杉树经过约15年到20年的生长后可砍伐,一次性大片砍伐杉树的收入比较可观,一立方约800元。瑶民视其为保管财富的“银行”。当下的杉树林基本都是各家各户的财产,村中常发生林地归属的纠纷。东寨瑶民在市场经济的引导下主动地将森林与市场相关联,人与山林的关系逐渐世俗化,山林的经济价值凸显。如村民唐芯妮所言:“家里的山前几年已经种了树,这几年除草施肥后可以不用打理了,等儿子要结婚时卖了,就有一笔收入。”(35)访谈对象:唐芯妮;访谈人:陈岱娜;访谈时间:2018年4月4日;访谈地点:东寨大风村。山林景观转变的背后带动的是社会关系的变化。蒂姆·英戈尔德(Tim Ingold)曾言:“人作为有机体的存在者,存在于人类和非人类的多种生物居住的世界之中。因此,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人之间那些被视为社会的关系,其实是一系列的环境关系。”(36)Tim Ingold, The Perception of the Environment: Essays on Livelihood, Dwelling and Skill.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pp.4-5.在生计方式转变的影响下,年轻一辈的瑶民已少有林粮耕作的经验,更缺乏进山采集的体验,导致大部分年轻瑶民难以理解山林背后的意涵。山林的意义逐渐地世俗化,成为家庭财富的一种象征。
生计方式的改变动摇了瑶民与山林的关系,也冲击了耍歌堂的信仰基础。学者多认为大庙的存在与祖先崇拜密切相关,虽然大庙中有地域性的“鬼”(37)在瑶民的观念中,人在生前都有“魂”,人死亡后,灵魂离开人的身体成为“鬼”,在瑶语中的词是[mian24]。因此,在瑶民看来,“仙”“神”“鬼”之间没有严格的区别,无论是自家的祖先或者是陌生人都包括其中。参见李筱文:《从“神灵意识”看排瑶的早期宗教》,广东省民族宗教研究院、中山大学人类学系等编:《排瑶研究论文选集》,广东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88-294页。,但瑶民将其视为共同祖先。(38)李筱文:《“耍歌堂”与祖先崇拜》,《新亚学术集刊》1994年第12期;许文清:《瑶族耍歌堂与连南排瑶文化》,广西瑶学会编:《瑶学研究》,广西民族出版社,1993年,第321-327页。在笔者看来,上述说法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大庙的地域性信仰。宏永就(Wang Wing-Chou)在1937年的调查中提及大庙中最大的神像为身骑公牛的“loh gon”(39)Wing-Chou Wang, “Yao Religion and Education”, Lingnan Science Journal, vol.18, no.3 (June 1939), pp.397.。结合笔者在村庄走访中所得,“loh gon”可能是当地瑶民崇拜的“罗公”。不少对大庙木像稍有记忆的老人家都提到了高大的“罗公”。据传,定居东寨后的瑶民本平安无事,生活舒适。可在几年后,村中出了一位男子,高大英勇却生性风流,他喜欢上附近城中的一位汉人女子,常流连在外。一日,他骑马回村,不幸在村口山坡上的石洞边摔马身亡。事后,东寨开始出现各种不祥的事件,接二连三有人去世,家家户户皆有坏事发生。在村民们看来,各种不幸皆因死亡男子的游魂作祟而起,故决定为其雕像,供奉在大庙中,并尊称为“罗公”,以求安宁。在大庙中,除罗公外,还供奉了不少因意外而身亡的恶鬼,如龙十九公、平王公、又天仙公等。立庙供奉恶鬼的目的是为了安抚灵魂,维护村寨共同的安宁,超越了一般的血缘与亲缘关系,与地缘相关。大庙作为老排的中心,是村寨公共祭祀的所在地。在传统耍歌堂中,有一个重要的游神环节,即是以大庙为中心,抬着大庙中的各个庙公,围绕老排走一圈,最终汇聚在歌堂坪活动。村民通过绕村寨游神的活动,以求村寨平安。1958年,东寨大庙在政治运动中被拆除,庙中的木神像被一把火烧得精光。据说,当日大庙对开的山里出现了“鬼火”。李石头公认为,“鬼火”的移动象征着“鬼”随着大火一同消失了。耍歌堂等仪式活动被视为是浪费钱财,致使瑶民贫穷的原因。而且耍歌堂的节日意义也被改变,从一个封建迷信活动变成庆祝丰收的节日活动。政府要求停止大型的庆祝活动且瑶民需要继续出工。(40)参见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广东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广东省瑶族社会历史情况》,1963年,第24页。由此可见,耍歌堂与大庙的关系逐渐被淡化。
耍歌堂成为国家级代表性非遗后,在地方文化局的支持下,东寨村委会重建了大庙。据负责大庙造像的时任村支书李二莎说,因为经费不足,大庙中原有的36个神像中只有“盘古王公”“盘古王婆”“盘古王嫂”“李海公”和“法真三郎”进行了塑像。新神像的人物面部肖像刻画清晰,与传统时期的木像不同。这是因为当地缺少会制作木像的工匠,李二莎唯有拿着自己和先生身着盛装的照片给连州的汉族工匠参照,打造新的神像。当下的大庙中不见身骑公牛的罗公。盘古王公夫妇作为最大的神像竖立在大庙中间。由此可以看出,村中政治精英在选择造像时,主推的是较有辨别度、知名度的瑶族祖先,而非地域性的罗公。这可能与1980年代瑶族各支系精英的频繁交流有关。通过交流,各地神的形象逐渐发生了融合。东寨的排瑶认盘古王为祖先,在祖先称谓上与广西的盘瑶、山子瑶等地称盘王有异,但这不妨碍民族精英们以瑶族始祖为纽带,一同打造文化交流活动。1984年,湘粤桂三省八个瑶族自治县共同商议,定于农历十月十六日举行纪念盘王的“盘王节”活动。东寨所在的县,即是上述八个瑶族县之一,因此在官方的宣传中耍歌堂常与盘王节同时出现。
重建后的大庙在村民生活中的重要性不如以往。2009年,东寨村委会曾以山顶的大庙为起点,举行耍歌堂活动。因为神像沉重,不易搬动,后来该村便再没有以大庙作为耍歌堂的起点。2016年的一场洪水冲垮了大庙,长达半年都无人问津,甚至倒塌的柱子都压到了神像身上。李四贵说起此事时指责村委会不作为,任由大庙坍塌而坐视不管。但村委会委员李好妹解释说是因为拥有大庙土地使用权的瑶民希望提高租金而一直协商未果。有村民将神像移到旁边的一个临时的木棚中祭拜。经过长达两年多的协商,大庙终于在2018年底得以重建。先生公们择吉日将神像请入庙中。但是,大庙“进伙”之日后,瑶民并不在庙中庆祝各种岁时节日,而是另选山脚的空屋作为举办活动的临时地点。再者,时下的耍歌堂出歌堂的路线常因观赏性的需要而变动。
重建大庙难以扭转瑶民的地域信仰转变的事实。大庙在精神上并未完全回归瑶民的生活,正是因为它所承载的地域性信仰几近消失,大庙重建,而神鬼不在。在瑶民生计分化后造成的人地关系转变影响下,有部分瑶民已经不再认可大庙所承担的庇佑地域性共同体的作用,东寨地域性的精神共同体已逐渐解体。同时,耍歌堂所蕴含的祖先崇拜可通过家族内部、乃至家庭内部的祭祀得以完成。
四、搬迁下山、分村而居与非遗保护
传统时期,东寨作为一个集体,共同举办耍歌堂活动。在瑶民生计、精神上与山林的关系逐渐疏远的同时,他们的“住”也远离了大山。老排本分为三大片:大沖,大昂和大行。1970至1980年代,东寨的各生产队为解决水源及耕作的问题,开始大规模地移民下山,就近在自己生产队所属的平地选择合适的搬迁点。第一批搬迁的瑶民居住在老排北部的大冲片,他们翻山搬往一个山坑,在耕作的田地附近聚居形成横青村。此后,居住在老排底部的大行片村民因为远离水源,饮水困难而自发搬迁,聚集在山下的一处靠近水源的小山坡,最终形成水景村。此后,在当地政府的统一规划搬迁下,瑶民在田垌处又形成了大风村和大北村两个自然村。但是,老排上仍有部分瑶民因经济条件差或是老人家生活习惯等原因而留守。在东寨村委会中,每个自然村有自己的村民代表。行政村的工作常以自然村为单位分配。在村委会委员李好妹看来,自然村的形成以生产队为基础,同时居住的瑶民大多有亲属关系,因此以自然村为单位推进工作阻力较小。自然村内部的运作良好。
从另一方面看,自然村之间存在一定的区隔。2018年横青村的村民自发为旅游开发而努力的时候,其他自然村的村民大多不关心横青村的事宜而持观望的态度。每年春节是东寨最热闹的时刻,其中一个亮点是始于2005年的瑶寨新春晚会(因在村中举行,简称村晚)。2018年的春节,东寨村委会资助东寨景区在村小学举办了春节晚会,同时老排、横青村、大景村三个自然村也由东寨的大学生自发以时下火热的街舞、健身操等形式搭配传统长鼓舞,自编、自导、自演了各自的村晚。引人深思的是为何同是东寨人,却要分散举行村晚?其中固然有地理因素的限制,上述三个自然村距离东寨村小学大概走路需时20分钟至60分钟。更重要的是,瑶民搬迁下山后,在新的聚落中形成了新的共同体,与东寨整体的联系被削弱了。在生计方式分化且又分地而居的影响下,民间举办文化活动的热情仅限于自然村内部。正如在大景村举办村晚的李玲说:“村里不少老人家,夜里走路去小学也不方便,反正我们村也有好多爱好歌舞的人,为何不能自己举办一个?景区那些大家都看过很多次了,没新意。”(41)访谈对象:李玲;访谈人:陈岱娜;访谈时间:2018年2月9日;访谈地点:东寨老排。李玲的话语中吐露出一种对自然村的自豪感。此外,她还提到为何不能整个行政村合作举办村晚的缘由:不同自然村之间的组织者有代际的差异,年轻一辈的大学生并不愿意遵循李信宁所代表的老一辈文化精英的安排,想要表达自己的喜好与对歌舞的理解,掌握阐释瑶族文化的话语权与表演的主导权。可见,代际差异也造成了合作的障碍。东寨的村晚变成以自然村为单位,各自举办的局面。由此可见,时下东寨集体行动的最佳单位是自然村,然而举办耍歌堂却不是一个自然村能够独自完成的事情。从东寨整体看,时下仍缺乏能联结自然村的自发地组织耍歌堂的社会组织基础。
五、结 论
在东寨耍歌堂的非遗保护过程中,不同主体的态度差异甚大,社区内部出现了较严重的分化。究其根由,乃是因为东寨作为一个有机联系的社区,在社会变迁中逐渐地分化了。由于生计方式的转变,导致地域性共同体所赖以为继的地域性信仰逐渐消散,同时搬迁下山的人聚在一起,形成了新的自然村。虽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社区参与作为非遗保护的一项重要的基本原则,重视社区参与也成为各缔约国的政府、专家学者与群众的共识,但是,不同地方的社区的状态会影响社区中不同主体的参与方式与互动模式。因此,社区参与并不是一个无需解释即可解决权威化遗产话语的方法。
安德明指出,由于“社区”自身条件限制等因素,政府的主导地位难以撼动,保证“社区参与”的责任在于政府。政府应以“文化对话”的态度,作为“文化协调者”平等地参与到保护工作中,达成一种交互协作的关系,而非强势干预。(42)参见安德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社区:涵义、多样性及其与政府力量的关系》,《西北民族研究》2016年第4期。这种观点将调整政府的姿态视为推动“社区参与”的关键。但是,笔者认为政府的态度也可能会影响到它参与协调的过程,譬如它因某种立场而支持社区中某一方,导致社区力量失衡,而可能引发更多的争议。在东寨的个案中,可见在国家权力支持下,非遗保护进入乡村中时所引发的资源重新配置引起了社区中力量的波动,因而引发矛盾与冲突。文化精英李信宁与非遗传承人称号之间微妙的关系反而成为其推广耍歌堂传承的一个障碍。在实践中“社区参与”成了一个标签化的词语,在社会中制造出主流群体与次群体的区分,导致社区内部出现争端与混乱。(43)Emma Waterton and Laurajane Smith, “The Recognition and Misrecognition of Community Heritag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ritage Studies, vol.16, no.1-2 (Feb 2010), pp.4-15.即便是社区中的不少个体参与了非遗保护,并不意味着非遗保护中实现了社区参与。非遗保护以文化为核心,但文化一直处在变化之中。非遗是对过去的一种新理解(44)Marilena Alivizatou, “Contextualising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 Heritage Studies and Museolog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angible Heritage, vol.3 (2008), pp, 44-54.,更重要的是为当下制造意义并指向未来,同时它也是一种参与和交流的行为。(45)David Lowenthal, “The Heritage Crusade and its Contradictions,” in M. Page and R. Mason (eds.), Giving Presevation a History: Histories of Historic Preserv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4, pp.12-44.部分精英的想法已脱离社会现实而难以成为社区的共识。因此,非遗的社区参与需要回归每个社区去理解文化和社会的转变方有可能取得成效。
社区并不是一个理所当然的共同体,也不是指人群在同一地理范围中生活就可形成一个社区。有学者已经指出,在非遗的动态传承中,社区具有非均质性,但社区中的人们可通过互有进退的协商和妥协,达成一个非遗项目内部成员共同接受的新传统。(46)参见安德明:《非物质文化遗产社区的能动性与非均质性——以街亭村民间信仰重建过程中村民互动为例》,《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6期。在传统的社会结构解体以及既有的联结方式消失的情况下,社区内部凝聚力的关键在于能建立新的以互惠为基础的联结方式。相反,若社区中不同的利益相关者之间无有效的联结,利益纷争则会让非遗保护陷入内耗之中,进一步加速社区内部的瓦解,导致社区参与陷入困境,最终非遗保护只能依靠地方政府的支持而维持表面上的红火。
最后,社区参与除了应在社会层面上重塑联结方式外,更为重要的是找到激发集体行动的核心文化。时下,耍歌堂的一个重要的社会价值——地域信仰,在社会的政治运动、瑶民生计方式转变及搬迁下山的作用下已经逐渐消散。因此,耍歌堂实际上难以再发挥凝聚村寨的作用。相反,形式更为灵活的乡村“村晚”可能成为联结村民的核心文化,从而引发新的公共行动,以实现社区参与。这正如牛光夏所提及的那样:“实现非遗保护的社区参与,是以提高人们尤其是年轻一代对非遗及其保护的重要意义的认识为前提的。”(47)牛光夏:《“非遗后时代”传统民俗的生存语境与整合传播——基于泰山东岳庙会的考察》,《民俗研究》2020年第2期。由此可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必须与时俱进,正视社会分化,重视社区利益的协调机制建设。